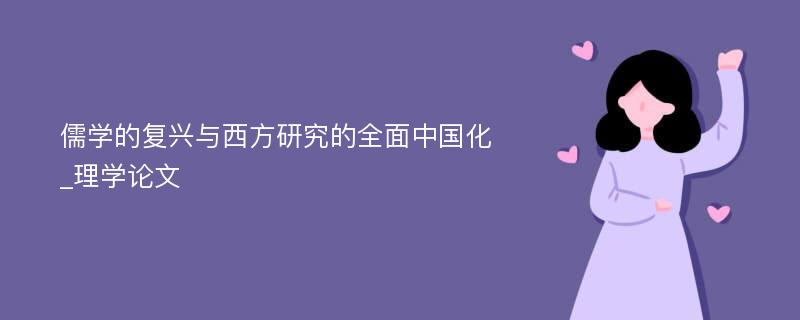
儒学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儒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2)06-0010-04
近些年来,“儒学复兴”的话题广受关注,影响很大。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一现象,或者换句话说,儒学的复兴是否已经到来?儒学的复兴还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儒学才能真正复兴?等等,这些疑问很值得梳理。本文拟就此谈些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如何理解近代儒学的衰落
为什么近些年来会出现“儒学复兴”的话题?原因固然多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儒学在近代的衰落。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儒学的这次衰落作一考察。
近代儒学的衰落,表现在方方面面,本文无意一一赘述,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近代以来,在与以近代科技文明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发生关系时,儒学屡处下风,几乎每一次交手都以失败而告终,可谓“一败涂地,史无前例”。
说其“史无前例”,是相对于儒学发展的历史而言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学也曾经遭遇过冷遇,但还很难用“衰落”两个字来形容。比如从魏晋时期到隋唐时期,儒学虽然一直居于正统地位,但门庭冷落,收拾不住,一流的学者很少有儒学家。魏晋时期,玄学是思想界的主流,一流的学者多为玄学家。隋唐时期,佛学独居显学的位置,一流的学者多是和尚(外国宗教哲学专家)。韩愈虽被后人誉为有“道济天下之溺”(苏轼语)之功,但就其哲学思想的深度言,与这一时期的高僧大德相去甚远。尽管如此,儒学也还没有衰落,其所遭逢的不过是冷遇而已。近代则不然,儒学值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捉襟见肘,无所适从,可谓每下愈况。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谈到儒学,人们或许马上会想到孔子,想到先秦。其实,近代儒学的衰落,乃是就儒学发展到宋代形成的一种理论形态——理学而言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谈到的儒学的衰落,是理学的衰落。“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高擎“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但具体批判的内容则是“吃人的理教”、“假道学”等等,这些都是针对理学而言的。所以今天所谓的近代儒学的衰落,是理学的衰落,是理学这种理论形态在近代与西方交手时处于下风。
那么,为什么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学,在近代会有这样的命运呢?原因也是方方面面,例如,儒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整体社会结构——在近代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这还只是外因。就理学内部而言,可以说其衰落是由于理学的理论思维到清代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已故著名易学家、哲学家朱伯崑先生在其四卷本《易学哲学史》中,在谈到清代易学时指出,“一般说来,他们的易说,缺乏探讨哲学问题的兴趣,在理论思维方面很少建树”[1]4,“因此,清代的易学及其哲学,就其理论思维发展的总的趋势说,可以说是由高峰走向低坡”[1]2。朱先生的这一结论,可以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清代儒学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形态,而只有汉学的复兴和汉学、宋学之争。
二、历史上儒学复兴的条件
汉武帝“罢黜百家”(《汉书·武帝纪赞》),儒学被定于一尊,一直到清代,儒学在传统学术的发展中始终居于正统的地位。但如前所述,在中国历史上,儒学虽长期居于正统地位,但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萎靡不振。不过,由于儒学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加之以《周易》为核心的儒家原典所具有的开放性,所以条件一旦成熟,以儒学的价值取向为灵魂的新的理论形态便会应运而生。
所谓“条件”,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从学理上说,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则是新的文化资源。如汉代儒学的复兴。汉代儒学是不同于先秦儒学的一种儒学新形态。其仍是儒学,是由于它彰显了儒家的核心价值理念;其所以新,是由于支持这一核心价值理念的是一套不同于或为先秦儒学所无的宇宙观,这套宇宙观来自黄老、阴阳五行家等。当然还吸收了其他诸家如法家、墨家等的思想。像董仲舒,特别喜欢讲五行生克,甚至把仁义礼智信和五行对应起来,用阴阳五行讲宇宙人生。被立为官学的孟熹、京房等人的易学,还大量吸收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以阴阳五行为间架的哲学体系。这些都不是先秦儒学的旧面目,而是汉代儒学的新面孔。这种新面孔,无疑是以先秦各家思想为文化资源,为我所用,打造出来的。
又如宋明理学。谈到宋明理学,大家都很清楚它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物,这本身就意味着理学与三家的文化资源都有密切的关系。儒学自汉代之后长期处于疲软的状态,宋代三教合流,为儒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化资源,儒学借助这些资源丰富自己,形成了复兴的一个很好的条件。如宋代儒者,多有“泛滥出入”的经历[2]59,像张载:“访诸释老诸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求之六经。”[3]381像程颢,程颐在所作《明道先生行状》中指出:“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4]638近现代以来,有哪位学者早年留过洋,回国后研究国学,人们便习惯于冠以美名:“学贯中西”。二程兄弟“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大半生都在儒学之外探寻摸索,也算是“学贯儒释道”吧!这表明理学的复兴是以老释为代表的诸家思想为文化资源的。
在程颐的哲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命题“体用一源,显微无间”[4]582,这是他在注释《周易》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但这个观点又与佛教《华严经》有关。唐代僧人澄观说过这样一段话:“体外无用,用即是体,用外无体,体即是用。”(《华严经疏》卷二十三)程颐的命题基本上就是这一个命题的转化。佛教华严宗特别重视理事关系,“理”之成为理学的核心话语,应该是与华严宗的影响分不开的。而理学中关于心性问题的讨论,与佛教的思想也难脱干系。他们是把这些作为资源,来丰富、建构自己的学说的。
三、历史上儒学复兴的途径
资源固然重要,但仅有资源尚不能产生出新的理论体系。考诸儒学发展的历史,儒学的复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途径,就是回归和开发原典,换句话说,就是经典诠释。
众所周知,儒家在汉武帝时被定于一尊。而定于一尊实际上是与经典的诠释联系在一起的。经过战国及秦汉之际的思想发展,汉武帝独尊五经,是回归原典;经学家们透过原典的解释,融会百家思想,回应现实问题,形成汉代儒学的新面貌,是经典的诠释。
宋代儒学的复兴也是如此。而尤其值得注意者,宋儒不但回归原典,还开发了新的经典——“四书”。每一部经书本身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并不是每一部经书在任何时候都能回答任何问题,所以宋儒在回归原典的过程中,又重新开发新的经典,“四书”的光辉于兹发显。像周敦颐,其《太极图说》是在诠释《周易》的过程中建立其宇宙论体系的;而其《通书》则是在“四书”尤其是《中庸》与《易传》互诠的过程中阐发其哲学、伦理思想。像朱熹,其注“四书”,有对文本本义的钩沉,更有对文本新意的阐发。这些“新”的东西便来自历史和现实的交汇,而最经典的诠释就是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做文章。所以说理学的产生也是以回归原典为途径的。
其实,如果再展开一点说,魏晋玄学理论的形成及发展也与回归原典分不开。《易》、《老》、《庄》“三玄”便是玄学家诠释的文本,同时也是玄学融会新知的理论依据。
在此,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唐初李世民命孔颖达等人撰《五经正义》,是不是回归原典?我认为《五经正义》虽然对于保存文献,总结经学研究成果不无贡献,但作为一部“部颁教材”①,其与回归经典还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可以说,国家部颁形式本身,一定程度上拒斥了多元诠释的可能性,不但不能“回归”,反而还影响了其他人的“回归”。任何理论,一旦成为标准,便终结了其诠释的空间。所以说,唐代开国之初颁的《五经正义》,还缺乏回归原典的气魄,也不具备这样一种魅力,因而也没有开出唐代儒学的新面孔。但不容否认,《五经正义》,对于宋代儒学的复兴确实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研究宋代的儒学,绝对绕不开《五经正义》;研究宋代的理学,也离不开《五经正义》。虽然它本身并没有开新,但为后来的开新提供了资源。
总之,儒学复兴的条件是新的思想文化资源,途径是回归、开发原典。
四、儒学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
回过头来再看当代儒学复兴的问题。
当代儒学的复兴,面临的问题非常之多。但如果“以人为本”来考虑这些问题,也仍有法则可循。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56虽然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还可以再研究,但“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这句话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儒学复兴所面临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在近代中国,人之存在于其中的诸多社会关系,即构成人之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在发生着变化,儒学必须适应这个变化。
而在这个变化中,有两样东西最值得关注,那就是“五四”学人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前者指向社会政治层面,后者指向知识层面。就前者说,虽然对“民主”的理解仍有分歧,但今天的中国在社会的政治层面,是把“民主”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之一的。就后者说,“科学”在当今中国已是被全盘接受了。这两点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现代新儒家一直希望从传统儒学中开出科学与民主②,也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这两个问题的绝对不可回避性。
儒学要复兴,首先不能与以科学与民主为诉求的近现代价值理念发生矛盾。我们没必要像许多好心的保守主义者那样,挖空心思要从儒学中开出科学与民主,那也是不可能的。只要保证儒学与科学、民主的价值理念不背道而驰,儒学的复兴就有希望。
众所周知,科学与民主的理念来自西方,这就意味着儒学必须勇敢地面对西方文化。如何面对?有三条路,其中两条路是走不通的:完全拒斥,则会失却自身的合理性;完全接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也将面临挑战。第三条路是“综合创新”。如何“综合创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综合创新”需要新的文化资源的意义上说,有必要提出“西学的充分中国化”这一命题,它不同于“全盘西化”,也不同于“民族文化本位”,却可以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丰富的资源。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成功的“西学的充分中国化”,那就是佛教。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到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形成了许多中国化的宗派,像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禅宗等。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是不可估量的,仅以日常语言里一画与二画中的部分成语为例:一心不乱,一报还一报,一丝不挂,一厢情愿,一刹那,一段清香,十八罗汉,十八层地狱,十恶不赦,八字没一撇,等等,都来自佛教。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变成佛教国家,而是佛教彻底中国化了,并为宋儒复兴儒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佛教中国化,是西学充分中国化的经典实例。有鉴于此,儒学的当代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的关系很值得思考。
近代以来,由于“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语),“西学的充分中国化”始终未能充分展开,对西学的学习始终没有深入进去(今天随着中国的崛起,西学又有遭到拒斥之嫌,令儒学复兴的前景蒙上阴影)。因此,学习西方,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西学充分中国化”的途径,将是儒学复兴的根本任务之一。
五、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儒学复兴需要资源——充分中国化的西学。但仅有资源还不能复兴。根据历史的经验,儒学复兴的途径还应该是“回归原典”。“原典”之所以为“原典”,乃由于它是一个民族之最基本存在形式的最经典的诠释文本。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原典,每一个民族的原典都是对那个民族最基本存在形式的最经典的说明与理解。正因为原典的这样一些特性,所以它才具有经典的意义。“回归”就是透过对这些原典的新诠释,重新理解历史与现实之交会的当下存在状态。
首先,“回归”意味着已有的理解方式已经不能完全表达人们对当下存在形式的理解,需要透过原典的诠释空间作出新的理解。如前所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56这个“总和”具有极强的历史性,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因此,反映、理解这一“总和”的原典也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实现自身的超越。
其次,“回归”是以对当下存在形式的反思为出发点的,但“回归”又是在对已有“社会关系的总和”之反思、体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两者的结合就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第三,“回归”以关照当下存在形式为目的。“回归原典”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关照当下的存在形式。当下的存在形式是原典里所没有的,是需要通过对“原典”的新解释来包容的。换句话说,这种新解释是指向当下存在形式的合理性问题的。所以,“回归”即创新,回归本身具有创造性。
第四,“回归”落实民族性,关照现实性,回归即诠释。所谓关照现实性,面向之一就是“西学的充分中国化”。儒学的复兴不只表现在儒学之受到重视,关键是它能解释现实,同时又能彰显固有的价值取向。儒学只有满足时代的需要,才能成为时代的需要,而它满足时代的途径就是诠释。
本文的开始曾指出近年来“儒学复兴”的话题广受关注,这是否意味着儒学已经开始复兴?答案是否定的。儒学的复兴不是喊几句口号、树几尊孔子像就能实现的。目前儒学复兴的条件还远未成熟——西学的资源未受到重视,当下存在形式的建构还在探索阶段。所以,儒学复兴并没有开始。
但是,儒学复兴的曙光已经出现,表现之一是“西学”解释不了我们当下的存在形式;表现之二是固有的中学(儒学)也解释不了我们当下的存在形式。儒学应努力在实现这种解释的过程中综合创新,挺立自己。可以说机会已摆在面前,只要抓住它,与时偕行,而不是画地为牢,夜郎自大,儒学的复兴就有希望。
注释:
①按:《五经正义》系唐代颁布的一部官书,唐太宗贞观十六年编成,唐高宗永徽四年颁行。士人诵习,全据《正义》,否则被视为异端邪说。
②如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即主要因此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