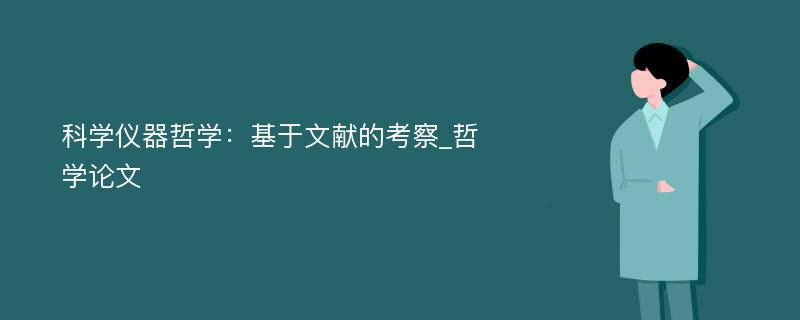
科学仪器哲学:基于文献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哲学论文,科学仪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5)11-0032-06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已经陷入相对主义不能自拔,科学哲学究竟向何处去?笔者所在团队长期在美国、澳洲、欧洲等学术机构从事科学思想特别是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研究,收集了一批与科学仪器相关的文献资料,既包括海外珍本图书,如“达·芬奇的哲学笔记”和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的“从柏拉图到哥白尼的宇宙论系统”(Le Système du Monde:Histoire des Doctrines Cosmologiques de Platon à Copernic)等,也包括一些被广为引证的专著,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等,还有近几十年来出现的一批文献如拉图尔的《实验室生活》等。从这些文献中,笔者了解到科学仪器哲学的兴起,挖掘出了科学仪器哲学的历史演进图景,窥见了科学仪器哲学的发端和进展。 本文从文献的梳理入手,思考了有关科学仪器哲学研究的思想源起、理论背景等问题,概述了科学仪器哲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体认到科学仪器问题不仅是影响科学知识进展的关键性问题,而且也是影响深广的哲学问题。最终,得出科学仪器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从仪器角度来理解科学思想的结论。 二、关于科学仪器问题的思想史考察 科学仪器及其相关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其内涵与组成和科学知识一样经历了重大变革,可以说科学史是理论、实验、仪器三者互相促进的发展史,但是对科学仪器及其思想的研究却经历了颇为曲折的转变。 科学仪器与古代科学思想:从古希腊到科学革命时期,科学仪器多是作为简单的观测或者测量工具,基本没有进入思想史的研究视野,科学家或哲学家对科学仪器的描述多数还停留在“演示神奇现象、炫耀个人技能”的层面。不过也有一批拥有真知灼见的学者,如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之一R.培根在其《大著作》(Opus Majus)中提出了不少仪器相关的论述和大胆的猜测[1]12-28,35-42,指出仪器不仅是科学实验的工具,也是科学实验的研究对象。 科学仪器与近代科学革命:16世纪、17世纪涌现的科学仪器加速了近代科学的发轫,当时很多科学专著是以仪器命名或作为主要内容的,如伽利略的《星际信使》(Sidereus Nunciu)、波义耳的《怀疑派化学家》(The Sceptical Chemist)、惠更斯的《摆钟论》(Horologium Oscillatorium)等,描述了各类科学仪器的制作、使用及改进方案,其中很多仪器是由研究者亲手制作,成为经验主义者的有利论据。同时,科学仪器也对与科学分离不久的哲学起到了辐射作用,如F.培根在其代表作《新工具》(Novum Organum)一书中就已经意识到了纯粹感官经验的不足,尝试寻求科学仪器的帮助[2]76,86,92。但是作为科学主流思想的理性主义依然坚称仪器不具有理论意义,科学家和哲学家几乎都没有对科学仪器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进行论述。 科学仪器与现代科学哲学:虽然仪器在科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却逐渐淡出哲学家的视野。19世纪中期惠威尔出版了《归纳科学的历史》(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和《归纳科学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在实证主义的框架下给出了科学仪器的经典图像,多数科学哲学家转向对命题的研究。20世纪中期逻辑实证主义者更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理论优位的局限,出现了“文本偏向”(text bias)和“语义上行”(semantic ascent)的障碍。但是同时也有哲学家在科学的整体框架下讨论科学实验和仪器对于科学理论发展的作用。例如,法国科学哲学家巴什拉在其认识论著作《科学精神的形成》(La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中提到了理论、实验、仪器对科学精神形成所造成的障碍[3]25,对后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62年,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范式”概念应该包含有科学仪器的维度,暗示了仪器在科学革命中可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但是这一时期的哲学家都没有对理论、实验、仪器进行区分,只是将三者联系起来,认为仪器是科学理论或实验的附属品。 科学仪器与科学仪器哲学的发端:20世纪80年代后,哲学界开始重视对实验的研究,影响比较大的包括SSK微观实验室研究和新实验主义。SSK微观实验室研究注重于对实验室的活动做实地调查,考察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派;新实验主义打破了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传统,通过对科学实验的哲学研究,认为实验相比理论更为基础和根本。代表人物及著作包括:拉图尔、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LaVie de Laboratoire);夏平、谢弗的《利维坦与空气泵》(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哈金的《表征和干预》(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等。但是SSK微观实验室研究和新实验主义的主体部分仍然是实验研究,没有独立考察科学仪器在科学史以及科学哲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纵观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史,我们不难发现科学仪器在科学中的作用和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哲学家对科学仪器的态度从早期用科学和哲学的统一视角对待仪器,到重理论而轻仪器,再到近年来重新在科学整体框架下审视仪器,仪器正在逐渐进入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并将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三、科学仪器哲学的兴起 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和确立必须具备几个基本要件,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察,确认科学仪器哲学已经正式进入科学哲学家的视野,成为科学哲学的范畴之一,但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研究领域的出现:随着科学哲学家对实验研究的推进,科学仪器逐渐占据了重要领域,科学仪器哲学成为科学哲学新兴的分支之一,科学史界也展开了对仪器定义和分类的研究,如特纳认为“数学仪器”比“科学仪器”的名称更为合适,并对欧洲15至19世纪的仪器进行分类;海尔布朗对18世纪的仪器进行分类;哈克曼区分了“消极的”仪器和“积极的”仪器。更早关于仪器的著作还有威廉·莱西(William Lacey)撰写的《仪器教程》(A Course of Instruction in Instrumental 1924),贝尔德认为这是最早一本明确聚焦于仪器的教科书。普赖斯在20世纪80年代正式提出科学仪器哲学这一术语,认为“It is unfortunate that so many historians of science and virtually all of the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are born-again theoreticians instead of bench scientists”[8]。 研究体制的确立:“科学仪器哲学”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IUHPS)所属的“科学仪器委员会”(Scientific Instrument Commission)中进行,该委员会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致力于在科学史框架下对科学仪器的历史进行学术研究,保存和收藏文献文件,并在更广泛的科学史领域使用。该委员会每年召开年度研讨会,会对不同的主题进行研讨,研讨会的备忘录、通讯录、书目数据库以及会议论文均会出版。此外该委员会还支持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Scientific Instruments on Display(2014); Cabinets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2013)等。 20世纪末,已经有一些科学哲学专著开始重新审视科学仪器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如科学史家约翰·A.舒斯特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中专辟一章[9]259-280,以伽利略的望远镜为例讨论“证实理论的事实是仪器发现的吗?”同时在一些科学哲学类杂志中陆续收录了一些专门研究科学仪器的文章,如《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s)杂志收录的The Divided Circle:A History of Instruments for Astronomy,Navigation and Surveying(1989)、Instrumental Unification:Optical Apparatus in the Unification of Dispersion and Selective Absorption(1999)等。2009年第4期该杂志推出了以“科学仪器”为主题的专刊,收录了包括Between the Beagle and the Barnacle:Darwin’s Microscopy,1837-1854、On Scientific Instruments等一批直接论述科学仪器的哲学文章,预示着以科学仪器为结合点的HPS研究的兴起。其他杂志如《英国科学哲学期刊》(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和《科学年鉴》(Annals of Science)等近年也有不少相关文章发表。 国内目前专注于科学仪器研究的学者包括郭贵春(工具实在论)、陈凡(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吴彤(实践优位问题)、石诚(HPS视角下的科学仪器)等。笔者也通过中国知网统计了一些国内哲学类期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尚未有专门的期刊发表科学仪器哲学研究的文章,而哲学类期刊发表论文又多集中于技术层面,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科学仪器的哲学”的体制虽然已经确立,却尚未成熟,因此还需继续努力。 标志性学术成果:目前在科学仪器哲学领域活跃的团队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哲学团队、SSK的爱丁堡学派和巴黎学派、技术哲学的“荷兰学派”等,代表人物有彼得·盖里森、D.古德曼、D.贝尔德、丹尼尔·洛斯巴特等。研究维度一方面是在科学实践哲学的框架下,重点突出仪器维度,如盖里森的思想;另一方面反对传统认识论并建立新的认识论,如贝尔德的思想。 拥有着物理学和科学史两个博士学位的彼得·盖里森,是哈佛大学物理教授和科学史学家、斯坦福学派的成员,也是早期新实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著作包括《图像和逻辑》(Image and Logic:A Material Culture of Microphysics 1997)、《客观性》(Objectivity 2007)等。盖里森认为传统哲学(不论是实证主义还是反实证主义)都是基于“统一科学”的目的而将科学还原为理论和实验,但是这种还原论并不能对科学进行合理的说明,需要引入新的维度——仪器。理论过程、实验操作、仪器制造这三个环节相互独立,但是也可以相互转化、相互契合,三者之间存在“交易区”。在《图像和逻辑》一书中盖里森说明了不同时期(实证主义时期、反实证主义时期、互嵌时期)的科学图景分期图[10]785,794,799,可以说是盖里森首次将科学仪器提升到与理论和实验同等地位,他批判了库恩和皮克林对于仪器的定位,在科学实践哲学的框架下重点突出仪器的维度,继哈金之后提出了“仪器有自己的生命”的论断。同时开始关注科学实验和科学仪器的客观性,在《客观性》一书的第三章中,盖里森提及“Mechanized or highly proceduralized science initially seems incompatible with moralized science,but in fact the two were closely related”[11]122。通过分析在科学和艺术中使用的各种成像技术和仪器,他对“mechanical”一词的具体含义及其演变作出了具体的说明。 作为南卡罗来纳州大学哲学教授的D.贝尔德,和盖里森还同为实践中的科学哲学学会(Society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Practice)的成员,他的著作《器物知识》(Thing knowledge 2004)获得了德国化学学会的保罗·邦奇奖,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贝尔德在该书的序言中就提出了“it is not well known ‘that the history of physical science is largely the history of instruments and their intelligent use’”[12]xv。针对西方哲学家关注科学理论、轻视器物知识的传统,贝尔德认为科学仪器同样可以表达知识,甚至仪器本身就承载着知识。作者首先指明对科学仪器进行准确界定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他仍然根据认识论的不同将仪器分为三类[12]5,这种分类并不是哲学上详尽而明确的功能学分类,而是对于不同类别的仪器采用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即模型式仪器作为表征性事物(Representing Things);装置式仪器所蕴含的操作性知识(Working Knowledge);测量式仪器所蕴含的包容性知识(Encapsulating Knowledge)。贝尔德用翔实的史料和相关引用对十多项科学仪器进行了具体分析,不仅涉及科学仪器的产生、制作、使用、改进等过程,更引用了科学家对仪器及其思想的描述。贝尔德的结论是科学仪器本身包含的认识论是用纯粹语言无法描述的,仪器和理论一样都是科学的产物,仪器是科学知识的组成成分。 学界反响:关于仪器、实验和理论三者的相互关系,以及科学仪器在科学进展乃至哲学发展中作用,盖里森和贝尔德对此的阐述和思考引起学界强烈的反响。 一方面,盖里森认为是科学仪器驱动了科学革命,明确了仪器与理论、实验同样重要的哲学地位,呈现了科学发展的连续图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量子电动力学巨擘弗里曼·戴森将盖里森与库恩的学说并称为“两种科学革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关注到科学中的仪器维度,如洛斯巴特在《哲学仪器》(Philosophical Instruments 2007)中就指出“The topic of instrumental skill,pervasive in current research,demands its own principles,which are not reducible to traditional categories of empirical knowledge”[13]xiii。另一方面,盖里森的科学仪器史与科学仪器哲学研究开创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对于仪器研究的新局面,他提出的“交易区”理论挑战了传统科学家和哲学家企图统一科学的野心,指出科学是分立的和非统一的,在不同亚文化之间需要通过“交易区”达成局部协调。较之库恩的“范式”转换,“交易区”理论可以更微观地探索科学发现的过程和科学演进的过程。此后,科林、格曼等人分别从自身研究背景出发对“交易区”理论进行了分类、拓展、深化,从而使其应用范围远远超出科学内部亚文化的合作与交流。 贝尔德对科学仪器的考察方式和对知识来源的新见解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盖里森认为《器物知识》“uses instruments to do philosophy…it is a book that brings the laboratory to philosophers and philosophy into the laboratory”。HPS领域知名权威艾瑞克·塞里认为贝尔德将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从逻辑、理论模型和实验拓展到了科学仪器和设备,这是“即时”类的知识。贝尔德试图克服“文本偏向”和“语义上行”这两个障碍,对于他所论及的物质(即科学仪器)是知识负载的形式之一,科学史家也有一个说法:“与其说蒸汽机属于科学,不如说科学更属于蒸汽机。”从历史发展看,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良并没有明显地应用科学理论,却触发了关于熵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观念;唐·伊德也曾指出古代的光学发明推动了几个世纪的科学思想。 可见,科学仪器哲学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其研究领域和方向正在逐步完善,最终将成为科学哲学不可或缺的独立分支。 鉴于上述相关的文献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仪器也有自己的生命。在实践转向和认识论两大框架下,科学仪器哲学将为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 1.重新理解科学仪器 对于科学仪器的传统定义往往狭隘地将其理解为科学实践的工具,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机械工程卷中将其定义为“用以检出、测量、观察、计算各种物理量、物质成分、物性参数等的器具或设备”。传统哲学讨论科学仪器对科学发展的作用,引发了工具主义和实在主义之间的论战。但是从科学仪器自身出发,这两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观点,我们对仪器采取何种态度取决于以仪器的自身特性及其在科学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正如贝尔德在《“工程实在论”》一文中所承认的,即使在定义和说明单一的实在论要素时也不存在简单的答案[14],哈金也区分了理论实在论(realism about theories)和实体实在论(realism about entities)。所以我们既不能用统一的观点看待科学,也不能用统一的观点看待科学仪器,而应该在科学知识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仪器的地位和作用。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在科学和哲学的整体框架下重新对科学仪器进行定义,依笔者拙见科学仪器应该是用于科学实践、承载有科学知识的物质实体,同时科学仪器必须能够在科学理论框架内获得合理的解释。 2.重新理解科学思想(史) 在科学表征中,科学仪器是科学理论与科学实践、科学理念与器物文明、科学建制与社会互动的集中体现,科学仪器与科学理论、科学实验是科学进展的三个基本判据。可以说不理解科学仪器,就不能完整地理解科学思想,也不能全面地把握科学史。例如传统的科学观认定科学实验具有可重复性和确定性,但是在复现传统科学仪器的过程中,学者发现这种可重复性和确定性是被多种条件所制约的。典型的例子如焦耳的热功当量实验,即使后人复制出了当时的实验仪器却无法重复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应该质疑焦耳的实验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科学家在使用仪器时的技能和技巧已经成为日益为人所重视的“默会知识”[15],这正是理论实体的体现,充分说明了理论-实验-仪器三位一体的关系。传统的哲学家虽然在提及科学时将其区分为理论和实验两部分,但是涉及科学知识进展时往往仅指向理论,贝尔德却提出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不仅包括“say things about nature”,还包括“do things with nature”,人类认识的产物不仅包括科学理论,还包括科学实验甚至是科学仪器,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科学仪器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从科学仪器的角度来理解科学思想。从这个角度看,科学仪器不是外在的工具,而是科学思想的器物形态;科学思想不仅仅是科学理论及其实践活动,而且还是科学命题、科学仪器和科学活动范式的三位一体。 3.重新理解科学哲学 从科学仪器的角度重新审视科学哲学的观点,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科学哲学,梳理科学哲学史、科学史、科学仪器史这三者的关系。在于他人的通信中贝尔德明确指出:科学仪器哲学与科学仪器史密不可分,科学仪器哲学为科学仪器史提供概念结构,而科学仪器史为科学仪器哲学提供概念的内容和含义。1962年汉森指出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没有仪器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仪器哲学的仪器史是盲目的”这一论断。从上世纪后半叶起,包括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哈金在内的众多哲学家已经开始关注仪器在科学知识进展中的作用,我们应该将库恩的理念推进一步,可以将科学思想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理解为科学仪器的制作、改进和取代的过程,一部科学思想史可能就是科学仪器演化史。科学仪器甚至比科学语言更基本,科学哲学不仅仅是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还是科学语言与科学器物的统一。 总之,从哲学层面理解理论、实验和仪器之间的关系是我们重新理解科学、科学与哲学关系的重要一步,将仪器放入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将有助于我们关注科学中的文本知识和物质知识、工具知识和实体知识、理性知识和经验知识,科学仪器哲学将会凸显出科学仪器在理解科学并解决科学哲学问题中的主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