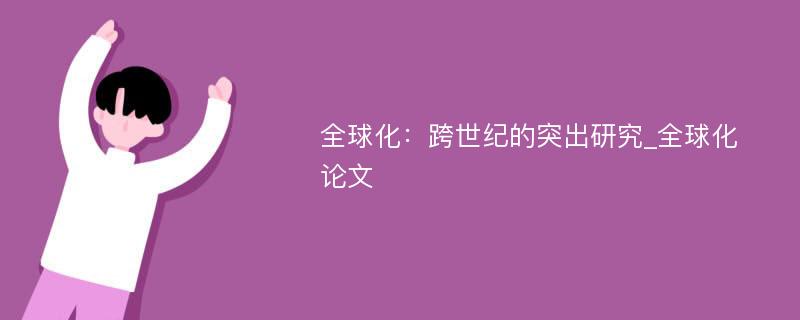
全球化——跨世纪的显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显学论文,跨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全球化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学术研究的跨世纪显学。自1999年以来,华人学术界围绕着全球化问题,也出现了可喜的争鸣局面。为了帮助华人学者及时跟踪英语世界的研究前沿,避免低水平的重复研究,本文试图对近年来的世界全球化研究作一简单的归纳和述评。
一、新左派:全球化等于新帝国主义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首先出现在60年代的法国和美国。到70年代,“全球化”已成为全世界各国的通用之词。(注:G.Modelski,Principl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Free Press,1972).)但至今有关它的精确定义和具体影响,仍然是见仁见智。大致而言,目前英文学术界围绕着全球化的定义、作用和功能出现了四大学派。
首先是新马克思主义派或新左派(Neo—Marxists and Neo—Left)。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S.Amin、A.Callinicos和S.Gill。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将全球化等同于帝国主义化、西化和中世纪主义。他们认为今日的全球化就是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注:A.Callinicos,et al.Marx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London:Bookmarks,1994).)。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两极分化,而国家和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注:S.Amin,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London:Zed Press,1997);A.Callinicos,et al.Marx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London:Bookmarks.1994); S.Gill,"Globalization,Market Civilization,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 Millennium,24 (1995).)
尤其是,新左派认为,目前的“政治全球化”是企图恢复古代的帝国系统,模糊国家和领土的概念,由一种文化和宗教(如罗马天主教)或一种政治制度(如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来统治一大区域,甚至全球国家。新左派认为,自古代以来,世界历史在帝国与反帝国,或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较量中,经历了五大历史时期。第一是发生在公元500—1500年期间的中世纪,可称第一次帝国时期或第一次全球化时期,它以神圣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为代表;第二是发生在1500—1800年期间的反帝国时期,也称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时代,它以欧洲国家脱离神圣罗马帝国为标志;第三是第二次帝国时代或第二次全球化时代(1800—1945年),以大英帝国和拿破仑帝国为代表,以地缘政治(geopolitics)为特征;第四是战后的1945—1970年,此乃第二次反帝国、反全球化时期,以民族独立(decoloniz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为特征;第五则是发生在世纪之交(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的第三次帝国时代或第三次全球化时期,以欧盟(EU)、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北美自由贸易组织(NAFTA)为代表,以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重新一统化(reterrito—rialization),以及地缘经济(geo—economy)为特征和趋势。(注:David Held,Anthony McGrew,David Goldblatt,and Jonathan Perraton,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33—137.)
对此,新左派认为,当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孕育了新兴的欧洲民族国家之后,帝国系统在欧洲开始瓦解。但自主之后的欧洲列强将这种帝国遗产移植到拉美、亚洲和非洲,直至二战之后,亚非拉国家开始回归当初的独立国家形态。如今,世纪末的全球化正在催生另一种形态的帝国体制。所不同的是,这次全球化不是以军事强制为先导,而是以市场和资本为杠杆,没有鲜血和暴力,一切似乎建立在市场规律的自愿原则之上。如果当初是通过战争打破主权界限和领土观念的话,那么今日全球化则是通过资本、信息和市场来冲击国家主权,促使国家和领土的界限再度淡化。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循环效应。另外,与19世纪的武力侵略、领土霸占不同的是,此次全球化的目的是夺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不是领土。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丢弃市场比丢弃领土更为悲惨,因为丢掉领土(如中国丢了香港)仍然可以再夺回来,领土是看得见的实体存在,而丢了市场,就一去不复返了。而且,目前的Internet就是一种“信息殖民主义”,WTO是市场帝国主义,IMF是金融帝国主义,联合国则是一种政治外交帝国主义,全体发展中国家再度成为西方帝国主义“臣民”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所以,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帝国主义、西方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体制的全球性扩散,也就是西化的全球化普及。(注:S.Amin,"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 (1996); L.Benton,"From the World Systems Perspective to InstitutionalWorld History:Culture and Economy in Global Histor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7 (1996).)
另外,新左派批判这次全球化是一种“新中世纪主义”(New Medievalism)的复兴。中世纪主义的本质是所有天主教国民不受一个主权国家的统治,每个国家必须在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绝对权威下,分享主权,其核心是表明国家主权是可以重叠的、效忠是可以多重的(overlapping authority and multiple loyalties)。(注:H.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 (London:Macmillan,1977),p.254.)演变到世纪之交的话语,即是“人权高于主权”。而且,新左派强调,古代的帝王(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中国的皇帝)往往只是统治(ruled)整个帝国,但并不管理(governed)帝国的所有领地和番邦。他们缺乏行政力量、人事资源、组织体系和信息渠道去管理所拥有的庞大疆土,也就是说它们注重“面子”,不重“里子”。但当代政治全球化的趋势是,强大的跨国公司和西方资本注重的是“管理”传统的民族国家,而只是“统治”它们的主权,要的是“里子”,而不是“面子”。(注:David Held,Anthony McGrew,David Goldblatt,and JonathanPerraton,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Economics andCulture,pp.33—34.)所以,“新帝国”比之于“旧帝国”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
很显然,新左派的研究存在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情绪色彩,使用了大量的概念性用语,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中世纪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并使用简单的历史类比,刻意强调今日全球化与昨日帝国主义的相似性,而忽略了两者的不同性。殊不知,尽管历史会出现重复,但更会产生“扬弃”效应,即更高一个层次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回归与复制。例如,1842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开放”与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开放,就不是同一性质上的门户开放,前者是被迫的,后者是自愿的;前者是丧权辱国的,后者是深得民心的;而且,前者的后果是积弱积弊,后者是强国富民。所以,不能简单地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也归类为新帝国主义或新中世纪主义。
另外,新左派将失去领土与失去市场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如果说,失去的领土可以随着国力的增长可以夺回来,市场照样可以随着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并且吐故纳新。尤其是,领土是相对固定和静止的,是一个“你得我失”的零和关系,而市场的“大饼”是可以不断做大的,“你得”不一定是建立在“我失”的基础之上,而是存在“双赢”的可能。所以,运用固定不变的“反帝国”思维,难以解释不断变动的全球化现象。对此,新自由派就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
二、新自由派: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象征
第二大学派是新自由派(Neo—Liberals),其主要代表人物是K.Ohmae和W.Grieder。他们认为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经济和市场的整合,其结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将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尤其是,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在促使全球市场和全球竞争一体化的出现。(注:K.Ohmae,The Borderless World (London:Collins,1990); K.Ohmae,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New York:Free Press.1995); W.Greider,One World,Ready orNot:The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Simon Schuster,1997).)
新自由派通过大量的世界贸易变化的定量研究,强调贸易全球化的结果是“双赢”。例如,从贸易结构而言,1965年到1995年期间,尽管发达国家间的贸易量仍在全球贸易总量中占有优势,但其比重已从59%减少到47%,同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则从32.5%增加到37.7%,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则从3.8%猛增到14.1%。(注: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1965—1995) (Washington,D.C.1965—1995).)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出口大幅增长,在1963—1995年期间,发展中国家(除中国外)的工业品出口比例占全球工业品出口的比例,从6%猛增到20%。(注:GATT/WTO,International Trade Yearbook(Washington,D.C.1963—1995).)
而且,新自由派大力赞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积极功能,认为它确定了国际贸易的四项革命性、普遍性原则。一是非歧视性(non—discrimination),由此恢复了大萧条危机前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二是互惠性和对等性(reciprocity),所有成员国享受对等的关税待遇;三是透明性(transparency),防止黑箱作业;四是公平性(fairness),旨在反对低于市场价格的倾销政策。由此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关税大幅下降,同时减少了在服务业方面的贸易障碍。据估计,从1960年到1980年代末期,按人口计,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到了90年代,其比例已上升到50%以上。中国一旦加入WTO,那么这一比例还将上升到80%以上。(注:J.Sachs and A.Warnet,"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 al Integr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5):1—95.)
同时,在超国界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组织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已对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产生巨大影响。为了因应经济全球化的压力,目前一些国家和政府被迫削减国家支出和减少政府干预。这样,经济全球化已经形成一种“铁笼”(ironcage)效应,迫使每个政府严格遵守全球金融的共同规则,促使现行的福利政策受到大幅度削减,政府的独立功能大大萎缩。(注:R.Cox,"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Limits to Liberal Democracy,"in A.G.McGrew,ed.The Transformation of Democracy?Globalization and Territorial Democracy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7).)
新自由派还强调,信息不可能是独占的,而是共享的,尤其是因特网上的信息是极为公平的,任何国家和民众在此都能得到同一种价格的信息、同一个商品交易会的时间,所以全球化下的信息流动是跨国界、无阶级的。尤其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国家,都将被开除球籍。如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大清帝国的命运,在道德上值得同情,但历史是无情的,拒绝现代文明,必然被历史所淘汰。如今21世纪的世界潮流就是全球化,不管你赞同与否,人类的选择只能是接受、适应和参与。而且全球化与西化不同,因为全球化导致全体地球的公民受益。(注:Anthony Gidder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
有意思的是,尽管新左派和新自由派对全球化的价值评断截然相反,但两派却一致认同全球化的巨大“威力”和必然趋势。所以,两派也可合称为超全球化学派(the hyperglobalist thesis)。(注:DavidHeld,Anthony McGrew,David Goldblatt,and Jonathan Perraton,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Economics and Culture,P.2.)他们一致承认全球化的重大意义,认为全球化不仅已经成为事实,而且全球化已经提出从根本上重建“人类行为架构”的要求。(注:M.Albrow,The Global Age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6),P.85.)尤其是他们共同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导致非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的趋势,传统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权威和地位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之下,传统的国家既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内部事务,也不能满足本国国民的跨国界要求,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下的传统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不自然、甚至不可能的经济实体”,经济全球化正通过建立生产、贸易和金融的跨国家体系,推动“经济的非国家化”。(注:K.Ohmae,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New York:Free Press,1995),P.5.)
在此没有国界的经济体系之下,每个国家政府的功能已经弱化为全球资本的“传送带”(transmision)而已,或者只是扮演一个“三明治”的功能,成为介于强大的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媒介机构”。这样,“客观的世界市场正在比国家的力量更强大”,(注:S.Strange,The Retreat of the State: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World Econom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4.)国家的主权和政治的权威最终将听命于全球化下的经济力量,经济全球化最终将形成一个超然于国家主权的社会经济组织,取代传统的民族国家,并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主体。总之,新左派和新自由派共同认定国家主权将让位于经济全球化,所不同的是,新左派是希望“劳动控制资本”前提下的国家消亡,实现无产阶级主导世界的共产主义理想,并对如今急速发展的全球化深表忧虑和悲观。相反,新自由派怀着兴奋和乐观的心情,赞美目前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控制劳动”下的国家权力弱化。
其实,新左派和新自由派之间的论战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可以归纳为“动机VS后果”、“道德评价VS经济评价”,以及“短期效应VS长期效应”这三大不同角度。首先,以“动机—后果”的关系而言,新左派习惯强调强权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自私动机,因此自然否定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援助”,因为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动机是无私的,他们必定是以盈利、剥削,甚至摧残为最高原则。而新自由派则乐于关注发达国家对第三世国家投资的后果,尽管其投资的动机是自私的,但资本投资或全球化的后果往往是正面大于负面。
其次,从“道德评价—经济评价”的关系入手,新左派自然侧重运用道德评价的方法论,强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手段和方式是不道德和不人道的,并将近代的军事侵略与目前全球化下的经济侵略相提并论,全盘否定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任何正面作用。作为对比,新自由派则刻意淡化道德评价,强调经济评价,即主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比较发达国家侵略前和侵略后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影响,或者比较全球化前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指数变化,其结论自然是对发达国家的侵略或全球化持正面的肯定态度。
最后,关于“近期效应—长期效应”的关系,新左派喜欢关注全球化的近期效应,其结论就自然是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市场、人才、资源,并最终削弱了国家竞争力,只能任凭发达国家予取予求,非洲国家的落后现状就是明证。而新自由派则强调全球化的长期效应,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短期损失只是一种“阵痛”,是必要的“学费”,其长期效应必定是正面大于负面,东亚四小龙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何协调这两种对立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也许正确的思路是平衡、兼顾和中道。对此,“转型学派”似乎正在朝此方向作出努力。
三、转型学派:全球化推动社会转型
第三大学派是“转型学派”(the transformationalist thesis),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 Giddens、J.A.Scholte和M.Castells。他们共同认为,身处新世纪的世界,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注: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 J.A.Scholt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lations of Social Change (Buck 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1993);M.Castells,The Rise of the Newwork Society (Oxford:Blackwell,1996).)目前的全球化完全是史无前例的,跨国界的政府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限已经不再清晰,所谓的“国内外相交事务”(intermestic affairs)日益成为一种新的领域,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和社区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注:J.Rosenau,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4—5.)所以,对这一学派而言,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transformativeforce),促使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和制度产生“剧变”(shake—out)。(注:Anthony Giddens,"Globalization:A Keynote Address,"UNRISD News 15(1996).)
但另一方面,“转型学派”认为,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变数,因为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过程,(注:M.Mann,"HasGlobalization Ended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Review ofInternational Economy 4(1997).)而绝不是如新左派和新自由派所认定的历史趋势与必然规律,谁都无法预测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和它所要建构的世界新秩序,也就是说,“转型学派”既不否认全球化的存在与威力,但也不断定全球化必然导致传统国家的消亡,而是尽量不对全球化作出价值判断,既不认同新马克思学派的全盘否定,也不赞同新自由学派的正面肯定,而认为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发生和发展充满自身的矛盾与各种合力的因素,尤其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的流向,在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可寻的。所以,全球化的内容与方向无法预知。
尽管“转型学派”并不认同全球化正在导致民族国家的消亡,但仍然承认全球化下的新主权不再是传统主权所具有的绝对性、排他性、不可分割性和“零和性”,(注:D.Held,"Democracy,the Nation—State,and the Global System," in D.Held,ed.Political Theory Toda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而且认为,“国界”已经日益成为全球化的麻烦制造者,日益面临着跨国界或无国界国际组织的挑战。例如,欧盟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混合体,其主体被分割为国际、国家和地方三大块,任何一方(尤其是国家权力)都难以独立处理发生在自己领土内的金融和生态等事务,所以全球化是促使主权、领土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发生转型的力量,传统的民族国家将不再是世界权力的唯一或主要的统治形式。(注:J.G.Ruggie,Winning the Peace:America and World Order in the New Er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这样,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他们认为理性、明智的国家政府应该转化自身的统治功能,变传统的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侧重推动经济发展、协调集体行为,以及促进国际合作。他们坚持认为,全球化不是促使国家消亡,而是促使国家和政府实行战略转型和重组,并导致政府的活动更积极、更重要。(注:J.Rosenau,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尤其是,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Anthony Giddens,轰动一时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和《超越左右》(Beyong Left and Right)的作者,主张中间偏左(Centre—left)的政治和社会哲学,由此为“转型学派”增加了理论厚度。(注:Anthony Giddens,The Third Way: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8); Beyond Left and Right(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4).)而且学派争论的历史表明,谁越站在“中道”的立场,谁就越能得到更多的掌声,因为中道总是代表大多数。
总之,如果“超全球化派”定义全球化是全人类行为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的话,那么“转型学派”则认为全球化是区域间关系和行为的重组,国家不会因此消亡,也不会因此强大,而是因此得到转型和重组。(注:David Held,Anthony McGrew,David Goldblatt,and Jonathan Perraton,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Economics and Culture,P.10,table I.1.)
“转型学派”似乎力图将新左派和新自由派的对立引向调和与中庸,但并没有明确提出“中道”的方法和途径。对此,笔者的“三面硬币理论”也许能够提供一些启示。“三面硬币理论”是指硬币除了显而易见的左右两面外,更重要的是介于左右之间的中间一面,其功能是协调、连接和平衡,(注:Zhaohui Hong and Yi Sun,"In Search of Re—ideologization and Social Order,"in Andrew Nathan,Zhaohui Hong,and Steven Smith,eds.Dilemmas of Reform in Jiang Zemin's China(Boulder,Colorad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9),pp.36—37.)尤其是硬币的第三面促使硬币从平面变成了立体,它表明分析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左右两面,而应该从中道、立体的角度,全方位地分析特定的现象与人物。
这一“三面硬币理论”能够鼓励人们从“动机—后果”、“道德—经济”、“短期—长期”的多重视角,具体分析全球化的结构与功能。也许,人们应该淡化对全球化进行简单的“好坏、优劣”的价值判断,而应该强调“有效、无效”的功能判断,尤其是不能对全球化作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论,应该侧重分析具体国家、具体领域和具体时段条件下的全球化效应,避免大而无当的概念性定论。
四、怀疑派:全球化是无中生有
第四大学派是“怀疑全球化派”(the sceptical thesis),简称“怀疑派”,其代表人物是P.Hirst和G.Thompson。与上述三大学派不同,“怀疑派”认为甚嚣尘上的所谓全球化,根本就是一个“迷思”(myth)和天方夜谭。
首先,“怀疑派”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20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不是什么新玩意儿,更不是史无前例的,因为19世纪末的“金本位”(the Gold Standard)时期,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程度的一体化。如今的所谓“全球化”,充其量只是一种发达国家经济之间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而已。(注:P.Hirst and G.Thompson,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PolityPress,1996).)他们中也有人认为世纪之交的全球经济,只是一种“区域化”(regionalization),而不是全球化,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的金融和贸易的合作,即欧洲、亚太和北美。(注:W.Ruigrok and R.van Tulder,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structuring (London:Routledge,1995); R.Boyer and D.Drache,eds.States againstMarkets (London:Routledge,1996).)而且,经济区域化正在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区域经济日益走向排他、封闭和保护。所以,目前的区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动力,而是阻力。(注:D.Gordon,"TheGlobal Economy:New Edifice of Crumbling Foundations?" NewLeft Review 168 (1988); L.Weiss,State Capacity:Governing the Economy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8).)所以,当代流行的所谓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注:P.Hirst,"The Global Economy:Myths and Realities,"International Affairs 73(1997).)
同时,“怀疑派”通过大量的定量研究认为,“超全球化”学派所认定的国家弱化和消亡的谬论,完全是耸人听闻、无知可笑,因为这在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际经济的持续性力量。目前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只有依靠具体国家和政府的协调和推动,才能达到经济自由化的持续,不然将一事无成。政府绝不是国际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主要的设计师和建筑师。例如,今日的国际化,就是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所推动的双边经济体系和民族经济自由化的一大副产品。(注:R.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经济国际化并不可能导致国家和政府失去机动性(immobilization),因为资本的国际化“不仅仅能限制政策的选择,也能扩大(政府政策的)选择。”(注:L.Weiss,State Capacity:Governing the Economy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8),P.184.)
另外,“怀疑派”认为,国际化并没有导致南北不平等的消失,而是意味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日益边缘化,因为贸易和资本更多地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并由此产生更强大的“排弱”效应。(注:P.Hirst and G.Thompson,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同时,他们根本否定全球化能够有助于全球劳工的分工与合作,有助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就业机会的奇谈怪论。(注:P.Krugman,Pop Internationalism (Boston:MIT Press,1996).)因为从经济结构而言,“怀疑派”认为过去一个世纪里国际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革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级结构。所以,所谓的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体化的出现。(注:Samu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6).)
这样,不仅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迷思,文化全球化更是一个天方夜谭,而这种一统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全球化“迷思”与“狂想”,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臆想和杜撰出来的。所谓的“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和“国际一致”(international solidality)总是那些自我感觉良好并企图强加于别人的一批强权国家的口号。(注:E.H.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London:Papermac,1981),P.87.)所以此派学者很不认同“超全球化”的观点,认为一方面,全球化不可能导致全球经济政策的一致;(注:H.V.Milner and R.O.Keohane,"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 R.O.Keohane and H.V.Milner,eds.,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1996),P.14.)另一方面,全球化不得人心,正在遭到许多国家和民众的有效抵抗。(注:M.Geyer and C.Bright,"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1995); J.A.Frieden and R.Rogowski,"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on National Policies:An Analytical Overview,"in R.O.Keohane and H.V.Milner,eds.,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1996).)发生在1999年12月美国西雅图WTO会议期间的大规模抗议事件就表明,不仅发展中国家反对全球化,而且发达国家的劳工团体与环保团体也成为强有力的反对者。
“怀疑学派”似乎有点标新立异,但研究就是在不断的怀疑过程中深化的。这一怀疑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不新鲜,它有可能借鉴了二战后流行美国学界的“修正学派”:(注:E.B.Smith,The Death of Slavery,The United States,1837—65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从历史心理学的角度强调,许多民众司空见惯的现象其实都是虚拟和假象,而现实中种种虚拟的“迷思”和冲动往往导致许多历史的冲突和人类的灾难。这样,全球化所引起的冲突,就像世界大战和美国内战一样是人为的,绝不是必然的,所以是可以避免的。
很显然,“怀疑学派”的方法论是唯心的。以此推论,任何存在的现象都是虚拟的和人为杜撰的,因而就不可能是合理的。笔者以为,种种客观的事实表明,全球化不仅存在,而且已成一种大势,任何人为的肯定与否定都不能改变全球化存在和发展的事实。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全球化似乎应该定义为跨区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扩展过程,并对地球另一区域的民众和社区产生广泛(extensity)、强烈(intensity)和快速(velocity)的影响。(注:David Held,Anthony McGrew,David Goldblatt,and Jonathan Perraton,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Economics and Culture,pp.15—16.)这里的区域(region)是指具有类似文化、宗教、观念或经济特点的一批国家,如欧盟和东盟等。(注:B.Buzan,"The Asia—Pacific:What Sort of Region,in What Sort of World?" in A.G.McGrew and C.Brook,eds.A 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London:Routledge,1998).)所以,全球化与民族化(nationalization)、国际化(internationalitizaon)和区域化(reginolization)存在不同的定义,民族化是指在限定的国界内所进行的社会交流过程;国际化是指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的交往;区域化则是指同类国家在限定区域内的交往;而全球化是指不同区域在不同地域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方位交流。(注:T.Nierop,Systems and Regions in Global Politics:An Empirical Study of Diplomac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rade 1950—1991 (Chichester:John Wiley,1994).)
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讨论,笔者以为至少需要遵循四大原则。
一是定性研究原则。即争论各方需要界定全球化的定义,包括全球化与现代化、工业化、国际化和西化等相关名词的联系与区别。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共同的话语和共同的“平台”,这是起码的争论起点。
二是定量研究原则。每当一个术语成为非学术的流行话语之后,尤其是当官方也普遍介入并使用这一学术术语以后,往往产生滥用和语义不详的现象。对此,学者有责任引导正确的研究方向,尤其需要对全球化的广泛性、强烈性和快速性有一个系统的定量研究和定义。
三是学科交叉原则。全球化贵在“全”,它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是经济或市场的全球化,它只能是全方位的全球化,包括信息、教育、文化、政治、军事和观念的全球化。所以,各领域的学者需要互补,共同推动全球化研究的深化。
四是价值中立(value—free)原则。目前全球化的讨论已经出现情绪化、立场化和阶级化的倾向,已经出现以国家和区域划线、以贫富和阶级划线、以政见和价值划线的倾向,其后果必然促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流向政治和情绪之争。对此,需要各方努力走向理性、逼近客观。
可以预见,有关全球化的学术争论是一个世纪性课题,每个参与其间的学者都在书写学术历史,为了促使这场世纪之争流芳青史,学术界需要呼唤科学、理性、客观、责任、合作、宽容与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