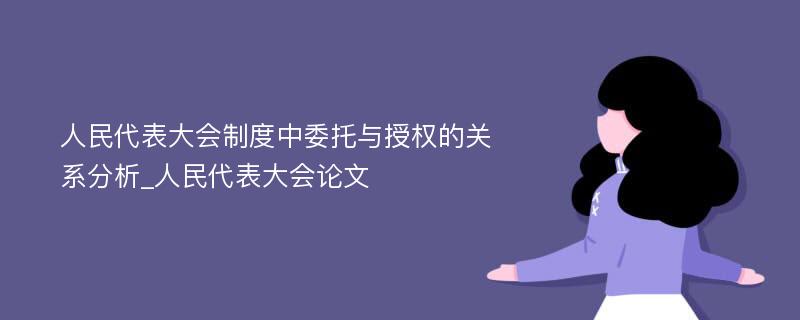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委托与授权关系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存在需要完善之处,其法定的最高政治权威与实际政治生活中我们的直接感受相比还有差距。其原因虽然十分复杂,但是,对人大制度中政治授权和政治委托作为权力配置具体样式的实质认识不到位却是重要的因素。本文从我国人大制度中政治授权和委托关系的实质、特点、原因入手,试图说明对它的形式的选择并不必然影响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变化。
一、委托与授权的实质:人民权力的具体实现形式,民权产生政权的逻辑起点
一般意义上来说,政治制度是权力归属问题,是对权力所有权的终极性标志,提供权力归属的合法性。我国宪法总纲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即谓在我国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人,人民拥有权力的所有权,我国一切形式的权力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统治权、管理权无不源于人民对权力的所有权。这种宪法性规定具有一种制度性价值。而现代组织行为学理论告诉我们,这种权力归属价值要转化成某种具体形式才能得以实现。这种转化过程的载体就是公共组织学上的所谓“政治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权力运行的载体就是权力所有权的实现形式。
新中国建政和施政的理论与实践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权力所有权宣示的张扬,而对其实现形式的论证过于简单,设计过于粗糙,从而影响了权力所有权的实现。制度建立之后,形式往往重于制度。只有发展出好的形式,才有所谓制度价值的实现。政治权力的实现形式,就是权力的布局、分配和界限的划分,提供权力实现的可能性。在现代国家民主体制的谱系中,我国属于代议民主制,人民拥有一切权力,这是一种根本的制度性价值,体现了我国政治的根本性质。而人民政治权力的进一步实现,其理论渊源与当代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并无两样,都取自于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等近代启蒙思想家共同构造的人民政治授权和政治委托理论。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代表就成为人民的政治代理人和受委托人,人民代表大会就成为国家各级最高权力机构,完成第一次授权和委托;然后,再由人大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其他诸如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完成第二次授权和委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内含两次权力配置过程,即两次政治授权和政治委托过程。作为人民代表制度实现的可能性机制,是民权转化为政权的关键环节,是公权力运行的逻辑起点,蕴涵着人大制度所有的特点,这是我国政治权力运行的基本形式。
二、我国政治委托与授权的特点:全部授予,一次性授予,授予一个机构
人民选举代表是权力布局和分配的开始,是委托和授权的程序,在制度设计时首先必须回答三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授予对象是一个机构还是多个机构;所委托和授予之权是一次性还是分次性;是整体授权、整体委托,还是部分授权、部分委托。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委托和授权的不同特点,决定人民权力的具体实现形式,关系到政治体制的具体样貌。
从我党建政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中事实上形成了三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全部授予。这是指人民把自己的权力全部授予和委托给代议机构和政府,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行理论和实践来看,正是属于这样一种情况。“是整体委托还是部分委托,全部授权还是部分授权”问题,从建政到现在,并没有在政权建设的理论中作为一个突出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也还没有在实践中提出系统、规范的改革。
第二,一次性授予。曾经表现在各种形式的事实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上。“一次授予还是分次授予”问题,长期受到忽视,导致公权力人员的职务终身制。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在多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中,着力强调推进领导干部由终身制向退休制、任期制过渡,如他在1982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顾问委员会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①。在这里已经提出了废除职务终身制实行任期制的思想,从思想和体制上逐步解决了人民委托权力时的“一次授权”转为“分次授权”的问题。
第三,授予一个机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和坚持的“议行合一”原则,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既是立法机构,又是各级最高权力机构,代表大会统一掌管“立法”、“行政”等全部国家权力。在制度设计时就已经明确提出不搞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实行“议行合一”的原则。
在我们国家所以形成以上特点,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人民集权思想,成为我国政治授权和政治委托的理论渊源。马克思在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经验时,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政权必须是集中的原则,“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兼管行政权和立法的工作机关”②。恩格斯也强调“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在人民代议机关”③。列宁更是明确提出“人民代议机关要掌握国家全部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完整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④。这种“议行合一”原则、“真正体现人民专制”的思想,在后来的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实践。
第二,我国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土壤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小农文化,农民自身地位的微弱,使得他们习惯于一个外在的高高在上的权威代表自己,这就形成了浓厚的“臣民文化”的社会心理传统。中国自近代尤其是清朝灭亡以来,国家权威荡然无存,政治上缺乏凝聚力,出现了一盘散沙的状况,人民吃尽了割据混战的苦头,期盼产生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政治权威中心。而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新政府的高度信任、对未来社会前景的美好期待,不能不深刻地影响新中国的政权建设。
第三,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异常艰苦的战争与革命的环境,这种环境中权力和权威的集中和统一,是取得革命成功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我党具有鲜明的革命党的思维和特征。由于多种原因,在建政后很长时间内未能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换。因此,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以鲜明的革命党身份特征施政,革命党的“革命”、“斗争”、“集中”、“统一”等价值观直接应用到政权建设实践中来,深刻地影响着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建设。
新中国建政以来,基于以上特点,尤其是至今还没有进一步明确和规范的第三个问题,使得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一方面表现出它的优势,如权力的集中可以保证人民权力不至于流失,施政效率比较高,国家动员能力强,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等。
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较多的在制度设计时不曾预料到的问题。公共权力机构成为全能主义机构,政府实为无限政府,国家无所不能,无所不管;民间缺乏权力,民间社会的空间几近消失。这样,人民监督公务人员、民间社会监督政治权力的作用无从谈起。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两个关系”出现变异:一是“人民与官员”的关系,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本来赋予人民一切权力,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务人员是人民产生的公仆,由于整体授权和全部委托的特点,容易出现主仆颠倒,官员坐大,失去监督,成为高高在上的主人;二是“民间社会与政府”关系的变异,人民应该保留一部分权力,形成民间权力,构成民间社会,这样就能使民间社会对政府保持一定压力,而整体授权使得民间权力消失,政府容易失去社会的监督,成为无限政府,有悖于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易致偏离宪法政治的轨道,政府机构也很容易产生脱离人民意志的官僚主义。因此,出现了民权与政权、民间社会与国家之间力量的严重不对称现象。如果国家和政府的决策一旦出现失误,则难以发挥人民拥有的制度性权利,人民很难纠正。在像“大跃进”、“文革”等长期性、全局性的错误面前,社会保持沉默,人民集体失语,甚至狂热地参与其中,不能不使我们从权力布局的角度反思其中的体制原因。
三、人民部分授权:政权保障民权的基础,社会监督国家的基石
“是整体委托还是部分委托,全部授权还是部分授权”,近代以来许多政治思想家、政府学者早有较为详尽的研究和设计,为我们思考和设计我国的权力实现形式,提供了可借鉴和吸收的宝贵的现成思想素材。他们大体有两种观点:一是主张全部授权,二是部分授权。
英国近代思想家霍布斯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思想家卢梭,在论述政府和国家存在的意义时,认为人民向公权力的授权是整体授权。霍布斯在他的《论公民》和《利维坦》中,承认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但他认定,一旦经协约把主权交给“第三者”,人民就失去了全部的自然权利,主权者拥有的权力应该是“至高无上”、绝对集中、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继承了霍布斯“主权不可分割”的理论,认为社会契约的订立意味着“每个分子连同他的权利都完全让予给整个的社会”④,他在解释为什么是整体让与权利的时候,认为这是因为“如果个人还有什么权利保留着,那么每个人在某些方面仍然由自己判断,而他很快又要求其他一切也都由自己判断,契约将变成无效”⑤。这类思想倾向后来被很多人认为具有引向新专制主义的嫌疑。后来恰恰是在卢梭思想影响下,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出现多次革命后的新的专制政权,人民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起来革命,最终在渐离卢梭“整体委托”论基础上,确立了法国近代代议民主体制,构成民间社会对国家、民权对政权的制衡结构。
而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和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则坚决地认为,人民在委托时是部分委托,部分授权,自己保留下不能够让与的天然权利。洛克在《政府论》第十一章中明确主张,“即使在人民同意基础上的最高权力,未经本人同意,任何人的财产权的任何部分不能被取去,因为,既然保护财产是政府的目的,这就必然假定并且要求人民保留享有财产的目的”⑥。在他看来,国家的权威必须以保护人的生存、自由和财产为目的,否则,人民就有权废除原来订立的契约,“人民和社会始终保留着一种最高权力,以保卫自己不受任何团体,即使是他们的立法者的攻击和谋算”⑦。洛克与后来的孟德斯鸠对政治代理人和政府有着一种深深的忧虑:生怕政府、立法机构权力过大,人民反受其害。因此,他们的思想深处一直呼唤着要人民保留权利,形成民间权力,构成民间社会(抑或市民社会)。洛克的思想成为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基石。
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曾经警示建国之初的美国人民,“权力如果全部授予,不加保留,不管授予的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都会导致专制,只是专制的形式不同而已”⑧。其实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在主张人民代议机构有必要集权、实行“议行合一”原则的同时,并没有反对人民和社会保留部分权利。他认为正是人民保留的权利,而形成民间社会对国家公权机构保持一种长期的压力和制衡,这样起到监督作用,防止人民政权体制中官僚主义的产生。
人民保留部分权利,已成一种不证自明的民主政治常识。
四、余论
尽管特殊的中国国情决定了无论是民主革命还是和平建设,都不能简单模仿别国,应该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在我国,确立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我国在政治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进步。但是,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根本政治制度价值的实现,必须摸索一套良好的具体实现形式。人民向代表、代表向各国家机关的授权与委托,仅是具体的权力实现形式,本身只是服务于制度的手段和方式,选择什么授权与委托形式,不会影响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性质。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借鉴国外政治建设的有利经验”,使我国的政治权力配置即政治权力的实现形式更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常识。因此,我们至少对“整体授权还是部分授权”的问题,应该从法理上明确,人民的政治委托产生政权,同时人民保留部分权力形成民权(人权),民权与政权的有机平衡促进民间社会的发育,构成对公权力体系的社会监督。我国新修改后的宪法,明确写进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也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思考和完善我国人民权力具体实现形式的空间。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3页。
②《马恩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3页。
③《马恩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46页。
④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4页。
⑤【法】卢梭:《社会契约论》,陈惟和译,九州出版社 2004年版,第15、13~14页。
⑥⑦【英】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44、91~92页。
⑧【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人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