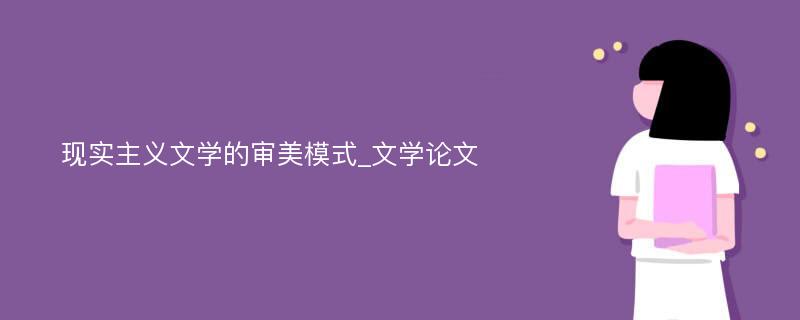
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范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还是作为一种文学类型,都属于历史的范畴。 自古至今没有完全不变的现实主义。 只要对中外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稍作考察, 就会有清楚的理解。 但是古代的现实主义和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直到后来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直到前几年出现的“新写实主义”,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都被叫做“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完全是一个意思的不同说法),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说,现实主义的内容可以因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但作为文学类型或文学思潮的现实主义在“变”中仍有不变的东西。这基本不变的东西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范型。在当前有人又重提“现实主义”话题,并对当前出现的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何申的《年前年后》等若干较之为贴近现实生活矛盾的作品大加赞扬,被有人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在这个时候,从理论的视野来讨论一下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范型也许是有益的。
(一)创作客体:想象的飞腾与逻辑的规定
现实主义的客体是现实主义审美范型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当然不能把现实主义文学的客体或对象,说成是实际的现实生活本身,客体或对象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我们可以如50年代美学大辩论朱光潜先生所作的区分那样,把实际的现实生活称为“物甲”,把作为主体的作家掌握的现实生活(即素材或题材)称为“物乙”。“物乙”诚然来源于“物甲”,但“物乙”又不同于“物甲”。“物甲”是纯然的生活本身,不具有主观性,它一般是科学家的对象;“物乙”是作家把握了的生活,或多或少、或浓或淡渗透了作家的主观性,这其中甚至已有作家的想象。
现实主义的作家运用带有主观性“物乙”进行构思、想象和艺术加工,在构思、想象和加工时,作家并不时时处处受真实的生活所制约,作家完全可以仅仅根据现实生活中那么一点点事情的启示,就虚构出一个看起来完全真实的故事。这里就出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悖论”:它是想象的、虚构的,甚至是完全想象和虚构的,但又要尊重客体的固有的内在逻辑性的规定。对现实主义作家来说,他必须“忠于”他的笔下的现实生活(物乙),而不能把笔下的现实生活当作自己的“傀儡”随意调动、安排。例如作家笔下的人物性格和命运是被其笔下的现实生活的必然性所规定的,现实主义作家必须寻找并揭示这种必然性,才可能创造出活生生的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的人物形象来。无论哪个时代的现实主义的作家和理论家都强调“真实性”。所谓真实性并不是如实描写生活本身,而是指作家所构思所想象所描写的对象的内在逻辑性。你可以写悲剧,但你要写出美好的事物损毁的必然原因,不是仅仅由于偶然性所造成的结果,当然这里也可以有偶然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但这偶然的背后仍然有必然的内在逻辑在延伸;你可以写喜剧,但要写出丑恶的事物败露的必然原因,你让读者笑,但笑过之后是有可以让人沉思的真实意义。对现实主义文学来说,重要的不是情节多么曲折,重要的是事物发展的普遍的规律和逻辑是不是被充分揭示出来。
对象的内在逻辑性并非表面的特征,它深藏在现实生活的底层,它就是作家殚思竭虑所追寻的生活奥秘之所在。列宁曾说过,事物有初级本质、二级本质、三级本质……。对象的逻辑性应该是事物的最深层的本质。这种本质由于埋得深、藏得远,同时又处在变动中、发展中,因此要把握它并不是容易的。也许这正是现实主义作家的一种才能,巴尔扎克说过:“在真正是思想家的诗人或作家身上出现一种不可解释的、非常的、连科学也难以明辨的精神现象,这是一种透视力,他帮助他们在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中测知真相,或者说得更确切点,是一种难以明言的、将他们送到他们应去或想去的地方的力量。”〔1 〕这种力量并不是每个作家都具有的。像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等这些现实主义的大师,应该说他们的把握社会生活本质的能力都是很强的,但就是这些大师常感到在构思好的作品被他们描写的人物所“推翻”,他好心好意让他的安娜·卡列尼娜活下去,但安娜“自己”不想活了,他要钻到火车轮子下面去,托尔斯泰无法挽救他的心爱的主人公的生命,只好听从安娜自己的命运安排。照理说,作家写作自己作主,人物命运得听他的安排、调遣,人物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在他的艺术规定之中,怎么会发生这种看起来是人物指挥作家而不是作家指挥人物的事情呢?作家作出这样的改变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关键就在作家开始构思时,他还没有完全把握自己所要描写的人物的固有的性格逻辑和命运发展的真实轨迹,只是后来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进一步展开,人物命运的真实的发展,作家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把握住人物的性格或命运的逻辑真相,没有揭示围绕人物形象周围的社会生活的本质,他所描写社会生活的内在逻辑向作家发出了呼声,作家听到了这种声音,这才作出了必要的改变。
这就说明了现实主义作家所描写的客体是“物乙”而不是“物甲”,“物乙”中已有想象的飞腾,但“物乙”由于是作家“研究”生活的结果,就会有其应有的逻辑的规定性,作家必须严格尊重这种逻辑的规定性,才能深刻洞见生活的本质,而其创作的现实主义性质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艺术想象与逻辑规定的“悖论”是现实主义的范型之一。
(二)创作主体:深情冷眼
创作客体的逻辑规定性及其艺术描写,必须在主体的“深情冷眼”中看出和写出,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范型的又一特征。现实主义作家与非现实主义作家不同之处,是他们对社会现实生活特别的关注和热情的介入,他们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种种“溃疡”、“癌症”,总想负起社会责任来,认真地当一名医治社会的医生,他们要把这“溃疡”、“癌症”的部位指出来,并提出医治的药方。他们希望尽快把社会的弊病消除掉。因此他们对现实生活不但不冷漠,而抱着常人所没有的“深情”。这种“深情”在作品中常常化为对现实的尖锐的批判与揭露,因为在他们的理解中,现实生活中社会问题如此严重而没有得到解决,首先是人们熟视无睹,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些社会问题将如何给国家、民族和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所以第一要紧的是把问题凸现出来,以引起人们的警觉,让人们感到社会问题已严重到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他们的这股赤热之心,真是无人可比。甚至连政治家,也很难有那样一种冲动之情。而且一般而言,他们对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并非要推翻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作家往往是入世型的“补天”派。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莎士比亚当年如何用人文主义精神来解救他所生活的社会,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如何用人道主义来改造社会,以及鲁迅如何揭示出社会的弊病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就可获得深刻的理解了。因此,现实主义的作家虽然常常不在作品中“露面”,给人以冷静甚至冷漠的感觉,但在字里行间却掩饰不住对社会改造的“深情”。这种“深情”是现实主义作家作为主体所必有的东西。
当然,对现实主义文学来说,“深情”是蕴含和埋藏在作家感情世界里的“心理现实”,是不能明言的;在艺术的表现上要求的是极度的“冷眼”。“深情”与“冷眼”作为现实主义创作的“里”与“表”看起来又是一个“悖论”,但真正现实主义文学的范型就要求这种看似难以相容的“悖论”。“冷眼”的意思,是指现实主义作家描写人物、场景时的极度的冷静和客观,不把自己的同情与憎恨等感情直接地显露于作品的艺术描写中。他们力图造成这样一种艺术效果:我只是把纯客观的事件的演变、人物的行止告诉你们,这是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东西,你们同情谁怨恨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是你们自己的事,我本人对我描写的事件和人物并没有什么“感情色彩”,我不下什么“判断”,更不想教训人,一切由你们自己去体会吧!在这个问题上俄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有几段话说得特别精彩和透彻,他在写给阿·谢·苏沃陵时说:
……你骂我客观,说这种客观态度是对善和恶的漠不关心,说它是理想和思想的缺乏等。您希望我在描写偷马贼的时候应该说明:偷马是坏事。不过话说回来,这种话就是我不说,别人也早已知道了。让陪审员(指读者——引者)去裁判吧,我的工作只在于表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写道,您要跟偷马贼打交道,那么您得知道,他们并不是乞丐,而是吃得饱饱的人,这些人算得是一种狂热的信徒,偷马不单纯是盗窃,而是癖好。当然把艺术跟说教配在一起是愉快的事,不过对我个人来说,这却非常困难,并且由于技术条件而几乎不可能。要知道,为了在七百行文字里描写偷马贼,我得随时按他们的方式来说话,按他们的心理来感觉,要不然,如果我加进主观成分去,形象就会模糊,这篇小说就不会像一切短小的小说所应该做的那么紧凑了。我写的时候,充分信赖读者,认定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在这段话中,契诃夫作为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主义的艺术描写的范式何以这样,说明了两点理由:1、 现实主义艺术描写的特征是客观性,不当“裁判”,描写人物就得按人物应有的方式来说话,按人物应有的心理来感觉,只有这样形象才不会模糊;2、 充分信任读者,如果你把“什么样的人”客观地写具体了,那么读者是有感受力的,他们会把作品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自动地加进去,读者的判断是不会错的。契诃夫在写给丽·阿·阿维洛娃的信中还说:
……我以读者的身份给您提一个意见:您描写苦命人和可怜虫,而又希望引起怜悯的时候,自己要极力冷心肠才行,这会给别人的痛苦一种近似背景的东西,那种痛苦在这背景上就会更明显地露出来。可是如今在您的小说里您的主人公哭,您自己也在叹气。是的,应当冷心肠才对。……在这里契诃夫更深一层地从艺术描写效果的角度,说明描写的客观性对现实主义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艺术描写背景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艺术描写中的“辩证法”问题。这使我们想到我们的相声演员在“抖包袱”引听众笑的时候,他们自己得绷住脸,显得极其认真严肃,这样的表情使听众觉得如此可笑的事为什么他们自己不笑,这就更觉得可笑。实际上他们心里何尝不笑,他们心里是在“观看”自己的艺术所引发的笑声,也许他们比观众笑得更得意。对现实主义的作家来说,道理是同样的,您描写你的心爱的主人公的痛苦,但你自己不要从文字流露出那种唉声叹气的态度来,似乎你不过是客观的呈现,这样你的态度与你所描写的内容就形成了反差,在这“反差”中痛苦就会因背景的衬托而变得更痛苦,鲁迅难道不同情他笔下的阿Q吗?但在小说中似乎对阿Q很无情,岂但是无情,还有点“残酷”,竟然把阿Q当作一个嘲笑的对象? 甚至引得读者开始时也一起去嘲笑阿Q, 但是真正有鉴赏能力的读者就会从这嘲笑中读出苦涩、读出难堪、读出痛苦、读出复杂的感情来。概而言之,深情的内在的态度与冷眼的客观的艺术描写的“悖论”构成了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描写范型。
(三)艺术至境:典型的创造
艺术至境是指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的追求。不同的文学类型有不同的艺术至境追求。一般而言,浪漫主义类型的作品追求意境的营构,象征主义类型的作品追求意象的呈现,而现实主义的作品则追求典型的创造。人类通过这三足鼎立的艺术至境的追求,实现人类自身心理功能知、情、意在文学上的充分的实现。现实主义文学通过文学典型形象的创造,使人类的“知”(认识)的心理功能在文学上放出异彩。没有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不通过典型形象的创造而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笛福的鲁宾逊,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巴尔扎克的葛朗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罗贯中的刘备、孔明、张飞,施耐庵的宋江、李逵、鲁智深、林冲,曹雪芹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鲁迅的阿Q等, 这些人物的名字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共名”而家喻户晓,一代又一代流传下去。现实主义若是不能创造程度不同的典型人物,也就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了。
那么,什么是典型呢?过去有许多讨论。有的说,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有的说,典型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别林斯基说:典型是熟识的陌生人。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没有揭示出典型的特征。因为,用哲学术语来解说典型,总是把问题大而化之,我们可以说不但典型是个别与一般的统一、偶然与必然的统一,实际上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个别与一般的统一、偶然与必然的统一。所以这种典型理论说了等于没有说。至于别林斯基的说法则是一种比喻,我们可以理解,但仍然没有得到确定的说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说法,都建立在“综合”论、“拼凑”论的基础上,就是说,典型是对于同类的许多人的相同的行为特点的综合和拼凑。要写一个商人的典型,就必须从许许多多商人身上的相同点去综合,这种理论实际上是“类型”论,不是典型论。对现实主义作家来说,最失败的事情是把典型写成类型。典型正如黑格尔说的独特的“这一个”,它不跟其他任何人雷同,但又的确有普遍性,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地区,都可以发现它的影子。
几年前,我提出一种典型论。我认为典型是具有特征的能够激发人们的美感的人物形象。在这个界说中,“特征”是一个关键词,按德国艺术鉴赏家希尔特的说法,特征是“组成本质的那些个别标志”,“艺术形象中个别细节把所要表现的内容突出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妥贴性。”〔2〕他的理论得到了黑格尔的激赏和发挥, 并提出了“特征化”原则。别林斯基谈过特征的美学功能。法国文学理论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一书中,也特别看重“特征”这个概念,前苏联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对此也有论述。按我的综合和理解,就其外延说,它可以是一句话、一个细节、一个场面、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种人物关系等,就内涵而言,特征也是一种“悖论”:它的外在形象是极其具体的、生动的、独特的;但它通过外在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内在本质又是极其深刻和丰富的。所以,特征是生活的一个凝聚点,现象和本质在这里相连,个别和一般在这里重合,形与神在这里联结,意与象在这里汇合。作家如果在生活中抓住了生活中的一些特征(不必考虑在数量上的多少),将其扩大、提升、深化,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特征化”(不是综合、拼凑),那么就可能创造出成为“共名”的、能够引起人们的美感的典型人物来。典型人物的创造成功,哪怕是一个典型人物创造成功,那么你的现实主义也就达到了极致。
(四)不算题外的话
如果我们对现实主义的范型的上述理解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对目前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也就可以获得一个衡量的标准并作出我们的应有的评价了。
目前我所看到的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当然多少有一定的价值,因为毕竟接触到了现实的某些矛盾方面的现象。但不能对它们估计太高,更不能任意“抬高”。就这些作品所描写的对象来看,只是接触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作家们似乎看见了什么就写什么,他们似乎并没有研究过生活。“研究”这个词似乎是与理论家相关,与作家无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作家要用自己的直觉去“研究”生活,在一瞬之间,就能洞穿生活现象而体认本质。)因此他们并没有把现实关系的“真相”深刻地揭开给人们看,他们看到的并不比普通人更多,甚至更少。这怎样能达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客观规定性的要求呢?不能想人所未想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没有艺术家的起码的勇气,就不要想在自己的头上戴上“现实主义”的桂冠。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艺术描写的范式看,主体与其主人公的感情太一致。他的主人公受苦,作家也在受苦,主人公叹气,他自己也叹气,作家真是跟他的主人公“分享”了“艰难”。作家作为创作主体“深情”不多,而“冷眼”则完全没有。有的描写给人一种中学生写作文的感觉。入得不够,出得也不够。“热”得不够,“冷”得也不够。比起前几年的“新写实主义”的“老辣”来所差就不是一点了。
第三,从创造典型的角度说,我很难记住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不是“共名”。这里没有堂·吉诃德,没有欧也尼,没有安娜,没有“变色龙”,没有曹操,没有王熙凤,没有阿Q,没有江姐, 没有朱老忠,甚至没有李双双,没有谢惠敏……总的说,没有抓住时代的特征,更谈不上典型。
我不是一味泼冷水,我想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伟大文学传统(其中包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泱泱大国,新时期以来又有一次文学“复兴”时期,出现过不少优秀作品,推进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在这之后,现在如果只能“捧”这些还比较粗糙的不成熟的“冲击波”,那么我们不是太可悲了吗!?
注释:
〔1〕巴尔扎克:《驴皮记·初版序言》, 《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07页。
〔2〕见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