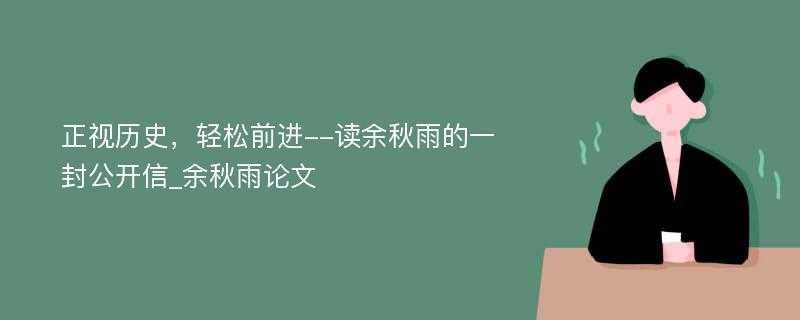
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读《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轻装论文,秋雨论文,一封公开信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这些年来,余秋雨接连推出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散文集,无论是题材的开拓,风格的创新,还是构思和语言方面的功力,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因此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一切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倘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我也敢断言,余秋雨散文和那些靠媒体炒作、凭名人效应产生轰动的作品不同,必将在我国的散文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记得好几年以前,《文化苦旅》出版不久,台湾余光中先生曾写过一篇长文《散文的知性与感性》,文章由古及今,洋洋洒洒,从唐宋八大家一直评述到新文学中的散文名家,褒贬得当,新见迭出,给人不少启发。该文结尾有一段话:“比梁实秋、钱钟书晚出三十多年的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性,举重若轻,衣袂飘然走过了他的《文化苦旅》。”记得初读时曾愣了一愣:用余秋雨殿后,直接钱钟书,是否有点评价过高?过后才悟到这正体现了作者宽阔的胸襟和敏锐的目光,试想:除了严肃的学术探讨和缜密的艺术分析以外,海峡那边的余先生何必为海峡这边的余先生进行鼓吹?像余光中先生这样不论资排辈,不问亲疏远近,突破门户之见和狭隘的地域观念,确是对历史对大众负责的表现。
近来不时有人指出余秋雨散文的“硬伤”,这得从两方面看:余秋雨本人对此自应虚心采纳,精益求精(目前看来还不够),别人则不必扭住不放,大做文章。“生也有涯,学也无涯”,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出现某些纰漏和欠缺。更何况治学向来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专治一门一科,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中穷搜博取,涓滴不遗,自然令人敬佩。有人则从文史哲各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有时也能见专家之所未见,发专家之所未发,给人以新的启迪,这同样值得学习和提倡。总之,双方互补,各尽所能,才有助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就难免有近视之嫌和门户之见了。
有人对余秋雨云游四方颇有看法,连余秋雨一张没有标明住址的名片也拿来做文章,这就更无必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何不好?余秋雨尽管行色匆匆,但常能俯仰古今,见微知著,从尘封的资料和人们见惯不惊的山水中发掘出深邃的内涵,进而做到历史和现实相沟通,哲理和形象相交融,引经据典而使人豁然开朗,独抒己见而能雅俗共赏,所有这一切努力应该说是十分可贵和难得的。不妨再举一个例子,我在周庄参观游览时,就曾听当地旅游管理部门的人说起,余秋雨的《江南小镇》助了他们一臂之力,余秋雨散文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毫无疑问,在精神文明建设亟待加强的今天,像这样的散文不嫌其多,只嫌其少。
近年来余秋雨的活动已大大超越了单纯的理论研究和散文创作,他和电视台联手,对大众演讲,向有关部门出点子,提建议,等等。有人对此不解,视为“媚俗”之举,我的看法则不然,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上述种种正不失为知识分子融入社会、拓宽用武之地的可贵尝试。孟子不是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一作‘善’)天下”吗?现在知识分子已经开始由“穷”而“达”,该是“济天下”、观民情,和群众取得密切联系的时候了。与其腹笥甚富但秘不示人,还不如倾其所有,直接服务群众,此说当否,请批评指正。
余秋雨近日在答记者问中说:“中国人际关系似乎有这样一种力量,只要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名气,他们就会找到任何一个缝隙把他灭了。”鲁迅写过《骂杀与捧杀》,今天确也有人或钟情于“捧”,或致力于“骂”,或二者交替而使用,着实教人忧心。但我想,写过《苏东坡突围》的余秋雨不必顾虑,当今社会环境已经迥异于北宋王朝,只要正确对待历史和自己,努力不受不良风气的干扰,是完全可以“突围”出来,取得更加出色的成绩的!
〈二〉
然而,《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答余杰先生》(见《文学报》总第1127期)却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使我十分惋惜和遗憾,一些在“文革”期间与余秋雨相识的朋友仿佛也有同感,有时,我简直要怀疑自己的眼睛:为什么余秋雨的文艺散文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而这封公开信却是可疑可虑之处不少?
古人云:“君子成人之美。”我当然不想做“小人”。但不管怎样,总得忠于历史,不违背历史真相,如果无端地“美”了此人,“恶”了他人,以致原本清楚的历史也渐渐模糊和扭曲起来,恐怕也非君子之道。于是想来想去,不顾妻子的再三劝阻(她劝阻的理由很简单:“这又不关你的事,何苦抛头露面,伤了和气”),决定独自执笔,对有关的事情作些补充和澄清。
《鲁迅传》编写组成立于1972年1月3日,朱永嘉和写作组的文艺组负责人到会正式宣布,说明主要任务是编写一本《鲁迅传》。不久,十一个成员便聚集到了复旦大学十号楼开始工作,余秋雨对此自然清楚。现在余秋雨在公开信中写道:“我这个一直被造反派批判的人也被学院军宣队分配到一个各校联合的教材编写组,工作地点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十号楼的103、104室。当时这幢楼里同样的教材编写组有二三十个”。这就发生了几个问题:1、 《鲁迅传》编写组成员名单是写作组圈定的,学院军宣队哪有这样大的分配权力?至于办办手续,在形式上走过场,那是另一回事。2、上头布置的明明是编写《鲁迅传》, 编写鲁迅教材不过是编写《鲁迅传》的前期工作,因为我们并非鲁迅研究专家,总得从熟悉鲁迅作品开始,余秋雨为何不把情况说得更加清楚一点?3、 十号楼确有一些教材编写组,但各组任务不同,情况有别,不见得都是写作组朱永嘉亲自宣布的,似乎没有必要加上“同样”二字。
公开信区别了“写作组系统”和“真正的写作组”,这没有错。照我看来,前者所以很大,是因为“四人帮”想要全面控制意识形态部门,后者所以很小,则是便于有效地驾御和使用有关人员。问题是余秋雨语焉不详,他只说:“真正的写作组很小,大多是‘文革’初期的老人马,加上后来的一些工农兵。”而漏掉了一个重要事实:余秋雨尽管不是“‘文革’初期的老人马”,也非后来的工农兵,但在离开“石一歌”以后,就上调到这个很小的真正的写作组,成为其中的一名正式成员。
公开信先是说:“当时工农兵学员的口号是‘改造学校、领导学校’。”接着又说:“这个教材组里的几个工农兵学员和他们的同班同学写过一本给小学生看的《鲁迅的故事》,署名‘石一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署名。”看似颇有强调工农兵学员作用之意。不是我存心替工农兵学员开脱,实际情况是我们组内四个工农兵学员从未起过主要作用。当时号召工农兵学员负起“上、管、改”的使命,我们则从无被“管”、被“改”(造)的感觉,倒是他们干了不少打扫之类杂事。那本《鲁迅的故事》也是我们这几个非工农兵的成员写的,而余秋雨正是主要执笔者之一。至于说到“石一歌”这个署名,那就更离谱了,实际情况是:编写组成立后用过好几个笔名,都不大满意,一天晚上陈教授(这自然是后话,此处借用余秋雨的提法)忽然想到“石一歌”(“十一个”的谐音)这个笔名倒不错,先和余秋雨等人商量,第二天在全组会议上提出,大家一致叫好,顺利通过,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余秋雨怎么能装作不知情的局外人呢?
公开信为了驳斥余杰所指不是事实,又特地写到:“我见过的那本署名‘石一歌’的著作全部是工农兵学员所写,即便硬把我推进去,年龄上也是最老。可见那个夸夸其谈的人完全不知道“石一歌”是什么。”是否“硬推”,前已说过,此处不赘。至于年龄,余杰所接触的人确实说得不够准确,但我作为“石一歌”最早的一个成员,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除去几个工农兵学员以外,余秋雨在“石一歌”内确实年龄最轻,如华师大陈教授生于1932年,复旦大学吴教授生于1935年,我生于1934年,余秋雨则生于1946年,比我们其他人晚了好几年。
公开信说他一九七三年下半年离开了《鲁迅传》编写组。时间不错,原因不明。现据有关事实予以补充。清查工作全面展开以后,我们回忆到一件事:一九七三年四月的一天,朱永嘉亲自到复旦大学十号楼,向我们布置整理几种资料,如鲁迅对“国防文学”的批判,鲁迅对新生事物的支持,鲁迅批孔等。整理资料派什么用场?有何背景?朱未作任何交代,因为这是几年来朱永嘉唯一一次到“石一歌”住地,因此没有忘记。这项任务没有搞完,又特地把余秋雨和另一位同志调到写作组的文艺组专门整理。后来清查工作深入后才知道,这是为姚文元修改他那本《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做准备的。由此可见余秋雨有任务在身,并不是随随便便离开“石一歌”的。
不妨再作一点补充。“四人帮”作恶多年,一朝覆亡,朱永嘉当时来不及销毁全部罪证。在写作组系统全面清理期间,曾经发现张春桥、姚文元两人给朱永嘉的一部分批件,其中有一件是姚文元于1973年4 月中旬为修改《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事给朱永嘉的批条,要朱永嘉找人员整理几项资料,我当时因工作需要看过这个批条,对批条中所说不要张扬等字眼记忆犹深。余秋雨答记者问时要求“拿出证据来”,这并不错,我完全相信这类材料至今还在,是可以设法找到的。我有长期记日记的习惯,查阅当年的日记,五月一日我也没有回家休息,还在复旦加班突击,着实可悲,现在回过头来,余秋雨理应比我们知道多一些,为什么不愿说上那么一、二句呢?
说是余秋雨完全离开了“石一歌”也不确切。尽管他上调到写作组的文艺组以后,所参与的活动更多更紧迫,但毕竟还是没有和“石一歌”完全分开。《鲁迅传》编写的办法是分头执笔,然后互相传阅,集体讨论,修改定稿,《鲁迅传》上册定稿以后(出版较晚,已在1976 年4月),继续写下册,不过此时的讨论已不在复旦大学十号楼,而改为康平路余秋雨所住房间外边的一间大办公室,这样的讨论举行过好几次,其时余秋雨的身份和作用当然与以前大不相同了。
余秋雨赴日访问是怎么回事?如果光读公开信,很容易得出如下的印象:余秋雨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受周纯麟少将委托去日本执行特别任务的。实际情况怎样,得多说几句。1976年10月19日恰逢鲁迅逝世四十周年,早在粉碎“四人帮”以前,日本方面就邀请我方组团出访,朱永嘉任团长,余秋雨就是朱永嘉提名作为“石一歌”代表参加的。一天消息传来,我们几个人(当时全组一共还有七个人)未免有点嘀咕,意思无非是既然老陈任“石一歌”组长,理应由他访日才对。倒是老陈并不怎么介意,对我们说小余能干,上头已经决定,不要再议了。这个代表团访日回来以后,余秋雨忽然跑到巨鹿路675 号(编写组于1976年7月23日由复旦大学搬至该处,即今上海作协所在地)来看我们, 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通他如何监视朱永嘉的情形,但我敢断言他当时从未谈起受周纯麟委派一事。也许有人会说:如此机密之事岂能让外人知晓?这似乎也有理,那就允许我先交代一下有关情况,再作一番推测,看看是否站得住脚。
粉碎“四人帮”以后,清查工作先在康平路写作组本部展开,余秋雨是正式领到“市革会”颁发的“写作组工作证”的一名成员,一开始就在本部参加清查,到后来,写作组下属外围组织的成员又一律集中到康平路本部,分别编入历史、经济、文艺、哲学等组参加清查工作,“石一歌”被编入文艺组。清查工作足足进行了两年多,大家差不多天天碰面,当时的我恐怕不能算是孤陋寡闻之人,但我明显记得,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是文艺组还是其他组,从未有人说起余秋雨受周纯麟委派之事,按常情,余秋雨当时正愁说不清楚,处境十分尴尬,如此“将功补过”之事岂能不说?现在周纯麟、车文仪同志已先后谢世,无法进行调查,我只能把这个疑问提出来请大家考虑。
公开信写道:“总之,把‘石一歌’说成是我,是不对的。”这样表述当然可以,如“石一歌”其他成员包括“我”在内的错误就不能往余秋雨一个人身上推,但还得补充两点才全面:一、余秋雨并不是早期“石一歌”的一般成员(尽管他没有“组长”、“核心”等名义);二、“石一歌”并不等于文艺组(文艺组用过丁学雷、方岩梁、方泽生、杜华章、任犊等笔名,如由余秋雨执笔、署名任犊的《走出“彼得堡”》就曾轰动一时),余秋雨的错误主要不在“石一歌”,而在进入写作组的文艺组之后。但无论如何,我得郑重声明:余秋雨决不是“文革余孽”(使用这种类似大批判的词汇是很不严肃的),他有错误,但以后改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写出了不少好文章,后又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说明他重新获得了组织和同志们对他的信任。人们完全不必对余秋雨扭住不放。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伏案长叹,真想恳切地奉劝余秋雨几句:今天,谁也没有权利强迫一位守法的公民进行反思和忏悔,你余秋雨尽可以集中精力研究学问,撰写文章,不必理睬某些不着边际的闲言碎语,但若真要发表公开信、回忆录之类,那就得实事求是,丢弃私心杂念,对历史对后代负责!
我甚至还有一个建议:把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收进你以后准备写的“自传”中去。我们大家都学过鲁迅,鲁迅杂文集不是收有很多附录吗?不管怎么说,拙文作为“附录”还是够资格的。
〈三〉
余秋雨应该正视历史,批评他的余杰等人也应该正视历史,对此我也想谈些零碎的感想。
想研究“文革”史,总结“文革”期间的经验教训,当然应该支持,无可厚非,关键是要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否则难免南辕北辙,收不到良好的效果。
常言道:“知人论世”。“知人”必须“论世”,“论世”才能“知人”。从某些文章来看,症结正在于对“文革”期间的情况了解得太少,体验得太浅。举例来说,余杰断言:“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患了这个疾病(指‘不忏悔’)。”情况真是这样吗?不提别人,就拿我这个普通知识分子来说,从反右到“文革”,不知道“忏悔”过多少次,检查过多少次,但愿以后不要再“忏悔”了,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不要再出现使绝大多数人“忏悔”的形势和局面了。真该感谢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使绝大多数人摆脱了动不动就要“忏悔”的窘境。另外,恕我直言,这种“绝大多数”的提法,调门之高,口气之大,着实教人害怕,莫非我们还没有从当年红卫兵那种“横扫一切”、“打击一大片”的错误做法中吸取教训?
张育仁在责问余秋雨时把“并不复杂的经验提示和逻辑思路”(《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作为立论的依据,言下之意是既然“经验”已经“提示”某些言行不对,按照普通的“逻辑”就了解该怎么办,你怎么还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并非我存心替余秋雨辩护,实在是不敢赞同如此简单的线形的思维模式,试想:“文革”期间,许多领导干部的革命“经验”不能说不丰富,逻辑推理能力不能说不强,为什么还会在群众一再批斗下“低头认罪”,检查自己的“修正主义错误”?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恰恰不是“并不复杂”,而是非常复杂。拿我们从五十年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的“逻辑思路”常常是混乱的,提示给我们的“经验”常常是互相矛盾的。不是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正在真诚地往“皮”上靠,哪里还敢作非分之想?不是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吗?我们在受了不少挫折之后还愿意再尝尝“灵不灵”的滋味吗?我们有没有怀疑?当然也有,但常常是始而怀疑,继而怀疑自己的怀疑,最后终于不再怀疑。今天,在改革开放和民主宽松的环境下长大的年轻一代,很难了解我们当年的“心路历程”,有鉴于此,我不妨谈一点小小的切身体验。“文革”期间,我从“牛棚”放出来以后,常常听到工宣队的训导:“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好好想一想:你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答案不言自明,但听多了心里也会嘀咕:“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也没有种过粮食、纺过棉花吗?”一次我把这个疑问同一位善良正直的老党员谈了,他听后赶忙摇手说:“你千万不能这样说这样想!”我立刻意识到问题严重,庆幸没有“滑得更远”,闯下大祸。当然,人长着脑子总是要想的,不过以后不是沿着原来的“逻辑思路”,而是反过来想:马克思、恩格斯何等伟大,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怎能相提并论?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忙于调查工厂,接触工人运动代表,我生活在东方农业大国,自当在农业劳动方面作出努力……于是,不再怀疑了,想通了。
今天回忆起来,可悲吗?可悲。奇怪吗?并不。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千条原因,一种结果”。事实正是如此。写到这里,我想恳切地向青年朋友提一个建议:你们在撰写万言长文时,能不能也从这些格言民谚中获得启示呢?
不是前有彭德怀,后有张志新这样的英雄人物吗?诚然如此。想起自己也曾写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但我也认真冷静想过:英雄人物和先知先觉终究是少数,倘若“绝大多数人”都成为彭德怀和张志新这样的人,不是纯粹的乌托邦是什么?不是要让“绝大多数人”都活不成吗?拿我前面提到的那位老党员来说,我过去感激,今天感激,以后也将感激下去,如果我不感激,反而责备他当时为什么不敢带领我去同工宣队顶撞争辩,把“逻辑思路”弄得清清楚楚,那我这个人还有良心吗?
总之,不能图痛快,贪简单,把斑驳复杂的“文革”场景画成一条简单的直线,更不宜用“抹着文化口红”等提法来制造轰动效应。对于复杂的历史现象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作出多方面的思考和研究,余秋雨提出的“辨轻重,合常理”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遗憾的是他自己有时也没有固守这两点。我想:余秋雨也好,余杰也好,笔者也好,都应该严肃而又宽容,认真而又虚心,正视历史,轻装前进,携起手来,停止无谓的争论,为精神文明建设多做点实事好事。
——是所望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