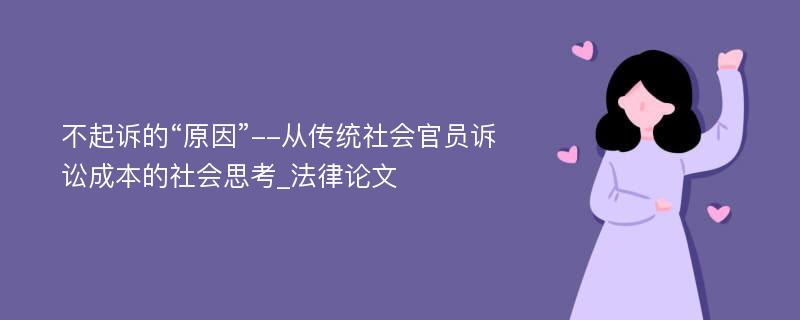
无讼的“理由”——来自传统社会官员对诉讼成本的社会考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官员论文,成本论文,理由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05)04-0055-05
任何一种思想都源于社会,并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得到强化。传统无讼思想源于、并主要表现为官方对王权主义秩序情结极致性的向往与表达,但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其生命力则来自社会各阶层、各方面对其运作成本所给予的经验的、心理的考量。正是这种考量孕育了它在传统社会的弥散性。由于无讼思想在传统官员那里得到普遍的共鸣,故本文以政令执行的唯一主体官员为视角,对传统社会诉讼的成本给以来自社会各层面的考量,希望这一历史的理解不仅能够厘清无讼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它得以滋生的可行性资源,而且能够澄明无讼思想的内在规定性,从而为全面解构传统无讼观念在传统社会的弥散性及其历史影响,提供社会学的理解和支撑。
一、为王权计:王权主义秩序情结的考量
无讼思想在官员那里得到普遍的共鸣。在历代官箴文书之中,劝民息讼之音不绝于耳。如汪辉祖《佐治药言》“息讼”、刘衡《劝民息讼告示》、褚英《州县初仕小补》“劝民息讼”、裕谦《戒讼说》等等,几乎构成地方“亲民”官至诚的为官心得及其不可或缺的行政内容之一。官僚对无讼的认同来自多方面,但首先源自王权主义高压下官吏对自身生存之力的考量。
中国的王权主义是传统仕人生存的最直接、最现实的背景与土壤。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生产力因其缓慢发展而不具备解构旧有社会关系的力量,政治强力和暴力便走向历史的舞台成为解决社会各种问题的主要方式,在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中,在社会诸种权力及其运转中,王权都成为主导、枢纽并具有至高支配力,王权主义由此产生,成为一种社会控制和运行机制。[1]①王权支配社会遂成为传统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在王权主义的秩序建构中,法即刑,是王权的外化和延伸。换言之,秩序是以权力来维持的,权力的话语因而遮蔽了权利的正式表达,权利依攀权力成为自然天理。而讼的实践因关乎小民对正当权益得以伸张的要求、体现个体对权利与平等的追求,被视为是对王权秩序的干扰和冲击。故早在春秋时期,子产“铸刑书”,叔向抨之:“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2](《昭公六年》)其后赵鞅“铸刑鼎”,同样遭到孔子的激烈反对:“晋其亡乎?失其度矣!……贵贱无序,何以为国?”[2](《昭公二十九年》)无讼思想由此产生。在王权主义的建构中,由于“民间讼牍繁多,最为闾阎之患。而无情之词纷纷赴诉,则全由于讼棍为之包媒”[3](P262),故唐代以降,历朝法典都严禁“讼棍”滋讼,体现着“一元化”极权秩序的强烈要求。
王权对秩序的关注构成中国历史的全部。维护王权即维护秩序,维护秩序即维护王权。对王权主义的维护及农业社会对稳定的强调诞生了传统中国人的“秩序情结”。这一情结既构成了“无讼”文化的起点和归宿,也成为官员自身生存的最直接的政治背景。历代君主对官员的要求不仅是清正廉明,更是“居官安静”。前者关乎民本的实践,后者却关系到王权秩序的实现。民本是君主统治的合法性理论基础,但它只具有哲学的价值意义。从实质上讲,不管对王还是对民,清正廉明都不具现实的品格:在民那里它只是一种奢侈的期待;在王那里则出现了“辩证的反转”:对“好官”的要求压倒了对清官的需要。如曾大力拔擢清官的康熙帝,晚年却屡斥清官为人多刻,性喜多事,“好收受词讼”。[4](卷211)“苟于地方生事虽清亦无益也”,故“为督抚者,以安静不生事为贵也”。[4](卷265)他多次赞许那些“不生事”的官员“未闻清名,亦无贪迹,而地方安静,年岁丰稔。此等便是好官。”[s]正是这一要求决定了士人的政治性格,并成为官员维持自身政治生命的第一考量,从而压制事端,拖延民讼,“须省事毋滋事”②成为官场的必然选择。
二、为官员自身计:职业资历与考成的考量
如前所述,中国的王权主义决定了“好官”标准在民与君视野中的抵牾与错位:出于建构极权制秩序的需要,为小民所期盼的清官在君主眼里并不一定是好官,好官须“安静不生事”。但反观社会,狱讼却大量存在并被视为社会治安不稳的标志,从而直接构成了政府对官员政绩的考项之一。由于“一州县所司不外钱谷刑名”,[6]在官员的考成中,只有治安稳定并确保皇粮国税的上缴以维持王权主义的运转,官运才得以保证。③对于惟一“亲民”的政府层级的地方官而言,“唇舌细故而致争,锥刀小利而兴讼”④的现象自然不利其考成,因而贱讼、息讼以求无讼便成为必需。但问题不止于此。对官员来说,政府考规的繁苛及其职业能力的严重不足所形成的两极对立,对他们安身立命构成更严峻的考验。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规范官吏成为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⑤但由于中国私法的不发达,就民事规定而言,这种规范“旨在使官吏知道如何处理相关事宜,而对具体内容却是甚少规定,并且没有系统。”[7]而一旦政务出现问题,针对官员的考规及惩处却极为繁苛。所有官员,在其怠忽职守、办事错谬、滥用权力、贪污行贿或犯有其他罪行时,都有可能受到诸如《大清律例》、《清会典·吏部》、《吏部处分则例》等法规的惩处。法律区分公罪私罪。公罪源于才能不及,私罪表明道德堕落。由于行政规章过于密苛,有的官员不由感叹,虽然一个人永远不应犯私罪,但也许谁也无法避免公罪。⑥政治弊在法密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⑦
法网密苛则人思防范。但官员专业知识的阙如,又决定了官吏应对考规、防范出错的智力资本是有限的。传统士人一向以政治家而非官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不器”,[8](《为政》)《礼记·学礼》强调君子“大德不官,大道不器”,讲究的都是“圣人之道不如器,施于一物”、“不官于事,而旁通于道”的政治人格,为后世的官、吏技术性分职埋下了伏笔。科举制度确立后,对士人的全部要求就是熟知儒家经典、撰写文章诗赋,学者“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9]唐宋时科考尚有“明法”一科,学生需习律令书判以应之。至明清时八股取士,明法科被取消,流于形式的判词之考也于1759年被废除,官学中与法律相关的只留下《御制律学渊源》,从而使教育与事务的差距遂日益增大,仕者对管理行政毫无准备。不仅如此,为防止生员以权谋私、包揽词讼,法律规定生监涉讼无报呈者不准,听令家人告官对理。⑧在官学的卧牌上所刻八条圣训中,其一便是警告生员远离衙门不涉讼争、不作证公堂,否则将受惩罚。⑨由于考时不考、学时不学、讼时禁涉,常见州县少年书画弈诗,“津津然自诩为能。而问之以律例,则呐呐不能出诸口。[6]“士之所务,类制艺帖括,而于管理人们之政治多未究心,至于国家之法律,更无从探讨。”[10]尽管国家要求官员应熟知律例,⑩有些官员自身也意识到读律的重要性,但即便是曾行幕多年的汪辉祖也只能是“每遇公馀,留心一二条”,择要读之。[11](“律例不可不读”)(11)这一则是由于律例繁杂难知;(12)二则一切可委诸幕友,(13)无需研读;三则王权主义“一人政府”体制下,公务繁忙,公文应酬繁多,无暇顾及;(14)四则因为法律相对来说不是熟人社会的主要的调控范式。[3](P4-5)故少有州县官能像刘衡那样(15)有专心于系统研习法律的机会和决心。
秩序要求、课规繁苛及行政智资的不足,每一项均构成官员倡导无讼的理由。课规繁苛体现了王权主义的秩序情结;但值得一提的是,专业知识的阙如造成的对该原则应对力的不足,不仅加重了无讼的理由,而且加重了官员对律例诏令等正规则的规避。如在乾隆朝1768年的叫魂案中,乾隆不停痛斥地方有司虚应故事,“各该省隐瞒于前,复又塞责于后”,“始则因循贻误,不据实入告”,[12](P236)希冀“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之习,各省皆所不免”。[12](P179)官员间“上下通同,逢迎挟制诸弊,皆所不免。”[12](P264)(16)所谓“处分重则人思规避,而巧宦生矣;条例多则法可移,而舞文作矣。盖法律之权不可在吏与幕,法密文繁条例日增,求其权不归吏与幕,得乎?”,[13](卷五“法网不能太密”)此语反映的便是“法律法令并不总是被遵守,文字上的法与现实中的经常是有差距的”[14](P2),社会现实。官员惯于在社会秩序规则二元化的理论预设的语境中讨论解决法律规避的问题。本来规则的出现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但“如果规范某些程序的正式规定无法操作时,他们就不得不遵循成规……全体衙门成员都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乐意且当地百姓也接受的行为规矩。”[14](P333)结果,“政府与公众看作越轨或腐败的行径,也许被看作遵循行业性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行规)而已。”[14](P336)王权主义政治整合的结果使规则最终走向自己的悖论:人们不仅承受正规则的钳制,而且还要承受潜规则的奴役。王权主义也随即走向自己的悖论:吴思所谓的“淘汰清官定律”由此产生,而潜规则与官僚机器本身颟顸迟缓的工作方式,却足以使抵制专权的诡计得逞。[12](P281)(17)
三、(清官)为小民计:陋规与执政力的考量
官员对小民诉讼状况及生存之力的同情理解,构成无讼思想内在规定性的另一面。这种理解源自对小民诉讼成本的各方面的考量,包括经济、精力、体制等问题。
陋规问题是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在王权主义体制下,传统中国的基本财政原则是每一类支出必有一确定的税费来源去满足,特定资金被特别指定给政府的每一特定用途。因此“州县官们不得不按上级确定的税额征税并全数上交布政使司;其征收的递送费用不得从税金中扣除。列入办公费用目录中用于公务支出的资金较小。衙门职员的薪金常不够维持生计,实际上,在某种情形下,他们甚至一点薪水也没有。”[14](P47-48)朝廷正式预算解决的只有书吏、衙役的薪水,但这仅仅是象征性的;幕友、长随的薪给则全由州县官个人支付。因此上自皇帝下至官员都承认,陋规是满足各种行政费用、填补各种财源亏空的唯一途径。政府要做的也仅仅是努力将陋规规范化,但无法获得成功。(18)政府对陋规收费的容忍及制度上缺乏监控,致使衙门各级职员包括官员自身,乃至士绅,都加入收取、分享陋规的行列,陋规收入陷入无节制的混乱并与日俱增。就诉讼来说,衙役可向当事人索要草鞋钱、鞋袜钱、酒饭钱、车船钱、雇驴钱、招结费、解锁费、带堂费等等,书吏则可索要挂号费、传呈费、买批费、开单费、出票费、到案费、铺堂费、踏勘费、结案费、和息费、命案检验费及职员们的伙食差旅费、与审讯有关的文具费、灯油蜡烛费及其他种种费用。(19)正像曲阜孔庙碑刻所描绘,百姓打场官司,告、诉、锁、开、走、睡、茶、烟、审、和、打、枷、赢、输,样样都得花钱。(20)真所谓“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狱讼之胜负常取决于财富之多寡。有时一桩杀人案收取的陋规费可高达几万至几十万钱。(21)有时不仅凶手或嫌犯常被弄得倾家荡产,甚至居住在现场二三十里内的富户都成了敲诈目标。(22)《刑案汇览》载有一案最足以说明问题:有位陈光余路拾他人遗失袜带,被失者诬以行窃赴控。衙役在押带陈投审的途中索诈差费,陈“因无处设措,欲行逃避。”衙役尾追,陈被迫投河身死。[23](P264),一件微不足道的纠纷居然酿成命案,贫穷欤?陋规欤?均在其中!
清官如汪辉祖曾如是描述了当时“一纸入公门,九牛拔不出”的情景,呼吁勿做“破家县令”:“谚云:衙门六扇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非谓官之必贪,吏之必墨也。一词准理,差役到家,则有馔赠之资;探信入城,则有舟车之费。及示审有期,而讼师词证以及关切之亲朋,相率而前,无不取给于具呈之人。或审期更换,则费将重出,其他差房,陋规名目不一……其累人造孽多在词讼。如乡民有田十亩,夫耕妇织可给数口。一讼之累,费钱三千文,便须假子钱以济,不二年必至鬻田。……不七八年,必无以为生,其贫在七八年之后,而致贫之故,实在准词之初。故……少唤一人,即少累一人,谚云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下笔时多费一刻之心,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惠。”[15](“省事”)
“令虽不才,必无忍于破民家者。然民间千金之家,一受讼累,鲜不破败。盖千金之产,岁息不过百有馀金。婚丧衣食,仅取足焉。以五六金为讼费,即不免称贷以生。况所费不止五六金乎?况其家不皆千金乎?受牒之时,能恳恳恻恻割切化诲,止一人讼,即保一人家。其不能不讼者,速为谳结,使无大伤元气,犹可竭力补苴,亦庶几无忝父母之称与?”[16](“宜勿致民破家”)
由于陋规的泛滥,加之户婚、田土被视为为民间“细故”,于秩序无大碍,拖延民诉成官员常事,使小民劳神费财,诉讼的成本加重。“常见一纸入官,经旬不批,批准不审,审不即结,及至审结,仍是海市蜃楼,未彰公道,徒使小民耗费倾家,失业费时”。[17](卷一“听讼”)即使是难得出现的清官,对小民来说,也只能是冤诉海洋中的冰山一角。“劝吾民要息讼,毋谓官清,清官断十条路,九条难预定,有理官司尚且输,无理如何能侥幸。”[18]不可否认,在息讼之术的运用中,有的劝民之谕带有威吓的意图,就连康熙皇帝都曾公开宣称:“若庶民不畏官府衙门且信公道易伸,则诉事必剧增。若诉者得利,争端必倍加。届时,即以民之半数为官为吏,也无以断余半之诉案也。故朕以为对好讼者易严,务期庶民视法为畏途,见官则不寒而栗。“(23)官方欲制造恐讼气氛以促成无讼。事实上它多少也做到了:刑罚本身的威吓力量(24)和刑讯逼供制度化的审断技术、低下的诉讼效率、与诉讼收益不成正比的过高的诉讼成本,有限的官员能力及其职业良心、缺乏权力制约的普遍化的司法黑暗,都在百姓的健讼需求中共同造就了“饿死不做贼,冤死不告状”的矛盾心态。即便“郑重反复之复审制度,对于百姓而言,仅系增加被剥削之机会而已,而无法期待国家之裁判得令其满意,反之于裁判中愈能发现毫无公平正义之情形,是以在现实生活上常迫使百姓‘宁屈死不讼’,而选择屈死一途。”[19]这些境况都为官员劝民息讼、无讼提供了最合理的理由,(25)也为无讼思想生命力的“内爆”提供了最适宜的社会土壤。而小民的权利,非至“零和社会”则无以正常表达。
综上所述,无讼思想作为传统社会对调控效果的理念追求,作为王权秩序追求中的一种极致性的表达,它的产生与在社会的蔓延绝非空穴来风。但所有支撑它的诸种社会因素都是在王权主义体制下诞生的,王权主义秩序的高压及其演生的对讼的忌讳与疏离,官员管理能力的缺陷、行政法规的繁密与紧逼、及由此二者造成的对正规则的规避和潜规则的产生,以及陋规的泛滥,诸此种种无一不是王权主义的产物。在这一架框下的无讼思想,夹杂着王权主义对秩序的强化、对个体权利的漠视,官员在秩序高压下对正规则与潜规则的博弈,以及官民对陋规的无奈、对强权的敬畏与依附、对国法的畏惧、远离、规避乃至违背,这些都有力消解了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推动了权力本位与义务本位社会的建立。因此,历史地理解无讼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彻底消解王权主义一元化秩序情结的历史影响,推动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和独立的利益主体及其阶层的出现,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宪政关系,是建构现代政治法律文化的必由之路。
收稿日期:2005-09-15
注释:
①关于中国的王权主义,刘则华先生有深刻精辟的论述,指出中国的“王权是基于社会经济又超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它是社会经济运行中非经济方式吞噬经济的产物,是武力争夺的结果……这种靠武力为基础形成的王权统治的社会,就总体而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社会经济”。他还将王权主义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适应的观念体系。见本文参考文献[1]第2页。
②袁守定《图民录》卷一“须省事毋滋事”“当官须省事,省事者不矜明察不事深求,遇事之来,直寻常视之,其可已者已之。案牍不繁,以养无事之福。”
③“一个州县官,只要他没有加征税费或滥用刑罚,只要在其辖区没有盗贼、没有赋税拖欠、没有官帑或官仓亏空,只要该地百姓生活安定且地方环境条件在其任职内有所改善”,就能被评为“卓异”列为政绩第一类。见本文参考文献[14]第60页。
④真德秀《真西山集》卷四十“潭州谕俗文”。
⑤滋贺秀三甚至认为,传统中国的整个法律体系是由刑事法与官僚机构的组织法、行政执行法和处罚法构成。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译,梁治平,王亚新等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⑥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58页;汪辉祖《学治续说》“能反身则恕”“且身为法吏,果能时时畏法,事事奉法乎?贪酷者无论,即谨慎自持,终不能于廉俸之外一介不取。”
⑦张经田《励治撮要》“求治在人”;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五“法网不能太密”。
⑧《大清律例会通新纂》“越诉条”附例;《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诉讼·官吏词讼家人诉》;《光绪朝大清会典》卷三十二;顺治九年颁行的《卧碑文》规定学生“不许干预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即有切己之事,只许家人代告”。
⑨《礼部则例》卷五十七,第1页;《学政全书》卷四,第2页,卷七,第4-5、7-8及13页;《汝东判语》卷一“王撤等呈判词”。
⑩弼教在于明刑。“律例一书……百司官吏士庶,均应熟读讲明。而在州县中之初任,尤其须臾不可释手者。”他们“应将大清律例逐篇熟读,逐段细讲,务必晓畅精意,而于轻重疏密之间,以会其仁至义重之理。”见本文参考文献[6]卷一“讲读律例”。
(11)同类论述还可见刘衡《蜀僚问答》“禁止棍蠹诬扰在熟读律例”、褚英《州县初仕小补》“研读律例”等。
(12)即使获得少量的法律知识也需花费相当多时间。仅获得关于名例的应用知识就要花大约半年。见本文参考文献[14]第210页。
(13)幕友掌诉讼、税收、帐务、登记、草拟文书、通讯、考试等职能。据张庭骧称,除州县官个人事务外,没有一件是与幕友无关的。(《赘言十则》第3页)仅就讼案讲,因官员溺于制举、帖括之业,鄙视申韩家言,故只能“一委之于幕客吏胥据案书判,不知牍中为何事。一狱到官,幕不动笔,悚息俟之,累日弥月不得申祥”。(刚毅:《审看拟式·自序》)同类论述还可见汪辉祖《学治臆说》“访延幕友”、《佐冶药言》“检点书吏”、徐柯辑《清稗类抄·幕僚类》、《福惠全书》卷一“延幕友”、《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三等等。
(14)“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清史稿》卷一一六《官职三》。据《牧令书》卷八陈宏谋《屏恶·申饬陕属不阅文稿檄》,“陕省民淳事简,上下文稿尚不甚繁,官即件件检阅,未至日不暇给。无奈官场陋习,动云官止出此一身,事上接下,其文书稿案则有书吏叙送幕宾点改,焉能件件亲阅”。
(15)见刘衡《蜀僚问答》“读律在熟读诉讼、断狱两门共四十一条”。
(16)在对江苏省按察使吴坛斥骂时弘历称他“一任外省,即染模棱腐败之陋习。殊堪痛恨……汝空耗时日,奏报但无一字是实。”《朱批奏折》,第862卷第4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
(17)孔飞力借叫魂案总结了最为乾隆痛恨的“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一个普通的清代官僚即便并非故意设置障碍,仅以他日常的贪渎和欺饰,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君主大伤脑筋。见本文参考文献[12]第305页。
(18)关于陋规的不可根除,见汪辉祖《学治续说》“陋规不宜遽裁”、“常例应酬不宜独减”;褚英《州县初仕小补》“裁规宜酌”;刘衡《蜀僚问答》“上官衙门常例旧规必不可省”等等。道光皇帝承认须靠陋规弥补亏空,曾试图对其加以控制。但许多官员认为通过律例将陋规公开化合法化极为不妥。道光遂取消了这一成命。见《清实录》卷四、卷五、卷七、卷十。
(19)“卡房最为惨酷,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及十数人不等;甚至将户婚、田土、钱债、佃故被证人等亦拘禁其中,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苦涩百倍于囹圄。”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5页。
(20)山东曲阜孔庙碑刻“忍讼歌”:世宜忍耐莫经官,人也安然己也安然。听人挑唆到衙前,告也要钱诉也要钱。差人奉票又奉签,锁也要钱开也要钱。行到州县细盘旋,走也要钱睡也要钱。约邻中证日三餐,茶也要钱烟也要钱。三班人役最难言,审也要钱和也要钱。自古官廉吏不廉,打也要钱枷也要钱。唆讼本来是奸贪,赢也要钱输也要钱。听人诉讼官司缠,田也卖完屋也卖完。食不充足衣不全,妻也艰难子也艰难。始知讼害非浅鲜,骂也枉然悔也枉然。
(21)《庸吏庸言》第29页;《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二,第8页;《抚吴公牍》卷三十五,第9页;卷三十六第5页。
(22)《庸吏庸言》第36页;《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二,第8页;《蜀僚问答》“富民涉讼必致破家之故”。
(23)转引达维德《古代主要法律体系》注[2],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页。
(24)“法者,罚之体;罚者,法之用,其实一而已矣。”[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一○○。“大堂之中,公案之上,本官是阎罗天子;书吏是催命判官;衙役三班,好比牛头马面;扳子夹棍,犹如剑树刀山”。徐忠明《法学与文学之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清《刑案汇览》还载有大量因子女被告或一时违法,令父母畏惧而导致自尽的案件。典型案例见本文参考文献[3]中清帝国案例评析之78.1、78.2、78.4等等。
(25)“小而结怨耗财,费时失业;大且倾家荡产,招祸亡身,何不自爱之甚也。每思乡里愚民,生平不见官长,出作入息何等安闲。至一入公门,便难自主,歇家保护作伪多端,累月经年,资斧莫继兼之胥吏把持,差役勒索,迨得质讯,已费多少花销。……即赢得官司,结下子孙仇怨,倘招来刑辱,徒增颜面羞惭,甚至坐狱沉牢,囚系毙命,披枷带锁,桎梏戕生,无一不缘争讼来也。”,徐栋《牧令书》卷十七之裕谦“戒讼说”,道光二十八年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