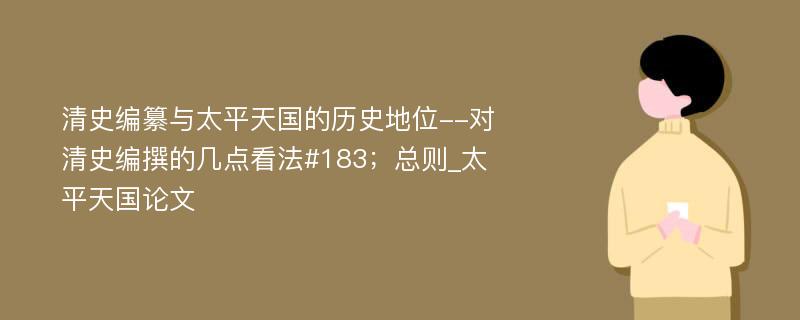
清史纂修与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①——对《清史#183;通记》纂修的几点意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史论文,太平天国论文,地位论文,几点意见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近来,在论及太平天国的评价时,大家常提到潘旭澜先生。我把潘先生的情况简要介绍如下:潘先生是复旦中文系教授。会前发下潘先生在《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上刊出的“洪秀全的政治性邪教”一文,署“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那是刊物编者弄错了。潘先生1952年考取复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那个特殊的政治岁月里,他为了坚持独立人格,竟做了22年助教。去年7月,因病不治仙逝。生前是复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导。他是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曾历时8年,主编过《新中国文学词典》;又是知名的文学评论家,代表作是杜鹏程《保卫延安》研究。此书将“文革”时期诬指“利用小说反党”的不实之词,彻底翻了过来,在拨乱反正时期产生过很大影响。他曾说,自中学时代起就对太平天国历史有兴趣,阅读了不少有关书籍,也积累了一些资料。经过10年浩劫,思考了不少问题,趁自己还写得动,想把自己的认识系统地写出来。他写的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发表后,收到不少赞同他观点的来信和文章,其中有些曾以复印件形式寄给我。
我与潘先生原本不认识。在2000年复旦校庆95周年时,《复旦学报》编辑部就潘先生所作“关于太平军的两个问题”[1] 举行了一次有关“太平天国研究”的小型学术沙龙,我才与潘先生相识。在沙龙上,我对潘文不称“太平天国”而称“太平军”等有不同看法,但赞同他对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客观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认为尽管潘文若干观点有待深入研究,却反映了当前史学界,特别是“太平天国”研究界迫切需要改变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普遍呼声。“太平天国史”研究要想有大的突破,要想结束了无生气的局面,必须摆脱美化、褒扬的主流意识和主流方法。会后,学报编辑向我约稿,希望我将会上发言写成学术专论。我应约写了“太平天国研究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文,在《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上发表,文章扼要回顾了各个历史时期“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成绩、特点与不足,指出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为了某种需要而歌颂农民战争、美化农民领袖,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新一轮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热中有了削弱和改观,但并没有消除,仍是研究中的主流理念。“令人感慨的是,对这种现象大声说‘不’的,竟然不是同行学人,而是一位年逾花甲的文学教授潘旭澜先生。”我在文章中指出:“看来,要改变目前太史研究萧条冷寂的局面,除了研究者要耐住寂寞、研究课题要拓展、研究工作要精耕细作外,还真需要提倡‘跨学科参与’——隔行论史。”[2]
我向来认为,学术研究应该百家争鸣。有不同声音,就不会“万马齐喑”、“众口一词”,学术才会繁荣昌盛。潘旭澜先生不是历史学家,他的文章也不是史学研究性质的学术论文,诚如他自己所标名的:“杂说”而已。但是他想“求真”的态度是不能抹杀和否定的。他的文章尽管辞锋尖锐,却观点鲜明,毫不含糊,代表了不少行外人的呼声。我们只要不讳疾忌医、不故步自封,保持一种开放式态度,把学术作为求真知的“天下之公器”,那么就会对原有的成就、结论,有再思考、再研究的必要。就“太平天国史”研究而言,不必担心以往取得的成绩,但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以往研究中确实有预设结论,美化、拔高洪秀全的倾向。自从潘先生等行外人发出不同声音后,现在不是有人也在说,“太史研究不要神化,也不要鬼化”吗?“不要神化”,此词不妥帖,确切地说应是不要美化,但承认以往研究中确实有过分美化的现象,就是一种进步;“不要鬼化”,此说更不妥,这是把潘先生和行外人的不同意见一概否定,用“鬼化”的帽子吓人。读了这类反批评文章,我总觉得在中允可掬的背后,隐含着以反对“鬼化”来维护“神化”的味道。
二
不少人对潘先生所称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是洪秀全的政治性邪教一说,口诛笔伐。我也认为潘先生指“拜上帝教”为邪教不妥,但又觉得无需多花精力去讨论是不是邪教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邪教之说历来是一种政治性用语。它并没有神学之争的意义。邪是正的对待字。中国既不是基督教为正教的国家,也不是以佛教、道教为正教的国家,何来神学上的异端、邪教?问题反倒是洪秀全有没有创立过“拜上帝教”(或称“上帝教”)的新宗教?这才是需要深入讨论的关键。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新纂清史通纪部分的编写,又是这次会议必须涉及的内容。会前发下的夏春涛同志新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正是谈这个问题的专著,所以我想多说几句。
我认为洪秀全并没有创立过“拜上帝教”这样的新宗教。早在20多年前的1980年,我曾在《北方论丛》第4期上发表过《洪秀全创立“上帝教”质疑》一文,指出无论检索太平天国钦定颁刻的43种印书、太平天国诸王7种供词、洪仁玕写的《洪秀全来历》以及外国人根据洪仁玕谈话写成的报告,全都没有提到洪秀全创立了“上帝教”一事,甚至连“上帝教”的名称都未出现。诸王供词中,最为研究者重视的是《洪仁玕自述》和《李秀成自述》两种。它们在叙述洪秀全早期活动时,都只说到洪秀全“劝世人敬拜上帝”,没有提到过他创立“上帝教”的片言只字。这只能说明洪秀全在1843年阅读《劝世良言》后,只是信仰上发生变化,皈依了上帝,并把自己的信仰传播给他人而已。
文章考察了张德坚的《贼情汇纂》、官文监修的《平定粤匪纪略》及今时出版的清方记载,发现在涉及洪秀全早期活动时,其说法在内涵、外延上都十分混乱,自相矛盾,出现了“上帝会”、“天帝会”、“添弟会”、“天帝教”等名目,甚至有洪秀全、冯云山师事过朱九涛倡立的“上帝会”,后又另立天地会,“亦名三点会,以秀全为教主”之说。经罗尔纲先生考证,朱九涛并未倡立上帝会,洪、冯也未师事过朱九涛。
如果说创立过“上帝教”,在金田起义前为了避免清方注意而采取秘密活动的隐蔽方式,秘而不宣,使清方不能确知,那么金田揭竿而起、公然反清之后就勿需保密,可以公开揭出上帝教之名。但是,专事收集太平军情报的张德坚、官文之流,竟对此毫无所知、妄加揣测,这难道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洪秀全没有创立过什么“上帝教”吗?所以我认为:洪秀全在1843年阅读《劝世良言》后创立了“拜上帝教”或“上帝教”,是缺乏史料根据的,此说很可怀疑。退一步说,后人因洪秀全信仰的上帝已与西方的上帝不同,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洪秀全创立了一个有别于西方宗教的新宗教,并将它命名为“拜上帝教”,简称“上帝教”,但那是为了解释历史的需要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解释历史和历史事实两者是不能混淆的。
文章发表后,居然没有反响。研究者仍持前说如故。1998年,我在《学术月刊》第1期发表“洪秀全与基督教论纲”一文,重申了10多年前的观点,指出:“17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审视洪秀全是否创教时,我认为上述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太平天国和清方记载的书刊俱在,人人都可索检查验;又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可以任何人理解和解释而具有弹性,它基本上是个有或没有的刚性问题。”[3]
研究太平天国宗教的学者都说到洪秀全与《劝世良言》的关系,但很多人没有说及梁发在《劝世良言》中,对《圣经》引文的注释和议论怎样影响了洪秀全对《圣经》的认知定势。按基督教教义,《圣经》是至尊和不可改易的。但洪秀全看到的《劝世良言》中,却有占全书五分之四的篇幅是梁发个人的说教,其中包括对经文的注释,对《圣经》篇章全旨的阐述发挥,对《圣经》故事的描述与意义引申。对于一个没有读过《圣经》原本,不知道基督教为何物的受宣者,《劝世良言》作为他获得神学知识的惟一来源,势必会产生可以用自己的感知和认识来解释《圣经》经文的错觉。心理学中有第一印象对人的认知形成至关重要之说。明白了《劝世良言》对洪秀全的这一层影响,就能理解为什么他在1846年从罗孝全学道时,仍时时处处用自己的理解来阐释基督教教义;就能解释他缘何会在《二训一歌》中,既用儒学知识解读皇上帝,又以阎罗妖作为邪神偶像、妖魔鬼卒的总代表;更能理解他为什么要批解《旧约》以及在《钦定前遗诏圣书》中作大量眉批的做法。这个神学知识极为零碎浅薄的门外汉,自以为是负有拯救世人的使命而在作教化众生、替天行道的大业。说他亵渎了《圣经》,歪曲了基督教教义,客观效果是如此,却冤枉了他的本意;说他另创了一个新宗教,似乎很像,但总给人以牵强附会的感觉;说他在《二训一歌》中提倡反封建压迫,主张人人平等的革命理论,完全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望文生义。不去指出他的无知浅薄、荒诞狂想,反而按构成宗教的四大要件硬套,说他创造了一个叫做“拜上帝教”或简称“上帝教”的新宗教,这种“反穿衣裳”的方法,出发点可以理解,无需深论,但并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解释。
那么,太平天国是否有一个宗教实体性的团体?有,这就是1845—1847年间由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区以教人敬拜上帝而团聚了数千信徒的“上帝会”或称“拜上帝会”。但从它的宗旨或主其事者的本意说,它并不是一个不同于基督教的新宗教,也不是寓有反叛现存统治秩序、以宗教为掩护的政治团体。“上帝会”的名称,不管是自称还是他称,当时人谁都不认为它是个新创的宗教或教派。与洪秀全一样,冯云山仅是在向众人宣传独拜真神上帝,勿拜偶像及劝诫世人悔改罪恶,信仰耶稣藉得天堂永久快乐。只是冯云山对耶教知识无多,在敬拜仪式中掺杂了中国传统的拜神方式。这些都是因无知或少知而起,不是因创立新教而标新立异。所以李秀成、洪仁玕等只称“拜上帝”,不称“拜上帝教”或“上帝教”;清方则认为它是“天主邪教”、“奉天主教”,“其实即天主教略变其格也”;外国传教士直到太平天国起义后,也不因为它掺杂了中国民间拜神方式而否认它的基督教性质,并对此寄予期望。既然当时情况与社会反应都如此,后人为什么非要把它说成是出于政治目标而对基督教进行有意识改造的新宗教呢?
三
《通纪》是新纂清史中不同于以往二十四史中的创新体裁,也是无成例可按、相当难写的部分。举行这样的讨论会,听取不同意见非常必要,对于义和团乃至辛亥革命等内容的编写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关于夏春涛同志的编写提纲,首先,我认为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夏春涛同志把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地反清起义,“置于清史的框架内来写,避免写成太平天国专史,给人以游离感”,体现了新编清史不同于以往王朝史的特点,肯定了农民战争的历史地位。《清史稿》最明显的缺点是修史者的史观有问题。他们身在民国,心系清朝。奉清王朝为正统,把反清的太平天国、捻军等各地农民起义军,一概骂为“贼”、“匪”。现在我们写清史通纪,承认太平天国是清代咸同时期客观存在的“与清政府相对峙的一个政权”,并作为这一历史阶段必须叙述的“核心内容之一”,让农民战争登上历史的殿堂,这就从史观上保证了新纂清史的历史唯物主义特性,避免把《通纪》写成王朝史。《通纪》就是“清代史”,既不是王朝史,其晚清部分也不是近代史。
其次,我感觉提纲从编纂体系上看,还是像中国近代史中的太平天国史部分,太平天国成了这一卷的主体,类似它的专史。太平天国是一个政权,但它不是像历史上南北朝那样对峙的政权,而是在清王朝统治下保有若干地区武装割据的政权。清王朝不仅在名分上,而且在实际上统治着中国;即使在太平天国割据地区,也客观上存在着巨大影响。整个中国的主体仍然是清王朝,所以承认太平天国是个政权,不等于这个阶段历史的主体就是太平天国,何况我们要写的是清史通纪,理所当然应以清王朝为叙述主体。
太平天国可以成为“本卷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所谓核心内容,主要是对其他农民起义而言,甚至可以相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而言,在篇幅上、内容上可以写得多而深入些。但不应该因此而将清王朝的镇压、应对及统治体制的变化等诸多历史事实轻描淡写,作为非核心内容带过,使主体线索不清,史事间的赓续及因果联系失序,成了太平天国的陪衬。按照我的私见,本卷仍以清王朝为叙述主体来写农民战争。在写农民战争和各地反清起义时,可以太平天国为核心,附带捻军等反清起义。这样写法确实有难度,也无先例可循(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第三卷第一篇,也专写《太平天国始末》)。惟其如此,如能有一个符合《通纪》体裁的新提纲,那么,这不仅是一种可贵的创新,而且对《通纪》其他相关部分的编写也是有价值的贡献。
注释:
① 本文根据作者在《清史·通纪》第6卷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标签:太平天国论文; 洪秀全论文; 历史地位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劝世良言论文; 太平天国运动论文; 远古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