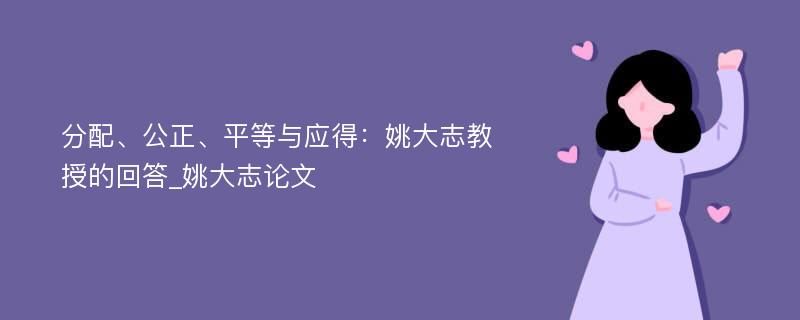
也谈分配正义、平等和应得——答姚大志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义论文,也谈论文,平等论文,分配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分配正义的三个问题——与姚大志教授商榷》的文章(以下简称《商榷》),对姚大志教授发表在《哲学研究》2011年第3期的文章《分配正义:从弱势群体的观点看》(以下简称《观点》)提出三点不同意见:分配正义只涉及如何在人们中间分配财富、机会和资源,而不涉及人们在福利上得到不断改善;正义的分配是平等主义的分配,不平等的分配不能被看作是正义的;分配正义原则只是判断分配正义与否的原则,而不是确定平等与福利的平衡点的原则。姚大志教授在《哲学研究》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回应我的文章《再论分配正义——答段忠桥教授》(以下简称《再论》)。不过,他在文中没有直接回应我的不同意见,而是提出并论证他与我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三个基本观念上面,即分配正义、平等和应得”[1]。在我看来,《再论》一文除了存在对我的不同意见的一些误解以外,还涉及我与姚大志教授对政治哲学中三个深层问题的不同看法,而这些问题对于如何理解我国当前存在的分配正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进一步说明我与姚大志教授之间的分歧,同时也为了改变我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的缺少争论的缺陷,我在这里对《再论》一文做出回应,并希望得到姚大志教授和学术界同仁的指正。
一、人们的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观念不是源于“现实的困境”,而是源于他们信奉的平等主义观念
针对姚大志教授在分配正义问题上实际持有的一种见解——人们在福利上得到不断改善,是与人们在分配上得到平等对待同等重要的决定一种分配是否正义的一个因素,我在《商榷》的第一部分提出,“分配正义只涉及如何在人们中间分配财富、机会和资源,而不涉及人们在福利上得到不断改善”[2],并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的相关论述、分配正义概念本身的含义和姚大志教授本人讲的“分配正义的实质”和“分配正义的关键”三个方面对这一观点做了论证。姚大志教授在《再论》第一部分的开头重述了我的观点,但没接着回应我的观点,而是反过来先推断我的观点“依赖于一种外在的分配正义观念”,然后证明“不存在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最后再为自己的见解辩护——说我对他有两个明显的误解。在我看来,他的推断、证明和辩护似乎都难以成立。
先看他的推断。姚大志教授先引用了我在《商榷》中的一段话——“分配正义的目的指的是它所要达到的结果,而这一结果是什么则是由分配正义本身的性质所规定的。前文表明,分配正义的性质是由平等主义所规定的,因而分配正义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平等主义的分配”[2]①,然后径直推断,“这些话语表明:如果我们持有某种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观念,那么这种分配正义的观念就决定了分配正义的性质;至于弱势群体的福利状况是否得到了改善,与分配正义无关”[1]。由此出发,他进而推断,“这种观点依赖于一种外在的分配正义观念。因为这种外在的分配正义观点具有客观的权威,所以我们只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就行了,而无论其结果如何。就西方政治哲学而言,这种外在的(或客观的)分配正义观念或者来自于上帝的神法,或者基于形而上学的自然法”[1]。然后,他讲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不存在某种外在的(或客观的)分配正义观念,以致我们一旦发现了这种分配正义观念,只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就行了。我也不认为分配正义观念需要建立在某种外在的(或客观的)权威上面,无论它是神法还是自然法”[1]。姚大志教授的第一个推断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无论从我那段话本身的含义,还是从其出现的语境,都推不出他认为那段话所表明的东西。他的第二个推断也不能成立,因为他既没有表明他讲的“一种外在的分配正义观念”其含义是什么,也没有表明我的观点如何“依赖于”这种外在的分配正义观念。他对其观点的表述则让人难以把握,因为他只告诉人们“他的观点相反”,即他认为“不存在某种外在的(或客观的)分配正义观念”,而没告诉人们他的观点是什么。
再看他的证明。姚大志教授说,“我的分配正义观念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思考目前社会存在什么样的正义问题(比如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然后我们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提出相应的制度设计,并提炼出相应的正义观念”。[1]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他把其在《观点》一文中提出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观念作为例证,指出这一观念源于他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分配领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并认为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不存在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此外,他还以自由主义者、平等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和至善主义者对制度的不同设计为例,提出“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正义观,不同的正义观导致不同的制度设计,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不存在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1]。我认为,姚大志教授的证明至少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他对其分配正义观念的阐述本身存在逻辑矛盾。当他说“首先我们思考目前社会存在什么样的正义问题(比如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时,他说的“正义问题”必定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否则,他就不能把“存在严重的不平等”视为正义问题,由此说来,他在“思考目前社会存在什么样的正义问题”之前,必定已经持有一种正义观念。如果实际情况是这样,那他接着说的“然后我们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提出相应的制度设计,并提炼出相应的正义观念”,就与他前边讲的那句话存在逻辑矛盾。因为依据前边那句话,他在思考目前社会存在什么样的正义问题时已经持有一种正义观念,因此,他后边讲的“提出的相应的制度设计”就必定是基于这种正义观念,这样说来,他接着讲的“并提炼出相应的正义观念”,即从基于已有正义观念的“相应的制度设计”提炼出“相应的正义观念”,就成了从已有的正义观念提炼正义观念,这从逻辑上显然是讲不通的。
第二,他提出平等主义分配正义观念的例子,不能证明“不存在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对于这个例子,姚大志教授是这样讲的:“按照我的理解,分配正义是一种制度设计。而提出这种政治哲学的问题,源于现实的困境。例如,我在‘分配正义:从弱势群体的观点看’一文中提出了一种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观念,源于我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分配领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1]。在我看来,姚大志教授讲的“我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分配领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他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分配领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即他所说的“现实的困境”,二是他认为这种情况是不正义的,进而言之,他认为平等主义的分配才是正义的。因为只有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他才可能提出“一种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观念”。那第二方面的内容源于哪里?显然不能源于“现实的困境”,而只能源于一种他信奉的平等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用他在《观点》一文的表述就是,“一方面,每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员是平等的,就此而言,平等是人的一种道德权利。另一方面,每一位公民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在社会上都占有平等的地位,就此而言,平等是一种法律权利”[3]。如果他的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观念不是源于“现实的困境”,而是源于他自己信奉的平等主义的观念②,那他的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观念就只能源于他认为并不存在的“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
第三,他列举的自由主义者、平等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和至善主义者的例子,也不能证明“不存在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姚大志教授说,“因为正义涉及到制度设计,所以在面对建立一个正义社会的问题时,不同的人可以设计出不同的制度,而不同的制度设计可以基于不同的正义观”。[1]例如,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是一个正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侵犯自由是最大的不正义,所以他们会设计一种确保自由优先性的制度;平等主义者认为平等是一个正义社会的本质特征,贫富两极分化是不正义的,所以他们会设计一种达到最大程度的平等的制度;功利主义者认为幸福最大化是一种正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幸福最小化是最大的不正义,所以他们会设计一种确保幸福最大化的制度;至善主义者认为使人的潜能(或某些特性)得到发展是一个正义社会的本质特征,阻碍人的发展是不正义的,所以他们会设计一种能够使人的潜能得到全面发展的制度。因此他认为,“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不存在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1]。在我看来,这些例子恰恰证明不了他想要证明的东西。这是因为,如果不同的人可以设计出不同的制度,而不同的制度设计可以基于不同的正义观念,那就意味着,人们持有的正义观念是先于他们的制度设计的。那他们的先于制度设计的正义观念源于哪里?能源于“现实的困境”吗?显然不能!如果不能,那他们持有的正义观念就只能源于姚大志教授认为并不存在的“外在的(客观的)正义观念”。
最后看他的辩护。在表明我的不同意见,即“分配正义只涉及如何在人们中间分配财富、机会和资源,而不涉及人们在福利上得到不断改善”之后,姚大志教授说,“这里段忠桥教授有两个明显的误解。首先,我说‘在分配正义问题上,人们抱有两个基本目的’,其中之一是希望自己的福利得到不断改善,这是指普遍存在的心理事实,特别是在中国这样还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福利制度的国家。但是显然,制度设计者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没有必要考虑所有人要求改善福利的愿望,正如我在提出分配正义的原则时只考虑了弱势群体的愿望,而没有考虑富裕群体的愿望。其次,我主张分配正义应该改善弱势群体的福利处境,但这里并没有‘包含所有人的福利都将得到提高的意思’。因为我提出的分配正义原则是‘把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其成员的福利’。按照这个原则行事,首先要考虑的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对于那些百万富翁们的福利,即使不会降低,但是也不会提高”[1]。姚大志教授这里说的我对他的“两个明显的误解”,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先说第一个误解。姚大志讲的“希望自己的福利能够得到不断改善”出自他在《观点》中的一段话:“在分配正义问题上,人们抱有两个基本目的,一个是希望得到平等的对待,另一个是希望自己的福利能够得到不断改善。”[3]从这段话能推论出其中的“希望自己的福利能够得到不断改善”指的是与“分配正义无关的”普遍存在的心理事实吗?显然不能!能推论出“制度设计者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没有必要考虑所有人要求改善福利的愿望”吗?显然也不能!如果这两个推论都不能成立,那姚大志教授说的我对他的第一个误解就是不存在的。
再说第二个误解。我在《商榷》一文中指出,“只要对姚大志教授的相关论述做一分析就不难发现,他说的改善虽然包含所有人的福利都将得到提高的意思,但还含有收入更多的群体会得到更大的提高的意思”[2]。我讲这些话的依据是他在《观点》中的一段论述。在谈到一种在他看来是正义的,而且适合用于解决当前中国“现实的困境”的“不平等的分配”时,姚大志教授论证说:“如果我们选择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方案’,出于某种机制,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方案会大大增加总体收入,从而使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了,即使对收入最少者也是如此,用流行的语言来讲,由于激励机制,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把‘蛋糕’做大了,所以每个人分到的份额也都增加了,尽管他们之间存在不平等。……收入更多的群体显然会赞成这种方案,因为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使他们得到了新增收益中的大部分……如果这些收入更少的群体是理性的,而且不平等不是非常严重,那他们也会同意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方案,即使另外一个群体会比他们收入更多一些”[3]。这段论述清楚地表明,虽然姚大志教授确实主张分配正义应该改善弱势群体的福利处境,但他的主张同时也“包含所有人的福利都将得到提高的意思”和“收入更多的群体会得到更大的提高的意思”。如果这段论述体现了姚大志教授的分配正义主张,而且我对它的理解也没有错误,那姚大志教授说的我对他的第二个误解也是不存在的。
二、人们同意还是不同意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往往不是只基于对正义的考虑,而且还基于种种其他的考虑
姚大志教授在《再论》的第二部分首先指出,“关于平等,段忠桥教授的观点集中体现在第二节的标题之中:‘正义的分配是平等主义的分配,不平等的分配不能被看作是正义的’。他引用了一些西方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来证明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观念。关于正义的分配为什么应该是平等主义的,段忠桥教授给出了两个理由:‘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应把人当作平等者来对待;二是不平等的分配是不公正的’”。[1]然后他提出,“对于上述观点,我赞同其前半部分,但不同意其后半部分,即‘不平等的分配不能被看作是正义的’和‘不平等的分配是不公正的’”,并说他“将以提出并回答三个问题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首先,平等主义意味着什么?其次,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如何能够成为正义的?最后,一种平等的分配为什么是不公平的”。[1]在回应姚大志教授“以提出并回答三个问题的方式”对其观点的证明之前,让我先来澄清一下姚大志教授这里对我的两个误解,和他的一个没有根据的暗含的假定。
第一个误解是,“段忠桥教授的观点集中体现在第二节的标题之中:‘正义的分配是平等主义的分配,不平等的分配不能被看作是正义的’”[1]。这是误解是因为,我的第二节的标题不是对我的观点的概括,而是对这一节内容的概括。在这一节我首先指出,由于姚大志教授把人们在分配上得到平等对待和人们在福利上得到不断改善视为同等重要的决定分配正义的两个因素,因而,他对“什么样的分配是正义的分配?”这一问题,就先后给出两种不同的回答:1)“正义的分配应该是平等主义的”;2)“一种不平等的分配也能够被看作是正义的”。接着我指出,“在什么样的分配是正义的这一问题上,姚大志教授虽然给出两种不同的、前后不一致的回答,但他实际上认可的是第二种回答”,并进而对他这两种回答存在的逻辑矛盾做了分析。最后我表示,“就什么样的分配是正义的这一问题而言,我原则上同意姚大志教授的第一种回答,但却不同意他的第二种回答”[2],并以西方一些学者的相关论述为依据,表明他的第二种回答为什么是不能成立的。简言之,在整个第二节中,我只是通过逻辑分析和引用西方一些学者的相关论述,来表明姚大志教授的第二种回答是不能成立的,其中没有一句话谈及我本人关于平等的观点。
第二个误解是,“关于正义的分配为什么应该是平等主义的,段忠桥教授给出了两个理由:‘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应把人当作平等者来对待;二是不平等的分配是不公正的’”。人们读一下我的第二节就可以发现,在讲完“就什么样的分配是正义的这一问题而言,我原则上同意姚大志教授的第一种回答,但却不同意他的第二种回答”之后,我接着指出,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而言,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正义的分配应是平等主义的,尽管他们对“平等主义的”含义,特别是有关平等的对象,即在哪些方面的平等,持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并引用了罗尔斯、戴维·米勒和威尔·金里卡的相关论述为证。只是在此之后,我才紧接着讲了这样一段话:“正义的分配为什么应是平等主义的?对此,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给出了种种不同的理由。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应把人当作平等者来对待;二是不平等的分配是不公正的”[2]。可见,我这段话讲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给出的两个理由,而不是姚大志教授所说的“段忠桥教授给出了两个理由”。
一个没有根据的暗含的假定是指姚大志教授将上面讲的两个理由中的第二个,即“不平等的分配是不公正的”中的“不平等的分配”的含义,假定为结果的不平等的分配。姚大志教授说他不同意“不平等的分配是不公正的”,但却没讲其中的“不平等的分配”的含义是什么,而是暗含地把它假定为“结果的不平等分配”,并以此为由反对“不平等的分配是不公正的”。但他的这一假定是没有根据的。前边表明,我在讲到“二是不平等的分配是不公正的”这句话之前已经指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正义的分配应是平等主义的,尽管他们对‘平等主义的’含义,特别是有关平等的对象,即在哪些方面的平等,持有种种不同的看法”。[2](在“持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之后我还特意加了一个注,告诉读者可参见韩锐的《正义与平等——当代西方社会正义理论综述》一文,因为他对这个问题有较为全面的介绍)因此,我接着说的“二是不平等的分配是不公正的”中的“不平等的分配”,是泛指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举的各种不平等的分配,如机会的不平等分配、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能力的不平等分配,优势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因此,姚大志教授把它假定为结果的不平等分配是没有根据的。
现在我来回应姚大志教授“以提出并回答三个问题的方式”对其观点的证明。
姚大志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平等主义意味着什么”?但他没有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话题一转,说“有两种基本的平等观念,一种是‘结果的平等’,一种是‘机会的平等’”。然后,他进而指出,“机会的平等”又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形式的机会平等,另外一类是实质的机会平等;实质的机会平等又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当代功利主义主张的福利平等,第二种是罗尔斯、阿玛蒂亚·森和德沃金等人主张的资源平等,第三种是以柯亨和罗默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优势平等。最后讲到他的自己的观点,即“在两种基本的平等观念中,我赞同‘机会的平等’,不赞成‘结果的平等’;在‘机会的平等’中,我赞同实质的机会平等,不赞成形式的机会平等;在实质的机会平等中,我赞同资源平等,不赞成福利平等和优势平等”[1]。在我看来,姚大志教授的这些论述并没有表明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因而,也就更难说是对其观点的证明了。因为第一,他只说赞同“实质的机会平等”的“资源平等”,但对这种平等意指什么却只字未谈;第二,他只说“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有三种重要的资源平等观念,它们是罗尔斯的差别原则、阿玛蒂亚·森的能力平等和德沃金的资源平等”[1],而没有表明他赞同谁的资源平等观念。姚大志教授自己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姚大志教授提的第二个问题是:“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如何能够成为正义的”?他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先假设,有两种分配方案供人们选择,一种是现有的平等分配方案,每一个相关的人都得到了平等的一份,另外一种是不平等的分配方案,但是出于某种机制,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会大大增加总体收入,从而使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了,即使对于收入最少者也是如此;再论证,“收入更多的群体”显然会赞成不平等的方案,因为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使他们得到了新增收益中的大部分,如果“收入更少的群体”是理性的,而且不平等不是非常严重,那么他们也会同意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方案,即使另外一个群体的人会比他们的收入更多一些;最后得出结论,“如果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得到了所有相关者的同意,特别是得到了弱势群体的同意,那么它就是正义的”[1]。在我看来,姚大志教授通过对问题的回答所表明的观点,即他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人们同意还是不同意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往往不是只基于对正义的考虑,而且还基于种种其他的考虑。以姚大志教授自己假设的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方案为例:“收入更少的群体”之所以会同意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方案,是因为这种方案会使他们的收入有所增加;“收入更多的群体”之所以会同意这种不平等的方案,是因为这种方案使他们得到了新增收益中的大部分。如果他们的同意都只是基于各自对收入增加的考虑,那就不能因他们“同意”就认为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方案是“正义的”,因为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方案是否使人们的收入都有所增加是一个问题,是否是正义的,即是否“把人当作平等者来对待”(姚大志教授也是赞同这一点的)是另一个问题。
姚大志教授提的第三个问题是:“一种平等的分配为什么是不公平的?”他的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段忠桥教授认为,‘不平等的分配是不公正的’。与其相反的观点应该是‘平等的分配是公正的’,而这个观点也应该是段忠桥教授所主张的。我则持有相反的观点。由于我更愿意使用‘公平’(fair)而非‘公正’一词,所以我将这种相反的观点表述为:‘平等的分配是不公平的’。仅仅表明观点是不够的,现在我还需要证明:平等的分配为什么是不公平的?”[1]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姚大志教授先将问题中讲的“平等的分配”界定为“所有相关者都得到了平等的一份”,并将需要分配正义来分配的对象限于三种主要的东西,即机会、资源和收入。然后,他对问题做了这样的回答:“首先,机会不能平等的分配,因为它们是有限的。所谓机会,主要是指上大学、就业和官职的机会。由于大学和官职等需要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即使机会可以平等的分配,这种平等的分配也是不公平的。其次,资源也不能平等的分配,因为资源也是有限的。在各种资源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是医疗资源。我们知道,医疗资源只应该分配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人(病人),而那些健康者则没有这种需要。因此,如果我们平等地分配医疗资源,这对于病人是非常不公平的。最后,收入似乎是最适合平等分配的东西,但实际上也不可能。因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为勤奋,劳动时间更长或者更累,创造的价值更多,从而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有些职业(如医生和飞行员)需要很多的知识和复杂的技能,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和长期的培训,为此所消耗的费用应该在其收入中得到补偿。有些职业(如常年在野外工作的地质和测量工作者)是令人不快的、艰苦的或者危险的,也需要给予额外的补偿。如果给予所有人以平等的收入,那么这是不公平的。”[1]在我看来,姚大志教授对“平等的分配”的界定、对需要分配正义来分配的对象的限定和他对平等的分配为什么是不公平的论证,都是不能成立的。
先看他对“平等的分配”的界定。前边表明,我是在谈到“正义的分配为什么应该是平等主义的”时引用一些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的相关论述的,我讲的“不平等的分配是不公正的”中的“不平等的分配”,是泛指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举的各种不平等的分配,由此说来,我讲的“不平等的分配”,指的只是与分配正义问题相关的各种“不平等的分配”。然而,姚大志教授对我讲的“不平等的分配是不公正的”却做了这样的推断:与“不平等的分配是不公正的”相反的观点应该是“平等的分配是公正的”,而“平等的分配意味着所有相关者都得到了平等的一份”[1]。这一推断显然是难以成立。因为我讲的“不平等的分配”是与分配正义问题相关的“不平等的分配”,这样说来,如果姚大志教授提出与此相反的观点,那他的相反的观点中的“平等的分配”也应是与分配正义问题相关的“平等的分配”。对于与分配正义问题相关的“平等的分配”,威尔·金里卡讲过这样一段话:“根据德沃金的看法,任何一种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政治理论都分享着同一种根本价值——平等。这些具有一定可信度的不同类型的政治理论都是‘平等主义’理论。假如‘平等主义理论’是指平均分配收入,这种看法就肯定是错的。但在政治理论当中,还有另一种更抽象也更根本的平等理念——即是说,要把人‘当作平等者’。对于这种更根本的平等理念,存在着多种阐释途径。一种理论是否是平等主义,只取决于它是否承认共同体内每一位成员的利益都同等重要”[4]7。可见,与分配正义问题相关的“平等的分配”指的是“把人当作平等者来对待”。姚大志教授这里论证的“平等的分配”无疑也是与分配正义问题相关的,但他却把“平等的分配”理解为“所有相关者都得到了平等的一份”,这样的界定显然不能成立。
再看他对需要分配正义来分配的对象的限定。前边表明,在分配正义问题上,姚大志教授是主张“实质的机会平等”的“资源平等”的,这样说来,机会在这里就不能成为与资源并列的需要分配正义来分配的对象,因为他这里讲的机会主要是指上大学、就业和官职的机会,而这些都属于“形式的机会平等”而不属于“实质的机会平等”。收入更不能成为与资源并列的需要分配正义来分配的对象,因为收入属于“结果”而不属于“机会”。此外,他的“在各种资源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是医疗资源”的说法也有问题,因为仅从这一说法我们无法得知他主张的“资源平等”中的“资源”到底意指什么。可见,他将需要分配正义来分配的对象限于机会、资源和收入是与他的分配正义主张相矛盾的。
最后看他对“平等的分配为什么是不公平的”回答。前边表明,姚大志教授讲的“平等的分配”是指“所有相关者都得到了平等的一份”,因此,他的问题已与分配正义涉及的“平等的分配”无关。不过,我这里顺便指出,仅从逻辑上讲,他对自己所提问题的回答也难以成立。姚大志教授的问题是:“平等的分配为什么是不公平的?”他的回答是:机会不能平等的分配,因为它们是有限的,因而上大学、就业和官职的机会就只应分配给那些具有相应的知识和技能的人,否则就是不公平的;资源也不能平等的分配,因为资源也是有限的,因而,作为重要的一种资源的医疗资源只应该分配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人,否则就是不公平的;收入实际上也不可能平等分配,因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为勤奋,劳动时间更长或者更累,创造的价值更多,从而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否则就是不公平的。这些论述是对“平等的分配为什么是不公平的”这一问题的回答吗?显然不是,因为它们是在分别回答三个不同的问题,即“机会的不平等分配为什么是公平的?”“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为什么是公平的?”和“收入的不平等分配为什么是公平的?”而不是在回答“平等的分配为什么是不公平的?”这一问题。
三、分配正义中“正义”的含义是给每个人以其应得,但人们对什么是应得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
我在《商榷》的第三部分表示,我同意姚大志教授反对以“拉平”来解决严重的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意见,因为“拉平”并不是分配正义所要求的,但认为他的反对“拉平”的三个理由和他的“需要一种分配正义的原则来确定平等与福利的平衡点”的说法,都存在对分配正义本身的误解,并对他的误解逐一做了辨析。姚大志教授在《再论》一文中不谈我的那些反对意见,而是反过来说我们在应得观念上存在分歧。他先推断,“段忠桥教授在批评我的分配正义观念时,引用了G.A.柯亨、戴维·米勒和麦金泰尔的观点,以说明分配正义意味着‘应得’,并且在文章的第三节也批评了我的‘应得’观念。因为麦金泰尔等人确实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而段忠桥教授是以肯定的方式来引用他们的观点的,所以我有理由推断,他同他们一样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1]然后,他论证他理解的“应得”是什么、“应得”为什么不能作为分配正义的原则,以及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如何与我主张的平等主义相冲突。在我看来,姚大志教授的推断和论证都不能成立。
先看他的推断。我在《商榷》中论述分配正义只涉及如何在人们中间分配财富、机会和资源,而不涉及人们在福利上得到不断改善时,引用了一些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有关分配正义概念本身的含义的一些论述,以表明“分配正义”概念中的“正义”,其含义通常被理解为“给每个人以其应有”。我引用了G.A.科恩的一段话:“但如果因为我的一些批评者坚持要求我必须仅以通常的话语说出我认为正义是什么,那对这些对此将感到满足的人来讲,我就给出正义是给每个人以其应有这一古老的格言。”[5]7③引用了戴维·米勒的一段话:“在断定每一种关系模式具有其独特的正义原则时,我诉诸读者对我们所谓正义的‘语法’的理解。依照查士丁尼的经典定义,作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德性的正义乃是‘给予每个人应有的部分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这一箴言表明,存在着A将会给予B的待遇的某些模式以及他将会给予C的某些其他的模式(也许一样,也许不同),依此类推。正义意味着以适合于每个个体自己的方式对待每个人。它也意味着待遇是某种B、C、D等等应有的东西——换句话说,某种他们能够正当地要求的东西和A归属给他们的东西。”[6]39-40还引用了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的一段话:“正义是给予每个人——包括他自己——他所应得的东西以及不以与他们的应得不相容的方式对待他们的一种安排。”[7]39对于我引用这三段话,姚大志教授首先推断,我引用它们是为了表明分配正义意味着“应得”,这是明显的误解。因为这三段话讲的都是分配正义中“正义”的含义是“给每个人以其应有(或应得)”,都不含有分配正义意味着“应得”的意思,因为人们对什么是“应得”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姚大志教授接着推断:“因为麦金泰尔等人确实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而段忠桥教授是以肯定的方式来引用他们的观点的,所以我有理由推断,他同他们一样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这一推断显然过于武断,因为我引用的是科恩、米勒和麦金泰尔三人关于分配正义中“正义”含义的论述,姚大志教授却把这三人的论述说成是“麦金泰尔等人确实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这有根据吗?“麦金泰尔等人”中的“等人”指的是谁,是科恩、米勒吗?如果是,那有什么理由说他们二人“确实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科恩、米勒都不主张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至于麦金泰尔本人是否如姚大志教授所说确实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篇幅所限,本文这里不涉及这个问题)如果不是,那“麦金泰尔等人”中的“等人”指的是谁?在当下的语境中,除了科恩和米勒,还能指别的人吗?此外,他说“段忠桥教授是以肯定的方式来引用他们的观点的”,这其中的“他们的观点”指的是谁的观点?什么观点?前边表明,我只引用了科恩、米勒和麦金泰尔三人关于分配正义中“正义”含义的论述,但姚大志教授却因此说“所以我有理由推断,他同他们一样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这种推断有理由吗?
再看他的论证。在做出上述推断之后,姚大志教授接着说,“但是我认为,应得不能作为分配正义的原则,而且,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与段忠桥教授所主张的平等主义是冲突的。因此,我在下面将首先讨论我所理解的应得观念,然后说明应得为什么不能作为分配正义的原则”[1]。什么是姚大志教授理解的“应得”?他说,“所谓应得(desert),就是人们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1]。他还针对西方一些主流政治哲学家(如罗尔斯和诺奇克)以“资格”(entitlement)取代“应得”的主张,进一步阐释了他对应得观念的理解:应得有独立于制度的一面,也有依赖于制度的一面;使一个人对什么东西具有资格的是规则,使一个人对什么东西具有应得的是业绩。例如,在市场经济的制度中,“按照实际贡献或者特殊才能给予报酬,就是应得”[1]。由于姚大志教授这里论述的是“他自己理解的”应得,因此,我这里无须谈他这样理解“应得”是否有道理。不过,我在这里要指出他对“应得”的论证存在的一个问题。他在前边说我同麦金泰尔等人“一样”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其预设的前提是我对“应得”的理解与麦金泰尔等人的理解是一致的,可他在这里却只字不提麦金泰尔等人理解的“应得”是什么,而是大谈他理解的应得是什么,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他理解的“应得”是麦金泰尔等人理解的“应得”吗?据我所知,显然不是!如果不是,那他说的“应得不能作为分配正义的原则”,其含义就只能是“他理解的应得”不能作为分配正义的原则,他所说的“把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与段忠桥教授所主张的平等主义是冲突的”,其含义就只能是把“他理解的应得”当作分配正义的原则与段忠桥教授所主张的平等主义是冲突的。从他理解“应得”出发,姚大志教授进而论证,按照应得的原则行事必然导致不平等,然后说,正是在这里,段忠桥教授的观点出现了矛盾:一方面,他的观点是平等主义的,主张“正义的分配是平等主义的分配”;另一方面,他又赞同麦金泰尔等人的观点,把应得看作分配正义的原则。姚大志教授讲的这种矛盾实际上只是因他的误解而出现的矛盾,因为我在前边已经表明,他说我“赞同麦金泰尔等人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此外,他说的“把应得看作分配正义的原则”中的“应得”,实际上是“他理解的”应得,而我怎么会把“他理解的”应得看作分配正义的原则呢?
注释:
①这里需要指出,姚大志教授是把这一段话拆成两段话引用的:“分配正义的目的指的是它所要达到的结果,而这一结果是什么则是由分配正义本身的性质所规定的”;而“分配正义的性质是由平等主义所规定的,因而分配正义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平等主义的分配”。为了使人们对我这段话的意思有准确的了解,我这里恢复了这段话的原貌。
②至于他的这一平等主义的观念又源于哪里,那则是需要姚大志教授另外加以说明的问题。
③不过,科恩紧接着说,他“对这一格言并不完全满意,因为仅就它本身来讲,这一格言与在正义和什么是人们应得关系上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的每一种都相容。根据这两种观点中的一种,正义的观念是由人民应得什么的信念而形成的;根据另一种观点,人们应得什么的信念在于来自下游的(独立的可确认的)关于正义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