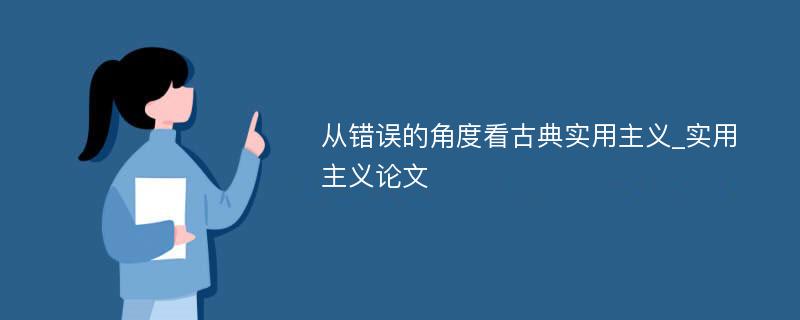
可错论视域下的古典实用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实用主义论文,古典论文,可错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用主义(pragmatism),以“实用”为词根,有术语传播上的便利,而也正因为如此,很容易造成培根所谓的“市场假相”。面对诞生之初所存在的庸俗化危险,实用主义的早期奠基人曾考虑以其他不易被误解的术语代替“pragmatism”,譬如,皮尔士提议“pragmaticism”,詹姆斯提议“practicalism”,杜威提议“instrumentalism”。但时至今日,“实用主义”依然是一个存在颇多争议的名称,加之近些年有学者又提出“新实用主义”一词,更是使得“实用主义”的真正所指成为困扰学术共同体的一个谜团。事实上,语词上的争议往往涉及实质,我们不能指望仅仅以字面更新加以澄清,除非能找到名称背后的核心主张。虽然实用主义准则关乎实用主义的要义,但实用主义的争论根源也正在于对实用主义准则的解读。本文认为,古典意义上的实用主义是在可错论的视域下展开的,可错论是实用主义者面对科学时代教条主义和怀疑主义所选择的一条稳健的中间道路,因此,我们需要首先厘定一种既反对教条论又反对怀疑论的可错论视域,然后才能对于实用主义准则给予一种免于表面化的适当解读。
一 从反教条论的视角看:不要阻碍探究之路
教条论是哲学上的宿敌,总是需要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做出新的回应。成长于19世纪下半叶的早期实用主义者们深受科学实验精神的熏陶,他们把自由探究作为健全哲学的第一要义,因而首先对于各种形式、各种程度的教条论提出了批判。
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教条论主要来自两个方向的哲学家。一个是皮尔士提到的那些试图以先验方法确定信念的形而上学哲学家。他们的形而上学体系“通常不是建立在观察事实之上,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它们之所以被采纳,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根本命题似乎‘与理性相适’。……其所指的不是那些与经验相一致的东西,而是指我们发现自己倾向于相信的东西。”①为了找到那种“与理性相适”的理论基石,形而上学哲学家们试图把某种不证自明的“先验公理”确立为绝对不可动摇的第一前提。正如詹姆斯所看到的那样,“有些人把标准定在知觉过程之外的某种东西,或者置于启示之中,或者置于民族公意之中,或者置于内心本能之中,或者置于种族经验体系之中。另一些人则以知觉过程本身作为标准——譬如,笛卡尔用的是以上帝真实性作为担保的清楚而明晰的观念,里德用的是他的‘常识’,康德用的是先验综合判断形式。”②显然,此种备受追捧的“先验标准”从未在具体内容上达成一致。因此,任何宣称“与理性相适”的标准,在持有不同标准的其他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种教条罢了。另一个持有教条论的群体是那些身居神学院或者以维护某种教义信条为宗旨的哲学家。不难想象,神学家为教会服务,当哲学不过是神学的婢女时,他们自然会从哲学上竭力论证“宗教信条”完全正确而不会出错。但绝非只有宗教影响深重的时代,也绝非只是神学家才会有此种教条式思维,在神学院之外的许多自称启蒙和理性的哲学家,甚至是具有科学训练背景的哲学家,也会出现先确立自己所相信的某种“派系”信条然后再寻求论证技巧以取悦自己的情形。此种明显有悖于探究方向的哲学思维,“不是让推理去决定结论最终如何,却让结论决定推理如何进行”,被皮尔士称为“冒牌的推理”(sham reasoning)。③导致哲学上各种伪推理、伪探究不时出现的,正是不同程度上的此类教条式思维。
应该看到,上述所谓的“教条主义”并非仅指某个狭小圈子,而是关涉哲学界乃至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相比宗教时代的不可错论者,科学上的不可错论者在今天更具有危害性;唯有足够彻底的批判,才能清除隐藏在“理性思辨”或“科学时代”名下的教条主义。为此,古典实用主义者试图从多个不同角度对于教条主义诸现象进行深刻而有力的批判:
第一,自由探究是科学的真正精神,教条主义是科学探究之路上的障碍石。所有获得成功的科学带给我们的教益是自由探究,此乃科学的真正精神。当人们说现代社会进入科学时代时,我们也应该在此种精神上予以理解,即此种自由探究的精神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可以说,不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且哲学乃至日常生活都是科学的,或至少是与科学相连续的。正如皮尔士所指出的那样,“为了学习,你一定渴望去学习,而当你渴望学习时,对于你已经倾向于相信的东西感到不满足。此乃理性的第一法则或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唯一法则,由此我们能导出一条推论,值得镌刻在哲学之城的每一面墙壁上,即不要阻碍探究之路。”正因为这样,任何“塑造绝对性断言”、“主张某种东西永远不可能知道”、“主张某种科学要素是基本的、最终的、独立于一切的”或“认为某种法则或真理已经获得最后的完美形式”的教条主义做法,都是思想上“一件不可宽恕的罪过”。④也就说,如果我们能从哲学上正确理解和发扬科学精神,可错论将是其中的首要意旨。“科学是活活生生的人的一种追求,其最显著特征是,真正的科学永远处于一种代谢和成长的状态。”⑤“没有什么比不可错论更彻底地同作为科学生活之产物的一种哲学相反对的了,无论它是穿着陈旧的教会服饰还是披着新近的‘科学派的’伪装。”⑥关于他自己的哲学形态,皮尔士坦言:“简单来说,我的哲学可形容为,一个物理学家,基于先前哲学家的成果,试图对于宇宙的构造做出科学方法所允许的一些猜测。……我所能做的顶多是提出一种假说,它不仅在科学思想成长的一般路线上不乏可能性,而且能够被未来的观察者所证实或驳斥。”⑦不仅是皮尔士,詹姆斯在《实用主义》一书中也谈及:“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一种观念占据上风,即我们的大多数甚或所有的规律只是一种近似”,与此相适应,实用主义在哲学气质上接近经验主义,它抛弃了“固定原理”、“封闭体系”等绝对性的东西,“意味着一种自然的开放空间与多种可能性,反对教条、人为性以及伪称的最终真理”。⑧杜威在《逻辑学》一书中,也指出:“确定性信念的获致是一件渐进性的事情;没有任何信念能够如此确定而不需要未来的探究。是持续性探究的会聚和累积的效果界定了知识的一般意义。在科学探究中,关于什么被作为确定的或作为知识,其标准的确定性是指它作为进一步探究的资源够用了,而绝不是指它在未来的探究中不会得到修正。”⑨在另一处,杜威更加直白地谈到:“科学并非由任何特殊的一组内容所构成。它是由一种方法构成的,这种方法借助于有检验的探究,不仅获致信念而且也改变信念。……把科学等同于一组特殊的信念和观念,这本身乃那些古老却仍旧流行的教条式思维习惯的一种延续,后者与科学实际相对立,是科学正要瓦解的东西。”⑩
第二,生活经验的流动和进化,使得人们对于经验世界的认识结果总是有待完善的。人类认识的对象是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并在生活中认识世界。实用主义在此种生活世界的意义上把“经验”作为“我们唯一的导师”、“最终的权威”。此种活生生的经验不同于传统经验主义的观念“经验”,也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的静止“经验”。它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同时又是认识成果的检验。它作为一种“事实”(out there)可以唤醒认识者的梦境,也可以强化认识者的信念。不过,由于此种经验是流动的、进化的,人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拥有全部的经验,经验的“沸溢性”(ways of boiling over)使得满足当前经验条件的信念并不必然同样地满足未来经验。(11)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那样一句传世格言,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Humanum est errare)。(12)“虽然我们可以获知真理,但我们不能不可错地知道何时获知。知道,是一回事,而肯定地知道我们已知道,却是另一回事。”(13)换句话说,“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在过程之中的,未来虽然与过去相连,却不是其完全的重复”,而又由于我们探究所用的手段总是现在所实有的,而探究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在未来,所以“在所资运用的手段与继后所出现的结果之间总是存在出入;有时,这种出入会很严重,导致我们所谓的过失和错误的出现。”(14)在这样的世界上,“任何人都应该时刻准备把自己满载的信念卡车倾倒出去,一旦有经验反对它们。对于学习的渴求使得他不能完全确信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实证型的科学只能依赖于经验;而经验从来不会导致绝对的确定性、严格性、必然性或普遍性。”(15)即便“在科学中常常要尝试来自本能的暗示,但我们只是对它们试用,将它们与经验比照,一旦有来自经验的通告,我们自身随时准备将它们推翻。”(16)“科学人根本不会执著于他的结论。只要有经验反对它们,他随时准备抛弃它们中的一个或全部。”(17)“我们不得不做的是,在今天依靠今天所能达到的真理,随时准备在明天宣布其为错。”(18)
第三,如果推理是人类认识的主要方法,那么有关经验事实的推理的或然性便决定了认识结果的可错性。古典实用主义者认为,探究是人类认识的本质所在,它以追求真理为目标,在推理形式上不仅会由作为规则(Rule)的大前提与作为个例(Case)的小前提通达作为某种结果(Result)的结论,而且会由既知的某种结果与某种个例通达作为规则的“大前提”,还会由既知的某种结果与某种规则通达作为个例的“小前提”。此种推理类型上的不同,用皮尔士的术语可分别表示为演绎(Deduction)、归纳(Induction)、外展(Abduction)。为了获得有关经验世界的某种知识,三种推理形式必须协同运作、循环推进,第一步:外展推理引入可能性的假说以供检验,第二步:演绎推理从假说推演出可检验的结果,第三步:归纳推理检验或证实它们。演绎,证明出(prove)某物一定是(must be)什么;归纳,显示出(show)某物事实上是(actually is)可行的;外展,建议(suggest)某物可能是(may be)什么。(19)光靠演绎推理,我们只能得出基于理想假设情况的数学判断,譬如,我们可以从数学上带着绝对的确定性讲“假若有2个人,而每1人有2只眼睛,那么就总会有4只眼睛”,但那不是事实问题,只是有关我们自己创设的数字系统的陈述。只有增加“房间里有两个人”、“每个人有两只眼睛”这样的经验事实,才算真正达到诸如“房间中有四只眼睛”一样有关真实世界的判断,但那样则必须运用到非演绎的或然性推理即归纳和外展。(20)换言之,数学上的那种必然性推理无法在我们的真实世界上独立而自足地运行,而以认识生活世界为探究目标的任何实际推理活动只能得出可错的结论。毋庸置疑,后者的推理同样追求某种意义上的确定性,但显然不是数学上那种绝对不可错的确定性结论。用杜威的话来说,虽然此种方法反对任何教条式信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关心真理。它代表对于那种获致真理之法的最高忠诚。”(21)
二 从反怀疑论的视角看:探究始于真实的怀疑
相比于教条论这种哲学上的宿敌,由于怀疑被认为是求知者的天性,怀疑论在历史上往往被视为哲学发展的推动力,或者至少与哲学的进步相伴相随。尤其是,在中世纪晚期,哲学家们把反教会权威作为自己的启蒙使命,并把怀疑精神奉为至上法宝。进入现代世俗化社会,笛卡尔提出的普遍怀疑原则,一度被认为是思想现代性的一个基本主张,“怀疑主义成为受教育阶层的标志甚或姿态”。(22)但是,当哲学家由反对教条论走向怀疑论时,当认识者由“相信过多”(over-belief)转到“相信不足”(under-belief)时,思想已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个死胡同。绝对怀疑论者如果主张“一切都是可疑的”,那么,该主张本身是否可疑呢?除非绝对怀疑论者不做断言,否则必然陷入一种自指性的矛盾。如果说此种形式上的悖谬阻止了常识健全的哲学家走向绝对怀疑论的话,古典实用主义者所要做的,则远不止这些形式指责。持有绝对怀疑论的哲学家毕竟只有少数,倒是各种类型的相对怀疑论极易以怀疑精神之名潜伏在许多现代哲学家的思想深处。古典实用主义在当时的怀疑论哲学家中看到了一种对于心灵诚正(integrity)毒害程度丝毫不亚于教条论的理智疾病,并从探究本性出发,做出了一种诊断和治疗。
第一,怀疑主义的普遍怀疑原则是行不通的。面对当时流行的普遍怀疑倾向,皮尔士直言:“我们不可能开始于完全怀疑。当我们踏上哲学研究时,我们必须以我们实际上已经拥有的所有前见(prejudices)开始。这些前见不能以一种准则而被驱逐,因为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们可被质疑。因此这种原初怀疑论只是自欺欺人,并不是真正的怀疑;追随笛卡尔方法的人,没有人曾感到满意直到他正式地重新获得所有那些他曾在形式上抛弃的信念。因此,那是毫无用处的一个预备行为,就像为了沿子午线逐渐到达君士坦丁堡,而跑到了北极去。的确,有人可以,在其研究过程中,找到理由来怀疑他开始时所相信的东西;但在此情形下他怀疑是因为他对于它拥有了一种实在理由,而不是根据笛卡尔主义原理。让我们不要在哲学上假装怀疑我们内心并不怀疑的东西吧!”(23)事实上,我们知道,即便是笛卡尔本人也做不到普遍怀疑,他不得不在“我思故我在”处停下。与皮尔士对于笛卡尔主义的批评相呼应,詹姆斯在《相信的意志》一文中对于当时流行的一种隐蔽怀疑论也提出了类似批评。这种怀疑论隐蔽在推理至上的笼统论调中,最早由于英国数学家克利福德(W.K.Clifford)的文章《信念的伦理学》而变得出名,即:“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基于不充分的证据而去相信某种东西都是错误的。”在詹姆斯看来,对于探究者来说追求真理是第一位的,防止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很多时候不可避免要相信一些东西,即便我们不具有清晰可鉴的推理过程,即便我们接受那些信念并不具有充分而不可动摇的证据,即便我们之所以相信它们主要是因为内心的一种情感或意志力。知错即改,相比“不犯错误”,应该是一种真正可行的人类德性。如果为了一劳永逸地避免错误而不相信任何东西,我们将无穷尽地把真理获知推迟下去。相比不自主地相信某种可错的东西,此种怀疑主义实则有着一种更大的风险,即“宁愿失去真理,永远不开始求真”。(24)虽然怀疑主义的方法与教条主义断言某种东西不可错因而不存在进一步探究的空间不同,但由于它如同布里丹之驴一样,止步于无尽的怀疑,无法达到任何信念,从根本上就没有让探究开始,与前者一样违反了“不要阻碍探究之路”这一理性原则。从自由探究的科学精神来看,倒是一开始的冒险不足为惧:正如皮尔士所言,“虽然我们在研究中最好讲求方法,而且要考虑上研究经济论(the Economics of Research),(25)然而,对于我们所想到的任何理论加以尝试,只要它在被接受时能够允许我们的研究继续畅行无阻,这在逻辑上是不存在任何过错的(no positive sin against logic)。”(26)甚至可以说,“接受对我们看起来非常明显的命题,是一件不管是否合乎逻辑我们都不能不做的事情。”(27)
第二,如果仅凭个人意志力去怀疑,那只能是虚伪的怀疑,并非真怀疑。通常,如果有人说相信了并非他从内心真正相信的东西,我们会认为这个人是虚伪的。其实,从哲学上讲,所谓虚伪并不限于“信念”,不仅存在虚伪的信念,同样也存在虚伪的怀疑。而且,由于近代以来哲学家对于中世纪权威高举理性的批判旗帜,把怀疑精神推向极致,似乎“怀疑即有理”,因此,在古典实用主义看来,分清什么是真正的怀疑、什么是虚假的怀疑,倒显得更加紧迫。“许许多多的哲学家似乎都认为,只要拿一张纸写下‘我怀疑什么什么’就等于在怀疑了,或者认为,怀疑这种事只要他决定想要怀疑什么,一分钟之内就可以做到。笛卡尔曾让自己相信,最可靠的办法是‘从一开始’就怀疑一切,他还告诉我们,他直接就照那样做了,除了他借自圣奥古斯丁的那句‘我思’。但我猜情况不会是那个样子;因为真实的怀疑不会讲一开始就怀疑。实用主义者知道,怀疑是一种必须很努力才能获得的能力……”(28)脱离经验的、无关生活的怀疑,并非真正的怀疑。“真实的怀疑总是要求有外部源起,通常源于惊奇;一个人足可以用一种意志行为设想数学定理的条件,但是他不可能单凭这样的意志行为就为自己创造一种真实怀疑,这就像他不可能单凭意志行为就能给自己带来真实惊奇一样。”(29)詹姆斯在《信念心理学》一文中发挥了皮尔士关于怀疑真伪的区分,他说:有一种病态的怀疑可称为“质疑癖”(德国人所谓的Grübelsucht),是指“不能够信赖任何想法,总是要求它被证实或解释”;“我们感觉所想到的某种东西不真实,这只能出现在那个东西与我们所设想的其他某个东西相抵触时。……任何对象只要一直未有相抵触的东西出现,它就因此被相信了,并被设定为绝对真实的。”(30)同样,在杜威那里,也有着类似的说法。他指出,我们之所以怀疑一定得是因为我们所在的情境具有内在的可疑性,(31)“凡是未由某现存情境唤起或与某现存情境无关的个人怀疑状态都是病态的;当它们走向极端时,就患上了怀疑癖(the mania of doubting)。”(32)当然“存在大量的特定问题,对之我们必须说不知道;我们只是探询并提出一些未来探究将能予以证实或驳斥的假说。但此种怀疑是伴随对于智力方法的信任而来的。它们标志着一种信念,而不是苍白无力的怀疑主义。”(33)
第三,无法根据既有经验进行怀疑的东西是探究由以开始的信念,它们使得后来的真怀疑成为可能。但凡真实的怀疑,总是先有某种信念开始的。推理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可控过程,只是获得新信念的方法之一,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得到信念并非是由于有意识地采取某些证据作为前提进行推理所致,而是由于那些并非称为推理的无意识的、无批判的推断或联想所致。更重要的是,即便推理也得从既有的知识或信念出发,“推断由以开始、所有推理都依赖的那些事实资料(data)是知觉事实(perceptual facts),它们是理智对于觉知(percepts)或‘感官迹象’(evidence of the senses)的可错性记录。”(34)这些觉知以及知觉事实并非可以从逻辑上评价对错好坏的对象,因为它们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但它们却是我们推理赖以进行的重要基石,而且正因为它们本身是感官知觉的本能所得,最起码在当时它们对于推理者是绝对信赖、不受质疑、无所谓好坏的“信念”。这样说,并不否定这些我们在当时无法怀疑的“信念”能够在后来变成需要经过推理才能消除怀疑的东西。“但是,只要我们是不禁接受了一种思想状态,它就必须被彻底地接受为真。任何对于它的怀疑都是无用的伪装与无法兑现的纸币。”(35)除了来自个体知觉上信念来源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无法根据既有经验进行怀疑的东西,它们同样构成了信念的来源。这些东西是“我们有关万物的根本思想方式,是远古祖先们的发现,它们能够历经所有后来的经验而保全自身。它们构成了人类心灵发展的一个伟大的均衡阶段,即常识阶段。其他的阶段均嫁接于这一阶段,但从未能取代之。”(36)这里所谓的常识,既包括历时性的“传统”,也包括共时性上的“共识”;不仅适用于日常生活,同样适用于科学研究中:“在达成共识的各种科学中,当一理论被提出后,它只被视为是试用的直到人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在达成一致后,确定性问题就变得无用了,因为没有什么人还怀疑着它。我们个人不可能有望达到我们所追求的最终哲学;因此,我们只能为着哲学家共同体而追寻。”(37)这种对于共同体、传统信念的态度,蕴藏着古典实用主义者有关我们人性的一个重要思考,即:“生活于现在的我们是伸向遥远过去的人性的一部分,这种人性与自然相互作用。我们大多数人为之骄傲的文明事物并不属于我们自己。它们的存在归因于连续不断的人类共同体的所为所受,我们只是这个共同体的一个环节。我们的责任是保存、传播、调整、拓展我们所接受的那些价值遗产,以便我们身后的那些人在接受这些遗产时能够比我们更加安全可靠、更加广泛可得、更加慷慨分享。”(38)
三 实用主义准则:一种绝非松散而是最严厉的逻辑规范
如果说教条主义和怀疑论分别代表着现代哲学中的两种“不良”极端的话,同时反对教条主义和怀疑论的古典实用主义显然走在了一条所谓“可错论”的中间路线上。沿着这条稳健的中间路线,我们看到:古典实用主义者相信真理可以达到,而且我们拥有很多有价值的信念,但基于内在的反教条论态度,他绝不会把某种知识绝对化进而停止探究,倒是随时准备在未来经验面前修正已有的信念;古典实用主义者会有“所有命题都是可错的”之类的非教条信念,但是,本着反怀疑论和反教条论的精神,他不会陷入类似绝对怀疑论一样的悖谬,即,“‘所有命题是可错的’是可错的”是不可错的。
也正是从这条中间路线出发,我们看到,皮尔士对于苏格兰常识学派持有同情态度,但深知:虽然我们具有毋庸置疑的信念作为出发点,它们却都具有极端模糊的特征,因此,怀疑的空间总是可能的,在此意义上他用“批判的常识论”(Critical Common-Sensism)来描述自己的“可错论”哲学。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詹姆斯持有明显的多元论立场和所谓的极端经验论,但如果是在他的实用主义可错论视域下来理解,它的实用主义就不会因此而等同于任何其他版本的经验主义(包括逻辑经验主义),而且也不会从多元论而走向相对主义。此外,杜威的哲学很多时候与民主理论联系在一起,但如果能够从可错论的视角解读杜威实用主义,我们不难发现,他所谓的“合作”、“自由”、“民主”等首先是有关自由探究的认识论概念,它们在政治意义上的所指完全源于认识论上的可错论。
古典实用主义既反对怀疑论又反对教条论的可错论原则,作为一种理论要旨,主要体现在所谓的实用主义准则,即以面向未来的实际效果而非既成的(过去或现在)某种东西作为判定我们观念合法性的依据。一方面,正是因为反对教条论,古典实用主义认为任何超出生活经验之外的标准都是无效的、非法的,任何知识或信念的意义,一定要放在“经验”域中去把握。“不是任何特殊结果,而只有倾向性态度,才是实用主义方法的意指。那种态度就是,不理会第一事物、原理、‘范畴’、假想必然性,而面向最后的东西、果实、结论、事实。”(39)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反对怀疑论,古典实用主义认为虽然没有绝对的确定性,但我们还是可以使得我们的观念明晰。正如皮尔士在《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明晰》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可能通过笛卡尔所谓的理性直观来把握“clear & distinct”的观念,但如果引入实用主义准则,我们便可以通过诉诸概念的实际效用(用法),通过面向未来行动的推理,获得一种更为高级的明确概念之法。(40)但是,正如对于任何其他所谓中庸之道的态度一样,至今依然有人认为,此种体现可错论精神的“实用主义准则”是无原则的“主观随意性”。因为他们担心“效果”会成为一种心理学上的私人东西,从而把实用主义引向心理主义陷阱,即只关注人的实际思维过程如何,而缺少思想本身所应具备的那种客观规范性。
这是一种并不怎么新鲜的对于实用主义的批评,早在实用主义学说问世之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指责。然而,笔者要指出:此种指责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完全不适用于古典实用主义的理论。由于古典实用主义者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方面的误解并作出了足够澄清,我们在这里不妨重新引用。首先是皮尔士。他原本就是著名的反心理主义者,针对当时德国逻辑学家把合理性(rationality)作为一种主观趣味的观点,他曾特别强调:“每一推理都提出有某种期望(expectation)。……如果事实支持它所做的允诺,那么……推理就是好的。而如果事实与允诺相背,推理就是坏的,不论人类理性已经如何存心地赞成它。因为推理的唯一意图不是满足类似于趣味或良心的有关合理性的感觉,而是探明真理……”(41)然后是詹姆斯。面对不少学者对于“实用主义”不求甚解的无礼驳斥以及他们所谓“实用主义放弃客观标准、过于变通随意”的诽谤性言论,他曾断然指出:“实用主义者比其他任何人都自认为受困于过去整个固定真理体的挤压与他周围感觉世界的强力之间,有谁能像他那样感到我们心灵运作所受到的客观控制的巨大压力呢?如果有人以为此种法则是松弛的,那就让他服从此种律令一天试试看……”(42)还有杜威,针对罗素曾指责他把个体满足作为真之基准以及最终的探究目标,他不无愤怒地作出回应:“罗素先生先是把怀疑情境换为个体怀疑……然后把怀疑变成个人不适,由此把真理等同于此种不适的消除。按照我的观点,唯一涉及的渴望是渴望尽可能诚实而公正地解决当下情境中的那个问题。所谓‘满足’乃对于问题所规定的那些客观条件的满足。个体满足仅在一开始时涉及,就像根据工作要求完成了某项工作任务一样;但它绝不会影响对于有效性的确定,因为,倒是那种确定性制约着它。”(43)“实用主义的批判家们令人吃惊所一致忽略的一点是,在重新解释知识之本性和功能时,实用主义必然彻底地重新解释所有那些认知机制。”(44)
需要在本文语境下予以补充的是,实用主义准则之所以有所谓“主观随意性”的误解,主要是各路批判家没有将实用主义准则放在可错论视域下进行适当理解。如果我们记得实用主义的可错论同时反对教条主义和怀疑论,就应该意识到:实用主义既不会像怀疑论者那样怀疑一切规范的可行性,也不会像教条主义者那样提供什么绝对不可错的教条。实用主义准则强调:我们连续不断的生活经验是唯一的权威,我们必须根据我们人类的可能行动及其效果来获致我们自身观念的意义,除此之外不存在任何所谓的“标准”,但是,“经验的权威”并不等同于任何个人的权威。经验世界当然是包含人的活动在内的世界,但人在此种世界上绝非毫无限制,这里存在着英国实用主义者席勒所谓的“构筑世界”(make our world)与“创造世界”(create our world)之间的区分:正如木匠并非凭空制造一把椅子一样,“我们不是凭空构筑实在……我们不是‘造物者’(creator),我们的力量是受限制的”。(45)如果我们意识到经验本身永远包含着难以驯服的野性、外在性或曰偶然性,就会发现:实用主义准则绝非松散,而是最为严厉的规范。
四 结语:行走在可错论之路上的当代实用主义
总而言之,美国古典实用主义者皮尔士、詹姆斯、杜威从“可错论”这一看似负面或阴暗的因素中找到了人类思想认识的新路径,那就是实用主义准则。古典实用主义的可错论同时具有反教条论与反怀疑论两种倾向,这使得古典实用主义走在了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上;与此同时,可错论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科学与常识、宗教之间的联系,因而使得古典实用主义在哲学气质上一方面体现出整体性、动态性、连续性,另一方面体现出多维性、非线性、相干性。几乎可以说,古典实用主义中的其他重要主题,如激进经验论、反基础主义、批判常识论、连续主义、工具主义、经验自然主义以及各种其他具体论点,要么是对于可错论的直接解读,要么是由可错论所产生的应用结论,要么就是为证明可错论而申明的一种前提预设。
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实用主义可谓方兴未艾,正在经历所谓的“第三次浪潮”。(46)有必要指出,这种思潮发展至今,可错论依旧是众多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核心论题,也就是说,实用主义依旧行走在可错论之路上。正如美国当代实用主义者伯恩斯坦所言,“批判的实用主义可错论不仅代表了美国传统的精华,而且具有全球意义。”(47)但是,近些年,随着各种版本“新实用主义”的出现,实用主义似乎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上:古典实用主义是否依然具有足够的理论吸引力,是要抛弃还是继承?(48)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关乎实用主义的发展前途,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必须回到另一个问题,即作为实用主义之精髓的可错论,在皮尔士、詹姆斯、杜威那里是否与在奎因、罗蒂等人那里有着相同的涵义?与之相连的另外两个问题是,古典实用主义可错论与欧洲世界波普所谓的可错论有何异同?皮尔士、詹姆斯、杜威他们各自对于可错论的意谓在共同主张之外又有哪些不容忽视的差别?这些都是可以在本文基础上继续探究下去的问题。
注释:
①C.S.Peirce,The Essential Peirce,Volume 1,edited by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J.W.Kloesel,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2,pp.118—119.
②James and Dewey on Belief and Experience,edited by John M.Capps and Donald Capp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5,p.102.
③CP 1.57.本文采取皮尔士文献的通用记法,CP代表Collected Papers of C.S.Peirce,v.1—6 ed.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v.7—8 ed.Arthur Burks,Cambridge:Haward,1931—1958,并以圆点前面的数字表示卷数,后面的数字表示节数。
④C.S.Peirce,Reasoning and the Logic of Things:The Cambridge Conference Lectures of 1898,edited by Kenneth Laine Ketner,Harvard,1992,pp.179—180.
⑤CP 1.232.
⑥Cornelis de Waal,On Peirce,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2001,p.39.
⑦CP 1.7.
⑧William James,Pragmatism,Dover Publications,Inc.,New York,1995,pp.20—22.
⑨John Dewey,The Later Works,1925—1953,Vol.12,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rnest Nagel,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2008,p.16.
⑩James and Dewey on Belief and Experience,edited by John M.Capps and Donald Capp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5,p.241.
(11)(18)William James,Pragmatism,Dover Publications,Inc.,New York,1995,p.86; p.86.
(12)CP 1.9.
(13)James and Dewey on Belief and Experience,edited by John M.Capps and Donald Capp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5,p.101.
(14)John Dewey,The Later Works,1925—1953,Vol.12,editedy by Jo Ann Boydston,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rnest Nagel,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2008,pp.45—46.
(15)CP 1.55.
(16)CP 1.634.
(17)CP 1.635.
(19)C.S.Peirce,The Essential Peirce,Volume 2,edited by Peirce Edition Projec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p.216.
(20)CP 1.149.
(21)(22)(24)James and Dewey on Belief and Experience,edited by John M.Capps and Donald Capp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5,p.241; p.224; pp.95—110.
(23)C.S.Peirce,The Essential Peirce,Volume 1,edited by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J.W.Kloesel,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2,pp.28—29.
(25)参看拙著《皮尔士哲学的逻辑面向》第五章第三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26)C.S.Peirce,Reasoning and the Logic of Things:The Cambridge Conference Lectures of 1898,edited by Kenneth Laine Ketner,Harvard,1992,pp.179—180.
(27)C.S.Peirce,The Essential Peirce,Volume 1,edited by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J.W.Kloesel,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2,p.126.
(28)CP 6.498.
(29)CP 5.443.
(30)(33)James and Dewey on Belief and Experience,edited by John M.Capps and Donald Capp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5,pp.60—62; p.249.
(31)关于杜威所谓“不确定情境”的真实所指以及如何把杜威的意指与可能的误解区分开来,可参看Richard M.Gale,Russell's Drill Sergeant and Bricklayer and Dewey's Logic,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56,No.9,1959,pp.401—406。
(32)John Dewey,The Later Works,1925—1953,Vol.12,edited by J.A.Boydston,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6,p.109.
(34)CP 2.143.
(35)CP 8.191.
(36)William James,Pragmatism,Dover Publications,Inc.,New York,1995,p.65.
(37)C.S.Peirce,The Essential Peirce,Volume 1,edited by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J.W.Kloesel,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2,p.29.
(38)James and Dewey on Belief and Experience,edited by John M.Capps and Donald Capp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5,p.249.
(39)William James,Pragmatism,Dover Publications,Inc.,New York,1995,p.22.
(40)关于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更多可参看拙文《皮尔士实用主义的逻辑学语境》,刊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9期。
(41)CP 2.153.
(42)William James,Pragmatism,Dover Publications,Inc.,New York,1995,p.90.
(43)John Dewey,The Later Works,1925—1953,Vol.14,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W.Sleeper,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2008,p.56.
(44)John Dewey,The Realism of Pragmatism,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Vol.2,No.12,1905,p.326.
(45)F.C.S.Schiller,Humanistic Pragmatism:The Philosophy of F.C.S.Schiller,edited by Reuben Abel,Free Press,1966,p.146.
(46)有关哲学史上三次实用主义浪潮的叙事,参看Joseph Margolis,Pragmatism's Advantage:American and European Philosophy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47)Richard J.Bernstein,The Pragmatic Turn,Polity Press,2010,p.30.
(48)Nicholas Rescher,Pragmatism at the Crossroads,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Peirce Society,Vol.XLI,No.2,2005 Spring,pp.355—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