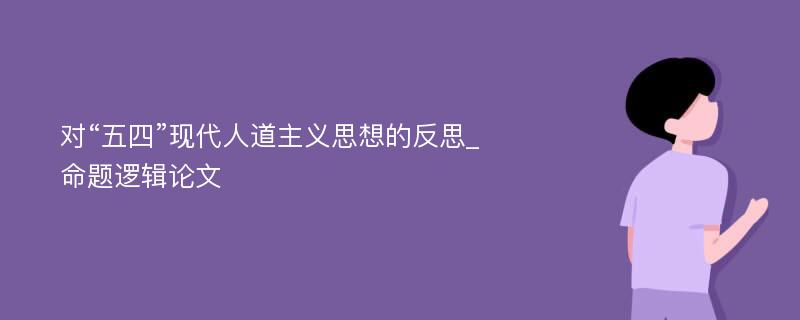
“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观念的当下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道主义论文,观念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0)01-0013-05
反思“五四”的思想资源,对当下极为必要,这是因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没有真正结束,由此“五四”的任务就没有完成,“五四”并未成为历史,成为过去,它所具有的意义,就当下的中国而言,既不是它的象在意义、符号意义,也不是它的纪念意义,而是其巨大的现实意义,它仍是活态的思想库。之所以要对“五四”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主要是缘于,包括“五四”在内,从辛亥革命到上世纪中叶,国人在引进西学的同时,做出了大量的思想创新,其中不少新的思想观念早已成为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主要根基,还有很多观念也蕴含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对未来的中国有着特殊的意蕴,特别是“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观念,在“五四”的思想资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包括“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观念在内的这些活态的资源,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及历史主义的客观评价的同时,更需要站在当下社会发展、思想发展的立场上,考虑如何活用这些资源,并将其纳入到新的思想生产与社会变革当中。要实现此目的,首先需要,从当下的社会需求出发,对这些思想资源作出一定分析反思。本文力图从三个方面,对“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观念进行反思。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观念自出现之日起,便不断地遭到质疑,并受到过严厉批判,甚至这一观念的重要理论代表也曾做出过严肃的自我批判,笔者以为,这些思想资源也应在我们当下的思考中得到充分的重视与考量。
一、关于人道主义社会改造观总原则的内在矛盾
“五四”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观的总原则就是“爱的哲学”观,主张以“爱”的力量,而不是暴力、反抗的方式,彻底解决人类问题,实现世界的大同。“爱的哲学”是“五四”现代人道主义长期被各种政治力量攻击的核心所在。这些批判与思考,尽管有其合理之处,但这些批判者们往往都是急于划清界限,并大多习惯站在自己立场,高高在上地审判,很少会居于“同情的理解”的位置去深切体察,挖掘“爱的哲学”的合理内核。因此,笔者对于这些否定攻击的言论一直深表怀疑,认为倘要真正反思这一观念,以冀对当前产生效应的话,与其接受这些盛气凌人的裁判,反倒不如去回顾现代人道主义者自己对“爱的哲学”内在矛盾的深入思考更为有益。
现代人道主义者在发展“爱的哲学”观念的同时,也意识到了“爱的哲学”观念,以及以其为基础建立的社会改造观本身存在着一些理论与实践困境,如“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最为关注的“憎”与“反抗”的命题,这一难题曾令许多人道主义者困惑,他们做出了以一下思考:
其一,某些人道主义者对“爱的哲学”及“无抵抗主义”发出了质疑。这些人道主义者提出了“憎”的存在,他们认为,当面临严重暴力事件及社会不公时,在人的心中“憎”是不可能不出现的,鲁迅在介绍阿尔志跋绥夫对托尔斯泰“无抵抗主义”的强烈反拨时就曾着重强调,“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也就是说,“爱”虽如“无抵抗主义”者所说是人的本能,但“憎”也同样会是善良人的天性。因此在一些人道主义文学家的作品中,与“无抵抗主义”所宣扬的由“爱”发出的不服从相对,出现了由“憎”发出的不服从的行为,这以阿尔志跋绥夫的《医生》为代表,医生拒绝拯救虐杀犹太人的警厅长;在有些作品中,“憎”甚至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如在梭罗古勃的《童子Lin之奇迹》中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幕“憎的奇迹”。对于这种“憎”的存在,鲁迅指出,它虽然有违“元抵抗主义”的宗旨,但仍没有偏离“爱的哲学”的核心——“爱”。其原因在于,第一,在鲁迅看来,就思想根柢而言,以医生为代表的人道主义者并未脱离“爱的哲学”的要求,他们的心理动机仍是“爱”,最终的目标也依然是人类爱的实现,况且他们往往是因为大“爱”才去深“憎”的,即他们所表现出的“憎”仍源于“爱”。他们甚至比一些纯粹的“无抵抗主义”者,怀有更宽厚、深沉的博爱之心。对此鲁迅曾做过较为圆满的解说:“这僧,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1]照此理解,《医主》中为反抗正是根植于更广大的爱,因为医生了解到他以前治愈的商人墨斯科皤涅珂夫积极鼓动、出资屠杀犹太人,于是他认为自己也对屠杀暴行负有一定责任,他觉得“倘那时我不曾医好他”,“现在就许要多活出几十个人”,[2]因此这次他为了更多人的生命,拒绝疗救恶人。而《童子Lin之奇迹》中除“恶”务尽的决心,表达的还是希求“完全的解决”,[3]期盼人间“爱”的实现的急迫心理,因此小说中的“憎的奇迹”实际上是别一种意义的“爱的奇迹”。第二,从《童子Lin之奇迹》与《医生》两部作品看,阿尔志跋绥夫们仍然是不赞成“以暴易暴”的,因为即使是在这两部态度如此激烈的作品中,他们也并未主张采取任何暴力方式,他们所赞许的医生和童子Lin所做的,只是基于“憎”的不服从,以及对施暴者灭亡的诅咒,并没有任何付诸行动的反抗。所以在鲁迅看来,阿尔志跋绥夫们终究“仍然不免是托尔斯泰之徒了,而又不免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反抗者,——圆稳的说,便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调剂者”[1],从根本上讲,他们始终没有离开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的根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无抵抗主义”进行了“调剂”。
发出这些质疑声音的现代人道主义者,往往会遭遇“爱憎的纠缠”的心理困境。虽然鲁迅为“憎”的心理反应寻找到种种理由,并说明其本质并未偏离“爱的哲学”,但对于当事人而言,当难以遏制的仇恨、憎恶充塞心胸,并欲将反抗落于实处之时,他们确实会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仇恨与反抗的欲望是对“爱的哲学”的巨大悖逆(因为虽然他们的动机与目的仍是“爱”,但他们所发出的“憎”的情感,与欲做出的反抗,毕竟不是爱,而是仇恨与暴力),毕竟他们仍是“爱的哲学”的忠实信仰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很难自圆其说,而且个体精神内部的矛盾、纠缠也难以避免。鲁迅说《医生》就“简单明了的写出了对于无抵抗主义的抵抗和爱憎的纠缠来”,[1]而《工人绥惠略夫》、《灰色马》等作品更表现出了这种“爱憎的纠缠”的精神悖论的深度。在这些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就是一幕幕激烈的心理交锋,其中不仅包括人物自身的心理斗争,有些作品还将这种个体精神的心理纠缠外化为人物之间的观念冲撞。经过反复的心理交锋,某些人道主义者暂时找到了圆满的解决方法,比如在《医生》中,医生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激战,最终肯定了基于“爱”之上的“憎”的合理性,小说描绘了他在寻找到出路时精神的畅快,“这刹时他尝着甜美的复仇的感觉,一切道德的苦痛的出路,以及从他全生涯中抢去了欢乐的,气厥的愤怒的出路,是寻到了”[2]不过与医生相比,更多人面对这一矛盾时,依然是在困惑,他们在精神痛苦中继续挣扎。爱与憎的心理纠缠在鲁迅所译的《工人绥惠略夫》里达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激烈程度,而且阿尔志跋绥夫在这部作品中对此问题的思考异常深刻,已经深入到了对诸如人性善恶、人类生存意义等终极问题,改革者与不幸者关系的悖论问题、牺牲与生命孰轻孰重等重大命题思考当中,这是很多普通的人道主义者都无法达到的深度。
其二,他们开始宣扬实际的“反抗”。这在安德列夫对一战中“比利时的义战”的肯定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对此沈雁冰在《欧洲大战与文学》中有过专门介绍,
伟大的安特莱夫曾经做了两部书很受世界的欢迎。《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忏悔》是一部日记式的感想录,《比利时的悲哀》是一篇戏曲。非战的色彩,在前者尤其浓厚;后者是赞美比利时民族的英雄。安特莱夫和其余大多数的俄国文学家一样,是同情于被压迫被侮辱的人们的,他赞美比利时,完全基于这一种心情。他果然也反对战争,但是并不十分反对自卫的或抵御强暴的战争;在他看来,俄国的加入战团是无理由的,应该反对的……但是像比利时那样的战争是可敬的,应该赞美的。这是安特莱夫对于大战的态度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在《比利时的悲哀》中,安德列夫通过描写著名学者爱米尔·葛雷罗由主张和平主义到积极反战的心理转变过程,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沈雁冰描述爱米尔·葛雷罗“本来是反对杀人的,但为抵抗强暴与反对破坏文化的恶魔起见,也赞成杀人了”,沈雁冰认为,“这是葛雷罗良心的呼声,也就是安特列夫良心的呼声。安得列夫也和俄国其它作家一样,常同情于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他反对侵略的战争,故有《红笑》之作,然而他赞成自卫的战争,《比利时的悲哀》就是站在这个论点上”。[4]阿尔志跋绥夫在《工人绥惠略夫》中对改革者的“反抗”与暴力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究,始终坚持“无抵抗主义”的亚拉藉夫,为销毁民意党的秘密材料,与警察枪战而死,他显然违逆了“无抵抗主义”的教义,使用了暴力;[5]从表面看起来,绥惠略夫已经远离了人道主义的原则,并且走向了极端,他本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6](20)应该说,即便从“调剂”过的“爱的哲学”来看,绥惠略夫、亚拉藉夫,以及爱米尔·葛雷罗也都远远地越过了人道主义观念的底线,但在鲁迅、沈雁冰等看来,他们总的精神仍是在人道主义光辉的照耀下,不仅人道思考仍是他们思考现实的精神背景,而且他们的一切行为、选择也都未尝离开对人类的爱:安德列夫反对战争,是基于对“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的同情,而他赞美自卫的战争与反抗强暴的暴力,也是基于这种同情,这就说明他所肯定的“反抗”,仍是出于“爱”而做出的选择;亚拉藉夫正如鲁迅所说,“虽然不能坚持无抵抗主义,但终于为爱做了牺牲”,[5]绥惠略夫一切行为最核心的根源仍是对人类热切的“爱”,爱而不得引发的强烈憎恨正说明了本来爱的深厚、强烈。因此,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他们“仍然不免是托尔斯泰之徒”。[1]
应该说,这些人道主义者对“爱的哲学”的理论与实践困境的反思,是极为深刻的,是基于对人类的更大的爱的思想探求,而且对人性及社会改造等问题的思考已经达到了相当深入复杂的层面。更重要的是,从此思考出发,寻找当下社会改造的新思路,必定会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二、关于人道主义社会改造观的理想主义特质
“五四”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及理念建构的理想主义特质,自“五四”落潮后,便逐渐遭到愈来愈严重的否定与深刻反思,这里不仅包括从20年代中后期革命文学观兴起迄今,革命意识形态的裁断及审判,而且还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道主义信念最为坚定的普通知识分子群体的反省、质疑,“五四”现代人道主义的理论代表之一周作人就有过很多重要的思考,其中1924年前后的思考最为集中,也最为深刻,他对“五四”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观的理想主义内核进行了较为彻底的解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在表明启蒙主义的理想主义预设的虚妄,并提出“教训之无用”的重要命题。1924年2月25日周作人发表《冤哉达尔文》,说自己“相信人类的行为不是轻易容易改变的,圣道不能使它变好,邪说也不能使它变坏”,[7]对此,他在第二天发表的《教训之无用》中又引用了蔼理斯的话加以说明:“在群众的坚固的大多数之进行上面,无论是甲种的书或乙种的书都不能留下什么重大的影响”。很显然周作人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出了“教训之无用”的命题,用来否定先前的“教训有用论”。紧接着周作人为“教训之无用”的观点提供了证据,周作人很明显是借用了蔼理斯的理论,蔼理斯认为“教训之无用”与人类社会存在的普遍事实有关。蔼理斯认为在社会上只有少数的精英分子能够进行创造性的思想、道德的创造与探索,这种创造与探索往往超越社会现行的道德规范与思想原则,甚至与之针锋相对;而广大群众只会盲目从命,严格遵循现实既定的僵死的道德规范与思想原则,丝毫不懂得创造。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普遍事实。从这一判断出发,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这种社会现状之下,广大群众是不太可能接受少数精英分子的思想与道德的创造的。除了这个证据之外周作人还在人类历史中寻找到了证据,他在《教训之无用》中列举出一些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他说:“希腊有过梭格拉底,印度有过释迦,中国有过孔老,他们都被尊为圣人,但是在现今的本国人民中间他们可以说是等于‘不曾有过’。我想这原是当然的,正不必代为无谓的悼叹。”[8]应该说这些人物在他们本国都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但在二千年后的今天,他们的思想在本国民众的精神中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看来“教训之无用”在人类历史上是具有一定必然性的客观事实,因此周作人说这些伟人教训之无效“原是当然的”,不必代为叹息,这种叹息反倒是无谓的。
其二,是从怀疑主义的立场,对理想主义作出彻底否定,将其归为狂信。周作人到了1924年最终完全否定了那种认为可以对国人进行思想、道德启蒙的信念,认为它们全是乐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东西,他称其为“单纯的信仰”或“固执的偏见”。[9]他不但希望从根本上排除自己精神世界中存在着的缺乏现实根基的乐天主义与理想主义信念,并且希望能够保证自己不再接受其他理想主义的“单纯的信仰”,并不再重犯这种不应犯的错误,他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在周作人看来,自己之所以曾经那样确信过这些理想主义信念,其症结在于自己的思想出了问题。他是从自身对那些信念以及以前的信仰的接受方式上开始进行反思的。周作人对他接受这些信念的过程是这样描述的:“在古今的贤哲里找到一位师傅,便可以据为典要,造成一种主见,评量一切”,很明显周作人在这一过程中对这些观念缺乏充分的怀疑的审视,他认为这种无怀疑的接受显然不可靠,自己之所以能犯盲目信仰的错误,原因就在于自己还缺乏彻底的科学态度,即科学家研究的态度。所以周作人认为必须提倡彻底的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不再犯盲目信仰的错误,并能在思想中排除不切实的成分。如果我们要解释周作人所说的科学态度的含义,首先我们必须说明周作人提出这一命题的思想根据。对此,周作人在《一年的长进》(1924.2.13)中有所说明,在该文中周作人说每日看报时,“实在总是心里胡里胡涂的,对于政治外交上种种的争执往往不能了解谁是谁非,因为觉得两边的话都是难怪,却又都有点靠不住”,[9]这种说法其实与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所总结的怀疑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此原则即为,“任何命题都有一个相等的反命题与它对立。我们相信,根据这条基本原则,我们就能够避免独断”[10](657),是早期怀疑派的观念。怀疑派反对独断论者的武断,独断论者坚信自己对于事物的认识以及自己的观念是唯一真实的,而别人的则是不正确、虚假的,针对独断论者的这种观点,怀疑派提出:任何一个命题都有反命题与之对立,而正反命题分别都有自己一套说得通的道理,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独断地作出判断,而且对于相对立的正反两命题,我们实际上应该做到,在这两者之间不置可否,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也不能够知道哪一项是正确的”,[11]周作人借用的正是这一基本原则。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周作人虽然借用了怀疑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但他并没有接受怀疑主义的所有结论,他既没有否定人的理性与感觉的可靠,也没有像古代怀疑论者那样对一切问题不置可否,不作判断,周作人的怀疑观念至多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可知论。不可知论者虽然认为我们无法认识现象之后的本质——“物自体”,但是他们认为我们能够认识现象,而且认为人类的理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信任的,因而科学知识也是确实可信的。周作人借用怀疑主义这一基本原则的目的仅仅是用它来反对现在的“独断论”与“独断论者”。他认为,确信自己的意见是绝对正确而且是唯一正确的这种独断态度是靠不住的,因为每种意见都有相反的见解,这说明正反命题都有可以信任和值得怀疑的地方。因而周作人认为科学的态度应该是,首先要宽容地承认各种不同意见都有存在的必要,然后在此前提下对各种意见平等地加以怀疑的分析审视,他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排除虚假的认识,获取真知;而与科学的态度相反,人们如果不顾任一命题都有相反命题这一客观事实而偏信正反命题中的任何一方,就只能是“狂信者的态度”,而攻击异端正是狂信的另一面,周作人认为狂信与攻击异端都是绝对不可取的。[12]
在经历近百年理想主义追求的历程后,今天的人们回过头来看周作人的这些反思,不能不承认其思考的深刻性,当我们反思人道主义观的理想主义设想时,他所提出的这个思考角度,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才能避免那种单纯以成败论是非的,批评理想主义社会改造观念的滥调,因为那些论调同样是“狂信者的态度”。
三、关于人道主义科学“人学”观建构潜存的内在矛盾
“五四”现代人道主义的“人学”观,是对现代中国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观念统系,这种观念的终极目标,是建构理想的人性及人类的正当生活,一言以蔽之,就是灵肉一元的“人”的本质及“人”的生活的建构。现代人道主义的人性观,就是现代“灵肉一元观”,这种观念认为,人的“肉”的生活与精神生活原为人性一体之两面,两者本质上应该是和谐的,共同建构起人类正当的生活,任何片面发展其中一端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均会导致人性的偏至发展,并将人类的道德生活引向歧途。这一观念是19世纪道德革命的重要理论结晶,既称为“科学”,其原因在于,现代人道主义者们力图将这种“人学”观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所以它存在的问题也就基本集中在其科学构想中潜存的深刻的内在矛盾。
论者暂撇开别的问题不论,单考察“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对于“灵”、“肉”关系问题的论证。应该说,这一理论建构是艰难的,存在着一些难以逾越的理论困境,首先,它既要满足经验科学归纳实证的要求,又要遵循“二希”理论框架内理论演绎的规则,但是这两者并不相互包容。其次,这一理论要求,统括所有人的生活,将其全部纳入两重的生活当中,而论证所有生活现象都必须在进化论为基础的生物学上寻找有力的依据,局限于这样一种狭隘的理论要求,却要解答如此复杂的人的本质问题,应该说,这种力求面面俱到的理论构想确实难以做到。
另外,这种理论构想存在着相当大的理论解释的局限性:一方面,人类已经远远超越本能生活,有了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与文明创造,已经很难找出很多精神存在、道德存在、制度存在等最初的生物学起源,而且追溯这种人类行为的生物起源对于很多“内面生活”的改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毫无必要,更不用说还有很多“内面生活”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生物学的起源。另一方面,完全以生物学等科学为基础的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难以解释自由意志等超乎经验领域的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这是经验主义哲学家以及极端的科学主义论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但以“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为代表的部分科学主义论者认为,这部分的人的“灵”的生活完全可以用人的动物性的经验生存来解释,从他们自己的表述看,他们从理论上也确信自己能够自圆其说,可是实际上他们对此问题根本无从解释。应该说,这种力图以科学解释,以至解决人的所有问题,甚至包括道德问题、超越性精神问题的努力一个世纪以来影响甚广,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很多现代文明的反思者就已经指出,这种努力虽然十分真诚却又过于自负,这种思考不仅在当时就已露出破绽,不断遭到分析哲学以及众多文明批评家的强烈反驳,而且自康德以来的哲学传统对此也并不支持。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理论设想不可谓不宏大,但是相形之下它的理论支撑就显得过于脆弱、单薄了,并且它的解释能力实在也不尽完备。
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文不是纯粹批评“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观念上的不足,而是更多地考虑它重新成为当代思想资源的可能性。在这种思考中,有一些问题必须得到强调:首先,人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探讨并试图解决的,皆是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的终极课题,但同时它的科学、哲学基础并非那么牢靠,对社会、经济等学理的积淀也并不丰厚,因此它在学理以及逻辑上,要达到无懈可击的完整性,是不大容易的。但是,由于人道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实践哲学、道德哲学,因此也就不必过于斤斤计较于其学理及逻辑的谨严。论者认为,当下,我们更需要把关注点集中于它的实践价值与道德价值之上。其次,我们在当下研究评价“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之时,既不能过于炫耀自己时代的历史高度,也不能以成败得失枉论这一观念的价值,而是要充分考量到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以冀寻找它真正的价值与当代意义。
[收稿时间]2009-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