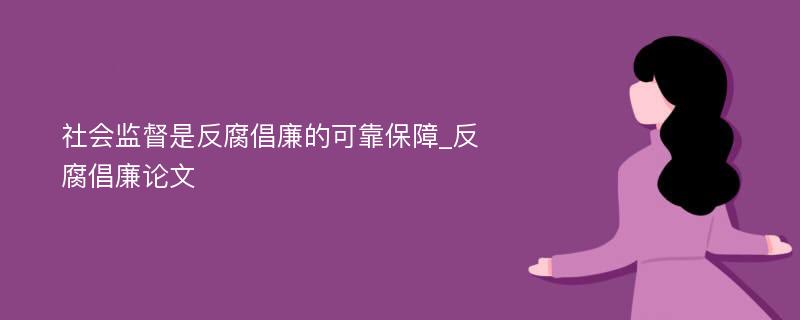
社会监督是反腐倡廉的可靠保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监督论文,反腐倡廉论文,可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论述社会监督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认为社会监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和特点的体现,是反腐倡廉、防止滥用权力的可靠保证。希望我们党和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进一步健全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体制,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社会监督,或称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外部监督,它与国家性质的监督不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非国家性质的监督,监督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或非国家机关的社会团体组织,监督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社会监督就是人民群众和社会团体组织对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履行职责、遵纪守法、为政清廉等情况进行检查和督促。
一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要有社会监督,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
马克思曾高度赞扬巴黎公社创造的、由选民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会是“伟大的创举”,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权”。公社委员会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属于中央政府权力的职能,不过,行使这些职能的勤务员已经不能够像在旧政府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1〕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十分强调建立一种对苏维埃政权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制。他说:“正是苏维埃与劳动‘人民’接近,才造成……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现在,我们愈坚决主张有极强硬的政权,……我们就该有更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2〕
毛泽东早在1945年7 月在谈到跳出历史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时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邓小平早在1957年4月指出,“共产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 八大强调了这个问题。”“要搞职工代表大会,加强它的作用,这就是要求我们在厂矿企业里扩大群众的监督。在这方面,八大决议中只讲了一面,强调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次……加了一条,即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既有自上而下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又有自下而上的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3〕1980年8月,邓小平又强调“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4〕
以上看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设想,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结构应是向下的结构,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监督指向应该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公众或群众监督。
二
社会监督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和特点的体现。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与历史上的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过去的国家都是剥削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国家,是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民群众还不能够也不可能立即实现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直接管理,只能主要通过执政的共产党、国家政权机关来进行管理。代表人民掌握政权的执政党和国家机关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群众掌握监督权,既是人民民主原则的直接体现,又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形式之一。
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政权仍然存在着两重性。恩格斯指出:“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5〕这段话告诉我们, 胜利的无产阶级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国家,但这个国家仍然具有两重性,即有益的和有害的、进步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尽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已经立即除去国家祸害的最坏方面,即把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变成压迫剥削者的手段,废除军事官僚制度,使国家变成廉价政府。但是,国家作为祸害一直要存在到共产主义阶段国家消亡以前。
社会主义国家祸害的存在决定了社会监督的必要性。其一,社会主义国家,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国家活动的根本原则。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群众主要通过执政的共产党、国家政权机关来行使社会的公共权力,这实际上就出现了权力的所有者与权力的行使者之间的某种分离。表现在并非党政机关和公职人员在任何时候都能正确和合理地行使这些权力,也并非执政党和国家机关所制定的所有方针、政策都能准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实践中常常出现权力行使者背离权力的所有者的意志,给人民群众带来种种危害的现象。在社会主义阶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要扩大公民直接参与管理的权力,另一方面更要扩大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的监督权,确保人民群众的所有权、占有权和分配权得到真正实现。
其二,即使行使权力的机构力求忠实地去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很难完全一致。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任何杰出的政治家,任何一个卓越的领导集团,在判断和思考什么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怎样处理人民群众的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利益的相互关系,利用什么方式和手段去实现这些利益的关键问题上,很难避免失误。仅仅依靠行使权力者的忠诚、信任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还不足以保证权力的合理运用,人民利益的实现还需要人民监督制度来保障。
其三,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公共权力本身也具有两重性。从本质上说,公共权力机关具有各种可能性和能力来实现人民的利益,但这些能力和可能性本身又能为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带来各种物质和精神的好处。即使行使公共权力的人自觉地抵制和拒绝利用和享受这些好处,但如果没有健全的权力监督的制度,久而久之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手中的职权所腐蚀。更何况,党政权力机关中不可避免地会混进一些官僚、以权谋私者,他们集中表现为权力欲望、权力增殖、权力占有、权力威慑、权力崇拜,把手中的权力作为谋求个人的、小集团的私利和特权的工具,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权力异化和蜕变。这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职人员,尽管是经济上政治上均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公仆”,其中一部分人还有可能借用国家这个工具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社会主人”。为了避免和防止一些人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就需要有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
三
社会监督是反腐倡廉、防止滥用权力的可靠保证。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干部。在新时期,我国党政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有腐败行为的只是极少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干部的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是积极作用。绝大多数干部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和各个岗位上,能正确地运用权力,为人民服务,对推动和促进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二是消极、腐蚀作用。极少数干部滥用权力,危害人民,对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阻碍、破坏作用。
“廉价政府”是资产阶级学者首倡的,标准是:(1 )政府官员不贪不受;(2)廉洁奉公;(3)待遇一般不能高过社会相应阶层。这些标准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国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主体,从本质上说已实现了廉价政府。但由于种种原因,少数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滥用权力,侵犯人民合法权益和为政不廉的腐败现象仍然存在。
当前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在官僚主义,行业、部门不正之风和贪污、贿赂等三个方面。官僚主义是行业、部门不正之风和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的温床,官僚主义造成国家大量人、财、物的浪费,使干群关系疏远,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行业、部门不正之风表现为党政机关经商办公司,权力部门乱提价、乱收费、乱摊派,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用公款请客送礼,大吃大喝,用公款购买豪华轿车和其他高级消费品,有些行政执法机关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等等。不正之风尽管形式多样,但其共同特点是利用职权和行业的垄断地位,巧立名目,为小集团和个人谋私利,加重企业、群众尤其是农民的负担,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贪污、贿赂是当前最严重的腐败现象。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从1991年至1995年检察机关立案侦察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大案,从13325万件增至29419万件。1995年1—11月, 全国纪检机关对县处级以上干部立案122476件,共处分102317人,其中县处级3084 人, 地厅级279人,省军级24人。 这些案件表现的明显特点:一是多数发生在中央确定的查办大案要案的四个重点部门中,即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二是都是现职领导干部犯罪,高级领导干部犯罪呈上升趋势,贪污的多是管钱的,受贿的多是掌权的,特别是直接掌管人、财、物管理权的;三是顶风作案多,绝大多数犯罪分子都是在1993年8月中央部署反腐败斗争后继续作案的;四是犯罪数额大, 绝大多数犯罪数额在几万元以上,甚至达几十万到上百万元。
贪污、贿赂影响坏,危害大。它破坏政府的管理秩序和行政权力的公正原则,激化社会矛盾,毒化社会风气,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意,影响社会的稳定;它干扰政府经济政策,导致公共决策失误,投资扭曲,生产成本非正常上升,经济秩序紊乱,巨额资源浪费,经济效益下降,人民负担加重,是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可见,腐败现象直接关系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政存亡。
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下最大决心,花最大力气揭了大案要案,表明党和政府惩腐倡廉的决心和力量。实践证明,防止腐败,为政清廉的根本措施是加强社会监督。据统计,近年来检察机关立案侦察的贪污、贿赂案件中,有60—80%来自群众举报。从1988年建立举报制度至1994年4月,我国检察机关受理的贪污、贿赂举报线索已达120多万件,出现了署真名举报多,举报领导干部多,举报重点部门多,举报重大问题多的“四多”现象,而且信访举报增加的势头不减。这说明在人民群众中已经形成了反腐败斗争的震慑力量,社会监督成为清政廉洁、防止滥用权力的可靠保证。
四
社会监督是社会主义监督体制的基础。社会监督,或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外部监督,既有自身的独立性,自成体系,又渗透在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经济监督等各项监督之中。社会监督的最大特点是非国家权力性和非法律强制性,是人民群众通过社会团体、社会组织、舆论机关的公民群体或个人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制定和执行各项制度、方针、政策以及他们的工作进行检查和督促,是人民民主原则的直接体现。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经济监督等各项监督都离不开社会监督、群众监督,离开了社会监督、群众监督,这些监督就会落空。
人民政协是全国爱国统一战线的形式,是我国多党合作的机构,是我国民主政治的形式。政协不属于国家机关,又不是一般的人民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爱国统一战线作了肯定,对政协的基本职能形成共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组织各党派、各民族、各社会团体以及民主人士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是指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在决策前进行讨论,和就决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民主监督,是指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及财政经济预算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履行职责,遵纪守法,为政清廉等方面情况通过批评和建议进行监督。政协向中共中央、人大、国务院及地方提出建议案,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政协的基本职能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的特色,即对于有关我国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一方面由政协讨论协商,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一方面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作出决策,在决策以后,由人代会和政协监督执行。这是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社会监督是整个社会主义监督体制的基础。社会主义监督体制大致由三方面构成,一是专门机关如纪检、监察、检察、公安、审计、税务、物价、工商等部门的监督;二是实行内部的自上而下的如中央对地方、上级领导对下级领导等的监督;三是实行外部的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三种监督都是重要的,必要的,在同腐败行为作斗争和发挥监督作用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严格执行法律、政纪和党纪,又要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和配合。但是,前两种监督都必须以第三种自下而上的监督为基础,离开了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其它两种监督就会失去依靠。
邓小平同志提出,反腐败不搞群众运动,但要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邓小平强调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6〕江泽民总书记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指出:“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一定要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真诚和主动地接受监督,广开言路,听民声,知民情,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群众监督是一种最深入最朴实的监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干部的工作是否有效率,是否廉洁,领导干部是否称职,是否值得拥戴,最有发言权的是群众。
监督的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在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痛恨腐败现象也渴望监督有畅通的渠道。1988年3月8日,深圳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举报中心,至1993年底,全国已有3600多个举报机构。这种举报中心,是在不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依靠群众揭露腐败现象的有效形式,是深入开展反贪污、反贿赂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和手段,解决了人民群众实行民主监督的中介环节和程序问题。完善群众来信来访举报制度,建立党风党纪监督员制度,聘请特约监察员制度,是新时期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新经验,也是群众揭举揭发贪污贿赂行为的重要渠道。
在社会主义监督体制问题上,要改变三个认识:一是要改变监督权只属于国家机构、行政机关的传统观念,建立起统一的、全面的、系统的社会监督体系和人民群众监督体系,用人民的监督权来约束权力;二要切实扭转监督对象对下不对上的倾向,人民群众监督权既要指向上级机关,也要指向下级机关;三要扭转监督权低于行政权、司法权、甚至低于个别领导的个人权力的传统格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让“人民监督系统同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享有相同的权利,让人民来监督政府”。〔7〕
总之,社会监督是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参与政事、管理国家经济和社会事务,行使权力的基本形式之一。只要举国上下增强群众监督意识,健全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体制,对于确保公职人员政务活动、公务活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蜕化变质,就有了可靠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4、438页。
〔2〕《列宁选集》第3卷,第526—527页。
〔3〕《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0—271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7〕《列宁全集》第48卷,第4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