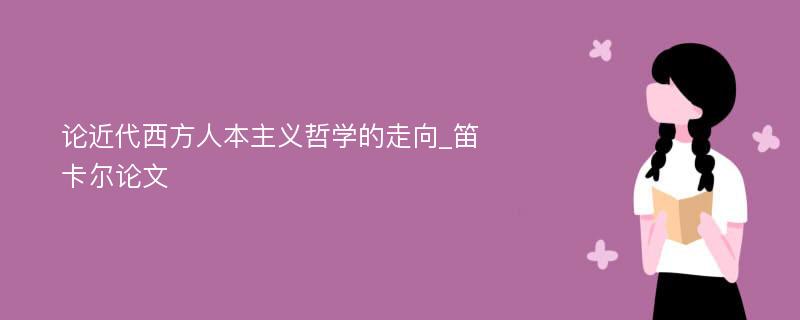
论近代西方的人文哲学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近代论文,人文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在近代哲学中,理性主义由于其对中世纪神学斗争的辉煌胜利,而在思想史上取得了十分显赫的地位,它在科学和技术上的巨大成功,导引着人们把近代标示为“理性的时代”和“科学的时代”。然而,当人们沉醉于理性主义的功勋榜上时,却潜藏着忽视近代西方文化中人文关怀思想的危险。而对这一方面的忽视甚至否定,必然导致我们认识不到西方近代文明的真正本质。当我们在设计现代化的道路和蓝图时,如果仍以这种“误读”的近代西方文明作为参照模式,那就必然要误入歧途,重陷西方文明之困境。因此,清理近代西方文化的另一条思路——人文哲学思潮,对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知识观、笛卡尔和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以及黑格尔的逻辑主义一直被置于十分显赫的地位。由这种极端的理性主义或唯科学主义所构成的哲学画面严重地歪曲了近代思想和文化的整体形象。作为近代知识或思想文化版图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历史学、语言学、浪漫主义的文学等等,在这一画面中都没有得到反映。帕斯卡尔、维柯、赫尔德等重要的思想家很长时间内一直没有获得适当的地位,卢梭等思想家也一直是放在理性主义的画面中来描绘的。
当然,由于近代科学对中世纪神学的胜利以及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功,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把近代标示为“理性的时代”或“科学的时代”也是可以的。但是,并不能由此否定近代西方思想和文化中的人文方面,特别是作为近代西方人文关怀之自觉反映的人文哲学。无视或否定这一方面,我们就不可能认识西方近代文化和哲学的真正本质。我们在设计现代化的蓝图和道路时如果仍然以这种“误读”的近代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甚至当作唯一的模式,那必然会误入歧途。“现代科学危机”或“全球危机”已经把这一点充分地展示出来了。本文试图清理出近代西方哲学中的另一条思路,即,从帕斯卡尔到赫尔德的人文哲学思潮。它不以科学(狭义的,即自然科学)为满足,认为在科学知识之外,人生尚另有其价值和意义,而那是科学所无能为力的。
与笛卡尔比肩的另一位人物
在17世纪的法国,除了笛卡尔以外,还有一位伟大的人物,即帕斯卡尔。他们都属17世纪最卓越的数理科学家的行列,但在哲学上却是根本对立的。帕斯卡尔指责笛卡尔哲学对科学的偏心,对人的忽视,强调理性不能认识人生。笛卡尔认为,理智是心灵的本质;而帕斯卡尔则认为,心灵有其自己的思维方式,那是理智所不能把握的。①前者重思维的逻辑形式,后者则关注生命存在的内容;前者是唯理论者,后者则是一个人生哲学家。
帕斯卡尔在《思想录》和《几何的精神与说服的艺术》中都区分了两种精神,即几何性精神与敏感性精神。相应地,也有两种人,一种人习惯于依据原则进行推论,不理解感受性,能细致地探讨却不能洞穿事物的底蕴;另一种人则习惯于根据感觉来判断,不理解推理,想一眼看穿事物的底蕴而不屑作细密的探讨。帕斯卡尔这里所说的敏感性精神不同于笛卡尔的理智能力,亦并非英国经验主义者所说的感知能力,而类似于艺术家所拥有的一种精妙的感受性,一种敏锐的洞察力,或者说,一种直觉力。如果要帕斯卡尔作一次非此即彼的选择的话,我想,他会选择后者,他明确地说,敏感性精神只属于少数人。人们往往认为从事哲学和科学只需要一种依据经验进行逻辑的思维和推理的能力就足够了;在帕斯卡尔看来,这种观念无疑是十分片面的。他说:“我们认识真理,不仅仅是由于理智而且还由于内心;正是由于这后一种方式我们才认识到最初原理,而在其中根本就没有地位的推理虽然也在努力奋斗,却仍是枉然。”②帕斯卡尔也承认理性在科学领域中的作用,但不像笛卡尔等人那样把理性的作用估计得那么高。他着重强调理性思维、推理的不可靠性和局限性,并且肯定我们难以达到绝对的确定性,没有绝对的真理。这里隐约地展现出后笛卡尔主义的当代科学哲学的主题和思绪。因此,人们说,笛卡尔和帕斯卡尔他们一个在哲学上重新开创了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而另一个则似乎要预告这一时代的危机。他们一个对近代有无可比拟的重大意义,而另一个对于人类的意义更多的是在当代。
如果说理性在认识自然时尚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那么它对探讨人自身来说则更显软弱无力。而且,在帕斯卡尔看来,探讨人自身是哲学的又一个基本任务,其重要性远甚于认识自然,人生的问题远比知识的问题重要。帕斯卡尔曾对自己只有三十九载的虽然短暂却伟大的人生作过深刻的反省和批评,对关于人的研究被忽视的状况感到不满。他说:“我曾经长期从事抽象科学的研究……当我开始研究人的时候,我就看出这些抽象科学是不适应于人的,并且我对它们的钻研比起别人对它们的无知来,更会把我引入歧途。”“研究人”“这是真正适宜于人的研究工作。”③在他看来,人不是为了知而存在,相反,知是为了人而存在。理性和科学不能解决人生问题,相反,应该在人生哲学的意义上被审视。*
帕斯卡尔划分出三种性质不同的秩序以及相应的三种不同的伟大:首先,是身体、物质方面的秩序;其次,是精神或理智方面的秩序;最后,是心灵、仁爱方面的秩序。在他看来,三者一个比一个高,而且不存在由此达彼的桥梁。物体不能产生精神,财富不会带来学识;仅仅通过科学也不能把握和理解仁爱的心灵,理智、知识都无法通达对上帝的信仰。帕斯卡尔把信仰和上帝置于其哲学的最高位置,但在近代唯科学主义形成之初就呼吁重视人的研究,强调理性与心灵的差异,这在人文科学史上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还应该指出,帕斯卡尔已意识到要把自己的人文思想与关于人的群体或社会研究区别开来。他注意到人性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加以考察,一种是根据他的目的,这时候人是伟大无比的;另一种是根据群体、多数,这时候人则是邪恶下流的。这样两种研究方式使我们对人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并引起了哲学家的无穷的争论。尽管帕斯卡尔没有给予关于人的社会研究一个恰当的地位,但完全可以肯定,他明确地认识到人文研究区别于社会研究的特殊性。这在人文科学方法论上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件。
遗憾的是帕斯卡尔英年早逝,没有完成对“笛卡尔主义”的系统批评,更没有进行系统的人的研究。
维柯的“反笛卡尔主义”
帕斯卡尔遗留的任务被18世纪意大利的维柯承继下来,力图在笛卡尔哲或数理科学之外建立一门关于人的思想和行为,即人的文化活动的“新科学”。柯林武德曾把维柯的学说称之为“反笛卡尔主义”,认为它是对笛卡尔主义的第一次进攻。④我们知道,18世纪是启蒙的时代,是理性主义凯歌奋进的时代,这样一种时代氛围就已昭示出维柯的学说本该具有多么深刻的意义。因为维柯学说强烈的叛逆性格,或者,如柯林武德所说的,维柯走在他时代的前面太远了,因而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影响。⑤
笛卡尔主义的根本缺点,一是机械的世界观,一是唯科学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科学观或知识观,两者是相互关连的。在笛卡尔“物理学”的范围内,物质或者说物体,是唯一的实体。在这种实体观或本体论中,精神或“心灵”没有独立的地位和特性。因而,在知识论上,笛卡尔认为,真正确定有效的知识仅限于对于具有广延性的事物的知识,自然科学,即数学(几何学)和物理学(机械力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在他看来,诗歌更多地是一种天赋而不是学问;历史学不论多么有趣和富有教益,不论它对于生活中的实践态度的形成多么有价值,都不能称为真理。“他根本不相信历史学是知识的一个分支。”⑥诗歌、历史学等人文科学既然不是知识,不是科学,就不值得哲学去关心、去追问。
而维柯则以制定人文科学(历史学)的方法论原则为己任。首先,他批判了笛卡尔知识论的根本原则,即确定性原则。笛卡尔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确定性,认为真理的标准乃是清晰明白的观念。维柯指出,笛卡尔的真理标准实际上也只是一种主观的或心理的标准。我认为我的一些观念清晰而明白这一事实,仅仅证明我相信它们是这样的,而并不证明这就是真实的。
在批判笛卡尔的原则的同时,维柯也致力于确立自己的知识论或方法论原则。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原则,借以能从不能认识的东西之中区别能认识的东西。这是一种人类认识的必然局限性的学说,即“真理与事实相互转化”的原理。维柯认为,“真”,即我们确凿地认识的东西,与“创造”,即我们所创造的东西,是共存的。根据这一原则,我们能够确切知道的只是我们认知者本人所创造的东西。说得更具体一些,能够真正认识一件事物,即能够理解它而非仅仅知觉它的条件,乃是它必须是我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大自然不是我们的创造,因此人类理性决不能获得对于物质实在的清楚明确的认识,物质实在决不是以唯理论哲学所设想的方式存在的,它只对上帝才是可理解的。与此相反,历史的过程是人类由以建立起语言、习惯、法律和政府等体系的过程,历史完全是人类头脑所创造的东西,所以特别适于作为人类知识的一种对象。人不能理解自然却能理解历史,因为是人自己创造了历史。
通俗地说,在维柯看来,历史研究的对象本身是人类意志和计划的结果与表达,历史学家所研究和理解的是人的世界,在历史学家的头脑和他所要研究的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预定的和谐,这种和谐的基础不是莱布尼兹式的奇迹,而是把历史学家和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那些人结合在一起的普遍人性。维柯认为,历史学家需要关心的不是作为过去的那种历史,而是自己时代的现实生活。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社会的结构,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人所共享的风尚和习俗。因此,历史是历史学家凭藉自己文明生活的经验和自己的人性就可以驾轻就熟地把握和理解的。历史学家能够在自己的头脑里重新构造出人们在过去借以创造这些事物的过程。历史学的方法,就是“想象”(fantasia)。由此,维柯证明,对于法律和语言等等这类历史或文化事件的研究,也能给人以像笛卡尔归之于数学和物理学一样的确凿有效的知识,人文科学(历史学)是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
不过,应该指出,维柯在确立“想象科学”(历史科学)在知识王国中的独立地位时,却把自然界当作神圣的、不可知的创造物交给了上帝。在确立起人文科学的地位的同时,却实际上否定了自然科学的科学性或科学地位。在自然实在的问题上同样犯了机械主义的错误,因而否定了自然实在的可知性和人文现象的客观性。
卢梭:启蒙思想的代表还是叛逆者?
卢梭也是18世纪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但对理性主义持一种尖锐的批评和反对态度。卢梭一般被看作18世纪法国重要的启蒙主义者。但是,事实上,“法国启蒙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同让·雅克·卢梭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针对于理智、知识的增长和科学的进步——这些本是启蒙运动引为文明的唯一希望——他崇尚友好和仁爱的情感,崇尚善意和虔诚。”⑦
启蒙思想的主旨是理性主义和自由精神。启蒙主义者把理性树为最高的权威,但仅仅在近代科学的形态中来理解理性,同时代的洛克派哲学已经表明科学知识的理性根据是可以怀疑的,这样,理性的权威就成了问题。更为严峻的是,启蒙主义者原本以为自由源于理性,借助科学理性的力量,人类社会将达到自由的理想状态。然而,卢梭发现,理性与自由自相矛盾,理性带来的不是更多的自由,而是更多的不自由。在《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厚》一文中,卢梭认为,科学、艺术的发展使人们成为虚伪的时尚、习俗和偏见的奴隶,窒息了人类天生的自由情操,使人们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并不能使人们变得更道德,而会产生道德上的堕落。他说:“等到生活上的各种便利蒸蒸日上,各种艺术臻于完美,奢侈广泛流行的时候,真正的勇敢就衰退了,英武的美德就消失了;这种现象仍然是各种科学以及这一切在暗室中制造出来的艺术的产物。”⑧
虽然卢梭“重返自然”的结论并不可取,但他的确提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问题:理性只是一种认识能力或认识形式,还需有所依托;科学技术只是一种工具而非人类终极的目的,需要价值取向来引导从而善加利用。若以为理性与自由一体,科学主宰一切,势必使科学技术的发展迷失方向,甚至成为毁灭人类自身的力量。这恐怕是启蒙思想家们始料未及的。如果说理性主义正如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个根本命题——“美德即知识”——所表明的那样,把全部伦理问题还原为知识问题,或者说,把伦理学建立在知识论的基础之上,那么,卢梭则把苏格拉底的命题变成了“无知即美德”。卢梭撕裂了连接美德和知识的那条虚幻的纽带。在他看来,知识不仅不等于美德,相反却是人类道德沦丧的一个阶梯。卢梭的立场未免失之片面,但却使道德领域从科学和理性的支配下摆脱出来,使道德学等人文科学的独立发展成为可能。
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
正是卢梭启发了康德,使他从理智主义的迷梦中醒来,卢梭是康德眼中的道德世界的牛顿。康德曾写道:“卢梭是另一个牛顿。牛顿完成了外界自然的科学,卢梭完成了人的内在宇宙的科学,正如牛顿揭示了外在世界的秩序与规律一样,卢梭则发现了人的内在本性。必须恢复人性的真实现象。哲学不是别的,只是关于人的实践知识。”⑨
康德哲学的根本变革意义,首先在于它摆脱了对科学理性的盲从。在康德看来,就自然认识而言,我们既不是从个别偶然的感觉经验中概括出普遍的自然法则,也不是完全由理性自身中抽引出全部知识,科学知识的获得不过是我们按照主体中先天具有的认识形式加工整理外界事物提供给我们的感觉经验的结果。因此,科学的自然法则并不是在自然中发现的,而是我们赋予自然的,正所谓“理性为自然立法”,主体认识形式的“先天性”是科学认识的普遍必然性的保证。不过,既然只有通过主体的认识形式才能认识世界,那么,人所认识的世界就是人化的世界,是现象而非世界或物自体本身,事物自身究竟如何是无法知道的。
这种不可知论乍看之下是消极的,然而对道德领域而言却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康德之所以作《纯粹理性批判》,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圈定科学理性的范围,防止它超越自己的疆界去蹂躏道德领域。在康德看来,理性的本性是追求某种超验的永恒理念,这种理念属于人的认识所无法达到的“彼岸”——本体界。既然永恒理念不能通过人的认识来感知和证明,那么就只有通过实践理性来信仰。康德看到了科学理性的局限性,所以他要限制知识的应用,为道德信仰保留地盘。这样,康德就在纯粹理性(科学理性)与实践理性(道德理性)、知识与信仰、必然与自由之间划出了严格的界限。一方面他证明了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和科学理性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又为自由留下了一个无限的领域,从而保证了道德学说的合法性。
不仅如此,康德还认为,实践理性优于或高于理论理性、道德重于科学,前者对后者具有“规范”作用。他强调不能颠倒次序,“而要求纯粹实践隶属于思辨理性之下,因为一切要务终归属于实践范围,而且甚至思辨理性的要务也只是受制约的,并且只有在实践运用中才能圆满完成。”⑩因为就纯粹理性(自然科学)而论,我们所能认识的无非是宇宙森严的必然规律,地球不过是无限宇宙中的一粒微尘,而人类只是被偶然地赋予了生命,只是这粒微尘之上的微乎其微的存在物,不知何时又要把生命还给自然,重新加入永恒轮回的物质循环之中。在这里,任何人都无法逃脱这无情的必然法则。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内心的道德律使我们独立于动物界,甚至独立于全部感性世界,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向往无限的自由世界。在康德看来,这才真正体现了人类的价值和尊严。
康德通过道德世界与自然世界、知识与信仰的分离摆脱了笛卡尔二元论的困境,也否定了霍布斯、斯宾诺莎以及法国唯物论者的机械决定论。然而,应该指出,在康德哲学中所谓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并不是两种理性,而是一种理性的不同应用。而康德的理性概念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一脉相承,是天赋的、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人的理性。理性一旦失去了与具体的人、现实的人生的联系,就无从确定自己的真实身份,无从知晓自己的出生地。因此,在康德那里,道德原则不是人类自身的文化创造活动的产物,而是借助至上的权威强加于人的“绝对命令”,因而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永恒不变的。康德虽然强调“人是目的”、“意志自律”,但人在他的心目中仍旧是表演、实现“绝对命令”的木偶和工具。
赫尔德与康德的论争
康德的理智主义倾向遭到了他的学生赫尔德的批判,后者因为《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而获得了与前者比肩的地位。
赫尔德借助进化的观念重新恢复了人与自然的联系,而且他不是把自然看作纯粹作机械运动的物体而是看作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序列。“赫尔德把人类生命看作是与其在自然世界中的背景密切相联系着的。他所设想的这个世界的普遍性质,是一个有机体的性质,这个有机体被设计成要在其自身之内发展出更高的有机体来。”(11)赫尔德依据这种与有机自然的联系,进一步重新解释了人的理性以及人类不同种族的文化特性。在他看来,自然的进化过程在人这里达到了顶峰,人在其理性的和道德的生活中证明自身的存在,人性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体系而在不断地发展着自身。“这样,人类便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一个连环,一个世界是人从其中成长起来的自然世界,另一个世界则是……现实存在的精神世界。”(12)
从人的这种自然与精神的统一和双重特征出发,赫尔德解释了人类的自然而历史的过程,把人类历史看作文化史。他因此而被称为“人类学之父”(13)。赫尔德认为,作为自然的生命,人分属于不同的种族,每一种族都和它的地理环境密切关连,并具有由那个环境所塑造的体质和精神的特征。但是,每个种族一旦形成,就成为人性的一种特殊类型,不再以它和环境的直接关系为转移。这样,不同种族的感觉能力和想象能力因此就分化了,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幸福观念和特有的生活方式。赫尔德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以系统的方式证明和肯定了不同人种之间的差别,并且承认人性并不是一致的。举例来说,中国文明之所以成为中国文明,不是因为中国的地理和气候,而是因为中国人的特性。如果不同的人种被置于同样的环境中,他们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开发那个环境的资源,从而创造出不同的文明来。因此,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一般人的特点,而是这种人或那种人的特点。可以看出,赫尔德的种族理论和人性理论既否定了启蒙运动以及康德哲学中的单一的固定的人性概念,也超越了霍布斯式的自然决定论和孟德斯鸠式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这就在有关人性的概念中迈出了重要的新的一步,因为它承认人性不是一个给定的数据而是一个问题;不是到处都一致的某种东西,它的基本特征可以一劳永逸地被人发现,而是可变的某种东西,它的特征要求在特殊的事例中进行单独的调查研究。”(14)
应该指出,《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中的人性理论仍然是不彻底的。赫尔德是在种族的范畴下考察人性的,因此,这里的人性概念还不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概念。这里还没有一个民族的性格乃是那个民族的历史经验所造成的观念;相反,它的历史经验却被看作单纯是它的固定性格的结果。每一种人性不是被看作历史的产物,而是被看作历史的前提。正如柯林武德指出的:“人性是已经被区别了,但它仍然是人性,即仍然是天性而不是精神。”(15)
但是,这种虽说不彻底或不全面的思想,却遭到他的老师康德的责难。赫尔德并没有屈从康德的先天的或理智主义的人性论和普遍历史的观念,相反,却朝着个体主义的方向深化了自己的人性观。赫尔德与康德的争论,实际上体现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分流。他们当时的争论与科学方法论相关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关于人和人类、个体与族类的关系问题。赫尔德强调前者,康德则强调后者。赫尔德指责批判哲学蔑视个人,抬高族类,认为族类不是普遍的概念,必须体现在具体的个体之中,否则就没有意义。康德认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单个人所没有的特点,只有整个人类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才能总是处于发展之中和达到自由的顶峰,而个人相对来说则是无能为力的。二是国家观。康德认为,由于人们滥用自由,因此就需要有统治者,也就是说,需要国家机构。赫尔德则认为,国家是和生命的本性相对抗的、死的、没有灵魂的机器,应当加以摧毁。争论的结果是加强了赫尔德要从根本上推倒康德的批判哲学,推倒康德树起的纯粹理性这座偶像的信念。赫尔德在其批判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论知识和经验》一书中强调,根本不存在什么纯粹的理性,只有人的理性,因为只有人才具有理性。而且,赫尔德还认为,理性和人的精神的其他能力是相联系的,例如,思想具有语言形式,不可能有语言之外的纯粹理性。对于康德的不可知论,对于那个超越理性范围的“自在之物”,赫尔德更干脆地说:“滚开吧,让人眼花缭乱的东西!”赫尔德与康德的观点和方法虽然针锋相对,但实际上在各自的范围内都有其合理性。赫尔德强调理性的历史性、个体性和语言性的表现形式,强调理性的经验基础,相对于笛卡尔和康德的先验论或理性主义来说,无疑是哲学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赫尔德否认族类、群体和社会是普遍的概念,否认国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必要性则又是片面的。
综上所述,近代人文科学的哲学思想在与机械论世界观的对立中,肯定人文现象的独立性,反对把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作为统一所有科学的原则,强调诗性智慧(想象)、实践理性和移情是人类理性或精神总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总算在机械的自然世界中发现了一片人文世界的绿洲。这些思想成为20世纪人文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前提,也是我们今天解决“全球性危机”和建立市场经济体系时必须认真研究和汲取的宝贵的思想财富。
注释:
①②③帕斯卡尔:《思想录》,1912年,布伦士维格本,第277、282、144节。
④⑤⑥(11)(12)(13)(14)(15)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2、80~81、67、101、102、104、104、105页。
⑦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下册,第645~648页。
⑧《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8~149页。
⑨《康德全集》,柏林,雷麦版第20卷,第58页。
⑩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4页。
标签:笛卡尔论文; 康德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赫尔德论文; 读书论文; 理性主义论文; 卢梭论文; 人性论文; 维柯论文; 科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