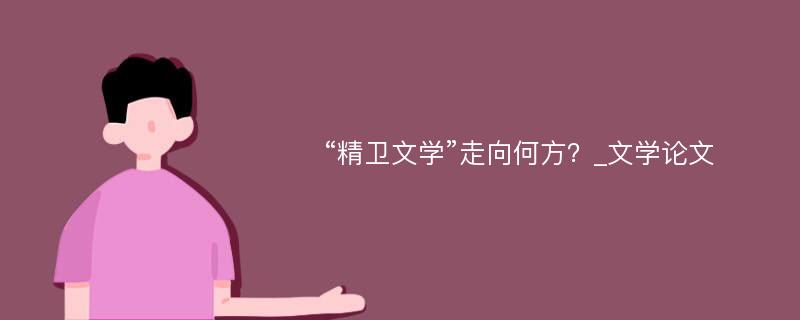
“京味儿文学”走向何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味论文,走向论文,文学论文,何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0月13日,北京日报《文艺周刊》、北京作协、北京文化热线网、北京汉风广告公司联合举办了“京味儿文学研讨会”。作家林斤澜、赵大年、毕淑敏、徐小斌、刘庆邦、星竹、陆涛、袁一强、赵凝、丁天、田柯、凸凹、学者陆昕、焦国标、编辑隋丽君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就“京味儿文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北京:心理认同与文化批判
北京是“京味儿文学”的发生地,因此对于“北京”的文化阐释,是“京味儿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会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学者们对“北京”朴素而直观的理解。
“老北京”、满族作家赵大年系统地回顾了北京的历史:北京最初发端于琉璃河(“北京人”的故乡),之后为蓟城,为辽代京都时称“南京”,拥有30万人口;为金代京都时称中都,以北海太液池为中心;为元代京都时称“大都”,以积水潭为中心;明代永乐18年,永乐帝带来能工巧匠3万人,按汉代建制建立了北京城;到清代, 北京更是成为南北交融的通衢大邑。明代嘉靖帝提出了要有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这种语言即“官话”,也就是北京话。赵大年认为,北京语言得天独厚,历史上五、六次的民族融合,使这种帝都语言成熟文雅。北京漫长的历史积淀下来博大精深的京味儿文化,它由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四个部分组成,而这些文化也是由历代各地的文化精英在京城汇聚、创造出来的。赵大年认为,京味儿文化既是地域性的,又是中华民族大文化的集中和代表。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北京人养成了“什么都信,什么都不信”的“自由”的文化个性。在北京,既有宫廷,又有很发达的平民意识,从语言的应用上可见一斑。比如什么人都可称“爷”——上至“万岁爷”,下至“板爷”、“倒爷”、“兔爷”,等等。一旦到了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北京人就会表现出惊人的团结与大仁大义大勇,那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燕赵风骨的余韵。
学者陆昕指出,北京是一个包容性和吸纳性极强的城市,由于近千年王朝时代的科举取仕制度,形成了良好的竞争空气,使北京人善于和有竞争力的外地人和谐相处。另外,北京人深受儒家文化的熏染,即使在市井之中,也守着一种坚定的道德准则来生活。他认为,北京在全国优越的文化地位是毋庸讳言的,外地人多有“只有在北京出名才算出名”的朴素观念,从一个侧面表明对北京文化层次的高度认可。
对于北京人的这种高度的心理认同、学者、杂文作家焦国标表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他指出,千百年的帝都文化不仅造就了北京人的仁义勇,更造就了他们的世故和奴性;不仅塑造了北京城“通衢大邑”的物质特征,也塑造了这个政治中心曲折幽暗的精神特征。比如旧时京城地名多以“安定”、“平安”命名,这与统治者内心的期望有关,是一种“语言巫术”;北京街道平直,与官场曲折、角落太多恰成对照;官衙厅堂之上所悬挂着的从封建时代的“正大光明”到本世纪上半叶的“天下为公”,恰与统治者的真正动机与行为构成“表里不一”的对应关系。在《京味儿现象:一种群体自恋》一文中,焦国标曾经分析过北京儿化音的社会政治文化底蕴:“皇城根儿的北京人说话儿化一切,但是谁也不敢把北京读成北京儿……北京城的九门……哪个都不儿化,可是东便门儿、西便门儿谁也不把它们不儿化……他们更不把皇上儿化成皇上儿,把皇帝儿化成皇帝儿……不说大人物,便是那些“现管”,如局长、处长、科长、主任、经理、老板,北京人也决不把它们叫成局长儿、处长儿、科长儿……由此大致可以得出结论说,“皇城根儿的北京人是世故的、长官崇拜的,只在那些小人物上儿化。”对于北京人作为皇都子民的心理优越感,焦国标指出,这是一种帝都崇拜,它是帝王崇拜的延展,这是一种以地域为核心的群体自恋,而不是一个现代平民社会的东西。当代北京人需要对这种“帝都优越感”保持距离和警惕。
“京味儿文学”如何界定?
“京味儿文学”是一个用得烂熟的词,但是在概念上如何界定,多年以来一直纠缠不清,此次会上也见仁见智。赵大年说,当年“京味儿文学丛书”编委会给“京味儿文学”归纳了四个特点:1、 作品中必须运用北京语言,这是第一要素;2、运用北京语言描写北京的人和事;3、作品中环境和民俗是北京的;4、发掘北京人特有的素质。因此, 京味儿文学是地域性的文学。《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以及老舍先生的作品是京味儿文学的颠峰,体现出北京语言崇高的美学境界。
作家袁一强指出,“京味儿”另外的重要特点是幽默和大家气派,以及北京人一些根深蒂固的心理质素。学者陆昕则认为,“京味儿”就是北京特有的传统文化对北京人心理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塑造,这种北京人的“集体无意识”,应是京味儿文学的表现对象,但至今在这方面也没有足够多的优秀文学作品问世。
对于“京味儿文学”这种地域化和传统化的理解,一些青年作家有不同的看法。陆涛认为,京味儿文学应当是一种人文精神。任何文学都是从共性中寻找个性,从个性中寻找味道,而这个“味道”就是地域文化和人格力量在文学作品中散发出来的气息。但是随着北京作为国际大都会的日益现代化的发展,原来正统意义上的“京味儿”事物必将慢慢衰落,新的“大都市文化”却将应运而生,因此“京味儿文学”就应容纳更丰富的意蕴,寻找和建立大都市的文学精神。毕淑敏也认为京味儿文学概念应该更开放和大气,让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流向在此有更多的表现,输入更新鲜的血液。
对于将“京味儿文学”概念的外延扩大化的主张,青年作家田柯持不同意见。他指出,京味儿文学、京派文学和北京地区文学不是一个概念,京味儿文学是北京文学的一个分支和一种传统,它在挖掘、展示皇城根儿子民的生活和心态上有独特价值和发展余地,但是对于表现“新人类”、大学生和中关村人等普泛化和现代化的人物与生活,却有着不可逾越的局限性。他认为承认这种限度,保持其个性,才能使京味儿文学的形象更为鲜明。
至于“京味儿文学能否和现代性兼容?”这个问题,赵大年认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时期以来西方现代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的涌入,中国新文学一直没有停止吸收现代文明的营养,“京味儿文学”也不例外,《红楼梦》之后有老舍,老舍之后还有林斤澜、邓友梅、刘心武,直到现在的王朔,事实证明“京味儿文学”一直是在承续衔接之中。说起老舍,赵大年指出,老舍先生是用英文写过小说的作家,但是他的汉语白话小说却一点看不出洋味儿来,这叫“大洋若土”;现在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说正相反,由于中西文化的修养都不深厚,写得很有些“大土若洋”。
作家刘庆邦认为,“京味儿文学”一直在不断地发展,有三个作家标志着京味儿文学的三个阶段:老舍、王朔、刘恒。他们的文学有共同的特点:表现北京的“民间生活”,有强烈的底层或边缘色彩。刘恒的作品所具有的“带笑之泪”的黑色幽默风格,是新“京味儿文学”的重要收获。
“京味儿”作为一种文学追求?
一个有趣的现象:出身于诗礼之家的“老北京”如赵大年、陆昕等对京味儿文学(尤其是北京语言)和京都文化都有着强烈的迷醉,另一些作家却对这种迷醉表示异议。
老作家林斤澜先生说,当年刘绍棠曾提倡“乡土文学”,“京味儿文学”无疑是乡土文学之一种;但是孙犁先生多年前在为刘绍棠书作序时就指出过:“乡土文学”讲不通。多数文学作品都会涉及一些乡土风情,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它们就是“乡土文学”。 比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里,虽然人物和环境是绍兴的,但是鲁迅的小说观却并非是乡土的。他塑造人物,是要“杂取种种人,杂取种种话”,最终做到解剖“国民性”。沈从文的小说虽然有浓厚的湘西色彩,但是他的美学追求并非是“湘西乡土文学”,而是追求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湘西的风俗和人物只是其文学的表象而已。因此文学不应把“乡土化”作为追求本身,而应当追求超越乡土,到达纯精神的高度。否则,如果各大报刊纷纷提倡写吃写喝的“京味儿文学”,文学的层次必将会越来越低,越来越“物质化”,也越来越重复。林斤澜先生指出,居住过北京的许多现代作家都在文章中赞美过北京的韵味——蓝天、黄叶、叫卖声,从容、悠闲的情调,但是鲁迅先生的作品里却没有。对他的故乡和旅居过的地方,鲁迅先生从未表达过沉醉之情,却总是带着嘲讽的目光去打量。任何一个对自己的时代和社会保持着批判立场的作家都是如此——他们无暇迷醉,他们要催促人类改进与前行。在这种价值理念的参照下,“乡土文学”、“京味儿文学”的提法就值得商榷,至少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文学追求来提倡。
青年作家凸凹认为,“京味儿”作为作品的一种色彩和风格,作为准确地表达人和事的手段,是可以存在的,但是没有必要一味强调和推崇。他认为京味儿文化属于历史文化范畴,和某些特定的社会形态相对应。随着北京作为政治、文化、社会交往的大都会,原有痕迹会越来越淡。因此对“京味儿文化”应重新定义,定位在“都市文化”上。一味追求京味儿文化,势必导致向传统的回归与追寻,结果是制造一批比真实的“京味儿”更“京味儿”的伪民俗、伪文化;这种制造越酷似,文学作品的现实冲击力越弱,伪文化的色彩越强。文学应表达的是对社会、人生的真实看法,不应沉迷在对旧有京味儿文化的留恋、把玩、回归与塑造上。
那些被认为是写了“京味儿小说”的作家是否真的就把自己定位在“京味儿写作”上?其实不然。赵大年说,京味儿小说从未形成流派,也从未有过自觉的创作群体,只是有些作家在写了带有这种特征的可观的作品之后,被评论家和读者归为“京味儿作家”而已。星竹认为,作家不会在写作之前做“我要写京味儿了”这一设定,文学的精神在于自由,一旦在写作之前就将主题、风格固定下来,文学就已经死亡。陆涛说,虽然他从不认为自己在“京味儿作家”之列,但是从《屈体翻腾三周半》开始到现在的小说却都被称为“京味儿小说”。他认为文学一旦强调“味儿”,视野就会不再宽广,作家就很难从整个人类的角度去把握自己的素材和问题。
编辑隋丽君女士指出,目前京味儿文学的主要问题是语言太“水”,而且一提“京味儿”就以为是“油北京”、“痞北京”;另外就是对人类的精神深处挖掘不够。文学应当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处,写人类共通性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王朔小说“不能过长江”、在台湾也卖不出去的原因。止于“味儿”、止于语言层面的共识和默契,其作品的命运就是如此。
文学:面对差异即将消失的未来
“京味儿文学”不能作为终极性的文学追求,文学应当超越狭隘的“乡土文学”观念,这些已是共识。但是展望人类文明的未来——全球化,现代化,“经济一体化”,随着人类物质匮乏的苦难日渐消失(或可能消失),现代化差距的日渐缩小,人类处境的差异也将被渐渐抹平。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不久前对中国读者说:现在和未来的日本年轻作家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的生活里已经没有了乡村,于是他们所有作家只能去写都市;就这一点来说,中国的作家和读者却是幸运的,因为你们有无穷无尽的丰富新鲜的写作资源。但是,从当下中国青年作家的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都市化”倾向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作品内部的生活表象的差异性已经很难辩认。如果说文学对于人类精神问题的探索可以千差万别,但是行诸笔端的形象却总是似曾相识,这前景总是不那么令人振奋的。对于单一和乏味的恐惧使人相信:在文化基因库(焦国标语)之丰富性的意义上,“京味儿文学”的存在的确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似乎也仅仅是这种价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