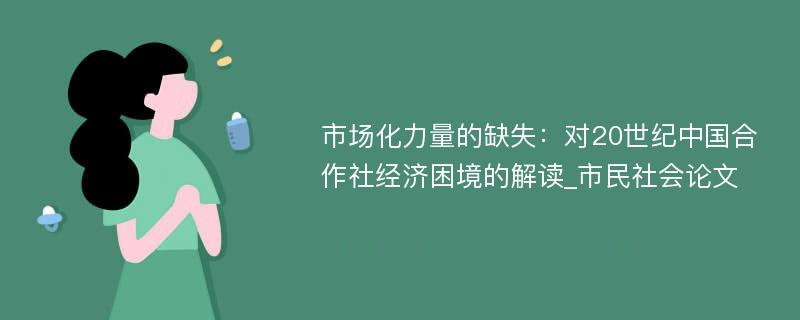
市场化力量的缺失:对20世纪中国合作社经济困境的一种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失论文,中国论文,合作社论文,困境论文,力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合作社制度作为一种植根于西方个人主义经济文化土壤中的经济制度,20世纪初被引进到中国后在其近百年的历程中,一直为国人和学界所重视和推崇。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人们有着一种共同的信念:推行合作事业,改善经济组织,可以谋中国农村之复兴和经济之进步。事实上,在中国社会从西方“舶来”的合作制经济并未达到人们的这种企图(注:与西方国家相比较而言,如在美国,1969年全美农产品36%以上是农民合作生产的,大多数农民至少参加一个、往往是同时参加好几个合作社。欧洲的合作事业更为发达,如丹麦在20世纪80年代时,农民合作社控制着91%的牛奶、65%的黄油和90%的生猪出口。(E·罗吉斯等:《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48页。)显然,中国的合作事业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在经济领域中所产生的绩效,都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相反,却被弄成了鲠喉的鱼骨,陷入到一种欲进乏力、欲吐不能的两难境地。缘由何在呢?应该说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元的,然而其中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不应被忽略的因素就是:合作制经济的行为主体即市场化社会力量的缺失或不足。对此,笔者拟站在经济文化层面上,从比较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做一探索性的讨究。
一、具有自主独立品格的市场化力量:合作社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所谓“市场化力量”,是指特定市民社会(以市场经济为轴心的经济社会共同体)条件下经济活动主体的自由意志,在非特权和非垄断资源占有方式中的体现,其核心是凡具有意志能力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体及其功能组织,获得了按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自身价值与发展目标的行动自由及其保障条件。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多元独立性利益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平等交易法则;二是符合社会分工体系的利益集团以及相应的自由流动空间和多种可能形式;三是平民意识及其大众功利主义。一句话,这种力量在市民社会中的直接表现就是,以最原始的个性要求来驱动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1](P132)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力量的存在与发展,不仅会导致诸多利益群体及其组织形式的出现,而且还使它们彼此之间的社会交换出现了地位与权力上的分化,形成社会经济生活“多元化”、经济利益“分殊化”、利益主体“异质化”的局面。易言之,市民社会的形成使社会发生出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团体组织,诸如:各种经济实体、产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等经济性组织;利益集团、压力集团等政治性组织;民众自发性联合体等民间自愿性组织。诸多组织一方面为个人提供必要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并保护其利益不被损害;另一方面也以社会的个体为其存在条件。基于此,可以更直接地说,市民社会的社会主体是个人和团体,其特质是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而非政治的,因而成员的活动形式,无论是纯粹的个人活动(包括为了家庭进行的各种谋生和社会交往活动),还是以个体为细胞,通过自愿和契约而成的团体组织(如公司、合作社组织,及各种非官方社团)之活动,都具有“私人”的性质。这样也就内在地决定了活动的利益诉求主要是为了个人或团体,而不是代表国家或者是政府的利益。
事实上,西方社会,正是在这种多元化的经济生活中,由于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被普遍公认是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则,国家要加以保护,社会个体也普遍加以捍卫,这样,作为利益主体的社会个体或社会集团从经济上获得了生存的独立性。经济上的独立性必然要导致社会生活的自主性。当社会个体的生活状态处于无保障境地之时,其很难谈独立与自由,也更谈不上自主性。而私有产权制度则为生活于这种制度下的社会个体提供了获得生存之坚实可靠的基础与充分机会,使社会个体由经济的独立而获得生存的自主性。不言而喻,这种由私有产权制度所衍生的利益自主的社会个体,在其面临国家政治权力的威胁时,会以契约为基础自发地组织各种政治的、经济的、职业的等等之类的社会团体来抵御这种威胁,以保护个体或团体自身的利益,免除社会政治与经济上的振荡。从这一意义上说,西方合作事业是在典型的市民社会中,具有契约人格和自由个性的商品生产者,在面对恶劣的经济社会环境及社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时(注:德国学者福斯特(Faust,Helmut,1977)和哈内尔(Hanel,Alfred,1992)对德国的合作社发展历程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经济社会环境恶劣和社会不确定性因素越多,社会成员对合作社的制度需求也越大。),为求保护自身利益而对产业革命后盛行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经济的一种反抗力量(或者说是一种“防御性力量”)而萌生的。合作社成员(最初主要是经济活动中的弱者)在合作运动倡导者及积极分子的推动下自发、自主地组织起来,以从中获得依存感和实现更多的公平和收益。之所以会如此,一个显著的因素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催酶下西方社会中的成员个体已经成为其自身利益以及知道如何促进这些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了。
由此可以粗略看到,奠立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以自由个性觉醒的个人和团体作为社会主体的市民社会,是合作制经济组织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同时,市民社会又是一个与市场经济密不可分的、以经济生活为主体和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为其基本指向的经济社会,而且契约作为其运作的形式,为经济行为的理性化、社会行为的秩序化提供了保证。所有这些,或者说成是不受国家支配的社会自主性力量的存在,是合作社组织“内生”和合作经济为一有效制度安排的社会性要素。然而,这一前提条件在20世纪的中国可以说是不存在的。
二、过渡经济(注:20世纪中国,尚处在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期中,市场经济和社会交换关系还极不发达,无论是前半期的小农经济的解体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是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乃至于现在的转轨经济,无不显现出过渡的特征。故用此语概括之。) 与依附性人格: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实在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随着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其国内市场呈逐步扩大趋势,但若从整体上考察,中国仍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广大农村还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不高。这一点可从粮食的商品率变化中看出,因为粮食等农产品的商品量在其产量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最能直接地反映出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程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承明先生的估计,1840年时我国粮食的商品化率约为10%,1895年约为16%,1920年约为22%,1936年约不足30%[2](P173)。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52年我国粮食的商品率约为20.3%,若再减去返销农村的部分,则为17.2%[3](P393)。这些数值都表明中国农民还远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本色,其生活资料自给的比重很大,对工业品的需求水平极低,而工业则是纯度很高的商业生产,城市人口又完全依赖市场交换来生活,那么,不论是工业品的交易还是农产品的交易,农民都没有重大的影响力量,大部分是由商人所控制。然而,商品关系是独立、自由与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低,农业生产者很少参与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交易活动,亦即农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分离程度较高,决定了农户的经济地位是不独立的,经济行为也无自主性,故其在市场经营活动中也就不可能居于主体地位。
同时就商品生产而言,市场因素十分重要,特别是外部市场的需求与诱导尤为重要。由于传统农业发展不充足,加之生产者个体与群体的消费能力有限,只有突破狭小的地方性市场的局限,也就是说只有在更大范围内使劳动价值得到实现,经济的市场化才有可能进一步的发展。然而,这一点的实现在当时也是困难的。虽然说,对外贸易与沿海市场在近代中国市场体系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国内市场与其联系仍然缺乏统一和顺畅的网络。居于国外市场和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农村基层市场,在多数地区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沿海地区形成的近代商业网,其向内地的伸展是缓慢的,并未使中国全部市场结构彻底改变,广袤内地和边远地区的市场仍保持着传统的特征。因而,统一的国内市场,只是处在形成的过程之中,极端强大与坚韧的自然经济势力处处设防,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以及制度变迁的滞后性如长期实行银本位制,顽固地抵制着中外经济联系的扩大和近代市场的深入[4](P35—36)。市场的网络越是到边远地区和内地,越是到基层即中级和初级市场,其资本主义化的程度越低,且保留的传统色彩越浓厚。其所起到的作用仍是以农民之间的余缺调剂为主,具有补充自然经济的性质。而且近代市场发育的这种不平衡性和有限性,使得社会交换相当的地方化,需求分布也极为分散化,以至于整个交换模式仍是分散型的[5](P154—155)。此种情况下,也就不可能以市场为基础对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进行大的转移与重组。所以,有论者说,20世纪的中国国内市场十分狭小,“还远非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6](P170)。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经济活动的分工程度和市场扩张能力的增强,及其交易半径的增大。市场的拓展促使了西欧完成了向现代市民社会的重大转变。由此我们可更深入地讲,市场交换关系的不足和市场交换规模的不大,实质上意味着作为社会主体法权人格自主意识和自我肯定、自我认同意识的缺乏。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泰勒(John·F.A.Taylor)所强调的那样:“交换,如果发生的话,存在于所有权的转移和双方各自所持权利的共同承认”[7](P289)。
经济领域有其自身独特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行规律,特别是市场经济,它本能地要求参与经济生活的主体能够行使自己的自由与权利,要求按照一定的规范并形成一种制度来对这种自由的权利加以确认和保障,结果必然会导致的社会分殊化和人际关系的契约化,最终形成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曾指出:“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8](P477)。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同构体,是市场经济对社会结构的改造过程的产物,它通过市场机制肯定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使个体摆脱封建体制或现代全能国家的束缚,从而解放每个人的创造力。而在商品经济不发达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之下,农民在相当大程度还不是具有自由个性与独立人格的商品生产者,加上“身份性社会”的制约和社会交换关系的匮乏,他们尚不需要也不可能建立只有在契约性社会才能生存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组织,故而也就不可能使社会生发出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团体组织,即所谓的“市场化力量”。对于这一点,中国的合作经济学者罗虔英说:“事实上,合作社确是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产生的,因为只有在大规模机械工业压倒小规模手工业的时候,才有手工业合作社的产生,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占优势的时候,才有农业合作社的产生,而且所有手工业合作社,或农业合作社开始时均以流通领域中信用业务为主,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条件之下,才有此实际需要”[9]。陈翰笙从中西方社会比较的角度也认为:合作社决不会把自己只局限在经济和商业的范围之内,“合作社从建立时起,就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产生了重大意义。对照欧洲来看,欧洲现代化城市的涌现,是伴随着自由公民的经济活动而来的。而中国在古老城市的大部分居民,则一向缺乏充分的经济和政治自由。普通老百姓向国家奉献贡赋,可是从无代表权以制定税制。他们反而要接受保甲制度,这个制度是维护统治安定和秩序的组织……这曾是维护国家统治的主要方法,在乡村和城市都施行这种警察统治”[10](P83)。毫无疑问,罗、 陈二人话语表达方式虽有所不同,但其内涵是一致的,字里行间都在强调市场经济和具有经济自由的社会个体和其独立自主性(特别是合作经济的行为主体——农民)对合作社经济组织的强大催生作用。
总的来说,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和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包括法人人格)的存在,是合作经济行为发生的“主体性”因素。因为具有独立利益和自主权的个体,他们之间的选择、协商、理解和举止是合作经济秩序得以生成的最终源泉。而20世纪的中国,尚处在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期中,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现代规模的资源流动、资源配置体制和社会交换关系,几乎没有或者说还极不发达(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同时在社会结构上仍是以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资源高度垄断、政府全面渗透和控制社会生活为特征,是一个分化程度较低、分化速度缓慢、具有较强同质性的“总体性社会”(也可说是“身份性社会”)。正如中外学者梁启超、陈独秀、孙中山、梁漱溟、马寅初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人对中西方社会的组织基础所分析的那样:中国社会是“家族本位”的社会,西方社会是“个人本位”的社会[11]。市场化程度的低下与中国的这种“家族结构式”(差序格局及家国伦理对个体的束缚)社会的耦合,形成了一种强固持久的掣肘性力量,使社会不可能形成或者说很难形成具有独立意识、个体利益和自由、自主权品格的“市场化力量”,以为合作社经济的运行提供支撑实力。
三、合作制经济与身份性社会的二律背反
任何一种经济行为都是嵌入在相当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限制同时又促成人们的经济行为。西方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和成长导致社会领域相对于国家的自主化而问世的。而市民社会的形成又造就了经济地位具有相对独立性、经济行为又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社会主体。正是以此为基础,内在地促生了西方的具有社会自治性质的合作社组织和合作经济制度。而20世纪中国的所谓“合作经济”,则是受西方合作经济思潮影响,在自身先天条件不足情况下的一种外部植入或“嫁接”。所以,从发生学角度来看,西方的合作经济是由社会自下而上自发、内生的;中国的则是在富民强国之功利的驱迫下对西方合作经济的“贩卖”,即“移植型”,最终又借助于政府的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形成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注:对于这一论点的详细研究或论述可参阅笔者博士学位论文:《政府·合作社组织·乡村社会》,华东师范大学2002年度;和博士后研究报告:《理论与现实的张力:西方合作经济理论与20世纪中国》,上海财经大学2004年度。)。可以说,前者是民众作为创新主体,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确立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的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后者则是由政府为创新主体,借助行政、经济、法律手段自上而下组织实施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创新。
也正是这种“先天的不足”必然带来了“后天的失调”。早在20世纪的40年代,合作经济学者陈仲明就已从反思的角度对中国合作事业进行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困境做出了总结:“从理论上讲合作运动在中国,既有发展的必要,也应该有其发展的可能的,可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变革,关系方面太多,也太复杂了,所以事实的表现,与据理的推断之间,往往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本来,合作运动是一种社会经济改革运动的具体实践形态,而事实的表现,往往非但对社会经济的改革无补,反而为经济现势中的坏的权力倾向所操纵或所利用,乃至于为其所控制。同时,合作社是社会经济弱者的自救运动的组织,是为改善社会经济弱者的经济生活,为提高社会经济弱者的经济地位的,同样,事实上的表现,也往往非但不能完成此项使命,反而握有社会经济操纵权的强者所利用,加强对社会弱者的压榨和窒息,中国过去合作运动的情形,虽未必尽走上反作用的歧途,但究竟有多少社会经济弱者(也就是广大的人民大众)在合作运动的开展下改善了生活,提高了地位,却也是很难说的,至改革社会经济的不良制度,矫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良倾向,那更是有心人的一种希望了。”在此之上,他更深入地强调:合作在经济上效用的发挥非但是其“真实灵魂”的存在,而且“本质上,也就是表现民主精神的一种尺度”。但这一切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有着极大关系,在民主体制的制度下,“代表人民的经济利益的合作组织,自能发挥其民主的精神;否则,整个政治经济的体制如果是在独占、操纵、垄断的情形下,则合作组织的民主精神往往被阉割,合作运动的灵魂往往被出卖,合作的效用,亦就往往被变质的利用”[12](P353—354)。 契约性关系是自由、民主、平等存在的前提和保障,而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身份性社会和习俗经济,却是以压抑人的个性自觉和否定契约人格为条件的,靠其来推动商品生产者的契约性联合,实现社会个体利益的组织化,无异于缘木求鱼。即便是勉强地合作起来,也是一种“有组织的无秩序状态”中的“垃圾筒”模式。
合作经济制度必须同相应的制度运行环境结合,才能展现它的效率、民主、平等诸价值。否则的话,合作只能是一种“浮面的东西”而乏持久的社会基础。这一“环境条件”就是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包括法人人格)的存在[13](P373)。从质上言,也就是要实现从身份性社会向契约性社会的转变。英国法律史家梅茵(Henry Marine)在其名著《古代法》中写道:“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义务上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关系就是‘契约’。……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4](P96—97) 只有在“契约社会”或者说“市民社会”, 社会成员才能挣脱以家族为核心的“礼俗文化”(或称之为“臣民文化”)形成的羁绊,走进具有普遍理性的公民意识,进而成为拥有独立个性的社会主体。马克思也说,“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彻底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则,个人的生存是最终目的;活动、劳动、内容等等都不过是手段而已”[15](P345)。合作社组织,就是经济理性精神成熟的自由个体在竞争中为求生存和实现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现代化的合作经济只有在现代契约性社会取代传统依附性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更直白地说,只有构成社会的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以及知道如何促进这些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时,合作制经济才能得以良好的进行。20世纪以来中国的合作事业(其中也包括建国以后的合作社、人民公社一直到现在的合作社经济等)和前苏联国家推行的合作制经济出现的困境,也都从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合作制经济的制度安排之基础是拥有所有权的私人之间的一种合约,契约性与依附性两种不同甚至是对立的社会性质与经济关系,是这种以契约为依托的合作制经济在依附性社会陷于危机的根由。
总而言之,合作制经济是市场化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它的生存与发展是以市场经济为经济背景的。也就是说,合作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就在于“农民的商业化”(或者是农民本身的现代化),即从不愿冒风险和“生存导向”的行为者转化为对部门间获利机会、市场价格、利润和财富积累敏感的现代经济行为者。所以,在不存在具有自由个性的商品生产者的自然经济(注:自然经济之中虽然也有一定的市场交换,但人们交换的频率、规模及交换市场的“半径”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人们的交换多是“亲临的”,用哈耶克的说法就是“face to face”,或用诺思的说法交换是“personal”。市场交换也多发生在族人、亲朋、邻里和熟人网络间,在这其中习俗和惯例是交换中人们遵循的准则,同时个人的信誉、熟人关系、亲朋网络、私人情谊、知识经验在交换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很明显,不同于人际关系已抽象化、交换也变成“非个人化”(impersonal)的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缘此,也有人称此种传统经济为“习俗经济”(customary economies)或“惯例经济”(conventional economies)。) 情景下,或者是在对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否定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或命令经济)状态下,都很难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组织。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合作事业在中国推行时会“淮橘为枳”,孳生出为众多人士所诟病的“质”的问题,诸如农民及其他社会阶层对合作社意愿不高;社员合作精神涣散,与合作社关系疏远;合作社业务单一,成为金融资本的尾闾;丧失合作社职能,缺乏生命力等现象[16]。这也就是为什么20世纪的中国(近代中国乃至于建国后)出现“异化”合作社和合作社“异化”的根本之缘由。
标签:市民社会论文; 农业合作社论文; 经济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农民合作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