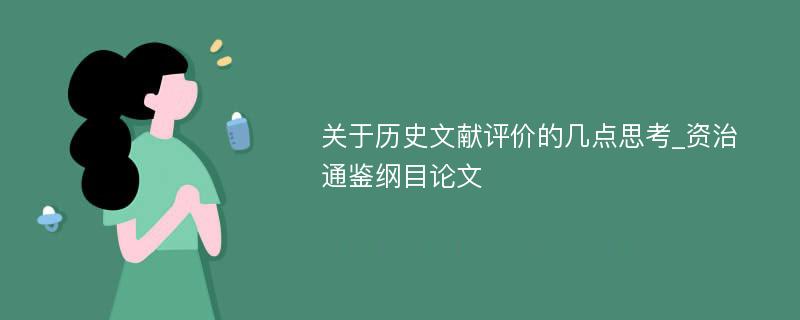
有关历史文献评价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文献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210(2016)02-0051-05 翻检当前的各种有关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的论著,可以发现对其评价普遍不高。仓修良先生撰写的《朱熹和〈资治通鉴纲目〉》①一文,对既有的成说提出了疑义,从《纲目》在促进史学走向社会、走向通俗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入手,另辟蹊径地发掘了《纲目》的史学社会价值。在这一启发和引导下,我们认为关于朱熹《纲目》还存有诸多待发之覆,如今人评价和古人评价有何差异,为何出现这种差异,为什么今人之评价如此,今人之评价有何问题,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历史文献,等等。 一、古今评判《纲目》之悬绝 为了突出反思今人对于《纲目》评价的主题,我们不妨先梳理一下今人对于《纲目》的评价。 正如上言,总体上来讲,今人对于《纲目》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的。“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和“无甚史料价值”的评价基本上是当今学者为《纲目》所下的普遍断语。在当今诸多学者眼中,《纲目》绝算不得史学“名著”。仓修良先生在编写《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时曾作过一个调查,“启动之前,曾拟定了一份收入史书目录,于是将朱熹的《通鉴纲目》也收入其中,并分别寄请多位师友征求意见。从反馈的意见来看,还是很少有人同意收入此书”②。朱熹《纲目》在当今社会的惨淡际遇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普遍的中国史学史做法,是把朱熹及其《纲目》依附于作为史学名著的司马光《资治通鉴》之后,寥寥几笔简单带过,这无形中把朱熹《纲目》的价值消解在了《资治通鉴》的光环之下。固然,这种情况与《纲目》的创制确实导源于《资治通鉴》及相关著作的史实是相一致的,但这是否也反映了当今学者们往往认为《纲目》从总体上来讲并不具备独立的史学价值这一学术倾向?一些史学史通史论著对《纲目》甚至只字未提,是否正是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 朱熹《纲目》之于当今的不受重视还体现在当今学者有关朱熹史学研究重心的偏离上。目前,学者有关朱熹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朱熹的一般历史观和史学观上,如关于对待史学态度的“倡史”和“反史”之说③,又如关于编纂思想、史学思想、史学方法等等。对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朱熹历史与史学理论实践之作的《纲目》则关注较少,学者们在研究朱熹史学的一般原则和方法时,也很少以《纲目》所包含的相关史料作为立论依据。为数不多的几篇以朱熹《纲目》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文章,论述的重心也多集中在朱熹和赵师渊分别在《纲目》成书中的作用的争论上。虽然此种研究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纲目》的基础,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学者们对于《纲目》研究重心的偏离起码说明了对《纲目》的正面研究亟须加强。 这里还需要特别交代的是,当今学者对于《纲目》也并非全然否定,比如对其开创的“纲目体”这一新体裁也是褒扬有加的。“他错综《资治通鉴》而成书的《资治通鉴纲目》,为我国史学增加了一个新体裁——‘纲目体’。”④“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⑤梁启超曾论及这一体裁的优点,“这体的好处,文章干净,叙述自由,看读方便。”⑥看来,“纲目体”新体裁的创制是当今学者肯定《纲目》的主要原因。在这一前提下,纲目体“看读方便”,即其于历史知识普及方面的贡献,也是当今学者主张重新认识和评价《纲目》的另一原因,如前已提及仓修良先生所论。 而朱熹《纲目》在古代,则是一幅全然别样的境况。 《纲目》于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首刊于泉州。嘉定十六年(1223),《纲目》就为经筵讲读官进呈于宋宁宗。理宗端平二年(1235),诏太学生陈均依《纲目》例编《宋长编纲目》。嘉熙元年(1237),以《纲目》下国子监并进经筵。咸淳十年(1274),经筵讲读官再进《纲目》于度宗。宋代学者们也是对其推崇备至,如真德秀言:“深乎信《春秋》以来未之有也,为人君而通此书足以明德威之柄,烛治乱之原;为人臣而通此书足以守经事之正,达变事之权,盖穷理致用之总会而万世史笔准绳规矩也”⑦。“穷理致用之总会”说明的是《纲目》在经世致用方面的普适性,而“万世史笔准绳规矩”则说的是《纲目》史法的楷模作用。可见,宋人不仅从对“君”和“臣”作用的角度,也分别从历史和史学的角度,极大地发掘了《纲目》的价值。《纲目》在宋代的影响,还表现在一批以续补、辨正、发明《纲目》为务的史籍的问世,如周密《纲目疑误》、尹起莘《纲目发明》、刘友益《纲目书法》等。需要我们特加注意者,即对《纲目》的辨正,学者们并不是针对朱熹发难,“朱文公《通鉴纲目》条贯至善,今本草行于世者,于唐肃宗朝直脱二年之事,亦由门人缀辑,前后不相顾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后,至于天祐之季,甲子并差。考求其故,盖《通鉴》以岁名书之,而文公门人,大抵多忽史学不熟,岁多故有此误。”⑧他们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其门人。这和当今学者把过多的精力投入争论朱熹和赵师渊分别在《纲目》成书中的作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入元以后,统治者和学者们对《纲目》的关注和褒扬依然如旧,并出现了一些进一步深化的气象。“纲目体”本质上来讲仍然为一编年体,但是由于其纲目清楚、便于阅读,更便利于宣扬古代封建礼教,一些史籍依从于《资治通鉴》并续补之,书名包含“通鉴”两字,但实际所用体裁已经具备了“纲目体”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元初金履祥的《通鉴前编》,“盖此书凡所引经传子史之文,皆作大书,惟训释及案语则以小字夹注,附缀于后,盖避朱子纲目之体,而稍变《通鉴》之式”⑨。从此书后来的刊本改名为《资治通鉴纲目前编》来看,都说明了以《纲目》为代表的“纲目体”大有取代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的趋势。到了元朝末年陈桱的《通鉴续编》,其虽仍名其为“通鉴”,但实际已经明确使用了“纲目体”,无怪四库馆臣如此分辩道:“其二十二卷皆宋事,始自太祖,终于二王,以继《通鉴》之后,故以《续编》为名。然大书分注,全仿《纲目》之例,当名之曰《续纲目》。仍袭《通鉴》之名,非其实也”⑩。饶宗颐先生所谓“金元之际,《通鉴》之学最盛”(11),这里的“《通鉴》之学”固然包含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影响,但《纲目》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愈益显化的。同时,此时期还出现了大量以解释和疏通《纲目》寓意的著作,如刘友益《通鉴纲目书法》、郝经《通鉴书法》、王幼学《资治通鉴纲目集览》、徐昭文《通鉴纲目考证》、金居敬《通鉴纲目凡例考异》、吴迂《重定纲目》等等,不下十数种之多。 明、清以降,《纲目》的地位愈益显贵,其受推崇渐超于司马光《资治通鉴》之上。明代学者叶向高言:“国朝列圣崇重表章,颁之学宫,令士子颂习,与六籍等。”(12)“与六籍等”的评价说明了《纲目》的学术和政治地位。并且,在许多学者的眼中,《纲目》有超越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趋势,“及我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表章四书五经,颁降天下,而《纲目》亦与,则视《资治通鉴》盖加显矣”(13)。从后来元、明、清三朝以“通鉴”命名的史书,大部分都采用了朱熹《纲目》的“纲目体”,而非严格遵循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体”的史实来看,朱熹的《纲目》于古代确实有超越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趋势。 不仅如此,《纲目》的影响并非仅在中原皇朝的史学系统内发挥着持久的影响,近现代的考古发掘和域外文献的发现也表明,朱熹《纲目》在古代中原皇朝以外的各少数民族政权或邻近国家中都有相当的影响。(14) 二、忽视实际传播过程:今人评判《纲目》时的一个普遍缺憾 在梳理、对比了今、古学人对于《纲目》截然不同的态度以后,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出现一个想法:古今态度何以如此悬绝? 有关于此,自然原因很多,前贤们都或多或少地对他们之所以褒、之所以贬给出了各自合乎情理的说法,前文多少已有涉及。就当今学者对《纲目》的态度(褒也好,贬也罢)而言,几乎不约而同地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即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纲目》的实际影响。这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今学者们在评价《纲目》时,没有很好地考察《纲目》于后世的实际流传情况;二是虽然对《纲目》的流传情况多有涉及,但并没有真正地把《纲目》的影响纳入我们评价《纲目》的体系中来。 有关于前者,其思路基本是这样的:《纲目》的评价自然要以《纲目》文本作为我们所依据的主要对象,直接从《纲目》的文本出发来评判《纲目》的价值自然是最为直接,也最为可靠的一个途径。此说自然有其道理,但仅从现存《纲目》文本出发来评价《纲目》的价值,在一般情况下其中也还存在一个潜在的理论预设,即评价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来讲不是《纲目》生发时的古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其更多依托的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价值理念。如当今学者对于《纲目》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的批判,显然就是这一理论预设的典型代表。又由于《纲目》本身历史内涵的丰富性,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自然能够得出不尽相同的评价结果,从而使得我们的研究各说各是,形成不了有效的交集,推进《纲目》的研究更是无从谈起。我们认为,史籍的产生自是一个层面的问题,而其传播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虽然两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产生”是“传播”的基础和前提,但我们并不能以此“产生”而完全漠视彼“传播”。 关于当今学者没有把对《纲目》流传情况的考察有效地纳入《纲目》的评价体系中来,一个显在的表现就是我们的学术研究思路是把价值发掘和影响梳理分为两途的。在文本呈现上,一般的做法是把影响梳理放在价值发掘的后面,这就使得价值发掘或评判的工作既已完成,影响的梳理也就无足轻重了。一定程度上,影响的梳理这一部分,往往沦为我们为了追求文本完整性而不得不记的一个部分。仓修良先生曾深刻地剖析了自己对《纲目》的研究历程,“然而对于这样一部史书以及在它影响下产生的一系列著作,在当代史学研究中,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原因在于一般总都认为它对于中国史学发展影响不大,因而在许多史学史专著中竟无一席之地。笔者本人也曾有过这样的看法,如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中,虽然列有一目作了介绍,但最后却说:‘尽管《纲目》在史学上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但其影响和流毒却是十分深远的’。这一说法显然是很不妥当的,只要深入加以研究就会发现,该书产生以后,不仅新增了一种史体,产生了一系列纲目体的历史著作,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为史学走向社会、走向通俗化开辟了道路”(15)。仓先生这段话不可谓不深刻。它向我们说明了一个道理,即史学传播过程不在场的历史评价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没有系统考察《纲目》在“史学走向社会、走向通俗化”等文化传播方面的价值,仅仅建立在《纲目》文本基础上的脱离历史时代、就物论物式的评判,得出“流毒却是十分深远的”的结论就在情理之中了。其实,对于这一问题的反思在历史学领域已经发生,如秦晖先生在分析古代社会“儒表”与“法里”的问题时言:“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典籍中的思想,尤其是这些典籍中思想的形而上层面。这种关注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性的还是‘社会思想’而不是‘典籍思想’”(16)。如果理解不差的话,仅仅以《纲目》文本展开的脱离时代现实、就物论物的方法显然可以比附于“典籍思想”,而充分梳理了《纲目》社会影响并把其纳入对《纲目》评价体系中的做法就可比拟为“社会思想”了。很显然,可以代表实际影响的“社会思想”与大致停留于“形而上”层面的“典籍思想”相比,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研究,因为它更贴近历史发生的实际。 因此,我们主张在整理和发掘历史文献时,不仅要对此一文献的传播过程大书特书,而且要真正把对这一过程的梳理充分地纳入对于这一文献的评价体系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充分发掘历史文献价值的愿望具备基本的前提。不如此,我们的研究就会在既否定《纲目》价值而又无法完全漠视其在社会实际层面的巨大影响的旋涡中打转,无所适从。 三、“历史地”:史学评价的一个基本立场 古人对于《纲目》的评价,已经充分地把其实际传播过程纳入其评价体系中,其实,当今学者对于《纲目》的有限肯定也多少有从这方面立论的表现。如肯定《纲目》在体裁创新上的“纲目体”,其着眼点还是就其于实际传播过程中的影响而言,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谓“看读方便”。也就是说,现代学者和古代学者在评价《纲目》时,虽然程度不同,但还是存在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都不同程度地把《纲目》的实际传播过程纳入对它的评价中来。但从评判的结果上看,其差别还是巨大的。明白了上述所论当今学者忽视《纲目》影响的两个层次,我们可以第二个层次以为解,就是说,虽然认识到了《纲目》的影响巨大,但并未把这一认识有效地纳入其评价中。这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仅以此论,恐未必周全。也就是说,当今学者们不够重视《纲目》于实际层面的影响过程,或者没有把其对实际层面的影响有效地纳入对它的评价体系中,并不能完全解释古今对《纲目》评判依旧悬绝的事实。另,为什么我们会不同程度地忽视《纲目》的传播过程及其影响?这些都逼迫着我们对今人的评判作进一步的反思。 我们进一步反思的展开还得从当今学者对《纲目》批判尤烈者入手。可以说,当今学者批判《纲目》的一个普遍的、几乎无一例外的口实,就是宣扬封建纲常名教。确实,这从《纲目》卷首《凡例》中明正统、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等内容的规定上都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也正是看中了《纲目》在维护其统治上的这一点,才对其激赏备至,褒扬有加。古代学者们也对《纲目》在有治于世道的层面上给予了充分肯定。前引真德秀“穷理致用之总会”的评价就是对《纲目》经世特点最为直接和贴切的肯定。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同样在肯定朱熹及其《纲目》经世特点的前提下,古代学者出现了“万世史笔准绳规矩”的褒扬,而当今学者却出现了“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的批判,这种迥异的差别只能说明古、今经世内涵的差异。 古人有古人经世的标准,今人有今人经世的内涵,那我们的历史研究究竟该依从于哪一个?有关于此,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要历史地考察历史问题。所谓“历史地”就是从历史的时代背景出发来认识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纲目》产生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封建专制时代。而且,联系到朱熹是一个有着强烈“得君行道”愿望,并且付诸政治实践的历史人物(17),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纲目》于其时的现实意义,绝不能将其理解为朱熹无所事事时消遣的玩物,更不是供我们后人把玩的工艺品,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诉求,宣扬封建伦理纲常是其“得君行道”经世价值诉求的必备前提之一。而现代学者往往在论述《纲目》经世学术特点时,对其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只字不提,把《纲目》宣扬封建伦理纲常视为其经世诉求的这一基本前提当然地忽略掉,从而使所谓“历史地”评价历史问题成为一句脱离历史事实的口号。余英时在研究理学家的政治活动时指出:“我们绝不能以现代的观点看待理学家的政治活动,讥笑他们对‘君’抱着太多的幻想。非历史的态度不能导致严肃的历史了解。”(18)这种做法正像基思·詹金斯在批判埃尔顿时所言:“它自我吹嘘地赋予解码者优于被解码之作者的特权。”(19) 其实,上述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是价值判断标准选择的问题,但其本质却是对有关历史价值和意义问题的追问。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目前仍然在争论、未来也很有可能不能有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的问题,但一些学者的观点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启发,如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所总结的科林伍德的观点:“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一个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活在现在之中的过去”(20)。这句话中有关“现在”与“过去”的紧张思考维度,对我们在认识《纲目》的经世与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并存的情况时不无指导和启发意义。当今学者对于《纲目》宣扬封建纲常名教特点的批判固然合理和必要,但也要注意到这种所谓“落后性”的东西,其另一面就是我们在其他场合所极力推崇的经世学术传统。白寿彝先生在《谈史学遗产》中言:“朱熹用《通鉴》的材料,节缩成《通鉴纲目》,不只要提供经验,并且要通过史书去宣扬封建专制主义。”(21)这段话告诉我们,强调封建伦理纲常与主张经世致用,只是以《纲目》为代表的朱熹史学一体之两面,不可全然否定和肯定。这同样要求我们在对历史文献进行研究时,一是要注意在不同的场合下、在不同的文章立意下来发掘其价值,二是要不管从何种角度立论,历史地评价历史文献都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这样的反思在现代学者中也已然发生,如向燕南先生在考察朱熹的“重义”史学观时就指出:“如果我们将朱熹这种‘重义’的史学观,置于理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对北宋以来越来越专制的君权思以限制的思想语境下考量,则朱熹等人坚持‘王政’的政治立场之欲超越历史一时成败而为历史‘立心’、引领历史向善的苦心,则未尝不可不使我们从价值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两个方面同情地理解或再认识传统史学家‘重义’的道德批判意向。”进一步而言,如果我们能尽量规避“认为传统道德已沦为恶之渊薮”的“极端情绪”(22),那我们就可能会透过《纲目》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的“罪恶”面纱依稀看到其另一面的历史价值。当然,这一方面我们还有诸多难以割舍的时代感情和难以回避的思维定式。其实,从根本上来讲,完全脱离我们时代价值影响的历史研究也不可能产生,但为史学健康发展计,我们起码也要时刻以此警醒,并努力做到历史地评价历史问题。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批判历史文献的落后性时不表现得义愤填膺,理直气壮,“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23)。而在发掘优良传统时又不表现得唯唯诺诺,完全无条件地热情拥抱。 ①②仓修良:《朱熹和〈资治通鉴纲目〉》,《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 ③许家星、何发苏:《反史倡史,一体两面——朱熹史学态度辨惑》,《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④汪高鑫:《试论朱熹史学思想的积极因素》,《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⑤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卷首《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页。 ⑦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昔人著书多或差误》,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⑨⑩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7《〈通鉴前编〉提要》,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页。 (12)叶向高:《苍霞草》卷8《重刻通鉴纲目序》,四库禁毁丛书本。 (13)许浩:《宋史阐幽》卷1《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明崇祯元年许锵刻本。 (14)请详参胡玉冰等《黑水城〈资治通鉴纲目〉残叶考述》(《西夏研究》2012年第2期)、杨雨蕾《〈资治通鉴纲目〉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世界历史》2002年第3期)以及戈振等《试论越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编撰及其若干问题》(《史学月刊》1995年第6期)等文。 (15)仓修良:《朱熹和〈资治通鉴纲目〉》,《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 (16)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 (17)详参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得君行道”——朱熹与陆九渊》、《朱熹“立朝四十日”辨》等章节。 (18)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22页。 (19)基思·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埃尔顿到罗蒂和怀特》,江政宽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4页。 (20)[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19页。 (21)白寿彝:《谈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41页。 (22)向燕南:《史学的求善诉求与传统史学之道德批判的省思》,《人文杂志》2013年第12期。 (23)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