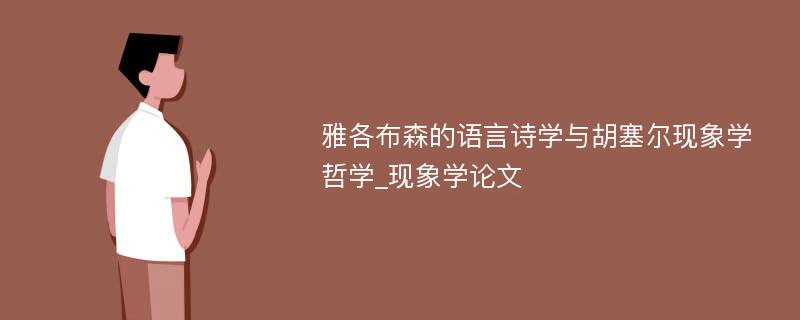
雅各布森语言诗学与胡塞尔现象学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各布森论文,诗学论文,现象论文,语言论文,学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5)-014-05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5.02.03 “现代思想当中的现象学思潮,对于我们不依赖价值给我们头脑的体现形式而辨别每一价值帮助很大”,[1](P375)1942年,著名语言诗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在评价波兰现象学语言学家波斯的《现象学与语言学》时这样说道。其实,对语言进行现象学研究不仅是波斯所做的,更是雅各布森所做的,其所接受的正是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1915年左右,雅各布森开始阅读胡塞尔的著作,他后来说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至今仍然是语言现象学论著当中最能赋予人灵感的著作之一”,[2](P91)“或许对我的理论著作产生了最大的影响”,[3](P73)这并非虚言。要论述雅各布森语言诗学与胡塞尔现象学哲学的关系,我们不得不从心理主义语言学研究开始谈起。 20世纪初,语言学被当作是一种解释工具的心理学,心理主义成为语言学者们非常刻板的信仰,这正是俄国当时推崇“联想心理学”的“库尔特内学派”的突出特征。在库尔特内看来:“人类语言的本质完全是心理的。语言的存在和发展受纯粹心理规则的制约。人类言语或语言中的任何现象,都同时又是心理现象”(《文选》),[4]也就是说,人类的整个语言(语言进程)只不过代表了一个联想的整体,这种心理主义的保守观点主导了俄国。在此背景下,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第一部分被译成俄文后(1909),立即在莫斯科产生了巨大影响。出于对德国哲学天然的亲近和接受,俄国语言学界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语言学者自然萌生了一种以胡塞尔式的视角来反心理主义的倾向。 当雅各布森在莫斯科大学开始语言学研究的时候,自然也受到这种影响。在老师切尔帕诺夫的研讨班上(1915-1916),雅各布森第一次熟悉了格式塔基础理论,并仿照考夫卡写了一篇关于“词语形象”的学期报告,最重要的是,胡塞尔哲学给他们带来了一次印象深刻、影响深远的训练,无论是狂热的心理学者还是激进的胡塞尔主义者,都受到同等欢迎,而他们的争辩都有着很高水平。在这群胡塞尔主义者中,就有雅各布森亲近的朋友之一、胡塞尔的俄国学生——什佩特,正是由于他的著作和演讲,使得莫斯科的语文学家们(包括雅各布森)对“形式”与“意义”、“符号”与“所指”这样一些形而上学观念逐渐熟悉起来。 1935年11月,76岁高龄的胡塞尔应布拉格“哲学学派”邀请来到布拉格,在卡尔大学等地就“欧洲科学和心理学的危机”问题做了几次演讲,并对布拉格“语言学派”宣讲了“语言的现象学”。当时雅各布森作为“语言学派”的副主席迎接了胡塞尔,并公开表示: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对普遍语言学的现代发展,特别是对句法、语义和纯理论性从心理主义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发挥了重要作用;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对莫斯科年轻的语言学者来说是一本“准圣经”,在战争时期他们甚至不得不通过非法的办法从源头来获得这本书。雅各布森这样说并非客套,因为在这之前的文章《何谓诗歌?》(1933-1934)中他就明确说道:“现代现象学正在揭示一个语言学的虚构。它巧妙地证明了符号和所指定的对象之间、词语的意义与内容(意义被定向于它)之间的最重要的区别。”[5](P377) 似乎雅各布森受胡塞尔影响是铁定事实,但奇怪的是,在1930年代雅各布森的著作中几乎没有对胡塞尔明确的引用或参考,而且在很长时间里,“胡塞尔”在雅各布森那里只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反心理主义者”而存在的。追溯来看,雅各布森在其《俄国现代诗歌》(1919)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胡塞尔,他指出,在某种新词中“胡塞尔所说的指涉事物的关系(dinglicher Bezug)”①是缺失的,这可说是他的莫斯科岁月中最前沿的反应。然而,这种对《逻辑研究》中一种理论元素的引用是完全中立的,并未对胡塞尔有任何具体评价;而且,他在质疑语音结构时使用的完全是心理主义而非反心理主义的语言,比如“联想”、“语言思想”、“分解”等库尔特内的一些标志性术语。当然,雅各布森在1920年代早期又确实批评了心理主义,比如在1923年他和博格达耶夫合写的一个关于俄国语言学的声明中,什佩特的语言学被批评为“语言学和心理学不合逻辑地融合的严重后果”。[6]可见,雅各布森此时在心理主义和反心理主义之间还是犹豫不决的,胡塞尔的影响尚未明确显现。 俄罗斯先锋艺术为雅各布森提供了重要的反心理学手段。在评论“未来主义”艺术的文章《未来主义》(1919)一文中,雅各布森专门讨论了形式和色彩互相依赖的法则,并指出其理论来源在于胡塞尔的老师、实验现象学的奠基人——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施图姆福: 本质上而言,色彩创造性的神秘在于引向这样一种认识法则:任何形式的扩张都伴随着一种色彩的改变,而任何色彩的改变都生成新的形式。在科学中,这种法则看起来首先是由施图姆福提出的,他是新心理学的先锋者之一,他谈到色彩和色彩的空间形式之间的关联:广延(extension)的改变和质化(quality)的改变是相应的。当广延改变的时候,质化也发生转换。质化和广延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和不能被彼此单独地想象。这种必要的连结,不同于两个部分缺少必要性的经验主义连结,比如头和身体,这样的部分能被单独想象。[5](P29) 雅各布森在此处的注释中提到,他所参考的著作是施图姆福的《关于空间观念起源的心理学》(1873)。施图姆福那时把自己关于现象的前科学称作“现象学”,但毫无疑问,他的“现象学”比后来他的学生胡塞尔的“现象学”要狭窄得多,至少他排除了胡塞尔《逻辑研究》时期现象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功能”或活动,并且“现象”没有经过“现象学的提纯”,而仅仅是处于心理学层面上的现象。但不可否认,胡塞尔将《逻辑研究》题献给施图姆福,不仅表示对老师的尊敬,更意味着二者之间的承继和相似,“二者都想从对于直接现象不偏不倚的描述出发。二者都同意寻求比单纯经验概括更多的东西,研究这些现象之中和现象之间的本质结构。二者都承认逻辑结构的世界是某种与单纯心理活动分离的东西。”[7](P109) 雅各布森通过阅读《逻辑研究》中胡塞尔论及施图姆福的那些部分,转而又直接阅读和借鉴了施图姆福的实验现象学理论,因为胡塞尔的整体与部分的逻辑明确贯彻了施图姆福的早期观念,所以,雅各布森在这里所引用的中心意思依然是与胡塞尔的“部分与整体”的逻辑相关的。他关注的是“感知”中的独立与不独立内容(independent and dependent elements),以及一种观念:一个复杂的整体不能拥有任意的构成部分,整体所具有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联结的,在绘画中,色彩(质化)和色彩的形式(广延)是不可分割和独立存在的,这种整体关系不同于头和身体的关系。胡塞尔是在形式本体论的范围内,由第二研究中所讨论的“抽象”与“具体”,过渡到第三研究中所讨论的“独立”与“不独立”以及最后的“整体”与“部分”的。所谓“部分与整体”准确地说是观念的整体(或作为整体的观念)和观念的部分(或作为部分的观念),在胡塞尔看来,“整体”并不等于无论大小都相对独立的内容,而“部分”也不意味着就是相对不独立的内容,这实际上就突破了施图姆福的“独立内容与不独立内容”的理论框架,而进入到纯粹形式理论的论域中。 承上所言,虽然雅各布森直接引用的是施图姆福,但他把作为心理学“工具”的语言转换为后来的一种反心理学的、感知现象的静态描述的语言,却是借用了胡塞尔的“部分与整体”的现象学学说,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三研究题名为“关于整体与部分的学说”,就探讨了这一法则作为一个系统、一个统一体的构成问题。雅各布森后来在《语言的整体与部分》(1963)一文开篇便明确说道:“在这部著作的第二卷中,有两篇文章涉及‘整体与部分’,介绍了这位哲学家对‘纯语法理念’的深刻思考。尽管语言的整体与部分在许多方面互相依存,但是语言学者却容易忽略它们的相互联系。”[2](P91)雅各布森自然不会有这样的“忽略”,因为他的结论是:“语言的结构包含整体与部分丰富的张力级别。一方面,部分为整体;另一方面,整体为部分,这些都是语言基本的手段。”[2](P96)也就是说,部分总是“整体的部分”,而整体总是“部分的整体”,他将胡塞尔的现象学学说与格式塔心理学相结合,恰当地应用于语言科学的系统研究和层级研究中,从而区别于形形色色的割裂主义的语言学研究。 这一思路同样体现在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历史观中。在《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问题》(1928)一文中,他认为:“文学史(或艺术史)和其他历史系列是密切联系的;历史系列中的每一种系列都包括一堆特有的复杂结构规律。如果预先没有研究过这些规律,就不可能确立文学史和其他系列之间严格的类比。”[5](P47)可见,雅各布森强调对文学系统内部结构规律的研究,把文学系统当作是和社会历史诸系统相互作用的一个独立系统,它既是整体的部分(社会历史系统中一个子系统),又是部分的整体(相对独立自足的文学系统)。这种态度无疑是对当时占主导的俄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文学史观的反拨,既驳斥了达尔文或斯宾塞式的生物进化般的文学演化论,也有别于机械封闭的、只专注于手法的形式主义文学史研究。正如梅特钦科所言,“形式主义的错误不在于把艺术形式作为文学特点的一个方面予以集中注意。单独析取一个成分来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科学认识的合理的必要举动。形式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不理解形式本身,在于把复杂的综合体的一部分当作整体。”[9](P160)雅各布森充分认识到文学的综合性与复杂性,他以“部分与整体”的现象学思想有效地避免了形式主义诗学的简单化。 总之,整体性作为雅各布森结构主义思想的重要特征,其核心在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特殊关系,诚如霍伦斯坦所言,“正是在胡塞尔的著作中,雅各布森发现了结构单元运作的普遍法则的第一系统模式。”[10](P2)当然,也正如上节所述,其直接的经验感知和对“部分与整体”关系的思考是从先锋派艺术那里得来的,而雅各布森在讨论课上所学到的“格式塔心理学”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格式塔心理学也吸收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思想,着重于强调心理现象的整体性,并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与雅各布森在未来主义诗歌的时空里所感受到的正可以两相印证,按其所言:“正是在诗歌里,部分与整体的重要关系非常鲜明,这激励我们通过运用胡塞尔和格式塔心理学的规则于这些基本问题,来深入思考和证实他们的教义。”[11](P11)而在1940年代进入美国学术圈后,他更明确地感受到自己与布龙菲尔德语言学派的根本分歧正是这思想来源的不同,他说:“我渐渐发现,我思想方法的倾向越来越朝向现象学,并与格式塔心理学的体验相近,而根本不同于行为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而行为主义者对美国学者尤其是语言学家的思想仍产生着巨大影响。”[11](P43) 此外,按胡塞尔所言,“整体与部分”的纯形式理论的核心是“奠基关系”(Fundierung),也就是说,如果一个A根据本质规律性在其存在上需要一个B,以至于A只有在一种全面的统一性中与B一起才能存在,那么A便是通过B而被奠基,A与B之间的关系就是奠基关系。奠基既可以是相互性的,也可以是单方面的:A选择B,B也选择A,即为相互奠基;A选择B,但B不选择A,即为单向奠基;在后一种情况中,被奠基者如果没有奠基者便不能存在,但奠基者如果没有被奠基者则能够存在。[12](P285-289)在雅各布森那里,胡塞尔的奠基关系即“意指关系”(relations of implication),构成了自然语言的系统,“双向奠基”和“单向奠基”分别对应于“双向意指关系”和“单向意指关系”,即意指的相互关系在哲学系统的二元组织中得到表达,单向关系体现在它的层级组织中。比如,在音位系统中,区别性特征如尖与塞、浊与清、圆与不圆等,彼此相互意指,二元对立的一方必然暗示它的对立面;而从最低的音位区别性特征层到最高的文本(语篇)层中间依次需经过音位层、音节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层、句组层:这种从低到高依次建立、从高往低依次辖属的层级关系,建立起自然语言系统的金字塔结构。总之,语言结构之所以具有系统性或整体性,应该归功于在胡塞尔“奠基关系”影响下构想出的这些意指关系。② 紧接着上段引文,雅各布森又借用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核心术语——“意向”: 对绘画而言,意向(set)于自然,为那些内容上断裂的部分创造了一种强制性的关联,而形式与色彩的相互依赖没有被认识到。相反,意向于图像表达,却导致一种对形式与色彩关联的必要性的创造性认识,在此情况下,客体被其他形式(所谓点彩画法)自由地渗透。[5](P29) 在注释中,雅各布森明确表明,俄国术语“意向”(ustanovka)是由德语Einstellung转借而来,是一个标示“知觉”的哲学术语,是感知者在确定客体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视点或精神意向。虽然雅各布森是在现象学意义上使用了“感知”概念,③却并未直言借自胡塞尔,但毫无疑问,他从现象学中借用此术语意在说明感知绘画的主体性原则,即作为意识主体的感知者对绘画的意向体验,如果以客观“自然”为意向对象,那么,意向行为的核心内容即模仿自然的意义,形式与色彩的纯形式关系让位于它们所指涉的现实内容和意义,正如观众在观看一幅古典主义肖像油画时,往往只关注画上的人究竟是“谁”,而对画面的色彩和形式置之不理;而如果意向体验以“图像表达”即绘画作品本身的质料为意向对象,那么,意向行为的核心内容即关注纯形式结构的意义,形式与色彩的关系超越指涉物而成为意识对象,正如观众观看一幅点彩画派的作品(如秀拉的《检阅》,1889),画面上直接堆砌的原色色点和彼此关联而显现出的整体形式,比表现的客体更值得“检阅”,因为客体已经完全是形式自由组合而成的客体。不难看出,雅各布森在未来主义绘画中理解了“图像作为图像”的形式本体论偏好,正如他在未来主义诗歌中理解了“词语作为词语”的自在诗语的价值一样;胡塞尔的“意向性”哲学不仅为雅各布森把握视觉艺术提供了超越传统心理主义的现象学术语和逻辑学理路,更为其进一步思考语言学和诗学中相关问题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为俄国形式主义、捷克结构主义灌注了新的活力。 “意向”根本上还是为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意义”(Bedeutung)理论服务的,④而后者对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它直接推动了雅各布森对语言和诗歌语言的“意义”问题的持续思考与实践。胡塞尔虽然在《逻辑研究》第一研究中就讨论了现象学中的语言问题,但因为他把感性的感知当作认识成就的第一形式,认为与意义相关的语言陈述和判断是奠基于感知、想象等直观行为之上的意向活动,即符号和相关的符号行为,因此,现象学的意义理论和语言分析只占有意识哲学之后的第二性的位置。与关心语词记号的意义分析不同,现象学关心的是意义构成的意向经验分析,在胡塞尔看来,意义“不是意向对象全部组成中的一个具体的本质,而是一种内在于意向对象之中的抽象形式。”[13](P319)也就是说,当我们以某个语言符号为意向对象的时候,这个语言符号本身已经蕴含着指向感知者的意义了,即意义就是在意向行为中语言符号所内有的部分,意向对象就具有意义;在感知对象时,当感知者在意向行为中将某个符号当作一种“表达”(即具有含义、意指某种东西)符号时,将获得符号所意指的实事(即通过这个符号而被标志出来的东西);而当感知者以直观意向朝向符号自身时,将获得这个符号的物理意义。以文字符号“QQ”为例。这个符号显现给我们(无论是手写的还是印刷的),作为意向对象引发我们(感知者)赋予意义的行为(意象活动),它甚至具有某种强制性,强迫我们将它视为“表达”,而引向它所意指的东西,比如腾讯公司的聊天工具,或“亲亲”的首字母缩写等,而一旦我们的意向朝向这个符号本身,将获得符号自身的物理意义(字母QQ的物理音响等),在这两种意向体验中,意向对象不发生任何改变,变化的是体验的意向性质,可以说,意向方向的改变,使得意向对象中所蕴含的意义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同时,在胡塞尔看来,“符号”一词具有“双重意义”,即意味着承担意义的符号——“表达”(Ausdruck)和不传递意义的符号——指号(Anzeichen),指号是被剥夺了或缺少了意义,但并不因此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正如德里达对此所理解的那样,“从本质上讲,不可能有无意义的符号,也不可能有无所指的能指。”[14](P17)胡塞尔的这一现象学意义理论对雅各布森等俄国形式主义者有着重大启示,尤其是对未来派“无意义诗(语)”的创作与批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为讨论无意义语言的符号与意义关系问题提供了理据。比如什克洛夫斯基在《论诗歌和无意义语言》中说道:“虽然讲到词的意义时,我们要求它必须用以表明某些概念,而无意义的结构仍然是语言之外的东西。但是,在语言之外的东西并不仅是无意义的结构;我们谈到的一些现象也促使我们考虑一下几个问题:在诗歌语言中,是否所有的词都有意义呢?或者是否应当认为这种看法是由于我们不注意而产生的空想呢?”[15](P27)其言外之意自然是肯定诗歌语言中无“意义”(概念、所指意义)的词语是存在的,因此,对于形式主义者或未来主义者而言,不是要把词语从意义中解放出来,而是要使符号能指在意向活动中获得先于所指的优越地位,换句话说,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不是意向于词语的概念,而是意向于指号结构(如字母的声音、书写、变形的字体词形等),那么,无意义的诗语便获得了与概念、形象等无关的独立自足的语言功能,这也正是雅各布森自己和赫列勃尼科夫等人创作“无意义诗”的旨归所在。在这个问题上,巴赫金的批评不妨视为胡塞尔“意义”观的补充,他说:“形式主义者为什么断定玄奥的词语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呢?通常的有意义的词语,不能充分表达出其物质的、物的现存性,不完全与之相一致。它具有意义,因而它要表现事物,表示词以外的意思。而玄奥词语完全与其本身相一致。它不越出自己的范围,它只不过作为一个成形的物体存在于此时此地。形式主义者担心‘非此时此地’的意义能破坏作品的物性及其此时此地充分的现存性——这种担心对他们的诗歌语音起了决定作用。因此,形式主义者力求确定:意义及其共同性、超时间性、外时间性与作为单个物品的作品的现存性之间成反比。‘玄奥的词语’的思想就符合这一公式的要求。”[16](P244)虽然巴赫金从时间性角度把意义当作是一种“非此时此地”的外在于符号的存在,但他正确揭示了形式主义者对“此时此在”的词语物性与现存性一面的热爱。 当然,在此“意义”理论影响之下,雅各布森的语言诗学所提出的纲领不是极端的“无意义诗(语)”,而是“诗歌是发挥审美功能的语言”、“诗歌是一种旨在表达的话语”,所谓“诗性”(poeticity),就是“通过将词语作为词语来感知,而不是作为被指称的客体的纯粹的再现物,或作为情感的宣泄。是通过诸多词语和它们的组合、它们的含义、它们外在和内在的形式,这些具有自身的分量和独立的价值,而不是对现实的一种冷漠的指涉。”[5](P378)综合这些诗学观念,不难看出:雅各布森如胡塞尔一般,先验地将外在于诗语符号的一切客观自然事物(现实指涉物)、情感逻辑等都置入括号之中,“悬置”不论,这样一来,诗语符号与指涉对象之间的正常关系就被取消了,符号作为自身即有价值的意向对象而获得了独立的审美品格和意义,如杰弗森所言,“不是事物决定词语的意义,而是词语决定事物的意义”,[17](P33)更准确地说,这“意义”作为形式要素或者说结构规范内含于诗歌的文本结构之中,而诗歌的结构构成不仅包含音位的和韵律的特性,也包含语法的和语义的特性,这些结构特性所形成的格式塔即“文学性”(literariness)之所在。雅各布森所定义的“文学性”概念——“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让我们不由地想起胡塞尔的“本质的抽象”理论,而这一理论主要由使一个可感知的事物成为一个事物的“物性”(thingness)概念发展而来,其旨归正在于通过直观而回到物之为物的物性、人之为人的人性上来,这才是现象学哲学的科学合理性。可以说,这种“回到文学本身”的语言诗学,与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纯粹现象学,在“表达与意义”问题上达成了某种本体论还原的默契与同构。而在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语言诗学成熟之时(1958),胡塞尔的“意向”身影再次顺理成章地出现在雅各布森对“诗性功能”的定义中。⑤ 与意义生成密切相关,雅各布森同样以胡塞尔的现象学著作作为奠定其“普遍语法”理论的哲学著作。胡塞尔关于“普遍语法”的学说在其《逻辑研究》第四卷,在胡塞尔看来,只有意义的类型,而没有出于普遍性考虑的意义的表达,这依然是传统学说的类型,从亚里士多德到17、18世纪以及中世纪的继承者们,都非常重视这一专题的研究。而“普遍性”也是与黑格尔和浪漫主义有关的一个术语,黑格尔对普遍语言思想的判断是轻蔑的,浪漫主义则习惯于突出自然语言的个人特性。相较而言,雅各布森早在大学阅读胡塞尔时便萌生了“普遍语法”的想法,⑥开始关注普遍与特殊、不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其第二部诗歌研究著作《捷克诗歌与俄国诗歌比较》(1923)中,推崇不变量的普遍主义态度就走到了前台;最终,他和朋友特鲁别茨柯依一起开创了从表达类型出发的关于“普遍性”的现代研究,率先在音位学和类型学两个领域建立了普遍语法。简言之,雅各布森对现代“普遍性”研究的特殊贡献在于,整合了变量与不变量的普遍类型的发现,使得这一来自于传统语言学而被经验学派思想所摈弃的术语,最终成为新语言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为后来者(如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坚实基础。 总之,胡塞尔的整体性、意向性、意义等现象学哲学理论始终贯穿于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中,这也正是霍伦斯坦称雅各布森的语言研究为“现象学结构主义”(Phenomenological Structuralism)的根本原因所在。[10](P3)雅各布森又以这样的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象学结构主义语言诗学”。需要注意的是,雅各布森没有利用黑格尔和浪漫主义去建立意义表达的普遍规则,而是利用了胡塞尔,这可看作他对哲学文本自由、自信又较为隐蔽的处理特性。雅各布森作为一位应用型语言理论研究者,结合具体的语言现象、文学文本来实践和阐扬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变抽象为具象,融哲学于诗学,正是其结构主义语言诗学的独特价值和成功关键。 注释: ①笔者查阅《现象学概念通释(第1版)》(倪梁康著,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未发现这一组合词语,可能是雅各布森自己根据胡塞尔的术语“dinglich”(事物的)与“Bezug”(关系)组合而成,姑且意译为“指涉事物的关系”。雅各布森的意思是,某种新词只具有自身的符号性,而没有相对应的指涉对象。 ②在《儿童语言、失语症和一般规律》(1940)中,雅各布森借助于胡塞尔“部分和整体”逻辑的语言,提出了自己语言学分析的经验主义内容,尤其以胡塞尔《逻辑研究》中“一切真正的统一者都是奠基关系”这句话作为他研究儿童语言的箴言。 ③在切尔帕诺夫的讨论课上,雅各布森承担的任务就是研究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斯坦塔尔(Heymann Steinthal,1823-1899)和胡塞尔著作中的“感知”问题。 ④从总体上看,“意义”(Bedeutungen)概念与“含义”(Sinn)概念在胡塞尔那里显然是同义词,但他对它们的使用始终各有偏重:含义概念更适用于语言逻辑分析,而意义概念则更适用于意识行为分析;与含义相关的是“表达”,与意义相关的是“行为”;在讨论语言的第一研究中较多使用“含义”,在讨论“行为”的第五研究中较多使用“意义”;任何“含义”都是有意义的,但并不是任何“意义”都具有含义。参见倪梁康:《现象学的始基——胡塞尔〈逻辑研究〉释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⑤雅各布森认为,当信息(information)“意向于信息(message)本身,为了其自身目的而聚焦于信息,乃是语言的诗性功能”此句原文为:“The set(Einstellung)toward the message as such,focus on the message for its own sake,is the POETIC function of language.”参见Roman Jakobson:“Linguistics and Poetics”,Language in Literature,edited by Krystyna Pomorska and Stephen Rudy,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69. ⑥雅各布森在《语言普遍现象对语言学的启示》(1963)一文中提到:“在莫斯科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考官问我对普遍语法可能性的看法,我回答时引用了该教授对胡塞尔‘纯语法’的否定态度。教授问我个人的态度。使考官恼火的是,我提出有必要让语言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见钱军编译《雅柯布森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0页。标签:现象学论文; 雅各布森论文; 部分与整体论文; 心理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语言表达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语言学论文; 形式主义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