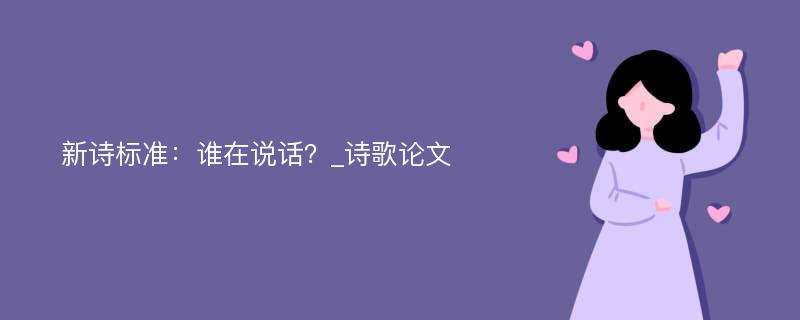
新诗标准:谁在说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谁在论文,说话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4)05-0005-05
十余年前我在新诗研究的一个专门机构工作,曾经碰到过这样的难题:台湾知名诗人 洛夫先生因为要参加一个会议,大概正在赶写会议论文,需要有关中国大陆新诗方面的 数据——中国大陆究竟有多少诗人,或者,至少大概有多少诗人?据说洛夫自己已经统 计过台湾诗人的数目。他可能是出自这样的考虑: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一家新诗的专门研 究机构,应该有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不知道洛夫是否在其他地方也寻求过这种帮助,结 果又如何。不过,很遗憾的是,至少我所在的机构,当时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为了 弥补这个缺憾,我们立刻展开统计工作,并很快查找了大量的文学、诗歌报刊,新近历 年出版的诗歌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名录,等等。几周之后,资料、数据收集了不少, 但最后仍然很沮丧地发现,根本无法回答中国大陆究竟有多少诗人这样的提问。
问题在于,我们找不到这项统计工作的基本依据,或者说衡量准则——标准。在取舍 之间,我们无所适从。比如:凡是发表过一首诗歌作品的写作者都是诗人?果真如此, 那就数不胜数,这种统计根本无法完成——在语文老师的指导下,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小 朋友也可能在晚报上发表一首诗;如果不是,那么要发表多少首作品,在哪里发表才算 是一个诗人?或者,凡是出版过诗集的写作者才能算是诗人?那么,为了各种目的,自己出钱找个出版社,把分行的中国字印成诗歌模样,且错别字连篇的东西也是诗集,这种人因此也是诗人?何况确实还有如此众多从未出版诗集的写作者因此被排除在外;又或者,凡是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名录中,同时又写诗的作者都算诗人?但我们又显然不能无视这样的情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80年代中期以后,不少写作者明确拒绝这样的协会。如果在这个时候仍然以会员身份来衡量,结果势必显得滑稽。
总之,从有多少诗人,到什么是诗人,从一项看来不是那么困难的纯粹技术性统计工 作,很快就被逼到对诗人的身份认证。最后,还不得不退至一个更始源性的环节:究竟 什么是诗,或者至少什么是新诗——这是衡量和取舍众多新诗材料和写作者的一个基本 标准。换句话说,必得先明确诗歌的标准,然后才能确定诗人,之后才能统计数据。
而一旦开始考量新诗的标准,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如此吊诡的情景:我们没有新诗标准 ,恰恰是因为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如此众多的标准,正好相互抵消,结果却 缺乏一个可以得到公众一致认可的说法和认定,给人感觉真是道理越多越糊涂,这倒似 乎真是应了穆旦的诗句,“……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 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出发》);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不管有 多少种不同的说法/标准,这些说法/标准之间的差异如何的大且多,但诗歌依然存在, 新诗标准也依然存在。我们仍然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并没有因此就张三说的是小说,李 四说的是话剧,换句话说,新诗以及新诗标准究竟还是有一个更为根本性的东西潜在于 这些差异之下。
在这种纷乱的情形中,如果仔细分辨,会发现所谓的新诗标准,其实暗含了双重标准 :其一衡量的是“是不是”;其二衡量的是“好不好”。这分别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是不是”涉及事实判断,而“好不好”涉及的是价值判断。就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新 诗标准问题而言,一种现代汉语的文学性写作,是不是可以叫做“新诗”,这是一个问 题;而这种样式的写作,写得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就像在校园林荫道上迎面碰到一 个行人,我们首先可以讨论这是不是一个人,然后如果还有兴趣,可以继续讨论这是好 人还是坏人。但不管这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是一个人这样的判断不能动摇,不能因为这 是一个坏人就因此连人这个判断也予以否认。谈论新诗标准的时候首先应该分清这两个 不同的层面。遗憾的是,很多的相关讨论多多少少忽略了这种区分,于是,两种不同层 面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相关讨论显得似是而非,交流和切磋根本无法实现。更多的 时候,其实是在以好不好的问题僭越了是不是的问题。比如,当我们阅读诗歌模样的现 代汉语写作,而且觉得不合意的时候,常常会不屑一顾:这算什么诗歌!言下之意,这 根本就不是诗歌。结果,价值判断覆盖和涂改了事实判断。
因此,不妨把这两个层面分开来看。
先看事实层面的标准。比较而言,事实层面的标准似乎更好确立:几乎所有的新诗爱 好者——更不用说专业工作者,都能在所有的文学创作样式中,一眼认出什么是新诗作 品(新诗这个概念也就是从这些具体的新诗作品中归纳抽象出来)。那么,他们凭什么可 以如此自信地确认?是根据自古以来的所谓“诗言志”、“诗缘情”,还是所谓诗歌是 对社会生活的表现这样类似的界定?显然都不是。因为如果真是可以“一眼认出”,那 么,什么是“志”,什么是“情”,什么又是“社会生活的表现”,这些都显得太过于 复杂。在我看来,事实可能比想象的还要简单许多,在文学创作这样一个语境中,我们 判定一首诗仅仅是依据它看起来像一首诗。而所谓“看起来像”,是指在外形上跟我们 一贯以为是新诗的东西正好相类。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事实层面关于什么是新诗或者新 诗的标准,在目前的现代汉语写作中,能够确定的大概只有分行排列的文学创作这样的 一个基本标准,换句话说,凡是分行排列的文学创作,都可以叫做新诗(作品)。虽然这 个形式主义的标准,其巨大的宽容性看起来有些像一个笑话,但除此以外,确实找不到 一个更具效用意义的新诗标准,不管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诗言志、诗缘情之类的经典说法 ,还是一直到20世纪,胡适、朱自清、朱光潜、何其芳等人关于什么是诗歌的经典说辞 (不管古诗还是新诗),我们根本无法用他们的标准来有效地衡量一个具体出现的新诗作 品。这些标准要么宽大得无边无际,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也就失却了标准——一种衡 量准则——应该具备的认识价值;要么局促狭窄得可怕,无形中捆绑和束缚了新诗形式 、内容上创新的可能性。关于前者,比如在“诗言志”中,不管对“志”有何种阐释, 它都显然不仅仅局限在我们今天谈论的诗歌这个范围内,更是适用于整个文学艺术,而 诗歌的标准和认定也就同时被湮没在“志”的语义海洋中,根本无法分辨哪一朵浪花是 我们要谈论的诗歌;关于后者,哪怕是在最近的新诗史上也屡见不鲜:当朦胧诗出现的 时候,人们根据其时现存的新诗标准而极力加以否定,当后朦胧诗出现的时候又转身肯 定了朦胧诗而再次极力否定后朦胧诗——这期间哪里有什么固定统一的标准。
不过,从分行排列的文学创作这种外形方面来树立新诗在事实层面的衡量标准,并非 没有危险,虽然它可以很大程度地宽容几乎各种形式的诗歌创作。人们还是很容易质疑 :三字经和百家姓都是诗?把报纸上的一篇社论分行排列也都是新诗?我以为从事实这个 层面上讲,这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是还涉及到它们是否属于好诗的问题。而一旦涉及好 坏,我们就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价值判断层面。
更麻烦的问题在于价值判断层面——困难在于我们认定谁的或者什么样的价值评判标 准,也就是说,好不好由谁来负责取舍,究竟是谁拥有了诗歌话语的权利,在诗歌领域 ,究竟谁在说话。不管是否最终能给出这样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但至少需要知道,究 竟有哪些因素对新诗标准的建立起着制约作用。
首先,漂亮然而并不可靠的说法是历史(时间),这样的说法经常可以听到:随着时间 的推移,历史最终会淘汰那些糟糕的作品,而留下优秀的作品,而诗歌的标准就来自那 些优秀的作品。事实证明,历史(时间)似乎确是有如此伟大的汰选功能,但问题在于, 对我们每个生命的个体而言,我们只能处在当下,而不可能去遥望历史与未来,因此, 这种说法多少有些不负责任的逃避嫌疑,更何况,历史(时间)本身并不具备任何取舍的 能力,历史的淘汰,其实也总是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人们“当下”取舍的结果。历史的能 力所以最终其实仍然是我们自己的能力的一种时间距离化的结果。
其次,除了这种相当普遍然而结果却似是而非的说法外,在我们的新诗历史上,很容 易看到另外一个标准:政治意识形态标准。新诗的政治意识形态标准的形成、发展、巩 固以及它的运作,跟整个新诗的历史相比,并不短多少:从1920年代末期的革命文学( 包括新诗),到1930年代的左翼写作,到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再到1950年代开始的新 政权下的新诗写作,尤其是大跃进中的全国写诗现象,等等。这种标准的存在,使得文 学史和现代诗歌史在对诗人和诗歌的评价上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倍感棘手。在我们的 历史甚至现实中,作为文学的诗歌与政治意识形态是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让我们在 对诗歌的言说中,很难清爽干净。一方面,目前我们很多的论说,以纯粹艺术、回归文 本等等名义,其实只是尽可能地远离这个十分敏感的话题,让它存而不论,但另一方面 ,我们显然也不能如此简单地就把这一路的诗歌写作,排除在论说范围之外,否认它们 作为新诗作品的事实。
除了前述这两种情形以外,真正能给出标准,或者说能够进行好坏取舍的,显然还有 作者(诗人)和读者——诗歌的制作者和消费者。
从读者这个方面讲,如果简单一点,不妨把读者分为高级读者和普通读者。高级读者 这里指诗歌评论者这样的专业读者,而除此之外就是一般的普通读者。正如接受美学或 者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家们所以为的那样,读者的反映、接受显然制约、规定着作者的 写作。换句话说,读者在给作者的诗歌写作制定着标准。这种标准的制定与标准的规约 ,在左翼文学、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新诗写作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虽然其中同 时也加入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而且1940年代末期和1950年代初期的转折,所导致不 少诗人的写作转向,可能是最清晰的一道折射。当然,在今天,其中意识形态的制约可 能已经相对淡化,但读者的制约力量不但没有减弱,可能反而更加突出:原来是政治意 识形态的力量混杂在读者制约力量中,在今天转为了商业经济的钳制。
在目前这样一个商业时代,数量显然起着巨大的作用,而读者就意味着数量。普通读 者的数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艺术时尚的是否成形,读者的偏好决定着诗人们的写作兴趣 。在一个商业化的时代,作为消费者的“俗人”,是一个庞大的无形力量,我们无法跟 他们形成真正的对话关系,但他们的力量显然不能小觑。他们什么都不是,但冥冥之中 又似乎是一切。
另一群读者是高级读者,他们往往是以个人的名义出现,他们凭着自己在诗歌方面的 专业知识,是秩序和规矩的捍卫者,也是诗歌纯洁性的追求者。从文学理论的传统意义 上讲,他们几乎是标准的制定者,拥有绝大的权利,因为理论指导着创作实践。不过, 这种说法可能是过高地估计了理论工作者的权利。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商业时代,显然, 他们的专业知识也多少受到读者市场的检验,结果,普通读者凭着自己数量的众多而参 与有关标准问题的话语权利的争夺,高级读者捍卫并同时不得不让渡自己的垄断权利。 我们发现,让诗歌理论专业工作者倍感无奈的是——在很多时候,他们的说法并不算数 。
而且不管是普通读者还是高级读者,他们的诗歌偏好都是变化的。普通读者的诗歌爱 好显然会随着时代、社会、阅读习惯等等因素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就像习惯了1949年以 后政治抒情诗的中国读者,骤然之下无法接受“朦胧诗”一样,他们甚至根本就不承认 朦胧诗是新诗,更不用说好诗还是坏诗的问题。而一旦“后朦胧诗”出现以后,读者又 表现出对当初朦胧诗一样的排拒态度,暗中却已经转身多多少少习惯和接受了朦胧诗。 其中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标准的滑行与移动。高级读者面临同样的处境:在他们那里, 变化的是不同时代中不同的学术兴趣而已。1980年代以前我们对新诗与社会的关系感兴 趣,而之后逐渐更对新诗文本自身感兴趣,所谓回归文本。但谁也无法肯定,这些兴趣 的转移与变化,哪一个是“正确”,而哪一个是“错误”,因为兴趣本身没有对错之分 。我们也因此不敢自信地肯定,今天的兴趣就一定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兴趣,可以从此让 我们树立一个不变的标准。
除了读者以外,对规则的制定有着巨大影响的显然还有作者。
所有关于诗歌的标准,都是建立在现存的新诗文本的基础之上。离开了这些新诗文本 ,就无所谓新诗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作为文本的制作者,对于标准似乎具有绝 对的话语权利——不是读者而是诗人自己建立了新诗标准,在通常情况下,一般读者甚 至高级读者也无力建立一个新诗的标准。诗歌写作是一种艺术时尚,没有人知道某个时 尚的出现和消失的真正原因,虽然作为读者或者评论者可以在事后以自己的方式揣度和 阐释。
不过,作者也并非是凭空成为了新诗的制作者,并非绝对自由而随心所欲。每一个作 者都在(甚至始终在)“成长”的过程中,这就意味着不断的学习和模仿。事实上,作者 的制造文本,正和读者的接受和理解文本一样,他也绝对不会处在一个意义的真空地带 (不管他/她接受或者反对什么艺术时尚),而是始终处在一个诗歌知识的上下文中。
在这一点上,美国当代批评家斯坦利·费什的意见也许是非常有价值的,当他在谈及 对一个客体的意义进行阐释时认为,“所有的客体是制作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它们是 我们所实施的解释策略的制成品。然而,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它们是主观(解释)的结果 ,因为使它们生成的手段和方式具有社会性和习惯性。这就是说,‘你’——进行解释 性行为,使诗歌和作业以及名单为世人所认可的人是集体意义的‘你’,而不是一个单 独的人。……因此,当我们承认,我们制造了诗歌(作业以及名单之类)时,这就意味着 ,通过解释策略,我们创造了它们;但归根结蒂,解释策略的根源并不在我们本身而是 存在于一个适用于公众的理解系统中。”(《看到一首诗时,怎样确认它是诗》,见《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第57页)对客体意义的阐释如此,对客体本身的制作同样 如此(对客体的识认、意义阐释,这本身就是对客体的制作),因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 ——谁也不可能在早晨醒来便异想天开地创造出一种新诗体,或者构想出了一套新的教 育制度,或者毅然决定摈弃(现存的)一系列准则以便采纳其他一些全新的结构模式。照 费什的看法,我们未能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压根儿就不可能如此,因为,我们所能进行 的思维行为是由我们牢固养成的规范和习惯所制约的,这些规范习惯的存在实际上先于 我们的思维行为,只有置身于它们之中,我们方能觅到一条路径,以便获得由它们所确 立起来的为公众普遍认可的而且合于习惯的意义。
这种公众普遍认可的理解系统,就现在我们所讨论的诗歌领域而言,也就是一个诗歌 知识共同体,如果用斯坦利·费什的术语,也就是“阐释团体”,即一种理解结构,一 种在集体意义上的自我(阅读)或者认知所依存的情势,一个社会化的公众理解系统。在 这个系统内范围内,我们虽然受到它的制约,但是它也在适应我们,向我们提供理解范 畴,我们因而反过来使我们的理解范畴同我们所要面对的客体存在相适应。对于读者的 阐释来说,“当我打开一本书看的时候,实际上我看到的是由我已经构成的观点写出的 东西,也就是我在二十五年来在文学团体中所形成的结构。”在我看来,对作者也同样 如此,因为无法想象一个置身于文学(新诗)知识共同体以外的人,能写作任何与文学( 新诗)相关的东西。
如果从这个角度重新回到前面所涉及的新诗事实层面的标准问题,就可以看到,即使 我们将分行排列的文学创作作为新诗唯一的事实判定标准,结果大概也并不会如置疑者 所预想的那样出现新诗天下大乱的局面。因为这其中已然潜藏着某种诗歌知识共同体或 者新诗标准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我们多少对新诗的标准心领神会,虽然我们可 能永远无力准确地将它表述出来,甚至也不一定有表述出来的必要。
于是,如果我们真的试图建立一个新诗的标准——有关什么是诗歌,什么是好诗—— 我们能够做到的就只能是置身于诗歌知识共同体内的“协商”、不知不觉中的相互让步 ;在已有的作品、正在出现的作品和将要出现的作品之间协商,在诗人、读者之间协商 ,在诗歌艺术和社会情势之间协商。而从常理知道,在这个共同体内协商谈判的各方之 间,各方的声音不可能同等程度的大小,而至于什么时候,哪一种声音更洪亮,谁的价 值标准占据上风,是作者、文本、读者还是社会甚至某种意识形态,这是无法预测的, 它只能是一个时代的艺术时尚、学术兴趣以及社会情势等相互交错的结果。
收稿日期:2004-0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