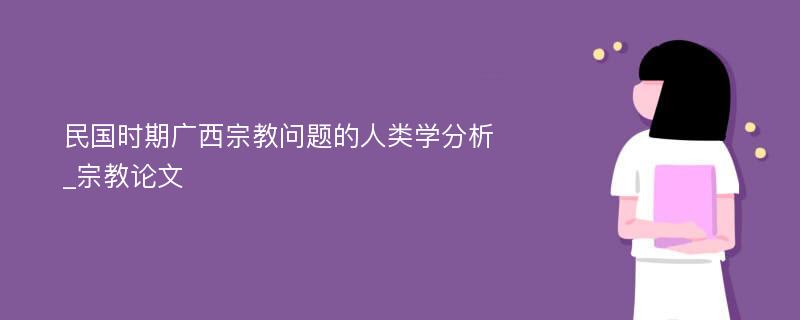
民国时期广西宗教问题的人类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广西论文,宗教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29;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3-0075-007
宗教问题是近代中国面临的普遍的社会问题之一,也突出地表现在广西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虽然清末时期广西的宗教问题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1] 但在民国成立以后,旧、新桂系大力推行风俗改良和破除迷信,给广西的宗教问题带来很大的冲击。与之同时,外来宗教在广西民族地区进一步扩张,并且更广泛地深入广西的各个角落,也产生了一些宗教冲突,但总的来看,已经没有清末那么严重,而且也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教案。不过,与清末时期一样,民间宗教仍然支持着人们的反抗斗争,而且其中还加入了更浓重的民族冲突意味。概括来讲,整个民国时期,广西始终存在着三大宗教问题,其中又牵涉到多次小型或大型冲突。
一、政府提倡破除迷信,遭到民间无形抵制
辛亥革命以后,广西进入了民国时代,先是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上台执政,而后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又掌握了广西的统治权。虽然期间也产生过自立军、李明瑞时代,但都是昙花一现,未能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不过,几乎所有上台的执政者都实行风俗改良,尽量用新式思想去武装民众的头脑,甚至还采取了专门措施来抑制民间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其中尤以新桂系统治时期最为明显。
早在民国初年,由于政府严禁阻止城隍神像出游,招致不少民众的反对,导致龚管带头部被飞石击伤。这一事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风俗改良运动,南宁都督府派兵四处倒毁寺庙里的神像,于是僧侣散亡,经典焚烧殆尽,只有女尼姑幸免于难。[2](卷四十) 伴随着风俗改良的政令,一些县份行动起来,捣毁了不少寺庙、神像。
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上台以后,掀起了更大规模的风俗改良运动。在新桂系政府看来,当时广西尚未破除的宗教迷信有:敬视鬼神,作偶像崇拜;建醮还愿,请僧道作法;迷信堪舆地师等。这些迷信不仅使个人的生活受到不良的影响,而且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进步,造成了严重的恶果。[3](p16) 因此早在1931年,新桂系广西当局就颁布了《广西各县市取缔婚丧生寿及陋俗规则》,其中不少条款就涉及到宗教信仰问题。如第三章第二十一条即规定曰:“丧家不准用地师、僧尼、道巫斋醮做亡”;第五章第三十四条进一步规定曰:“凡游神、醮会、求神、拜佛、送鬼、放花炮、完花愿及清明、中元节焚烧冥镪、纸扎等迷信行为,均应革除”。[4](pp427-428) 这样的规定就把广西民众千百年来的信仰认定为违法,看作一文不值,严重影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为了使破除宗教迷信的政策得到贯彻实施,新桂系各级政府还采取了不少具体的实施办法。具体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种:(一)倒毁偶像。新桂系政府认为:“偶像可以说是迷信的重要工具,打倒了偶像,愚夫愚妇便失掉了迷信的信仰,使他没有足以崇拜的偶像,而且,偶像在愚夫愚妇的目前看见给人倒毁,原来是毫无灵验的东西,必因此而促其觉悟。”[3](p17) 因此新桂系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做了很多的工作,使大量的寺庙、道观以及地方神庙受到严重破坏或转型。如在三江县,在省政府打倒神权、捣毁偶像的命令之下,“城乡寺宇寺产,悉充失所凭依,一蹶不振,今式微矣。”“县属观宇观产,悉充学校校舍校款之用,集结无所,其势亦微。”[5](卷五) (二)禁绝僧道地师营业。新桂系政府认为:“僧道可以说是迷信鬼神的支持者,因为他们是依靠着作法建醮来生活。而迷信的人,也以僧道可以通鬼神,用他作为求福消灾的一个通神的媒介。有时,偶像捣毁了,僧道们还可以书写神位,大打其平安醮。所以我们应严厉地去禁止僧道营业——作法打醮。禁止地师看风水要钱。”[3](pp17-18) 因此新桂系各级政府纷纷采取具体措施来严禁巫道,三江县政府甚至规定了十分详尽的处理办法:“由各区团局分投,先将团内巫道登记,呈县备案,然后实行,勒令于一个月内改业,如逾仍操前业者,处以五元以上、二十元以下之罚金,延请之家,罚金相等,此项罚金,分充当地学校,及团局经费各一半。”[5](卷二) (三)禁造迷信品物。新桂系政府认为:“纸人纸马纸屋,以及枉生神咒、纸钱、香、烛、冥镪等。这些迷信品物,可以说是迷信的工具。而大宗财物消耗于无益,也是上面的品物为大宗。”[3](P18) 因此不仅严厉禁止制造这些物品,而且还在那些没有制造的乡村间禁止贩卖。(四)严厉的处罚。新桂系政府认为:“依照改良风俗规则规定,对于迎神建醮等是规定严予处罚的。做乡村长的,决不通融,依着执行,这也是一件重要的制裁方法。”[3](p18) 查《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则》,其第五章第二十四条曰:“不得迎神建醮,违者没收其所聚集之捐款,并处首事者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金,其在场僧道之法衣法器没收之”;第二十五条曰:“不得奉祀淫祠,及送鬼完愿,违者处五元以上二十元以下之罚金”;第二十六条曰:“不得操巫觋地师等业,违者处五元以上二十元以下之罚金,再犯者加倍处罚”。[6](pp27-20)
在这些措施的打击之下,广西各地的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遭受到了重大打击,当然其中受打击最为严重的是佛、道等中国传统宗教。因为不仅它们的宗教活动场所被充作了学校,而且它们的从业人员也受到严密的监控,难以维持原有的信教事业。如贵县“比年改良风俗,黄冠辈多已别营生业。”[7](卷二) 隆安县“把全县神庙内偶像尽行打倒,并禁绝道巫。拘拿的拘拿,罚款的罚款。一时雷厉风行,道巫为之歇业”。[8](卷三) 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遭受到了巨大打击,而同时政府却不敢触动外来宗教的利益,这就给了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等教派以可乘之机,使他们能够在广西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民间宗教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已经深深影响到各族群众的行为方式,因此面对强权政府所提倡的破除迷信的政策,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抵制措施。如宁明县在1933年时仍然相当流行自身的民间信仰。田曙岚就此有记载曰:“每岁于新岁家家门外,设一祖翁神位,或书‘祖德流芳’四字,并无讳号。供奉过年糕饼等物,亦无烹鲜以荐之,至上元节后乃撤。……又该处习俗,家家门外,或屋角,或后园,皆立有‘先锋爷爷之神位’,奉祀惟谨。”[9](p34) 三江县也出现这种情况,虽然传统的佛、道信仰被摒弃,“然民间禳灾建醮、送死荐亡,恒喜延用此辈,乡里尚少,城市特多,此辈亦藉以广结善缘,大行其道,教之真义如何辄不谙,直视为一种营业矣。”[5](卷五) 隆安县大家族势力很强,他们“公然延请僧道,大设道场。党部无法禁止,遂使民众藐视党令,群相效尤。故至今(指修志时)暗用道巫者,仍是不少。”[8](卷三) 雷平县“自政府严行取缔以来,城市已不多见,而村陇之间,人或时逢不济,不求自勉以图其成,惟求神保佑、乞灵于木偶。”[10](第三篇) 邕宁县“(民国二十六年)现虽为政府严禁,乡间犹然举行。”[2](卷四十) 如此之类的事例,比比皆是,兹不赘述。
事实上,民国广西历届政府都尽力推行破除宗教迷信的政策,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毁坏了很多历史文化遗产,甚至更造成政府与民间势力的矛盾加大。虽然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大规模的反抗运动,但是在各个小社区里,各种无形的反抗斗争是时时存在的,他们在家庭、宗族和社区内部仍旧奉行着他们古老的信仰。
二、外来宗教势力扩大,与当地民众矛盾尖锐
进入民国以后,广西外来采教的传教事业并没有受到冲击,相反却在政府的支持下更加蓬勃发展起来,即或是十分偏僻的少数民族村寨,也都能见到传教士的踪迹了。在这个过程中,外来宗教势力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文化事业尤为发达。
首先是传教机构和信教民众的增多。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1935年时已经建立了56所天主堂,其中有18所成立于民国年间,占总数的32.14%,另外还有17所教堂没统计出具体的建造时间。随着传教机构的增多,信教民众也随之剧增。据统计,天主教在1911年仅有教徒4523人,到1921年时就升到了5119人,[11](p63) 至1935年更达到了空前的15453人,[12](p1019) 比1911年时已经增长了两倍多。与天主教相比,基督教各教派的发展显得更为迅猛。1933年版的《广西年鉴》第一回中,所统计的宣道会就有52所,其中1所时间不详,仅成立于民国时期的就有37所,占了总数的71.15%;所统计的浸信会共7所,成立于民国时期共6所,占总数的85.71%;所统计的中华圣公会共9所,成立于民国时期共7所,占总数的77.78%;所统计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共7所,全部成立于民国时期,占总数的100%。[13](pp760-763) 到了1935年版的《广西年鉴》第二回中,统计到的基督教宣教会多达64所,成立于民国时期的多达35所,占总数的54.69%;所统计的浸信会数目升到12所,其中成立于民国时期的8所,占总数的66.67%;中华圣公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统计则和1933年的统计完全一致;其他的基督教循道会、基督教传道会、内地会福音堂、自立基督教会等界全部成立于民国年间。[14](p1026-1029) 不过,通过两次统计的比较可以看出,宣道会后一统计中清末时期、民国时期都比原来少了2所,而多达17所的教堂没有界定出年代,这说明后一次的统计更为谨慎。在传教机构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基督教的信教民众也大量增加,至1935年时已经达到4264人。[12](p1019)
其次是宗教文化事业的发达。随着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外来传教士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些文化性机构来支持他们的传教事业,于是就开办了不少学校、报纸、印书局等文化教育机构。在天主教方面:一战期间来桂的天主教玛利诺外方传教会不仅选送青少年教徒去广东江门拉丁书院学习,甚至还在他们高中毕业后送到香港华南大修院去修读神学哲学;1917年以后,法国天主教会先后在贵县覃塘、伏龙、大圩、三板桥等地办小学校,除上普通课外,还讲授天主教的来历和教义;教士唐汝琪于1946年6月创办了广西天主教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立梧州圣心小学”,学生最多时达到700多人。[11](pp8-174) 在基督教方面:宣道会不仅在梧州建立了建道圣经学院,专为教会培养华人教牧人材,而且还开办了宣道书局、《圣经报》以及《宣道消息》等出版机构;浸信会除开办圣经学校、培贤圣经妇女学校、储才学校以及培真女校外,还在开办真光书楼以及创办了《真光旬刊》、《和会集刊》、《福华报》、《晨光报》、《田道月刊》等刊物。[11](pp236-347) 据广西统计局1933年统计:“本省教会学校,计有培正中学1所,小学校22所(书院2、传习1所在内),其中回教设立者,小学校2所,天主教小学10所,基督教中学1所,小学7所,浸信会小学3所,分布于全县、桂林、平乐、修仁、荔浦、榴江、苍梧、平南、桂平、贵县、横县、邕宁等县,各校学生共1300人。经费来源,除少数由本国教徒捐助外,多数来自外国教会,或由中外善士捐助。”[12](pp724-725) 这表明: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早就建立起了较为发达的文化教育事业,这其中还不包括圣经学校、主日学、诵经班等形式多样的宗教性文化教育机构。
再次是偏远民族地区传教事业的拓展。自天主教传入广西以后,法国传教士就一直努力向偏远的民族地区进行拓展。供职于美国宣道会的英籍加拿大人陈法言约于1910年被派到广西工作后,他曾三次由平南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向瑶族布道。[11](pp.265-269)“平南是瑶山的门户,福音由此传入久不信道的民族。在这个土族中传道是出天意。一个瑶人到平南卖玉桂,他在街上游行,被一群人引进福音堂。……瑶人听得很有兴趣,他回家之后,派一个瑶人代表到福音堂,请求派人去教导他们如何拜大神。华人传道伴同一位传教士在几个月后,照着邀请进入瑶山。”[11](p.223) 他们经过崎岖山路到达罗乡时受到了南部瑶王的欢迎。当时,大瑶山宣道会信众中有一位是南部瑶王的主要助手。他后来觉得自己“要向他的人民作见证,而且决定他要到梧州圣经学校受训练”。[11](p.224) 不仅如此,当地瑶民还“请求为他们的儿子开一间教会学校,教导他们,学校设在罗乡南部酋长的家。……开学时有学生二十二名,还有继续来的。在土族人办学校是一种革新举动,起初他们拒绝送孩子入学,这明显是神的能力消除了他们的偏见。”[11](p.224) 这个瑶乡宣道会的传教工作后来交给华人联会① 作为福音布道所,“由一位常住的工作人员定期巡行,把福音传与土族人”。[11](p.224) 1938年2月,成立梧州自理区区会,大瑶山的罗香和龙军两堂受该区管辖。浸信会从隶属梧州教会向象州、修仁等进行传教。1929年11月,浸信会布道者“往修仁属之长毛瑶,同行者二人,历时二十二日,道行千余里”。[11](p.341) 1931年6月,复往修仁县属乡村工作。同年10月前往长毛瑶所在山区,行者3人,为期21天,“虽值严寒,惟信者心切,不畏寒冷,决心领浸者七人”。[11](p.341) 1933年9月前往长毛瑶,同行3人,为期17天,领浸者2人,途长2000里。[11](p.342) 另据刘粤声编《两广西浸信会史略))记载,包厚德牧师“鉴于瑶山布道工作之紧要,于1929年,率颁布道队及秦善崇先生入长毛瑶布道。初在六巷、门头等处。惟因风俗简陋,一时工作不易,故特聘秦善崇君常川来往瑶山传道。1930年,始有瑶民兰海廷悔改信主入会。1931年,又有六巷瑶民秦巷明悔改信主入会。1934年,更请余信良君担任瑶山一带传道职。今有教友袁生和君出组布道队,协助教务之进行,常往大平瑶等处布道。现有查道者数人”。[11](p.363) 需要指出,当时虽已成立了“专以引导瑶民归信基督为主旨”的瑶山传道部,但该部主要在义宁和龙胜广南一带布道,似未进入金秀大瑶山地区。
民国时期,基督教特别是宣道会和浸信会的传播效果最为明显。宣道会先是向平南传播福音,结果成功地打入了瑶山,在偏僻的罗乡瑶族地区建立了1个教会,开办了1间教会学校;至1926年,宣道会宣布在龙州以北40英里靠近安南境界的福兴村建立了1个完全由壮族信徒的教会;甚至还在很偏僻的田林开辟了新的分堂,“布道工作在西部遥远的黑彝和别种土族人中发展,而且定出了明确的步骤向这些人传福音。”[11](pp224-230) 与宣道会相比,浸信会更坚决地执行了向偏远民族地区传教的决心,它们甚至设立了“瑶山传道部”,不仅派人赴修仁、义宁等地的瑶山传教,而且还向更偏远的龙胜民族地区开拓。1929年,在广南侗族地区筹建新堂,次年即成立教会;1931年,又在宝赠侗族地区开设基址;1932年,又在官衙壮汉混居区开设基址,以广宣传。[11](p342) 后来,甚至还曾在相当偏远的龙脊侯家寨建立了福音堂。[11](p364)
综上所述,在民国成立后的20多年中,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在广西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随着外来宗教势力的无限扩大,不可避免地与广西各民族的民间势力发生一些冲突,见证了它们与当地民众矛盾之尖锐。根据有关资料,矛盾最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两次教案上:一是昭平教案:1924年4月间,因桂林爆发陆沈战争,导致全城粮荒和瘟疫。梧州传教士瞿辅民、康建德、米勒尔和理力善4人由梧州运粮上桂林,意图营救当地的传教士,不料路经昭平附近时所带的粮食被抢劫一空,传教士4人也被掳去。不久,瞿辅民、米勒尔2人就被放出以筹赎款,接着,理力善又从匪巢中逃出,只剩下康建德1人在匪帮手中。后来,在传教士陈法言的压力下,昭平县长迫令居民筹集白银2000元,乘夜把康建德赎出。康建德等4人完全脱险以后,竟把这事告到领事馆去,由领事馆出面压迫、威胁当地政府清乡剿匪,竟把无辜农民杀害了100余人。[11](p286) 二是灌阳教案:1926年的“非教”风潮之时,灌阳亦卷入此风潮中,灌阳群众发传单、贴标语、街头演讲。时灌阳县教育局长为周德昂,有意趁此机会,将灌阳中华圣公会礼拜堂改为学校,于是周德昂就发通知给县立城关学校校长周学愚,要他把学校迁往礼拜堂。但周学愚乃一信徒,不但抗不迁校,并将此情况转告教会负责人彭治江,彭即在灌阳各街头撕下各种标语传单,汇成一束,寄往全县牧区区长宋辅仁,宋又立即将此项材料送主教候礼敦。候即将此材料送英国领事馆再转中国外交部。外交部立即行文广西省府,查明办理。省府又转教育厅查办,立即下令将周德昂撤职。文到灌阳,周德昂向周学愚哀求宽免。周学愚允诺教会不再追案,而周德昂因此去职,流亡在外,多年未归。[11](pp.426-427)
除了上述两次较为典型的教案以外,还有华籍神父覃路易被杀事件、灵川教案等不少小规模的教案发生。上述一系列教案的发生,表明了民国时期外来宗教与当地民众的矛盾仍比较尖锐,但从教案发生的频率与规模来看,总体上已经比清末时期缓和了很多。当然,这也跟外来宗教日益显现出它的正面效应有关,特别是随着一系列教会学校、医院、育婴所的举办,使得广大民众也看到外来传教士友善的一面,无形中减低了他们对外来宗教的顽强抵触。
三、与民族问题相交织,参与发动反抗斗争
宗教问题不是孤立的社会问题,它经常和其他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在广西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宗教问题经常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少数民族民众发动反抗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民国时期的广西历史上,最重大的反抗斗争就是爆发于兴安、全州、灌阳、龙胜等地的桂北瑶民起义。民国时期的桂北瑶族民众“举凡病疾婚丧一切大小事件而不能解决者,悉取决于鬼神,疾病时不用医药,只向鬼神祈祷而已”。[14](p109) 同时,正如时人刘锡蕃所言:“苗蛮苟有一次之扰乱,必有一段之神话为因缘”。[15](p193) 因此,领导者能够利用传统的民间信仰号召动员群众参加反抗斗争,其中为起义所直接利用的民族宗教因素主要是“瑶王”、“法宝”、“符水”和“打醮”,它们在这次起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瑶王”信仰。起义以前,全州桐木江地区出了“瑶王”的消息很快就得到了广泛传播,当时传说“瑶王法力无边,能抵御一切枪炮子弹,能灭汉兴瑶,能使瑶民今后利益无穷”,[14](p109) 因此远近的瑶族民众都争着去桐木江拜“瑶王”和送礼。有些人最初去时是抱着一种好奇心去看“瑶王”的,如灌阳后塘初时仅去了几个人,后来看到事情搞得很大也很认真,回来后赶紧又派人送礼去,表示也参加。同时,盘天保、凤福林、凤有林、凤福山等一批“降神”者的宣传对加强和鼓动瑶民们的“盘王”信仰也起了很大作用。盘天保说:“瑶人从盘古出世就苦,现在盘王要翻身了……”。每到“降神”时赶去听的群众非常多,据说是神魂附体,神的意志都通过他们的嘴讲出来。届时“降神”者两眼发愣,指头向天,嘴唇不时弹动,一身发抖,手舞足蹈,脸色发白,嘴里呢呢喃喃,断断续续地指示起义的有关事项。瑶族民众在听到“瑶王”和“降神”者的话后,都求神祷告,喝佛水保佑如愿。[16](p18) 可以说,“瑶王”信仰是桂北瑶民起义的旗帜,正是“瑶王”信仰使得广大的桂北大地能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
(二)“法宝”、“符水”信仰。桂北民间广泛流传着起义领导人有“飞刀”、“火葫芦”、“水葫芦”的传说。在桐木江传说有一宝葫芦,里面可以放出飞刀来杀人。当时还有人宣传:东山附近的瑶族都要到弄岩去集中,否则性命难保。因为“火葫芦”可以让火烧到哪里就烧到哪里,“水葫芦”要水淹到哪里就淹到哪里,所以东山附近各处的瑶族慑于“法宝”的威力,在短短两三天内就迅速地扶老携幼赶到了弄岩。后来前往调查的学者们问及起义者参加的原因时,他们甚至一致回答道:“我们瑶人出‘瑶王’了,那时都说到大地方去有好房子住、种大田、穿胶皮鞋,有谁不愿意去呢?他们的‘法宝’要杀人,不参加恐怕命保不了。”[16](p18) 更为玄乎的是,当时还传说喝了领袖人物划的“符水”后,可以刀枪不入,老年人变青年,男女老少当时都是喝过“符水”的。即使因为路远不能亲自去喝的,也让家里人或别人带回来喝过。有的老年人直到现在仍很相信“符水”的效用,似乎瑶人之所以能凭大刀、柴刀和镰刀与新桂系军队现代化的机枪、步枪相对抗,全是因为“符水”壮了胆。
(三)“打醮”仪式。在起义军出发以前,在桐木江和弄岩这两个起义中心地都大了“大醮”:桐木江名为“开天醮”;弄岩则称为“万民醮”。由于瑶民尊崇“瑶王”和害怕受到“法宝”的惩治,因此桂北各县乃至湖南的瑶族都大量赶往参加。参加“打醮”的人,可以在那里随意吃喝,各地瑶人领袖也趁机商量起义有关事宜,并且在那里编队、练武、祭旗等,因此“打醮”实际上是各地瑶族领袖碰头联系及组织队伍的过程。其次,“打醮”还添入了诸多神圣性的因素,比如桐木江的“开天醮”就扎起了高台子,有打长鼓等响器,烧香纸及念咒等。此外,“打醮”仪式还进一步强化了瑶民们的“法宝”信仰,盐塘村的“打醮”就耍了“法宝”,此“法宝”是椭圆形的圆筒,长七八寸,内有很多明亮的小刀,刀柄上并镶有珍珠。
事实上,即使在后来的行军打仗过程中,也都伴随着大量的宗教性因素。对此,新桂系的御用文人刘宾一有记载道:“惟其作战法术完全以邪术行之,殊属可笑。因瑶民平素迷信甚深,发难时又有军师作种种邪术以坚定其信仰,使之勇不畏死……每与军队民团作战,其军师必亲临前敌,身披红袍,散发持剑,念念作词,即大声喊杀……”[14](p113) 虽然其中不无污蔑之词,但更多的也是记录了瑶民起义者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对民间信仰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已经有了很充分的展示。
总之,民国时期广西的宗教问题主要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其中又以政府破除宗教迷信与民间信仰者之间的矛盾为最为尖锐,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产生的社会历史影响也更为巨大,特别是政府对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的不同态度,导致了本土宗教受到严重抑制,面外来宗教却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与清末时期相比较而言,广西各民族民众与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的矛盾相对没有那么尖锐,在战乱之时,本土士绅和民众还得到教会势力的庇护。传统的民间信仰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各民族民众发动反抗斗争的有力武器,参与着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也反映了宗教问题的复杂性。
注释:
① 因受1925年“非教运动”(即“基督敦促进会”倡立本色教会,驱逐外国教士)的影响,1926年差会主席陈法言由美国总会带来华人教会自立方案,并于1927年4月在梧州召集广西各地华人头目20余人开会,成立了“广西宣道会华人省联会”(简称“华会”),而在西差会和华会之上又成立“广西宣道会协会”,正主席由西差会主席担任,华会主席则担任副主席。
标签:宗教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广西民族论文; 基督教教育论文; 历史论文; 新桂系论文; 天主教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