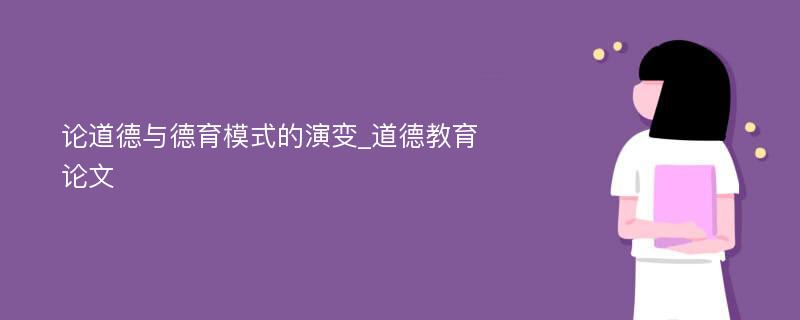
论道德与道德教育范型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德教育理论的成熟,在学术资源方面与两大因素深度相关,一是伦理学的理论供给;二是教育学理论与伦理学理论的生态整合。”[1]“道德教育”是“道德”与“教育”的合成词,我们以前只注重对“教育”的考察,而忽视了对“道德”的考察。其实,道德教育是关乎道德的教育,道德的不同定位是决定道德教育范型的关键。而对道德的认识,最终取决于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存在状态。故此,本文从历史的人的存在状态开始,考察不同的道德范型以及由此所要求的不同的道德教育范型。
一、道德始点或本原:人的二重性
什么是始点或本原?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是:“始点或本原是一种在其充分显现后,就不须再问为什么的东西。”[2] (p.6)就是说,始点或本原是“只知如此,不可或无须究诘”的那种东西。道德和道德教育的对象是人及其行为,道德的主体是人的德性,道德教育的基本目标是人的德性的培育。因此,道德和道德教育始点,也就是德性的始点。
德性的始点何在?就是要从根本上回答“德性源于何处?”德性是人的一种品性,它从根本上源于人的存在状态。人的存在始终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任何人都是一个个体的存在物,有属于自己的肉体和精神,而且各不相同;另一方面,任何人都不是纯粹的个人,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只有在关系中才能存在。这就是说,人同时又是一定群体、社会的成员,是一定群体、社会的存在物。人把自身的个体性与社会的整体性内在于一身,成为马克思所言的人本质上“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成为海德格尔所言的“此在”是“在世界中的共在”。
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决定了人的需要或利益的二重性。人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物,每个人都有维持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个人对外部世界发生的作用和关系都具有“为我性”,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发生的;同时,人作为一个群体或社会的存在物,每个人又有维持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人只有在一个整体中才能生存,否则只能是互相侵犯或自相残杀。人的生存的二重性所导致人的需要或利益的二重性,是客观存在的、必然的。人虽然表现为个体,但其行为离不开群体或社会,也离不开其他人。所以,道德就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通过这种调节既满足个人的利益和需要,又使人与人之间保持和谐统一。所以,道德既是个人追求,又是社会规范,这是从人性的角度对道德发生的静态考察。
马克思认为,研究人性要有两个层次:“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3] (p.669)。人的一般本性转化为现实人性,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关系。历史地考察社会关系,体现了个人性和社会整体性关系的不同变化,正是这些变化造就了不同的道德范型和道德教育的范型。
二、群体整体性、规范伦理与灌输式道德教育
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4] (p.87),再到后来,就有阶级的形成和国家的出现。
在蒙昧的古代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浑然一体的,个人力量的有限性,使人与人之间必须共同联合起来对付大自然的侵袭。对于一个部落的个体来说,根本不存在个人的概念,人就等同于他的部落。没有单数的个人,只有复数的人。个体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只有族群的人格,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以群体的方式发挥着他们的主体性。
从蒙昧时代进入古代文明社会之后,随着分工和交换的出现,人有了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弱小的自我意识,打破了原始自然关系结成的部落或氏族群体。但取代原始族群共同体的是神权等级共同体或皇权等级共同体,人在宗教或宗法的等级关系中并未摆脱“人的依附关系”的生存形态,个人仅在其所处的等级地位角色中获得其有限的非自我性的人格权,人的性质还是在其所属的等级群体中获得给予的规定,个人仍不具有自我的身份,他们被当作君王的臣属、主人的奴仆、丈夫的妻子。即使皇帝或教皇也没有其真正的独立人格,他们也只是贯彻神或上帝意志的奴仆。个人身份只有在这种隶属关系中得到确认。这一时期仍属“集群主体”形态的阶段,只不过由最初对自然的依附转向强制的对人的依附,形成了“权力和等级阶梯上的依附人格”。
总之,在近代工业社会之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个人与社会处在直接的同一之中,社会的群体性淹没了个体性,单独的个体,每一个“自我”,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个人不过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而已”。把个人视为部落、城邦或上帝之子,而丧失了自身。道德在其发生的价值始点上,强调整体性,强调群体的、社会的利益的满足而压制个人的需要和个人的利益。因此,道德是一种社会的强制规范,它维护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它所要反对和压制的是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对这种群体整体性的破坏。
这种维护人与人之间依附关系的道德,把道德看作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需要,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其实这种关系不是公平、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为了统治阶级利益的人身依附关系。道德教育只不过是人身依附关系的训练而已,它以服从、驯服、恪守本分为特征,它要消解的是那种自主、自尊、个性自由为特征的独立人格。这种教育也必定是在人对人的约束和强制灌输中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奴化受教育者。学校道德教育的任务就在于尽一切可能让学生了解、掌握这些道德规则并最终按这些规则行事。“强迫学生接受,伴随着对服从的学生给予奖励,对不服从的学生施以惩罚乃是最基本的教育方法。”[5] (p.4)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消解了个人的主体性,以至于今天对道德和道德教育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规范伦理和灌输教育上。《现代汉语辞典》对道德的解释为:“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对道德教育的解释为:“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影响,把一定社会的思想和道德转化为个体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该定义把道德看作社会的要求,是外在的、正确的乃至唯一的价值规范,道德教育的过程可以不考虑受教育者的主观感受,用灌输的方法和辅助于惩罚的手段让受教育者接受。虽然已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受教育者作为被动对象的不妥,提出了主动的道德接受的观念,认为“道德接受是道德接受主体出自于道德需要而对道德文化信息反映与择取、理解与解释、整合与内化以及外化践行的求善过程”[6] (p.58)。道德教育的过程就是把特定社会的思想和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思想品德的过程。与“施加影响”说相比,主动接受的“内化说”考虑了受教育者的主动性,但仅仅是使用了更加“巧妙”的方式让受教育者“接受”,归根到底仍然是一种道德灌输。其实,只要把道德看作外在于人的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规范,道德教育的方式就必然是灌输,改变的只不过是灌输的方式,使其更加“巧妙”而已。古代社会的道德教育整体上属于灌输式教育,因此,当属不“道德”的道德教育,在此意义上,古代缺少真正“道德”的教育。
三、个人主体、主体道德与主体道德教育
近代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工业社会的到来,商品经济的出现,人们开始摆脱了原始社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以及古代社会的种种人身依附关系,确立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独立性”。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客观上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关系,代替了人对自然和对他人的被动依附,使个人从群体中分化出来,确立了个人的独立身份,人的个性得到张扬;同时,市场经济也驱动着个人对其利益的最大追求。由此,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开始确立,人变成一个追求经济利益的“孤立个体”。
在人类发展的这一阶段,个人成为“单子式存在”,人只为自我的利益而存在,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内在的共通的联系,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的“自由人”。卢梭的《爱弥儿》刻画了这种人的典型人格:自爱、自主、自立、自制——他是“整数的单位”,是绝对的统一体,只为他自己而存在,而不管别人,同时也不要别人为他烦恼;他对谁也不尽义务,也不要别人为他尽义务;他在人类生活中是独立的,他所依靠的只是他自己;他不受任何人的压制,是个完全自由的人。“服从”、“命令”、“责任”、“义务”统统不属于爱弥儿,属于他的只是“自私”、“自由”和“独立”。
在这种单子式个人看来,道德就是对自己利益的最大维护,是对自己利益的认可、满足和享受。道德放弃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利益,使人与人之间走向利益对立、分争的“豺狼关系”。因此,社会只能通过某种契约关系,通过建立特定的制度以及借助于惩罚的手段,维护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道德发生的二重性中,个人性大于整体性的要求,个体道德凸显,社会公德失落,社会公德只能由制度来保障。
20世纪的伦理学家对道德的认识都凸显着个人的主体性。现象学伦理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认为道德价值是作为价值存在之个人的内在价值,个人是道德价值的真正主体,“惟有个人才能成为道德善的或恶的”。“意志行动和行为也只有根据行动着的个人自身来理解这些个人的情况才能是善的恶的”。在舍勒看来,“个人的价值是最高的道德价值”[7] (pp.52—53)。被称为“存在主义之父”的基尔凯戈尔(S.A.Kierkegaard)否定黑格尔社会总体主义的伦理观,他认为,黑格尔的伦理观醉心于社会整体,忘却了活生生的个人;偏于群众,漠视单个个体,或者把个人降为零。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一个具有真实存在的自我体验、自我关切和自由选择的“孤立的主体”。个人绝对自由的存在特性,决定了他在本质上是作为伦理的个体而存在和行动着,个人主体是一种伦理个体,伦理个体最大的特征是其内在的主体性,其基本的表述命题是“选择你自己”。存在主义的代表萨特(Jean-Paul Sartre)更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本体上把人看作自由的存在。他说,人的存在根本上是他的绝对自由,人的行动是一种选择。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一种“存在”对“存在”的关系,个人的自我存在是最基本的;其次,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关系不是“共在”,而是一种不平衡的否定关系,永远处于主客轮换的不平等之中,“一个人必须要么超越‘别人’;要么让自己被‘别人’所超越。意识与意识之间各种关系的本质不是共在,而是冲突”[7] (p.163)。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对道德的认识也突破了规范伦理学,走向目的伦理学和主体伦理学。目的伦理学认为,道德不是规范,而是一种可能的生活,规范是为了生存,自由则为了生活,道德当以人为目的,指向人的幸福。主体伦理学也认为,人是道德的主体,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内在根据,道德产生于个人自我确证、自我肯定和自我发展的需要,道德在本质上是一个高度自主的人的领域,具有为我性、求善性、内在超越性和自主自律性、自由意志性、自我约束性等。目的伦理学和主体伦理学在把道德视为人的主体活动,道德在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幸福这点上,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
对应于这种主体道德,道德教育放弃了" ought to be" 的规训和劝导,走向了主体道德教育。这种道德教育模式,在20世纪初杜威的道德教育理论中得以显现,价值澄清模式表现得最为典型。杜威认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从“实用”标准评价的,能满足人的愿望、需要和兴趣的就是有道德价值的,因此,道德没有绝对的价值,没有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戒律。他批判传统的道德教育把现成的应然的道德规则“灌进等待装载的心理和道德洞穴中”,不仅不能促进,反而会阻碍儿童的道德发展。杜威反对道德教育的外部灌输,倡导尊重儿童个性的自由教育,“以自由活动反对外部纪律”,以个体的选择代替外部的灌输,以个人的价值判断代替公共的价值认同,最终走向了价值相对主义。
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价值澄清学派直接秉承了杜威道德价值的思想,认为经验乃是价值的源泉,道德的发展就是个体经验意义的增加,不同的经验产生不同的价值,经验因个体而不同,因此,价值具有相对性。拉思斯(Louis E.Raths)等人指出,社会的变化破坏了先前生活的简单性和划一性,“现代生活的节奏和复杂性使决定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正确的和什么是可取的等问题变得更为困难,以至于为数众多的儿童发现,要确定什么是值得珍视的、什么是值得他们为之付出时间和精力的等问题,变得日益令人困惑”[8] (p.9)。在价值澄清学派看来,传统的价值教育方法——树立榜样、说服、限制选择、鼓舞、规则与制度、文化或宗教信条、诉诸良心等——都是基于一个正确的价值预设,教育就是将这些“正确”的预设传授给他人,让其接受,这些方法“并非一无是处”,但面对价值多元和价值混乱的状态,利用传统的教育方法,“当我们在进行某种说教时,儿童同时也在受其他一些榜样和主张的影响,而这些榜样和主张可能是以完全不同的价值为基础的。当儿童因缺乏目标或无视目标而出现价值混乱时,我们就坚持己见、惩罚儿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甚至强制儿童必须接受我们坚信的某种价值。但这样做,只能使许多儿童进一步陷入混乱,更无法确定他们应该相信什么”。“于是,许多儿童长大后,只知道假装相信某种价值。我们假装相信民主、信仰某种宗教,然而,对我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这些信仰实在无法令人信服。”[8] (p.45)因此,价值澄清模式帮助人们澄清个人的价值观,发展他们理智的、自主的行为能力。它首先强调个人对价值的选择,然后要珍视和珍爱自己的选择,按照自己的选择去行动。
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在强调儿童道德判断能力的形成上,也归入主体道德教育之列。柯尔伯格借鉴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指出传统“美德袋”的说教式道德教育对道德品格的发展没有什么影响。他认为,儿童是自己道德的建构者;儿童的道德既不是固有的善性的展开,也不是单纯环境强化的产物,而是主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不是向儿童传授某种具体的道德规则,而是促进儿童道德判断、道德推理能力的发展,促进儿童道德判断与行为的一致性。道德教育就是要创造机会让儿童接触和思考高于他们已有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一个阶段的道德理由和道德推理方式,引发学生的道德认知失衡,引导儿童在寻求新的认知平衡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认知水平,因此,他常用的是道德两难故事讨论法。问题是这种方法固然重视了人的道德发展水平和道德教育的主体形式,但忽视了具体的道德教育内容,成为无内容的道德教育,因而也受到质疑。
无论是杜威的实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还是价值澄清学说以及柯尔伯格的道德教育的认知发展理论,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都反对道德规范的教授和灌输,认为道德是个体的自主建构,尤其是杜威和价值澄清学说所主张的价值个体化,使道德走向了相对主义和普遍价值的虚无化,就像拉思斯所说,“从来没有人教会我们把某种价值体系变成我们内心的信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20世纪60年代,这种道德相对主义十分盛行。美国道德教育协会前主席里考纳(T.Lickona)在总结这一时期的道德教育时指出:“20世纪60年代,个人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它倡导人的价值、自律和主体性,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责任。”[9]
这种主体道德教育使每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存在,尊崇个人的价值、尊严,强调个人的利益,而不是作为“我们”群体的一员的责任、义务和整体的利益。它们虽然在反对规范伦理和灌输道德教育方面有积极意义,但却走向了极端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最终使道德共识崩溃,社会陷入了道德的无序和混乱。美国的一份教改报告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儿童时指出,“今天的学生被人称为‘自我的一代’,只顾及个人的目的——这些学生受到不同糊涂观念的影响,一方面是理想主义,另一方面追求个人私利,放弃政治和社会责任”。“二次大战以来膨胀的个人主义传统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个人处在社会中的这一传统却越来越弱,失去了内聚的共性意识。”在英国,“传统的社会道德规范已经荡然无存了”,“个人主义正在起消极作用,它使家庭和社会的人际关系变得日益淡薄”。在法国,在学校,学生一切反社会的倾向和行为均呈上升趋势。[10] 个人道德、社会道德的混乱使传统的社会基础变得非常脆弱和不稳定,人们忧心忡忡,迫切要求加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增强责任意识。这意味着个人主体道德教育已经陷入了深深危机之中。
四、人与人之间的共在、商谈伦理与交往式道德教育
现代社会的发展,使我们看到建立在单子式个人主体性基础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越来越暴露出它消极的一面,由此引发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冲突和恶化。这一切都说明,单子式个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理念正在逐步丧失其存在的历史根据,20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开始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共在性,提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概念,作为走出个人主体性危机的尝试。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认为,每个生命个体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但这些“自我”却拥有一个共同的生活世界——“世界不只是我的,世界也是你的,世界是他的,世界是我们的”。我、你、他因为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而成为共同体。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把个体当作“此在”,他认为,“此在”中渗透了世界和他人,“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此在自己本来就是共同存在。此在本质上是共在。”所以,“此在”不可能单独、孤立地存在,“共在在生存论上规定着此在。此在之独在也是在世界中共在。”[11] (p.136、140)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也认为,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自我,并不是纯粹个人的事情,因为“这种存在的主体性从一产生就已经是一个主体间性”[12] (p.134)。主体间性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的关系,它超出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模式,进入了主体与主体关系之中。在主体间关系中,每个主体都不再是单子式的主体,也不是把他人当客体对待的主体,而是一种共主体,它不仅尊重个人的“在”,而且也要他人之“在”,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对立的“豺狼关系”,而是基于共在的整体性关系。
共在性的存在是对单子式存在和群体主义存在的超越,从而也是对长期以来处于两极对立之中的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利己与利他等等的超越,体现了一种辩证关系。[13] (p.89)一方面,共在性存在以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它并不像群体存在那样排除具有独立个性的个人或压制个性,使个人成为群体、社会的工具;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也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彼此交叉重叠,每个个体都是在共在性关系中所不可缺少的,共在性关系构成了一个密切交织着的多元动态的整体。
建立在这种共在性基础上的道德和道德教育,也开始走出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强调道德的整体性或社会性。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在《德性之后》一书中,对当代道德理论的情感主义和自由个人主义进行了切肤抨击。在情感主义看来,所有的价值判断、道德判断都只不过是偏好的表达,是态度和情感的表达,因此都可以从自我所采取的立场上来判断,不需要对事物本身进行理性的认识和分析。要成为一个道德主体,就是要坚守自己选定的角色和价值,不去考虑社会的具体性背景。因此,任何人成为道德主体就是立足于自我而不是社会环境所规定的社会角色。道德的情感主义,使作为道德主体的“自我”丧失了社会同一性,道德就是自我的偏好,走向了相对主义,这使西方社会陷入了道德的混乱,成为“无道德”的社会。麦金太尔认为,当代道德的困境,从根源上讲是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失误。他重提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把德性与实践的内在善、与个人生活统一性、与社会传统生命力结合起来,重新赋予人的行为以统一性,用善的实践的目的性引导人的生活,把德性诉诸实践,联结共享善的社团,由己到群到人类。
哈贝马斯也反对道德相对主义,坚持道德规范的普遍性立场。但是他所说的普遍的道德不同于以往无视个人的群体规范,而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共识。为此,他提出了伦理的普遍化原则:“每个有效的规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那些自身从普遍遵循这种规范对满足每个人的利益所产生的结果和附带效果,都能够为一切有关的人毫无强制地加以接受。”[14] (p.65)在另一处,他再次表述了这个原则:“只要一切有关的人能以一种参加实践的商谈,每个有效的规范,就将会得到他们的赞同。”[14] (p.66)在哈贝马斯看来,为了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规范和道德律令,就必须进行必要的讨论和商谈,容许一切参与者发表不同的意见,旨在照顾所有参与者的利益。哈贝马斯把道德规则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是通过主体之间平等的交往、对话、商谈建立起来的。脱离共同的交往企图寻求一种至上的道德法则,不仅不可能反映共同的利益,而且扼杀某些人的个人利益。因此,道德规则的建立必须诉诸于交往理性和语言的商谈。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把普遍的道德规则建立在主体间商谈对话的基础上,它尊重每个人的选择、顾及到商谈方的利益。他认为,一切的伦理观念都以相互性和承认关系为中心。这种建立在人与人利益基础上的共在伦理,既超越了无视或泯灭个人利益的群体规范,又超越了只为个人利益的主体道德,实现了道德发生原点中个体性与整个性的统一。
与这种伦理观相对应,道德教育也开始走出主体的困境,而走向主体间的道德教育。在西方的道德教育模式中典型性的是体谅模式。
体谅模式的创始者彼得·麦克菲尔(P.McPhail)对英国中学生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他们对“好事”有着共同的认识,就是对人体谅、幽默、愿意谦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共享、和睦相处,而不是支配与霸权,因此,他认为,利他、关心应该是道德的核心品质。道德教育的目的就在于把个人从“自我中心、自我陶醉、自私自利、粗暴乖戾以及作为对不幸与不健康的社会的反应而产生的其他品质”中解救出来,使个人从恐惧和不信任中解放出来,使学生能够给予和接受爱,至少是兄弟般的爱,并使学生体会到关心体谅他人是一种愉快的事情。道德教育重在引导学生学会关心。体谅模式主要是依靠一套《生命线》的道德教育课程而展开的,它在内容上强调要教人“学会关心”;在形式上,强调把“学会关心”本身予以关心的氛围中,重视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但体谅模式的影响还在于其《生命线》的教材,它主要还是从德育内容的角度,促进人的利他品质发展的。
体谅模式认为,理解是道德形成的基础,也是德性的核心。所以,道德教育要创造一种和谐氛围,在其中使人相互理解。在人与人的理解中,发展利他的品质,扩展利他的范围,使每个人摆脱孤立的状态,而成为社会关系中的“我”。这种认识也为其他伦理学家所共有。黑格尔就把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依次划分为三个阶段:单个的自我意识、互助的自我意识、全体的自我意识。伦理学家帕尔默也认为个体的道德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分离的自我”到“结合的自我”,最终到“彼此相关”的过程。
近年我国也有学者把道德教育置于交往、理解的范畴中考察。鲁洁教授提出了“人对人的理解是道德教育过程的基础”。刘铁芳博士提出了走向对话的道德教育模式。对话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平等基础上的商谈,基于合作的共识,而不是基于少数人的天才设计和强迫灌输;多元社会的道德教育就是通过对话沟通形成道德共识,以谋求价值多元社会成员间的伦理共契、共生共存,社会共同体的和谐。[15] 杨小微教授也提出多元社会的价值教育必须走向价值商谈。价值商谈不同于强迫的价值灌输和一相情愿的价值引导,而是双方或多方主体在反复不断的商谈和体验中、在一个特定的具体的交往情境中形成的道德认同和自主建构。[16]
五、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特殊性与道德教育方式的选择
道德教育既取决于道德观,也取决于教育观。不过,没有抽象、空洞的道德观和教育观,一定的道德观与教育观都是特定时代的,而二者最终都取决于特定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在特定的时代,道德观和教育观又是一致的。
关键是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如何,这是我们当前确立道德教育方式的一个前提。
数千年的封建宗法统治,造成中国从未出现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主体。处于主导、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一贯强调个人服从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孔子的“无我”、“毋我”,宋儒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都是要泯灭个体的追求,维护社会的整体有序结构。这种泯灭个人的儒家文化传统与小农经济、封建宗法制度互为表里,塑造了中国人封闭、保守的心态,甚至成为一种民族的劣根性。中国社会的落后,与个人主体性的缺乏直接相关。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生存方式。人的发展开始从“依附性人格”走向“独立性人格”。社会生活中的“以人为本”,个人生活中对自我的关注,标明了康德所理想的“人是目的”在今天逐渐成为现实。
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是一个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与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发展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时代落差。在西方社会以历时态的形式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在中国却重叠和积压成一个共时态的存在形式。当前,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正以浓缩的方式集中地反映出西方社会几个世界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发展状况的演化,本是历史演化中的渐进的矛盾,在当代中国却集中凸现出来。当代中国人的发展正处在这种困境的选择中:一方面处在从“群体依赖性”向“个体独立性”转变的历史时代,这是历时态的转变;另一方面,西方的文明发展已经走过了“群体依赖性”和“个体独立性”的历史阶段,处于从“个体独立性”向以主体间性为基本特征的“类主体”转变之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已不可抗拒地进入这种转变的实际过程。也就是说,当我们启蒙个人主体性时,西方社会正在消解个人主体性;当我们高扬个人主体性时,又不得不与西方社会一道吞噬着工业文明酿成的苦果。[17] (p.110—115)当前,我们既要考虑到我国历史传统所造成的无“个人”之现实,又要面对西方强大的反个人主体性思潮的冲击,以主体性的黄昏为参照。为此,培育人性的道德教育必须确立双重的任务:既要成为个人主体的催生剂,又要成为个人主体的解毒剂。
1.坚持主体道德教育的方向,弘扬道德的主体性
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18] (p.167),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19] (p.511),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表现为一种“为我关系”。道德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个人的利益。利己或自利可以说是人的本性,也是人参与交往活动的动机所在。利己只是一个客观事实,它本身没有道德不道德之分,关键是看如何达到利己的手段。如果是损人利己,或者损公肥私,当然是不道德的;如果是互利中的合理利己,谈不上不道德。道德归根结底是发端于个人利益,它是个人在交往中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而形成的一种“默契”。
就我国的现实来看,一方面,我们长期受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灭私”成为道德教育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片面理解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道德上把“利他”、“奉献”、“自我牺牲”作为道德的核心,排斥个人的利益。这两种状况都是无个人主体性的依附关系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解放了生产力,也赋予了人的主体性,使人由依附性走向独立性,个人的利益得到了认可和保证。个体从道德的讨伐对象变成道德的主人,道德也从对个人利益的讨伐,变成个人利益的保护者。道德教育不再“灭私”,而是要引导和规范人们通过利他而合理地利己。[20]
主体的道德教育就是要弘扬人的道德主体性,使道德实践成为人与人之间在利益公平的基础上通过利他实现合理地利己,而不是为了他人利益牺牲自我。只有这样,道德才能够成为人的一种自觉实践,而不是“被迫”地做好事。道德教育才能够成为个人自觉的善性追求,才能够自主自觉地建构德性。道德不是“教”出来的,也不是“强制”出来的。道德是人的精神的自律,源自个人利益的追求。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建构人的道德主体性,这包括自主自律性、内在超越性、自由意志性等。
2.以道德的制度确保社会的公德,培养个人的社会性或集体责任感
社会公德是公共生活领域的社会道德,社会公德的基本功能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但是它与古代社会的整体性规则不同,古代社会没有独立的个人存在,个人依附于他人或社会,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公共领域,也没有公共规则的出现,所谓的整体性规则是以压制个人的道德主体性为归旨的。现代的社会公德是基于公共理性的基础上,贯彻平等、公平的原则,其实质是赋予道德主体一种责任,维护道德主体间的共同利益。
在主体道德教育中,个人作为道德的主体,就必然维护个人的利益,展现个体的道德主体性,但容易带来公共利益的失落,甚至会为个人的一己私利,不惜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在一个追求个人利益的社会中,公共利益很难成为人的自觉追求。因此,它不能诉诸或者主要不能诉诸道德教育,而必须用制度来约束、限制个人的主体性。这正如鲁洁教授指出的,在单子式的生存方式和人学观中,道德被驱逐出社会的中心而边缘化,法律和制度走上了前台,成为维系人与人关系的主要手段和工具。[13] (p.81)
因此,公共利益的维护需要制度。“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21] (p.3)制度是为了规范人的交往行为,合理地分割公共生活中的利益而结成的“公共契约”,因此,制度在本质上指向“公正”。这说明,并非任何的制度都能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利益,只有基于公正的制度,才能联结个人的利益,走向共同的利益和整体性。
在一个追求个人主体性的时代,寻求个人利益的私德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为了公共利益的社会公德则被边缘化。因此,我们认为,培育人的德性,不仅要诉诸于主体道德教育,还要诉诸于制度。制度虽然是外在的,但它是约束单子式个人、维系他们一体关系的有力手段。主体道德教育就是维护个体的利益,注重内在的自觉;制度的作用是为了维护公共的利益,注重外在的约束。在现阶段,对道德的培养,坚持道德教育和道德的制度“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可谓是此阶段可行的选择。
标签:道德教育论文; 教育论文;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依附理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伦理学论文; 主体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