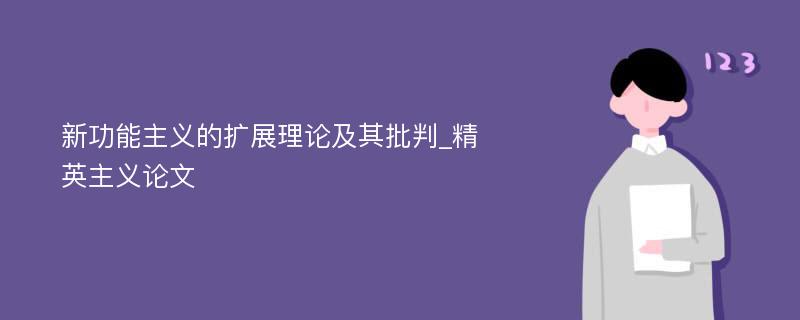
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及其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功能论文,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扩溢理论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它既是对欧洲统合(integration)实践的概括与总结,又是对欧洲统合前景的展望与指导。以厄恩斯特·哈斯(Emst Haas)、雷吉纳德·哈里森(Reginald Harrison)、菲利浦·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利昂·林德博格(Leon Lindberg)、约瑟夫·奈(Joseph Nye)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功能主义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功能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更加科学、系统地阐释了欧洲统合问题,提出了具有重要导向价值的新功能主义方法。其中,“扩溢”(Spillover)和超国家机构是新功能主义统合理论的核心概念。新功能主义认为,国家之间在经济、技术等功能性领域的合作可以扩溢到政治性领域,从而实现政治统合,并逐渐形成超国家权威机构。因此,新功能主义又被称作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新功能主义统合理论又被称作扩溢理论。
尽管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的解释力随着欧洲统合的进一步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对新功能主义提出批判,旨在重新诠释欧盟发展的新理论,如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和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应运而生,并倍受青睐,但是,不论政府间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它们都以新功能主义为理论源头,都从扩溢理论那里继承并汲取了很多营养(注: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和新制度主义是探讨欧洲统合问题最具影响力和解释力的三种主流理论。关于它们的相互关系,请参见George Tsebelis and Geoffrey Garrett文。)。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欧盟各国正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安全与防务实体,某些欧盟主要成员国还倡议设立欧盟统一的外长,甚至总统。虽然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所设想的超国家机构尚未出现,但是欧盟发展的新动向却使这一理论正在重新得到关注。因此,新功能主义对扩溢基础、过程、目标、途径、机制与战略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欧洲统合过程,以及把握用于解释该过程的各种新理论,而且对于我们认识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国际合作的实现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扩溢的基础
传统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于1943年出版《有效的和平制度》一书,提出功能主义方法,认为政治因素和技术因素可以明确区分开来,功能性领域的问题可以实现非政治化从而不触及政治主权问题。他说,“任何政治性计划都会导致争论,而功能性机构安排则带来信任与耐心。”
但是,政治与技术的严格区分作为功能主义的理论基础招致了严厉的批判。例如,哈里森指出,大多数功能化服务最终将会涉及资源的配置,而对这些资源配置的决定必然是政治性的。因此,新功能主义对此作了修正和完善。哈斯提出,对政治性与功能性作绝对的截然划分是不对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福利是难以分割的”,“经济与政治、政治家和专家的截然区分并不存在,因为技术化的决策基于一个先行的政治性决定。”由此,新功能主义对经济或技术等功能性领域向政治性领域作了相对的区分,认为两者既具有适度的分离,又有内在的联系,从而奠定了从功能性领域和政治性领域扩溢的基础。在新功能主义看来,经济虽然不能与政治完全分离开来,但是仍有一种可以作为政治统合基础的相对区分,欧盟发展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经济或技术等功能性领域和政治性领域的相对可区分关系构成了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的基础。
与功能性领域和政治性领域的区分相对应,新功能主义提出,扩滥包括功能性扩溢(functional spillover)和政治性扩溢(political spillover)两个方面。就功能性扩溢而言,国家间的统合不会局限于特定的经济和技术部门,一定领域的合作活动会扩溢到相关领域和部门,并使更多的行为体参与其中。就政治性扩滥而言,国家间的统合会在功能性合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政治精英会将注意力逐渐转向超国家层次的决策活动,并使超国家机构和非政府行为体的作用增大,民族国家的影响式微。作为扩展逻辑的结果,国家间统合会由经济、技术、社会等功能性领域扩溢到政治性领域,从而推动统合的发展与完成。
二、扩溢的过程与目标
米特兰尼认为互赖会自动扩溢,他以其“扩展说”(doctrine of ramification)来强调功能合作的扩张性,认为某一部门的功能合作有助于其它部分的功能合作,而功能部门的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形成一种功能性的互赖网,并逐步侵蚀和归并到政治部门。他说,“经济统一”(economic unification)即使不使“政治协议”(political agreement)多余,也为政治协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传统功能主义的自动扩展逻辑却过高估计了功能合作的效应。新功能主义强调,“扩溢”不是一个自动过程,而是一个自觉过程、能动过程。它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基本变量与条件的成熟,否则就会发生“环溢”(spill-around)或“溢回”(spill—back)现象。
新功能主义的扩溢概念假定,国家和区域政治经济中的各种因素是相互联系的,以致于一个领域的问题会引起其它领域的问题或要求相应的解决。在新功能主义看来,不同领域的合作具有潜在的关联性,任何领域合作的成功都会增强在其它领域进行合作的愿望与信心。一开始,这种扩溢现象只发生在某些具体的功能性任务中,但随着统合进程的发展,具有政治内涵的部门也将受到影响。哈里森认为,随着扩溢的发展,核心机构的任务和权力会相应增加,统合将逐渐侵占成员的政治敏感领域并危及其关键利益,因此,一个新生的政治共同体将出现和成长。政治性扩溢是新功能主义将经济与政治重新联结起来的必然结果。经济和技术的任务既有各自的特点而可以单独充分实现统合,又不是与政治截然分离的以至于一旦移至超国家水平就失去了与主权国家相关的权力联系。基于这种经济与政治适度分离的观念,新功能主义把欧洲统合的进程概括为:首先,经济统合逐步推进并扩溢到越来越多的领域,特别是政治性领域;然后,核心性机构将以加速度扩展,共同体建设也因之真正起步。
新功能主义侧重于统合的过程而不是特定的结果,并在很大程度上以欧盟的发展为背景和分析蓝本,或者说是对欧洲统合实践的理论诠释。新功能主义不设计统合和扩溢的具体终点或可能的选择,而是把它看作是一个不断进展中的和不断变化的过程。但它认为,最终形式应该是机构化的。如,哈斯强调:“政治统合是一个进程,通过这一进程几个处在不同国家环境中的政治行为体被说服将其忠诚、期望与政治行动转向一个新的中心,该中心的机构拥有或要求拥有对现有民族国家的管辖权。”林德博格认为,统合是一个过程,在统合过程中,“各国放弃独立推行对外政策和关键性国内政策的愿望和能力,转而寻求作出共同决策或将决策活动委托给新的中央机构。”在新功能主义看来,超国家机构对于统合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简·斯维尼(Jane Sweeny)提出,机构建设既是统合过程的重要成果,也是统合成功的测定标准。只是对未来这些机构的形式,新功能主义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作为扩溢与统合的结果,超国家机构既可能是一个联邦国家,以可能是一个非联邦性质的国家,还可能是一个缺乏国家性的共同体。
三、扩溢的动力与机制
在动力和机制问题上,新功能主义认为,统合是管理需求扩溢产生压力的反应和结果。哈里森写道,管理需求扩溢导致功能扩溢是“统合的扩展逻辑”,并因此称之为扩溢效应,即与最初任务相对应的政治决策和权力授予只有任务本身扩大时才会实现,并体现为与这些任务相关联的国家之间的妥协。对每一阶段统合进展的最好解释,是民族国家内部及其相互间利益的聚集与一致,而不是基于一系列相同的要求与希望。新功能主义以欧共体发展为例,认为正是超出民族国家权力范围的管理需求扩溢导致了超国家水平上的管理功能与机构扩溢。成员具体经济与社会管理任务和基础性政治权利的完全的或者相当程度的分离,是欧共体现实发展的政治基础,也是设计与推动这一统合进程的唯一有效方法。欧洲统合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表明,它确实经历了一个从纯经济领域起步并以经济领域为主,然后逐渐推进或扩溢到相关领域并将某些传统意义上的成员国部分主权集合起来的过程。
与传统功能主义不同,新功能主义不认为技术合作可以忽视政治因素,在统合的过程中,行为者的行为与立场会逐渐政治化。哈斯认为,部门统合具有扩张性,“部门统合的扩张逻辑”(the expansive logic of sector integration)是部门功能合作所产生的结果。在哈斯看来,开始时各行为者会在若干技术性或非争议性的领域内进行合作,但是日后他们逐渐发现,唯有将较多的权威让度给集体决策机构,或向其它相关功能性领域扩大其合作范围,才能达到他们设定的目标。当合作范围日益扩大时,原始的合作会逐渐向有争议的部门进行。最终行为者逐渐政治化的发展,使得原来只是经济部门的统合,提升到政治方面的统合。因此,统合的关键在于行为者原先技术性或非争议性目标的逐渐政治化。
此外,新功能主义还设定了背景变量(background variables),经济联盟变量(variables at the moment of economic union)和过程变量(process variables),以及实现扩滥的互动关联模式。根据哈斯和施米特的研究,每一项变量的分值越高,经济联盟扩溢到政治统合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民主、多元和工业社会的背景下经济问题更有可能扩溢到政治统合。在此基础上,奈创立了一个以“过程机制”(process mechanisms)和“统合潜力”(integrative potential)概念为核心的新功能主义模型,进一步阐发了扩溢和统合现象发生的条件。奈认为,新功能主义所讨论的过程机制,包括扩溢、互动的提升、刻意的联系、精英的社会化、地区集团的形成、意识形态—认同的魅力、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等等,并不一定或足以保证统合的顺利进行。真正影响统合早期承诺与后期计划的是统合的潜力,即进程机制所激发的统合条件。统合的潜力主要由单位的对称或经济平等,精英价值理念的互补性,社会多元性的存在,成员适应和应变的能力等四个方面因素决定。只有进程机制将统合潜力释放出来,才能有力地推动统合进程。此外,奈还认为关于利益公正分配、可能的代价和外部压力等方面的主观认知电会对统合进程产生影响。
四、扩溢的战略要求
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认为,尽管统合的过程不应是“自上而下”而就是“自下而上”,即由低政治(1ow politics)逐渐到高政治(high politics),但扩溢逻辑的非自动性要求成员各方必须考虑政治意愿中的各种因素,因为即使共同体内有着日益集中化发展的压力,成员依然有着足够强大的能力影响实质性权力的转移。因此,扩溢的发生不仅取决于经济联系的政治化,而且有赖于政治精英的努力、刻意的“联系战略”(link strategy),以及认同感的建构。
新功能主义者普遍认为,成功的统合取决于人们“内化”(internalize)统合过程的能力,即成员精英,而不是外来精英,为统合进程指明方向的能力。哈斯指出,“只有当各行为体在切身利益所激发的认识基础上,希望将某一事务所学到的统合经验应用到另一个新情况时”,扩溢现象才会发生。因此,在统合过程中,扩溢现象的发生有赖于精英的推动。哈斯认为,主要精英和政治领袖具有一致的政治使命和承诺,是统合顺利发展所必需的。
施米特认为,扩溢是因为尝试统合的成员国家对原有统合目标不够满意而不断扩大合作范围与领域的过程。扩溢的实现主要取决于:第一,各种功能性事务本身的互赖性;第二,精英通过学习可以主动赋予统合新任务,使扩溢效应持续出现。
奈认为,功能联系(functionalist linkage)是扩溢的轴心。恰当的“刻意联系”(deliberate linkage)有助于加强彼此间的“功能联系”。“刻意联系”将不同类型和领域的问题联系起来,使一个问题的解决或改善经常仰仗另一个问题的处理。奈认为,这种“刻意联系”往往不是因为技术上必须如此,而是具有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或政治上的方便,是由政治人物、官僚机构和利益集团所推动的。因此,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又将政府的主动角色作为分析成功扩溢乃至政治统合的关键。
另外,新功能主义理论假设,国民忠诚感是可以改变的,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可以转移到对有利于国际合作的框架上来。当功能化统合产生权力越来越大的超国家机构时,政治需求和公民的身份认同感也将发生一个扩溢过程。哈斯写道,“个体的政治忠诚是对关键政府机构功能运作满意的结果。”既然人们可以同时忠诚于不同的机构,对某一机构忠诚的转移也就是可能的。尽管最终政治忠诚转移的条件是十分严格的,如共同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紧密的经济联系等,但当人们觉得从功能性机构中可以得到他们从民族国家中不能得到的需要时,他们即会将原来对国家的忠诚转移到对功能性组织的忠诚。因此,新功能主义认为,从共同利益出发,建立共同认知后,各方才可能完全统合,认同感的建构乃是实现扩溢的重要条件之一。
五、对扩溢理论的批判及其启示
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并不是解释欧洲统合问题的唯一理论尝试。政府间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也对欧洲统合实践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与新功能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扩溢理论的缺陷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批判。
首先,关于扩溢的基础,新功能主义对功能性领域与政治性领域的区分是僵硬的、机械的、理想化的。现实中,二者的界限往往难以厘清。特别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趋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和突出。正是对功能性领域和政治性领域的线性区分使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对扩滥过程、目标、动力、机制与战略的解释陷入了难以逾越的悖论。
其次,关于扩滥的过程与目标,各国间将合作习惯从一个领域扩展到另一个领域,特别是政治性领域的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欧盟的发展并未像新功能主义所预想的那样导致超国家机构的出现。新功能主义极其重视的功能性联系并不一定具有决定性意义,它的扩滥效应是有限的。政府间主义对新功能主义扩滥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它忽略了高政治(外交、安全与防务)与低政治(经济、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区别,功能性统合未必一定能够导向政治性统合,功能性合作的“滚雪球”效应不会自动出现。政府间主义的重要代表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就认为,扩溢效应只适用于低政治领域,而不适用于解决高政治问题,国家间关系不会超越政府间合作而发展到高政治上的超国家统合。虽然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设想欧洲统合的结果应是各国将权力转交给超国家机构,但欧盟至今并没有朝这一方面发展。相反,欧盟却代表了主权的集中或共享,在欧盟内各主权国家政府仍然是最主要的决策者。因此,罗格·汉森(Roger Hansen)断定,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只对低政治领域具有解释力。
再次,关于扩溢的动力与机制,欧洲各国政府对于统合的政治诉求和政策趋同,相比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所强调的“部门统合的扩张逻辑”更具说服力。虽然功能性领域的合作与联系可以扩滥到政治性领域,但是在没有共同的政治意志与政治诉求的情况下,功能性领域的合作如何可能?功能性扩溢与政治性扩溢又如何可能?尽管表面上看,推动欧洲统合进程逐步发展的是经济因素,但政治因素却是促成欧洲走向联合的真正初始动因。常常被新功能主义用来作为扩滥理论佐证的欧洲统合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却恰恰暴露了它的缺陷。20世纪50年代初的煤钢联营计划,作为欧洲统合的起点,是出于消除危害欧洲安全的动机而开始的。在二战刚刚结束之际,煤炭和钢铁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质,它们关涉到各个国家的切身安全利益,没有政治上的推动,这样的功能性领域合作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实证明,政治影响和政治压力在西欧统合进程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欧的统合经历本质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非政治性’的。”1986年《欧洲单一法案》、1991年《欧洲联盟条约》和1998年《阿姆斯特丹条约》的签署,进一步对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提出了挑战。例如,政府问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安德鲁·莫拉维斯克(Andrew Moravcsik)指出,仅仅用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无法解释《欧洲单一法案》的出现。相反,他认为,导致该法案出台的政治共识综合了诸多因素,包括欧盟国际机构内部产生的动力、较广泛的支持、以及来自各国政府和国内政治的动力等。
最后,关于扩溢的战略,新功能主义强调精英和政治家在欧洲统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扩溢理论对他们的突出有些过头,并因而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和专家技术决定论倾向。在统合过程中,政治精英主要关注的仍是各国国内的政治问题,而不是超国家层次的政治决策。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还过分强调了超国家机构的作用,实际上,在国际统合的过程中,民族国家及其政府才真正发挥着主导性和决定性作用,超国家机构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现实中,民族国家并不是本着解决共同问题的精神进行国际合作的,成员国政府是否接受超国家机构的决策仍主要取决于其国内政治的需要。即使是关系到成员国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共同体的决策最终仍要由各国政府来做。因此,在政府间主义看来,统合不是扩溢的自然生长过程,而是国家理性决策和交易的结果。政治性领域的统合只能通过政府间的磋商、妥协和讨价还价来实现。自《欧洲单一法案》以来,欧盟制度的变化已经不能仅仅用扩溢理论来解释,甚至不能主要由扩滥理论来解释。政府间的讨价还价为《欧洲单一法案》和《欧洲联盟条约》的扩溢提供了动力。虽然扩溢肯定是统合的一部分,但政府间的讨价还价是怎样快速或广泛地扩溢到其它部分的,仍是一个尚待回答的问题。
另外,新功能主义将国民真诚感的转移理解得过于简单。实际上国家认同的变迁是极其复杂的,其间的障碍常常并不是简单的功能合作就能够消除和逾越的。在欧洲统合的过程中,公众对政治行为体的支持与忠诚实际上并未真正从成员国转向共同体,他们对超国家机构的认同也并没有像新功能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发生。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怀疑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对欧洲统合问题的解释力。在各种理论流派中,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是唯一在专门研究欧洲统合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而言,它对欧洲统合进程的影响更为深刻。虽然《欧洲联盟条约》的诞生为超越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准备了基础,但是该条约在签署过程中经历的挑战与波折(注:如《欧洲联盟条约》在丹麦全民公决的结果是反对;在法国全民公决勉强通过;在英国则引起了激烈争论,许多人持保留态度;在英国和德国甚至受到了法律质疑。清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的著作。),作为扩溢、环溢、溢回现象的例证,却为扩溢理论提供了新的注脚。特别是,欧盟各成员国正试图建立自己的安全与防务实体,以承担现在山北约承担的军事任务。这需要进一步推进欧盟政治统合,并在对外政策、军事思想、军事指挥等方面达成充分一致。如果这一实体得以形成,那将是新功能主义部门统合由功能性领域向政治性领域扩溢的一个重要范例。欧洲的统合过程一直是走走停停,各种理论诠释常常随统合进程的潮起潮落而此消彼长。迄今为止,任何单一理论都无法令人心服地全面解释极其复杂多样化的欧洲统合问题。对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等进行综合可能是未来欧洲统合理论的发展方向。
辩证地看,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的价值和缺陷同样是不可否认的。全面理解它的长处与不足无疑有利于世人更完整地掌握欧洲统合的动力与机制,并将欧洲统合经验更好地应用于解决世界其它地区的国际合作问题。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以及政府间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对它的批判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三点关于区域国际合作的有益启示:第一,从经济、技术等功能性领域入手加强国际合作,可以为地区主义的出现提供重要的统合基础,并有利于形成以国际组织为形式的国际制度和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机制;第二,功能性领域国际合作并不必然导致政治性领域国际合作,政治、军事、安全方面的国际合作既需要功能性扩溢效应的累积,更需要各国政府形成相近的政治诉求和政策导向;第三,区域国际合作并不必然产生超国家权威,但是国际合作的机制化和机构化是确保合作进程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