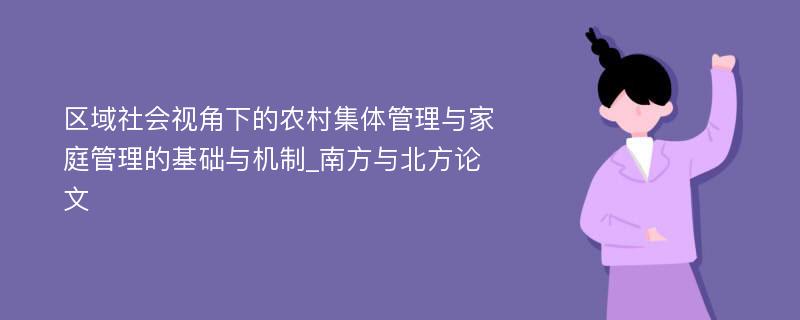
区域社会视角下农村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的根基与机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根基论文,视角论文,区域论文,农村集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村发生了两件具有长久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50年代轰轰烈烈的农业集体化,即从土地改革发展到互助组、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最后到以社队为单位的集体统一经营。集体化改变了中国数千年一家一户生产经营方式,实行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集体共同劳动,分配大体平均,即通常讲的集体经济时代。二是80年代迅速兴起的家庭承包经营,它直接造成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使农村生产经营恢复为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体制。从集体统一经营到个体家庭分户经营,这两件一脉相承又相互矛盾的大事所发生的原因,以及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和评价,截至目前很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由此也影响到相关研究的进展。尽管近年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开始增多,但方法上又存在很大的局限。笔者认为:作为一个研究问题,最重要的不是如何评价,而是拉开时空维度,探讨其发生原因和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地方性经验与全国性政策之间的合理张力,以加深对中国现行农村基本经营体制的认识。由此,本文将从区域社会的角度,对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的根基与机理作出一种新的解释。 一、问题的追问及区域社会视角 农业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为什么在中国发生?目前大致有两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是领导人的主张。他们指出:为了克服农民贫苦的状况,必须实行集体化;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与传统个体生产经营所不同的集体统一经营。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步地集体化”①。而在5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进程中出现“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②之后,有人甚至将人民公社统一经营模式视之为“狂想”。家庭经营则被认为是少数地方官员推动,后被中央领导认可并在全国推广的产物。民间也一度流行“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③的说法。农村改革进行了20多年后,因为存在对农村改革的争议,有人甚至认为: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只是少数“官老爷”的“阴谋”。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是对苏联模式的照搬和否定。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率先实行农业集体化,并以集体农庄的方式进行经营管理。而中国数千年来都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在50年代推进农业集体化时,中国正值向苏联学习的时期,所以农业集体化实行集体组织统一经营,无疑带有模仿苏联模式的成分。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以“共同劳动,计工计酬,集中经营”④为蓝图,而中共中央也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⑤形式。以此为逻辑,到80年代以后农村改革实行家庭经营,也正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 可以说,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根据,但并不是完全合理的解释。毫无疑问,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都有领导人决策和推动的因素,也有向苏联学习的元素。但是,不可忽视的是,集体统一经营和个体家庭经营绝非少数领导人一时的头脑发热,甚至“狂想”和“阴谋”。事实是:在全国推进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的决定出台前和推进过程中,各地都已存在大量的典型事例,而领导人也只是将它们拿来和提升后,又向全国推广而已。 因此,我们研究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不能只从领导人的想法和政策文件出发,而要首先从事实出发。而当我们从事实出发时,又会发现两个很有意思的事实逻辑。 一是集体经营起源于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由北向南推进。集体统一经营的典型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例如,山西的张庄早在40年代后期土地改革刚结束时,就开始了集体互助。50年代农业集体化进程中的模范典型也大多产生于北方区域。例如,山东的厉家寨就被视为合作化的典范。人民公社则最早发源于河南和河北。在人民公社化的进程中,最早实现人民公社化的9个省,有8个在北方区域。⑥到六七十年代,作为全国集体经营旗帜的大寨则位于山西。直到80年代后,北方还有一些村庄仍然在坚持集体统一经营。 二是家庭经营起源于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由南到北推进。50年代,因对过快集体化产生抵制,被毛泽东认为进行“生产力暴动”⑦的地方是浙江。5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则主要发生在安徽、浙江、四川、湖北、广东等地。⑧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受到批判的包产到户的发生地,主要位于安徽、广西、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南方地区。70年代后期,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改革首先发源于安徽、四川等地。⑨邓小平就表示:农村改革“开始的时候,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赵紫阳同志主持的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万里同志主持的安徽省”⑩。 早在集体化发生之初,作为集体经营雏形的互助合作组织就存在着南北差异:北方的数量大于南方(11)。“按地区分布来看,组织起来的农户在各大行政区占农户总数的比例是:东北区75%,华北区50%多,华东区50%左右,西北区45%,中南区30%,西南区40%。在各大行政区组织起来的农户中,参加常年互助组的户数比例是:东北区33%(加上三大季组即占70%),华北区33%,华东区35%强,西北区10%,中南区14%,西南区10%。”(12)在集体化进程中,毛泽东也注意到党内有人提出过南北区域差异现象。但他只是将其视为一种不积极推进集体化的借口。(13)而到80年代初,当家庭经营还未成为国家决策时,地方领导产生争议的代表性意见也分别来自北方和南方的领导。(14) 那么,我们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集体化之后的集体经营始于北方且至今在北方仍有深远影响,而家庭经营始于南方且至今在南方仍根深蒂固?对于这一问题,现有的研究未能很好地给予回答,因此需要寻找新的研究视角。 截至目前,在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中,主要有两种研究视角和学术传统。 一是整体国家的视角,即将全国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是一种宏大叙事式的宏观研究。这种研究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档案文献,或者理论建构,其成果甚多。仅就农村研究看,代表性著作有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等。这种研究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但也存在相当的局限。例如,《乡土中国》一书就主要是基于中国核心区域的研究,而许多次生区域或边缘区域的现象就被忽视。 二是个案社区的视角,即将某一个个案作为研究对象,是一种微小叙事式的微观研究。目前,这种研究日益增多。就农村研究看,可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代表。这种研究主要是基于实地调查,其优点是可以进行深入的挖掘。但其也有一定的限度:一是在社会多样化的条件下,一个案例很难解释一类现象;二是因为选取的案例不同,在一个地区内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甚至自相矛盾的结论。近些年,有关农村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孰优孰劣的争论分歧甚大且难以对话,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我们需要借助于其他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进展,而历史学界也开始注意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即区域性研究。其中,傅衣凌提出:“由于生产方式、社会控制体系和思想文化的多元化,由于这种多元化又表现出明显的地域不平衡性和动态的变化趋势,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许多西欧社会发展模式所难以理解的现象。”(15)而杨念群则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中观”理论。由于区域社会研究进展较快,产生了不少区域性研究成果,它们开始被视为某种“学派”。其中,山西大学和南开大学对华北农村的研究就被视为一派,而基于对华南农村的研究也出现了所谓的“华南学派”等。 与中国学界的情况类似,国外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视角也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部分的变化过程。在早期,比较多的研究是国家整体研究,以美国学者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为代表。后来,随着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问世,区域社会研究开始迅速增多,其中代表性著作有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美国学者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和《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美国学者濮德培(Peter C.Perdue)的《榨干土地:湖南的政府与农民,1500-1800》等。 现有的区域社会研究无疑大大弥补了原有学术传统的不足。但是,对于本文要研究的现象来说,它们仍然不够理想。其主要在于:相当多数的区域研究,只是对某一个地区的某一现象的研究,更多属于国家整体之下的地方性研究,如华南的宗族研究、华北的水利社会研究、湖南的土地、农民与政府研究,等等。因此,有学者甚至将区域史与地方史加以等同,认为“区域史,又称地方史”(16)。 在笔者看来,区域研究不能等同于地方研究,区域社会研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某一个地方的现象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寻求造成区域性特性的构成要素,从而形成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特质。因此,区域研究至少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同质性,即同一区域具有大体相同的特质,正因为这一特质而造成该区域相类似的现象较多,具有区域普遍性。当然这种同质性并不是区域现象的绝对同一性,主要在于其规定的现象多于其他区域。二是异质性,即不同区域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性特征,正因为这一特质造成该区域同类现象不同于其他区域的同类现象。无论是同质性,还是异质性,都需要经过比较才能体现。而比较则需要有确定的标准。因此,区域研究与地方研究都属于国家整体的部分研究,但又有不同。地方研究可以不用比较,是某个地方就是某个地方,其研究限定于某个地方。而区域研究一定要发现该区域与其他区域所不同的特质,一定是在比较中才能发现其特质,且这种特质是内生的、内在的,而不只是外部性的现象。 二、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的区域社会根基 中国的集体经营是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形成的,家庭经营又是对集体经营的替代产生的,这就使得中国农村经营体制及其变迁呈现出多层次和复杂性。 通常来讲,传统中国的个体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个体经济既表明生产资料为个体家庭所有,同时又表明生产经营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家庭是产权单位、生产经营单位、生活单位、社会单位和政治单元的统合体。这也是传统中国农村的基本底色。(17)从对农业集体化的最初认知看,它既包括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否定,也包括对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的否定,由此产生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的集体经济。家庭经营则是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方式。仅从生产经营单位看,当代的家庭经营与历史上的家庭经营没有什么差异。这就是说,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基础上,中国农村的生产经营方式经历了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在不同区域有不同表现。其根源就在于农业社会对自然条件依存度高,传统中国是一个在长期历史上形成的超大规模的农业国家,自然—社会—历史条件的区域性差别大。 在中国,最大的区域差异是北方与南方。中国地理分布的分界线之一是淮河,淮河以北为北方区域,淮河以南为南方区域。费正清曾描述道:“凡是飞过大陆中国那一望无际的灰色云天、薄雾和晴空的任何一位旅客,都会显眼地看到两幅典型的画面,一幅是华北的画面,一幅是华南的画面。”(18)在世界上,也很难找到有中国这样南北差异之大,并对经济社会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家。中国历史上就曾数度出现过南北分化、分裂、分治时期,如南北朝。南北差异也给政治决策和走向带来影响,如开辟大运河、首都东移和北进、政治过程中的南巡和北伐等。这都表明中国北方和南方有着不同的自然—社会—历史土壤,会生长出不同的结果,由此也构成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的区域社会根基。 农村社会是由一个个村庄所构成的。在中国,集体化也是以一个个村庄为单位进行的。因此,通常所说的集体指的是“村集体”。(19)村庄是农村居民的聚落,体现着人与空间的关系。村庄首先就是一种空间形式,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个体经营都是在村庄这一空间中发生的。法国学者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社会生产关系仅就其空间中存在而言才具有社会存在;社会生产关系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将自身铭刻进空间。否则,社会生产关系就仍然停留在‘纯粹的’的抽象中。”(20)因此,我们要理解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首先要将其放在村庄这一空间中考察,而中国南北区域差异就最为直接地体现在村庄这一微观空间社会中。 村庄在英文中是village。有一句西方谚语说:“Every village has its idiosyncrasy and its constitution”,就是说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特性和脾气。在中国,农村村庄属于长期历史上形成的共同体,有着共同的特点。首先,村庄都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其次,村庄都是以家庭为核心单位和基础,往往以姓氏命名。其原因一是在于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方式,二是在于中国血缘关系的独立性和延续性。除了“中国性”以外,中国村庄的南北区域差异也很大,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即“村”和“庄”的名称指代、涵义、类型及其分布都有所不同。 在中国北方,村庄更多是以庄、寨、营、屯等命名。如前文所述的作为互助合作集体经营典型的山西张庄、大寨,山东的厉家寨(相邻的徐家寨、张家寨等),河南的七里营(该乡包括刘庄、余庄、杨庄、刘八庄、丁庄、马庄、大赵庄、大张庄、小张庄、曹庄、夏庄、陈庄、东王庄等43个村庄)。 在中国南方,村庄更多是以村落的自然性命名,如村、冲、湾、垸、岗、台等。如太平天国起义的发源地广西金田村,孙中山的出生地广东翠亨村,蒋介石的出生地浙江溪口,毛泽东的出生地湖南韶山冲,刘少奇的出生地湖南炭子冲,邓小平的出生地四川石牌村,林彪的出生地湖北林家大湾等。 名称是一个标识和指称。这种标识和指称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想象,而有其内在的涵义。庄、寨、营、屯等,更多的是一个人口居住相对集中的农村聚落,集居、群居,集聚度高,属于集聚型村庄,即“由许多乡村住宅集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大型村落或乡村集市。其规模相差极大,从数千人的大村到几十人的小村不等,但各农户须密集居住,且以道路交叉点、溪流、池塘或庙宇、祠堂等公共设施作为标志,形成聚落的中心;农家集中于有限的范围,耕地则分布于所有房舍的周围,每一农家的耕地分散在几个地点”(21)。村、冲、湾、垸、岗等,更多的是人口居住相对分散的农村聚落,主要是散居,甚至独居,分散度高,属于散漫型村庄,即“每个农户的住宅零星分布,尽可能地靠近农户生计依赖的田地、山林或河流湖泊;彼此之间的距离因地而异,但并无明显的隶属关系或阶层差别,所以聚落也就没有明显的中心”(22)。鲁西奇就针对传统中国的农村聚落问题提出:“从总体上看,北方地区的乡村聚落规模普遍较大,较大规模的集居村落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南方地区,“大抵一直是散村状态占据主导地位;南方地区的乡村聚落,虽然也有部分发展成为集村,但集村在全部村落中所占的比例一直比较低,而散村无论是数量、还是居住的人口总数,则一直占据压倒性多数”(23)。 中国南北农村居民的集居或散居形态,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1.原始起源。人类在初始年代,特别需要以群体组织的力量获得生存。尽管考古学证明中国的农业文明起源是多点而不是一点,但农业文明的起源和由点到面扩展开来,则是在北方的黄河流域。中国早期农村居民一般是“聚族而居”,即一个家族(宗族)的众多人口同居一个村庄。当下,华南地区还大量保留着这种形态,即宗族型村庄。(24)从这些村庄看,其居民的渊源基本来自北方地区,居住其中的人被称为“客家人”。因此,北方的集居、群居的历史更为久远。 2.经济基础。村庄作为人们的一种居住单位,必然有其功能。人们以集居或以散居方式居住,在于满足其需要。这种需要首先是经济,由此赋予村庄经济功能。 物质生产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也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条件。而物质生产是以自然条件为前提的,愈是农业文明时代愈是如此。 中国南北方以淮河为线,并不是简单的位置居中,更主要的是气候的差异,俗称为“天”。淮河以南属于亚热带范围,最冷月平均气温不低于0℃,且雨季较长,年平均降水量为750~1300毫米;淮河以北则属暖温带范围,冬冷夏热,四季分明,日平均气温低于0℃的寒冷期普遍在30天以上,雨季较短,年降水量一般不超过800毫米。 尽管北方和南方分别有黄河、长江两条大河,但其气温、雨水及分布有着很大的差异,农业生产方式也不一样。北方主要是旱作物。特别是华北平原适合连片耕作,人口也可以相对集中。金其铭就考证指出:北方农村聚落多为大型聚落,密度稀,形状虽各异,但以团聚状占多数;特别是“华北地区的农村聚落一般很大,也可以说是全国农村聚落最大的地区。一般都是上百户和几百户的大村庄,有些村庄甚至超过一千户,村庄分布比较均匀,这与华北地区农业发达、开垦历史悠久有关。华北地区主要是旱作,作物受到的管理照料要比水稻少得多,也不必有水田地区那样许多笨重农具,因而在历史上形成农村时,耕地可以离村庄远一些,一般村与村之间,相距1—2公里,虽然比长城沿线和东北距离小些,但比南方长江流域,间距要大得多。在华北平原,尽管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500人,但由于村庄规模大,因而每百平方公里拥有的村庄数仅35—70个,相当于长江流域每百平方公里200—400个村庄的1/5—1/10”(25)。费正清也指出:“水稻是长江流域和南方各处中国人生活的支柱。”(26)而种植水稻,难以连片耕作,只适宜随地形水情分散居住,大多表现为“因水而居”。 北方自然条件相对恶劣,普遍面临缺水问题,单个农户的生产生活能力弱,需要群体互助。在北方,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定数量的人口,有若干口水井(或者其他水源),集聚在一定空间内而形成村庄。而南方自然条件较好,大多依靠自流灌溉,单个农户的生存能力较强。因此,在南方,存在大量的单家独户,他们甚至与世隔绝也可以生存下来。在南方,往往是一个家庭,一座房屋,一片田地,构成一个生活空间;另一个家庭,另一座房屋,另一片田地,又构成一个生活空间;而相互之间缺乏紧密的有机联系。因而,村庄只不过是一定数量家庭的聚合。 正是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国家的经济重心逐步发生了由西向东、由南向北的转移。因此,“南粮北运”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3.国家统治。村庄是国家的基本构成单位。在农业文明时代,国家主要是由一个个村庄构成的,村庄是国家组织的微观基础,国家统治格局影响着村庄的特性,并赋予村庄政治功能。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中国文明发源于北方黄河流域。尽管经济重心日益向南转移,但国家统治中心长期在北方。其重要原因是,在北方黄河流域的更北方有游牧民族。这一民族会经常性地侵扰中原地带。而为了免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国家的军事和政治重心长期位于北方。在中国,作为马克思所说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其重要特征是国家不仅占有全部领土,而且占有相当部分用于直接耕作的土地,属于典型的权力支配财富。皇帝及其家族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更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同时,地方的豪强也会利用权力和势力占有大量土地。因此,中国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化程度高。当然,这种集中化在不同区域的表现形式不一样。由于统治重心在北方,由统治权产生的土地所有权集中主要在北方。皇族、豪强占有大片土地不可能由他们自己耕种,只能雇用他人耕种,由此形成一个个便于集中管理的村庄。在北方,尤其是河北、河南、山东,农村聚落大多以“庄”命名,就在于它们属于皇族或豪强大户的占有地。在这些地方,农村社会的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特点突出,“行政村”的历史久远,如秦汉时期就开启的乡遂制度。鲁西奇也认为:“自战国秦汉以来,乡村控制制度的设计,基本上是以集中居住的集村为基础。”(27) 由于地域辽阔、统治手段有限和中央集权统治体制,传统中国政府的直接管辖能力由中心到边缘出现递减。换言之,距离国家统治中心愈远,国家统治愈是“鞭长莫及”。因此,相对于北方,国家统治在南方较为薄弱,运用国家权力占有大片土地的现象在南方也较少。由于南方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化程度远远低于北方,农村聚落很少用“庄”命名。同时,国家行政管理的历史短且更为松散,农村社会自治程度高。因此,南方的农村更多是“自然村”,即在漫长历史中自然形成的农村聚落,较少行政建制的特性,其分散性和离散度较高。 4.战乱迁徙。农业社会以土地为生,而土地是不能移动的,因此农民具有安土重迁的特性。但对于人类的生存发展而言,安全总是第一位的。在中国,各类战争与动乱一直伴随着国家发展,农村社会成员不得不通过迁徙他地,或者群居来保卫自己,从而使村庄具有相当程度的保卫功能。而这些村庄一定是以群居、集居为条件的。 中国政权中心在北方,且北方战乱多于南方。据统计,从公元前221年到1840年,以战役为基本单位,中国历史上共发生战役840例。以秦岭—淮河一线划分南北,则北方为644例,占总数的77%,南方为196例,占总数的23%。(28)大量的战争和抢劫,也使得北方民众有据险群居的需要。例如,河南七里营之名就来源于宋朝将领萧寅宗在此安营扎寨,距小冀七里,且“小冀到新乡,一溜十八营”。再如,山东厉家寨是明朝洪武年间,厉家祖先因为战乱及其引起的灾荒而逃至山东的大山中,据险而居所形成。除了“营”“寨”外,还有许多村庄是通过长期屯兵和兵农合一形成的,因此被命名为“屯”“卫”。另外,由于北方的豪强地主多,其构筑的庄园具有很强的群居保卫功能。例如,《水浒传》中描述的祝家庄,仅粮食就值100万贯(约合今天的5000万元人民币),价值相当于晁盖等人所劫生辰纲的10倍。 与北方类似,位于华南的一些宗族型村庄也具有保卫功能,其原因一是其始祖来自于北方,对于战乱和以族自卫有着深刻的体认;二是其属于由北方迁徙而来的“客家”,要在他乡生存繁衍,必须群居自保。但是,华南的宗族型村庄数量不多,主要原因是社会环境相对安全。 集聚和散居不仅仅是一种居住形态的差异,同时也孕育了人与人之间的结合关系及其意识形态,从而建构起“村庄性”。鲁西奇就认为:“采用怎样的居住方式,是集中居住(形成大村)还是分散居住(形成散村或独立农舍),对于乡村居民来说,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方式(来往田地、山林或湖泊间的距离,运送肥料、种子与收获物的方式等),还关系到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与组织方式,甚至关系到他们对待官府(国家)、社会的态度与应对方式。”(29)而在法国学者阿·德芒戎看来:每一居住形式,都为社会生活提供一个不同的背景;村庄就是靠近、接触,使思想感情一致;散居状态下,“一切都谈的是分离,一切都标志着分开住”。因此,也就产生了法国学者维达尔·德·拉·布拉什(Vidal de la Blache)所精辟指出的村民和散居农民的差异:“在聚居的教堂钟楼周围的农村人口中,发展成一种特有的生活,即具有古老法国的力量和组织的村庄生活。虽然村庄的天地很局限,从外面进来的声音很微弱,它却组成一个能接受普遍影响的小小社会。它的人口不是分散成分子,而是结合成一个核心;而且这种初步的组织就足以把握住它”。(30)因此,散居和聚居存在着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上的深刻差异。这种差异也具有南北区域的特点。 第一,北方集居村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小、与土地的空间距离大,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南方散居村庄因为人与地之间的空间距离小,与人的空间距离大,更加注意人与地的关系。正如德芒戎所指出:“在(集居)村庄的景观中,房屋群聚在一起,这多少有点加强了耕地上的孤寂感;村庄与其土地是截然分开的。在散居的景观中,房屋不远离耕地,房屋相互间的吸引力,远小于房屋和田地间的吸引力。农庄及其经营建筑物都建在田地附近,而且每块耕地的四周,常有围墙、篱笆或沟渠。甚至那些被称作小村(hameau,Weiler,hamlet)的小房屋群,似乎也应当一般地看作散居的形式,因为它们几乎总是意味着房屋和田地是靠近的”;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位于田地中央的孤立居住的形式,是一种很优越的居住方法,它给农民以自由,它使他靠近田地,它使他免除集体的束缚”(31)。 第二,北方集居村庄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整体性强,强调村庄的同一性和一致性。在北方村庄,居民基本都从事农业生产,居住的房屋形态大体一致,区别在于其大小。南方散居村庄则充分考虑自然地理因素,农村居民分工分业,差异性明显,村庄随山水而形成,民居也各不相同。 第三,北方集居村庄的组织性和集体行动能力强,各农户的生产条件和能力大体相同,社会结构缺乏分化,更多的是平均式的平等。为防止外部力量的侵入或者改善自我生存条件,居民比较容易组织并形成集体行动能力,村庄集体本位强。就是要饭,也要“抱团”。村庄与农户的社会联结较紧,甚至离开村庄,农户便缺乏生存发展的条件。南方村庄各农户的生产条件和能力则明显不同,社会结构有所分化。村庄各家户的自我生存能力强,不太依靠集体,家户个体本位强。村庄与农户的社会联结较弱。 第四,北方村庄集中居住,行政村与自然村往往合为一体,对外有较清晰的边界,对内有较强的内聚力。正如鲁西奇所指出:“集聚村落的居民之间的交流相对频繁,关系相对紧密,从而可能形成相对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在集村地区,地域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单位是“村”(32)。而南方村庄顺应自然地形,居住分散,行政村与自然村二分分立,对外的边界模糊,内部的内聚力较弱。正如金其铭所指出:“这种散村,就是一个行政村的房屋沿着路或河,按一定走向三三两两散布展开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它们的住宅彼此互不连接,与其说它是一个村,不如说它是分散住宅的组合。这些住宅既保持一定距离又不过远,以致从外表上看来,很难确定某一户的住宅是属于哪一个村的。”(33)而鲁西奇也认为:“分散居住的区域,各农户之间的来往、交流与互相依靠均相对少一些,彼此之间相对疏远,其社会联结方式与社会组织结构则要复杂得多;官府控制散居村落的难度较大”;因此,“在散村地区,由于村落规模太小,‘村’很难成为‘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亦即不可能作为一个地域性社会集团而存在”(34)。 第五,北方集村的集体人格权威强,为了维系组织性和整体性,管理公共事务,村庄集体一般都有一个权威性人格担任领导,如庄主、寨主。而南方散村的差异性大,公共事务不多,缺乏权威性人格。即使有,也不具有庄主、寨主那样的地位。 第六,北方村庄为了维护村庄的同一性,集体可以干预个体,并有惩罚机制。南方村庄则更多依靠村民自我认同的亲情和习俗这一“软实力”形成村落认同。 总体上看,北方村庄具有集体社会的特性,村庄社会成员集中居住,能够集合力量满足共同需要,通过集体人格权威集中权力,集合共同意志处理共同事务,其集体性强;而南方村庄具有个体社会的特性,村庄社会成员分散居住,主要以个体家户的力量满足自我需要,家户间的联系相对松散,缺乏与生俱来的共同需要和集体意志,其个体性强。南北区域集居与散居两种村庄形态,也为以“村集体”为单位的统一经营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户经营提供了村庄基础。 三、集体化与个体化的区域社会机理 中国有句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前面,我们从南北方村庄的名称已经追溯到其生成的根源和基因,即“水土”。那么,南北方的“水土”对于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的行动又有什么影响呢? 前面已经说明,中国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不是凭空而来,而有其内在的根据,即有孕育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的社会土壤。它不仅包括物质条件,也有人的主观意识。在集体化进程之初,主政者已意识到这一现象,并以诸如“倾向”“积极性”等词语加以表达。农业合作化起步之初,中共就敏锐地注意到,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发扬的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二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35)后来,毛泽东分别使用了“半社会主义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积极性”来形容农民的集体积极性。同时,中共文件将包产到户等个体家庭劳动视为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这就意味着,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不仅仅有内在的条件,同时也是内在条件与在此条件下生长出来的人的意识和行动交互的结果。只是这种行为和结果具有鲜明的区域社会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村庄的区域性 无论是农村集体经营,还是家庭经营,都是人在一定村庄内进行的。村庄的特性会塑造人的行为特性,并对经营体制能否持续产生基础性影响。由于南北村庄的差异导致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的发生及其不同结果。 其一,合作意识和集体行动。集体意味着众多社会成员的合作和共同行动。社会成员是否合作并产生集体行动,则取决于其条件。 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和生产资料要求较高。在中国,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农民之间的互助早就存在,甚至与生俱来。这种现象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北方地区表现尤其突出,如“伙种”(36)、“搭套”(37)、“搭工”、“搭种”和“搭庄稼”(38)等。但在土地改革以后,互助合作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环境,这就是过去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虽然获得了土地,却因自然条件恶劣和缺乏生产工具,农业生产和再生产面临困难。 在北方,由于许多地区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只有“组织起来”,通过互助合作才能发展农业生产,所以率先进行土地改革。例如,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在1946年就进行了土地改革。但该村生产条件恶劣,是一个“光山秃岭乱石沟,庄稼十年九不收”的穷山沟。于是,在李顺达的带领下,该村成立了全国最早的互助组和合作社,以集体的力量共同发展生产。再如,在50年代的集体化进程中,河北遵化县有一个名为“穷棒子”的合作社,其生产条件特别差,后来也是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改变面貌。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的按语中说:“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39)又如,山西昔阳县大寨村是太行山区一个山村,自然条件恶劣,号称“七沟八梁一面坡”。该村依靠集体的力量改造自然,创造了著名的“大寨田”。由上可见,正是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共同行动,为后来的集体统一经营提供了基础。 南方的情况则不一样。长期以来,农民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生产活动,虽然有互助,但主要发生于生产过程以外,更多的是生活交往的需要,而且这种交往更多的是一种利益的互换。南方农村也有过生产互助活动,但更多的是“换工”,是一种期待对等回报的互助。例如,“福建省的互助组就部分利用了传统的‘换工’形式”。(40)但是,交换一旦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合伙”很容易“散伙”。而且,农民对“合伙”有一种天然的怀疑和抵触。(41)同时,与北方农村的长年互助不同,南方农村更多的是临时性互助,如农忙时因人手不济的“帮忙”。这也是南方许多村庄只是单家独户聚合而难以持续联合的重要原因。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分得土地,基本可以运用原有的生产工具独立生产和再生产,对于生产互助合作缺乏紧迫性,这也为后来实行分户经营提供了前提。(42) 其二,生产资料的所有性。集体和个体的存在和延续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属性基础上的。集体经营起源于农民的劳动互助合作,并由此发展到生产资料从个体所有转变为劳动农民集体所有,并延伸到集体统一经营。这一进程和结果在南北区域有所不同。 在北方,长期以来由于大量土地为国有,且经常发生战乱,土地变动不居,“田无常主”,将土地私有并固化到家户的意识不强。即使是有土地,单个农户也难以完成全部生产。因此,土地改革以后,随着生产互助和劳动合作的推进,土地实行合作,进而推进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例如,河南省七里营将集体生产组织命名为“人民公社”就有其历史根基,是其生产资料不断集中和生产组织不断扩大的结果。 在南方,村庄成员中的自耕农占有很大比例,土地个体家户所有制的历史长,个体家户希望通过购置田产发家致富的意识强,而集体化恰恰会妨碍个体产权及其梦想的实现。集体化进程在南方造成“生产力暴动”的原因就是农民认为“生产力”在集体化后将不再属于自己。尽管后来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但村民对集体缺乏认同,甚至以各种方式抵制集体,也使得集体经营缺乏所有权的支撑。 其三,生产经营和劳动的统一性。集体与个体既有所有权的意义,更有生产经营和劳动的意义。集体化除了将生产资料归属集体所有外,在生产经营和劳动方式上也实行集体制,而在这方面,南北方区域的进程及结果差别最为突出。 集体劳动意味着一定数量,特别是不同家庭的人共同劳动。这种共同劳动对劳动的整体性和集体管理成本要求高。在北方村庄,人们长期面对共同的生产条件,集居方式造成人们相互间的紧密联系,活动的整体性强。特别是历史上的兵营式和行政村底色,造就了人们的共同活动习惯,由个体家户劳动过渡到集体统一共同劳动是一个自然过程。与此同时,北方大多为旱地,且一年至多两熟,生产环节相对简单,集体劳动统一管理也较为容易。 在南方村庄,家户习惯于个体劳动,而不习惯于集体共同劳动,且认为集体劳动会限制个体劳动的自由,因此缺乏积极性。作为个体家庭经营形式的包产到户之所以多次起落,就在于集体劳动中的出工不出力。而家庭承包经营和劳动的最大好处是村民获得了自由。与此同时,南方大多为小块水田,且为两熟,甚至三熟,农业生产时间长,环节多且细,集体劳动管理困难。作为集体化进程中个体劳动先声的浙江省温州永嘉,最初并不是包产到户,而是学习苏联集体农庄的管理方法。只是这一管理方法也不适宜于精细化、复杂化的水田生产。而包产到户的家庭经营则无须解决复杂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问题。(43) 其四,收益分配的均等性。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作为不同的生产经营单位,必然带来不同的收益结果。中共在土地改革后迅速启动集体化和阻止包产到户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担心收益分配出现差距,甚至发生两极分化。但是,这一意图在南北区域的反映有所不同。 北方村庄作为一种集体社会,社会分化程度不高,其整体性和同一性强。如果出现差异及其私心,集体社会就会瓦解,个体也失去生存发展的根基。因此,在北方村庄,财富收益的平均分配比较容易接受。大寨之所以成为人民公社的样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著名的工分分配制——“大寨分”。其依据主要是集体觉悟,是为集体作的贡献而不是个人的回报。依靠工业富裕起来的村庄,也倾向于普遍的福利分配,如河南刘庄长期沿袭村庄集体统一建房的分配方式,河南南街村甚至主要实行实物的平均分配。 南方村庄是个体社会。个体家户自我生产、自我分配。不同家户之间有差异性,有一定的社会分化,甚至天然地产生分化分裂的因子。这恰恰是家户小农经济的生产经营动力和农业生产持续进行的条件。进入集体经济时代后,平均分配使村民的劳动缺乏自我经济预期,因此出现集体性“偷懒”这一被人称为“反行为”的行为。 其五,权威与认同。任何组织的生成和持续运行,都需要相应的权威及其认同。组织规模愈大,对权威与认同的要求愈高。 在北方集村,整体性同一性强,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强,在相当程度取决于有一个集体人格权威。为了满足共同需要,实现共同发展,集体中会产生能够体现集体意志的人格权威。同时,集体成员也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与期望托付给这一集体人格权威,从而形成对集体人格权威的自我认同。换言之,村庄集体人格权威就是全村人的“大家长”,或者“庄主”“寨主”。北方集体化的村庄典型,几乎都有一个权威能量特别大,甚至说一不二的“大家长”(班长),并能够通过多种方式造成集体成员的服从。 如果说北方村庄是村集体为基础,造就的是村集体的“大家长制”,那么,南方村庄长期历史上实行一家一户为单位,造就的是家户“小家长制”。这种“小家长制”难以造就村庄集体人格权威,即使有社队干部,也容易因为小家意识而缺乏集体人格权威那种道德感和感召力,自然也缺乏集体成员的高度认同和自觉服从。 其六,体制与机制。组织的持续运行需要相应的体制与机制加以保障。家庭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原生组织,并长期形成一套人们习以为常的制度。集体统一经营组织是次生形态的组织,具有建构性,更需要相应的体制与机制加以维系。 在中国,经历集体化产生的集体统一经营组织具有“政社合一”的特点,并实行军事化管理,行政力量的他组织性强。这一体制对于长期以来实行“行政村与自然村合一”的北方农村来说,比较容易接受。例如,河南刘庄从集体化时期一直到如今仍然实行以村庄(人民公社为生产大队)为单位的集体统一经营,从未发生变化,就与其历史制度底色相关。而对于南方散村来说,行政村与自然村相对分离,且以自然村为基础,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就比较困难。60年代初,在经历了以大队,甚至以公社为生产经营核算单位的体制以后,人民公社体制作出重大调整,后来确定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毛泽东还特别指出:生产队是指生产小队,而不是生产大队。(44)这背后的原因实际上就是考虑到村社体制的有限性,将生产经营单位下沉到生产小队(南方表现为自然村),使其离家庭经营更近一些。 (二)地方领导的区域性 中国的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体制都有一个由点到面的扩展过程。其路径是先有少数村庄典型,再扩展到地方,再由地方扩展到全国。村庄是基础,而要让村庄典型成为地方样板,且在地方推广,则与地方领导的行为相关。 中国长久以来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地方官员主要是中央决策的执行者。但即使如此,地方领导在执行中央决定时,也有相当的自主空间。这首先在于国家规模大,中央决策不可能特别详尽,更多情况下表现为原则和精神,地方在将中央原则、精神转换为领导行为时,就出现一定的自主空间。其次在于,中央决策本身也会存在差异,甚至不断变化,由此为地方领导决策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地方领导是一方的主政者。一方水土不仅养育了一方民众,也会影响到一方领导。地方领导要有效地治理地方,必须“接地气”,从地方实际出发,由此也为领导行为提供了行动空间。由于区域社会差异,在南北方的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进程中,不仅村庄特性提供了不同的微观基础,地方领导也会有不同选择。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央机构所在地的政治影响力较大。特别是在交通信息不发达的时代,国家的统治影响力具有很大的区域差异性。愈是距离中央近的地方,受中央决策的影响愈强。换言之,在靠近中央的地方,领导的政治敏锐度愈高。中共取得政权的路径是由地方到中央,在还未获得全国性政权前就在一部分地区先获得政权,并推行自己的主张。这部分地区被称为“老区”。老区地方领导接受中央精神快,对中央精神跟得紧。而老区主要分布在北方区域,如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与此同时,正是这些地方的村庄集体社会底色特别深厚,并自生出集体互助合作的因素和雏形,遂被称为“社会主义积极性”。因此,当集体化启动时,一些更“接地气”的基层干部率先挖掘集体互助合作的村庄经验,并加以概括。这些个别经验又很快得到地方领导的高度重视,将其宣传扩展成为地方实践,集体化由此从点向面扩展。互助组和合作社率先在山西由点向面扩展,人民公社率先在河南、河北由点向面扩展,都与地方领导扮演的积极角色相关。事实上,早在集体化初期,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山西等地就出现了互助难以为继的现象。山西省委在向上级提交的《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中,就表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必须在互助组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自发势力,积极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形势。”(45)而为了加强互助合作组织,巩固集体统一经营,一些地方的干部甚至采取“强迫命令”(46)。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中央数度批评地方的“急躁盲目”和“强迫命令”倾向,这些倾向就主要发生在北方,特别是老区(47)。 与之相比,南方距离北方的首都较远,有的地方甚至长期是“皇权”鞭长莫及之处,中央决策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地方领导的政治敏锐度也相对较低,受当地社会的民情影响更大。与此同时,相对于北方的“老区”而言,南方属于后解放的“新区”。主政新区的大量地方领导是从老区输入的,但他们进入新区后,也不得不考虑新区的特点。丁龙嘉指出:南下干部“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江北地区来到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地区”,“如何面对新的情况以及如何运用老解放区的经验,对于这个群体的每一位成员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48)。土地改革时,中央批评广东的“地方主义”问题(49),而当时的主政者主要出自本省,后来则委派来自北方的领导主政。但即使如此,南方地方领导在贯彻中央决策的精神时,还是得依据当地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因此往往会在中央精神与地方实际之间发生摇摆。例如,新主政广东的陶铸就在《新区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和保证质量问题》一文中谈到:当地干部“对于依靠小农经济吃饭还很有‘兴趣’”(50)。特别是更为“接地气”的基层干部对地方性因素考虑得更多。集体化在南方困难重重,而家庭经营不断在南方冒出,便与此相关。在合作化推行之初,浙江发生了毛泽东所称的“生产力暴动”。随后,永嘉县的基层干部开始探索集体统一经营中的责任制,不仅得到县委领导的支持,得以在全县扩展,而且得到省委领导的认可,直到中央高层叫停。当时,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就专门发表《“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一文,提出:“农民在个体经营时期所表现的这种‘主动性’‘细致性’也应该视为中国农民的宝贵遗产和中国农业生产的优点”,“应该把它保存下来”,为社会主义服务(51)。因此,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经营从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70年代后期,并由点向面扩展,主要发生于南方,并与地方领导的推动相关。由此,才有了所谓“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说法。 (三)国家决策的区域性 中国的集体化与个体化实践是自下而上,先产生村庄典型,再扩展到地方,最后推广到全国。与此同时,也有一个先有中央精神,再传达到地方,最后推广到全国的双向互动过程。在向全国扩展的过程中,国家决策的区域性也制约着中央的决策。首先,中央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时,除了自我构想外,还会寻找和依据地方经验。地方的典型和经验,也就会对中央领导人的决策产生影响。中国有最高统治者到地方视察的习惯,特别是从北方首都到距离较远的南方视察。这种视察会产生两方面效应:一是对视察地方的政治影响,二是对决策者视察地方后的决策影响。其次,中央决策者作出决策时,也会受到其个人理念、经历和经验的影响,并有可能产生决策思路的差异。 中国集体经营由北向南扩展,家庭经营由南向北扩展,除了与村庄特性、地方领导有关外,还与国家决策者的区域差异相关。早在陕甘宁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地方经验,提出:“如果全体人民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劳动之中,那末现有全陕甘宁区的生产力就可提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这办法可以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52)。在集体化启动初期,各地上报了大量报告,后来编辑成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亲自为此书撰写序言,并写了104篇按语。当时,北方的集体合作走在全国前列,而上报和选取的典型材料也主要出自北方。随着集体化的推进,合作社扩大为人民公社。而在当时,毛泽东只有扩大农民集体合作的思路。究竟这一组织样式是什么,并以什么名字命名,他并不确定。为此,他开始沿首都附近的河北向南视察,并在河南新乡七里营和河北徐水发现了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遂加以定名,扩展到全国。罗平汉认为:“各种材料表明,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与毛泽东的推动是密切相关的。”而这背后的原因,又与1958年8月他对河北、河南、山东三地的实地考察相关。(53)毛泽东自己也表示:“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54)到60年代,毛泽东又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大寨坚持集体统一经营。 在是否实行集体化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执政高层没有分歧。但在实行集体化的进程、形式方面,执政高层却有差异。这与决策者的区域差异相关。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来自于南方。但是,与毛泽东相比,刘少奇长期工作在南方,有自己的思考。由此,决策者中也就形成了由互助合作走向集体经营的两种不同的思路。(55)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给中共中央、华北局送交了题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刘少奇担心集体化进程过快过急,对此提出批评。他说:“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56)而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立即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表示:“不能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1953年,中央为推动农村集体化工作,专门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由邓子恢担任部长。邓子恢为南方福建人,且长期在南方工作,对南方情况比较了解。他作为“农民化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农村的特点有较深的认识,认为:集体化必须从“中国小农经济现状出发”;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的个体生产,是中国农村生产的主要形式;这在于,“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家庭小群体,团结一致,利害与共,能够自觉地全心全意地对生产负责,以适应农业生产复杂、多变的情况,经过它们长期的努力,已经创造出一套优良的传统耕作方法和管理经验。由此使它们虽然经历了千百年的曲折,仍保留了它的生命力,使其成为整个农村经济肌体组成的细胞。即使农业合作社实现了土地公有化,家庭经营这个生产细胞和它的自我责任意识,不能废掉,要加以保护”。(57)在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后,邓子恢对推进集体化较为审慎,结果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60年代初,邓子恢又支持包产到户,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高层领导的支持,但最后仍被否定。与此类似,70年代安徽和四川率先推行包产到户,也引起较大争议,只是得到邓小平等高层领导的支持才得以扩展到全国。 四、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结果的区域差异及政策启示 农村集体经营与个体家庭经营是20世纪后半叶发生在中国的两件大事,并引起社会的深刻变革。同时,这一过程也付出沉重的代价。本文从区域社会的角度研究集体经营与个体家庭经营的发生、发展与结果,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总结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探讨在一个区域差异大的超大国家,如何寻找基层地方多样性与国家整体一致性之间的合理张力,及其相应的农村政策选择。 中国实行了数千年的个体经济。通过集体互助合作的方式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则是中共的追求。就这一基本问题看,上下分歧都不大。即使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生产力暴动”,但也仅仅发生在南方少数地区。但是,集体经济毕竟是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经济形态,集体化的进程及其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因此会有所不同。其重要原因就是各地的实际条件不一样,其中包括南北的条件差异。但是,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对集体经济的认识较为简单,除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以外,生产经营和劳动分配也都要求集体统一,而且将是否统一经营提升到是否是集体经济属性的高度,出现了所谓的“一刀切”。 应该看到,正是由于存在地方性差异,作为国家整体有追求统一的天然要求,“大一统”在中国与多样化一样历史悠久。特别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和交通信息的发达,现代国家获得同一性整体性的条件更加充分,更容易造成某种国家意志的傲慢——国家决策忽视地方的差异性,由此支付巨大的进步代价。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制度建设过程,其国家基本制度必须遵循统一性、一体性,这是支撑现代国家的制度支柱。与此同时,国家制度又要为地方发展保留下足够的自主空间,其基本依据就是各地条件不一样。为此,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既要重视地方和个案经验,从中寻找决策依据;同时也要充分注意其限度,此地的经验不一定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毕竟中国的地方差异性太大。1980年,中共中央就“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专门指出:“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生产情况和耕作习惯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不相同。”“某一地区的实践证明确实是先进的、有效的经验,在其他地区推广,就不一定是或不一定完全是先进的、有效的。”(58) 根据这一思路,从区域社会的角度来研究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的发生和发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集体化的目的是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是可以分层次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是基础性层次,生产经营、劳动组织和收入分配单位是派生层次。后者受多种因素所制约和影响,表现出多种形式。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基础上,村集体统一经营与家户个体经营都是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经营,并非历史上个体经济的简单回归,而是在集体所有基础上根据农业生产特点和实际探索的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它将集体所有的优势与个体经营的优势结合起来,创造出人类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 第二,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是一个分阶段的过程。从一般意义看,集体经营比家庭经营需要的条件更高。集体经营是由不同的人组织起来形成的整体,需要集体成员对集体的高度认同,存在着是否愿意加入集体经营的问题。家庭是与生俱来的原生的血缘共同体,不存在人们是否愿意加入家庭经营的问题。因此,集体统一经营的难度更大。 北方村庄集体社会为集体经营提供了历史基础,而集体统一经营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村庄地域共同体。这一地域共同体为其成员提供了平等的家园,能够为他们在恶劣条件下遮风避雨,甚至共同富裕提供条件。其内部拥有的共创共有共享精神更是人作为类的存在的久远向往。但是,也必须看到,北方村庄在集体化进程中形成的村庄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个性独立与自由选择的集体社会,其主要困难是可持续性。在一定历史阶段,集体社会依靠的是集体人格权威形成的凝聚力,而不是高度自主自愿的结合。这使得作为集体统一经营的北方村庄也迅速走向个体家庭经营。 中国的个体家庭经营的基础在于长期历史形成的个体家户制。家户制使集体化进程困难重重,且始终难以形成北方村庄那样的完整的村庄共同体。尽管在国家强力推动下,南方村庄也进入集体化时代,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但并没有形成北方村庄那样的完整共同体,至多是半共同体,或者只是形式共同体。主要原因在于其成员缺乏集体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需要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短期的社会主义教育并不能解决问题。半共同体有家户自由,并能够迅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但原本脆弱的共同体也迅速解体,造成公共性和共同性的缺失。正因如此,人们对集体时代仍有一定的怀念。 第三,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是一个殊途同归和不断提升的过程。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既受历史条件的规制,也是人类的自我选择,其目的都是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邓小平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59)还提出:“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60)北方农村有集体社会的悠久传统,可以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变,在家庭经营基础上运用集体传统资源,探索新的生产经营形式,如山东东平的土地股份合作。而南方村庄则需要克服历史上长期的个体经济所造成的狭隘自私性,从而在个体自主基础上,建立公共性和共同性。 正是经历了数十年的艰苦探索,中国目前已经形成农村基本的经营制度,即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但在实际进程中,为什么和怎么样才能做到“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却还有待继续深入探讨。在实践中往往出现的是:“统得过死、分得过多”,很难因地制宜作出决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地”的属性缺乏深入调查和研究,对整个国情的认识更多的是片断的、零碎的、表层的。这就需要学界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调查和深度研究,以为因地制宜的国家决策提供依据。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1页。 ③赵紫阳于1975至1979年间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万里于1977至1979年间担任安徽省主要领导。他们在任职期间都积极支持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的农村改革。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村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98页。 ⑤《农村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第98页。 ⑥参见《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501页。 ⑦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⑧参见《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459页。 ⑨参见徐勇:《包产到户沉浮录》,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220—240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43页。 (11)参见《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1356—1376页。 (12)《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177页。 (13)毛泽东在1955年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一文所写的“按语”中,明确提到当时党内有人提出“合作化北方可以快一些,南方无法快”。参见《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73页。 (14)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在会上,“包产到户”问题激起了广泛的讨论。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明确不赞成包产到户。而支持包产到户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则表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5)傅衣凌:《集前题记》,《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页。 (16)李玉:《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综述》,《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17)参见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18)[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4页。 (19)“集体”本来是与“个人”相对的概念,指多人构成的有组织的整体。集体的组织规模和范围有大有小。在农村社会,集体具有特定的涵义,是以村庄为单位由若干家户构成的组织整体。因此,村庄对于集体组织,村庄性质对于集体组织的生成与延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20)转引自[英]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编,谢礼圣、吕增奎等译:《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5页。 (21)鲁西奇:《散村与集村: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22)鲁西奇:《散村与集村: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23)鲁西奇:《散村与集村: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24)本来,华南也属于南方区域,但与大多数南方区域不同,华南一些地方存在着大量宗族型村庄。中国一些学者就此研究,并形成所谓“华南学派”。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为了深度发现中国农村社会的起源和特性,于2015年启动区域性村庄调查,第一步就是华南的宗族型村庄调查。 (25)金其铭:《中国农村聚落地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第183页。 (26)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12页。 (27)鲁西奇:《散村与集村: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28)参见宋传银:《秦至清代湖北人口迁移特征析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9)鲁西奇:《散村与集村: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30)[法]阿·德芒戎著,葛以德译:《人文地理学问题》,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92页。 (31)[法]阿·德芒戎著,葛以德译:《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46、169页。 (32)鲁西奇:《散村与集村: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33)金其铭:《中国农村聚落地理》,第183页。 (34)鲁西奇:《散村与集村: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35)参见杜润生:《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第25页。 (36)“伙种”指若干人合伙耕种土地,主要分布于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安徽北部等地。参见郭松义:《清代农村“伙种”关系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37)“搭套”指华北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共同使用役畜的互助合作形式。 (38)“搭工”“搭种”和“搭庄稼”指若干家有亲戚关系的农户,将人力、畜力及农具进行合作,以完成农业生产。参见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1—12页。 (39)《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71页。 (40)王士花:《论建国初期的农村互助组》,《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41)参见王士花:《论建国初期的农村互助组》,《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42)参见刘金海:《互助:中国农民合作的类型及历史传统》,《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43)参见徐勇:《包产到户沉浮录》,第30—32页。 (44)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4页。 (45)《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43页。 (46)《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35页。 (47)《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89、201页。 (48)丁龙嘉:《论“南下”与“南下干部”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及当代价值》,《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期。 (49)新中国成立之初,广东省由熟悉省情、力主因地制宜治理的本地领导主政。后因推行所谓的“温和土改”,被中央批评为“地方主义”,并对主要领导干部作了调整。 (50)《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308页。 (51)《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460页。 (52)《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5页。 (53)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54)转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9—140页。 (55)参见赵德馨:《两种思路的碰撞与历史的沉思——1950-1952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目标模式的选择》,《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56)《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42页。 (57)转引自徐勇:《包产到户沉浮录》,第8—11页。 (58)《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884页。 (5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 (6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