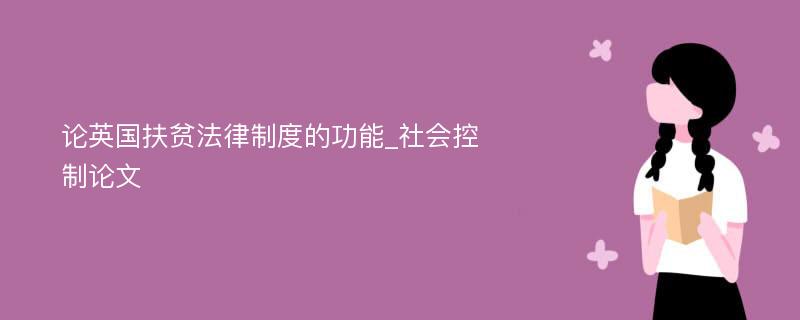
试论英国济贫法制度的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试论论文,法制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济贫法制度的社会功能
济贫法制度具有社会救济功能,这也是英国济贫法制度最基本的功能。16世纪英国济贫法制度颁布和实施的基本原因是为了给老弱病残者等所谓的“值得救济者”提供必要的生活救济,对流民等所谓的“不值得救济者”予以惩罚并强制其进行劳动,①早期济贫法制度虽然惩罚性功能强于救济性功能,但是毕竟为值得救济者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救济。17世纪英国济贫法制度的救济对象虽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是对于劳动救济的强调以及劳动救济机构的出现,在客观上也为所谓不值得救济者提供了必要的救济来源。值得指出的是,16、17世纪的济贫法制度除了提供现金救济以外,还提供相关的实物救济,主要包括食物、衣物、住所等,此后一些地方的济贫法管理机构甚至还向身患疾病的人提供少量的药物救济。②18世纪,英国济贫法制度不仅在救济方式方面不断改善,而且对一些特殊人群如儿童、麻风病人、精神病人等提供专项救助,乃至对以前所谓的不值得救济者如失业者及其家人提供必要的救济,③斯宾汉姆制度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过度救济制度而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强烈批评。
1834年新济贫法颁布实施以后,英国名义上实行严格的院内救济原则,济贫院也曾被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但到19世纪中期以后,济贫法制度经过不断改革,其社会救济功能逐渐完善。如改变混合济贫院的传统,把院内贫民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实行区别对待;改善济贫院的环境,增加济贫医院的床位,建造新的条件较好的济贫院,改善济贫院的伙食等;对济贫院中的违反规定者的惩罚也逐渐减轻;逐步放宽临时性救济条件并扩大临时救济人群。④尤其重要的是,新济贫法虽然规定严格的院内救济原则,但在整个19世纪后期,济贫院外的救济不仅事实存在,而且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1840-1890年,英国接受济贫院外救济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始终高于接受济贫院内救济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⑤而济贫院外救济无疑是一种较之济贫院内救济更为合理的一种救济形式。正是由于19世纪后期经过改进以后的济贫法制度不断完善其救济功能,并逐步走向合理化,才使其能够在社会保险制度出现以后作为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补充而长期存在。
济贫法制度具有惩罚的功能。英国济贫法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惩罚与救济相结合,这也是济贫法制度实现其社会控制功能的主要措施之一。这种惩罚功能不仅表现在新济贫法制度之中,而且也是旧济贫法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英国早期济贫法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惩罚与救济相结合,其对所谓值得救济者提供救济但数量极为有限,而对于不值得救济者如流民等则实施强制性劳动作为惩罚,甚至直接施以严酷的惩罚。17世纪的济贫法制度虽然有所改进,但其惩罚性依然严重存在,不值得救济者必须接受强制性劳动救济,值得救济者所得到的救济极为有限,定居法严格约束贫民的流动,对流民的惩罚性法律虽然有所改进但其惩罚依然十分严格。直到18世纪末期,这种惩罚性才开始有所改变,救济性功能逐步提升,斯宾汉姆制度便是这种变化的集中体现。但是,旧济贫法制度惩罚性功能的下降与救济性功能的上升,立即引起英国自由主义者的强烈批评,并导致1834年新济贫法的颁布实施。
新济贫法制度的惩罚性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1855年,舍费尔德济贫法监督局主席对济贫院的功能做出如下评论:“济贫院所要培养起来的是这样一种传统,接受救济者的目标就是防止自己成为济贫院的长期居住者……贫民十分自然地得出结论,他在济贫院中所得到的救济只是对其失去自由的不充分的补偿,包括全日制劳动、他的劳动价值、他所必须忍受的耻辱以及他已经全部丧失的自我和自尊的痛苦体验等。谁还会怀疑最诚实的贫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使自己身居济贫院之外呢。”⑥1867年,利物浦慈善家拉斯博也评论道:“济贫院确实成功地阻止了贫民向教区申请支持……但是,作为公共慈善制度,它是失败的。它在应对社区公平的复杂要求、对懒惰者更加严厉、对那些陷于贫困者的怜悯及同情方面,都超过了英国议会所能及的范围。诚实的贫民中有着难以忍受的匮乏,社会存在着难以名状的饥饿、肮脏及痛苦,孩子缺乏食物,母亲双眼疲惫身体虚弱,毫无用处地在寻觅生存所需,但是,济贫法当局对这种挣扎毫无记述。”⑦19世纪中期的法国批评家H·泰恩参观了曼彻斯特一个模范济贫院之后指出:“济贫院被看成是监狱,穷人把是否进入济贫院看成是自己名誉的转折点。或许应当承认,这种管理制度是愚蠢的专制,令人担忧。这是每一项管理制度的缺陷,每一个人在这里成了机器,仿佛他们没有情感,总是无意识地受到侮辱。”⑧
英国济贫法制度尤其是新济贫法制度的惩罚性功能是由该制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济贫法制度下的救济基本上仍然是一种责任与权利不协调的制度,大部分救济的领取者几乎不履行任何个人责任,加之英国社会经济尚未发展到可以为大部分贫困群体提供有效的社会救济,政治民主化也没有发展到全体公民都能够享受普遍的社会保障权益。因此,为了避免贫困人群对济贫法制度下的救济产生依赖,也为了给英国工业社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济贫法制度必然实行极端严格的管理和极为低劣的条件,这使得济贫法制度尤其是新济贫法制度的惩罚性功能始终存在,并在19世纪中期达到顶峰。
济贫法制度还具有社会控制功能。中世纪晚期,英国济贫法制度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实现社会控制,应对各类贫民尤其是流民成为包括济贫法制度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政策措施的首要目标,对值得救济者所提供的生活救济、对不值得救济者提供的劳动救济、对流民的严厉惩罚、严格实施的定居法、针对儿童的学徒规定等,无不凸显着通过直接的、外在的、强制性的社会控制实现社会政治稳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初期定居法的放宽和吉尔伯特法的实施。早期济贫法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基斯·怀特森指出:17世纪“济贫法制度所体现的救济与控制的混合,在社会分化与社区聚合的平衡中,提供了一种对分化与差别行为的强有力的弥补。”⑨阿彻指出:“16世纪晚期济贫法制度的实施,旨在强调比较贫困的教区成员要依靠教区中的富人,这些富人因此也有更多机会去缓和贫民的行为,济贫法制度逐渐被用作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⑩博尔顿指出:“济贫法制度下的救济成为控制或者约束贫民的那些办法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济贫法制度变成了复辟王朝以后英国社会结构的整合工具。”(11)里姆林格也指出:“政府对贫民救济的关注从本质上不是出于救济不幸者的目的,而是为了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与贫民救济相关的立法起源于对流民的惩罚并将这种救济制度的特点保持至今。”(12)
新济贫法制度同样具有社会控制功能,但这种社会控制较之旧济贫法制度发生一定的变化。新济贫法制度通过废除旧济贫法制度对流民的惩罚,从而改变了社会控制的方式和性质;通过取消值得救济者与不值得救济者的划分,院内救济与次等权力原则对接受救济者做出限制,院内救济原则与院外救济的事实存在,生活救济与强制劳动等,使得新济贫法制度下的社会控制具有外部控制与内在控制、强制性控制与非强制性控制相结合的特征,从而改进和提升了济贫法制度的社会控制效果。新济贫法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在当时已经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关注,他指出:“在国家的这个措施中,英国资产阶级是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当权者出现的,在这里他们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真正愿望,表明了他们那种使无产者处处遭殃但又把这归之于个别人的罪过的恶劣行为的真正含义。这个措施不是出自于资产阶级某一集团之手,而是得到了整个阶级的赞许的。……这样就宣布了无产阶级是不受国家和社会保护的;这样就公开地宣布了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们当人看待。”(13)这种社会控制功能还得到当代学者的认同,著名学者弗雷泽就曾指出,新济贫法制度具有三种社会控制功能,即它被用做强化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权威的一种工具,它被用来操纵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工资标准,它还被用做将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强加于工人阶级身上的一种工具。(14)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济贫法制度的作用和地位开始明显下降,其在英国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社会控制功能不仅明显减弱,而且随着享受社会保障逐步成为一种公认的公民权利,作为社会保险制度必要补充的济贫法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的强制性明显减弱,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减轻社会问题压力,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进而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成为英国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济贫法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也便逐渐表现出内在控制的基本特征。
英国济贫法制度的经济功能
济贫法制度除了具有上述社会功能以外,还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旧济贫法制度具有稳定就业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功能。14世纪的黑死病使得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家园成为流动人口,16世纪开始的圈地运动更使大量人口离开土地成为流民。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前,英国经济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依靠大量劳动力从事生产劳动,显然,大量人口的流动必然影响英国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于是,如何为农业经济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便成为包括济贫法制度在内的早期英国社会政策的主要目标,旧济贫法制度的重要经济功能之一,便是保证足够数量的从事农业经济的劳动力。因此,旧济贫法制度的各种相关内容无不与此目标直接相关,早期的劳工条例、对流民的惩罚条例和延续几个世纪的定居法都是如此,而对劳动救济措施的关注和强调同样是如此,旧济贫法制度正是适应英国农业经济并维护其稳定发展的一种社会政策工具。
索拉尔在论及工业化以前英国济贫法制度的经济功能时指出:“英国的旧济贫法制度要优于欧洲大陆的贫民救济,不仅是因为英国的旧济贫法制度建立在依靠税收作为财政、覆盖全国及其救济的综合化的基础上,旧济贫法制度还对英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5)哈蒙德夫妇也指出:“18世纪的济贫法既是一种救济制度,也是一种就业制度。”(16)里姆林格更指出,旧济贫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将所有无以为生者和没有经常性或间断性工作以维持生计者置于工作之上。为了实现就业的目标,旧济贫法制度管理当局有四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它们可以依靠公共赞助或者与私人实业签订协约为穷人创造就业机会;(2)它们可以通过限制行乞或者使救济很难得到以迫使穷人为自己寻找工作;(3)它们可以为贫民儿童寻找就业机会以便使其能为家庭收入提供补充;(4)它们还可以通过提供工资补贴以促进贫民就业。上述四种办法在整个17-18世纪都曾被广泛采用,而第一种办法在18世纪初更为流行,第四种办法则流行于18世纪末。(17)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并逐步进入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农业社会需要大量劳动者固着在土地上,而工业社会则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于是,工业社会的发展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便与旧济贫法制度下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与束缚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工业革命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太普遍,太强大,以致不能用个人手段予以阻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愈益不耐烦地感到那些障碍还在对抗它的进展,”旧济贫法制度尤其是定居法成为严重阻碍英国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自由劳动力形成的主要因素。早在1753年,罗格·诺斯就已指出:“定居法使得贫民被囚禁于他们所在的城市并深陷于贫困之中,他们被剥夺了通过移居到更适合他们的地方以改变其生活条件的办法。”“人们需要工作,工作也需要人,工作与人之间的协调关系被定居法所割裂。”(18)威廉·皮特也指出:定居法“阻碍了工人到他可以根据最有利的条件出卖劳动力的市场上去,同时也阻碍了资本家雇佣那些能为他所投的资本带来更高报酬的能干的人们。”(19)
旧济贫法制度所具有的经济功能与工业化的发展所期望的济贫法制度经济功能的变革之间的矛盾变得越发明显,济贫法制度经济功能的改变意味着它的本质必然发生变化。于是,新济贫法制度的经济功能便从旧济贫法制度所具有的保证农业劳动力规模以促进农业经济稳定为主,变为提供大量自由流动的劳动力以适应工业经济的发展为主,并发展成为适应和促进工业经济发展的社会政策工具。
19世纪中后期,英国新济贫法制度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为英国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自由劳动力仍然是新济贫法制度的重要经济功能之一。院内救济与次等权力原则等使得大部分贫民难以将进入济贫院作为自己的首要选择,而是把依靠自己工作维持生活作为主要选择。芬纳在论及新济贫法中的次等权力原则对英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时指出,次等权力原则的重要性在于,它从理论上具有了将对身体健全的工人的救济与自由劳动力市场、工人阶级的勤劳、远见与独立意识等的发展衔接起来的可能性。(20)里姆林格也认为,次等权力原则是一种新的劳动力政策措施,如果得以充分实施,将使得救济不仅“安全”而且“持续有效”,反映了新的市场文明的商业价值观念。(21)
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新济贫法制度的另一经济功能。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但却导致社会问题的社会化,工人阶级生活的贫困化,劳资关系的对抗化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极端化,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势必影响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如何有效缓解社会问题,减轻贫困化程度,化解社会矛盾,不仅成为英国社会政治的需要,也成为英国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新济贫法制度虽然实行严格的院内救济与次等权力原则,但其从救穷改变为济贫却扩大了接受救济者的人数,院外救济的事实存在也发挥了一定的救济作用,从而比较有效地缓解了英国的社会矛盾,保证了英国工业革命的顺利进行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芒图在论及新济贫法制度对英国工业革命顺利进行的影响指出:“在欧洲革命和战争期间继续开展着的那一伟大的经济运动,多亏新的恤贫法才把若干使其进展延迟的障碍搬开了。在某些地区中,教区发给救济金使得反机械化几乎完全消失了,因为救济金部分地补偿了工业前此所提供的家庭劳动的工资的损失,而且比工资又有不费任何努力的好处,人们看到乡下纺纱女人自己粉碎了自己的纺车。”(22)
英国济贫法制度的政治功能
济贫法制度不仅具有社会与经济功能,还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济贫法制度确立了英国民族国家及政府的合法性。宗教改革以前,英国如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基本上是一个神权社会,教会不仅拥有极大的宗教权力,更拥有广泛的世俗权力,同时也拥有很大的经济权力。神权政治的合法性不仅依靠宗教的精神控制,也依靠教会地产与什一税等经济力量,更与其所实施的广泛社会救济密不可分。可以说,正是由于宗教慈善救济所体现出的社会责任,才使得英国社会对神权国家表示认同,亦使得神权国家的合法性得以确立。维尔纳·格兹曾就教会的救济功能明确指出:“在那个‘国家’还没有社会政策的时代,除了对灵魂的关怀和教育,修道士的第三个任务就是社会救济。”(23)
宗教改革在英国开始了一场神权国家向民族国家、神权政治向世俗政权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最终通过17世纪革命的形式加以完成。但是,权力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与政府合法性的确立,权力转移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重大转型过程,重大社会转型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权力转移的合法性必须通过责任承载的现实性加以实现。英国民族国家及政府权力的建立通过宗教改革与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实现,但英国民族国家及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必须通过建立相关社会政策,承担原来由神权国家与宗教组织所履行的社会责任方能确立。因此,中世纪晚期英国济贫法制度的出现,不仅是英国社会转型的需要和近代社会政策的起源,也是实现英国民族国家及政府权力合法性的需要。于是,从宗教改革开始,英国对贫民的救济逐渐从依靠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教会救济,转变为依靠建立在民族国家责任理念基础上的政府救济政策。正如斯莱克所指出的那样,宗教改革与解散修道院“意味着16世纪英国的济贫改革,不像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样只是对现存规定的重组或增补,它需要世俗政府和单个捐助者的介入去取代教士的职责,因此,它看起来好像就是从头重建一个社会福利体系。”(24)斯莱克进一步指出:“1500年以前,对贫民的救济与帮助表现为各种方法的混合,如宗教性机构——修道院、兄弟会以及基尔特、城镇的劳动介绍所、济贫院以及教堂捐助等,除了有关要求劳动、惩罚乞丐和流民的法令外,国家对济贫几乎没有参与和行动。然而,从1530年以后,政府干预、中央化以及统一化的趋势开始出现并不断增强。”(25)
斯莱克的观点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认同。德国经济史学者豪斯赫尔指出,宗教改革与解散修道院“这有损于履行旧教会履行过的救济义务。旧的修道院居住者们凡是不住在自己家里的,多半被人毫无顾忌地抛向街头,变成乞丐。当时,对贫民的救济和教育关注甚少。这就是英国为什么在十六到十七世纪的转折时期制定世俗的济贫法的原因。”(26)里姆林格也指出:“正在出现的民族国家及政府逐渐认识到,它们不得不关注由于大量的贫困个体所导致的问题,事实上,几乎从近代民族国家开始出现之时,贫困便成为国家必须关注的问题。毫无疑问,如何处理劳工贫困的问题,在那些关注国家经济政策的人们的心目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27)
其次,济贫法制度逐步扩大了公民享有社会救济的权力。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中享有救济权力的比例极为有限,最初的贫民法以惩罚为主,毫无公民权利的色彩,随后的济贫法制度表现出一个以惩罚为主逐步走向惩罚为主救济为辅的变化过程,济贫法将贫困群体划分为“值得救济者”与“不值得救济者”两种群体,享有救济权力者仅仅为一小部分所谓的“值得救济者”,且受到家庭收入、个人品行、居住地点等方面的严格限制,“不值得救济者”不可能得到救济,而必须接受相关强制性劳动,否则将受到严厉惩罚。显然,早期英国济贫法制度是一种救穷不救贫性质的社会政策,但对所谓的“值得救济者”提供有限的救济,应该说已是对英国公民享有救济权力的一种认可,这种认可随着英国社会的变化和济贫法制度的变化而逐步发展变化。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公民享有救济权力的扩大成为济贫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涵之一。
1834年新济贫法的主要政治功能是部分扩大了公民享有救济权力的范围。虽然新济贫法制度确立了严格的院内救济原则,实行歧视性的贫民次等权力理念,推行带有侮辱性的以公民权利为代价换取有限救济的做法,但是,从公民享有救济权力的角度来看,新济贫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进步,最为突出的变化是不再将贫民划分为“值得救济者”和“不值得救济者”,“值得救济者”、“不值得救济者”都可以申请救济,实现从救穷向既救穷也救贫的转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济贫院内救济之外,济贫院外救济的事实存在及不断扩大的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院内救济原则对部分贫民的排斥,使得一部分贫民不必进入济贫院而可以在济贫院外获得一定的救济,从而使得更多的英国公民或在济贫院内或在济贫院外获得济贫法制度所提供的相关救济。此后,随着英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及济贫法制度的不断改进,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内容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英国公民享有的救济权力逐步扩大。
再次,济贫法制度固化了地方政府的权力。英国济贫法制度这一政治功能的出现导源于济贫法制度最初出现时的特点,即地方政府率先进行济贫尝试,其后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各种济贫尝试的基础上加以规范或推广。利普森对此明确指出:“从本质上讲,《伊丽莎白济贫法》无非就是将各自治市政府所确立的济贫原则推向全国,该法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所创造的济贫组织系统,而在于它将自治市当局现存的济贫组织系统推广到全国。”(28)可以说,早期济贫法制度的几乎所有方面均以地方政府的探索性实践为主,甚至作为英国社会最基层组织的教区,在早期济贫法制度实施中都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并且始终保持了济贫事务中教区拥有较大自主权的传统。地方济贫尝试在早期济贫法制度出现时的重要影响,直接导致英国济贫法制度管理中地方政府拥有很大自主权的事实,这种自主权随着英国政治社会的变迁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存在一种逐渐强化的趋势。
17世纪中后期,英国济贫法制度管理中地方政府的自主权进一步增强,雷恩对此曾做出如下概括:“英国内战爆发时,各地治安法官与枢密院之间的联系被打断,此后直到19世纪,几乎没有任何中央政府的权威能够指导和保持济贫法制度的统一。法律所赋予治安法官的权力虽依然存在,他们还会指定济贫监督官,还有权确定济贫税,还可以接受济贫监督官和教区委员呈递的报告,也可以要求从比较富裕的教区提取济贫基金以帮助那些贫穷落后的教区从事济贫事务,可以对争议做出裁决,可以处理有关定居法的相关问题,并关注感化院的建立和运行,但是,济贫事务的真正管理落在了济贫监督官的身上,推动相关法律实施的压力来自于地方对贫民救济需要的程度,各地济贫法实施的状况也存在明显的不同。”(29)
进入18世纪,不仅英国济贫法制度管理中地方政府自主权更加明显,甚至在济贫法管理中出现了明显的教区化趋势。斯莱克在总结济贫法制度管理中的教区化时指出:“教区不仅负责这一时期济贫法日常管理的具体工作,而且还对济贫法的宏观原则产生重要影响。除了那些保护济贫税纳税人的个别法令以外,几乎所有成为法律的济贫法案都建立在教区济贫实践的基础之上。……事实上,可以相对准确地说,在征得大多数教区的认可以前,议会几乎不会批准任何有关济贫的法律。”(30)这种地方化甚至教区化趋势的增强,虽有助于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实施救济,但也使得各地济贫法制度极不一致,最终使济贫法制度成为英国社会关注、批评和要求改革的焦点所在。
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济贫法制度管理中的中央化初露端倪并逐渐增强,济贫法修正法提出建立济贫法委员会,建立联合教区济贫院,要求实施严格的院内救济,禁止提供院外救济,1847年甚至在中央政府建立了济贫法局,实现了济贫法制度管理机构的中央化,1871年又通过地方政府事务部法,将济贫法制度管理明确划归地方政府事务部等,所有这些无不表现出强化济贫法管理制度中的中央化迹象。20世纪初的一些学者甚至指出:“济贫法制度的管理是统一的……贫民不可能在一个教区救济过度而在另一个教区挨饿而死,每一项法律及行政规定在联合王国的每一个地方都会不折不扣的推行……地方的济贫法管理当局及其官员是如此严格地执行济贫法相关规定,以至于几乎每一项法令都好像是在地方政府事务部的统一指令下实施的,除了执行包含在地方政府事务部各种一般或特殊规定中的指示外,济贫监督官几乎毫无他事可行。”(31)
然而,19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济贫法管理中央化的程度极为有限,济贫法委员会虽然建立但并非中央政府的济贫法管理行政机构,联合教区济贫院虽然建立但进程缓慢且许多地方并未建立此类联合教区济贫院,院内救济虽为新济贫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但并未严格实施,院外救济虽被禁止提供但却事实存在并不断扩大,济贫法局虽然建立但并未根本上颠覆地方政府管理济贫法事务的自主权,济贫法制度管理虽明确划归地方政府事务部但并未改变地方政府管理济贫法制度的基本政治格局。“济贫法制度的统一化与中央化较之现实性来说更具想象性”。(32)因此,济贫法制度管理中央化趋势的出现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地方化的传统,济贫法制度管理权仍然是英国地方政府的一种具有较大自主性的传统权力,这种地方化传统如此根深蒂固和举足轻重,以至于20世纪初的自由党政府虽深知济贫法制度的弊端却没予以废除,而是选择对其施以改进的基础上任其继续存在。
总之,济贫法制度既与英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迁直接联系,更对英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变化产生重要影响,英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决定了济贫法制度性质与功能的变化,济贫法制度性质与功能的变化反过来影响英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使得济贫法制度在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内容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以前,成为适应英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变化的核心社会政策,不仅对英国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现代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斯莱克关于旧济贫法制度与英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述,即可窥见整个济贫法制度与英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整体发展变化关系的全貌,他指出:“旧济贫法制度与近代早期英国历史中许多极为有趣的议题直接相关,当然,它与经济与社会环境有关,与其所欲应对的贫困与赤贫的存在有关,它还受到社会思潮与观点的影响,不仅因为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其理解常有变化,而且因为它并不倾向于仅关注可资测量的经济需求,还具有广泛的目的和相当广泛的影响。最后,它受到英国政府发挥功能的方式的影响,并强有力地影响英国政府发挥功能的方式。”(33)
注释:
①R.H.Tawney and E.Power,Tudor economic documents,Vol.2,Longman,1924,pp.328-331.
②尹虹:《近代早期英国流民问题及流民政策》,《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③J.Burnett,Planty and Want,a Social History of Diet in England from 1815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1979,p.33.
④丁建定:《从济贫到社会保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50-151页。
⑤K.Williams,From Pauperism to Poverty,London,1981,pp.158-162.
⑥W.J Mommsen,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London,1981,pp.10-11.
⑦D.Fraser,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Macmillan,1985,p.55.
⑧郭家宏:《19世纪英国济贫院制度评析》,《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
⑨K.Wrightsen,English Society 1580-1680,London,1982,pp.181-182.
⑩I.Arche,The Pursuit of Stability,Social Relations in Elizabethan London,Cambridge,1991,pp.96-98.
(11)T.Hitchock,Chronicling Poverty,the Voice and Strategies of the English Poor,1640-1840,Macmillan,1997,p.19.
(12)G.V.Rimlinger,welfare Policy,Industrialization in Europe,America and Russia,New York,1971,p.19.
(13)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76页。
(14)W.J.Mommsen,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London,1981,p.24.
(15)P.M.Solar,Poor Relief and English Economic Development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95,No.1.
(16)J.L.Hammond & B.Hammond.The Village Laborer,Longman,1978,p.98.
(17)G.V.Rimlinger,welfare Policy,Industrialization in Europe,America and Russia,New York,1971,p.19.
(18)E.Lipse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London,1948,pp.463-466.
(19)(22)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2、354-357页。
(20)S.E.Finer,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Edwin Chadwick,London,1952,p.45.
(21)G.V.Rimlinger,welfare Policy,Industrialization in Europe,America and Russia,New York,1971,p.52.
(23)汉斯·维尔纳·格兹:《欧洲中世纪生活》,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79页。
(24)P.Slack,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Longman,1988,p.13.
(25)P.Slack,The English Poor Law,1531-1782,Cambridge,1995,p.6.
(26)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05页。
(27)G.V.Rimlinger,welfare Policy,Industrialization in Europe,America and Russia,New York,1971,p.13.
(28)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Vol.Ⅲ,London,1984,p.411.
(29)H.E.Raynes,Social Security in Britain,A History,London,1960,p.70.
(30)P.Slack,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Longman,1988,pp.8-9.
(31)W.J.Mommsen,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London,1981,p.20.
(32)W.J.Mommsen,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London,1981,p.21.
(33)P.Slack,The English Poor Law,1531-1782,Cambridge,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