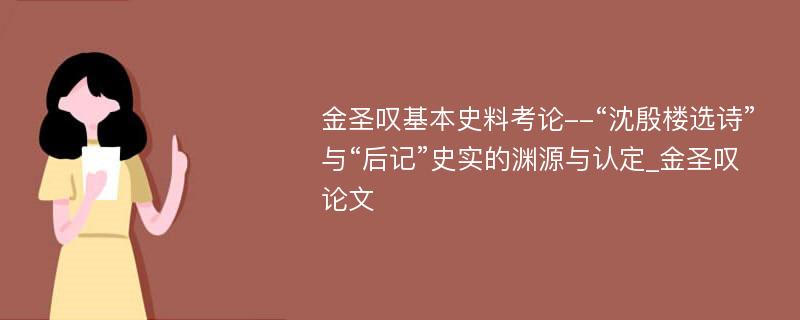
金圣叹基本史实考论——《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史实探源与辨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诗选论文,读后论文,金圣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7)03-068-10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出版清钞本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以下简称《诗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排印问世《金圣叹全集》(以下简称《全集》),这是上个世纪最后20年金圣叹研究勃兴的一个坚实基础。
对近20年金圣叹史实研究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当数《沉吟楼诗选》所附俞鸿筹撰“读后记”(本文所引,均据上海古籍版手稿彩印本自行标校)。在许多研究金圣叹的著述中,不难发现借鉴或沿袭此文的明显痕迹。然而对俞鸿筹所云,应作认真考论。拙文试图对“读后记”所涉史料逐一考论,并兼议《全集》因理解及其它缘故造成的标点问题,希望以此引起对金氏史实研究的进一步关注。为行文方便并求醒目,以下将俞鸿筹“读后记”以引文方式过录,分别进行评说。
《读后记》:《唱经堂著述总目》,见于金昌所刻《第四才子书杜诗解》四卷附页。其中《诗文全集》列入“内书”,据陈登原谓并未刊行。
陆案:据《杜集书录》著录,《唱经堂杜诗解》于金昌《才子书小引》后,原有“《唱经堂外书总目》:《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唐才子书》、《必读才子书》(以上刻过),《杜诗解》四卷、《左传释》、《古诗解》二十首、《释小雅》七首、《孟子解》(嗣刻);《内书总目》十三种子目从略,《唱经堂诗文全集》(嗣刻)”[1](P475)。然与《诗选》钞本所附《唱经堂遗书目录》对勘,不仅《诗文全集》是列入“外书”之中,而且内、外书之具体目录及次序亦颇有出入。此“目录”系研究金氏著述总貌的重要史料,今人整理《杜诗解》及《全集》不知为何未收。
最后一句“据陈登原谓并未刊行”,引出了陈氏其人其说。陈登原(1899—1975),字伯瀛,浙江余姚人,曾任教于西北大学,现代著名史学家,代表作是《国史旧闻》。早在70余年前,他即著有《金圣叹传》。“并未刊行”并非陈氏原话,他只在《唱经堂诗文全集》书名后括注“未刻”二字[2](P58)。陈登原对金氏著述各种版本非常熟悉,超过了今天的许多学者,如所引徐增《才子必读书叙》,《全集》本《天下才子必读书》和1988年安徽文艺出版社版《金圣叹选批才子必读新注》便失收。他对笔记杂著和碑传中有关文献的钩稽,确立了金圣叹传记轶事类资料的基本藩篱;他对许多史实问题的见解,如果不是采用新的史料,今人鲜有超出其右者。在金圣叹史实研究领域内,陈登原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第一人。与其成果相比,孟森(1869—1937)汇抄史料而成的《金圣叹考》只是小巫而已。今人研究金圣叹,就史实问题而言,无论史料还是观点,多采自陈登原《金圣叹传》,尽管一般并不说明。陈登原《金圣叹传》结尾有感于时局之艰危、文坛之不堪,因王斫山赠圣叹诗“一例冥冥谁不朽”之句而慨然兴叹:“人生会当有一死,不必谓或重泰山、或轻鸿毛。居今之世,论今之人,放眼多酸丁,举世无豪杰。有咬文嚼字而自诩正学者;有卖友背朋而斤斤风雅者。呜呼!家国残破,倭寇南来;狐鼠共争,相期共尽。同为无用之学,奚济危亡,正不知何者谓之不朽也?不觉掷笔怃然云。”[2](P77-78)足见作者之感时伤事、正直爱国。如今国运兴旺、民族自强,已非当时所可想象。
《读后记》:此《沉吟楼诗选》一册,录古今体诗三百八十四首,有雍正五年吴江李重华序,云系圣叹之婿沈六书录出,大兴刘继庄处士选订。以钞胥字迹及纸色审之,应为乾隆初年钞本。并从李序中,知圣叹尚有外孙元一、元景,二人“慧且博,有先生风,幼受书母夫人”一节,为各家记载所未及,则此“诗选”流传必不甚广也。
陆案:沈六书指吴江沈重熙(1650—1722),字明华,六书为号;元一名培祉(1676—1743),重熙长子;元景名培福(1682—1738),重熙季子;元一、元景之母即重熙之妻金法筵(1652—1705),乃圣叹第三女。李重华(1682—1755)乃雍正二年(1724)进士,为《诗选》作序时间是雍正五年“首夏”(农历四月),当其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时。刘继庄即刘献廷(1648—1695),圣叹去世他才14岁,五年后始从大兴迁至吴地,然此人与金氏和沈氏颇有关系,我曾撰文探讨[3],此处从略。
李重华与沈培福同乡、同庚,序云沈氏兄弟“幼受书母夫人”,当为亲见。金法筵7岁能诗,出嫁后生活贫苦,曾作诗勉励诸子:“人生少壮时,旭日初升天。金光浴沧海,照耀无中边。致身贵及早,东隅岂迟延。惜阴计分寸,千古称圣贤。逝者本如是,白驹况加鞭。老大有伤悲,谁为挽百川。”[4]其父不良死,母、兄皆远流,而诗中毫无消沉颓丧之感,充满昂扬奋发之气,词意老成,笔力不俗,故引为“幼受书母夫人”作一注脚。
《读后记》:圣叹原名采,鼎革后更名人瑞,稗史有云本姓张氏,或云名喟,皆臆造不足据。卒时为顺治十八年辛丑七月十三日;其生年无可考,仅见杨保同所辑《圣叹轶事》云生于三月三日。又钱蒙叟撰《天台泐法师灵异记》述天启七年事,已称“金生采”,则当生于万历年间矣。
陆案:金氏原名、更名之说未必可信,鼎革后始改名更属臆测。此论始于粤人廖燕(1644—1705)《金圣叹先生传》(见《二十七松棠集》卷14,又见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44。以下简称廖“传”)“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之说,经陈登原《金圣叹传》征引而几成定论,其实大有再议的余地。其一,廖燕为广东曲江人,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始至吴门,其时圣叹友人多已凋零谢世,廖“传”跋语亦云“予过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所记诸事,当主要从“读先生所评诸书”(廖燕《吊金圣叹先生》诗云:“我居岭海隅,君起吴门湄。读君所著书,恨不相追随。”)及闾里传闻而来。自陈登原至今,征引廖“传”多是根据民国闵尔昌编《碑传集补》所收者,编者已将原传跋语略去,因此使用者均未注意到廖氏来吴,已是圣叹死后35年之事了。故对其所云圣叹事迹,今人实有重新逐一衡估史实可靠性的必要,然后才能决定取舍。其二,早有证据说明在“鼎革”之前金氏已名人瑞、字圣叹了。如崇祯十四年(1641)自序《水浒传》,便有“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云云[5](1册P6);另近人叶恭绰(1881—1968)旧藏明末邵弥所画绢本山水长卷,有金氏手书长跋,时在“崇祯甲申夏尽日”(1644)。时江南尚在明朝治下,故仍用崇祯年号。落款处钤有阳文印章两枚,一为“圣叹”,椭圆形;一为“人瑞”,方形。跋文在叶氏《明邵弥山水卷》一文中有详细记载[6](卷7),但笔者始终以未见金氏跋文手迹为憾。金跋山水图卷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7 ](P377),不知何时能得有心者公之于世,以飨吾等。其三,虽然此后金氏多自署“金人瑞”、“金圣叹”,但是称其为“金采”、“金若采”者亦时有可见。如圣叹友人浙江嘉善李炜,曾撰诗《寄怀墨庵兼询圣叹》(墨庵指嘉兴沈起(1612—1682),因所撰《学园集》未见传本,故此诗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知最能直接说明四库馆臣所谓其“与金人瑞相善”的史料),首句便是“海内谈经金若采”;再如稍后吴江周廷谔(约1670—?)编辑《吴江诗粹》,称金法筵为“吴趋采之幼女”[8](卷30)。廷谔生年虽晚,然与乡前辈、圣叹得意门生沈永启(1621—1699)为“忘年交”[3],其言当有所本。就已知史料来论,笔者倾向于认为:金氏名采,字若采,一名人瑞;“更名”说缺乏证据,“鼎革”后更名尤难成立。“一名”说亦非独家首创,早在康熙初年周亮工编辑《尺牍新钞》已著录“金人瑞,字圣叹,一名彩”,乾隆初年沈氏后人编辑《吴江沈氏诗录》亦云法筵之父为“圣叹公人瑞一名采”。
关于圣叹“本姓张氏,或云名喟”,固然属“臆造不足据”之说,然考其出处,则首见于陈登原所引同为无名氏所撰之“稗史”《哭庙纪略》“名人瑞,庠生。姓张……”和《辛丑纪闻》“名喟,又名人瑞。姓张……”[2]。查陈登原所列《参考书目》,此两书分别是商务印书馆排印《痛史》本和《申报馆丛书》本。经与有关版本核对,“庠生。姓张”和“姓张”两句,不是所有版本皆是如此[9](P22);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申报馆丛书》本的原文在“又名人瑞”之后,并非“姓张”,而恰恰是“庠姓张”三字①。笔者不认为身为史学家的陈先生不知庠姓与本姓之别②,只能猜测圣叹“姓张”之“臆造”,是由于所引“稗史”版本不同,经陈登原先生(有意?)片面征引所导致。其实,如非先有一个“庠姓张”之不可能的主观在③,即便是仅据《痛史》本《哭庙纪略》,亦不妨将有关四字视为一句,即“庠生姓张”,这样与“庠姓张”并无二义(考虑到“生”与“姓”在形、声上的相近,从校勘角度看,笔者更倾向于“生”为衍文)。由于种种原因而以庠姓、榜姓代替本姓应试的现象,在明末清初之大变动时期极为普遍,人称“明季入学者多冒他姓”[10]。如晚明吴县吴安伏(明崇祯十年进士吴嘉祯之弟)便是“庠姓严,名龙”[11]卷36。明末如此,清初亦然。即以圣叹友人论,刘逸民庠姓潘,戴之儦庠姓吴,同为顺治二年诸生;许来先“榜姓朱”[12](卷7),为顺治十一年拔贡;熊林庠姓张,顺治十三年诸生;丁兰(十八诸生之一)弟丁王肃庠姓王,顺治十八年诸生;陆志舆榜姓吴,康熙十六年北榜举人。陈洪先生通过比勘各种版本的《哭庙纪略》和《辛丑纪闻》,认为“庠姓”为“不词”;并出注说明:“黄霖兄曾撰文,称询及某前辈,得知‘庠姓’之可能。惜尚缺文献依据。”[9](P26、29)(据复旦友人说,“某前辈”是朱东润先生)应该承认在现有的语词类工具书中尚未载有“庠姓”、“榜姓”等词,但是作为一种古代应试的非常规现象及有关语词,对其事实的存在及其在古籍中的著录应该是无庸置疑的④。至于《哭庙纪略》和《辛丑纪闻》的祖本,就现存文献分析,当属苏州顾公燮(1722—?)撰成于乾隆五十年(1785)之《丹午笔记》中所收的《哭庙异闻》为最早,先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白鹿山房刊行《丛刻三种》本《哭庙纪略》问世约35年。其中有关金氏姓氏字号的一段颇具参考价值:“金圣叹,名人瑞,庠姓张,字若来,原名采……少补长邑诸生,以岁试之文怪诞,黜革。次年科试,顶张人瑞就童子试,拔第一,补人吴庠。”[13 ](P162)顶张人瑞就试,较之后出之“顶金人瑞名”的记载或后人的“顶张采名”应试的理解,应该顺理成章得多。
金圣叹的卒年(1661),任何一种详细反映“哭庙”案经过的古代文献均有记录;其生年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在今天也已不成问题,见《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等权威著述(故得年54岁)。但是,在陈登原尚认为“独其生时,今无可考”,最后借助《第五才子书》序,推论其“当生在神宗万历三十七年也”[2](P5、8)。在未发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其结论能如此接近事实,陈氏的考辨功力令人服膺。而惟一涉及圣叹准确年龄的史料,是嵇永仁(1637—1676)《葭秋堂诗》卷首以《葭秋堂诗序》为题收录的圣叹致永仁尺牍。金氏此札开头便说“弟年五十有三矣”,由信中言及“自端午之日……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余章”[14](卷4),知此年必为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5](3册P32)。逆推53年,即得其生齿。予见也寡,在“金学”学术史上,所知最早引用嵇永仁此篇“人瑞手札”者,为邓之诚(1887—1960)去世前一年写就的《清诗纪事初编》(此书亦是最早向学界介绍《沉吟楼诗选》者)。所惜邓氏误认此札“作于己亥顺治十六年,自言年五十三,被祸时当为五十五岁”。揣度其意,当以万历三十五年(1607)为圣叹生年(如其在文中复云“天启七年,是时人瑞年仅二十一”)[15](P336-337)。以1607年为金氏出生之岁,所从者甚少,惟钟来因先生整理《杜诗解》时“取邓说”。
此段“读后记”所引杨保同、钱蒙叟云云,亦见于陈登原之书。前者引及杨氏有关文字为:“俗传三月三日,为文昌生日,而圣叹亦于是日生。故人称圣叹为文曲星,圣叹虔祀文昌,或亦因此欤。”[2](P9)后者引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陈登原早以天启七年牧斋“已称金生”为圣叹生于“万历三十、四十年之旁证”,并注明钱文出自《初学集》卷四十三[2](P8),给后人直接引用提供了方便。
《读后记》:诗中所述诸人姓氏可考者:斫山为长洲王氏。按《西厢·闹简》批语有云:“吾友斫山王先生,文恪之孙。”廖燕撰圣叹《传》云:斫山为侠者流,与圣叹交最善。一日以三千金与圣叹,曰:“君以此权子母。”甫越日,挥霍已尽,斫山一笑置之。邵宝撰王文恪鏊《墓志》,公有男延喆、延素、延陵、延昭四人。延喆为昭圣皇后之甥,少以椒房入宫中,性豪侈。斫山与之相类,或即其所出也。
陆案:此段关于王瀚(号斫山)的文字对今人影响颇大。“文恪之孙”金批《西厢》原文为“文恪之文孙”[5](3册P133),“文孙”是对别人之孙的美称。廖燕撰圣叹《传》全名为《金圣叹先生传》,所涉王斫山的一段共86字,此处改写、节录为41字,且将“甫越月”抄作“甫越日”,更加强化了传闻的色彩。今人整理“全集”,复将“邵宝撰”之后诸字标点为:《王文恪鏊墓志》:“公有男延喆、延素、延陵、延昭四人。延苗为昭圣皇后之甥,少以椒房入宫中,性豪侈,斫山与之相类。”前38字均标在同一引号内,即均视为邵宝之言。此举误甚。邵宝(1460—1527)与王鏊(1450—1524)基本同时,如他在任何文字中谈及王斫山,那么斫山至少约生于明正德五年(1510),即邵宝去世时斫山起码约17岁左右(否则难以看出有与延喆“相类”的“豪侈”之性)。这样算来,“圣叹事之为兄”的王斫山,在圣叹出生那年便已99岁,何谈“与圣叹并复垂老”[15](P133)?“邵宝撰王文恪鏊《墓志》”等数十字,不见陈登原书,系由俞鸿筹首次征引。然查邵宝《大明故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致仕赠谥文恪王公墓志铭》,根本无后38字,大致可以对应的只是“吏部阙侍郎,侍郎韩公摄事,以公与寿宁故有连,既贵而能远之,其正可敬也,首荐而用之……子男四:长即延喆,中书舍人;次延素,南京中军都督府都事;次延陵,郡诸生;次延昭”等内容[16](卷16)。但是此段文字并非俞氏杜撰,前13字当节录自《文恪王公墓志铭》,后25字乃出自《池北偶谈》:“明尚宝少卿王延喆,文恪少子也。其母张氏,寿宁侯鹤龄之妹,昭圣皇后同产。延喆少以椒房入宫中,性豪侈。”[17 ](P210)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清初王士禛(1634—1711)这段话除了“母张氏”和“性豪侈”之外,可信者不多。王延喆(1483—1541)为王鏊长子,而非少子;延喆“少以椒房入宫中”与邵宝所云“既贵而能远之”可谓针尖麦芒;其母张氏(1462—1487)为王鏊继室,乃成化年间沧州人丹阳县令蔡寔(本姓张,少孤依蔡氏,故又姓蔡)之女(为省篇幅,略去出处)。据《明史》,寿宁侯张鹤龄乃孝宗昭圣张皇后之弟,他们的父亲为兴济人老寿宁侯张峦(1445—1492)。如延喆母张氏为鹤龄妹,则亦为张皇后妹,便必为张峦之女;从延喆母张氏生年看,乃张峦虚龄18岁时所出生,为其女当然尚不勉强,但如要张峦在此之前先要生出一后、一侯来(只有如此,才能符合延喆母乃“寿宁侯鹤龄之妹,昭圣皇后同产”的说法),即便对于无“计划生育”约束的古人,亦颇让其为难了(此非主要指生理上是否可能,而是包括习俗、养育、经济、学业等多方面的考虑)。且据张峦《墓志铭》,其女张皇后成化二十三年(1487)应选太子妃时已“生十七年矣”(即生于1471年),王士禛之说便不攻自破了。考虑到沧州(今沧县)、兴济(今青县)为河间府毗邻属县,邵宝所谓“公与寿宁故有连”,如非指王鏊与张峦原本为友,亦只是指其岳丈张(蔡)寔与张峦略有葭莩亲。话要说回来,俞鸿筹虽不辨真伪乱引《池北偶谈》,对今人的理解难辞误导之咎,但是必须指出:其一,“文恪之文孙”确实出自圣叹之书;其二,俞氏对“斫山与之相类,或即其所出也”的推测是非常准确的。笔者对王瀚与王鏊的关系已作考述[18],此处只能极简单地交代如下:王瀚(约1606—?),字其仲,号斫山,明末吴县附例生,入清隐居,为延喆之孙禹声的孙子,康熙八年(1669)尚在世。金批《西厢》所谓“文孙”,当为“玄孙”之形近误刻。后者有远孙、裔孙一义,如说王斫山为王文恪之裔孙,应是毫无疑义的。
《读后记》:贯华先生为韩住,字嗣昌;道树为王伊,字学伊。《西厢·惊梦》批语云:“知圣叹此律[解]者,……居士贯华先生韩住、道树先生王伊。既为同学,法得备书。”崇祯十四年初刻本七十回《水浒传》版心有“贯华堂”字样,即嗣昌所刻。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谓金彩有《贯华堂集》,误以《水浒》版心所刊为圣叹集名,乾隆《苏州府志》亦沿其误,皆宜改正。
陆案:仅从“诗选”《病中承贯华先生遗旨酒糟鱼各一器寄谢》[5](5册P790)和金批《西厢·惊梦》“居士贯华先生韩住”[5](3册P198),说贯华先生韩住字嗣昌固无问题;然据《鱼庭闻贯》第十四条《答韩贯华嗣昌》[5](4册P40),以《鱼庭闻贯》署名惯例,韩住似又为以字行者。此人或与圣叹亲家韩俊(金雍岳丈)为昆季(名皆以“亻”为偏旁),惜乏史料相证。今存《云东韩氏家谱》所记乃苏州另支韩氏,与圣叹友人诸韩(另有韩藉琬、韩魏云)均无涉,书此以免“金学”同好浪费精力。
据《惊梦》金批,认为王道树名伊自然无错,然说其字学伊却是误解。在金氏著述中,与“道树”联袂而出的称谓只有两处,一是俞氏明引的“道树先生王伊”,一是其暗引的“王道树学伊”。后者见于《鱼庭闻贯》首条《答王道树学伊》[5](4册P36),如据此便判断王道树字学伊是难以成立的(排比一下《鱼庭闻贯》姓氏字号抄写顺序,即可发现何为名、何为字号的规律)。今综合各种文献考知,王学伊(1619—1665),原名伊,字公似,号道树,明末岁贡生,入清为遗民,隐居苏州胥门之郊,终身不入城市;为王斫山幼弟,现代昆曲大师王季烈(1873—1952)之九世嫡祖[18 ]。
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谓金彩有《贯华堂集》,确有此事,但却未必是“误以《水浒》版心所刊为圣叹集名”所致。康熙元年(1662)周氏辑刻《尺牍新钞》时,于卷五所选金氏尺牍两封,为《答王道树》和《与家伯长文昌》。当时《唱经堂杜诗解》、《沉吟楼诗选》皆未问世,金批刊行之作仅为《水浒传》、《西厢记》、《唐才子诗》三种,而这三种恰恰均冠以“贯华堂”三字。不是后来清理遗书者如圣叹堂兄金长文或女婿沈六书,是不可能知道有所谓“唱经堂遗书目录”的。周亮工言其著作为《贯华堂集》,虽不够准确,但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他当时所见金书皆为《贯华堂……》,且所选两篇亦均出自《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之《鱼庭闻贯》[5 ](4册P39)。退一步说,如果非要认为周亮工有误,也当主要是因为误以“贯华堂选批”之书为圣叹集名,未必与已刊行20年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的“版心”有直接关系。今人或因周亮工著录金氏有《贯华堂集》便说他“对金圣叹的情况很不了解,仅仅是道听途说而已”[19]。其实,周亮工对金圣叹的了解与同情,远远超出后人之所知;即以《尺牍新钞》卷二对《与黄俞邰》一信的眉批为例:“圣叹尚有《历科程墨才子书》,已刻五百叶。今竟无续成之者,可叹!”此则史料在数十年的“金学”研究中,不知有几人注意过?在笔者看来,周亮工与金圣叹的关系是金氏史实研究中的一个颇有价值的题目,值得专题探讨[20]。
《全集》对“读后记”抄录的《惊梦》金批,点校上有两处失于核查:“知圣叹此律者”,“律”字原文为“解”,系由俞氏误书,宜径改或出校;在“居士贯华先生”之前,原文尚有“比丘圣默大师、总持大师”10个字,标点时宜加省略号“……”。
《读后记》:阎牛叟名修龄,善咏诗;百诗名若璩,为经学大师。阎氏顺治时侨居淮安,后归原籍太原,诗中同游邓尉、虎丘,正其寓苏之时。邵僧弥名弥,长洲人,吴梅村所咏“画中九友”之一。文彦可名从简,衡山曾孙,端容之父。
陆案:“诗选”中涉及阎修龄、若璩父子处,有《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丘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命酒重上卧[悟]石轩,快饮达旦,绝句记之》、《阎子牛叟游邓尉,有怀故园梅花……》、《牛叟阎子游玄墓,有怀故园梅花……》等[5](4册P822、834)。诸诗写作时间向无确考,今据张养重《粤游春别》七绝诗序“辛丑正月,再彭观梅光福。二月,余与丘子曙戒有粤行。道出姑苏,相遇于虎丘,置酒言别。同集者姚山期、金圣叹、曙戒弟季贞、再彭子百诗,暨镜怜较书”的叙述[21],得知阎氏父子“观梅光福”乃在辛丑即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同年二月,张养重和丘氏兄弟始“道出姑苏”,得与金氏诸人相遇。联系金氏诗题中“廿三日既成别矣……快饮达旦”云云,可证事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晨,即“哭庙”事件发生后之20天。可与圣叹“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快饮达旦”诗相印证的,还有丘象随写于顺治十八年的《泛虎丘》古风一首,该诗详细歌咏了众人虎丘欢会经过,其中“侧身迎左檐,有客美风度。殷勤达姓名,金子宿所慕。旧交与新知,一心欢参互”等诗句[22 ],勾勒出金圣叹的儒雅风姿,并体现了诗歌作者对其由衷的仰慕。阎牛叟(1617—1687)名修龄,字再彭,牛叟其号。祖籍山西太原,自高祖之父始居山阳(今江苏淮安)。崇祯八年(1635)为诸生,明亡聚儒衣冠而焚之,从此遁世隐居。牛叟与圣叹之交谊,向无记载,从金氏《阎子牛叟游邓尉……》之二“山下春流泯泯深,送君一片古人心。自从李白闻歌后,不见汪伦直到今”诸句,足证阎、金友谊深厚。此年圣叹54岁,阎牛叟45岁。百诗为其子若璩(1636—1704)之字,号潜丘,此年26岁。以“经学大师”名世乃是以后之事。由于金氏上述诸诗是其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那年在遇害之前的重要作品,所涉姚山期、张虞山、丘曙戒、丘季贞亦皆为清初重要文化人,故笔者对有关问题已撰文考述[23],此处只是将稀见史料的有关线索再作披露而已。
邵弥(约1598—1642),字僧弥,号瓜畴,善书画,性不谐俗。吴伟业(1609—1672)所撰《邵山人僧弥墓志铭》[24](P953),述其生平事迹甚备,惟于其生卒语焉不详。梅村曾撰《画中九友歌》,对“风流已矣吾瓜畴”,以“一生迂癖为人尤,僮仆窃骂妻孥愁。瘦如黄鹄闲如鸥,烟驱墨染何曾休”怀念之[24](P290)。
文从简(1574—1648),字彦可,晚号枕烟老人,曾祖征明(1470—1559)、祖嘉(1501—1583)、父元善(1555—1589)皆为书画名家。从简为明崇祯十三年(1640)贡生,例得学博,不赴选,入清隐居为遗民。其女文俶(1594—1634),字端容,擅画草木昆虫;嫁赵均(1591—1640),为赵宦光(1559—1625)子。
《读后记》:“家兄长文”系圣叹族兄,名昌,字长文,号矍翁,法名圣瑗,曾撰《第二才子书离骚经跋》及《第四才子书杜诗解序》。“诗选”中“鼠肝虫臂”一首,即临难时寄示长文之作。儿子雍,字释弓。按圣叹《才子尺牍》卷首有“男雍释弓撰”五字。《哭庙纪略》载圣叹有一子,曾请乩仙题号,乩仙判曰“断牛”。及圣叹获罪,妻、子流宁古塔。“诗选”内亦有《与儿子雍》七绝一首,此可正梁拱[恭]辰《池上草堂笔记》所云圣叹无子之误。
陆案:此处对金昌的字、号及与圣叹关系的描述甚确,原始材料见于其《才子书小引》和《叙第四才子书》的落款“同学矍斋法记圣瑗”、“矍斋金昌长文”及“小引”文中所谓“唱经,仆弟行也”[5](4册P524、525、523),凡此皆已见陈登原《金圣叹传》征引。关于金昌,拙文只有两点补充:其一,“家兄”与“家伯”之别。对于金昌,出自圣叹之口,皆称其为“家兄长文”,如《圣人千案序》“同其事者,家兄长文”[5](3册P731)、《春感八首》序“家兄长文具为某道”及第八首尾注“为家兄长文”[5](4册P858、859);而在金雍辑《鱼庭闻贯》第11、24条则分别署作“与家伯长文昌”和“与伯长文”[5](4册P39、42)。由于“伯”在古代有长兄和父亲之兄等多义,故自周亮工辑《尺牍新钞》始,即将选自《鱼庭闻贯》第11条“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中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一段,径题作《与家伯长文昌》,殊不知在《鱼庭闻贯》中,凡称与金氏有亲缘之圣叹同辈者,皆是以金雍之辈份或身份相称。直言之,此处之“家伯”恰恰是对本家或同宗伯父的称呼。鉴于圣叹此篇与家兄长文的尺牍仍时常为今天编选古代家书或书信者所青睐,故将金氏著述中“家兄”与“家伯”之别略作辨正。其二,金昌《叙第四才子书》曾言及自己是“兹淝上归”后,始从事“搜辑、补刻”圣叹遗著《杜诗解》的工作。淝上指合肥(清为庐州府治所在县),古有淝水(今名肥河)流经其地。查该县“国朝”训导名单,康熙朝第四任即“金昌苏州人”[25]卷16,虽于康熙朝历任具体时间均缺署(康熙《庐州府志》同缺),但毕竟有助于推考《第四才子书》的刊行时间。
圣叹有子金雍(1632—?),字释弓,这在金批《水浒传》序三“今与汝释弓……今年始十岁”[5 ](1册P9)和《鱼庭闻贯》所署“男雍释弓集撰”[15](4册P35)等常见金书中即不难寻到证据。俞鸿筹所谓《才子尺牍》一书,当是据《鱼庭闻贯》选编者,有民国七年(1918)上海求古斋书帖社石印本和上海大达图书社民国二十四年(1935)排印本等,卷首有“男雍释弓撰”五字。所引《哭庙纪略》有关“断牛”的逸闻,亦见于顾公燮《哭庙异闻》[13](P162),惟俞鸿筹于“妻、子流宁古塔”后,抄漏“其居室之后,有一断碑,但存‘牛’字,殆亦前定数耶?”诸句,不仅令人读后不知所云,亦失去了此段逸闻原有的宿命色彩。如果俞氏引此仅是为了说明圣叹有子,亦毋庸抄录“曾请乩仙题号”等十二字。据陈登原征引,“梁拱辰《池上草堂笔记》所云”[2](P69),出自该书卷八。惟作者乃梁恭辰(1814—?)而非梁拱辰。《全集》点校有两误,一是“梁拱辰”之“拱”字宜径改或出校(误始于陈登原),二是“圣叹无子”并非梁氏书中原话,不宜标引号。查该书此条为:“汪棣香曰:施耐庵成《水浒传》,奸盗之事,描写如画,子孙三世皆哑。金圣叹评而刻之,复评刻《西厢记》等书,卒陷大辟,并无子孙。”[26](卷8)汪棣香名福臣,嘉庆、道光间钱塘人,辑有《劝毁淫书征信集》,存同治四年(1865)刻《琼瑶合编三种》本[27](P1443)。
《读后记》:《杜诗解》卷二有附录圣叹幼年所作五律一首:“营营复[共]营营,情性易为工。留湿生萤火,张灯诱小虫。笑啼兼饮食,来往自西东。不觉闲风日,居然头白翁。”今《诗选》内不载,其遗佚固已多矣。
陆案:“幼年所作”四字,影印本有细笔改乙,勾为“所作幼年”,《全集》标点为“所作《幼年》”。然据《杜诗解》卷二《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至《早起》等五首的总批语“曾记幼年有一诗”云云[5](4册P605),细笔改乙之痕迹当为后人所加(何人所为?),《全集》点校者未核引文出处,遂将“幼年”作诗理解为“所作《幼年》”。如不细审影印本《诗选》而仅据《全集》本,读者会以为错在“读后记”作者身上。另原文首句为“营营共营营”,俞鸿筹误将第三字抄作“复”,整理本亦宜据原作径改或出校。
金圣叹一生作诗甚夥,据李重华序称,《诗选》所录者仅“什伯之一”[5](4册P777),可知佚者极多。笔者留心数年,才发现区区三首,即徐崧(1617—1690)、张大纯(1637—1702)辑《百城烟水》中的《题平丘沈君善木影》、《寓慈云寺旬日留别》和袁枚《随园诗话》中的《宿野庙》[28];另在金圣叹友人徐增(1612—?)《九诰堂集》中,有其《岁暮怀悬瀑先生兼寄圣默法师》佚诗一首,可见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读后记》:圣叹之墓在苏州城外五峰山下博士坞,至今犹存。十余年前,张仲仁(一麐)撰《阳山十八人祠记》,谓苏州浒关阳山东麓有土地庙,塑像十八人,衣冠各异,故老相传,即哭庙案中同难者之像;又谓哭庙诸生怀光复明社之志,缇骑搜其家,得与嘉兴友人书,多不讳语,故借哭庙事以罪之。今阅《诗选》中如《甲申秋兴》、《效李义山绝句》、《塞北今朝》、《元晖来述得生事》诸作,亡国之思,触处多有。当时文网綦严,犯者辄有不测。选此诗时,想见慎之又慎,而仍不免错杂其间,则此诗后之流传不广,良有以也。
陆案:圣叹墓在博士坞之说,可能始于同治修《苏州府志》卷四十九《冢墓一·吴县·国朝》“文学金人瑞墓在五峰山下博士坞”,而盛行于民国年间。如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日本学人“辛岛骁谓数年前,
上海某书店曾刊《苏州快览》,一通俗旅行书也。内记圣叹之墓,在苏州城外五峰山下之博士坞。辛氏并谓曾托当地人士,前往探得之”[2](P70);稍后所修《吴县志》卷四十《冢墓一》沿用前志而有所补充:“文学金人瑞墓,在五峰山下博士坞,近道林精舍,吴荫培立碣。”日人虽重田野调查,惜非躬亲其事,所得尚不能以确论视之;然吴县吴荫培(1851—1931)乃光绪十六年(1890)探花,民国七年(1918)任《吴县志》总纂之一,按理不会有误。但是李根源(1879—1965)在民国十五年(1926)三月,曾亲赴其地寻访:“上午八时入白阳山金井坞……入博士坞,访金圣叹墓。……走遍博士坞,终不得圣叹墓。适遇一老妇,询之,云:‘金墓在西山坞,非博士坞,前年吴探花重修之。’转入西山坞,经吴江史氏墓坊,山坞尽处为圣叹冢,建‘清文学金人瑞墓’碑,吴荫培书。右侧为白马涧通济庵僧觉阿遗冢,僧俗名张京度,著“通隐堂”、“梵隐堂”诗者也,可谓德有邻矣。时坞中杜鹃盛开,有红、紫、黄、白四种,灿烂悦目,为诸山所未有,其圣叹、觉阿精灵之所集与?登五峰山……”[29 ](卷2)所不解者是:李根源虽为云南腾冲人,然自民国十二年(1923)即定居苏州(故居在今十全街111号,为市级保护单位),且亲身实地勘察,何以会在接替吴氏任《吴县志》总纂后,在新修方志中仍云金墓“在五峰山下博士坞”?
张仲仁者,名一麐(1867—1943),字仲仁,亦为《吴县志》总纂之一,《阳山十八人祠记》写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与俞鸿筹引文相关的内容是这样两段:“余去冬至浒关,丁君南洲方为区长,与余有中表谊,同游阳山。山之东麓有土地庙,塑像十八人,衣冠各异。丁君告余,故老相传即哭庙案中同难十八人之像”;“南洲又曰:哭庙诸生怀光复明社之志,缇骑搜牢其家,获与嘉兴友人书,多不讳语,故借哭庙事以罪之”[30](卷3)。俞氏此篇读后记,撰于“辛卯孟春”即1951年,距张一麐写“祠记”整整20个年头,故不宜云写于“十余年前”;此外,“祠记”于“故借哭庙事以罪之”后尚有“一则议斩,一则斩且籍没”,说的是丁氏先人丁观生(1610—1661)、丁澜(1625—1661)。此二人是同祖的堂兄弟,于哭庙案同时遇难[31],《读后记》省略了两个“一则”等10字,极易让人误解“获与嘉兴友人书”的人是指金圣叹。金氏虽在嘉兴确有友人
且多为遗民,但从“祠记”的上下文判断(文长不录),“与嘉兴友人书”作者姓丁而不姓金。另其节录之文字,与原文颇有出入,整理时以不加引号为妥(《全集》标点作:谓:“苏州浒关阳山东麓,有土地庙,塑象十八人,衣冠各异,故老相传,即哭庙案中同难者之像”;又谓:“哭庙诸生,怀光复明社之志。缇骑搜其家,得《与嘉兴友人书》,多不讳语,故借哭庙事以罪之。”)此段《全集》标点尚有两处显误:《甲申秋兴》[5](4册P820、830)、《效李义山绝句》[5](4册P819、836)明是两题组诗,却标为《甲申秋兴效李义山绝句》,将两首弄成一首了;《塞北今朝》[5](4册P849)诗题之后二字,标成下一首《元晖来述得生事》[5](4册P806)的前两字。出错之由,真令人难以猜想。
《读后记》:刘继庄生顺治五年,卒康熙三十四年。全谢山为立传,云年十九寓吴中,居吴江者三十年。则继庄始寓吴时,为康熙五年。金释弓已于前数年流宁古塔,而继庄所著《广阳杂记》有与释弓问答《南华会解》之语,似释弓后曾归吴,方有此事,惜无他种资料可为互证也。
陆案:全祖望《刘继庄传》原文作“继庄年十九,复寓吴中,其后居吴江者三十年”[32](P521-522),俞鸿筹节录为13字,《全集》加以引号,未必尽妥。所谓刘献廷“有与释弓问答《南华会解》”之事[33 ](P335),必发生在金雍自流放地归吴之时。与“释弓后曾归吴”可为互证的“他种资料”,今人知者有三则:一是沈永令(1614—1698)[临江仙]词“金释弓从辽归,代闺怨”:“自别河梁成永诀,十年梦绕辽西。梦中牵袂数归期。刀环真浪约,何日照双栖。蓦地归来真是梦,归来日日分离。不如依旧在天涯。梦回鸡塞远,犹得到深闺。”一是同一作者的《送金释弓还辽》诗:“鸿飞万里异翱翔,叫断寒云认故乡。嗣世可堪成汉史,十年无复说蒙庄。关河历尽霜花白,岁月移来鬓影苍。塞外只今书种在,更谁笔札问中郎?”一是金法筵《家兄归自辽左感赋》诗:“廿载遐荒客,飘零今始归。相看疑顿释,欲语泪先挥。郁塞千秋恨,蹉跎万事非。不如辽左月,犹得梦慈帏。”这三首诗词说明金雍于发配后曾两次归吴,一在10年后,一在20年后,前为暂返,后为终还(参见张国光《金圣叹的志与才》,南京出版社,1988,第148页)。据杨凤苞(1757—1816)注全祖望《刘继庄传》,献廷“于康熙六年丁未来吴,至二十六年丁卯入都”[35](P522),其与释弓问答《南华会解》,在后一时间的可能性较大。前两首诗词的作者沈永令,字闻人,一作文人(见周铭《松陵绝妙词选》卷三小传:“沈永令,字文人,号一指。”康熙刻本),吴江人,浙江秀水庠生、副榜贡生(今人或有因此认为永令乃秀水人),与圣叹所交吴江沈氏诸人有着较为密切的血缘关系。《鱼庭闻贯》有圣叹与永令尺牍,《全集》整理本作“答沈丈人永令”[5](4册P49-50),如非排印误植,当是整理者以为“文人”于此不讲而径改为“丈人”。
《读后记》正文考辨到此为止。从文末落款“辛卯孟春俞鸿筹读后记”和所钤白文方型印章“虞山俞鸿筹印”,可知此跋的写作时间和作者籍贯。俞鸿筹(1908—1972),字运之,号啸琴,别署孱提居士、舍庵居士,江苏常熟人。毕业于震旦大学预科及上海法政学院。曾从事爱国抗日活动,民国三十四年(1945)初遭日军逮捕,严刑不屈。战后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支团部佐理”,旋辞职。著《松禅老人逸事》、《唐律疏义校注》、《舍庵诗词残稿》、《舍庵居士题跋》、《干禄字书笺证补》,校补《中国藏书家考略》等[34](P862、878、1092)。其父俞钟颖(1847—1924),清末官至河南布政使,入民国参加复辟帝制的筹安会,而鸿筹自己又有着三青团干的特殊身份,其于建国后之境遇可想。郡人郑逸梅(1895—1992)1985年为《中国藏书家考略》撰写的前言中,有一段文字颇具史料价值:
这书上起秦汉,下迄清末,都七百四十余人,可谓洋洋大观。直至前年,我友张慎庵来访,出示这书,书本的天地头满写了蝇头细楷,却增添了一百三十四人,订正了二百多处,钤有孱提居士印章,……经我寓目,断为常熟俞鸿筹运之的订补。……运之为俞钟颖嗣君,钟颖字君寔,号幼莱,又号遁庵,有时署南郭先生,为大儒俞钟銮之弟,与陆润庠状元为同治壬申同科,由总理衙门章京,出任琼崖道,擢河南布政使,署理河南巡抚。著有《耐庵随笔》、《归田集》等。运之渊源家学,工书,擅辞翰,精考证,以及版本目录,无不通达。我在陈季鸣的文旡馆,得见季鸣的《正反同形篆文汇录》,运之用正反同形篆文为题,工稳娴雅,妙造自然,始心仪其人。既而由钱释云之介,得识运之夫人庞镜蓉女史,藉知运之晚年病废,食贫励品,旋即谢世,镜蓉掇拾其遗著,名《舍庵诗词残稿》,委我为撰一序,他的作品,确有如李太白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概。词亦精微婉约,饶有情致。那孱提居士,为运之的别署[35](P3-4)。
虽然纸帐铜瓶室老人有所误记,但是对于鸿筹一生学术的介绍,还是比较全面的;尤其有关俞氏后半生的境况是从俞夫人庞镜蓉女史处直接得知,故其真实性无须怀疑。而在“晚年病废,食贫励品,旋即谢世”寥寥数语中,不难体会到省略了多少难言的酸辛。
俞鸿筹此篇《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写于1951年其44岁时,前十数年战乱频仍、遭逢寥落,建国初之百废待兴、政治先行,在此背景下评估俞氏研究金圣叹的得与失,无疑应该更多地看重其宣传圣叹之功和保存《诗选》之举;相比之下,无论其文中有多少疏漏和缺憾,都是微不足道的。俞鸿筹擅诗文,精书法,于版本、目录和藏书研究颇有造诣,然今人所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1985年修订版)、《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1993年版)等专书皆未见其名;《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续编》(2001年版)虽收录其人,但生卒、著述、经历皆有所缺。如能因拙文而能将其事迹补入后出之有关工具书中,笔者固然可以于心稍安,逝者或许亦可瞑目于九泉了。
注释:
①《申报馆丛书·记载汇编》本,光绪四年(1878)排印。另民国昆山(长洲邻邑)赵诒琛(1869—1948)辑刊《又满楼丛书》本《辛丑纪闻》,此句亦为“庠姓张”。
②所著《国史旧闻》第三分册〔六五五〕条《金圣叹》引《辛丑纪闻》此句写作“名喟,字人瑞。原姓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00页。如非排错,此当以“庠”为误植,而径改为“原”。
③陈登原,《金圣叹传》:“圣叹深恶秀才!何至以庠生之试,而轻易其姓耶?”第3页。
④“庠姓”一词,除以上引《七十二峰足征集》外,另见道光刻本《国朝昆山诗存》卷七周奕钫《哭吴缄三》诗题注:“缄三名若海,庠姓余。”
标签:金圣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