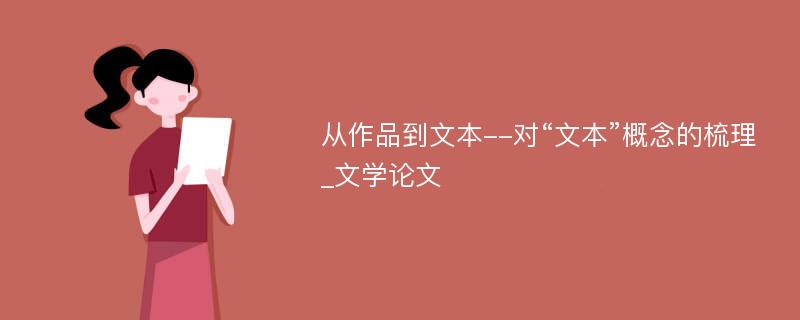
从作品到文本——对“文本”概念的梳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本论文,概念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0)01-0037-05
西方语言中,无论是法语中的Texte还是英语中的text本来都是日常语言中的普通词汇,也是文学批评的常用术语,和作品(法语是oeuvre,英语是works)这个词汇一样,它们都曾经因为太熟悉反而使人看不见①。而二战以后的文学理论浪潮使它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涵义的概念,甚至成为区分新批评和传统批评的关键词②:新批评研究文本,传统批评谈论作品。我们现在回顾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作品”这个词语变得非常罕见,而“文本”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文学的核心概念。巴尔特曾明确提出,文学研究和批评从作品的问题转为文本的问题③。关于这场文学理论的重大变革,我们的文学理论界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对于“文本”这个概念也非常重视,并且在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中,“文本”同样铺天盖地。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文本”概念有足够清晰的理解。Texte这个概念翻译为“文本”并进入是在80年代以后,随着结构主义的浪潮进入中国,直到90年代才逐渐成为文学批评话语中的关键词。中国的特殊语境,对于这个概念的吸收和旅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首先,汉语中并不存在一个与texte完全对应的词,当时中国学术界制造了两个词来翻译,一个是文本,另一个是本文。经过80年代的争议,90年代,“文本”作为texte的翻译得到了学术界主流的认可,但是并未得到完全的承认,“本文”的翻译依然还有一定影响④。这些都说明,在汉语中难以找到在意义上一个完全对应texte的词汇,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也并不存在一个与texte相同的范畴。傅修延先生在《文本学》一书中提到中国古代的“文本思想”⑤,实际上是一种误读。因为,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文本观是建立在“文本”与“作品”的对立之上的,倘若没有这种对立,也就不可能发生“从作品到文本”的转变。中国文学传统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对立,虽说中国也有“文”和“文章”之类的诸多概念,但是古汉语中,“文”并非是一个客观的对象,更非简单的文字所组成的任何东西。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这里的文带有强烈的价值色彩,与西方的text并不是一回事,不能简单归为一类⑥。尤其是汉语中,原本不存在一个与“文”相区别和对立的“作品”概念,这样的差别不仅造成翻译上和接受上的困难,也使我们难以理解西方文学理论中文本观念兴起的革命性意义。在西方的语境中,文本和作品作为语词的对立项,是必须相互参照才能理解的;而在中国的语境中,却常常难以理解这样的对立。
就在文本理论进入中国的同时,西方的文学理论则已经从最初的疾风暴雨般的颠覆热情转向更为冷静的反省,法国的先锋批评家们取得思想斗争的胜利并且掌握话语权以后,也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握手,在文学批评话语中,“作品”这个概念也逐渐回归。1999年,在对热奈特的一篇名为《从文本到作品》的访谈中,他强调了文学研究新方法与传统审美批评的相互结合⑦。也就是说,当中国学术界开始把texte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加以接受的时候,西方文学批评界中所发生的却是传统的回潮。当然,理论风暴并不是风过无痕,巴尔特等理论家已经被奉为经典,他们的思想遗产在当代的学术地图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但是,这个时代的错位在中国文学界所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种种概念和思想有所了解,但是由于并未设身处地真正经历先锋理论思潮的强烈冲击,所以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常常似是而非;另一方面也难以深刻把握回流的传统,因为这个回归的传统已经打下先锋思想深深的印记。直到今天,中国对文本概念的理解大部分都是接受美学的理解模式,而对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文本观念缺乏深入理解,即使在对西方六、七十年代先锋批评的研究中,也仅仅把文本作为审美判断的客观依据,而没有看到文本与作品的对立之处,因此也难以理解“从作品到文本”这一过程的真实意义。因此,对西方文学批评和理论在六、七十年代“文本”概念的命运和历程进行梳理,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反思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理论,是非常必要的。
一、传统观念中的作品和文本
每一位文学作品的读者都曾经面对过同一部作品的不同的版本,相同的文字以不同的装帧和印刷方式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会根据喜好或者经济的承受能力加以选择。然而,作为文学的研究者和批评者,说起文学问题,他就必须承认这些不同版本的书是完全相同的,它们是同一本书,他必须无视它们在外观上和在物质上的所有区别,印刷的纸张、字体的大小、装帧的图案,因为所有这些特征都不是文学的。书是有形的,而作品和文本是无形的。在实际的文学批评中,也很少会提到书,除非是作为作品或文本的替代。然而,倘若不能用视觉或触觉来确定一个作品或者文本,那么它们在什么地方,如何来确定它们呢?初看上去,这似乎不是一个文学问题,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使用这两个概念,就像呼吸空气一般自然。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可能通过书籍这样的印刷品来定义作品和文本,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社会,作品和文本的存在形式有很多:计算机、互联网、数码等等。
在传统的观念中,相对来说,文本是一个与物质联系更紧密的概念。在《说文》中,文被定义为:“文,错画也。象交文。今字作文。”在拉丁语中,文本(texus)的原意是纺织物,是纺织行为(texere)的产品。所有与texte相关的词都与纤维的交织有关。无论中文还是印欧语系的词源都指出了,文与纺织物的相同之处是横竖交织的结果。这与语言本身的性质也有密切的关系,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把纵横两种方向的交织称为组合关系(syntagmatique)和聚合关系(paradigmatique)⑧。在《小罗贝尔词典》中,对文本做出如下定义:“文本:构成写作和作品的词句。”[1]词典指出了文本所构成的是什么,但是没有指出是什么构成了文本。巴尔特在为大百科辞典所写的著名的词条中这样描述通常意义上的文本概念:
对于一般的意见来说,文本是什么?它是文学作品的表面现象;它是在作品中的词语交织形成的纺织物,它的组织是为了尽可能确定独一无二的稳定的意义。尽管这个概念是谦卑和部分性的(无论如何,它仅仅只是视觉的对象而已),文本还是参与了作品在精神世界取得的荣光,文本是作品的平庸但不可或缺的仆人。由于它构成了书写(文本,就是被写成的东西),也许因为,文字的形状虽然依然是线性的,但是它还是比口头语言和纯粹的编织(文本texte在词源学上的意义就是编织物tissu)有更多的意味。在作品中,它意味着所写出来的东西的保证,它身上集中了保护者的功能:一方面,它是固定不变的,文字书写可以用来纠正不准确的靠不住的记忆;另一方面,通过具体有形不容抹杀的文字的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人们会认为作者在这里按自己的意愿表达了意思;文本是打败时间和遗忘的武器,口头语言是容易磨损的,很容易就改口、变化、自我否定,而文本则是战胜这一切的武器。因此,文本的概念从历史上就与一系列制度联系起来:法律、教会、文学、教育;文本是一个伦理道德的对象……[2]
在传统的观念中,文本总是在与作品和文学制度的关系中加以定义的,它的职责就保证作品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维护作品的确定性,其存在总是被限定为“某某作品的文本”,文本没有独立性,最终必须走向作品,后者才是它的归宿。即使在强调“文本”重要性的接受美学那里,文学的最终价值依然是以“作品”的方式呈现的。
而作品,则是精神性的,还是在《小罗贝尔词典》中,作品被定义为“被符号或属于某项艺术的材料组织起来的整体,由创造者的精神使它成型;文学或艺术的产物”。与文本不同,一切艺术门类的产物都名之为作品,文学作品只代表其中的一部分。在文学领域,作品与文本处于很特殊的关系之中。一方面,它们似乎是同一的,比如说,“《狂人日记》这个文本”与“《狂人日记》这个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相同的,它们都由同样的文字构成;另一方面,它们又处于不同的层面,作品总是意味着文本的“彼岸”,意味着比文本更深邃的地方,如果说文本意味着书面上的文字,那么作品就意味着文字之上的意义和价值,当某一个书写的产物被称为“作品”的时候,也就意味它有某种超出文字本身的东西获得了承认,正是这种东西让人们把它称为“文学作品”。米凯尔·杜夫莱纳(Mikel Dufrenne)从三个方面考察了“作品”概念。第一,有某种价值体系“来把古希腊的雅典娜神庙(Parthénon)与其他的废墟区分开”[3]。在任何时代,这个体系与一切意识形态一样都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作品之完成似乎总是遵循某种内在的必然性(……)作品,是某种自足的东西,它以一种确定无疑的方式出现在那里,让人们接受,而这都是为了观赏者的快乐”[4]。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是体现了价值的文本。第二,作品意味著作者,其尊严与价值息息相关。人们根据作品的价值来评价作者,反过来也是一样。例如朗松的文学批评,他这样评价著名的皮埃尔·高乃依的弟弟:“托马斯·高乃依的精神是柔软的,虽然优雅但还是不免平庸,他什么都能做,但是没有任何超人之作。”[5]在朗松的眼中,弟弟得到这样的评价是因为他没有像他的兄弟一样创作出伟大的悲剧,而拉辛的悲剧是宝贵的,因为这些悲剧的创作“都源自其独特的天才,他在悲剧中倾注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从内部改变了它,在我们眼中,他成为一个戏剧体系的创造者”[6]。作者作为作品的源头,倾注其精神,而作品则表现了作者的激情、伦理观念和品味。这两者之间构成一个不可分解的同义反复的圆环:作者是伟大的,因为他的作品是伟大的;作品是伟大的,因为作者的精神是伟大的。虽然荣誉总是从对作品的评价开始,但是在因果关系上,作者与作品则保持着同一性,因为作品的源头是作者。因此,面对作品问题的时候,不在场的作者实际上总是以某种方式在场。即使在无法考证作者是谁的时候,也必须设想一个“无名氏”,因为作品需要一个“创作者”。第三,根据康德的美学,作品总是给予欣赏者无功利性的快感。一篇文字总是在它超出其文字本身意思的时候才会成为作品,如托多洛夫所说,“对作品的描述所针对的是文学的要素;批评家试图给它们一个阐释”[7]。读者就是在这种阐释之中寻找文本的彼岸,在彼岸中与作者达成交流。换言之,真正的交流不是在作者的言辞和读者对文句的理解中达成的,而是在言辞之外,在精神的彼岸达成,文本只是帮助他们在这个彼岸相会的工具。简单说,作品这个观念的形象就是从价值、作者和阐释三个角度加以解释的文本。
在这个概念系统和文学制度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作品”和“文本”到底所指的是什么,而是通过这两个概念所建立的一个价值等级:文本是低级的,同时也是基础的,因为它是从字面上来理解的;作品是高级的,其特征是形象和象征,给各种不同的阐释留下了空间,因为它代表了精神。而文学最终之所指是精神。在文学领域,作品与文本这两个概念联系紧密,长久以来,这两个概念的意义非常稳定,自文艺复兴以后,文学领域中,各种文学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文学观念也发生了不少变化,然而,作品和文本的概念却似乎坚如磐石:文本,即作品之现象,是语文学的范畴;而作品,则意味着精神、美感、深度等等。一直以来,人们都认可这两个概念的身份和关系。然而它们的身份和关系却并不是“理所当然,天生如此”,因为这样的身份和价值体系并没有实在性的基础,只是一种文学意识形态的产物。无论作品还是文本,它们都不是物质,并非我们可以用感官接触的实体,它们的存在是观念性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写作和阅读行为中,依据我们的观念确定它们的身份和性质。而一旦我们的观念发生变化,作品和文本的身份和性质也会相应发生变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理论的革命从根本上对这两个传统概念的意义和关系提出全新的理解。
二、作品和文本概念的新用法和新语义
在结构主义兴起之前,作品与文本之间的关系相对固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用一个短语来说明:“某某作品的文本”。然而结构主义之后,对作品和文本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就逐渐变得微妙起来,事实上也制造了不少语义的混乱。尤其是某些作者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两个概念,例如福柯,在某些文章中,他以传统的方式使用这两个概念,当他谈及结构主义的主要成就的时候,他写道:“在文学分析领域,不能不提到巴尔特关于拉辛的作品。”[8]在此处,作品的概念是传统的,意指重要的写作产品。但是在《话语的秩序》中,他却把“文本”与“作品”在同一个层面上对立起来:“一个人写作文本,在这个文本的视野之中总是徘徊着一个可能的作品,他自己又重新承担起作者的功能。”[9]在这里,文本受到“可能的作品”的威胁。假如从文字本身的角度去看,这个文本变作“作品”,它们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文字的改变,区别只在写作者与阅读者的眼光。在福柯这里发生的变化是,“作品”从一个肯定的概念变成否定的概念,从崇高精神的呈现物变成需要防范的威胁,因为福柯所要提防或者说反对的正好是前面所说的“作者的功能”,倘若在传统的文学概念中,作者保证了作品的精神价值,而在福柯看来,作者的功能更多的体现为对文本意义的控制,造成了话语意义的缩减。文本与作品之间融为一体的关系开始受到了威胁。
在60年代,“作品”这个词开始逐渐退出文学研究和批评的领地,而“文本”则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其把这种现象看做是“文本”概念的兴起,不如看做是“作品”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概念的“死亡”或者说“危机”,这些遭遇危机的概念还有:作者、阐释、品味、美、精神等等,它们都曾经确保了作品的价值,使文本最终能够成为作品,现在却遭到新的批评范式的质疑和抛弃。福柯宣告“人的死亡”,巴尔特宣告“作者的死亡”,作品的死亡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结局。
作品概念的死亡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忽视,而不是被谋杀。20世纪早期,俄国形式主义试图确立文学语言的独立性,深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的青年学者努力建立一种以语言学模式为基础的文学研究范式,努力建构“科学的文学研究”,达到类似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托多罗夫这样来总结他们的追求:“目标是研究文学性(littérarité),而非文学……人们所研究的不是作品,而是文学话语的潜在可能性,什么使文学话语成为可能:这样的文学研究就可以成为文学科学。”[10]在当时的文学批评氛围之中,作品的美学价值本身并没有被怀疑和颠覆,只是被轻轻撇在一边,结构主义者并不否定拉辛悲剧和波德莱尔诗歌的美,只是不再讨论这个问题。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被介绍到法国的时候,激发了对叙事进行形式分析的极大兴趣,《交流》为此专门出了一期“叙事的结构分析“专刊”⑨,然而,在这期文学批评的专刊中,我们看到研究的对象有007小说和电影、报纸的叙事和电影叙事理论。在大部分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笔下,“作品”这个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语言学术语:信息、编码、组合,等等。研究者们放弃了“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而是探索对一切叙事作品都有效的话语功能和运转原则。在看完这一类批评之后,完全无法了解批评家是否喜欢阅读詹姆士·邦德或者《包法利夫人》。科学,作为客观的知识体系,与研究对象的价值没有任何关系。如同在自然科学当中一样,例如,对于一位化学家来说,黄金和铁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特殊的内在价值,不过是不同的元素而已。所谓价值问题,仅仅存在于他的研究成果之中,而不是在研究对象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作品的科学”将隐藏内在的悖论,因为作品是根据对象的价值来判定的,而科学本身却不能为对象确定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科学将把它的对象确定为价值中立的“文本”,不管所研究的是荷马史诗,还是民间故事或报纸新闻,不必考虑它们有什么审美价值,面对科学,它们都是文本。
与此同时,结构主义要超越具体的作品,达到普遍的结论,他们设想的文学研究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其结论应当是普遍原则,而不是只能对某个特定的对象才有效。巴尔特在《真实与批评》这样来定义文学科学的对象:“必须重新分配文学科学的对象。作者、作品仅仅是以语言为视域的分析的起点而已:不可能有但丁的科学、莎士比亚的科学或者拉辛的科学,只可能有话语科学。”[11]因此,传统批评中的最重要的作者要素在这些批评中都消失了,弗朗索瓦·多斯在《结构主义史》中回顾说:
人们越来越用文本的结构性取代对作品产生过程的探究,功能的概念取代了作品的概念,而且在文学分析中围绕内在性(immanence)的概念使用俄罗斯形式主义的观点。把这些不同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是同一个规划,就是在语言学的模式之上进行研究,一方面要消除直到那时为止文学中最重要的“创造者主体”(sujet créateur)的角色,另一方面赋予文本的整体结构以最重要的地位,这个整体结构的内在合理性与作者的主观性没有关系,因为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对此并不明白[12]。
这样,价值、作者和美学三个要素都被结构主义批评置于一边,“作品”概念也就丧失了立足之地。取而代之的是文本,作为结构主义的科学研究对象,它无关价值、作者和美学,而只有客观的确定性。
“作品”概念所遭受的第二击则来自后来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先锋派文本理论,在这场争论中,文本不再意味着价值为零度的客观性,也不纯粹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成为与传统文学价值相对立的另一极。如果说在结构主义批评中,文本取代作品是因为价值的中立,它身上没有负担意识形态和美学价值判断的重负。那么在后结构主义的批评中,文本与作品的对抗恰恰在于“文本理论”(théorie textuelle)在它身上赋予了反叛的价值。70年代初的巴尔特把作品和文本之间传统的价值关系彻底翻转过来,作品不再是作者与读者精神交流的汇聚之所,也不是神秘的艺术谜题,也没有任何内在的属于它自身的价值,而只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出发点,读者可以不受拘束地加以利用,进行种种文本实践(pratique textuelle)。而这种实践中的文本,不再是作品的精神价值的物质承载物,而是更加神秘的语言革命中的实践行动,它并非具体的文字,而是一种永远变动不居的过程。巴尔特完全赞成克里斯特瓦对文本的定义。
茱莉亚·克里斯特瓦对文本的定义基于认识论的目标:“我们把文本(Texte:大写)定义为一种超语言学的装置,它重新分配语言的范畴,把本来用于直接传递信息的言语与以前或同时代的其他言辞联系起来……”[13]此后,人们就不再从文本走向作品,而是从作品走向文本,因为是文本确定了作品的位置,……文本使人们可以根据作品的意指活动(signifiance)的强度来确定作品的价值[14]。
巴尔特和克里斯特瓦所定义的文本绝非价值中立的客观物,而是要起到颠覆话语秩序的实践方法。在后结构主义看来,作品是话语秩序的产物,一个书写的结果之所以成为作品是因为现存意识形态承认其价值和身份,为了颠覆这个意识形态和话语秩序,必须以作品为出发点,摧毁其意义的建构,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对它进行语义学的操作和实践,破坏它在传统中的位置,从而实现语言的革命,这就是所谓意指活动。“从作品走向文本”,也就意味着从话语秩序走向对秩序的破坏和越界(transgression)。
巴尔特的《S/Z》就是这种破坏和越界的典范之作。他对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的操作既不是解读和阐释,也不是批判,而是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寻找突破的可能性,通过《S/Z》的一段段别出心裁的插话,他把自己的书写重新编织(文本的原义就是编织)《萨拉辛》,从而对原来的作品在语义学上进行了重新的分配,巴尔扎克小说中语句,原本看上去浑然一体,此时它们的相互关系却被拆散,加入了碎片般的意义的星云。此时的巴尔特不再是结构主义时期的研究者,而是破坏旧话语秩序的行动者。既然是实践活动,那么价值就再度成为关键所在。巴尔特更进一步在“经典的作品”或“可读的文本”(texte lisible)和“可写的文本”(texte scriptible)或“不可读的文本”(texte illisible)之间划定了相反的价值。
价值评估所寻找的价值是:能够在今天被写(被重写)的:“可写的”。为什么可写是我们的价值?因为文学工作(作为工作的文学)的关键是把阅读者变成文本的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我们的文学被文学制度可怜地分裂了:文本的生产者和使用者,文本的所有者和顾客,作者和读者。读者陷入一种轻浮、不及物之中,或者说:他们是严肃的(sérieux):他们不愿游戏,不进入能指的链条中享受书写的快感,而仅仅只保留了最可怜的一点点自由:要么接受要么拒绝阅读文本,阅读成为全民公决。可写文本的对面是反面的和反动的价值:可以被读,而不是被写的:可读的文本。我们把一切可读的文本都称为经典(classique)][15]。
先锋的文本与经典的作品成为针锋相对的文学价值观念的代表,可写的文本意味着不断重新再来,永远也没有终点,是新的文字游戏绵绵不绝的出发点,变动不居和漂浮成为文本实践的理想状态,一切固定化的东西都在“重写”中消融和变形。巴尔特对“可读文本”和“可写文本”的区分确立了一种新的价值——反对一切价值体系。然而,他所定义的“可写文本”始终具有某种神秘色彩,他并不能确定什么样的文本是“可写”的。当然索莱尔斯的小说可以算是。然而,经典作家的文本就一定只能是可读文本吗?假如巴尔扎克那样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所写的都是可读文本,那么巴尔特不是也能够通过他的操作把它变成可写的或曰不可读的吗?假如一切文本都可能进行这样的操作,只要我们在游戏中拆解、颠覆、编织语言,岂非一切文本实际上都能成为可写文本?巴尔特并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只是说:“可写的文本不是一件东西,不能在书店找到。而且其模式是生产性的而不是表现性的,它消灭一切批评,它生产……可写的文本是无穷尽的现在……可写的文本是我们正在书写(nous entrain d'écrire)……”[16]也许,我们不应当把可写的文本看做可以读到的文字,而是一种与传统的文学观和文学制度相对立的文学观,它的首要特征是反文学制度、反价值体系,只要在这种操作之下,一切可读的作品都可以被改造成可写的文本。
巴尔特没有确定什么是可写文本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因为索莱尔斯等先锋作家将来也会经典化,如同巴尔特自己的书写一样,曾经的先锋将变成今天的经典,人们会把他们也按照作家与作品的模式加以解读和阐释,曾经的不可读会变得慢慢可读起来。真正的颠覆性不能依赖印刷在纸面上的文字,文本的意指活动依赖的是不断“重写”,因此,没有哪个固定的文本可以被称为“可写的文本”,与其说它是一个具体的书写产品,不如说是没有终点和永无停歇的意指实践和生产过程。
三、结语:作品的回归与文本的多样化理解
六、七十年代的法国文学理论是一场颠覆、反叛和革命的暴风骤雨,作品与文本这两个概念的命运是其风向标,作品概念的危机实际上是整个文学制度的危机。文学理论的革命不同于以往文学史上的任何一次变革,二战以前的文学争论中,人们所讨论的问题是:这种作品还是那种作品更好?哪种作品更有价值?诸如此类。然而,在六、七十年代的理论风暴中,被质疑的是文学本身:不再是这种或者那种价值的问题,而是文学的价值体系是否有合法的理由存在。从作品到文本,绝非简单的词汇和概念变化,更不是术语的新潮和流行问题,而是动摇了传统话语秩序的基础。直到今天,当人们提起“文学是不是死亡”的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三四十年前那场理论爆炸的回响,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文学作品”如何存在,它的合法性来源到底在哪里?
今天,作品的概念终究没有真正死去,虽然先锋理论家们已经早就宣布了它的葬礼。甚至“文本理论”的旗手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最后几年的研讨班和授课中,重提“作品”,在1978—1980年的研讨班上,他提出要准备写一部文学作品(uvre littéraire:大写)。因为他发现:“某种东西在我们的历史中游荡:文学的死亡;它就在我们身边徘徊;必须注视面前的这个幽灵,从我们的实践开始……”[17]虽然巴尔特自己的文本理论在“文学”的头上悬起一把铡刀,但是文学的死亡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重归作品,重归价值⑩。在80年代以后,无论是法国还是西方文学批评和理论界,“作品”又重新回归批评话语,保持了传统的涵义。而“文本”概念则变得非常复杂,大致说来,西方的文学批评和文论中有这几种情况:第一,在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的文学批评中,文本与作品保持了曾经的和谐关系,文本是作品的书面文字确定性的保证,也是语文学的基本对象,文本分析的目的是进一步探讨作品的精神和美学价值。第二,在继续以语言学工具探索文学话语的普遍规律的学者那里,文本依然是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文本研究目的是掌握整体文本的结构。第三,继承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批评家依然不愿承认“作品”的权威,继续使用“文本”概念来反对固化的价值体系和话语秩序。第四,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一切表意的文化产品都被视为“文本”,一部电影,一幅画,甚至一种时装都是文本。这一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中国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如前文所述,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对“文本”概念的运用和理解与西方的texte有所区别,许多学者对“文本”与“作品”的差异不甚了了,尤其是对这两个概念在不同层面上的联系和对立不太清晰,以至于在大部分情况下,文本成为作品的替代词语,是学术时髦的标志。实际上,在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中,对概念的运用和理解有所不同,这本身是常见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差异缺乏足够的了解,就会造成种种误读,阻碍对历史语境的还原和探讨。虽然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文本理论”在中国也激发过理论的热潮,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研究还不够细致,其理论和思想资源有待进一步的梳理和挖掘。
注释:
① 由于本文参考的西方文论中,法国的理论占有突出地位,因此所引用的外语词汇更多的是法语拼写。
② 此处所说的新批评不是美国的新批评(new critics),而是指法国二战以后兴起的各种新的批评潮流(nouvelle critique),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反对传统文学史批评方法。
③ 参见Roland Barthes,De l uvre au texte [J].Revue d' esthétique,3e trimestre 1971,repris dans ? uvres complètes,édition établie et présentée par ? ric Marry,t.lI,Paris,le Scull,1993.
④ 例如《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本文诗学”论》依然使用本文作为text的翻译。屠友祥翻译的《S/Z》和《文之悦》都采用“文”这个单音词来翻译texte,虽然应当肯定屠先生试图沟通中西古今的努力,但是应当看到中国古代的“文”与法语中的texte在涵义上有很大差异。
⑤ 参见傅修延:《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第6章至第9章。
⑥ 在法语中,复数的lettres比texte更接近中国古代的“文”,有文采之意,也可指称文学。《Littré法语词典》就把中国古代的文人翻译成lettré。而texte在西方传统中是没有价值判断色彩的,因此不宜与中国古代处于价值体系崇高之处的“文”进行互译。
⑦ Gérard Genett,Du Texte àl' cEuvre [J].Entretien avec Gérard Genette,le Débat,1999,Janvier,p.170-182.
⑧ 参见:Ferdinant de Saussure,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M].édition critique et préparée par Tullio de Mauro,Paris,Payot,1972.
⑨ 参见Communications °8 [J].réédition sous le titre L'analyse structurale du récit,Paris,le Scull,coll.Points,1981.
⑩ 参见Antoine Compagnon,les Antimodernes de Joseph de Maistre à Roland Barthes[M].Gallimard,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