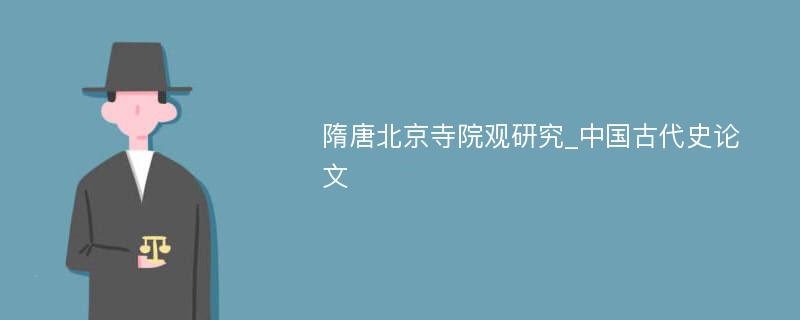
隋唐两京寺观丛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寺观论文,隋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205(2011)02-098-08
寺院与道观是隋唐两京重要的建筑群体。由于历史记载不清晰或历史文献传抄过程中造成的信息讹误、遗失,今人对于一些重要寺观的基本认识有模糊不清之处。澄清某些寺观的具体位置以及寺观的名称变化,是了解这些宗教建筑所处自然与人文环境、历史沿革的基础工作。本文对于时贤的研究拾遗补阙,不足之处,祈望方家教正。
一 隋代清禅寺遗址的性质
清禅寺位于长安通化门内兴宁坊南门之东,由隋文帝(541年-604年)在开皇三年(583年)为昙崇(515年-594年)建立①。1986年6月4日,榆林地区驻西安办事处在基建中发现隋代遗物,郑洪春报告了遗址的结构、出土遗物并公布已经破碎的砖志上的墨书楷体志文,将遗址的性质判定为清禅寺僧侣墓②。徐苹芳认为这是舍利塔基所在③,王亚荣称之为“舍利地宫”④,辛德勇认为是“塔基地宫”⑤。都对遗址的性质做了新的判断,但没有提出论证。另外,董理认为出土遗物中的棋子实为双陆⑥,有助于进一步判断整个遗址的性质。遗址出土砖志志文如下:
大隋开皇九年,岁星在东井,次皇龙入大□十月□□□十一日京师于兴宁坊清禅寺主人德□□□昙崇,从八年敷化四方弟子等,出砖石聚运,迄今起基,发自泉营筑。安舍利佛骨八(六?)粒,并诸亡宝,定□基下,广渐造修。累积达教岁始成□□内大□杜崇,遂聘儒林大夫□尤□□□□深可谓□□阿育王普妙塔者哉。□谷十月十一日雍州大兴县老界福化盘内,建立十级浮图。⑦
郑洪春认为“清禅寺主人德□□圆寂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圆寂后,于公元589年10月11日将舍利骨灰埋在大兴城兴宁坊清禅寺内”。作出这样的判断,是由于志文中僧人的名字没有识读出来。德之后的三字虽然无法识读,但“昙崇”二字却可辨认。这样,仍然可以判断砖志所指的清禅寺主人为昙崇。根据《续高僧传》卷17《隋京师清禅寺释昙崇传》,昙崇在开皇十四年(594年)去世之后,被葬于终南山至相寺之右。显然,清禅寺不是他的墓葬地。砖志志文提供的信息并非是僧人“德□”的生平经历,而是佛塔修建之前的筹备、掩埋佛舍利以及寺院财宝的经过。
道宣《续高僧传》记载清禅寺佛塔建立的经过可以与此相互比较:
开皇之初,敕送绢一万四千疋、布五千端、绵一千屯、绫二百疋、锦二十张,五色上米前后千石。皇后又下令送钱五千贯、毡五十领、剃刀五十具。崇福感于今愿,流于后望,建浮图一区,用酬国俸。帝闻大悦,内送舍利六粒,以同弘业。于时释教初开,图像全阙。崇兴此塔,深会帝心。敕为追匠杜崇,令其缮绩,料钱三千余贯,计砖八十万。帝以功业引费,恐有匮竭,又送身所著衣及皇后所服者,总一千三百对,以助随喜。开皇十一年,晋王镇总扬越,为造露盘并诸庄饰。十四年内,方始成就。举高一十一级,竦耀太虚,京邑称最。⑧
砖志与道宣的记载有若干共同点。如昙崇是佛塔的筹建者,工匠杜崇为营建主持人,佛塔的主要材料为砖,推测该塔是砖结构。佛塔地宫中藏有舍利,舍利数量不一致,六与八形近,容易致误,但无法确定正确的数目。《续高僧传》具体指出舍利来自宫中。砖志与道宣的记载也有不同的地方。例如,砖志强调昙崇向僧俗弟子筹集物资,《续高僧传》则记载佛塔建造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皇室;砖志提供了舍利塔初建的情形,昙崇自开皇八年(588年)就开始筹措,计划是建十层塔。《续高僧传》记载开皇十一年(591年),清禅寺得到晋王(杨广)的供养,建造佛塔的露盘。开皇十四年(594年),营建工程完成,建成后的佛塔为十一层。砖志完成于开皇九年(589年),表明佛塔初建时的情形,《续高僧传》则增加了开皇九年(589年)之后营建中遇到的变化。这两条文献资料生动说明了清禅寺佛塔建造的经过。
昙崇之外,另一位僧人慧胄(569年-627年)也参加清禅寺的创建与经营活动⑨。根据道宣的记载,慧胄“后住京邑清禅寺。草创基构,并用相委,四十余年,初不告倦。故使九级浮空,重廊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圆成。所以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硙,库藏盈满,莫匪由焉。京师殷有,无过此寺。终始监护,功实一人。年至耳顺,便辞僧任,众以勤劬经久,且令权替。及于临机断决,并用咨询”⑩。从慧胄的活动看,他参与清禅寺的开创,并且是寺院事务的实际经营者,但他进入清禅寺时不足二十岁,资历远不能和昙崇相比,与皇室、贵族的交往以昙崇为主。砖志提到“清禅寺主人昙崇”,也反映了昙崇在佛塔营建中的主要地位。
从清禅寺出土遗物看,其中有佛像、传世玉琮、玉猪、玛瑙、水晶饰物、金饰、萨珊玻璃器、货币等,表明这一寺院在得到皇室持续供养的情形下,聚集多种宝物(11)。结合砖志所称的“安舍利佛骨八(六?)粒,并诸亡宝,定□基下,广渐造修”,可以判定这是清禅寺佛塔的地宫。
二 隋代静觉寺的位置
自小野胜年以来,学者一直将隋代静觉寺的位置考订在曲池坊(12)。王亚荣搜集考察了隋代大兴城各坊里的寺院,也将静觉寺置于曲池坊(13)。
王先生的依据是道宣《续高僧传》中的有关记载。其一是卷7《周渭滨沙门释亡名传》附僧琨传:“后于曲池造静觉寺,每临水映竹,体物赋诗,有篇什云。”其二是卷26《隋京师静觉寺释法周传》:“初住曲池之静觉寺。林竹丛萃,莲沼盘游。纵达一方,用为自得。京华时偶,形相义举。如周者可有十人,同气相求,数来欢聚。偃仰茂林,赋咏风月。时即号之为‘曲池十智’也。”
这里首先涉及对“曲池”概念的理解问题。道宣在同书中提及曲池的其他记载有卷2《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彦琮传》:“炀帝时为晋王,于京师曲池营第林,造日严寺。”卷4《京大慈恩寺释玄奘传》:“初于曲池为文德皇后造慈恩寺。”卷9《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道庄传》:“晚出曲池日严本室,又讲《法华》。”卷11《唐京师延兴寺释吉藏传》:“逮仁寿年中,曲池大像举高百尺,缮修乃久,身犹未成。仍就而居之,誓当构立。”卷29《周鄜州大像寺释僧明传》:“(晋王)及登储贰,乃送于曲池日严寺。”显然,慈恩寺与日严寺都不在曲池坊,而分别在晋昌坊与青龙坊。曲池,在道宣文中指的是以曲池为中心的一片地区。同样道理,静觉寺也未必就在曲池坊,但必定位于曲池所流经的地区。
笔者认为静觉寺故址在晋昌坊。从环境上说,不同的文献对静觉寺周边自然景观的记载是一致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慈恩寺建立时的情况:“于是有司详择胜地,遂于宫城南晋昌里,面曲池,依净觉故伽蓝而营建焉。”(14)这一隋代的净觉寺面对曲池;段成式记载:“慈恩寺,寺本净觉故伽蓝,因而营建焉。”(15)
最近,郭声波对隋唐长安水利设施进行了复原研究,指出流经慈恩寺的曲江水面是曲江西支(16)。
清人徐松已经注意到唐人在记载延康坊的静法寺时将“静”、“净”两字混用的情况:“‘静’一作‘净’。《名画记》:净法寺有张孝师、范长寿画。”(17)同样地,唐人也会将静觉寺的“静”写成“净”。综上,本文将静觉寺的故址考订在晋昌坊。《长安志》卷8晋昌坊条记载:“半以东,大慈恩寺。隋无漏寺之地。武德初废。”(18)表明晋昌坊在隋代同时有无漏寺和静觉寺两座寺院。重新确定静觉寺的位置,不仅澄清晋昌坊在隋唐之际的佛教历史沿革,也可清晰了解大慈恩寺周边的自然环境。
三 恒济寺的名称沿革
《宋高僧传》卷14提到两位著名的律僧怀素和道成,他们隶属于恒济寺。但恒济寺位于何处,语焉不详。其实,恒济寺就是弘济寺。
明成化本《长安志》卷9“昭国坊”记载:“西南隅,崇济寺,本隋修慈寺,开皇三年鲁郡夫人孙氏立。贞观二十三年,以尼寺与慈恩僧寺相近,而胜业坊甘露尼寺又比于崇济僧寺,敕换所居焉,本‘弘’字,神龙中改。”(19)
弘济寺本来在胜业坊十字街北之西。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由于该寺与甘露尼寺相邻,而位于昭国坊的修慈尼寺又与南面晋昌坊新建的大慈恩寺相邻,因此朝廷将弘济寺与修慈尼寺的位置作了调整。由此可以知道,怀素等人隶属的弘济寺,在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迁入昭国坊。
关于这一事件的时间,《长安志》卷9两处的记载有不同。在昭国坊下记为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而在胜业坊下则记为贞观二十年(646年)。此处采用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的记载,因为这一年五月唐太宗去世,朝廷对京城寺院作了调整,如《长安志》卷9记载:“贞观二十三年,徙济度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以其所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徙道德寺额于嘉祥坊之太原寺。以其所为崇圣宫,以为太宗别庙。”
弘济寺以律学见长。贞观七年(633年),律师智首的弟子慧满任弘济寺上坐,慧满在此“专弘律训,奖导僧徒。丞有成规,旁流他寺”(20)。道宣除了短期参加玄奘主持的翻译事业外,主要在西明寺或终南山的丰德寺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在长安期间,他在弘济寺也有讲学、弘法活动。段成式记载:“(弘济寺)东廊从南第二院,有宣律师制袈裟堂。”(21)显庆三年(658年),道宣被任命为西明寺上座,他汲引弘济寺律学僧道成、怀素等随之到西明寺,促成律学在高宗和武后时期的繁荣。乾封二年(667年),道宣在终南山创立戒坛,怀素参加了这次活动(22)。唐中宗神龙时,为避孝敬皇帝李弘的讳,弘济寺改为恒济寺。唐穆宗时,为避帝讳“恒”,又将“恒”字改为“崇”,所以,段成式在会昌后期访问这一寺院时记述为崇济寺。
四 崇先寺所属都市
垂拱四年(688年)正月,武则天在神都建立祭祀唐高祖、太宗和高宗的太庙,另立崇先庙祭祀武氏祖先(23)。永昌元年(689年)二月,武则天建立崇先府的官署机构(24)。关于崇先府的位置及其演变经过,学者之间有不同的看法。雷闻推测崇先府最初建立在长安永兴坊,长寿二年(693年)窦家落难之后,辅兴坊的窦诞宅改建为崇先府,他确认《唐会要》卷48所记载的崇先寺不在辅兴坊,具体位置不详(25)。陈金华在《哲学家、实践家、政治家:法藏的多重身份》一书中,结合《唐会要》卷48的崇先寺条与卷50的玉真观条,编制了窦诞宅在武周至玄宗时代的演变史,认为长安辅兴坊崇先府先改为崇先寺,景云元年(710年)改为玉真观,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又恢复为寺院,名称是崇先寺(26)。可是,玉真公主(692年-762年)是玄宗时期皇室中有影响的奉道成员(27),将玉真观改建为寺院是不合情理的。
笔者认为,应当从唐代前期两京制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永昌元年(689年)二月所建崇先府当在神都洛阳。根据《资治通鉴》卷204永昌元年(689年)二月丁酉条,武则天发布诏令的地点在神都,因此,首先会在神都建立崇先府。从《唐会要》卷48的记载体例看,该卷所记寺院沿革,前一部分为长安的寺院,从宁仁坊龙兴寺条以下转入记载东都部分。崇先寺条虽然没有记载坊里名称,但却放在洛阳部分,这说明崇先寺所属城市在洛阳,而不在长安。
再从记载内容看:“崇先寺。证圣元年正月十八日,以崇先府为寺,开元二十四年九月一日,改为广福寺。”崇先寺在武周时代是重要的国家寺院。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十月,崇先寺上座法宝、都维那文彻就参加佛授记寺举行的刊定佛经目录工程。此后,该寺僧人法宝、神英、道琳等参加两京地区多部佛经的翻译。敦煌出土多件武周时期的佛经写本,其尾题中有崇先寺僧人的名字(28)。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崇先寺改名为广福寺。之后,该寺院在玄宗、代宗时代仍有重要的地位。据《大唐东京大广福寺故金刚三藏塔铭并序》,金刚智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八月卒于大广福寺。东都广福寺一名还见于《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7。周一良指出赞宁《宋高僧传》卷1《唐洛阳广福寺金刚智传》所记卒年的错误,但说广福寺一名仅见于《金刚智传》(29),不确。
笔者推测崇先寺可能位于东都洛水南岸的旌善坊。据《河南志》“旌善坊”条记载:“唐有崇化寺,宁王宪宅,本安乐公主宅。”(30)崇先寺一名在抄写中可能误写为崇化寺。根据福山敏男、唐雯的研究,《河南志》这部分记载间接来自于韦述成书于开元十年(722年)的《两京新记》(31)。韦述记载时,这一寺院还没有改名为广福寺。
五 两京地区武氏外家纪念性寺观名称沿革
随着武则天逐步走向权力巅峰,两京地区兴建了纪念武氏外家的寺院与道观。这些寺观由武氏外家住宅改建而成。位于长安颁政坊西北隅的崇福观,本是隋杨士达的住宅,咸亨元年(670年)九月二十三日,改建为道观。陈寅恪指出,武则天的母亲杨氏为隋宗室观王雄弟始安侯杨达之女,因而武则天奉佛有家世渊源(32)。将武氏外家住宅改建为道观,至少不能说是佛教渊源,这一做法是隋文帝以来都城地区国家寺观并建模式的延续。
昭成观的名称沿革有不同的记载。雷闻梳理颁政坊太清观、大业坊太平女冠观与金城坊太清观之间的关系(33),惟史料之间的承袭关系尚需进一步辨析。《唐会要》记载:“昭成观,颁政坊。本杨士建(达)宅,咸亨元年九月二十三日,皇后为母度太平公主为女冠,因置观。初名太清观,寻移于大业坊。垂拱二年,遂改为魏国观。载初元年,改为崇福观。开元二十七年,为昭成皇后追福,改为昭成观。”(34)《新唐书》记载:“太平公主,则天皇后所生,后爱之倾诸女。荣国夫人死,后丐主为道士,以幸冥福。”(35)《长安志》卷10记载:“(颁政坊)西北隅,昭成观。本杨士达宅,咸亨元年太平公主立为太平观。寻移于大业坊,改此观为太清观。高宗御书飞白额。至垂拱三年,改为魏国观。载初元年,改为大业崇福观。武太后又御书飞白额。开元二十七年为昭成太后追福,改立此名。”(36)《类编长安志》卷5与此略同,惟“载初元年,改为大崇福观”(37),无“业”字。
《唐会要》与《长安志》的矛盾之处是这一道观的最初名称。根据福山敏男和妹尾达彦的研究,开元十年(722年)之前的史实中,《唐会要》卷48《寺》和卷50《观》与《长安志》相关坊里的记载主要来自于韦述的《两京新记》(38)。既然有共同的史源,记载当不会出现大的差异。《唐会要》记载的“初名太清观,寻移于大业坊”,显然有脱漏。《长安志》卷10记载立观的原因是为武则天母亲祈冥福,名称是太平观,后又将太平观的观址迁到大业坊。这一记载可以得到《长安志》卷7的验证:“(大业坊)东南隅,太平女冠观,本徐王元礼宅。仪凤二年,吐蕃入寇,求太平公主和亲,不许,乃立此观,公主出家为女冠。初以颁政坊宅为太平观,寻徙于此,公主居之,其颁政坊观改为太清观。公主后降薛绍,不复入观。”(39)这就是说,道观最初的名称是太平观,太平观迁址之后,原观至晚在仪凤二年(677年)改名为太清观。
太清观改名为魏国观的时间,《唐会要》记在垂拱二年(686年),《长安志》记在垂拱三年(687年),如果道观与寺院同时改名的话,可能是垂拱三年(687年)。
魏国观改名为大崇福观之后,至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改名为昭成观(40),昭成是玄宗母亲的谥号。为给母亲追福,不仅改变道观名称,也对道观内部进行改造、装饰。《道教灵验记》记载:“上都昭成观,明皇为昭成太后所立,在颁政里南通坊内,北临安福门街,与金仙观相对。有百尺老君像在层阁之中,□折三十尺,像设图绘,皆吴道子、王仙乔、杨退之亲迹。命天下道门使萧邈字玄俗为使以董之。阁上觚棱高八尺,两廊檐溜去地三十余尺。京师法宇,最为宏丽,唯玄都观殿可以亚焉。”(41)又:“玄宗命天下道门兰陵萧邈监造昭成观,既毕,于观为昭成太后追福,修明真道场七日。至第二日,祥云覆坛,天乐奏雨点上,夜有介金神兵三十余人立侍坛侧,空中言曰:孝德动天。皆具以上闻,载其事于萧玄裕传及碑文焉。”(42)以上是颁政坊崇福观的名称演变经过。
东西太原寺在武则天时期是重要的皇家寺院,这里汇集了高僧名德,详细研究这两个寺院的名称沿革,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佛教与政治的关系,而且,由于一些高僧的著作在这里完成,但只提到寺院的名称,没有具体的写作日期,这样,通过寺院的名称可以大体知道这些著作的写作时间。富安敦(A.Forte)、徐文明关注武则天时代的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对东、西太原寺的名称沿革有详细的研究(43)。
先看位于休祥坊的崇福寺的建立与名称演变经过。富安敦的考察是:该寺始建于咸亨元年(670年)九月。依据是:1,《两京新记》卷3:“本侍中、观国公杨恭仁宅。咸亨元年以武后外氏故宅立为太原寺。”2,《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卷1:“至咸亨元年(藏年二十八),荣国夫人奄归冥路,则天皇后广树福田度人。”3,《旧唐书》卷5提到朝廷赠太原王的时间:“(九月)闰月壬子,故赠司徒、周忠孝公士彟赠太尉、太子太师、太原郡王,赠鲁国忠烈太夫人赠太原王妃。甲寅,葬太原王妃,京官文武九品已上及外命妇,送至便桥宿次。”由此可以确定:太原寺的建立不可能早于咸亨元年(670年)九月。
富安敦未对《唐会要》的记载作考辨。《唐会要》卷48《寺》记载:“崇福寺,林(休)祥坊,本侍中杨恭仁宅。咸亨二年九月二日,以武后外氏宅立太原寺。垂拱三年十二月,改为魏国寺。载初元年五月六日,改为崇福寺。”(44)《长安志》卷10的记载与此类似:“(休祥坊)东北隅,崇福寺。本侍中、观国公杨恭仁宅。咸亨元年,以武皇后外氏故宅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改为魏国寺。载初元年,又改为崇福寺。寺额武太后飞白书。”(45)
根据S.5319《妙法莲花经》卷3尾题,咸亨二年(671年)五月已经有太原寺写经,因此,太原寺不会建于咸亨二年(671年)九月,《唐会要》中的“咸亨二年”中的“二”为“元”之误;又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则天的父母亲在咸亨元年(670年)九月十二日才分别得到“太原王”和“太原王妃”封赠(46),九月二日的记载也错误。综上,杨恭仁宅改建为寺院的时间当在咸亨元年(670年)闰九月十二日之后。
光宅元年(684年)九月,“追尊……考士彟为太师、魏定王;祖妣皆为妃”(47)。富安敦认为太原寺没有立即改名为魏国寺,其改名为魏国寺的日期是垂拱三年(687年)闰正月二日。依据是:1,《起信论义记教理抄》引《纲目别记》卷1:“垂拱三年丁亥二月,改西京太原寺为魏国西寺。”2,《起信论义记教理抄》:“垂拱三年闰正月二日,改京太原寺为魏国西寺。”
富安敦找到了一条太原寺名称变化与武则天外家封号变化密切关联的线索,按照这条线索,光宅元年(684年)既然已经追尊“考士彟为太师、魏定王”,那么,太原寺也应该相应地改名,不会到三年之后才改名。英藏敦煌文献提供了改名的线索,S.0083号文书“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罗尼经出经题记”:
出明咒藏六万偈经中,出此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罗尼经具足成就竟。
右此经唐垂拱元年岁在乙酉,在京兆长安魏王西寺三藏地婆诃罗法师,为诸修道行人僧等,请问要法,为其译出,恐年代夐远,莫知所由,故抄记时代年处,后人体之。(48)
据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撰定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1:“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罗尼经一卷(四纸),右大唐垂拱元年地婆诃罗于西京西太原寺译。”文书提到的“魏王西寺”必是“西太原寺”无疑,这不仅补充了富安敦的考证,也为他归纳的线索找到另一条证据。
永昌元年(689年)二月,“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49)。据上引《唐会要》卷48(50)、《长安志》卷10记载,载初元年(689年),魏国寺改名为崇福寺。然而,武周时期的碑铭或文书的题记提到这一寺院时使用的是“大周西寺”一名,目前还没有发现“崇福寺”一名同时存在。富安敦倾向于在这一期间同时使用了“崇福寺”和“大周西寺”两个名称。藤善真澄认为这一期间只有“大周西寺”一个名称(51)。笔者赞同藤善真澄的观点。《唐会要》与《长安志》的记载来源于《两京新记》,而韦述可能会避免提及“大周”这样的字眼,因而略去武周时期的大周西寺这一段史实。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被迫退位。二月,中宗颁布《即位赦》:“业既惟新,事宜更始,可改大周为唐。社稷宗庙,陵寝郊祀,礼乐行运,旗帜服色,‘天’、‘地’等字,台阁官名,一事已上,并依永淳已前故事。其神都依旧为东都,北都依旧为并州。”(52)
据此,带有“大周”国号的大周西寺改名为西崇福寺。同年,中宗在《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中提到了这一寺院的新名称(53)。
上元二年(675年),东都教义坊的杨氏故宅改为太原寺,后迁移至上东门内的积德坊。辛德勇对此有明确考辨(54)。证圣元年(695年),太原寺名为“大周东寺”(55)。P.2314《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进表及总目》提到长安的大周西寺及神都大福先寺(56)。圣历二年(699年),东、西太原寺分别称为“大周西寺”和“大福先寺”(57)。
武氏纪念性寺院扩至全国主要城市,道观也有向地方扩展之势。例如,荆州在圣历二年(699年)建有武则天题名的大崇福观(58)。
注释:
①[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0,《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0页。
②郑洪春:《西安东郊隋舍利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第61—65页。
③徐苹芳:《中国舍利塔基考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收入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417页。
④王亚荣:《隋大兴城佛寺考》,《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1期。收入王亚荣:《长安佛教史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注3。
⑤辛德勇:《隋大兴城坊考稿》,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27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⑥董理:《“隋琉璃、玛瑙围棋子”考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第71—75页。
⑦郑洪春:《西安东郊隋舍利墓清理简报》,第64页图5,第65页录文。其中,昙,郑录为手写体;东井,郑录为“车井”,均从辛德勇录文改。敷,郑录无,据图版补。达数,郑录为手写体,从辛德勇录文改。杜,郑录为“社”;州,郑录为“城”,均据图版改。
⑧[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7《隋京师清禅寺释昙崇传》,[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9年-1934年,第568页。
⑨[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43页;辛德勇:《隋大兴城坊考稿》,第24页。
⑩[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9《唐京师清禅寺释慧胄传》,第697页。
(11)齐东方:《佛寺遗址出土文物的几个问题》讨论六朝至隋唐佛寺遗物的定名、外来文化的影响等,胡素馨主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第81—96页。
(12)[日]小野胜年:《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资料篇》,(京都)法藏馆,1989年,第145页;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97页。
(13)王亚荣:《隋大兴城佛寺考》,《长安佛教史论》,第101页。
(14)[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9页。
(15)[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续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2页。
(16)郭声波:《隋唐长安水利设施的地理复原研究》,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3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15页。
(17)[清]徐松撰,[清]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0页。
(18)[宋]宋敏求:《长安志》卷8,第117页。
(19)[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卷5“崇济寺”条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7页;辛德勇:《〈唐两京城坊考〉述评》,《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4页。
(20)[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2,《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618页。
(21)[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续集卷6,第260—261页。
(22)[唐]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卷1,“京师弘济寺怀素律师”,《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5册),第817页。
(2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25《礼仪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44—945页;[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资治通鉴》卷204,垂拱四年正月甲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47页。
(2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8页;《资治通鉴》卷204,永昌元年二月丁酉条,第6457页。
(25)雷闻:《玉真观的前身:窦诞宅——崇先府》,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0—242页。
(26)Chen Jinhua,Philosopher,Practitioner,Politician:The Many Lives of Fazang,Leiden:Brill,2007,p.401,note 44.
(27)丁放、袁行霈:《玉真公主考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41—52页。
(28)池田温:《中国古AI写作本识语集录》,(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243、244、247、258、262、264、273、274页。
(29)Chou Yiliang."Tantrism in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8(1945),pp.282—283,note 56—57.
(30)[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7页。
(31)[日]福山敏男:《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中国建筑と金石文の研究》,第168页;辛德勇中译文:《两京新记解说》,[唐]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第5页;唐雯:《〈两京新记〉新见佚文辑考——兼论〈两京新记〉复原的可能性》,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
(32)陈寅恪:《武曌与佛教》,《“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本第2分,1935年,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2页。据[唐]魏征等:《隋书》卷43《观德王雄传》,杨雄弟士达,左光禄大夫;子恭仁,隋吏部侍郎,(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17—1218页。
(33)雷闻:《唐长安太清观与〈一切道经音义〉的编纂》,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0—213页。
(34)[宋]王溥:《唐会要》卷50《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27页。
(35)《新唐书》卷83《太平公主》,第3650页。
(36)[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0,《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5页。
(37)[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卷5《寺观》,第145页。
(38)[日]福山敏男:《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中国建筑と金石文の研究》,(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83年,第167页;辛德勇中译文,[唐]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页;[日]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39)[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第112页。
(40)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上篇《西京》,(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41)[唐]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1《上都昭成观验》,《道藏》(第10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第802页。
(42)[唐]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14《玄宗昭成观验》,《道藏》(第10册),第849页。
(43)Forte,A.,“The Chongfu-si(崇福寺)in Chang’an.A Neglected Buddhist Monastery and Nestorianism” in Paul Pelliot,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edited with supplements by Forte,A.,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and Collège de France,Kyoto and Paris,1996,pp.456—460;Forte,A.,“The Great Fuxian Monastery in Luoyang:A Forgotten Center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in Benn,James,et al.,eds.,Monasticism:Asian Perspectives,Forthcoming徐文明:《唐东西太原寺名称演变略考》(未刊稿);徐文明:《太原北崇福寺初考》,2006年8月太原“佛教本土化与晋阳文化嬗变学术研讨会”发表。徐先生赐赠他的研究成果,谨致谢意。
(44)《唐会要》卷48,第991页。
(45)[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0,《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7页。
(46)《资治通鉴》卷201,咸亨元年九月壬子条,第6365页。
(47)《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九月己巳条,第6422页。
(48)池田温编:《中国古AI写作本识语集录》,第234页;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20页。
(49)《资治通鉴》卷204,永昌元年二月丁酉条,第6457页。
(50)Forte,A.,A jewel in Indra’s net:the letter sent by Fazang in China to Uisang in Korea ,Kyoto :Istituto Italiano di Cultura,Scuola di Studi sull’ Asia Orientale,2000,p.64.
(51)[日]藤善真澄:《华严经传の记彼方·法藏と太原寺》,镰田茂雄博士古稀记念会编:《华严学论集》,(东京)大藏出版,1997年,第321页。
(52)[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2,(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6页;《资治通鉴》卷208,第6583页;《旧唐书》卷7作“二月甲寅,复国号,依旧为唐。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第136页。这里的“寺宇”二字,显然是《即位赦》中“等字”的鱼鲁之误,此处可以校正为“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等字、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中宗初即位,改元而未改国号,卫先楷《石浮图铭并序》可证,《全唐文新编》卷260,(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2941页。
(53)S.46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7—198页;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47—350页;Chen Jinhua,“Another Look at Tang Zhongzong’s(r.684,705-710)Preface to Yijing’s(635-713)Translations:With a Special Reference to Its Date”,《ィンド哲学仏教学研究》11(2004),pp.3-27。
(54)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下篇《东都》,第153—154页。
(55)S.2278《佛说宝雨经》卷9尾题;池田温编:《中国古AI写作本识语集录》,第240页。
(56)池田温编:《中国古AI写作本识语集录》,第246页。
(57)S.523《金光名最胜王经》卷8尾题;池田温编:《中国古AI写作本识语集录》,第262页。
(58)[唐]陈子昂:《荆州大崇福观记碑》,《文苑英华》卷822;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1页。
标签: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三国论文; 大正新修大藏经论文; 唐朝论文; 武则天论文; 高僧传论文; 曲池论文; 崇福论文; 唐会要论文; 长安志论文; 两京新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