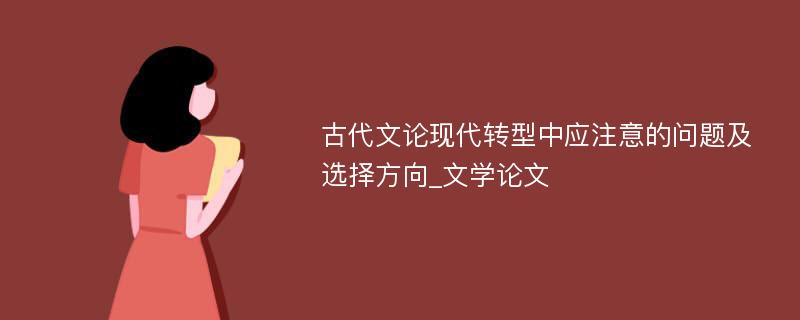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中应注意的问题及可选择的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可选择论文,古代论文,方向论文,中应注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古代文论现代研究的一贯追求。既往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在进行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时候,应警惕泛化倾向,要解决对古代文论本体性的理解问题。在解决对古代文化本体性理解的基础上,坚持向内求深度、向外求形式同时并举,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可以选择的恰当策略。
关键词 古代文论 现代化 比较研究 创造性阐释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古代文论现代研究者魂牵梦绕的理想。为实现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理想,几代学人风雨兼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有令人振奋的实绩,也有启人思索的教训。其中,最值得回味的是50年代和70年代的转换实践。
1956年,为解决文艺思想里的现实论争,茅盾在夜深人静之际,用现代文艺学里的某些观念,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批评进行了大胆的剪裁。《夜读偶记》那几句短短的前言,暗示出茅盾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自觉动机。这一动机,很有几分吸引力。1958年,郭绍虞沿茅盾的思路,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对立为贯穿线索,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了全面地改写。等不到杀青,改写过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上卷就被人拿去作为“跃进”丛书的一种向建国十周年献礼了。尽管多年之后,依然有人固守这一思路,但是,再也未听说过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改写本下卷的写作计划。在以后的岁月里,郭绍虞献给学界的,是一部又一部经过精心选择、精心校点、精心注释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这一转折意味深长,很富戏剧性。它向每一个致力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人提问:究竟什么才真正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过程中的“名山事业”?我相信,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程中,这一问题还会反复被提出来。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或许是最令古代文论感到兴奋的年代。全国的大小报刊,内行外行,都在兴趣盎然地讨论着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比兴。古代文论似乎成了学术话语的中心。那场热闹非凡的讨论,对比兴研究本身的推动尽管十分有限,但它发挥出来的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思想的释荷解缚作用,今日想来,犹觉神往。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中国新时期学术的繁荣,是从那场比兴讨论开始的。一个偶然的机缘,使古代文论成为牵引中国文学、中国学术走向繁荣的“火车头”。偶然引发的“古代文论热”,一方面证明了古代文论具有现代转换的巨大潜力,另方面也显示出在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时候,始终潜在一个将古代文论泛化的危险。泛化的根源,是把古代文论在偶然的机缘中发挥出的作用误认作古代文论的永恒魅力。泛化的标志,是试图从古代文论中发掘中国新文艺学的学术规范。泛化,总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当古代文论无法满足泛化者的要求时,泛化者会毫不犹豫地“适彼乐土”。果然,经过文学理论上所谓的“方法年”、“观念年”的洗礼,古代文论重新退居中国学术的边缘。在短短的不到十年工夫里,古代文论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从“中心”到“边缘”的轮回。这在中国学术史上,并不常见。伦理生活里的世态炎凉,令人尴尬;学术研究里的炎凉世态,却有它水落石出式的明快,有时是促使学术研究走向成熟的契机。
瞻前顾后,在“水落石出”的背景上谈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转换的基础将落实在下述两个层面:其一,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目标进行定位;其二,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操作进行定性。
古代文论的现代研究,应该为建设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服务。这一表述,在一定范围内已经成为可以接受的共识。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可以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目标作如下定位:把古代文论作为对文学原理的一种把握,发掘其价值,彰显其智慧,令其以自己独有的理论威力介入当代文学活动,为繁荣文学,为建设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提供积极的知识和智慧。这样定位,从积极方面说,突出了对古代文论的本体性理解,给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一个明确的方向。实践证明,对古代文论本体性的理解,始终是制约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能否圆满实现的关键因素。这样定位,从消极方面说,确定了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充分施展的最佳位置,可以避免重蹈既往实践中已经看到结果的急功近利的误区、能够预测到结果的盲目自信的误区。
目标定位之后,操作定性就有了明确的尺度。为实现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定位了的目标,在操作上需要“向内”、“向外”两项工夫。向内工夫可以定性为“向内求深度”,向外工夫可以定性为“向外求形式”。
“向内求深度”,首先要解决对古代文论本体性的理解。即在进行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时候,是把古代文论当作对文学原理的一种概括,当作东方智慧的一种形式,还是当作历史空间里某个具体人兴会神到之辞的联缀,某个文学派别文学趣味的汇集,当作西方文论的参照系或补充?如果是后者,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将失去基础。历史空间里某一个人的兴会神到之辞无法复现,历史空间里某一派别的文学趣味无须复现。只有在把古代文论作为东方智慧的一种形式,作为对文学原理的一种概括来对待的时候,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才充满生机。学术是天下公器,人可能有南、北之别,道决无东、西之分。文学之道或文学基本原理古今一贯,东西无别。古今中外的不同,仅仅在于各自根据自己的实践和智慧,用不同的方式提出问题,按不同的途径解决问题。唯其如此,歌德才会提出“世界文学”的理念,李德裕才会产生“譬诸日月”的奇想。唯其如此,“他山之石”才“可以攻玉”,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才有必要和可能。假如希望人们对古代文论有一个深入的本体性理解,就需要把古代文论的思想风采如实展现出来。因而,古代文论范畴的整理、概念的界定、思想脉络的把握、理论是非的澄清、名著名篇的校点注释、批评文献的发掘整理,事虽琐屑,却是关系到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大局的基础工程。郭绍虞未竟的“名山事业”,应该有组织、有系统地接着去做,尤其是在热情期待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时候。“琐屑”工夫不到家,对古代文论缺乏全面深入的理解,真切的本体性认识就无从确立。对古代文论本体性认识失当,现代转换充其量只能是一种为“误解”、“误读”提供通俗证据的行为。
从本质上说,现代转换是对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必须同时兼备文学理论家的器识和文学批评史家的眼光。因而,“向内求深度”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出发点:一个是站在现代文论所遇到的普遍问题的立场,对古代文论深味细察,把握其意义和脉络,品味古人解决问题的方式;一个是站在古代文论的立场,对现代文论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思考探究,显现其智慧和价值,指示今人解决问题的途径。虽然说前一个出发点是还原古代文论的心境,后一个出发点是给古代文论一个理性处理,但这两个出发点却导源于一个共同的动机,即寻找古代文论的普遍形式;奔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激活古代文论的生命。可以说,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中的“向内求深度”实际上是通过深味细察和思考探究,把古代文论各家各派“实际上说的”、“真正意谓的”、“可能说的”与“应该说的”意蕴发掘出来,让它们和现代文论的基本问题接头,在与现代文论的对话中,向现代文论提供积极的知识和智慧,使古代文论在文学实践和文学反思中得到批判地继承和创造地发展。
“向外求形式”的动因,导源于对古代文论重实用而轻反思、重体悟而轻逻辑、重智慧而轻知识的总体特征的正视。当然,“重”、“轻”是与现代文论的理论形态、与西方文论的理论形态相对而言。在中国古代,似刘勰那样专门从事对文学进行理性思考的文论家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文论家是由作家兼任的。一般说来,兼作文论家的作家,既无建立体系的宏愿,又缺严格选择形式的耐心。兴之所至,顺手拈来的形式,例如诗赋、序跋、论赞、书启、家训、问答乃至注释,都可以用来固定自己对文学的体悟与洞见。这一方面使古代文论呈现出自由活泼的姿态,另方面也给古代文论带来了形式散乱的弱点。“形式散乱”并不说明古代文论缺乏真知灼见,相反,形式散乱的古代文论中,随处可见闪光的思想,只不过这些闪光的思想,或如游骑而未归,或如散珠而未串。这种状况,把“耽思旁讯”的任务置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前沿:通过细察把握精神,运用博览征服“散乱”,把淹没在散乱形式中的真知灼见发掘出来,在四面八方的联系中整理出文论家没有充分展开的逻辑关系,给古代文论一个严谨的形式。
“向外求形式”,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所追求的目标之一。“现代转换”中的“现代”,包含“现代意识”和“现代学理”两层意思。文学之道千古一贯,对文学之道的意识却是历史的。所谓“现代意识”,实际上是现代对特别感到有困难的文学基本问题的意识。人只有在实践中遇到特别困难的时候,才去回顾历史,以求获得历史所能赉与的征服特别困难的珍贵馈赠。而对外来(主要是西方)学理的吸收应将现代学理与古代学理区分开来。“现代意识”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动力,“现代学理”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操作。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是用现代学理在现代意识的砧石上对古代文论重新锤炼,使之重新成为披荆斩棘的利器。
“向外求形式”涉及到的虽然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问题,却不是仅靠操作就能圆满解决的,它依然与对古代文论的本体性理解密切关联。1956年茅盾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思想进行大胆剪裁时使用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不能说不是现代学理,70年代末比兴讨论时贯穿的现代意识不能说不强劲,这两场运动,持续时间的长短不同,波及范围的大小有别,但结局却出奇地一致: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那些问题用别的方式也能解决,事实上也是靠别的方式顺畅解决的。)智慧和识见并未随着解决问题增长几分。究其原因,前者或多或少把古代文论当作从正面或反面印证现代文学观念的思想资料,后者或多或少把古代文论当作可以随时打开、各取所需的武库。无论是前者后者,都无意识也不准备把古代文论当作在文学基本问题上可以互相启发、共同切磋的对话伙伴。既往的教训把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向外求形式”时的心态调整问题,呈现在十分醒目的突出地位。在互相尊重、注意倾听的对话氛围中,才能顺利找到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形式,才能顺畅完成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任务。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一场对话。“比较”经常是促成“对话”的有效手段。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应该鼓励对古代文论进行跨学科研究,应该鼓励跨学科的人对古代文论进行研究。《墨经》说“异类不吡”。“比较”首先要弄清比较双方所属的“类”。类属不明,尽管有“比较”这一现代转换的锐利形式,结果也只能引出诸如“战马不会拉车,奶牛不能耕地”之类的谁也不能说错误但谁也不会承认有意义的结论。不妨举一个时过境迁的小例子。在中国,《文赋》第一次把“应感”(略似西方诗学中的“灵感”)作为文学理论中的一个范畴来探讨。“应感”也是现代文论特别感到有困难的理论症结之一,存在着进行现代转换的可能性与迫切性。对陆机的“应感”理论,在一段时间内习惯于用认识论这一现代学理进行转换。这样转换过的“应感”理论,充其量是所谓“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一个标本。这样的转换是毫无意义的敷衍塞责。第一,“应感”理论实际上说的和真正意谓的,并不是彼岸世界究竟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第二,判断陆机认识论的归属,需要更多的资料,《文赋》那几句话不足为据;第三,文学理论家不同于哲学家,不必首先回答彼岸世界究竟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固执审查陆机的认识论归属,实是多此一举;第四,即便判断出了陆机的认识论归属,对“应感”理论中可能蕴含和应该蕴含的文学理论智慧的认识与开掘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影响。“应感”理论的现代转换,另有工夫,另有路头。“向外求形式”,路头一差,愈骛愈远,“所求”不当,劳而无功。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过程中,对古代和现代坚持采取多层面地透视,是防止和克服敷衍塞责的有效手段。因而,多一点“以道观之”、“以物观之”、“以差观之”、“以俗观之”、“以功观之”、“以趣观之”的“齐物”襟怀,学一点“回到事实本身”的现象学方法,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向外求形式”时实在必要。
“向内求深度”、“向外求形式”,是确保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顺畅进行的两项基本功。向内求深度,存在一个开掘浅深的问题;向外求形式,存在一个形式与内容和谐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苦学工夫,又需要思想上的机智。苦学决心,当即可下;思想上的机智,却不是一朝一夕可达。正因为此,才应该突出强调,才值得刻意追求。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妨从这里出发:首先破除急于求成的观念,其次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收稿日期:1996-0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