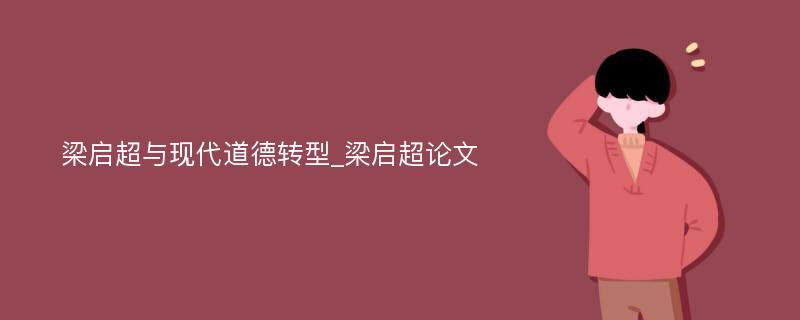
梁启超与近代道德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道德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发生一百周年了。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著名的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运动。这次运动虽然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残酷地扼杀了,但是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在文化上提倡和推动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积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本文则试图对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在提倡和推动传统道德向近代道德转型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批判封建旧道德的鼓手
二千多年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专制统治,突出宣扬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这种封建旧道德在宋明后越来越片面化和僵化,成为禁锢人民的精神枷锁。梁启超为了救亡图存,奋起批判毒化人民的封建旧道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旧道德的要害是抹煞人的个性,束缚人的思想。“中国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实为德育之中心点。”(《新民说·论公德》)而“辱莫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矣。”(《新民说·论自由》)“心奴”是封建旧道德毒害人民的结果。他强调要反对奴性心理,提出一曰,勿为古人之奴隶,二曰,勿为世俗之奴隶,三曰,勿为境遇之奴隶,四曰,勿为情欲之奴隶(见同上)。他特别反对做古人的奴隶,“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此奴隶根性之言。”(《国民十大元气论·独立论》)他以新旧道德的对比,对封建旧道德给予了系统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封建旧道德主“束身寡过主义”、奴隶主义,不讲独立、自由、自治、自尊,不讲公德,不讲权利,不讲利己,不讲刚毅勇武,不讲进取冒险等等。由此可见,封建旧道德为害甚烈,它们是国家不兴、社会不进步的重要原因。为了救亡图存、振兴国家,必须批判封建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并认为这是变法维新的首要任务。由此他提出以新民德、新民智、新民力为内容的“新民说”,并激呼“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新民说·论新民为中国今日第一要务》)。
封建旧道德是造成国民性中的弱点和不良因素的根源,因此,对国民性的批判是梁启超揭露批判封建旧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讲,国民的人心内俗中存在着不良因素: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二曰为我,四曰好伪,五曰怯懦,六曰无动。他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中,又讲我国之品格缺点为:一爱国心之薄弱,一独立性之柔脆,一公共心之缺乏,一自治力之欠阙。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再次认为中国人之缺点在于: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守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梁启超认为,国民性中的这些弱点和不良因素,不适合生存竞争激烈的当今世界,国人必须自觉、猛省,对之加以克服和改造。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批判,其目的是为了适应社会变动的历史要求重建国民文化心理结构,亦即使人的个性发展由“为人的资格”转变为“为国民的资格”。
梁启超之批判封建旧道德和国民性不良因素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批判封建旧道德并不全盘否定传统道德。封建旧道德并不等同于传统道德。传统道德是一个内容宽泛性质复杂的概念。在性质上,它包括着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在内容上,它包括着民族传统美德、人类公共生活道德和为封建宗法等级统治服务的封建旧道德即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近代以来,一些人常将封建旧道德与传统道德混为一谈,一同批判。梁启超的可贵处在于,他一方面抓住封建旧道德的实质给予猛烈和抨击,另方面对传统道德中合理的有价值的东西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批评一些人“摭拾欧美学之一鳞一爪以为抨击之资”(《先秦政治思想史》),指出:“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之上也。”(《新民说·释新民之义》)联系当时在对待传统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的倾向,他的这些认识无疑是很有价值、很可贵的。
二是认为国民性既有不良因素,又有优良因素。在近代,由于西学东渐和国人对世界的逐步了解,人们开始对本民族民族性进行反思和批判。应该说这是民族自觉、自省、自我警策的一种表现。但一些人片面夸张民族性的弱点和不良因素,以为我国民族似乎只有不良因素而没有任何优良因素。这显然是很错误的。梁启超作为倡言批判、改造国民性的先驱者,他不仅对民族性中的弱点和不良因素进行无情的揭露批判,而且对民族性中的优良因素给予了肯定和彰显。他讲:“吾国民性之不良者固多,其良焉者抑亦不少”,并列举出四民平等之思想、自营自助之精神、泱泱乎大国之风等(见《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为国民性的优良因素。他认为,民族性无论其长处和短处都不是绝对的、恒久不变的,而是相对的、与时推移的。在他看来,中国民族中的弱点和不良因素,有许多属于“一时之现象而易治者”(见《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同时也指出,国民性的不良因素主要是由于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如他讲中国人之所以缺乏独立性格,是由于“二千余年俯首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以服从为独一无二之天职”(《新民议·论独立》);在他看来,一旦结束封建专制政体,近代工商业经济发展之后,国民性中的不良因素是可以得到矫变的。所以他满怀激情地讲:“他日二十世纪,我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论中国人种之将来》)。
二、构建近代新道德体系的先驱
梁启超在批判封建旧道德的基础上,借鉴、吸纳西方近代道德和道德思想,并继承传统道德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道德,对构建中国近代新道德体系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尝试。
关于公德与私德。梁启超讲:“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无公德则不能团。”(《新民说·论公德》)他以重公德或重私德作为新旧伦理的分野,“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同上)。他强调公德的社会功能作用。他讲:“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同上)“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新民出焉矣。”(同上)他强调注重“公德”,并不因此而轻忽“私德”。他认为没有私德作基础公德也不能成立。“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同上),所以他强调“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同上)。
关于独立与合群。梁启超讲:独立即“不借他力之扶助,而自然自立于世界者也。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国而不能独立,时曰附庸”(《国民十大元气论·独立论》)。他认为,由于缺乏独立的德性,“乃至一国之人,各各放弃其责任,而惟倚赖之是务”(《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从而造成了国家的不能独立和腐败。因此,他提出欲救治国家,“惟有提倡独立,人人各断绝倚赖……扫拔已往数千年奴性之壁垒”(同上)。梁启超不仅提倡“独立”,而且提倡“合群”。他讲:“群者,天下之公理也。”(《说群—群理》)”合群云者,合多数的独而成群也。”(《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无合群之德,“终不免一盘散沙”(同上)。在“独”与“群”的关系上,他强调“独”服从“群”,“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同上)在他看来,当今世界处于竞争和弱肉强食的时代,只有“养群德”,才能“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同上)。梁启超强调“养群德”也就是强调国民应有“国家思想”,即“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新民说·论国家思想》)。他指出独立与合群并不矛盾,“独立之反面,倚赖也,非合群也;合群之反面;营私也,非独立也”(《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因此,二者可以并存,“以独而扶其群,以群而扶其独”,“知有合群之独立,则独立而不轧铄”(同上)。
关于自由与服从。梁启超讲:“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新民说·论自由》)在他看来,所谓自由就是“排除他力之妨碍,以得己之所欲”(《自由书·论强权》)。与自由相对立的是奴隶,“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新民说·论自由》)。所以,他猛烈批判封建旧道德提倡的“束身寡过主义”、“心奴思想”。梁启超不仅讲“自由”,而且讲“服从”。他讲:“真爱自由者,未有不真能服从者”,“服从者实自由之母”,“服从者亦天下最美之名词,而为国民必不可缺之性质”(《服从释义》)。他认为,如果只讲自由而不讲服从,团体之自由便不能伸张,最终个人之自由也不能牢固。所以不可不讲服从:一曰不可服从强权,而不可不服从公理,一曰不可服从私人之命令,而不可不服从公定之法律,一曰不可服从少数之专制,而不可不服从多数之决议(见同上)。与此相应,他还指出:“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新民说·论自由》)、“自由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等等,强调自由与服从的内在关联。
关于权利与义务。梁启超认为,个人生活于社会群体中,必然要有对社会群体的权利与义务,“权利义务两思想,实爱国心所由生也。”(《新民说·论义务思想》)他认为权利和权利思想是自由国民所必须具备的,否则便丧失了自由国民的资格,“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在他看来,人民具有强烈的权利思想是国家强盛的原因,“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感情之敏锐,即英之所以立国之大原也。”(《新民说·论权利思想》)他批判中国封建统治者摧残人民的权利思想,使之“渐萎废、渐衰颓、渐销铄”(同上),而一国“国民无权利思想者,以之当外患,则槁木遇风雨之类也”(同上)。为了抵御外患、救亡图存,就必须提倡权利思想。“人人务自强以保吾权,此实固其群善其群之不二法门也。”(同上)梁启超认为国民也必须具备义务思想。他所讲的义务,主要是指个人对社会群体应尽的责任。他指出,在中国义务思想虽然发达,但是一种“不完全之义务思想”:一是无权利之义务,犹无偿之劳作;一是私人对私人之义务,无个人对团体之义务(见《新民论·论义务思想》),因此,他强调要培养国民的“公义务”思想。梁启超还指出权利与义务二者是对应的、相均的,“人人生而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生而有应尽之义务,二者其量适相均……苟世界渐趋于文明,则断无无权利之义务,亦断无无义务之权利。……故夫权利义务两端平等相应者,其本性也。”(同上)
关于利己与利他。强调利己、个人利益是近代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思想。梁启超对之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他指出“为我”、“利己”、“私”这些为古义确定为“恶德”者,其实并非“恶德”,“天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弛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因此,他指出,西方的功利主义、“为我”、“利己”的伦理思想,“实有足以助人群之发达,进国民之文明者”。梁启超既讲“利己”,也讲“利他”。他讲人在过群体生活共营生存时,“势不能独享利益”而不顾他人,否则,“则己之利未见而害先睹矣。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而进焉”(同上)。他的这一认识,与西方的“合理利己主义”相类似。梁启超在论述利己与利他的关系时,过于简单而理想他看待二者的统一,从而陷入所谓“举利己之实,自然成为爱他之行;充爱他之量,自然能收到利己之效”(《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之类的空谈。但他也曾讲过“团体之公益与个人之私利,时相枘凿,而不得兼也,则不可不牺牲个人之私利,以保持团体之公益”(《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他还批评边沁讲的自利动机造成利他、利群后果,每不能如其所期,“公益与私益非惟不相和而已,而往往相冲突者,十而八九也”(见《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因此,他讲,人人求乐求利之主义,不可以为道德之标准(见同上)。这表明他的思想有矛盾之处,也表明传统的为公、利他和整体主义的道德论在他思想中的印记。
关于进取冒险。梁启超称进取冒险精神为“浩然正气”。他描述道:“其当时道天下之所不敢道,为天下之所不敢为。其精神有江河学海不到不止之形,其气魄有破釜沉舟一瞑不视之概;其徇其主义也,有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观,其向其前途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其成也,涸脑精以买历史之光荣,其败也,迸鲜血以赎国民之沉孽。”(《新民说·论进取冒除》)他认为这种进取冒险精神对人而言,“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对国家而言,“国有则存,无之则亡”。在他看来,欧洲民族之所以强于中国,其富于进取冒险精神乃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他批判道家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等以及儒家的“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等保守思想,指出,一味倡导这些思想,将使“进取冒险精神,渐灭以尽”(同上)
综上可见,梁启超关于近代新道德的这些论述,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在中国树立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思想,用近代形态的道德取代传统形态的道德。
梁启超讲,他构建近代新道德体系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曰,“淬厉其所本有”;二曰,“采补其所本无”。并认为此二者缺一不可(见《新民说·释新民主义》)
所谓“采补其所本无”,就是参照、借鉴和吸纳资产阶级的道德和道德思想。资产阶级道德是高于封建道德的道德形态,其先进性是自不待言的。向西方学习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称道它,将其介绍给国人,并试图以之为参照改造中国传统道德,以实现向近代的转型,是很自然的事情。梁启超就讲:“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西学书目表·自序》)又讲:“故今日不欲强我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新民说·释新民主义》)他的这些认识反映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但他的可贵处在于,他构建中国近代新道德体系,并没有“心醉于西风”,全盘搬用西学。他指出,“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国民,必非徒以区区泰西之学说所能为力也”(《新民说·论私德》)他还讲:“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文化,一面仍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清代学术概论》),“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将得不偿失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对西方近代道德思想诸如“个人主义”、“现在快乐主义”以及“生物进化论”、“自己本位主义”在社会政治伦理生活中产生的危害,给予了揭露和批判(见《中国道德之大原》)、《欧游心影录·学说影响一斑》。可见,梁启超对待西学的认识和态度是比较全面的、客观的,他的许多讲法,在今天仍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所谓“淬厉其所本有”,就是有分析地提炼传统道德中有价值的东西,以之作为构建近代新道德体系的重要因素。如他所试图构建的新道德体系,既讲公德又讲私德,既讲独立又讲合群,既讲自由又讲服从,既讲权利又讲义务,既讲自己又讲利他,等等,就是很好的说明。他讲:“古今新旧不足以为定善恶是非的标准,因为一切学说,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种含有时代性,一种不含时代性”,对于“不含时代性”的思想道德,“不可以为时代古思想旧而抛弃之”(《儒家哲学》)这里他提出了以是否含时代性作为判定道德能否继承的标准,尽管其在表述上不够标准,但仍然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因为某种道德之所以能继承,即在于它具有不受时代限制的普遍意义。他又从保守和进取的关系上讲传统道德的继承问题。他讲:“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之运用此两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冲突则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新民说·释新民之义》)这里他强调“调和”即保守和进取的并存兼用,他还以行走和拾物为例加以说明,“譬之跃步,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譬之拾物,以一手握,以一手取”(同上)。关于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是近代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但这里梁启超以保守和进取的并存兼用说明道德进步既要创新又要继承,无疑也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采补其所本无”、“淬厉其所本有”,也就是中西思想的结合、融通。在梁启超看来,“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西学书目表·后序》)因此,他强调中西文化的结合。他讲:“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又讲:“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欧游心影录·中国人对世界文明之大责任》)对于怎样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他提出: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保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见同上)。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梁启超就提出这样一些认识,应该说是颇为难能可贵的。
三、梁启超在近代伦理思想史上的地位
从上面谈的两个问题,即可看出梁启超在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过我们还想从其伦理思想的特点、对后人的影响和评价方面再作些说明。
梁启超的伦理思想体现了民族性和爱国精神的鲜明特点。梁启超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宣传家、政治活动家和学者,而且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是他从事政治活动、写作政论文章的出发点,也是他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的出发点。他批判封建旧道德和国民性中的不良因素,论述近代新道德都和爱国、救国联系起来,他热心学习西方文明是出于爱国、救国,他研究和宣传中国传统文明也是出于爱国、救国。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的伦理思想不仅在激励时人的爱国精神和伦理道德观念更新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影响了一代代后人,就是在今天,人们读一读他的包含爱国、救国激情的论著,也会很受教益的。
梁启超伦理思想的又一个特点是,善于把握时代脉搏,富有前瞻性。如他曾提出人类文明发展要解决好两个问题:“其一,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问题,其二,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问题。”(《先秦政治思想史·统论》)可谓高屋建瓴,见识非凡。人类历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道德和文明所面临的仍然是这两个问题,且以更为尖锐的形式摆在人类面前。又如,他在发生于二十年代的“人生观论战”或“科玄论战”中,批评“科学派”过信科学万能,“玄学派”轻蔑科学,“各有偏宕之处”(见《人生观与科学》)。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正确说明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他的“各打五十板”的批评,时常受到非难,以及他参与这次论战的出发点和所持的观点、方法不无问题,然而,他却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在今天,这个问题仍然困忧着世人。由此,我们不能不叹服他的思想的超越性和预见性。
当然,梁启超的伦理思想也有它的局限性。如他夸大道德的决定作用,对传统道德肯定过多,以至想靠祖宗留下来的固有之旧道德挽救社会道德危机,同时,他对一些伦理道德问题的具体论述也还存在矛盾之处。而这些局限性的实质,则是他所代表的阶级的局限性,由于这种局限性,他不可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认识伦理道德问题,因而不可能揭示社会道德现象的深层本质和发展规律。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也正是由于这一局限性,无论戊戍钜子还是辛亥革命代表人物都未能完成传统旧道德向现代新道德转型这一历史任务,也就是说他们在批判旧道德构造新道德这两个方面都未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程度。完备的资产阶级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在中国近代始终未能建立起来。而且由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异常曲折和复杂,也由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同程度的远离群众,他们提倡的新道德新思想也未能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得到实践。然而,尽管如此,他们在这方面的历史性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所遣留给我们的无论是理论思维的积极成果还是失足失误之处,都是很有价值的。
胡绳同志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对梁启超的早期活动曾作过如下的评价:“在戊戍维新运动时期的舆论界中起过显著作用的梁启超”,在戊戍运动失败后他“写了大量文章,以流畅浅显的文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经济学说,歌颂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中的历史人物,鼓吹种种同中国的封建传统相违背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观念。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宣传工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同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分子。读他的文章的人,固然有受他的影响而赞成君主立宪的人,但也有不少人是经过梁启超而迅速地趋向于当时正在兴起的革命潮流。应该承认,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是做了富有成效的思想启蒙工作,帮助许多原来只知道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人们(特别是青年)打开了眼界,并且从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对比中,更感到自己民族的落后,更强烈地燃烧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该书下册,第691页)对于梁启超动摇于“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矛盾现象,胡绳同志也指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正在取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而成为先进知识界的主导思想的反映(同上书,第692页)。这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对于我们认识评价梁启超的早期伦理思想是有帮助的。那么对梁启超中后期、特别是五四运动后的伦理思想应该如何评价呢?有一种意见认为,梁启超在中后期的思想倒退了,从离异传统到回归传统,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这评价是不够妥当的。其实梁启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并不反对的。他在1922年写作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指出:“到第三期(按:指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按:指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俊等)一躺一躺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传得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可见,他并没有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方面,而是从总体上肯定了它的进步意义。至于所谓梁启超的从离异传统到回归传统,也应该具体分析。如同离异传统有盲目的离异和有分析的离异一样,回归传统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完全回到旧传统、固定旧传统,使自己同新事物、新生活对立起来;一种是更加客观、更加冷静地看待传统,肯定传统中的积极的有价值的因素。应该说所谓梁启超的“离异传统”和“回归传统”,都是属于后者,而不是前者。况且如我们前面所言,梁启超在早期即重视传统,只是在后期对传统研究和认识的更深入更系统罢了。所以,严格说来,对梁启超而言,就没有什么“回归传统”的问题。至于以是离异传统还是回归传统作为进步、革命和保守、反动的标准,就更值得研究了。这个曾经惯用的简单化的“评价模式”,事实上已被和正在被突破。
总之,梁启超的伦理思想,从早期到后期,从总体上看是一贯的,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内容、特点和社会功能作用,但从总体上看都是积极的、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