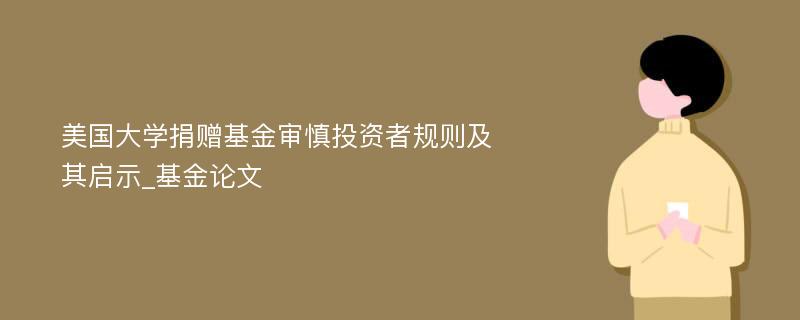
美国大学捐赠基金的谨慎投资者规则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投资者论文,启示论文,谨慎论文,美国大学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43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628(2007)04-0118-04
众所周知,美国大学捐赠基金是以规模庞大,投资回报率高著称。在2006年度美国高等学府捐赠基金回报排名榜中,麻省理工大学(MIT)脱颖而出,以23%的回报率力压排名第2的耶鲁大学,名列全美回报率最高的大学捐赠基金。而20年来,耶鲁捐赠基金创造出16.1%的年平均回报率,排名全美大学第一,高于其他大学平均11.6%的回报率。最新数据还显示,哈佛大学拥有全球最大的捐赠基金资产,捐赠基金总值达292亿美元。[1] 笔者认为,美国大学捐赠基金的庞大规模和高回报率固然与美国逐渐好转的经济状况,优秀的投资管理团队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大学捐赠基金有谨慎投资者规则作指导,从长远意义上来看,该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大学捐赠基金能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环境下实现保值和增值。对于该谨慎投资者规则,笔者试分析之。
一、谨慎人规则:美国大学捐赠基金之谨慎投资者规则的雏形
在1830年之前,美国绝大多数大学将捐赠基金投向票据、抵押、信贷和不动产领域。但也有一些大学捐赠基金因被一些基金管理者(受托人)投资到风险较高的非政府支持证券(non-government-backed securities),最终亏损累累。人们开始对大学捐赠基金受托人的这些投资行为是否合适产生纠纷。在1830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在哈佛学院诉艾默利案的裁决中确立了“谨慎人(prudent man)”规则,[2] 初步建立了捐赠基金的投资管理规则。这起裁决指出基金受托人的义务是:
尽忠尽责,秉持合理的判断,如谨慎之人管理其自身事务般尽己判断和智力,不可作短暂投机,而应持久处置其基金,顾及可能的收益,以及资本投资的安全可靠性。[3]
该谨慎人规则以一个理性的“谨慎人”为参照模型,要求基金受托人在管理基金时应立足长远收益,规避高风险的投机领域,尽可能将基金投资到收益稳定风险小的“安全”领域。此后,美国大学捐赠基金在该谨慎人规则的指引下,被投向各种能产生固定收益又安全的领域,比如政府债券。应该说,谨慎人规则是一种比先前死板的投资“法定名录(legal lists)”灵活,但又相对保守的信托投资策略,其基本精神被后来的谨慎投资者规则所吸纳。
虽然哈佛学院案后,美国大学捐赠基金还曾一度到证券市场上“淘金”,但到了1960年代后期,美国大学捐赠基金管理人又被迫采取起比较保守的投资策略,因为当时法律只允许将捐赠基金投向能产生一定收益的地方(这里的收益包括:抵押收益、不动产收益、红利和利息等等)。然而,当时证券市场飞速膨胀,许多捐赠基金事实上被大量投资于公司证券,这一切促成基金管理人重新审视传统的投资策略。大学捐赠基金管理层意识到了证券市场的未来发展潜力;然而,束缚于这些管理层身上的传统投资策略却不允许将大学捐赠基金投向风险较高的资本市场,只允许将资金投资到那些能产生固定收益(fixed income)的领域。
在整个1960年代及其后期,管理层在投资其捐赠基金时对“何为适度的风险”争议较大。特别是,当时许多捐赠基金管理者认为到资本市场获取资本增值能让捐赠回报最大化,他们相信牺牲收益的稳定性以求较大的投资收益成长性要比只保持捐赠基金的购买力好许多。他们还认为,如要实现公司股票投资利益最大化,必须得改变其会计方法(accounting methods)。捐赠基金管理层须从单一收益会计法(an income-only accounting method)转为全部回报会计法(total return accounting)。依据全部回报会计法,捐赠基金的“收益(income)”不仅包括公司股票的红利,还包括一些未实现的资本增值(unrealized capital appreciation)。与这种动向遥相呼应的是,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在1972年通过了《统一机构基金管理法》(Uniform Management of Institutional Funds Act,以下简称UMIFA)。可以说,UMIFA的诞生平息了困扰捐赠基金管理层的这种争议。
二、UMIFA:美国大学捐赠基金之谨慎投资者规则的集中体现
截止到2002年,美国已经有47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通过了UMIFA。统一州法委员会制定该法是给慈善机构(eleemosynary institutions)的捐赠基金管理树立指针。若大学要落入该法慈善机构的范畴,那大学必须是因教育目的组织并运作起来的,或者如果大学是政府性组织,而UMIFA就能适用于“只因教育目的而持有基金的大学”。[4]
自1960年代起,大学董事会(governing boards)对如何使捐赠基金的效用达到最大化的兴趣越来越浓。在制定UMIFA之前,大学董事会及其法律顾问常常纠缠于全部投资回报以及相关捐赠资金的支出,所许可的投资范围和管理捐赠基金的法律权限和职责等问题。UMIFA对此设计了一套合理使用大学捐赠基金的谨慎投资者规则。该规则主要规定在如下四块内容:投资基金增值的谨慎投资标准;特定投资权限;代理作出投资管理决定的授权;董事会依据该法其他条款履行义务的商业注意和谨慎标准(义务)。
(一)基金增值的谨慎投资标准
UMIFA第二节适用于赠予大学的资金,其部分母本不能被支出而被永久投资。[5] 这些赠金被称为“真实的”捐赠(" true" endowments),因为这些赠金意味着能给大学提供永久的利益。在制定UMIFA之前,捐赠基金管理者们倾向于将“真实的”捐赠基金投向固定收益高的领域,因为管理者只能支出捐赠所产出的收益。这样做是为了将捐赠基金所能带来的收益最大化。即使这些高收益的投资将捐赠基金收益最大化了,但无论如何,这些投资通常也只有非常小的价值增值。不难想象,如果美国的大学仅把筹集到的捐赠基金以定期或活期储蓄的方式存入银行、收取利息,那么过不了几年,恐怕通货膨胀率就会使留本基金实际价值多少发生贬值。[6]
UMIFA第二节主张对管理者适用更加宽松的支出策略:“董事会可拨出一笔开支来设立捐赠基金,这一节并不限制董事会依据法律,赠与条款或者机构章程来支出基金的权限。”[7] 第二节还隐约扩展了收益的概念并明确支持全体回报会计法。因为第二节授权董事会可依据支出目的拨付捐赠基金中变现或未变现的净增值,而拨付净增值到支出领域拓展了“收益”的外延,即此“收益”包括现有的收益和任何其他董事会认为谨慎支出的净增值。捐赠基金管理者们通过将部分捐赠基金放在非流动投资领域而产生更多的资本增值,比如风险资本或者不动产,而无需担心是否有足够的“传统收益”可支出。因此,大学捐赠基金董事会愿意更多地投资于普通股票和其他比固定收益证券带来更多资本净值的领域。
董事会在依据支出目的拨付捐赠基金中变现或未变现的净增值(net appreciation)时,需按照“行动或决定之际的情势尽一般商事注意和谨慎”标准(义务)来支出其增值。[8] 该注意义务与公司董事的注意义务不相上下,比得上更严格的私人受托人的注意义务,而该注意义务是“非盈利机构管理者义务和责任的投射。”[9]
(二)特定投资权限
UMIFA第四节规定了大学董事会(board of trustees)选用捐赠基金进行投资的一般投资权限。第四节还规定:除了由法律或捐赠协议授权投资以外,并不限制受托人的投资,董事会依据捐赠协定中或者除与受托人投资相关的规则之外的特定限制条款,它可以:
1.将机构基金投资或再投资于任何董事会认可的不动产或个人财产,无论其目前是否产生收益,包括抵押、股票、债券、信用债券或其他营利或非营利公司的证券,社团、合伙或个人的股份或债务,以及任何政府或地方政府或中介的债务;
2.只要董事会认可,可保留捐赠者捐献的财产;
3.包括机构所持有的任何普尔或共同基金中的全部或部分机构基金;
4.将全部或部分机构基金投资于任何适合于投资的普尔或共同基金,包括在受监管投资公司(regulated investment companies),共同基金,共同信托基金,投资合伙,不动产,投资信托,或其他由基金组合起来的类似组织的股份或利息,并且由个人而不是董事会作出投资决定。[10]
第四节表明UMIFA的起草者认识到新的投资工具和产品正不断地出现在金融市场上,大学捐赠基金管理者可投向他们认为谨慎的投资领域。
(三)作出投资管理决定的代理权
许多捐赠基金规模庞大,对大学的发展极其重要,加上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易变性,这就要求基金管理人必须天天盯紧捐赠基金,并尽其所能管理好所投资的项目。然而,许多美国大学由于缺乏资源、经验和时间未能积极管理好这些日常投资事项。因而,从美国大学的实际运作来看,大学董事会(college trustees)必须承担大部分或者全部投资职责,但在UMIFA出台之前,董事会却不能这么做。当出现慈善团体时,《信托法重述(第二次)》曾对此作出区分:“这可能是合适的,例如,慈善机构董事会任命由其董事组成的委员会来处理该机构的基金投资事务,而董事会只监督该委员会的行为。”[11] 即便有这种规定,法律对大学有关人员或者大学顾问或外界管理者是否能单独代理开展捐赠基金投资活动的规定还是不够明确。
UMIFA第五节规定了董事会代理作出投资决定的权力(power)问题。该法第五节指出:除了由捐赠协议或者与政府机构或基金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外,董事会可(1)代表其委员会、机构或基金的职员或雇员,或代理人,包括投资顾问,有权取代机构基金投资或再投资委员会行事,(2)与独立投资顾问,投资顾问或管理者,银行,或信托公司订立合同,和(3)就投资咨询或管理服务批准支付一笔费用。[12]
可见,该节赋予董事会有权代理投资管理,又能购买投资咨询和管理服务。然而,在承担投资政策职责和选任能胜任的投资代理人时,董事会必须恪尽商业注意和谨慎义务。
UMIFA第五节生效后,美国许多大学聘请了校外的职业理财师来投资其捐赠基金。据调查,到2002年,全美高等院校协会(NACUBO)所属的654所学校中的绝大多数聘请了外部理财人士来管理其超过50%的捐赠基金。[13]
(四)董事会的商业注意和谨慎义务
最具资本增值收益潜力的投资工具也就是最容易出现风险的。因此,投资者越是投资于风险资本或对冲基金,而不是债券或其他货币市场基金,那投资者就越可能获得资本收益,但与此同时资本损失的风险也较高。在教育机构董事会能自由选择投资工具和投资管理者之际,捐赠基金不能达到预定目标而且还有损失时,诸多问题就出现了。这些问题包括:当作出糟糕的投资决定时,除了经济损失,还会有什么后果?谁应该并能对这种投资决定负责?在UMIFA第六节生效之前,在裁决针对慈善机构董事会的官司时法院或主张适用更严格的信托标准(即谨慎人规则)或主张适用更宽松的公司标准(即公司董事应负有的注意和忠实义务)。此种模糊性使得董事会或其法律顾问无法预知特定行为的司法后果。UMIFA第六节生效后就澄清了这种问题,其规定:
在行使价值增值,投资和继续投资和代理机构基金投资管理的权限时,董事应依照行动或决定之际的情势恪尽普通的商业注意和谨慎义务。在此过程中,他们在执行机构教育、宗教、慈善或其他慈善目的时,应考虑到机构的长期和短期需求,其目前和预期的金融需求,预期投资全部回报,价格水平趋势,以及整体经济状况。[8]
第六节规定了“标准(义务)…通常可与公司董事相比,而非私人受托人,但是它是非营利机构管理者义务和职责的投射。”[9]
在采纳UMIFA后,大学捐赠基金董事会就能将自己从单一收益投资(income-only investing)和谨慎人规则(the prudent man rule)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odern portfolio theory)使捐赠基金的回报达到最大化。
三、美国大学捐赠基金之谨慎投资者规则的启示
谨慎投资者规则是指导受托人投资基金的行为指引,在美国大学捐赠基金的保值和增值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谨慎人规则演变到谨慎投资者规则顺应了市场需求,体现了捐赠基金投资多样化和回报最大化的客观要求。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有:
(一)启示之一是大学捐赠基金应该与资本市场结合,通过规范基金投资的谨慎投资者规则来引导我国大学捐赠基金更好地实现基金的保值与增值目标。如果只容许我国大学将筹集到的捐赠基金以储蓄的方式存入银行、收取利息,那么恐怕基金迟早会因通货膨胀因素而出现贬值,过分保守得强调捐赠基金的安全性无异于切断了捐赠基金的自我增值能力。那么捐赠基金的规模化出路在什么地方?无疑,美国大学捐赠基金在谨慎投资者规则指导下从资本市场上获得了可观的回报,这对我们颇有启示意义。可是我国教育部于2004年6月曾就直属高校进行股票和风险性债券投资的问题,印发了《关于禁止直属高校进行股票和风险性债券投资的紧急通知》,严禁各校进行股票和风险性债券投资。笔者认为,对于高校资金介入资本市场不能有恐惧心理,而通过法律进行规范与引导才是正确的选择,单纯地靠行政规范性文件禁止不会有很好的效果,只会将“明的”转为“暗的”造成更多的负面问题,况且我国《证券法》、《公益事业捐赠法》和《基金会管理条例》并未禁止包括大学捐赠基金在内的高校资金从资本市场上套利。诚然,2006年的天津大学“单平事件”一方面确实反映了资本市场的高风险特征,[14] 但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包括大学捐赠基金在内的高校资金如何在资本市场进行谨慎投资的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结合本文主旨,如何来规范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活动,如何实现捐赠基金的保值和增值,如何实现捐赠基金投资回报最大化,这才是我们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启示之二是要塑造我国大学捐赠基金的谨慎投资者规则,必须启动相关立法程序,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公益事业捐赠法》和《基金会管理条例》是目前我国规范大学捐赠基金管理和运作方面的基本法律法规。《公益事业捐赠法》是在1998年抗洪捐赠的基础上仓促出台的,侧重于鼓励和规范捐赠活动,保护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有关捐赠基金的增值问题,只有原则性的规定。其第18条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应当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积极实现捐赠财产的保值增值。尽管“合法和安全”特意放在“捐赠财产的保值增值”面前,但在实践当中,包括大学捐赠基金会在内的不少基金会还是出现了各种有关基金增值问题。有的基金会以基金的增值、保值为名直接或变相从事借贷、信托等金融活动,背离了章程订立的公益使命;有的基金会将捐助资金用于股权投资或者实业投资,没有按照捐赠人的意愿使用资金,违背了捐助人的意愿和基金会的非营利原则;有的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或将存单转借他人作抵押,甚至用捐赠基金为企业贷款提供质押担保,置公益基金于高度风险状态。[15] 故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8条再次强调:“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可见,当初我国立法者的重心是放在基金会的合法运行和安全运行上,正如该《条例》参与者朱卫国所言,“基金规模小是情况,不是问题。”但笔者认为,我国高校捐赠基金规模小确实是情况,但也应是个问题,因为实现高校捐赠基金的“有效”增值却是个颇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尤其在目前显现高校还贷危机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谨慎投资把高校可观的捐赠基金实现最大增值,进而给其他大学资金寻找到一条增值之路,对于避免或缓解目前我国高校的经济压力不啻是条可行之路。事实上有报道称,汕头大学至今没有任何负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李嘉诚基金会在一支优秀管理团队的谨慎投资下实现了良好的保值和增值,这给2006年的汕头大学提供了超过45%的收入来源。[16] 可见,大学捐赠基金通过谨慎投资,实现基金的增值与保值对于我国大学来讲,意义重大。但要塑造我国大学捐赠基金的谨慎投资者规则,笔者认为,可选择这样的立法路径:从宏观层面看,大学捐赠基金之谨慎投资者规则最好在将来的《慈善事业促进法》中有所体现,比如继续原则性地规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从中观层面看,今后应相应调整《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8条,并增加四款,规定“基金投资的增值,特定投资权限,作出投资管理决定的代理权,以及理事会的注意和谨慎义务”等相关内容;从微观角度看,最高人民法院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形成一个有关捐赠基金投资问题的司法解释,具体规定捐赠基金投资的相关法律问题。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三个立法层次,最终形成我国的(大学)捐赠基金之谨慎投资者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