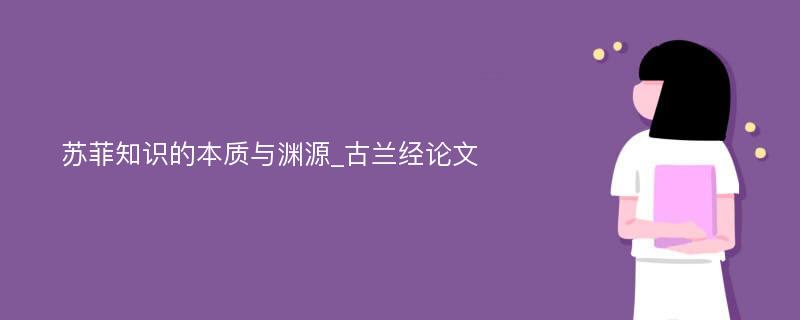
苏菲行知的实质与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实质论文,行知论文,苏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558(2014)03-0113-13 假若我们把这部《古兰经》降示于一座山,你必定看见它谦卑地弯曲,并因畏惧真主而崩裂。(《古兰经》第五十九章21节) 由于伊斯兰教是建立在天启之上的宗教,所以,根据上述经文的精神可以预料,真主以天启为途径全方位地向人展示自己,人必然会对真主作出反应,而这肯定会在人自身之内唤起一种共鸣,这种共鸣则必定会超越一般的外显教乘的平庸。“这一点毋庸置疑,可这种超越何时产生呢?”这也许就是一个明显的疑问。虽然没有任何理由去假定《旧约》天启在全方位展示真主方面显得更逊色一些,道乘在《旧约》的追随者中间被开发出来的具体时间尽管也难以确定,但是,这的确经历了一些时间。不管怎么说,《古兰经》就是突发的“世界末日”的先兆,而且,伊斯兰教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其突发性。假如要对“何时”给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极有可能就是“现在”,这一即发性在以下这节经文里表现得很清楚,这节经文在最早降示的章节中出现了两次:“这确是教诲。谁愿意,谁可以选择一条通达其养育主的道路。”(《古兰经》第七十三章19节;第七十六章29节)一般而言,《古兰经》把伊斯兰教称作“养育主的道路”,亦即由真主钦定的道路,可以说,这条道路既包含外显的教乘,又包含内隐的道乘。然而,只在这两章经文里所提到的“养育主的道路”很明显就是指内隐的道乘之道,原因是其中的道路用“教诲”(tazkirah)这个词作了强调,教诲是用来催生“迪克尔”(赞念真主)的,而“迪克尔”本身就是苏菲行知的核心。 正如在天启降示之初就已经提到的那样,这些经文所提示的内涵在其他多处经文中得到了完全的证实。最早降示的另一章经文(第五十六章)说,伊斯兰社团是由“先行者”(Sabigoon)和“右顺之邦”(Ashab al-yameen)这两伙人组成的。第二伙人就是普通信士构成的大众,他们与将被打入火狱的“左逆之徒”(Ashab al-shima'l)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至于“先行者”,经文说他们是由“许多前人和少数后人”组成的,而“右顺之邦”则是由“许多前人和许多后人”组成的。经文进一步把“先行者”描述为“被眷顾的近主之士”,这个术语是用来在高品天神和一般天神之间作区别的。由此可知,“先行者”就是那些最终有幸得道的少数行道者。另一章经文告诉我们说,这种“近主品级”意味着可以直接从一洞名叫“太斯尼姆”的泉眼中饮水的特权。 早先降示的一些经文也提到了第三伙人,即那些被叫作“善人”(Abra'r)的人,但这并不能改变把社团主要分为两伙人的事实,因为,按经文所讲,“善人”所饮的天醇是一种混合饮料,它就源自“近主之士”所直接饮用的那一洞叫作“太斯尼姆”的泉眼。(第八十三章27~28节)这就说明,“善人”紧随着“近主之士”的步伐,而且,他们所追求的境界也锁定在“近主之士”的境界之上。尽管他们还没有达到彻底悟道的境地,可是,由于有幸与这些“近主之士”在一起,他们的求道者身份得到了保证,因为另一章更早的经文说:“善人们必得饮含有樟脑的醴泉,即真主的众仆所饮的一道泉水。”(第七十六章5-6节)那些有资历可以直接从这一至高泉眼中饮水的人士被称为“真主的众仆”,这一称号在《古兰经》中有两层明显的含义。第一层是广义的,指一切生命,甚至包括撒旦,因为撒旦也是真主的一名奴仆;第二层是狭义的,它排除了所有还没有体悟到真仆实质的人,所谓的真仆实质,就是化己归真。显然,这里的经文所指的是化己归真的真仆。经文接着指出,真主的众仆不但从樟脑醴泉中直接饮水,而且他们将随自己的意愿“使它大量涌出”。考虑到那些化己归真的众仆都是精神性贫穷(faqr)的化身,这就意味着他们那“不可抗拒的空乏”与由泉眼所象征的真主极其丰富的无尽宝藏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伊本·阿拉比常爱引证的那句名言“要以我所不拥有的(即贫穷)来努力接近我!”原本出自苏菲大师艾卜·叶基德·巴斯塔米之口,是真主给他的一句启迪。这句名言认定,近主的品级是守贫的果实,其实也在说明“众仆”实质上就是“近主之士”这样一个道理。①顺理成章的是,同样的道理也非常清晰地展现在真主下达给穆圣的一项早期命令之中:“你应当为真主叩头。你应当亲近真主。”(第九十六章19节)穆圣对经文的注释“仆人与真主最近的时刻便是他叩头之时”所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叩头就是象征贫穷的姿势。②此外,近主之境与仆人身份相似,都有一种双重含义。就玄学层面而言,近主之境就像仆人身份一样,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的一个铁的事实。虽然这一真理已经在真主的尊名“临近之主”(al-Qarib)中显得很清楚,《古兰经》仍然强调说:“那时候(即死者灵魂出窍之时),你们大家看着他,我比你们更临近他,但你们不晓得。”(第五十六章84~85节)然而,就苏菲体验而言,“他离我们很近,但我们离他很远”,③只有那些能直接感悟到真主确实离我们非常近这一真理的人才能被称为“近主之士”。 就仆人身份与近主之境所内含的高级与特定意义而言,还有必要在其相对意义和绝对意义之间作一个区别。当《古兰经》讲到“近主之士”和“真主的众仆”时,其中所用的复数形式本身就说明这里所指的是相对意义上的近主之境和相对意义上的仆人身份,以及两者所可能表达的最高境界,这样的境界会带着一些圣徒的灵魂在不致使自己的个体存在彻底消失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抵达真主临在的近前。就天堂一词所表达的普通意义而言,这里就是金字塔式的层层天园的最高一层。超越了这一层天堂,便是真主至高本然的绝对近在,苏菲们把这叫作“本然的天堂”,所有的二元性在那里都被排除无遗。《古兰经》说:“我比他的命脉还近于他。”(第五十章16节)“你们要知道:真主的确周旋于人与其心灵之间。”(第八章24节)。体悟这一认知境界的可能性在穆圣使命的后期被讲述得很清楚,假如穆圣在这之前还没有讲述过的话,那么他这时用以下这段圣洁圣训彻底表述了这一境界:“只要我的仆人以比我钦定给他的主命功修更为我所喜爱的功修接近我,只要他不遗余力地以各种余功功修接近我,直到我喜爱他,当我爱上了他时,我就是他用来听的听力,就是他用来观看的视力,就是他用来击打的手,就是他用来行路的脚。”④ 这就意味着圣徒品级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相对意义上的近主之境,另一个是绝对意义上的近主之境,即体悟合一境界。换句话来表达,人所追求的最高精神性目标是一个二重性的统一体。因此,早先降示的经文许诺说,信士将拥有两座天堂(第五十五章46节)。有一些《古兰经》经文是针对完美的灵魂而讲的,也早已证实了这样的二重性统一体:“安定的灵魂啊!你应当喜悦地,被喜悦地归于你的主。你应当入在我的众仆里;你应当入在我的乐园里。”(第八十九章27~30节)即使穆圣的如下圣训本来不是针对这些经文作出的注释,也无妨把它看作是对它们的一个脚注:“真主将对乐园中的人说:‘你们满意了吗?’他们将回答:‘主啊!你已经把你不曾赏赐给你的任何被造者的恩典赏赐给了我们,我们怎么不满意呢?’这时,真主会说:‘我要把比那更好的赏赐给你们,好吗?’他们说:‘主啊!有什么比那更好呢?’他说:‘我将为你们降下我的喜悦(Ridwān)。’”⑤ 据权威注释,由喜悦带来的极度安详指的是真主把个体灵魂带向他那里,在真主阙前得享永恒的喜悦。上述《古兰经》经文所讲的“你应当喜悦地”所表达的就是个体灵魂在享受相对意义上的近主之境中的幸福时的喜悦感(亦即:你应当入在我的众仆里),而“被喜悦地归于你的主”则表达着绝对意义上的近主之境(亦即:你应当入在我的乐园里)。也就是说,属于真主自己的天堂就是喜悦(Ridwān)的天堂,它要“比那更好”,即比一般意义上的天堂更好。同样的二重性统一体在后期降示的天启经文中再次被提到,而且也证实了同样的优先原则: 真主应许信道的男女们将进入下临诸河的乐园,并永居其中,他们在常住的乐园里,将有优美的住宅,也得享真主的更大的喜悦(Ridwān)。这就是伟大的成功。(第九章72节) 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是,穆圣归真之前,真主让他选择自己的未来,而他选择的归宿也是用一种二重性语言来表达的:“与我的养育主相会,以及乐园。”⑥ 本文开头这几段被着力强调的目的就在于,从一开始就要讲清楚这么一点:就对教义的认识而言,穆圣的那些圣门弟子对呈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去追求的最高精神性成就的可能性一点也不马虎。至此,我们可以转向修炼方式的问题了。以下这几节被公认为是最早降示的《古兰经》经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你要在夜间立站,除开不多的时间,夜的一半,或从中减少一点,或其上增加一点,你要字字分明地咏诵《古兰经》……你要赞念你养育主的尊名,你要以贞心去专心致志地侍奉他。(第七十三章,2~4节,8节) 这些启示命令穆圣——从而也间接地命令他那些最亲密的弟子,要他们持守某种高强度的修持,而这样的高强度修持则超出了一般的教法义务范畴,不可能以命令的形式颁布给社团的所有成员。此外,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赞念真主的尊名历来就是苏菲修炼的关键方式,这一点已经在这里被明确指定,而这节经文的降示就发生在这个宗教的建立之初,虽然不能肯定这发生在正规的礼拜仪式被昭示给穆圣以前,但完全可以肯定的是,那时,作为在外显的教乘之道中占有中心地位的每日五次礼拜的定制还没有被建立起来。至于其他那些较为关键的苏菲修炼方式,尽管它们还不像赞念真主的尊名那样早就已经被建立起来,它们也是源自穆圣亲自建立的传统。其中一些是在麦加建立的,另一些则是在麦地那建立的。实际上,静坐独修(i‘tikāf,或khalwah)这一修炼方式是一个源自伊斯兰教之前的做法,可以说,它标志着易卜拉欣大圣的传统与伊斯兰教在内隐的道乘上的一种延续性。至于作为补充性修炼方式的精神性聚会,即那种叫作“赞念席”(majlis al-dhikr)的在自愿基础上由社团集体参与的赞念礼仪,其名称也源自圣训,据很多圣训记载,穆圣曾亲自称赞过它。在穿越多少个世纪的时间里,苏菲们一直保持了这两种修炼方式的鲜活性,而且一般而言,他们就是时至今日仍然在坚守着这些修炼方式的唯一的穆斯林群体。苏菲修炼方式的其他一些内容的情况也是如此,都传承自穆圣及其圣门弟子。 如果“迪克尔”(即赞念或祈求)这个术语首先是用来指上文中引证的经文“你应当赞念你的主的尊名”这层含义的,那么也要知道,这个术语一直有一种延伸含义,它也包括了其他一些修炼方式,如阅读《古兰经》,咏诵《古兰经》以及某些赞辞。所谓的赞辞,通常指取自《古兰经》的一些经文,或者由被穆圣所赞许的其他一些宗教惯用语组成,并按特定的赞念次数组合成的赞文。无须赘言,讽诵《古兰经》绝不是局限在苏菲圈内的一种特有礼仪,被《古兰经》和穆圣所赞许的赞辞也同样为所有的穆斯林所钟爱,随机咏诵。内隐之道在这方面区别于一般穆斯林大众的独特之处只在于他们对赞辞的格式化了的规范,即他们赞念的“量”(《古兰经》命令要“多多赞念真主”),以及苏菲之道所赋予他们的“质”,即隐秘的精神性内涵。在许多苏菲道统中,三个惯用语被串联成了一套赞辞,表达着一种通向纯洁、完美和真理的三维追求。这三个惯用语便是:恳求真主恕饶的求饶辞,赞美穆圣并向他祝安的赞圣辞,作证真主独一的认主独一辞。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去假设这样的复合型赞辞在穆圣时代就已经被诵念,但毫无疑义的是,单个的惯用语及其各自本身的内涵就是由第一代伊斯兰传人传授给后来的那些渴望近主之境的求道者的。据信,苏菲人士所使用的念珠的原型就是圣门弟子艾卜·呼莱勒为自己设计制作的打了布结的捻线。 到了伊斯兰教被稳固地建立于麦地那的时期,内隐的道乘人士已经变成了少数。有一节在迁徙之后不久便已经被降示的经文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这节经文提到“你的同道中,有一群人也是那样做的”(第七十三章20节),这里所指的就是圣门弟子中那些尽自己努力最大限度地紧密追随穆圣的一切圣行的人士。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可以认定,这些圣门弟子组成了一批精神性精英。上述这节经文被降示的目的在于修正一节最早降示的经文,那节经文下达过关于长时间立站夜间的命令,我们已经在前面见到过那一节经文了。但是,不能把这样的修正简单地当作是对教乘的一种妥协来看待。这节经文应该与另一节大约在同一时期降示的经文“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第二章143节)放到一起去理解,这是一个来自天国的明证,意在说明这个新宗教的整体性导向——温和与平常,亦即趋同于万事万物的本性,当然了,这样的导向也包括这个宗教内隐的道乘层面。这方面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穆圣与他的一名圣门弟子之间的一次对话,那也发生在迁徙麦地那的早些年头。有一位圣门弟子名叫奥斯曼·本·麦祖欧尼,据他的姐夫欧麦尔说,“他是我们中间一位最远离尘世俗务的人”。正是对这名弟子,穆圣发话说:“你没在我身上找到榜样吗?”在奥斯曼以坚决的口气表示肯定之后,穆圣告诉他不要再坚持日日白天封斋、夜夜彻夜干功。“的确,你的眼睛有权利向你要求睡眠,你的身体有权利向你要求休息,你的家人有权利向你要求给他们尽义务。所以,你要礼拜,也要睡觉;你要封斋,也要开斋。”⑦只要伴随着赞念之舌和感恩之心,那么,合理的享乐也是真人的“迪克尔”,那也就会成为赞念真主的一种方式,穆圣曾经把这些与拜主的功修放在一起,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圣训:“真主让我从你们的尘世中喜爱美香和妇女,我眼中的温馨快乐也被造在了礼拜之中。”⑧后来的几代更倾向于苦行修炼的苏菲尽管没有否认穆圣具有典范作用的实质,但他们毫不怀疑地以自己比起圣门弟子而言需要更多的净化为理由,为自己所投入的高强度苦行修炼作了辩解。然而,穆圣的中庸之道,即为了真主而放弃对尘世享乐的迷恋与允许一些合理享乐之间的平衡——当然了,这些合理享乐早已被感恩之心和对这些合理享乐的天界原型的灵智性感悟赋予了精神性意义,历来在苏菲人士圈内有一批强有力的代表人物在践行,而且这些代表人物也并非一些并不那么显赫的人物。 至此,关于苏菲修炼方式的起源,我们只考虑了自愿进行的余功功修,而没有论及伊斯兰教的教法所制定的那些被穆斯林大众一起遵守的义务性功修。由于教法关乎大众,所以那些义务性功修被称为外显的教乘功修。然而,由于教法所具有的简易性和透明性,那些义务性功修也可以被形容为外显化了的内隐功修,当那些义务性功修被追求精神之道的少数人所实践时,它们也就被再一次内隐化了。“这些功修的内隐的道乘属性不仅寓于其可见的圣化功能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而且也寓于这样一个事实:只要我们自己就是内隐的求道者,那么,我们的一切功修都属于内隐的道乘范畴。”⑨此外,伊斯兰教制定的礼仪更易于把一切宗教仪式招归于其基本的内向型价值意义,这是因为在伊斯兰教里,履行宗教礼仪的人是独立于任何一个中介的:每一个穆斯林都是他自己的神父。也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怀疑外在礼仪的内向化这一特征就是溯源于穆圣本身的。穆圣在这方面所建立的一个重大而具有深远意义的先例就是他在一次后期的征途中归来时所讲的一句著名圣训:“我们从小圣战回归到了大圣战之中。”⑩他当时对大圣战所下的定义就是“针对自我的战斗”(jihād al-nafs)。由于穆圣也说过妇女的圣战就是朝觐的话,因此也可以在外在的朝觐和内在的朝觐之间作一个区别,甚至可以说,对一个具有求道使命感的人而言,这样的区别极有必要。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封斋和出散天课,封斋象征着不贪恋尘世,而出散天课则象征着把自己奉献给真主。至于正规的礼拜仪式,我们已经在标志着礼拜最高顶点的叩头仪式中看到了最深奥的内隐含义。就礼拜仪式以及礼拜之前必须完成的净化仪式而言,外显的教乘与内隐的道乘之间的区别决定于“只要我们自己就是内隐的求道者,那么,我们的一切功修都属于内隐的道乘范畴”,亦即在这两样功修仪式中,区别决定于我们自己关于礼仪的内涵深度和广度的认知,换句话讲,决定于我们的举意:礼拜象征着谦卑,出散天课则象征着纯洁。 伊斯兰教的第一大天命作证言概括了这个宗教的全部,既包括其外显的教乘层面,又包括其内隐的道乘层面,它是由两个作证词构成的:作证“无一主宰,惟有真主”,以及作证“穆罕默德,主之钦差”。这又是一个与认知程度和渴望程度有关的问题。就一个对绝对真实有某种感悟,亦即对真主的本质属性有某种足够感悟的人而言,第一个作证词给他提供着一个转瞬即逝的吉庆时刻,让他暂时忘记一切非主之事物。当一个道乘之人诵念“无一主宰,惟有真主”时,他的认识中还包括了这个真理:“无一实在,惟有真主的实在”。假如遭遇非议,他可以引证穆圣关于世界被造之前的状态而讲的那一句圣训:“只有真主存在,没有任何一物与他同在。”这句圣训有一句补注,虽然无从得知注者是谁,但其本身是无法驳斥的:“他此刻也存在,就如他当时存在。”(11)教乘之人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可他也无法否认,因为否认当即就意味着招惹亵渎之大罪,意味着把永恒不变的真主描述成了可变的事物。更何况《古兰经》也在时刻坚持着真主作为绝对实在的权威呢: 除他外,无一主宰。除他的尊容外,万物都要毁灭。判决只由他做出,你们只被召归于他。(第二十八章,88节)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节经文,苏菲的术语“法纳”(化除、浑化、消失)和“拜噶”(持续、留存、生存、永存)就是源自这节经文的: 凡在其上的,都是要消失的;惟有你的主那具有威严与恩惠的尊容,将永恒存在。(第五十五章,26~27节) 这就是喜悦(Ridwān)的境界,因认识到一切显露出来的灵魂都被重新整合到了“隐蔽的宝藏”的无限一统性之中而感悟到的宁静安详。用“隐蔽的宝藏”来表述真主的本体是源自如下圣洁圣训的:“我曾是一座隐蔽的宝藏,我喜爱被认识,因此,我创造了世界。” 至于第二个作证词,鉴于钦差圣人不仅源自他的差遣主而已,而且也回归于他,所以说,这个作证词的作用就是在相对者,即人与其神圣起源和归宿,亦即绝对者,即真主之间建立一种交融。诚如穆圣就是一个完美的理想境界,他因而也是一个榜样,他身上最值得效法的第一件事只能是他那最为关键的属性,说白了,就是这一交融,伴随着这一交融的是对自己源自何处、归于何处的最大可能的强烈感受。 似乎没有什么文献记载可以证明,究竟是否有人向穆圣请教过这个问题,请他用明确的语言界定一下自己那一最为关键的属性。但是,一个人,当他自己的存在就是完美理想境界的化身,而他被要求去界定一下完美理想是什么时,其答案要点则是他的回答应该是主观性的。实际上,人们期望得到的答案是对另一个问题的答复。当大天神询问“什么是‘伊哈萨尼’(ihsān,即完美的境界)”时,穆圣其实可以回答:“穆罕默德,主之钦差。”但是,这样的回答肯定会显得太晦涩难懂了。所以,他转而采用了一种与第二个作证词相对应的答复,在其中勾画出了绝对者与相对者之间的一种连接线索:“完美的境界就是:你要侍奉真主,好似你确实看见他一样,如果你还没有达到看见他(的境界),那么,(你就应当确信)他的确是注视着你的。”(12) 就穆圣本身以及作为他精神生命的延续的继承人即圣徒的情况而言,那一连接线索是双向运作的。“好似你确实看见他一样”这样的译文表达比起阿拉伯语原文来,显得更有一些否定意味,其实这句话几乎可以翻译为“就像一个确实看见他的人那样”,进一步讲,这句话也可以意译为“就像一个心灵清醒的人那样”。要记得,穆圣曾在另一个场合说过:“我的心灵是不入睡的。”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我们已经引述过的那一段圣洁圣训中的那些话:“当我爱上了他时,我就是他用来听的听力,就是他用来观看的视力,就是他用来击打的手,就是他用来行路的脚。”就被真主爱上的那些人而言,绝对意义上的真主会把自己的视力“出借”给相对意义上的人,以便让因人的坠落而断开了的太初的视线重新得以建立。人的关键性职守就是参悟,精确地讲,这就意味着人的完美境界依赖于自己走向超然真主的通道。至于“侍奉”则既包括信仰层面又包括修行层面,大天神在询问“伊哈萨尼”完美境界之前就已经先请穆圣界定了这两个问题。因此,“你要侍奉真主,好似你确实看见他一样”就意味着信仰(īmān,伊玛尼)的完美和顺从(islām,伊斯兰)的完美两个方面。所谓顺从,就是顺从通过教法表达出来的真主的意志。 这就等于在信仰和行为这两个向度之上又增加了一个向度,这个向度关乎高度和深度,是人在天地之间进行参悟的轴心。其实,苏菲人士也并不是穆斯林群体中间坚持主张“伊哈萨尼”就属于神秘追求或隐秘之道,亦即苏菲行知的唯一群体。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苏菲行知建立在天启之上,而这部天启不是专门给道乘之人降示的,所以,苏菲行知必然要与教乘结为一体,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宗教。这个宗教不像犹太教和印度教,而像佛教和基督教一样,是一个普世性宗教。然而,又与这两个普世性宗教不一样的是,伊斯兰教像犹太教那样建立在天启的教诲之上,而没有建立在带来教诲的人物之上。此外,这样的教诲还是本次时间循环之内的最终一次教诲,这就意味着,这次教诲的内在层面除了具备每一种内隐之道所必然具备的普世性特征之外,还要具备任何一种终极性内隐之道所必然具备的那种综合性普世特征。就这方面而言,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它强调“他们人人都确信真主和他的众天神,一切经典和列圣”(第二章285节)。此外,人还是真主的代理者(khalīfah),一个代理者必然要与他所代理的真主的属性保持一致,因为,人就是按真主的形象造化的。仿佛随着以下经文的降示,伊斯兰教的普世性特征被拉开了序幕: 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无论你们转向哪方,那里就是真主的尊容。真主确是宽大的,却是全知的。(第二章115节) 《古兰经》有三次抱怨说,“他们没有真切地评认真主”(第六章91节;第二十二章74节;第三十九章67节),《古兰经》也特别不容忍这样一种狭隘的态度,即在不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某个特定宗教的荣耀而偏要去牺牲真主的荣耀。不止一个宗教的教乘主义观点建立在一些假定之上,如果把他们这些假定放到逻辑的角度予以推理,结果似乎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真主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把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人置于黑暗之中,不让他们享受精神生活。《古兰经》一举扫荡了这方面的所有幻觉:“每个民族都有一个钦差圣人。”(第十章47节)“在这之前,我们确已派遣许多钦差圣人,他们中有一些,我们已经讲述给你了,也有一些,我们没有讲述给你。”(第四十章78节)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引证这一节经文:“的确,信道者、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星教徒,凡信仰真主与末日,并且行善的,他们在他们的化育主那里得享自己的报酬,他们之上没有恐惧,他们也不忧愁。”(第二章62节)最后,为了不让人有余地去想象这些经文所讲的只是针对过去的,其他所有启示已经被取代,《古兰经》当即表示:“我们已为你们中每一个(民族)制定一套教礼和一条道路。如果真主意欲,他必把你们造成一个民族。但(他把你们分成许多民族),以便他考验你们能否遵守他所赐予你们的(教礼和道路)。所以,你们争先行善吧!你们全都要归于真主,那时,他要把你们所争论的是非昭示给你们。”(第五章48节)(13) 还有另一个特性,即原生性,它与普世性一起被每个正宗的道乘宗教所拥有,然而,苏菲所拥有的原生性有双重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次时间循环的结尾会与自己的开端重新连接起来,伊斯兰教被界定为一个原生的宗教:“你应当面向正教,即真主的本性(即认主独一),他把此(本性)赋予了人类。”(第三十章30节)结尾与开端之间这种神秘关系被《古兰经》以持续强调造化这一奇迹的方式标注出来了。宇宙的造化被作为一个用“真主的种种迹象(āyāt Allāh)”编织起来的参悟对象,摆到了人的面前。“七重天和大地,以及其间的一切生灵,都在赞颂他清净,无一物不在赞颂他清净。”(第十七章44节)这里提到的赞颂就是指真主某一德性的展示而言的,真主的意志就是展示其本然,没有任何一件事物不依赖于真主本然的流行而存在,这一点是绝无异议的。可以这么说,上面引证过的那段圣洁圣训“我曾是一座隐蔽的宝藏,我喜爱被认识,因此,我创造了世界”,其实已经总结了一切形式的神秘主义的宇宙生成论。在道乘之人看来,造化无非就是真主在展示其本然。举例而言,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者在这方面与苏菲不可能有什么分歧。即使这样,我们不能说充满《新约全书》的主题就是关于造化的思想,然而,在《古兰经》里,真主造化世界这一主题无法抑制地一再被重复。《古兰经》塑造的苏菲必然有义务具有原生性,不仅是他渴望要获得的人的完美——这是每一种神秘主义的首要目标具有原生性,而且他追求的所谓的“感悟造化”也具有原生性。我们有很多理由去假定,我们早期的那些祖先最不需要有人去提醒他们,自己和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如果对他们而言,宗教并不是必需的,那是因为“韧带”——宗教这个词就以此词得名,而且也总在试图重新修复这一“韧带”——在那时仍然充满了生机。拿大树这个在传统上被看作世界,既包括大世界又包括小世界的象征物为例,就可以得知我们的早期先人认识深沉,可以直接感悟到他们就附着在自己的神圣根本之上,而且,他们也能够把自己这种主观的定信之知推及自己周遭的一切事物之中。在他们看来,每一件事物都是一件引人深思的奇妙对象,感悟到它就是在展示超然实在,就是在象征着它要展示的那一隐蔽宝藏。丢失了这样的认知态度,就意味着丢失了对万物的象征意义的感悟,而把某一个事物只当作那一个事物本身来看待,这就意味着忘记了事物的原本性象征意义,这正是人坠落的原因。这就是《古兰经》的典型立场,因此,这部经典所塑造的一个观点就是,就平常意义而言,人根本就不需要奇迹的发生。下面这一段落经文表达极其朴素,被认为是原生性的代表:“难道他们不观察吗?骆驼是怎样被造成的,苍天是怎样被升高的,山峦是怎样被竖起的,大地是怎样被展开的。”(第八十八章17~20节)。 原生性与普世性是互相照应的。在一次时间循环的开始,成见、偏执等一些限制因素还没有产生,不可能扭曲并混淆人对万物本质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讲,普世性和原生性在伊斯兰教的外显教乘层面上已经有所反映。但是,这两个特征就其本质来讲,是属于内隐道乘的,一个生活在教乘层面上理解有所局限的穆斯林不可能从其中参悟出更深奥的道理。因此,客观公正地理解与《古兰经》所讲的普世性和原生性相关联的问题这项义务就只能落在苏菲的肩膀上。如果不把这一项义务与这一项殊荣考虑进去,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对苏菲行知的本质作出一个恰当的界定。然而,实际上,苏菲道统中也只有一小部分成员能够圆满地逃离出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他们的教乘的种种局限的感染。 《古兰经》宣称自己就是“准则”(Furqān),所以,它必然要求一种极为准确的判别力,这一点作为对普世性的补充,也与它一道支配着苏菲的基本态度。世界的构造要求我们对层级性秩序有一种感悟。尽管万物都在反映着真主的某一个德性,而且“无一物不在赞颂他清净”,高声赞颂也好,轻声赞颂也好,清晰的反映也好,模糊的反映也好,这一切都取决于赞颂者自身的世界与真主之间的距离远近,也依赖于赞颂者在这个世界中占据的相对重要或相对次要的位置。《古兰经》持续不断地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别和先后次序,往往在针对内隐之道上的少数人发出的教诲旁边,或者在一些教诲发出之前,追加一些呼唤之语,如“有眼光的人们啊!”或者“有心灵的人们啊!”因此,苏菲除了时刻保持清醒之外别无选择,他只能打开观察之眼与判别之心,去把每一件事物放到其恰当的位置上,给每一个事物交还它的应有权利。 要求苏菲具备的另外两个灵智条件就是辽阔和细致。就涵盖教乘和道乘的整体水平而言,伊斯兰教的根本特征就是其“真理性”,而辽阔和细致则是对这一真理性的补充,然而,对这一真理性在最广最深层面上的阐释只能由内隐之道来承担完成。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能说苏菲之道是一条认知之道,而不是一条爱之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菲之道常常要去驳斥爱之道所必然要去纵容甚至鼓励的那些偏执。忠于一个人物意味着要盯住这个人物,而不能左顾右盼,《新约全书》所讲述的是一条爱之道,就是由于这一点,我们发现它似乎就是围绕着耶稣这个人物而转的,其宗教也得名于这个人物的名字。相比较而言,忠于真理则意味着尽可能遥远、尽可能清晰地去观察四面八方,这就是《古兰经》所要推行的观点。尽管如此,有两位苏菲大师的称号与爱有关,一位是巴士拉城的苏姆农·伊本·哈姆宰(归真于回历三○三年,即西历915年),号称“爱士”(Muhibb);另一位是欧麦尔·伊本·法瑞德(归真于回历六三二年,即西历1235年),号称“恋者之王”(Sultān al-āshiqīn)。第二个称号涵盖了整个苏菲圈子,因为苏菲被称作“恋者”。然而,这里讲的爱,是一种结果,而不是玄学透悟的起点。换句话表达,这里的爱建立在超越了所有二元性的认主独一基础之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里的爱首先象征着相对者在绝对者之中的浑化,有限者在无限者中的消失。 对苏菲学理所讲的“浑化之后的永存”(al-baqā b‘ad al-fanā)或“浑化之浑化”(fanā alfanā),上面引证过的经文已经讲得非常明确:“凡在其上的,都是要消失的。惟有你的主那具有威严与恩惠的尊容,将永恒存在。”后面的那个词“恩惠”具有独特意义。假如有人要问,在所有的接受者已经浑化了的情况下,哪里有“恩惠”存在的可能性呢?答案是:母亲对在自己的肚腹里还未出生的婴孩的恩惠,就是真主的本体对万物原型的恩惠的象征,婴孩与母亲神秘地合一,万有与真主神秘地合一。但是,如果要进行逆向类推,那么,子宫中的胚胎处于其生长的低级阶段,而本体中的原型却是最高境界,一切显露物均源于此,最终也重新归于此。伊本·阿拉比把这些原型叫作“不变之体”(al-a ‘yān al-thābitah),(14)它们也正是他这几行文字阐述的主题:“我们曾是一些字母,崇高而无变化,高高擎起在至高顶峰的城堡主楼里。在那里,我是你,我们也是你,而你是他,一切都在他中,他就是他——你去请教任何一个抵达了终点的人吧!”(15)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我们也会发现同一个真理,《古兰经》极度频繁地拿出来让人去参悟的一个“迹象”是“白昼和黑夜之间的不同”。这种不同在多个层面上含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白昼和黑夜就像它俩的神圣原型,即真主的威严与恩惠一样,也像各自所象征的绝对与无限那样,在超越一切差别的同时保持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差别。然而,由于白昼来自黑夜,所以白昼在代表着真主的威严的同时,也象征着发自真主本体的无限黑夜的一切显露。作为被迫求的最高对象,真主的本体被拟人化地表述为莱拉,这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意思是黑夜。从回历四世纪(即西历10世纪)起直到今天,许多苏菲情诗的赞美对象一直就是她。以此为背景,我们可以说星星就是一些“不变之体”。在白昼的幻觉中,它们是隐蔽的,黑夜的真实降临时,它们就现身了。因此,筛赫阿拉维在他写给“莱拉”的诗歌中用如下词句证实了他自己的精神性体悟:“我的星星在她的天空里闪烁。”(16)一千多年前,“爱士”早已表达了同样的真理,他以与黑夜一样具有同样象征意义的海洋为象征物,直接向真主表露自己的心声:“主啊!你把我扔进了你那神圣的海洋,让我游泳。既不存在,也无痕迹,我在你中寻找你。”(17)这两种表述方式都属于典型的苏菲表述方式,确切地说,就是在真知的框架之内对爱的表述,两者也都与喜悦(Ridwān)的机密相关联。 讲到苏菲行知的实质,还有一个问题也必须予以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发展。如果每一个宗教的内隐之道就是其创立者生命临在的延展,那么,它也肯定就是对他离世导致的损失的一种补偿。假如苏菲行知的起源就在于穆圣的时代,并从那个时代汲取自己的营养,那么,它也在直接水平和“垂直水平”上已经得到了丰富,这样的丰富表现在多个领域,其中之一便是多少个世纪以来那些精神大师们所获得的启迪(ilhām)。 前文中已经提到,所有关键性的苏菲修炼方式都统统源自穆圣。苏菲人士就是这么宣称的。试举一例,很多道统在各自的赞主场合中会有让身体随着旋律摇动的做法,在某些情况下,假如确有必要为这样的行为辩护,他们就会引证穆圣的如下圣训:“赞念被爱者时不摇动的人不够慷慨。”其实,左右摇动就是万物的一个本质属性,或者可以说,一些类似的摇动何尝不是集中注意力的一个得力助手呢?然而,要想把毛拉威耶道统举办的那种正规舞蹈也算进这个范畴,几乎是不可能的。毛拉威耶道统的人在西方被叫作“跳旋转舞的求道者”。这种舞蹈的关键特征就是让胳膊在身体的两侧全幅展开,右掌心朝上,象征着接受来自天国的吉庆,左掌心朝下,象征着把来自天国的吉庆传输给大地,并以完美的挺立身体为轴心不停地旋转。这种用身体的语言来表述普世性和原生性的做法,其精神无疑就是符合《古兰经》的,可是,它命中注定要在天上潜伏六个多世纪的时间,直到它有朝一日作为天国的一份礼物,降落到了回历七世纪(即西历13世纪)在安娜托利亚生活的波斯苏菲大师哲俩伦丁·鲁米身上。其前和其后的许多苏菲大师也得到过启迪创立了一些摇动身体的做法,尽管看起来不像毛拉威耶道统的旋转舞那么壮观,可是作为集中注意力的得力助手,其效力一点也不逊色。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产生于穆圣时代之后的一些做法并非都是“关键性苏菲修炼方式”,因为,这些并不是所有道统的一致修持。然而,就其本身而言,它们无可争辩地具有关键性精神价值,所以,相对于其他那些均源自穆圣的被各个道统所普遍遵守的“关键性苏菲修炼方式”而言,它们可以被算作是一个例外——也许可以说,是个唯一的例外。 在伊斯兰教里,教乘从四面八方包围着道乘,而且一般而言,教乘对任何一种在穆圣时代没有授过权的做法和理论都持怀疑态度。这样的态度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一个异端邪说不在宣称自己是建立在一个独特的启迪(ilhām)之上的。在苏菲看来,这样的一些质疑会迫使他们去辨别真假,甚至保守机密,这一点并不对内隐之道构成一个不利因素,因为从穆圣生平最后几年的情况看,这样的一些疑虑在麦地那时代就已经扎根了。圣门弟子艾卜·呼莱勒说:“我在记忆中储藏了来自圣人的两罐子知识,其中一罐子我已经公开给你们讲过了,而那另一罐子,我假如把它公开的话,你们肯定会割断我的喉咙。”他是指着自己的脖子这么说的。(18) 自从伊斯兰教之初起,苏菲所取得的那些最重要的成就无疑就在学理领域之中,当然这并非是说苏菲在创立一些原则,而是说他们在用理论分析方式阐释伊斯兰教已有的原则。作为一个案例,我们已经看到伊本·阿拉比所建立的关于“不变之体”的那一异乎寻常的理论。显然,像他这样的学理阐释所引发的整个作品往往具有品级极高的启迪(ilhām)性质,由他本人以及其他一些人物撰写的苏菲文论也可以说具有同样的性质。同样,与此相关并具有相同性质的还有一些苏菲格言,它们处于与学理分析相对应的另一极,来自诗歌之光迸发的火花,或突发的警句,如“苏菲不是受造的”,“你的存在就是一件罪恶,没什么罪恶可以与这件罪恶相比”等都属于典型的苏菲表述方式,都具有彻底的内隐道乘性质。此外,这里也必须提一下被真主作为恩惠储存起来,预留给无缘与穆圣相遇的后人的那些普适性恩典,由于他们远离穆圣时代的吉庆,所以更需要这样的一些恩典。此类恩典关乎日后发展起来的一些表述风格,虽然其存在一开始依赖于苏菲,却与整个伊斯兰教息息相关。穆圣许诺说:“大地永不会缺少四十位像至仁主的挚友(即伊布拉欣大圣)那样的人,你们因他们而得饮,你们因他们而得食。”显而易见,这40位人就是构成宗教之心脏的那一内隐核心。正如人体内的心脏从上天接受神秘的生命礼物,并把它传送给其余肢体一样,被大家惯称为“伊斯兰教的心脏”的苏菲,则必然有义务要把自己接受的天国礼物充分地传送给这个宗教的所有动脉干线。与上述诺言中结尾的话有关的是,必须记住,每一个宗教在其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必然会发展出自己的独特文明,并使这一文明尽可能圆满地成为自己精神性追求的托板。每一个神圣宗教文明都有这样的托板,而这托板上占据着一个支配位置的要素就是神圣宗教艺术。神圣艺术远非仅仅是人的发明,其源头往往是作为一件礼物,从天国降下来的。神圣艺术史说明,在每一个时代和环境中,自己是无法割裂地与内隐之道捆绑在一起的,苏菲行知对伊斯兰教神圣艺术的发展产生过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影响,毫无疑义,这些影响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建筑艺术和书法艺术的影响了。(19) 然而,绝不允许末尾这几段文字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误以为苏菲行知也时不时地被所谓的“发展精神”所渗透。除了在天国启迪(ilhām)的指引下完成的那些成就——这属于圣道文明顺势成长的一部分。之外,苏菲人士是伊斯兰社会中最不可动摇的保守因素。也就是说,假如他们势必顺从于来自上界的压力,那么,他们已经证明,自己就像其他各种内隐之道的代表人物那样,在抵制来自下界的各种压力方面显得坚不可摧。来自下界的那些压力可以表现为“与我们生活的时代保持一致”的要求,苏菲一把挡开这样的一些口号,站在以永恒的准则判断万事万物的立场上,反问道:“这个时代值得我们与它保持一致吗?”同样的价值观念既包括对伊斯兰教精神性遗产最关键部分的觉悟,也包括要去保护她的坚强意志。在整整三代人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内,苏菲在近东和中东一直遭受了谴责,说他们应该为“穆斯林世界多个世纪以来的停滞”负责,在每一个穆斯林国家,他们作为抵制现代主义的最后前哨招惹了来自各方的敌意。只是到了今天,才出现了一些羡慕的眼光,这一趋势或许正在加强,承认苏菲人士站在正确的一方。 ①伊本·阿拉比.麦加开启录[M].贝鲁特:萨迪尔出版社,第2版,第2卷,16,214,263,561页。 ②《艾哈迈德圣训集》,第二卷,421页。 ③这是一句苏菲格言,有多种表述方式。法瑞顿丁·安塔尔在其《百鸟来朝》中提到了这句格言,还有许多其他苏菲经典名著也提到了它。 ④《布哈里圣训集》,第81章,37。 ⑤《穆斯林圣训集》,第51章,2。 ⑥《伊本·伊斯哈格圣传》,1000页。 ⑦《伊本·赛阿德圣传》,第三卷,289-290页。 ⑧《伊本·赛阿德圣传》,第一卷,112页。 ⑨福瑞斯杰夫·舒昂.幔帐与实质[M].斯托达特英译本.世界智慧出版社:1981.147. ⑩艾哈迈德·白赫根仪著,《大圣行》(淡泊章)。 (11)《布哈里圣训集》,第59章,1。 (12)《穆斯林圣训集》,第1章1节。 (13)《古兰经》在讲述真主的语言时,不仅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和复数都用),而且也使用第三人称,有时还在前后紧密相连的句子中转换使用不同的人称。这几节经文就是一个例子。 (14)伊本·阿拉比著,R.奥斯汀译.智慧的磨具[M],师斯(shīth)章.拉合尔:苏海勒研究院出版社,1988.60. (15)引自回历七世纪至八世纪(西历13世纪至14世纪)一部由无名作者撰写的题名为《授道的妙理》(Latāif al-i‘lām)的苏菲文论,这部文论则是从伊本·阿拉比撰写的那部可能已经遗失的《人的求道驿站》(al-Manāzil al-insāniyyah)中引述这段文字的。乔德基维奇把这部文论翻译为英文,让我得以引述,深表感激。 (16)马丁·林斯.二十世纪的一位苏菲圣徒[M].伦敦:1971.225. (17)艾卜·奈斯尔·散拉吉著,尼克尔逊编译.闪烁经[Z].伦敦:鲁扎格出版社,1914.150. (18)《布哈里圣训集》,第3章,42。 (19)参见:提特斯·布尔克哈特.伊斯兰教的艺术[M].伦敦:1976.又见:马丁·林斯.古兰经书法艺术与内明[M].伦敦:1976.13-41,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