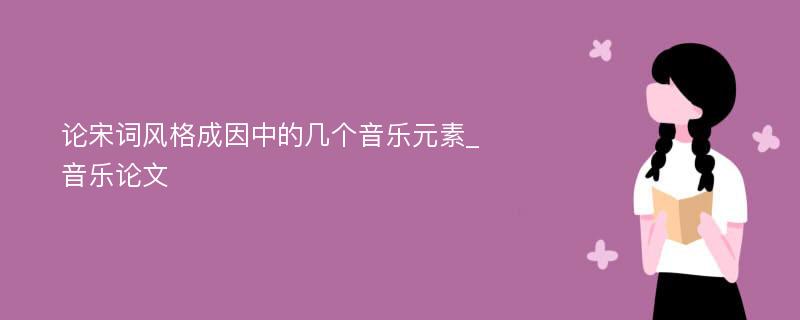
略论宋词风格成因中的几个音乐元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成因论文,宋词论文,元素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0)02-0101-06
作为一代文学之盛的宋词,名家名词众多,灿如繁星;流派风格不同,异彩纷呈。如果说风格即人,那么众多的词人词作,其个体风格确实无一相类。诸如晏殊的雍容娴雅,晏几道的凄婉幽峭,欧阳修的清疏深婉,柳永的自然真率,苏轼的狂放,辛弃疾的沉雄,秦观的清婉柔媚,姜夔的柔婉典丽,真是荆山之玉,灵蛇之珠,争奇斗艳,美不胜收。但如果把宋词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风格分为婉约与豪放两大类型,应该说已是共识。①
婉约及豪放风格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但如果我们把今天说的宋词回复到它的原始状态中,也就是回复到歌曲这一点来考究,应该可以找到一些相对简单明晰的答案。
宋词说到底就是歌曲,而歌曲则是文学与音乐杂交融合出的一个新的艺术品种。当然也可反过来说,歌曲这个艺术品种,可以分为文学和音乐两个部分。歌曲的文学部分就是歌词,由于种种原因,宋词的音乐部分绝大多数都已失传,即便有极少的曲调以乐谱的形式流传下来,但由于记谱方法的不够科学,如今已难以演唱。而这些硕果仅存的乐谱中保存的音乐信息也极少,如它的速度、节奏、配器、演唱等等,大都不甚了了。因此想根据原曲谱演唱以回复其原始效果风貌,几乎不可能。更何况宋代以后,词渐渐与音乐脱离关系,逐渐形成为一种新的诗体而不再供演唱。这样,宋词研究中对婉约和豪放风格的形成原因的探究,不得不集中到它的文学部分,即今天所谓的“词”上。当然,歌词本身也有不少音乐元素,如声韵,如句读长短,如对偶(字调要相反),如四声阴阳,但这些本文不论,只谈歌词以外的音乐元素。宋词毕竟是歌曲,而它的“依声填词”的创作方式更使我们在探究它两大风格类型的形成原因时不能不考虑其音乐部分。本文试图对宋词音乐部分中的几个元素略作分析,以了解它们对婉约和豪放两大风格形成的影响。
在分析宋词两大风格成因中的音乐元素时,我们不妨先从宋词中歌词与曲调的关系说起。
平心而论,作为歌曲,宋词的歌词部分也即我们今天说的“词”,对宋词风格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现在的歌曲创作,一般是先写出歌词,然后根据歌词的意义和所表达出的情绪情感,再进行谱曲,曲调的谱写很大程度上受到歌词的制约。它要根据歌词的意义情绪情感,写出旋律(也即曲调),选择适当的节奏、速度、配器,甚至还要考虑到由什么人演唱,是男声,还是女声,是高音,还是中音,抑或是低音。但宋词的创作路子却与此相反。它是“依声填词”,也就是说,宋词的创作,是先有现成的曲调(也可是“自度曲”,即由通音律的词人创作出的曲调)再根据曲调所表现出的情绪情感,填入歌词。歌词要表达什么情感,选用什么题材,采取什么结构,提炼什么词语等等,都必须考虑与曲调的适应。曲词情调相谐,也即所谓声情与词情相谐,才可成为一支好的歌曲。这样看来,歌词的创作,也就对其词风格的形成,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作为文学学科所学之宋词在谈到宋词风格的形成时,主要还是从宋词的文学部分也就是歌词着眼,但即使歌词创作,也与曲调脱不开关系。
在歌词的创作中,对宋词婉约和豪放风格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题材。以婉约词为例,它的题材,前人用八个字差可概括:男女之情,离愁别绪。主要写的是艳情。而豪放词呢,举凡怀古、感旧、状物、记游、寓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它“言壮夫之志,抒豪士之情,写达人之怀”。[1][p.42]那么,与婉约词相谐的曲调,也就应该是纤柔婉媚的;与豪放词相谐的曲调也就应该是豪迈、奔放、旷达的。因此,宋词的歌词创作,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选择与歌词情绪情感相适应的曲调,也就是所谓的“定曲”。但是,我们在宋词中,却可发现许多歌词与曲调未必相谐的情况。先看苏轼的两首《江城子》:
其一,《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见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其二,《江城子 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袒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前一首写儿女之情,柔情蜜意,情深似海,风格纤柔婉媚:后一首写英雄豪气,胸怀宽广,风格豪迈奔放。但两首词用的却是同一曲调。
再看辛弃疾的两首《鹧鸪天》
其一:
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 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重楼。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栏杆不自由。
其二: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檐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前一首典型的离愁别恨,后一首标准的豪士之情。一婉约,一豪放,风格的差异,再明显不过,用的却也是同一首曲调。这样的情况,在宋词中并不少见:辛弃疾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写了鼓乐大作、军营沸腾、沙场点兵的雄壮,激烈战斗的惊心动魄。即便结句“可怜白发生”的感叹,也是英雄报国无门壮志未酬的愤懑。其感情的迸发,真有“裂竹之声”,与《破阵子》的词牌名及曲调再适应不过,而李煜的《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呢,除了“几曾识干戈”的无奈,剩下的就是“垂泪对宫娥”的感伤叹息。其感情的哀婉欲绝,与《破阵子》“声闻百里,动荡山谷”“发扬蹈历,声韵慷慨”[2][p.297]的雄壮军乐,何曾扯得上边。此外,像《念奴娇》曲调虽说高亢,苏轼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曲词也还相谐。但词牌名多少有些柔弱。而李清照的《念奴娇 萧条庭院》却无论如何也不容易唱出高昂嘹亮的歌声;晏几道的《南乡子 新月又如眉》是典型的浅斟低唱,婉约之作,而辛弃疾的《南乡子 何处是神州》却大声鞺鞳,豪气十足;《浪淘沙》本是民间歌咏淘金人劳动情形的民歌,曲调怎么说也不至于凄婉,但李煜的《浪淘沙 窗外雨潺潺》却是那么凄惨;《临江仙》曲调清雅和婉,晏几道的《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曲词十分吻合,但苏轼的《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却全是狂放之气;《诉衷情》在花间词中只写男女之情,而陆游的《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却与风月了无干系而是苍凉激越之情。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种情况,宋代沈括早已注意到,并且很不满意。他在《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章中说:
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合。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3][p.24]
哀怨之曲调用以歌唱欢乐之情,欢乐之曲调用以歌唱哀怨之词,声情与词情是不相谐的。尽管沈括说这样“不能感动人情”,但宋代词人还是照写不误,歌手还是歌唱不已,而且使之成为文苑中的一朵奇葩,一代文学之盛,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应该说“依声填词”所创作出来的宋词,大多数曲词情调是相吻合的,当然也不是一刀切。苏轼“不喜剪裁以就声律”,[4][p.86]“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5](p.594)对作为文学和音乐结合的歌曲,他强调其文学性,有意削弱其音乐性。这或许是他同一曲调的《江城子》有两种迥异风格的原因。但宋代其他词人也有许多用同一曲调填词,各人所作风格却不同,这就很值得我们思考了。
其实,歌曲的创作,写出了曲谱,填入了歌词,只算完成了一半。因为词是要唱的,要“付之歌喉”的,另外一半,则需要选择歌手,进行演唱。那么,歌手的选择,演唱的方法,也就不能不影响到歌曲的风格。此外,歌曲的基本旋律,固然重要,但歌曲的旋律除了乐音组织之外,还受到调式、节奏、速度、音高布局乃至配器等等制约,这些因素只要稍加改变,其曲调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对改变乐曲风格来说,也是有决定意义的。所以沈括说“不能感动人情”,也就未必。
据俞文豹《吹剑录》记载: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6][p.138]
这段话,连大名鼎鼎的龙榆生先生,都只认为“是一个带有滑稽意味的笑话”,[7][p.229]但就算是个笑话,它却告诉我们,宋词风格的形成,与歌唱者有极大的关系。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豪放之作,“十七八女郎”根本不可能唱出那种“壮夫之志,豪士之情,达人之怀”,只能由“关西大汉”去唱,才能表现出苏轼的豪情。反过来说,柳永的《雨霖铃 寒蝉凄切》如果由“关西大汉”来唱,也无法唱出那种轻柔婉转,往复缠绵的情绪。倒是由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来唱,方显本色。如果说俞文豹所记的这段话只是个笑话,那么,苏轼的《与鲜于子骏》,就决不能只算个笑话了。
近颇做小词,虽无柳七郎之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以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8](p.207)
苏轼“作得一阙”的“小词”,就是《江城子 密州出猎》。那么谁来“首唱”呢?这里分明说到“首唱者”是“东州壮士”,因为只有这些壮士才能唱出那种“千骑卷平岗”的恢宏气势,那种“西北望、射、天狼”的激烈壮怀。这样的“小词”,给那些十七八岁女郎来唱,不论怎么唱,甚至喊,甚至吼,也不足以表达苏轼的豪放情怀。
但是,词在宋代,却又基本上是由十七八岁女郎来演唱的。这一特点的形成,却又自有它的历史渊源。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兰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9][p.174]可以说,词最迟在五代,已是由歌女“举纤纤玉指”按拍而轻歌曼唱了。原本歌唱,并不限于女子,男子亦可。从王灼《碧鸡漫志》所列“古人善歌得名”者看,男歌唱家甚至比女歌唱家还要多。但为何“今人独重女音”呢?[10][p.219]这是因为词本源于南朝乐府清商曲辞和宫体诗。南朝乐府清商曲辞的歌唱者已难考证,但宫体诗的演唱者为宫中歌女应无可置疑。唐代李太白之《应制清平乐词》显然也只会由宫中歌女演唱。词之发达在于五代权豪的歌舞宴饮,花间樽前。在这样的场合,歌唱的词,不可能配以豪放悲壮的音乐。词的内容也无非是男女之情,离愁别绪,而演唱者,也就用不着“关西大汉”或“东州壮士”,只能是年轻的歌女了。而女声之于男声,音色是明显不同的。以音高来看,男高音高亢嘹亮,女高音华丽柔美。男低音低沉浑厚,女低音最多只能说宽厚。至于中音,虽说介于高音低音之间,但男女中音仍有很大区别。即使发声音高相同,响度相同,但就其音色,我们的听觉仍能一一分辨,决不会混淆。总的说来,男声偏向阳刚,女声较为阴柔,不同的音色,适合于不同情绪的表达。这样看来,宋词两大风格的形成,也就不能不与演唱者有关。
除了与演唱者有关,演唱方法也值得注意。一支歌曲,演唱方法不同,风味是可以不同甚至大异其趣的。这个问题,曹丕早已注意到,他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11][p.60]意思是曲谱相同节奏一样的歌曲,由于行腔运气不同,歌唱起来,也就有巧有拙。歌唱方法,数不胜数,行腔运气之法,只是其中之一。而这一种,也是因人而异,千变万化的。这也是宋词两大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宋词的演唱方法,有一些资料可供参考,如沈括《梦溪笔谈》卷五的《乐律》,张炎《词源》卷上的《讴曲旨要》之类,但其内容多涉及正音吐字之法,而这些仅仅是演唱方法中的一种,且术语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古人所说“清讴曼唱”“引吭高歌”之类,其实已涉及行腔运气,速度处理,甚至演唱风格了。这样的演唱方法和风格,难道就不会影响到宋词两大风格的形成?《江城子密州出猎》的“首唱”,是“东州壮士”,他们怎么唱呢?“抵掌顿足而歌之”。今天看来,“抵掌顿足”似乎不过是配合节拍,但可以想象,在那样的场合,在那种强节奏中,这些“东州壮士”不可能是“清讴曼唱”,甚至也不是“引吭高歌”四个字就能概括,那必定是扯开嗓子的大叫、大喊、大吼。不如此不会是“颇壮观也”。一些不喜欢豪放词的人批评豪放词缺少含蓄,流于叫嚣,不够风流蕴藉,绝不仅仅是指歌词,显然也是与唱法有关的。这里还要特别特别提一提“嘌唱”这种唱法。宋沈义父《乐府指迷》中说:
古乐谱多有异同,至一腔有两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长短不等者。盖被教师改换。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12][p.44]
由于古乐谱的不同,早期词的字数并不是固定的,一个句子之中,字数是可增可减的,不像今天我们看到的宋词,同一词牌的词,句数、字数大都固定。但是,所谓“嘌唱”,却可在演唱时增减字数。其实,“嘌唱”不仅可以增减字数,连曲调也可做变化。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九说:“凡今世歌曲,比古郑卫又为淫靡。近又即旧声而加泛滟者,名曰嘌唱。”[13][p.44]“嘌唱”可以说是旧曲新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对旧有的歌曲做新的诠释,方法是“加泛滟”,即演唱时在主旋律的某些音符上加上一些装饰音。这些装饰音伴奏者可加,演唱者也可加,包括颤音、波音、倚音、滑音等等。音乐知识告诉我们,装饰音正是曲调风格的重要特征。装饰音过多,不免油腔滑调,所以程大昌才会感叹“比古郑卫又为淫靡”。这些都说明,演唱方法也是可以对宋词两大风格的形成,产生大影响的。
再说“配器”。所谓“配器”,是指乐队演奏乐曲(包括为歌曲伴奏)时所使用的各种乐器的搭配。不同的配器,适合于不同乐曲意义情绪的表达。
中国古代戏曲乐队有文武场之分,文场指管弦乐器部分,武场指打击乐器部分。文武二字,恰如其分的说明了两大类乐器的性质。文场之文,有文雅、文弱、文质彬彬的意味。是说管弦乐器音响不大,音色柔美。武场之武,有粗犷、热烈、有力的意味。当指打击乐器的音响巨大,音色刚健。其实细分起来,简直没完没了。譬如管弦乐器,即便同居文场,但管乐器与弦乐器音色音响音高相差不小。而弦乐器中拉弦乐器与弹拨乐器音色音响音高也不可等量齐观。总而言之,每种乐器都有不同的音色音响音高,把几种不同的乐器搭配起来演奏乐曲为歌曲伴奏,效果不同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如此,曲调也就有了“文曲”和“武曲”之分。词的风格,也就有了豪放和婉约之说。
前引俞文豹《吹剑录》中说柳永的词适合“十七八岁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红牙板即红木或紫檀木所制绰板,也叫拍板,属音色清脆音响不大的打击乐器。在器乐演奏或歌曲伴奏中起击节作用,也就是打打拍子。这里没有谈到演奏旋律的乐器,但苏轼词适合“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则谈到了演奏旋律的乐器——铜琵琶;击节乐器——铁绰板。这当然只是个比喻,所以才有“笑话”之说。琵琶并非铜制,绰板也没有铁的,那位“善歌”的“幕士”之所以这样说,是取铜铁等金属类乐器音色浑厚、响亮有力而言。其实已接触到了配器问题。而前引苏轼的《与鲜于子骏》则已明明白白的谈到了《江城子 密州出猎》演唱时的伴奏乐器:“以吹笛击鼓以为节”,打拍子不用绰板而用鼓,旋律的演奏则用笛。“击鼓为节”比起拍板为节,其音色音响显然不同。以击鼓为节,不用说是为了节奏的强烈。那么,以吹笛为伴奏,又有何音乐上的意义呢?
已故云大教授刘尧民先生在《词与音乐》一书中谈到了宋词演唱的配器问题。他认为,“燕乐以琵琶为主要的乐器”,[14][p.294]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但他说:
五代、北宋的词是以小令为主,这时所用的乐器是琵琶。到南宋时则慢曲流行,而乐器不用琵琶而用管弦乐器为主了。因为乐器一变,词的形式随之而变,而词之情调也随之而变。南北宋词是这样,南北曲也是这样。北宋以前之词“促碎”,是管弦乐器使之然。南宋的词“啤缓”,是管乐器使之然。[14][p.298]
他又说:
在弦乐器下产生的词,其形式是富于变化性,所以流利活泼,最适宜于抒情。而在管乐器下产生的词,则形式漫长,不及小令之变化多端。而不免流于呆钝沉思,对于抒情的价值上未免逊色。[14][p.300]
刘先生从音乐变化推论到南北宋词的风格变化,是很有些道理的。但以为伴奏乐器的变化是其关键,则稍觉简单。尤其刘先生以为管乐器使得南宋词变得“呆钝沉思”,则未免过于武断,很有必要做些探讨。本文反复提到的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的首唱,伴奏的正是管乐器中的笛。可是这支歌曲,却是公认的豪放之作。苏轼令“东州壮士”演唱,毫不谦虚地说“颇壮观也”,未见有“呆钝沉思”的一丝痕迹。那又是为什么呢?这还得说说笛。
笛古时又称羌笛,原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乐器。传入中原后,发生了变化。流行于北方的,形制短而细,音色高昂清脆,是后来北方梆子戏曲中的主乐器之一,遂称为梆笛;流行于南方的,形制长而粗,音色低回润厚,是后来南方昆曲中伴奏的主乐器之一,又称曲笛。《江城子 密州出猎》的演唱,伴奏当属梆笛无疑。梆笛不仅音色高昂清脆,音量也较琵琶大得多。正因为用的是梆笛伴奏,而且也只有用梆笛而非曲笛,这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的“首唱”,才会那样振奋人心。即使如南宋词,也有这样的情况。如《六州歌头》本是“鼓吹曲”,有笛伴奏那是必定的,但张孝祥的《六州歌头 长淮望断》,歌曲悲壮,音调急促,使人感慨。如果非要说南宋词“呆钝沉思”,而且一定要把原因推到“管乐器”上,那也只会是曲笛伴奏下的效果,不可一概而论。
关于演唱速度。音乐中的速度,是曲调演奏(唱)时每一拍快慢的表现,它受乐(歌)曲风格的影响,反过来它也影响乐(歌)曲的风格。这是探宋词风格时不能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宋词演唱时的速度,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不过“急慢”二字,虽语焉不详,但仍可见些端倪。
宋词中有长调慢词之说。慢词之慢,指的是曲调调长拍缓,这类曲调称慢曲,慢曲子,与急曲子相对而言。急曲子的特点是“声繁拍碎”,演唱速度快;慢曲则相反,其特点是歌拍散缓,演唱速度慢。慢曲的词调,一般在调名上都称有“慢”字,如《木兰花慢》、《卜算子慢》、《浣溪沙慢》等等。慢曲一般调长,但调长未必是慢曲(反之调短的未必是急曲),而速度的快慢,不能说不是宋词两大风格形成的一个原因。且看张孝祥的《六州歌头》: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此词共三十九句,三言句犹有二十三句之多,占了全词几近三分之二,其曲当属急曲子中的“促拍”,也就是所谓的“促节繁音”。三言短句,配合的是短乐句,而它的速度,是“促节”,也就是演唱时快速行进。这支歌曲如果把速度放慢二分之一,风格就会改变,那真会出现“呆钝沉思”的效果。哪里还有什么“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的感觉?[15][p.166]更不可能让张浚“罢席而去”。[16][p.295]
以上简略地谈了宋词音乐部分中曲调(旋律)、演唱者、演唱方法、配器、节奏速度等等对宋词两大风格形成的影响。其实,歌曲的创作及演唱处理,因素众多,千变万化,极为微妙复杂,常常只要改动其中任何一个元素,歌曲风格就会受到影响,更何况创作及演唱处理一支歌曲,往往多管齐下,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这些问题如果需要显而易见一些,不妨把今日之歌(乐)曲拿来作些参照发明,因为物有同理,理有同识。古今歌(乐)曲虽不可同日而语,但基本元素并无二致,完全可以推今及古。
改编自古曲《夕阳箫鼓》的民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所用乐器主要是琵琶、二胡、箫、筝,速度中慢,曲调悠扬典雅。此曲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的文艺表演中填入歌词以女声独唱,声情词情完全相谐,传达出中国古代文化悠远的韵味。但到了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上,此曲用来欢迎欢迎运动员入场,用的是西洋管弦乐队,速度加快了,风格完全改变,变为热烈而欢快;电影《末代皇帝》中,当溥仪的英文老师苏格兰人庄士敦离开中国返回家乡时,溥仪用了一支小乐队演奏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为他送别。但这支小乐队用的是京胡、笛子、笙,配器不同,与原歌曲风格迥异,颇觉滑稽;陕北民歌《骑白马》原歌曲轻佻滑稽,但把速度放慢,以西洋管弦乐队演奏,再填入庄重的歌词,歌曲内容性质已然改变,原歌曲的风格,被彻底颠覆;演唱《国际歌》,倘若把速度加快两倍,那就是“恶搞”了,完全妖魔化,毫无庄重严肃之感;国人耳熟能详的《哀乐》,在电影《大腕》中的葬礼上,速度加快了几倍,用的是民族管弦乐队演奏,毫无哀痛之感,而是兴高采烈,不无反讽;如今遍地皆是的碟片《红色经典》之类,把从前的一些“红色”歌曲作了重新演绎,找来一些音色甜得发腻的歌女,懒洋洋地唱着本属“革命”的内容,当年的那种浩气激情早已荡然无存;有的人唱歌往往加上好多装饰音,骚声浪气,无论什么歌曲从他们口中唱出来都成了靡靡之音。而蒙古族歌唱家腾格尔的演唱,即便是再婉约不过的云南民歌《小河淌水》,也透出一股阳刚之气。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对我们探究宋词两大风格形成的原因,难道没有启示吗?
[收稿日期]2009-12-14
注释:
①“婉约”“豪放”之说,最早见于明代张綖《诗余图谱·凡例》:“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此后还有“三体说”、“四体说”等等,但以词学界而言,“婉约”“豪放”之分影响最大,当无可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