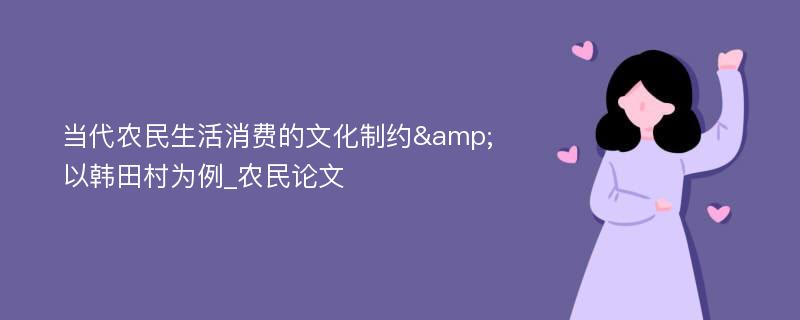
当代农民生活消费的文化制约——韩田村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农民论文,文化论文,韩田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活消费作为一种与生产行为相对应的行为,能够反映出当代农民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状况,能够反映出社会转型期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研究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农民的生活消费状况是较好的观察视角。
从经济学角度看,生活消费作为一种消费者行为,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消费者的主观态度,即消费者对一定价格的商品和商品组合的偏好程度;二是消费者的客观能力,即消费者的现实收入对一定商品和商品组合的购买能力。但从文化学角度看,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文化①。生活消费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观念、习惯的支配制约下所发生的文化行为,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他著名的《江村经济》一书中所指出的,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文化提供了各种手段来获取消费物资,但同时也规定并限制了人们的要求。文化建立起一个标准,对消费的数量和类型进行控制②。
本文以韩田村为调查点,试图对当代农民生活消费的文化制约作些探讨。
一
韩田村是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镇东北方向靠近山边的一个村落,以生产汽车摩托车配件为主要产业。1999年,全村共1135户,4752人,社会总产值4701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1010元。
该村共有30个村民小组。2000年6月至7月份,我们在开展专题社会调查组,分别从每个村民小组抽取3户样本户,全村共抽取了90户样本户,占全村总户数的7.92%。抽取样本户的标准是依照贫富程度,每个村民小组中好的、中等的、差的各抽取一户。在村干部的配合下,逐户进行问卷调查。
本文指称的当代农民生活消费,指的是农民用于生活方面的总支出,由房屋、耐用消费品等家庭资产和日常生活消费三部分构成。据调查汇总,1999年,样本户的生活消费情况如下:
表1 1999年样本户生活消费总构成单位:元.%
房屋耐用消费品日常生活消费总计
总数额65999970
16517430564534088162740
平均每户 733333 183527 62726979586
比例
74.86 18.73 6.40 100
表2 1999年样本户平均每户耐用消费品构成情况单位:元.%
手表 家具 燃气灶 油烟机 电饭烫 电视机VCD
价格
1868 13600 9836310
567 9000 442
比例
1.02 7.41 0.54
3.44
0.314.90 0.24
音响 空调 电冰箱 洗衣机淋浴器
微波炉
首饰
价格
7900 7633 2267
1839
1233384 11950
比例
4.30 4.16 1.24
1.00
0.670.21 6.51
电话 传真机手机
摩托车 汽车电脑 合计
价格
5028 965
11834 16382 80000
3342 183527
比例
2.74 0.53 6.45
8.93
43.59
1.82 100
表3 1999年样本户平均每户日常生活消费数额及构成单位:元.%
食品 副食品 酒店 衣着燃料水电
交通
数额 856 15647 11083 3533600 1683
6990
比例 1.36 24.94 17.67 5.630.962.68
11.14
通讯 医药
学费 书报娱乐人情
总计
数额 9017 3000
3633 3171834 4533
62726
比例 14.384.78
5.79 0.51
2.92 7.23
100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当代农民的生活消费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改革开放初期,农民除了房屋,几乎没有家庭资产。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基本上靠自给自足,即使有少量的消费支出,也是以满足实用为目的。而在1999年,韩田村村民平均每户的房屋价值733333元;耐用消费品的价值183527元。日常生活消费支出62726元,是1981年温州市农户生活费支出146.9元的427倍③。
我们知道,“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地区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世界通用标准。所谓“恩格尔系数”,指的是食品类开支在家庭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百分比,数值小意味着富裕;数值大意味着贫穷。如果系数大于45%,则说明这个地区还处于贫困状态。1981年,温州地区农村全年平均生活费支出146.9元,其中食品类支出86.8元,“恩格尔系数”为59%。而1999年,韩田村样本户的系数为26%。这说明,1978年以来,温州农民的生活水平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活方式的变革密切相关。韩田村世代务农,人多地少,民谚“韩田韩田,落后多年”就是对该村落后的生产水平与生活水平的生动概括。1978年,该村的年人均收入203元。自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以后,该村逐步发展起汽车摩托车配件制造业,生产方式逐渐从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向以工业生产方式为主转变,1978年,全村社会总产值250万元,其中农业产值为238万元,占95.2%。1999年,全村社会总产值47015万元,其中工业产值45837万元,占97.5%。这一年,全村2163名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351人,占16%,从事工业等非农行业的1812人,占84%。
根据韩田村村民家庭资产的形成状况,我们把它分为三个阶段:1980—1989年为形成期,添置的主要资产为老屋拆建的二层楼房、黑白电视机、自行车、手表、电冰箱、金首饰等;1990—1994年为增值期,添置的主要资产为电话、传呼机、彩色电视机、VCD、音响、摩托车及临街而建的四五层楼房等;1995—1999年为高峰期,添置的主要资产为传真机、手机、空调、微波炉、汽车、电脑及在工业区新建的合厂房和住宅于一体的别墅。而1980—1989年,该村人均收入从239元增加到763元;1990—1994年,人均收入从873元增加到3310元;1995—1999年,人均收入从6100元增加到11010元。两相对照,我们发现,20年来,在工业化进程中,村民的生活消费支出随人均收入增加而增加,而且增幅大致相等,生产方式、人均收入、消费支出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生产方式决定了生活消费的具体内容、结构和水平,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着生活消费方式的变化。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代农民的生活消费状况还与各种正式制度有关。如国家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使用制度、税收信贷制度、计划生育制度、殡葬改革制度等,都曾对农民的生活消费起推动或限制作用。
从广义上理解,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三大类,从大范围说,农民的消费行为无疑也受制约于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我们在前面的简略论述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农民的生活消费如何受观念文化的制约与影响。
二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最基本的单位是村落。几千年来,传统的村落家族文化在农村一直占统治地位,以自己特有的一套观念、制度和行为方式影响着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我们理解,传统村落家庭文化首先是一种乡土文化。土地是农民获得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主要资源,是农民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乡,即村落则是农民生活居住的场所。传统农民依恋与崇敬土地。其次是一种家族文化。家是村落共同体最基本的单元,具有生产、消费、文化教育等基本功能,家族则是扩大化了家庭。家庭和家族派生出血缘和地缘关系,构成了农村社区最普遍、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再次是一种礼俗文化。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社会是礼俗社会,维持社会规范的力量是文化传统,即礼俗。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农民的生活无不带有礼俗文化的鲜明印记。
人与动物的一大区别,是人的行为受文化决定。尽管在当代农村,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但这种转化是突然发生的,中间缺乏必要的缓冲与过渡,传统文化的迟滞性、稳固性、继承性、广泛性、社会性特点所形成的综合力量,还在发挥着巨大的惯性作用,继续制约着当代农民的生活消费,这主要体现在:
房屋仍然是农民生活消费的首要选择和最大支出。如表1,在样本户的生活消费总构成中,房屋的价值最大,所占的比例也最高。另据调查,1978年以来,90户样本户中,建过一次房屋的52户,建过二次的23户,建过三次的12户,建过房屋的户数占总户数的97%。
从全村范围看,1978年以后,该村曾出现过四次相对比较集中的建房热潮,第一次在1983—1985年间,村民在老屋基上原拆原建或在宅基地上建新房,建成新房屋102间;第二次在1986年,在前岸自然村旁的田地里建了一条新街,106户共建房屋162间;第三次在1990—1993年,在新街的西首建了一条大桥路,共建房屋65间;第四次在1994—1996年,在村庄的西南首划出土地250亩,298户在此建成房屋1042间。
农民如此看重房屋,是有它经济方面、文化方面的理由与原因的。从传统角度看,对土地的依恋和崇敬是农民的一个特点,传统农民一旦手里有了笔积蓄,最大的愿望就是将这笔资产转化、固定为田地。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土地这笔资产是最有价值、最为稳妥的,只有拥有土地才是村落的真正主人。但1949年以后,国家的法律制度禁止了土地的私人拥有和自由买卖,农民只得将这种对土地的依恋和重视转移到与土地密切相关的房屋上来。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的农村家庭是合生产、生活于一体的基本单元,无论是以种田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还是以汽摩业为主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发展生产都需要宽敞的住房为场所。从家族角度看,一个家族要保持生生不息、世代繁衍,就必须不断地裂变、扩大,就是说,一个家庭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就象水分流,树分杈一样自然地需要分家,而自立门户的前提之一是具备足够的房屋。同时,在信息资源共享的村落共同体内,农民的所有行为包括消费行为都与家族的荣誉有关。住房的优越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家庭在村落社区的层次和地位。如果住宅宽敞、豪华,对内而言,光耀门楣,象征着家族的共同荣誉;对外而言,显示实力,可为儿女的婚事增加筹码。房屋既然具有这种集经济上的实用功能和文化上的表意功能于一体的独特功能,难怪会成为农民生活消费的首要选择。
温州古称东瓯国,东瓯文化历来有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的传统。农民习惯于推己及人,他们认为,既然房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生活消费的首要选择,那么,在阴间的祖宗们肯定也会有同样的认识和愿望,因此,尽可能为去世的祖宗建造好的“阴间的住宅”——坟墓,就成为当代温州农民生活消费的另一重点。据我们对样本户的调查,1978年以后,有85%的家庭在村庄附近的大罗山(简称后山)和凤凰山(简称前山)为在世的父母建造过坟墓(当地人称生寿坟),或修理过祖宗的坟墓。按当时价格计,一座坟墓的一般造价大约12000元。
在农民的传统文化观念里,有阴阳之分,必定有因果报应,在冥冥之中,祖先的魂灵时刻都在监视子孙后代的行为,或加以保佑,或予以惩罚。只有对祖先多加崇奉,才会获得祖先对等的保佑④。在这种文化观念的支配下,1984年以后,随着农民经济收入的骤然增加,温州的沿海地区农村在建房热的同时,兴起了一股建坟热,坟墓越建越豪华,开支越来越大,直至1994年以后,温州地方政府在农村强制实行殡葬制度改革,严格禁止建造椅子坟,这股建坟热潮才得以遏制。与建造坟墓相联系,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食物的供奉、冥钞的祭献、忌辰的举行、祠堂的设立、清明的扫墓等构成了祖先崇拜的文化系统,同时,也成为当代农民生活消费中一笔不可节省的开支。
三
物质生产力是冲击传统村落家族文化内在逻辑和内在机制的根本力量。1978年以后,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由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商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生产活动的内容、形式、范围有了很大的变化,作为文化形态的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也随之出现变化,一种与传统文化相对的现代文化正逐渐在农村形成。
如果说,在传统家族文化的制约下,农民生活消费的突出特征是对“家族集体利益和荣誉”的重视,那么,受现代文化的影响,当代农民生活消费则呈现“注重自我、现时享受”的鲜明特点。
传统文化依靠社区内部祖祖辈辈长时间的凝聚积累,通过继承和传递的方式而内生为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与传统文化不同,现代文化是沿着从城市到乡村的路径,以扩散和辐射的形式,逐渐渗透传入农村的。有学者认为,与现代的接触是农民改变原有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的关键所在。学校、大众传媒、工厂和城市经验是个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最重要的背景因素⑤。
调查表明,1999年,韩田村1135户村民家庭,办汽摩配企业的98户,办家庭工厂的826户,从事运输、餐饮等相关行业的124户,就是说,自己办企业当小老板的占了92%。众所周知,温州的家庭工业是在计划经济的夹缝里长成的,原料、资金、技术、市场都得自行解决,严酷的生存环境与竞争压力逼迫温州农村的小老板们在实践中学习发展市场经济的本领,学习企业管理的经验。同时,频繁的流动与城市生活体验,使农民有机会置身于与传统村落文化迥然不同的城市文化中,潜移默化,逐渐受到科层组织,次属关系、制度规范等现代城市文化基质的感化与影响⑥。在“市场经济”这所大学校的培养下,当代温州农民逐渐形成了工业社会所要求的计划性、时间感、效能观念、契约原则、理性思维等现代文化品性。
1999年底,样本户的电视机平均拥有率达1.8台/户,收看电视节目已成为时下农民休闲的主要方式。电视所具有的迅速同步、形象直观、信息量大的特点,能够持续不断地把世界上大量的新观念、新事物、新产品、新时尚迅速传达到农村,对个人现代性品质培养的重要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就这样,现代文化逐渐改变着旧有的文化价值观,使当代农民形成了以“注重自我、现时享受”为核心的生活消费新观念、新倾向,具体体现在:
一是注重消费与发展的有机结合。样本户中,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电话、传呼、手机、摩托车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发展型耐用消费品,一些家庭还拥有传真机、汽车、电脑,这部分资产占了家庭耐用消费品总额的64.05%。另外,样本户平均每户一年交通费、电话通讯费两项开支为16007元,占全年消费总支出的25.51%。这部分消费兼有生活、生产的双重属性,从生活角度看,呈效用边际递减规律;从生产角度看,作为生产资料投入,则会在扩大再生产中产生更大的产出。这方面消费行为的出现和增加,固然是科技发展和时代进步的结果,但同时也反映了当代温州农民生活消费观念与行为的成熟与进步,一向有节俭、敛财、藏富习惯的农民开始懂得工作和生活都是美好人生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高质量的生活与消费对事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这一消费新特点还体现在对下一代的培养上。样本户户主自身文化程度的结构是:小学34%,初中53%,高中13%;而下一代孩子中,在读高中或高中毕业的38户,占42%,在温州、杭州、上海等地读大学的5户(其中3人为自费生),大学毕业的2户。据了解,供养一个孩子读高中,一年的总开支大约8000元,读普通大学的一年总开支大约20000元,自费生一年大约30000元,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文化教育消费,但许多样本户在接受调查时都表示乐意支出。在回答“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成为①有财富的人?②有知识的人?③有地位的人?④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人?”这道题目的时候,69%的家庭选择②,即希望孩子成为有文化的人。6号样本户说,培养孩子是长线投资,给他万贯家财比不上给他好本领。
二是享受型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增多。在样本户的耐用消费品构成中,电视机、VCD、音响、空调、洗衣机、冰箱等享受型资产占了23.23%。这部分资产不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但样本户的每百户拥有率却高达87.6%。另外,近年来,样本户的灶具、家具等生存型消费品也基本得到了更新,这种更新并没有改变此类消费品的基本功能,其本质也是追求高效与舒适感。
与传统的节俭积蓄行为不同,当代温州农民的享受型消费行为有追求现时消费、感官刺激的明显倾向。温州人讲究吃,韩田村一个村就开有酒店、小吃店20余家。样本户全年副食品、酒店消费为食品消费的31倍。9号样本户一家4口人,一天的菜金支出50元左右;温州人讲究穿,我们在韩田村调查时,样本户家的男主人大多穿着一件600元左右的鳄鱼牌汗衫,女的穿着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但都质地不错、价格不菲;温州人讲究玩,玩的最多的是打麻将、打“双扣”。我们在调查时设计了这样一道题目:“闲暇时间,你的主要休闲方式是:①看电视?②看书看报?③打麻将打扑克?④与家人聊天?⑤上街唱歌跳舞?”结果55%的人选择了③。一些人在访谈中认为,家人或朋友之间在一起玩玩麻将,一个晚上输赢几百元,这不算赌博。
三是注重身份显示与消费效用。当代温州农民在创业上敢为天下先,在生活消费上同样敢为人先。自1978年以来,从购买走私录音机、走私手表、梦特娇汗衫,到时兴骑上海产小凤凰自行车、穿阿迪达斯运动鞋、开日本产本田摩托车,再到近年的买传呼机、手机,买小轿车、个人电脑,富起来的温州农民掀起了一阵又一阵消费新潮流。从表面看,这似乎只是跟风赶潮流,但从深层次分析,这种行为却蕴涵着当代温州农民在消费时的身份显示心理和消费效用预期。就是说,在一定的精神文化氛围里,拥有某种商品或者进行某种消费行为,即显示了消费者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消费者通过这种消费行为,不仅获得物质上的实用感,还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这种消费心理有趋强倾向,如6号样本户在1996年购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1999年底,他以14万元的价格卖掉了这辆车,花38余万元买了一辆日本产本田轿车。他说,虽然都是轿车,但感觉和效果完全不一样。
四
把文化对生活消费的制约分为传统的与现代的,只是为了方便叙述的一种相对划分。实质上,当代中国农村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时期是“巨大的发展的连续体”。在社会转型期,传统的文化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方式与现代的文化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方式往往处于并存、重叠、糅合的状态⑦。
关系主义就是这么一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糅合体。
费孝通先生说过,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差序社会。在差序社会,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⑧。对这种因人办事的行为标准,社会学称之为“特殊主义”。与之相对应,现代社会的“普遍主义”行为标准则是独立于行为者与对象在身份上的特殊关系的⑨。但是,在当代中国农村,由于存在着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异质性、重叠性,一方面,特殊主义的行为标准已经开始退位,另一方面,普遍主义尚未成为社会普遍的行为尺度,于是,血缘、乡亲、交情等特殊的关系开始侵入货币、契约、分数这些普遍主义行为准则支配的区域,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糅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关系主义行为准则,即身份与契约共存,关系与成就共存,人情与原则共存。无论在政治生活,还是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人们无不受到关系主义行为准则的制约与影响。作为生活在社会转型期的“过渡人”——当代农民,他的一只脚刚从“传统”拔出,另一只脚刚踏进“现代”,生活在传统与现代双重价值系统中,因此,其生活消费除受主体自身文化价值的制约,势必也受到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糅合而成的关系主义社会心理和社会风气的制约。
关系主义行为准则在生活消费领域建立起一种标准,这就是生活消费的文化制约线。它指的是在一定社会心理的驱动下,在一定文化价值观的引导下,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在生活消费时,表现出的普遍流行的稳定的社会行为。文化制约线从全方位制约农民生活消费的内容、方式、数量、类型,但相对而言,对农民购衣购物盖房子等属于个人消费行为的制约较为潜在,对农民的婚丧礼俗、人情来往等与他人关联的生活消费行为的制约较为明显。在这些场合,生活消费的文化制约线往往是个体消费行为的衡量尺度,是社会交往的交换原则,是社会舆论的评判标准。下面,我们以85号样本户家的一场丧事为个案,观察文化制约线是如何发挥它的这些功能的。
这位村民是一家小型汽摩配工厂的企业主,经济状况在村里属于一般。他的爷爷去世后,一位曾担任过村里领导的宗族长辈主动过来担起了丧事主持人的角色。在征求了丧主的意见后,对丧事的进程作了详尽的安排。
三天丧事,这户人家的开支情况如下:(1)每天同时请吹打班、军乐队、请佛先生等三班人马吹念弹唱,其中第二天,还以1800元的价格,请了一支由8人组成的轻音乐团前来演唱,这部分开支10000余元。(2)共摆“小饭”50桌,酒席31桌,“小饭”每桌约150元,酒席每桌约450元,酒席部分开支21000余元。(3)购买用于赠送亲友的香烟、味精、香皂、洗衣粉、毛巾、饮料等物品的开支17000余元。(4)雇工人、租物品等开支4000余元。这样,85号样本户的丧事总费用大约为52000元。主事的那位同宗长辈说,按照乡风,该办的仪式都已经办了,这个丧事在当地属于中上档次。
作为亲族、亲戚、朋友,他们的义务不仅是在丧事中帮忙,在出殡时送丧,还要送人情,这也是文化制约线所早已规定好的。人情的数额视关系远近而有差别,大致是至亲2000元,一般亲戚1000元;至好朋友1000元,一般朋友500元、300元;近亲家族300元,一般宗族200元。讲究一些的亲友在送现金的同时,还要送花圈、花篮、被单等物品。一场丧事下来,85号样本户共收到22户宗族送的人情4600元,36户亲戚送的人情24800元(已扣除回礼),94位朋友送的人情43500元,共收到人情72900元。这个数字远远大于他的丧事开支52000元。当然,他也因此欠下了亲戚朋友的大量“人情”,这笔“人情债”要留待在以后的岁月里,别人家举办婚丧礼仪的时候慢慢地偿还。
灵柩出殡时绕村庄一圈。送葬的人们及其站立道路两旁观看的村民,其实就是这场丧事是否达到文化制约线标准的评判员,也是社会舆论的宣传员。85号样本户家的丧事,花圈、花篮二三十个,酒席摆了31桌,彩旗前导、鼓乐喧天,送葬的人数多达五六百人。因此,社会舆论的总评价是“这户人家人缘好、面子大、能力强”。与此相反,村民对丧事冷清家庭的评价是“为人差,独自孤命”。别小看这舆论评判,在信息共享的村落社区共同体内,这种评判将对被评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乃至儿女的婚事都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生活消费的文化制约线下,消费早已经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与家族的荣誉有关,是在尽社会义务。如果达不到文化制约线的标准,就过不了人生的一些关口,除非这个人愿意放弃自己在村落社会结构中的任何地位。因此,爱面子、重人情、讲关系的中国农民是那么一致地以文化制约线来衡量自己的消费行为,家境好的相互攀比,由此引发奢靡之风;家境差的负债消费,由此陷入贫困境地。由于文化制约线的存在,婚丧礼仪已成为一些农民沉重的负担。
但是,文化制约线的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价值日趋多元、规范相对缺位、信任程度降低、国家救济弱化的今天,文化制约线作为一种民间互助模式,以它的“互欠人情”为纽带,维持着人们之间高情感的来来往往,它对于克服当代农民普遍存在的乏力感,加强亲友邻里之间的有机团结和互助互爱,促进农村社区秩序朝文明方向的整合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标签:农民论文; 中国温州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家庭观念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