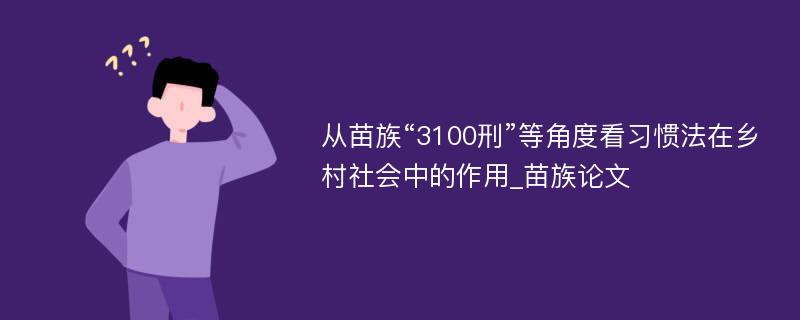
从苗族“罚3个100”等看习惯法在村寨社会的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苗族论文,习惯法论文,村寨论文,功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圈分类号:DF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5)03-0009-07
一
在我们对苗族传统习惯法进行调查时,几乎所有的苗族村寨都有对一些严重违反习惯规范的行为施以罚3个100(或3个120等)的惩罚,而且这些传统惩罚习惯,近年来还堂而皇之地写进了村民民主订立的“村规民约”之中,可见,即使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村规民约也部分反映传统习惯法的内容。
如雷山县郎德镇也利村“村规民约”第35条规定:“(触犯村规民约)第二次以上的,由其家长或监护人拿出肉100斤、米100斤、酒100斤(苗族习惯上称“罚3个100”),请村干部和全村寨老共同进行教育,并由寨老带其巡回全村喊寨一次。”有的村寨各增加20,为120斤肉、120斤米、120斤酒。
这种惩罚方法在现今苗族村寨中常被使用。1999年11月我们对雷山县陶尧片区进行调查时,据陶尧片区虎羊村村民唐千文介绍:同年7月,虎羊村的一名妇女偷盗别人家十斤李子,被发现后拒不承认错误,还找借口说谎,村里决定罚她三头猪,供大家会餐。但该妇女不执行处罚决定,并到片区告状。该村又决定对其罚款两千元,该妇女仍拒不执行,于是村里组织人到她家强行拿走120斤米、120斤酒,拉走四头猪,当日全村老小会餐一顿,以表示对偷盗、抵赖行为予以足够的惩罚。(注:1999年笔者在该地调查时,由唐千文讲述,笔者记录。)
有的村寨规定“罚4个120”。1998年11月,人类学学者周星教授曾在雷山县西江镇对苗族习惯法和苗族鼓藏节情况进行调查。在该镇新开的一间卡拉OK入口处挂有一个牌子,上面书写“严禁扰乱秩序和喧哗,违反者根据村里的规定,罚4个120,并且送派出所接受处罚。”周星教授访问了该镇羊排村的“鼓藏头”,根据“鼓藏头”的说明:“罚4个120”是西江苗族村寨对违反规则行为的处罚,即罚120斤酒、120元现金、120斤糯米和12000响的鞭炮,这与“扫寨”的处罚相当,对‘罚4个120’的规约所有人必须执行,以保证鼓藏节期间的社会秩序。”(注:周星:《习惯法与少数民族社会》,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协会:《文明21》第9期,2002年10月。)
2004年6月21日到23日,我们也到雷山县西江镇调查苗族习惯法的遗留与时代性变化问题,几年前周星见到的卡拉OK的门牌已经不见了,但我们在镇司法所收集到的西江各村村规民约中却有几项关于罚“3个120”的规定,如羊吾村规定:“农村在办红白喜事和集体举行娱乐活动等社会事宜中,借酒而闹事、吵架、打架等的人,抓到罚款120元,还要用120斤肉以上的猪一头,120斤酒来赔理”。麻料村“村规民约”规定:“凡划定的集体风景树不准任何人破坏,违者罚糯米120斤,肉120斤,酒120斤”。此外,“羊排村也东寨风景林保护民约”对破坏该寨风景林区的5种行为处以罚“4个120”在内的6项内容,即现金120元,白酒120斤,糯米120斤,猪肉120斤,响炮18万响,鸡、鸭各一只。(注:“西江镇羊排村也东寨风景林保护民约”,笔者在该镇司法所收集。此次调查时贵州民族学院世居民族中心副主任、苗族语言学者李锦平教授及贵州省社科院法研所文新宇陪同前往。)
雷山县丹江镇脚猛村“村规民约”规定:“寨内一旦发生重大火灾,村民必须全力以赴,不准擅自搬迁自家财产。等火灾全部灭后,不论灾情大小,由火灾发生户承担扫寨等责任。救火洗手猪一头,扫寨猪一头(100斤以上),大米120斤,酒120斤,肉120斤。”(注:周相卿:《黔东南雷山县三村苗族习惯法研究》(博士论文)第38页。)雷山县郎德镇也利村规定:“各自然寨一旦生寨火,村民要积极参与扑救,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同时罚纵火户救火洗手猪一头(100斤活气以上),120斤米,120米酒,供救火人员共餐,扫寨礼节仍按各自然寨原有规定执行。”(注:周相卿:《黔东南雷山县三村苗族习惯法研究》(博士论文)第52页。)
还有的村寨的“村规民约”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罚3个100”或“罚4个120”,但所罚实际数量已经超过这个数目。如雷山县郎德镇报德村“村规民约”第44条规定:“故意造谣诽谤他人,如某家有老虎鬼或某人有蛊(泛指神秘毒药)等,致使其声誉狼籍或人格受辱的,除罚款200元外,还要诬谄者供全村每个人口五两肉、半斤米和三两酒集体吃一餐(含柴火),以此避(辟)谣和消除隔阂;罚款百分之五十归受害者,百分之五十交村委会。”(1994年11月1日订立)这一规定从保护名誉权、破除迷信出发,是值得肯定的。
距这个村寨不远的该镇下郎德村就有过这样一个案例。1999年12月7日,该寨W某作东请客时,来客Y某酒醉说:“W某家以前有人染上过蛊”。W某知道很气愤,要求按习惯法,让Y某出100斤重的生猪一头、100斤大米、100斤酒,到W家杀猪摆宴,公开道歉。12月17日,Y某按照要求和家人一起带所要食物,到W家赔礼道歉,为W家洗去“染蛊”恶名。
那么,“罚3个100”来做什么?从上面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是全村的人一起聚餐一顿。这一点有的村规民约规定得很直接,如雷山县陶尧片区干皎村1996年对1991年订立的村规民约增加了几条补充规定,在这个“补充规定”的后面,又用手写增加了一条“严罚盗窃魔芋行为”的“补充规定”,主要内容是“盗窃魔芋的,除赔偿损失外,盗窃者应向被盗窃(魔)芋村民赔礼,请吃一餐。合伙作案的,应向全体村民赔礼,请吃一餐。多村人合伙作案的,应向该多村民赔礼,请吃一餐(1997年11月12日张贴于干皎村等村)。”这说明此时该村对经常出现的偷盗魔芋的行为实行“严打”。这种从传统遗留下来的惩罚犯罪方式——聚餐,从法人类学角度看应该有其特有的文化意义。
中国汉族地区,历史上也有某些法文化意义上相同或相似的习惯规则。如梁漱溟在《儒家文化要义》中引梁启超所著《中国文化史》“乡治章”,以盗窃为例,列举汉族地区乡村自治中的习惯规则:“犯盗窃者缚其人游行全乡,群儿共噪辱之,名曰‘游刑’。凡曾经游刑者,最少停胙一年,有奸淫案发生,则取全乡之所豢之豕悉行刺杀,将豕肉分配给乡人,而令犯罪之家偿豕价,名曰‘倒猪’。凡曾犯‘倒猪’罪者,永远革胙。”[1](第276页)杀自己的猪责令加害者赔偿和苗族直接罚取加害者家的猪,实际上是一样的,只是处罚思路不同而已。
二
现在贵州省的广大苗族地区,在经济和生活方面仍然非常落后,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没有因为改革开放的大潮而有明显的改变。从我们调查的苗族村寨的经济情况看,都出乎我们的想像。俗云: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这说明黔省雨量充沛,水源充分,但山地多,可耕地少。苗族传统的农业作物是水稻,但可以找到较大面积的可耕地极少。苗族喜居山区,受耕地的限制更为明显,寨前村后很小的一块地都要种上水稻,以解决相对紧张的粮食问题。耕种仍采用传统的方式,受地形条件限制无法实现规模种植和机械化耕种,水稻的品种改良也非常滞后。一些新的农业技术无法在本地推广。
由于封闭的环境养成苗族人比较温和、保守和安土重迁的性格。村寨中除少部分家庭有外出打工的,赚一些钱回来将房屋翻修一遍(苗族居住吊角楼一般为三层,均为木质结构。第一层比较低矮,主要放一些农具和栓养家畜家禽。二层是居室,隔开几间,供男女分住。第三层空间较低,接近屋顶,主要放粮食和杂物。近年新修的房屋第一层改为钢筋水泥结构,第二层以上仍有木质结构)外,大多数家庭还是比较破旧的吊脚楼。房屋均随地势而建,木楼鳞次栉比,聚成山寨。木楼与木楼之间过道窄狭,路况很差,卫生条件也不甚理想。屋内摆设也非常简单、破旧,虽然大多数村寨已经通电,但冰箱、彩电对大多数家庭来说还是奢侈品,一般没有经济能力购买,就像我们在电影《二嫫》中所见到的,很多家庭还为买一台电视机,在节衣缩食地攒钱。从我们在苗族家庭就餐情况看,粮食基本上是够吃的,但蔬菜不多,油水很少。一般在村头场坝上有猪肉出售,但普通家庭没钱买。鱼在每一家田里养一些,供招待客人,自己家也不经常吃。因为粮食和场地的原因,每家养鸡的数量不多,有尊贵的客人来访才杀鸡招待。
苗族一般是在过年(苗年)时才将养了一年的猪杀掉,这时可以尽情地喝酒吃肉。由于无法保鲜,大部分要熏制成“腊肉”,以供一年之中食用。由于苗族多居高寒山区,天气寒冷,加之食物相对匮乏,所以饮食习惯喜食“火锅”,多以酸汤为主,故而苗族“酸汤”名传遐迩。
长期以来,在封闭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得以基本保留。作为乡土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传统法律规范在国家大力提倡“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也没有很大的改变。历史上苗族村寨与内地农村相比,国家权力的介入水平更低,基本处于高度自治的状态,各种纠纷的处理、各种刑罚的运用,包括死刑的执行都能在村寨内部完成。像清朝那样民族统治比较周到、强硬,国家统治权相当巩固的朝代,面对部分苗族地区的情况也无可奈何,多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认可苗族习惯法的效力。
苏力教授在谈到中国内地农村法律状况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因素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还在重新改造着乡土中国。但是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国家权力在农村某些程度的退出,国家正式权力至少在某些地区对乡土社会的影响实际上是有所削弱的。即使是国家权力以法治的名义或方式进入乡土社会也很困难。[2](第47-53页)从我们对贵州苗族地区的调查情况看,苗族地区的情况尤甚于内地农村,所以苗族地区的法律情况在中国民族民间法的研究中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它的情况可能与汉族地区边远乡村相似,但汉族地区边远的乡土社会又缺少民族习惯法的独有特色,因此更显现出了它的研究价值。如电影《被告山杠爷》中,山杠爷以一套传统的习惯做法将山村“治理”得井井有条,但他的一些整治措施严重侵犯了村民的人权,如将一名刁蛮、不孝的妇女捆绑游村,出了人命,最终他还是被追究法律责任。而在苗族村寨像“喊寨”(相当于汉族地区的鸣锣游街)(注:西江镇羊排村“村规民约”规定:“如果任何家,任何人发生火灾、火警,每次罚款40元,造成火灾的户罚款100元以上,并罚敲锣打鼓喊寨一个月”。)、“罚3个100”等做法仍然被沿用,人们都认为是正常的事情,国家司法机关即使知道有这种情况,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的发生。受到“整治”的人也不愿意(或没有这种意识)到法院去起诉或向上级部门反映,因为这样做他以后在寨子里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更严厉的“整治”。
“罚3个100”等在苗族村寨是较重的惩罚,从村规民约的规定和惩罚实例看,多是针对屡次违反村规民约以及侵犯他人财产权、婚姻家庭和名誉权或失火、纵火、盗砍林木的行为。具体是针对盗窃、强奸(包括通奸)、诬陷他人为“蛊”等习惯上认为可使用这种惩罚的行为,根据情节的轻重和村寨人口的多少所罚的数量也不同。
前述,苗族家庭贵重的财产不多,加上长期封闭安定的环境,很少出现盗窃现象。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大多数村寨几十年没有出现过盗窃现象。即使出现盗窃一般也不是本村所为,很多是外地人经过村寨顺手牵羊,拿走村民的东西。几乎所有苗族村寨都是出不锁门、夜不闭户。牛马牲畜散放在山地上,用的时候找来,用完放出,一般都不丢失。采石、砍柴一时拿不回家的东西,用芭茅草打一个节放在上面,即表示物有所属,别人不会乱动,苗族人称其为“草标”。苗族村寨社会治安秩序良好,打架斗殴现象并不多见。
正因为这样,苗族人对偶尔发生的偷盗和打架闹事行为非常痛恨,惩罚也非常严厉。前举虎羊村一妇女偷人家十斤李子,这种行为本身尚未达到“罚3个100”的标准,问题是这种妇女态度特别不好,先是拒不承认错误,不交纳所罚牲畜,还向片区领导上告(片区一般对这种情况很难处理,只能推给村里“妥善”解决),不给村里“领导”面子,有损村“领导”的威信,所以才逐渐加重处罚。从罚三头猪,增加到罚款2000元,在这名妇女仍拒不执行的情况,村里才派人强行拿走米和酒,拉走她家的猪。这种激烈的执行行动,也是有“法”的依据的,如西江镇南贵村“村规民约”在规定了方方面面的11条规矩后,第12条规定:“以上各条,希望大家共同遵守,若受罚者到期交不出或抗交,一律做拒交处理,执行捉猪、拉牛、用家具、拆房屋、鸡鸭折价抵交,严重者交法律机关追究责任”。此外,对破坏乡土社会公共秩序和打架斗殴行为规定重罚,也是村寨安定的需要。
在苗族人们传统观念中没有强奸和通奸的区别,即使是在青年男女“游方”(苗族自由恋爱的方式)中发生两性关系,致使女方怀孕的,也要赔偿女方一头水牛,并责令男方娶该女子为妻。因为苗族恋爱虽然自由,但是以结婚为目的,“游方”是婚姻的前奏曲。一般来说,男子与有夫之妇通奸要赔偿三四头牛。随着时世的变迁,苗族的“村规民约”仍在传统的基础上具有了时代性的内容,注意到强奸属于犯罪范围,由国家法律处理,而通奸则属于道德范畴,村规民约就可以调整,对此有了既传统又有现代意义的规定,如雷山县郎德镇报德村“村规民约”第41条就规定:“对强奸和通奸行为,一经发觉,除供全村人吃一餐(数量另定)作消邪外,对强奸者押送司法部门依法惩处”。这里供全村人吃一餐的食物,不会低于罚3个100或3个120,所以才注明“数量另定”,可能实际操作中数目更大。对强奸者以习惯法处罚后,即供全村吃了一顿以后,还要交司法部门依法惩处,实际上是一罪多罚。
黔东南苗族地区雨量充沛、非常适合林木的生长,苗族人民至少在清代新开始植树造林。林木的利用和种植是一种社会行为,需要相应的规矩加以制约。在林业方面苗族有着丰富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范,几个世纪以来在森林的保护与利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苗族非常重视集体所有林木和“风景树”的保护,对偷砍“风景树”的处罚也是很重的。在我们所见到的村规民约中,对林木的保护规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注:徐晓光:《黔东南自治州传统林业习惯法规范与时代性变代——苗族、侗族林业习惯法的历史、现状及其与国家法律的衔接》,载徐杰舜,周建新主编:《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人类学高级论坛”2002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263页。)
苗族房屋多是木质结构,所以防火是每个村寨和家庭的头等大事,因此,对失火家户的处罚很重,前述脚猛村和也利村对火灾发生户或纵火者要罚3个120。“扫寨”是苗族村寨为消除灾害隐患,增强防火意识的一种宗教仪式。现在苗族村寨每年还举行这种仪式,各寨扫寨时间不尽相同,但程序都基本相同。仪式由鬼师主持,鬼师带人到每一家念鬼,用水将每家每户火炉里的火熄灭。等到每家的火神被送走后,全寨的人拉着一头水牛(有的村寨用猪),到寨前河对岸把牛(或猪)杀死,每户分一份,然后在扫寨堂中煮食,大家洗净嘴、手方能回家。另外,在杀牛(猪)之前派人到别的村寨买火,作为全寨的新火种。有的村寨由鬼师念鬼保留火种,人们认为鬼师念过以后,火种是安全的,举行过仪式后,各家用保留的火种重新生火。
举行扫寨活动,对于每个寨民来说都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村民们必须遵守相应的禁忌,如果有人违反就会使整个村寨处于危难之中。所以一旦有的家户失火,就必须承担扫寨的开销,包括规定中的扫寨猪一头和“3个120”等。近年来扫寨活动在苗族村寨经常进行,在防火安全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关于“放蛊”,唐律中就有关于“造畜蛊毒”的罪名。苗族“放蛊”的观念久远而神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一些民族学者都想解开这个谜,(注:详见吴泽霖,陈国均等著《贵州苗族社会研究》中“苗族的放蛊”和“苗族放蛊的故事”等文,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210页等。)但面临很多困难。因为“放蛊”都是在秘密中进行,谁家被“放蛊”,人们心照不宣,有意识地疏远“有蛊”之家。苗族人认为谁家有“蛊”不能说出来,否则就会发生纠纷,因为这是对家庭及人格的最大伤害。正是因为有没有“蛊”没有明确的证据,结果谁说出来就一定会输掉“官司”,必拿酒、肉、米去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当前这种习俗与国家法律中的人格保护制度冲突颇深,且由于蛊迷信的结果对被认为有蛊的人公开进行直接的人格伤害,任何人都不能直接说出谁有“蛊”,否则会带来麻烦,势必引起冲突。前述郎德村“村规民约”就规定对此类行为要罚款200元,分别交与受害者和村委会。另外罚供全村人聚餐的食物。按全村人口计数,每人五两肉、半斤米和三两酒,以此“辟谣和消除隔阂”。
按以上标准计算以一村200人计算,就是100斤肉、100斤米和60斤酒,大体上是罚3个100的数目。实际上大一点的村寨人口不只二百人。长期以来随着苗族人的繁衍,除一些小村寨外,现在大多数村寨人口都有几百人或上千人。人口的增多,所罚食物的数量也会增大。罚3个100可能只是所罚底线,在此基础上增加就是罚3个120,再倍数增就达到240或360,这正适合由于人口增长在罚餐时所消耗食物的需要。反过来,对当事人来说就成了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的灾难。拿出这么大数目的食物,当事人肯定是不情愿的,但是却抵不住强大的习惯势力,又不敢去法院或向上级申诉,因为村民基本上不知道起诉和反映问题的途径。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做了,他以后的麻烦就更大了,就会成为孤家寡人,为全体村民所耻笑,在村寨中难以抬头,所以只能“认罪伏法”,忍气吞声,以取得村民的原谅。
三
由于商品经济落后,大多数苗族家庭资财不多,可支配的现款有限,所以苗族多是罚畜、罚物;实施罚款的情况不多,即使是这样,对相对贫困的苗族家庭来说,“罚3个100”或“3个120”已经是很难承受的了。在我们调查中,问及被采访者为什么要罚这么重时,回答的几乎是一句话,就是“罚他倾家荡产”。由此可见,“罚3个100”等习惯规则首先是它的惩罚意义,说明传统习惯法也很重视对公私财产权、人格权和婚姻家庭关系的保护,致力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对破坏这种乡土秩序的人必给予严厉的惩罚,使这类事件以后不再出现。这是习惯法实施惩罚的主要目的。
一般来说对大多数村民和受害人则呈现出另一种心态,他们要通过惩罚及相关的活动,发泄他们憎恶“犯罪”的情绪,这里习惯惩罚又体现它的宣泄功能。法律活动是宣泄不平情绪的重要渠道,人们和社会组织通过诉讼和仲裁程序进行指控、辩护或辩解,在司法机关主持下解决具体纠纷,当具体纠纷得到公正解决时,不平情绪也就随着消除。甚至审判与刑罚执行过程也具有明显的宣泄功能,如中国古代法场上人们对罪大恶极的罪犯投以石块、呐喊、咒骂等,是人们对犯罪痛恨情绪的宣泄。明清时期,在凌迟刑执行过程中,还准许被害者家属到刑场“生啖其肉”,这是中国古代法律设计的对被受害者家属的抚慰和宣泄仇恨情绪的途径。在少数民族传统的司法审判中,这种宣泄作用体现得尤为明显。解放以前,苗族人对重大争端,缺少证据或调解不成,或对判决不服的,喜欢选择“烧汤”的形式来解决。烧汤神判用的三脚架,约五尺许,一口深锅高置其中,将米、油、斧子放入锅内,大火烧煮,然后架梯于锅旁。双方当事人,分为“烧方”、“捞方”,双方当众辩理后,“捞方”伸手入锅内取出斧来,手起泡为负,“烧方”则胜;手不起泡,则“烧方”负(烧汤时,习惯上把烧汤一方称“雌方”,把“捞斧”一方称“雄方”)。与此同时,烧、捞两方亲朋人等分别站在锅的两旁。当烧汤理词念毕,“理老”一声令下,叫准备捞斧。捞方在他们声援者的呐喊助威下,便七手八脚地把柴火退出灶孔,而烧方人则在他们助威者的叫喊下争着将退出的柴火又放入灶孔中去,以使火烧得更旺。[3](第79页)双方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已经形成固定的仪式。捞斧者在双方争夺柴火之中,完成这一神明裁判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双方的助威者、参与者,甚至捞汤的人内心积压已久的怨恨借助“神”的力量渐渐得以释放。
美国著名法人类学者霍贝尔在谈到美国北部沿海爱斯基摩人原始法律时说:“如果斗歌在解决争端和恢复已疏远的团体内部成员的关系方面有所帮助的话,那么它就是法律上的一种措施。参加比赛的双方的一方将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然而不可能有按真实的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特权作出的公正的判决。通过赛歌,参加赛歌双方感到轻松,怨言也被放置一旁。即从心理上获得满足,权衡丁恢复如初的利弊。……因为斗歌中无残酷折磨的因素。超越自然的威力也有助于加强这些有自主权利的歌手的勇敢。我们应当牢记,这种对歌唱者或歌唱的结果并不重要(尽管或多或少积累了一些控告有罪的事实,来反对他的对手的歌唱者在事实上处于有利地位)。由于法庭上的比赛可以成为在辩护律师双方中的一场体育运动的项目,所以,法定的歌赛首先就是——所有比赛都是为了提供最大的快乐。”[4](第86页)
苗族没有文字,所以口承法律文化非常丰富。在传统的司法审判中,理师(法官)的调解和审判,当事人双方的自我辩护都通过唱词表现出来,生动形象,朗朗上口,讥讽、嘲弄蕴含其中,这种反映司法过程的唱词被称为“理词”。石宗仁翻译整理的《中国苗族古歌》,第七部分“婚配”,第八部分“纠纷”,从分类上应属于“理词”,但形式上却是古歌。下面摘录其中几段有关苗族婚姻纠葛的古歌:
首先是婆家对儿媳的行为进行指责:
“婆家请来天才的理老,婆家请来天才的理郎;你俩的智心象光辉的北斗,你俩的慧眼象耀眼的星辰。……讲的是他家的这个姑娘啊,在我家不肯好好做工,不肯好好做人。割草她跨过高山,拔笋她越过峻岭。他上山去吹传情的木叶,他上山坡去打风情的口哨。她跟人站在看不清的暗处,她跟人坐在看不见的地方。……她家的姑娘啊,破坏了世上的德行,她家的女娃啊,忧乱了人间的理规。败坏了我的家室,脏污了我家的名誉。……我才来请理老,我才来请理郎。”
此时娘家一方也在现场,开始唱道:
“我娘家听了理老传来婆家的话,我娘家听了理郎转过婆家的理。婆家父母和儿子来到理场,娘家父母和姑娘来到理场。理场来了很多亲友,理场来了很多人。现在轮到娘家来讲,现在轮到娘家来答。我娘家有理说给理老细听,我娘家有话讲给众亲分明。”
接着娘家辩解并反驳道:
“你婆家讲我家的姑娘,说我家女娃,在你家不好好做工,不愿好好做人,我要问你婆家她做什么?要问你婆家她为何不做?你要说我姑娘割草越过崇山,你家讲我姑娘拔笋跨峻岭。问你过山过了多高?问你跨岭跨了多远?一个栏里,猪你提得了两头;一个笼里,鸡你拉得了两只。那理亏是我姑娘,那理输是我姑娘。……说理给老理郎来评,说理给大庭广众来听。你家不把姑娘当人,不把我姑娘当媳。姑娘一天要受你家奚落千回,姑娘一晚要受你家骂百次。……”[4](第86页)
婆家和娘家经过充分的辩论后,理老根据古理,划清是非责任,纠纷才得到解决。这里正如拉斯穆森说:“K和E就是这样,看起来像是彬彬有礼地互相奚落对方,并唱出自己的辩解之词……。”(注:石宗仁翻译整理:《中国苗族古歌》第八部分“纠纷”,天津古籍出版1991年12月出版。)可见苗族的传统“司法”是一种“歌唱司法”。
四
日本学者汤浅道男等编著的《法人类学基础》一书中,收有莒本胜《哈奴诺·曼仰纠纷处理法——菲律宾·明都洛岛的固有法》一文,其中讲到哈奴诺·曼仰的各个村落以前对不义不贞(如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盗窃、恶语伤人等名誉侵害行为,要对加害者进行处罚。即判处加害者准备自己所罚的慰寄费比索(有的时候作为赔偿交付实物和现金)和向参加者提供食品。加害人在交慰寄费时要向被害者道歉。按哈奴诺·曼仰的价值标准,比索价值为最高,所以对他们来说支付慰寄金是经济上的重大负担。其中慰寄费是交给被害者的,提供的食品则是村民们共同享用的。“加害人向参加全体人员提供食物(大量的米饭和猪与鸡做的莱),这与仪礼、祭祀时的食品规格相当。前述菲律宾·明都洛岛哈奴诺·曼仰人的村落要求,作为处罚的食品必须准备,对加害人来说也是很重的经济负担,而对其他的参加者则是快乐的事情。特别是在粮食不足的雨季(5月到10月份),人与人之间积蓄着不满,为了熬到睛天就飞各种各样传闻。这时由于富裕者(米和家畜)很多,大家就会对他们所嫉妒的人以各种理由起诉,人们听到要开审判会议都非常高兴。这种情况下,裁判人的处理方法是将鸡毛蒜皮的小事当大事情来处理,从而为大家搞定一次吃喝,准备伙食的过程中参加者共同来做,然后进餐。”[5](第130页)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郁闷的心情得到宣泄,渐渐变得愉快起来。
苗族“罚3个100”等传统的惩罚方式同样有着多功能的作用,即惩罚、警诫、宣泄、娱乐、教育等作用。通过聚餐既惩罚了违反习惯法的行为,同时在此项活动中教育了村民,让村民亲眼目睹受重罚之惨,提高“守法”的认识。与此同时,大家在开荤、饱口福活动中的一些细节,如交谈、笑话戏谑等,又本身带有娱乐的功能,起到融洽村寨社会人际关系的作用。宣泄与娱乐作用是不可分的,有时宣泄是娱乐的前奏和形式,娱乐是宣泄的目的和结果。比如一些人在卡拉OK中声嘶力竭地唱歌,就是一天劳累和郁闷情绪的宣泄,同时会渐渐地达到娱乐的目的。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讲到:“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呀学语时,他已是所属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社群的习惯便已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已是他的戒律。每个出生于他那个群体的儿童都将与他共享这个群体的那些习俗,而出生在地球另一面的那些儿童则不会受到这些习俗的丝亳影响。”[6](第5页)在苗族传统的村落社会中,人们已经习惯了诸如“罚3个100”等惩罚方式,并积极地参与与其相关的各种活动之中。虽然这些方式不为现代国家法律所接受,但在苗族村寨社会人们愿意这样做,习惯这样做。如前举虎羊村妇女偷窃李子事例中,那次会餐时该片区的双语(苗语和汉语)教员,农民教育专干唐千文就在场,他当时曾指出这种惩罚方法是违反国家法律的做法。据他自己说:“我自以为自己有文化,年龄也比较大,在村寨中素有威信,说了以后大家可能会听”。可是还没等他把话讲完,就被众人呵斥,险些被打,只好乖乖地坐下,吃到聚餐结束。
收稿日期:2005-0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