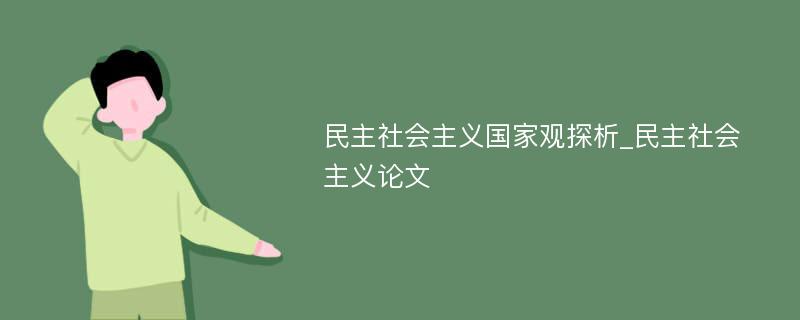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社会主义国家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论不仅是民主社会主义整个思想体系的主要基石,而且是各国社会党制定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探讨这一国家学说,对于我们正确分析各国社会党政策的发展和变化,认清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的实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学术价值。
一、超阶级的国家观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国家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一种支配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人类共同享有的组织体。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写道:“国家应当成为一个从各种社会力量中吸取其内容并且为人的创造精神服务的文明国家。”(注:[德]苏珊·米勒、海因里希·特波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求是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第347页。)1986年8月,该党通过的新纲领草案(依尔塞草案)说得更清楚:“国家并不是必然要成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者有势力的利益集团的工具。国家也能够成为按更加民主的方向变革社会的那种势力的重要工具”。(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草案》,第25页,波恩德文1986年版。转引自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页。)奥地利社会党纲领指出,本党的目的是使国家人性化,而不是使人国家化。该党领袖及理论家布鲁诺·克赖斯基在谈到国家问题时指出:“重要的问题在于,不仅要控制权力,而且首先确定它在道义上的意义”。(注:《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德文1975年版,第14页。转引自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页。)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人的生命、尊严和良心是高于国家之上的。……国家应当为每一个人在独立的自我负责和履行社会义务的过程中得以发展自己的个性创造先决条件。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应该保障个人在国家面前享有自由,而且还应该作为组成社会共同体的权利来参与奠定国家的基础。”(注:[德]苏珊·米勒、海因里希·特波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第346页。)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认为,“国家应当为经济公民设定一个可靠的框架,保证他们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在国家作出经济上重要的基本决定——特别是关于税收的——时有参与的可能,而在其他方面则让经济和社会中发生的事情及其结果听凭客观力量的活动去支配。”(注:[德]托马斯·迈尔著:《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页。)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民主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抽掉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个实质,而把国家人格化,国家就成为超阶级的“全民国家”了。可见,超阶级性和人格化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的两个显著特征。
民主社会主义对国家性质的分析,是以他们对现存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为基础的。在民主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稳定的,因此,不需急于改造。基于这种认识,他们确定自己经济政策的基础是经济民主。法国社会党1969年原则声明强调,“经济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特点。”(注:[法]让·马雷、阿兰·乌鲁著:《社会党历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86页。)目前各国社会党普遍主张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并在这一框架内由国家对生产和市场实行宏观调控,主张工会和工薪劳动者参与经济决策和企业的生产管理(即所谓的经济民主),同时维护社会福利国家。这种认识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从第二国际起,社会党的各派基本上一致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主要是国有化)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民主社会主义起初仍旧主张这一观点,一些执政的社会党还曾努力推行国有化。后来它们逐渐改变看法,不再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主要标志。1997年英国工党决定修改党章第四条,取消其中关于公有制的主张,突出地说明了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观念方面的这一根本性变化。其次,他们认为,战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白领阶层”即中间阶级,使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得复杂化。他们声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已经停止,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正在趋向缓和,革命已成无益的冒险,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自身的不断调节,能够减少失业,避免经济危机。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工人阶级已丧失“历史动力的那种主导作用”。(注:[德]托马斯·迈尔等著:《论民主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141页。)实现社会主义已不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上的阶级不再以对立的姿态出现,而是彼此进行合作。因此,只有通过阶级合作,才能达到“和平地实现社会变革”的目的,而阶级合作的最好方式是改良。他们声称自己是作为改良主义的继承者出现在西欧、中欧的工业发达国家的。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表现在民主和专政问题上,就是把民主超阶级化,认为民主和专政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政治范畴,无产阶级专政妨碍了人性的自由发展,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合理形式。1951年《法兰克福宣言》强调,民主社会主义包含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三方面内容。宣言称:“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手段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注:金重远著:《战后西欧社会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9页。)宣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对苏联和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了抨击。1978年奥地利社会党党纲指出,“民主和专政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社会党人是“法西斯专政和共产主义专政的坚定不移的和毫不妥协的反对者。”(注: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7页。)1986年社会党国际《利马委托书》,“表示反对一切形式和一切阶级的专政。”(注:金重远著:《战后西欧社会党》,第254页。)法国社会党1987年原则声明强调,社会党是民主的政党。“自由既和经济民主相联系,也要充分发挥政治民主、社会民主和文化民主。”(注:[法]让·马雷、阿兰·乌鲁著:《社会党历史》,第189页。)该党1990年原则声明再次强调,社会党承认各种自由是相互联系的,“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充分行使自由,是促进和深化民主的必要条件。”(注:[法]让·马雷、阿兰·乌鲁著:《社会党历史》,第190页。)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民主制度的危机导源于它还不够民主。”(注:[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5页。)
在民主社会主义看来,专政无论是什么阶级的专政,都意味着独裁,意味着对民主的践踏。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明确地讲:“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基督教”。(注:内恩宁著:《社会民主党》,维也纳德文1965年版,第144页。转引自黄安淼、张小劲编:《瑞典模式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页。)
总之,在社会党人看来,国家已不是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而存在,而是社会各派政治力量、社会集团为扩大影响、争取权力和创造机会而斗争,并按照预先确定的规则彼此争论、相互理解和结成联盟的政治制度,是能够朝着民主的方向变革社会和经济的这样一种进步的社会势力的重要工具。社会党人对国家内涵作出的上述界定成为他们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将民主超阶级化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据,从而导致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性质。
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来源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如果仅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来说,可以追溯到拉萨尔主义。而伯恩施坦、考茨基则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拉萨尔抽象地谈论国家的永恒本质和使命,认为普选权的实行是国家社会化的开始,强调工人阶级单凭利用普选权就可以对现存国家进行干预,并能帮助工人阶级摆脱困境。
第一,国家是道德规范的共同体。拉萨尔认为,“国家是个人在一个道德整体中的统一”,(注:《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第71页。)“这种合乎道德的国家观念是推动国家前进的动力”。(注:《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第83页。)他把发展自由、使人类朝着更自由的方向发展看作是国家的崇高使命。他认为:“国家的宗旨就是使人的本质能够积极地发展和不断地完善;……就是教育和推动人类走向自由”,“就在于实现这种自由的发展,实现人类向自由的发展”(注:《拉萨尔言论》,第71页。)。可见,国家道德化是拉萨尔国家观的本质特征。
第二,普选权绝对化。在拉萨尔看来,争取合作社与争取普选权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争取普选权以建立民主国家,然后在国家帮助下建立合作社,以解放工人阶级。可见将普选权绝对化是拉萨尔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伯恩施坦继承和发展了拉萨尔的国家观,并直接推动了社会民主主义由革命向改良的转化。
第一,国家是实现共同意志的社会组织。伯恩施坦提出了关于国家本质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国家是一种共同生活的形式,是一种管理机关,它的社会政治性质随着它的社会内容的改变而改变”。(注:《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第442页。)就是说,随着社会管理职能的加强,国家已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巨大的共同利益的天然捍卫者,国家已不再是有产者事业的代理人了。他引用了英国工党创始人和改良主义政治家麦克唐纳的一段话,来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1909年,麦克唐纳在一篇论述社会主义和政府的论文中,针对恩格斯关于国家的经典定义写道:“国家不是政府也不是社会,国家是各个独立民族组织起来的政治个体,是一个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其共同意志的社会组织”。伯恩施坦认为,“这是在无私的历史裁判面前能够长期站得住脚的一个关于‘国家’的定义”。(注:《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第443页。)可见,伯恩施坦承认在不具备社会经济利益一致性基础上,能够构成集体的全体成员的意志总和。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是一种批判的国家观,是只看到了国家的镇压职能,忽视了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的职能。他认为国家的镇压职能是19世纪以前国家的特征,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国家的主要职能已经不再是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工具,而是越来越多地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充当社会生活的管理者。
国家是实现共同意志的社会组织,这个定义可以说是伯恩施坦全部国家理论的基础。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构成了他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看法及其基本态度。伯恩施坦根据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生的新变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具有“更为巨大的扩展和改进的魔力,其发展延续得更为长久”,“这一经济形态现在就完全不可避免地会创造出新的组织形式”。(注:伯恩施坦著:《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第4页。)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不会马上灭亡,而且具有一定的弹性。
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认识,伯恩施坦认为,不必运用暴力革命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而主张对这一制度进行点滴改良。他认为,“具有各种僵化的等级制度的封建主义几乎到处都必须用暴力来炸毁。现代社会的各种自由制度同那些制度的区别恰恰在于,自由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为此需要组织和积极的行动,但不一定需要革命的专政。”(注:伯恩施坦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第208—209页。)他认为,从政治上看,“一切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特权一步一步地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注:《伯恩施坦言论》,第73页。)因此,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全部理论和实践应归结为在促进和保证现代制度不发生灾变的情况下过渡到一个更高级的制度。
第二,民主既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又是社会主义的最终形式。对于民主这个政治概念,他不赞成把它解释为“人民的统治”。如果这样定义的话,会给多数人压迫少数人这一思想留有余地,而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不民主的表现。他认为,“民主这一概念包含着一个法权观念: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注:伯恩施坦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90页。)他认为,民主在实现社会主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在论述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时说,“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注:伯恩施坦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91—192页。)他认为民主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美洲大陆都证明是“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杠杆”。(注:伯恩施坦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92页。)“说到作为世界历史的一种运动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不仅是对它在时间上的继续,就是从其精神内容来说,社会主义也是它最正统的继承人。”(注:伯恩施坦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97页。)他还说,虽然自由主义最初获得的固定形态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但这并不妨碍它“在事实上表现一个更为广泛深远得多的普遍的社会原则,这一原则的完成将是社会主义”,因此“可以把社会主义也称为有组织的自由主义”。(注:伯恩施坦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200页。)
如何通过民主去实现社会主义呢?伯恩施坦认为,关键问题是工人拥有普选权,“民主选举权是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更大权利和贯彻更多的旨在改造社会的措施所能运用的巨大杠杆。”(注:伯恩施坦著:《什么是社会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第19页。)普选权“随着工人的数目和知识的增长,它就成为使人民的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成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注:伯恩施坦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93页。)所以,伯恩施坦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选制当作把整个世界翻过来的“一块立足的地方”,宣称“给我平等的普选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注:《伯恩施坦言论》,第389页。)由此,伯恩施坦把阶级斗争的文明化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他说:“我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的到来或将要到来,不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决战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其活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一批经济和政治胜利的结果。不是工人所受的压迫、贫困和屈辱大大增加的结果,而是他们日趋增长的社会影响和他们所争得的经济、政治、一般社会和道德的相对改进的结果。——我看到阶级斗争本身采取愈来愈文明的形式,我正是把阶级斗争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这种文明化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注:伯恩施坦著:《什么是社会主义?》,第25页。)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失去意义论。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时候,是将法国革命的恐怖时代当作典型事例的,它对于铲除封建主义及其等级制度来说是适用的。但是,随着时空的变化,“继续谈论‘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句话已经过时了”。如果要用“专政”这个词,必须有个条件,即只有把专政一词的实际意义去掉并且赋予它随便什么削弱了的意义,才能使这一词和现实相一致。他断言,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具备自己十分强大的经济性质的组织,并且没有通过在自治机构中的训练而达到高度的思想独立性的地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俱乐部演说家和文人的专政”,(注:伯恩施坦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261页。)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属于较低下的文化。如果一定要坚持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可避免要通过这一形式去实现的话,这种思想只能看成是“一种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由此,伯恩施坦得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结论,即用民主的手段,以普选权作为杠杆,以议会为场所,在不打碎资产阶级国家的前提下,通过改良的途径,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
考茨基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说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如何对待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
考茨基认为,“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民主同样也意味着保护少数派”。(注:考茨基著:《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1963年,第20页。)他认为,人按其本性不只是社会的人,而且是要求民主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追求民主是人从他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社会本质的一个方面。考茨基对民主的理解决定了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他认为,专政只意味着镇压和暴力,而不可能成为民主的一种形式。他把马克思总结历次革命经验得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公式,说成是马克思本人信手拈来的一句话,这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并且认为,马克思当时只是想用它来表明一种统治状态,而不是表明一种政体。
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说评价
(一)民主社会主义否认国家的阶级性,是为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服务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本质是它的阶级性。恩格斯指出,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列宁指出,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组织”。(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页。)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关。国家的本质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即国家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组织,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组织,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组织;国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机构,它虽然是管理全社会公共事务的机关,但首先必须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说明,国家具有明显的利益性、排它性和强制性,国家的实质是它的阶级性。民主社会主义把国家看成是一种超阶级的人类共同享有的组织,从而否认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其目的是否认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
(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国家观所依据的前提条件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变化,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第二,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对其生产关系作了一些自我调节,最主要的是发展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三,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导致了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这些新变化说明,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国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和中间阶级的心态与愿望,因此,民主社会主义这一国家理论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
(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把民主和专政对立起来,从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性。民主的阶级性决定了它和专政是对立的统一。而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民主和专政是相互排斥的,要获得民主就不能实行专政。
综上所述,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具有资产阶级的改良性质,只有深入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才能借鉴其合理成份,从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避免重蹈苏东覆辙,坚定不移地把我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标签:民主社会主义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