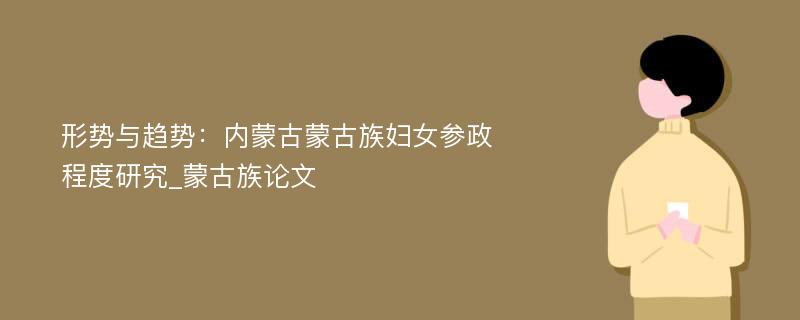
状况与走向:内蒙古蒙古族女性参政程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族论文,内蒙古论文,程度论文,走向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大首次将政治文明写到报告中,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而公民参与程度是衡量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指标,女性参政则是其重要的构成,因此拓宽中国公民包括女性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提高其政治参与的质量,成为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举措。提高女性参政的程度有利于加强民主,有利于充分地使用人力资源,有利于性别平等的真正实现。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有效尺度。在妇女解放的进程中,女性参政是妇女解放最显著的标志和最重要的尺度。它不仅体现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诸方面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而且从管理层面上体现了女性在治理与管理国家中的能力和才华,是女性主体意识的真正体现。
对于女性参政程度的衡量,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主要从女性任职比例及女性在民主选举和社会参与中的比例两个方面分析和衡量中国妇女参政状况;二是从女性参政比例及参政意识两个方面,以隐性参政与显性参政的形式来衡量女性参政程度。然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在衡量妇女参政程度方面都提到了参政比例问题。女性参政比例,即女性参政要在数量上达到一定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都明确规定,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女性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1]然而从目前女性的整体素质及参政意愿等多个层面考虑,在中国妇女队伍中,仍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意愿或者没有能力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在鼓励妇女参与政治的同时,尊重妇女的个人选择。这样衡量一个地区女性参政程度,在数量标准上应包括两个方面。从横向维度上:一是社会为有意愿参政女性提供的机会;二是大众女性中有意愿参政女性的比例。从纵向维度上:即历史的比较。女性的参政意识与有参政意愿的女性走上领导岗位的数字有无提高。因此,以上所提及的“比例”的基数就应有所变化。即由以整个妇女队伍为基数转为以整个有意愿、有能力参政的女性总数为基数。另外,女性参政在数量上的要求只是一个方面,质量上也要达到一定标准。衡量女性参政的质量,可以从女性意愿的体现程度、在位女领导的参政意愿及体现妇女整体利益的能力、女性领导者的管理水平、社会对女领导及女性地位的认同、女性干部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等等多个方面来分析。根据以上阐述,笔者就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女性参政状况进行分析。
一、蒙古族女性参政状况及其特点
内蒙古自治区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以汉族为多数,汉、回、朝鲜、鄂温克、鄂伦春、满等40多个民族杂居的地区。蒙古族与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状况,决定着整个地区经济、政治的发展与稳定。而其中蒙古族女性是否拥有与男性或其他民族女性平等的就业、劳动、参政权,正是蒙古族女性发展状况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影响内蒙古经济及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内蒙古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治、法治进程的推进,尤其是有关男女平等,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相关法律、政策的出台,蒙古族妇女更是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来,在各行各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她们政治参与的数量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目前我区女干部已有30.2万多人,全区少数民族女干部12.44万人, 其中蒙古族女干部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同时根据对内蒙古自治区盟、市及旗、县、区四大领导班子中妇女干部及蒙古族女干部配备情况的调查来看,内蒙古地区蒙古族妇女的参政数量较过去已有大幅度的提高。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内蒙古盟市级蒙、汉女干部配置情况
民族 总数
汉族
蒙古族
其他
数量 5932
234
比例%
100
54.24
38.98
0.07
数据来源:内蒙古妇联组织部(内部资料)。
表1为内蒙古自治区盟、市级四大领导班子妇女干部配备情况及民族状况。可以看出在59个女干部中,蒙古族女干部23人,占总数的38.98%,汉族则占了54.24%。这些数字有力地说明国家男女平等的国策的推进,蒙古族女性参政的程度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也说明蒙古族女性是内蒙古迈向小康社会的一支重要的建设队伍。然而除了这些我们还应该看到内蒙古族妇女参政工作中存在的深层次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很大一部分的蒙古族女性对于进入政治领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即在自己参政意愿不强的情况下由组织推荐选拔为领导。根据对全国女干部参政思想准备进行的调查,内蒙古女干部的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内蒙古女干部参政思想准备状况
调查总数
A充分准备
B较多准备 C有点准备
D无准备
E根本没想到
C+D+E
186
13 36 53 49 35 137
100% 7% 19.40%
28.50%
26.30%
18.80%
73.66%
资料来源:叶忠海主编《中国女领导人才成长和开发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注:此表是总表的一部分,专指内蒙古女干部参政思想准备状况。
那么,依据女性参政程度应以在职女干部与有意愿参政的女性总数的比例来评定的标准。C+D+E占总数的73.66%,即有这么多的女性并没作好参政的思想准备。用这个比例来分析蒙古族女干部,盟市级就会有很大比例蒙古族女干部没有充分的参政思想准备。一个没有充分的参政思想准备、强烈的参政意愿的女性领导在工作上就很难发挥自己的特长,游刃有余地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实现高水平的领导;或者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才智,实现领导的科学化。
二是蒙古族女性参政权利的虚化。即现行选拔女干部的条件人为限制了许多有意愿、有能力的蒙古族女性进入权力机构。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成为选拔女干部的硬件。这种硬性条件造成一方面只要具备了某个或某几个条件,不管能力如何、意愿的强弱,都可以由组织提拔到女性领导的队伍中,这是对国家的女性参政的25%的比例保证的误解。另一方面,一些有能力、有意愿的蒙古族女性被排除在领导队伍之外,或许只是因为其不具备其中的某个硬性条件。
三是蒙古族女性领导权利的边缘化,即大部分女性领导处于非决策层面。从表1的内蒙古地区的盟市级蒙汉女干部的配备情况可以看出,在23个蒙古族女干部中,就有16位处于副职或非决策岗位上,占蒙古族女干部的70%。而且分布面比较窄,主要是教科文卫体系统的居多,处于决策层的只是少数。这种非实质意义上的女性参政,即使有再大的女性比例也不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参政。
四是一些进入领导岗位的蒙古族女性领导者逐渐失去女性意识。这种情况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一些女性领导者进入领导队伍后,忘记了自己与女性大众委托代言人的政治契约关系,淡化自己的性别特征,迎合整个政治系统重男轻女的趣味来换取自己“铁面无私”的美名。另一方面以男性标准作为干部选拔的条件,使得许多本身具有女性意识的女领导为了自己在仕途中的顺利,不得不以男性的要求来约束自己,最后失去自己的女性意识。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蒙古族女干部的参政情况在深层次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只有在一定比例保障的前提下,让更多有意愿有能力的蒙古族女干部分布在领导岗位上,才能更有利于内蒙古的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社会进步及蒙古族女性参政程度的真正提高。而这些女领导的参政意识的强弱、意愿的高低正是广大蒙古族女性参政程度的最好体现。
二、蒙古族女性参政水平影响因素
蒙古族女干部作为整个女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参政水平的影响因素既包括影响整个妇女队伍参政水平的一般因素,又有其特殊原因。对于影响女性参政的因素,许多学者做过分析,大体包括:传统观念的束缚;干部人事制度的制约;女性政治参与意识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教育等资源分配不公等涉及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传统观念上的多个方面。除此之外,影响蒙古族女性参政水平的因素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蒙古族女性强烈的政治认同感。政治认同感是属政治文化中情感性成分的范畴,体现人们对政治体系及政治活动的情感与认同。其形成的基础是长时期的经验与知识的积淀,反映个人与集体的选择偏好。具有强烈政治认同感的群体成员就尊崇一种冷漠顺从型政治文化,对政治体系的规范,角色及自己在政治活动中的责任以及作为参与者的自我取向的反映偏低。蒙古族是崇尚团结的民族,有着强烈的整体意识和政治认同感。这种政治认同感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原因。从建党初期,我党的领导人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就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1924年到1926年间,从蒙古族青年中发展了乌兰夫、吉雅泰、奎璧等为第一批蒙古族党员,派他们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第三国际主持的党校学习、到黄埔军校学习、到广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亲自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教诲。因此早期蒙古族领导者,接受中央民主、统一的政治理论比较早,且受其影响程度比较深,同时蒙古族自古就是一个崇尚精英领导的民族,具有超凡的品质与个人魅力、领导力的个人可以成为整个民族的领袖。因此,那些早期的蒙古族革命者的思想与行为就深深影响了这个民族。正是在这种政治认同感的感召下,内蒙古人民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努力发展地区经济,取得很大成就。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生活的蒙古族女性高度相信政策体系的合法性、稳定性和决策者的决策能力,具有高度的政治宽容精神。其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相对偏低。对自己的社会责任未能充分认识。在她们认为,无论自己介入与否,都不会影响事态的发展,自己的行为与意愿可以由社会选拔的男性予以体现。
其次,蒙古族女性对参政的成本收益分析。如果一个公民认为介入政治活动得到的报酬低于其从事其它活动之所得时,他就不可能介入政治[2]。根据佛隆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的“择业动机理论”,存在这样的命题,即:择业动机=f(职业效价,职业概率),其中职业效价就是择业者的职业价值观,即他对某项具体职业要素,如劳动条件、成本收益(直接、潜在)、职业声望、兴趣等的评估。职业概率即其获得此职业可能性的大小[3]。这个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因素的制约。 作为蒙古族女性,在对自己人生道路做出抉择的时候,首先会对职业效价中各因素做出权衡。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对成本收益的分析。一个把“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作为自己行为准则的女性,在她面临事业与家庭的二难选择时,一般都最终放弃事业。因为,在她看来,家庭的美满,孩子的健康、快乐胜过于事业的辉煌。如果让她因为选择了事业而不得不分散或减少对家庭的注意,她就会认为这是经济学中的“高成本低收益”。与此相对,一个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女性,即使因为自己过于关注事业而忽略了对家庭的关心时,除了歉意以外,她还是会选择事业。当今仍有很大一部分蒙古族女性的家庭意识高于其自我实现的意识。在蒙古族的家庭里母亲不仅是汉族家庭中的“妈妈”,更是孩子的“老师”。蒙古族的母亲在家庭中对孩子的教育一般重于父亲与汉族的母亲,有“英雄母亲”的美称。为此她们宁愿放弃自己实现价值的机会,而把注意力过多地倾注在家庭上,实现她们的“高收益”,即使孩子成为英雄化的人物。另一方面作为蒙古族,她们又不得不对自己进入政界的概率进行分析。基于对自己各方面素质包括语言等的考虑,在竞争力方面明显低于汉族女性。以上两个方面致使她们的参政积极性相对较低。
第三,蒙古族生活习俗所致。蒙古族自古以来就以游牧、打猎为生,称为“马背民族”。对于这个民族的每个成员来说,骑马、打猎、放牧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女性生理上的弱势,造成女性谋生能力相对低于男性。这种情况造成两种结果,一是造成蒙古族家庭的天然分工。男性在外打拼,女性在家“相夫教子”。这种分工长时期造成女性对外界活动参与程度较低,对自己在家庭与社会中角色定位有失偏颇,并已达到对自己角色的认可。另一个就是女性依赖心理增强。习惯了生活在男性为其搭建的天地里,放弃了许多自己的权利及对社会的责任,参与政治活动积极性相对于男性很低。这种依赖长时期演化成一种懒惰,当然包括对政治活动的冷漠。而根据罗欧的需要理论,家庭的气氛及早期的教育,环境影响个体对未来职业的选择。因此在一些有传统分工特色家庭中长大的,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蒙古族女性,依然会选择与其母亲一样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对政治生活选择不关心。
第四,内蒙古地区幅员辽阔的地理环境所致。内蒙古自治区东西直线距离2400公里以上,南北直线距离约有1700公里。东与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接壤,西与甘肃为邻,南与河北、山西、陕西三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毗邻,北与俄罗斯、蒙古国交界,国境线长达4221公里,全区118.3万平方公里,有很大部分是信息沟通不畅的农村和牧区。这就造成两种情况,一是由于面积大及经济不发达,许多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关于保护女性权益,提倡男女平等的法律、政策得不到及时的传达,造成这些法律执行力度不够。另一方面,长期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地方政府组成人员,对这些法规认识肤浅或重视程度不够;或者由于上级政策向下传达的过程出现故障,使得基层妇女对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了解甚少,对自己的权利义务的认识还停留在初级水平。这对于唤醒妇女的民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及责任意识都有很大影响。造成中央与基层妇女群众的联系纽带脱节,严重影响蒙古族女性参政水平的提高。
最后,蒙古族女性参与政治的语言障碍。蒙古语是蒙古族女性的母语,在蒙古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流一般都是用蒙古语。这其中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蒙古族女性,这造成了很大一部分蒙古族女性难以用汉语与他人交往,语言上的障碍造成她们的日常与汉语的电视节目、报纸、刊物等的接触频率不高,对政治体系了解不多,关注社会现象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影响。表达自己意愿的方式仅限于本民族语言。这样造成一方面蒙古族女性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较低。另一方面各级党政领导想了解蒙古族女性意愿的愿望亦受到影响,从而造成沟通渠道不畅。因此在蒙古族聚居区加强蒙、汉双语教学是使蒙古族女性走出语言障碍的困境,使其能够自如地表达自己,从而提高蒙古族女性参政水平的极为重要的途径。
三、提高蒙古族女性参政程度之对策
针对上述影响蒙古族女性参政程度的因素,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蒙古族女性参政水平低的现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从思想意识上把蒙古族女性参政提升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平等的高度上来予以重视。在衡量社会和谐的众多指标中,各个民族的男性女性都有平等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然而美国劳动部“联邦玻璃天花板委员会”所定义的“玻璃天花板”现象(女性和少数民族的提升人为被设置障碍,这种障碍是看不见的,然而却是使女性和少数民族无法登上组织阶梯上层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不管他\她们的资格和成就如何),[4]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我国女性包括蒙古族女性的社会处境。一个国家的发展首先应该以其个体公民的充分价值实现为前提。在父权文化浓郁的大背景下,蒙古族女性实现其社会价值的渠道被人为阻塞,这既不符合联合国关于人权的相关规定,也由于各项建设事业没有女性文化的润泽而受到影响。没有妇女个体利益、权利的实现,单纯强调男性参政程度的提高,很难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另外从民族平等的角度讲,任何民族之间都是平等的,蒙古族与汉族等其它民族之间有着同等的权利。只有各民族都得到充分发展,整个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同时《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少数民族有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力”的规定,也应该包含了蒙古族女性的政治参与权力。因此无论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还是从实现民族平等的角度,都应该把蒙古族女性纳入参与政治活动的范围之内。这需要政治体系中的各层面在各项具体工作中都以此为指导,充分考虑到蒙古族女性的参政权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体现。
第二,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认同感,构建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法国学者雷蒙·博兰指出:“凡是建立在价值基础之上的并以此得到公共舆论承认的即是合法的。”[5]正是这种被蒙古民族公认“合法的”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宽容精神,成为影响蒙古族女性参政程度的重要因素。这就需要构建一种与现代化政治取向一致的参与型政治文化,从根本上改变蒙古族女性把自己作为政策客体的思维定势,自觉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作为组织公民的义务。这在“阳光政府”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就需要公共权利机关通过各种途径将政治体系的、与现代化政策相适应的主导政治意识向蒙古族女性个体扩散,使其接受与社会相适应的政治情感与信仰,并按着它进行活动。通过政策体系的作用,进行政治文化的再造,使她们开始关注政治、关注政策过程,开始考虑通过政策参与实现自己对权力的支配。同时也需要大众传媒、学校等社会化工具向社会大力传播现代政治意识,强化蒙古族女性的政治参与的责任感,让她们自觉、自愿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
第三,构建阳光政治体系,改变内蒙古的地理弱势,强化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针对内蒙古地区幅员辽阔的地理状况和相当部分地区信息沟通不畅的现实,有关部门应加大信息传输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设力度,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力度,改变内蒙古地区的地理弱势。让蒙古族女性更多了解政治体系的相关信息及政治体系的运作情况,改变蒙古族女性与政治体系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实,实现二者的良性沟通,使更多的蒙古族女性在享有基本的知情权的基础上,走进政治体系,自己支配政治权力,实现女性大众的利益,从而建立和谐阳光的政治体系。这是推进政治文明、搞好民主建设的具体举措,也为蒙古族女性更多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提供了更快捷、便利的渠道,有利于提高蒙古族女性的参政程度,从而实现男女在政治参与权上真正意义的平等。这就需要公共权利机关的各项配套措施的出台及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当然也离不开决策层领导者的大力支持。
第四,蒙古族女性的参政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建设。在中国虽然男女平等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但由于长期的父权文化的影响,两性在各方面都还未达到真正的平等,并且长期的女性压制,使女性自身自我发展意识较弱。强化蒙古族女性的参政意识是提高蒙古族女性参政程度的重要举措。参与政治事务的管理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就像参与家庭事务管理是男性女性共同的权利与义务一样。作为新时代的女性,要解放思想,从旧的框框中解脱出来,以组织公民的责任意识,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才能实现自己对社会、家庭的双重责任,才能在自己价值的实现和对社会贡献上达到双收。然而除了这种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外,女性参政意识的提高还在于国家民主制度的健全,即是否为女性参政意识的提高提供现实条件,这要求政府改进管理模式,从高度的集权向公民广泛参与转变,使决策机构由金字塔式向扁平结构发展,同时应以分层次、多方位、多角度、多渠道的信息传输方式把信息传递给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以外部力量的方式加强女性的主体意识、参政意识,当然女性自身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理解社会问题的能力。
女性意识是提高女性参政程度的重要方面。女性参政程度的高低其中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本集团内女性意愿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反映。因为女性参政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女性的特殊利益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得到体现。而对于普通大众女性来说,其利益和意愿的实现途径之一,就是在领导岗位的女性在政治活动中的争取,这就需要参政女性有强烈的性别意识和广大大众女性的代言人的强烈责任感。因此女性参政不应该是单纯关注有多少女领导在位,更应该考虑到有多少女性有女性意识,这一方面工作,就需要像妇联这样的妇女组织的积极努力,代表广大女性把强大的女性声音传输到政治体系之中,特别是参政的女领导的耳中,增强这些女领导的紧迫感和自觉意识,从而有意识地向保护女性利益方面转移一些注意。同样女领导自身也应该作好大众女性的利益代表者,以一种责任感,去为女性争取更多的利益并给予女性以充分的信任,并在干部选拔等方面给予充分的关注。
最后,在尊重蒙古族妇女选择的前提下,鼓励有能力、有意愿的女性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了解政治体系,加强自身修炼,作好准备,随时加入到领导队伍中来。“女性文化摆脱男性文化附庸者的地位,并不等于对男性文化的敌视和反对,也不能作为男性文化的对立物存在,而是要寻求两者共同发展的契机和动力所在。”[6]因此在男女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尊重双方的选择,而对那些走上政治活动舞台的女性,也应当兼顾家庭责任,使二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为此蒙古族女性自身应以“四自”为准绳,努力提高自己,在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中,以独立的主体意识,满怀信心地投入到学习、生活、工作中去,不断发展自己、完善自己,为自己享受参与政治的权利和履行参与政治的义务准备条件,同时兼顾家庭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在男性强势的社会中,懂得自我价值的实现,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参与到政治活动和美满家庭的构建过程中去,从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等各层面使自己成长为一个“四有”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