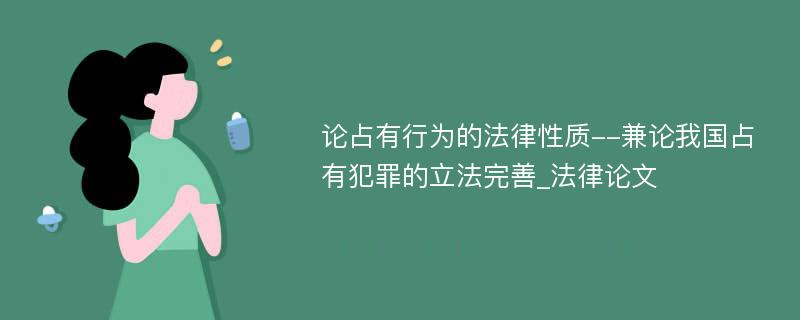
持有行为的法律性质再探讨——兼论我国持有型犯罪的立法完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质论文,论我国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810年《法国刑法典》规定持有型犯罪伊始(注:《法国刑法典》第278条:乞丐或游民,经发现持有价值逾一法郎之物品,而不能证明其获得来源的,处276条所定之刑。),各国刑法典纷纷效仿,我国也在1997年新刑法典中规定多种持有型犯罪。但该种犯罪的诸多问题在刑法学界仍存在争议,笔者拟就争议的中心问题即持有行为的法律性质作些力所能及的探讨,并通过立法目的的考察,对持有型犯罪的立法提出建议,以推进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一、持有行为的界定
持有行为是对某特定事物事实上的支配。(注:《法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增订版,第666页。)持有一般表现为行为人对特定物品的占有、收藏、控制和保管。持有体现的是行为人与物之间的一种支配和被支配、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持有行为并不要求行为人随时随地随身携带,处于一种行为人眼能观、手能触的显性状态中,也不必要求持有物必须置于行为人之居所,即是说只要物品处于行为人的支配或控制状态中即视为持有,无需处于行为主体的物理性控制力下。
持有行为的起始行为既可以是合法行为,如路上拾得、受赠、买卖行为;也可以是盗窃、抢夺、走私、贪污和受贿等非法行为。持有行为的起始行为可以是作为,如路上拾得某管制品;也可以是不作为,如对他人带至己处的毒品不加反对也未同意地持有等。持有行为何时完成?我国刑法并未规定。但《加拿大刑法》第316条作出规定:“犯第322条及第344条第(1)项6款之罪,于行为人依其情形已单独或共同持有或支配各该条所示之物或帮助隐藏或处理时,为持有之完成。”(注:王玉成译:《加拿大刑法》,载《各国刑法汇编》(下册),台湾司法行政部1980年印,第2290页。)行为人一旦掌握控制物品,就视为持有之完成。
二、持有行为的法律性质
持有行为的法律性质,是指持有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抑或是独立于作为和不作为之外的第三种行为样式。对此,刑法学界有两种观点——附属说和独立说。
(一)附属说
该说认为作为和不作为已穷尽了所有的犯罪行为样式,持有行为不能独立于作为和不作为之外,只能附属于作为或不作为。此说将作为和不作为的关系比例A与非A的关系,而互相排斥。一个行为经刑法评价,如被认定为作为则不可能又是不作为,反之,亦同。(注:林山田:《刑法通论》,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第2版,第77页。)以此作为附属说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具体言之,该说又可分为作为说和作为或不作为择一说两种。
1.作为说
该说认为持有行为属于作为。持此说的学者从民法上的所有权涵盖的权能出发,认为行为即是人对物的作用力,只能通过取得、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五种方式表现出来。并以为持有的内涵完全等同于占有,进而得出“如果持有是新的犯罪行为方式,那么……使用……处分也是新的犯罪形式”的悖论,籍此认为持有行为不是独立的行为形式。然后从刑法规范的性质出发论证,持有型犯罪属作为犯罪(如非法持有毒品罪)。(注:秦博勇:《也谈持有型犯罪——非法持有应是作为犯罪》,载《中外法学》1994年第2期,第58-59页;熊选国:《刑法中行为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第125页。)
2.作为或不作为择一说
该说以为持有行为有时属作为,有时则属不作为,不能一概论之属作为或不作为,该说又分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将持有行为划分为“单纯的持有”和“只有一种行为状态的持有”两类,然后在此基点诠解持有行为的归属。论者认为“单纯的持有应该是不作为”,如私藏枪支罪;如果“持有只是一种行为状态,则应根据先前的行为性质确定为作为”,如盗窃之占有。(注: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69页。)
另一种观点则从持有某特定物的方式或手段的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说明持有行为是由作为或不作为都可构成的犯罪。论者说,如果行为人利用犯罪手段来占有管制品,行为人取得后的持有状态,当属作为形式的犯罪;如行为人是用非犯罪手段来占有管制品的,则属不作为的犯罪。(注:刘玉旋:《持有型犯罪的若干问题》,载《政法学刊》1996年第4期,第52页。)
(二)独立说
该说认为持有行为是独立于作为和不作为之外的第三种行为样式,其阐释理由如下:
1.法律根据。该说广泛引用美国的《模范刑法典》第2·01条的规定:“持有者故意取得或收受该物件,或如欲终止其持有时,在有足够时间去终止之期间内,对其自己支配该物之事实有认识时,在本条适用上,持有即为一种行为。”(注:陈耀东译:《美国模范刑法典》,载《各国刑法汇编》(下册),台湾司法行政部1980年印,第1904页。)
2.逻辑根据。该说认为刑法上“作为”与“不作为”的关系不等于形式逻辑中“A”与“非A”的关系。刑法上的不作为并非作为的全称否定,两者不存在形式逻辑的排中关系,因此在作为与不作为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犯罪行为形式。
3.持有行为具有特质。“持有”这一行为样式具有犯罪性在于主体对非法财物的控制状况,“作为”的犯罪性明显蕴含在其身体动作中,“不作为”的犯罪性在于主体与法律要求产生的义务关系。持有是二元结构(主体行为与外界条件结合),不同于一元结构的“作为”(主体行为本身构成犯罪行为)。持有又不同于“总是和特定义务相联系”的不作为。(注:有关状态犯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洪增福:《日本刑法判例评释选集》,汉林出版社1977年版,第207页;喻伟主编:《刑法学专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附属说中的作为说从民法的所有权内容得出“持有”不是一种新的犯罪行为样式,应该说它为我们研究持有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拓展了我们研究的思路,有其合理之处。但从民法理论阐释刑法相关问题则难免有些牵强,说服力较差。择一说中,有的从持有的分类出发论述持有行为,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把握持有行为有很大的助益。但论者并对“单纯的持有”和“只是一种状态的持有”作严格的界定,事实上“只是一种行为状态的持有”的犯罪则是状态犯,状态犯实际上不是“犯”,不具有可罚性。(注:主要参见储槐植:《三论第三犯罪行为形式“持有”》,载《中外法学》1994年第5期。第20-21页;另参见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宣炳昭:《香港刑法导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94-95页;饶景东:《议持有型犯罪》,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6期,第47页;陈正云、李泽龙:《持有行为——一种新型的犯罪行为态样》,载《法学》1993年第5期,第17-18页;谢家友、唐世月:《论持有型犯罪》,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4期,第30页;肖志坚:《浅论持有型犯罪》,载《江西法学》1992年第1期,第31-32页。)择一说的另一种观点依据持有物的占有方法或手段论述持有行为的归属,显然混淆了持有行为和其先前行为的关系。持有行为之所以构成犯罪,关键在于行为人实施了持有行为。行为人的先前行为只是持有行为的条件和前提,绝不可将行为人持有行为的起始点当作刑法意义上的持有行为来对待,如持有假币罪中,假设持有人因疏忽在一买卖行为中误收了假币,后知假币而持有,这里持有假币的前提行为——买卖行为是合法的,不会受到刑法的责难评价,不具有可罚性。独立说主要是从持有行为和作为、不作为的对比中得出结论的,而忽视了从它们之间的联系中去论证,显系不足。
笔者倾向于独立说。持有是指物主对物的实际支配和控制行为,其有一定的时间延续性。从刑法规范的性质出发进行剖析,持有既有作为因素又有不作为因素。动态来看,持有状态犹如布满时点的一个线段,在每一个时点上,该状态则表现为一个积极的作为“持有”,若连结这些时点,则该状态表现为一连串的作为。从刑法角度分析和评价,该一连串的行为违反了刑法的禁止性命令,即不应持有而持有,显然持有有作为因素。与之伴生的是持有是一连串的不作为,因为在每个时点上,持有的财物应上交而没上交,违反了刑法的命令性规范。因此,持有又有不作为的因素。由此可知持有行为是一种动静交融、作为和不作为互相叠合的一种行为样式,独立于作为和不作为之外。《美国模范刑法典》第一·一三第一般定义中第(5)项把“行为”释为:“系指伴随一定之心理状态作为或不作为,有时亦包含在一连串之作为及不作为在内。”(注:陈耀东译:《美国模范刑法典》,载《各国刑法汇编》(下册),台湾司法行政部1980年印,第1901页。)照笔者理解,“一连串之作为及不作为”即为“持有”。由此可见该法即将作为、不作为和持有行为并列为三种行为样式。
三、对我国持有型犯罪立法的思考
(一)持有型犯罪的立法目的考察
持有型犯罪之所以进入刑法的视野,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评价,成为刑罚罚及之对象,就在于其有一定抽象或现实的客观危险性,给社会秩序和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持有犯除少数外,大分部是同其他犯罪行为密切相关的,它既可以是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盗窃、抢劫、抢夺及贪污受贿等行为之结果,也可是实施这些行为的预备行为。创立持有型犯罪,可以通过惩罚早期预备行为来防止严重犯罪的发生,把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司法层面上,当公诉机关难以查明持有现状的来源和去向时,为了减轻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不放纵一些犯罪分子,迅速地打击犯罪分子,以提高刑法之威慑力,强化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创立持有型犯罪便成为合理之选择。
(二)持有型犯罪立法之完善
我国新刑法废除了类推制度,实行严格的罪刑法定主义,为了不放纵犯罪分子,因此有必要将一些多发性的社会危害行为纳入刑罚评价之范畴,最大限度地发挥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之机能。笔者认为,在经济犯罪领域中,应增设持有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罪,持有伪造、变造的证券罪和持有伪造或擅自制造他人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1.增设持有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和证券罪
笔者之所以建议增设该持有型犯罪,理由有三:第一,在伪造、变造票证、证券后,使用它们之前,有一段持有行为。如果持有人拒不提供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证券的来源,司法机关也难以查证的,只对伪造、变造和使用行为进行处罚,显然对持有行为之环节则不能很好地科刑,从而使刑法保护金融秩序之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落空。第二,从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来看,刑法规定有伪造、变造货币罪和使用伪造、变造货币罪,同时还规定有持有假币罪,既然金融票证、证券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能替代货币,发挥货币之功能,那么结合货币犯罪,我们为何不增设持有伪造、变造之金融票证、证券罪呢?第三,外国刑事立法例也可资借鉴。意大利刑法典第461条规定了持有伪造证券罪,西班牙刑法典第297条规定了持有伪造证券罪和加拿大刑法典第412条(1)项规定了持有伪造、变造的有价证券罪。(注:参见《各国刑法汇编》(下册),台湾司法行政部1980年印,第1594、1773、2337页。)
2.增设持有伪造或擅自制造他人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当前假冒伪劣产品在市场上屡见不鲜,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之事也常有发生,一些经营者伪造他人注册商标和擅自制造他人之注册商标标识后,将其卖出或使用于商品之前,他人买进后使用之前,有一段持有行为。持有主体往往拒绝提供商标标识的来源和去向,司法机关也无法证明,这时应增设上述罪名以打击此种非法行为。如果不将持有伪造、擅自制造他人的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上升至刑法意义来处罚,显然会造成刑事法律的空白地带,不能有效地保护商标专用权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知识产权的彻底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