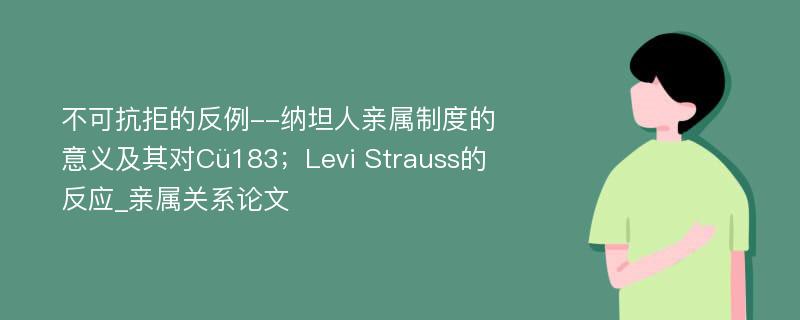
不可抗拒的反例——纳人亲属制度的意义,兼回应C#183;列维—斯特劳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特劳斯论文,亲属论文,意义论文,制度论文,列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学田野调查观察表明,禁止兄弟姐妹之间的交媾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兄妹不可能结婚。但也有例外:有些民族禁止Ego(自我)与自己堂兄弟姊妹的性爱,而表兄弟姊妹非但不禁,反而成了优先考虑的联姻对象,如传统的彝族社会。而传统的汉族社会允许姑舅表和姨表兄弟姊妹结合,但严格禁止堂兄弟姊妹间发生性爱。纳人(即摩梭人)社会则严禁Ego与其母的姐妹的孩子之间的性爱,而舅舅的孩子却在性爱的对象之列。无论在这个星球的什么地方,不管一个民族的遗传学知识有多少,均以避免生产畸形后代为理由来解释这类禁忌的必要性。如果这种说法是准确的,那么,从生物学的角度观之,在一个民族内部,在一种情况下(如汉族的堂兄弟姊妹)被避免了的“乱伦”现象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汉族中的表兄弟姊妹)发生,在某些民族中被阻止的“乱伦”出现在另一些民族中。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研究均以生物学原理为基础。然而在此论及的角色(堂兄弟姊妹、姑舅表兄弟姊妹),根据生物学,相对于Ego,他们都是亲属。因此,生物学似乎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的这些习俗。怎样解释人类性行为的这种多样性呢?在这种多样性之下隐藏着统一性吗?
既有的普遍命题
人类学发端于对亲属关系的关注,亲属关系人类学被视为人类学的王冠领域。长期以来,为了解释人类习俗的上述多元性,人类学家做了大量的研究。早在1935年,A·R·拉德克里弗-布朗(以下简称布朗)对分布在各洲的一些民族实行的身份、权利和义务在代际之间传递的不同制度进行比较后说:“某些基本因素决定了单系原则,而这种原则又反过来固定了社会身份或继承形式。很遗憾,我们对这些事实的知识和理解尚不足以让我们确定决定选择一种单系原则的那些基本因素。”[1](P93)这实际上也是在探讨制度决定行为,而制度又取决于什么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对人在选择异性伴侣方面的行为(因此也涉及异性配偶的选择)呈现出多样性的解释处于亲属关系的逻辑起点上,它构成了在亲属关系人类学中出现的所有理论难题的核心死结。为此,一方面,它是否具有可理解性成了判别亲属关系其它要素的性质的前提,另一方面,这个难题的解决也是人类学理论化过程中识别每一种亲属制度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的首要条件。
1941年,布朗就亲属关系提出的理论框架如下:用来建构亲属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基本家庭。它由1个男人、其妻子和他们的孩子组成,创造了3类社会关系,即单亲(父或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1对父母的孩子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这些孩子的父母的夫和妻之间的关系。这3类关系是第一范围的关系。通过与Ego的血亲或者姻亲,源于两个基本家庭之间联系的这些关系构成了不同的范围。“所有社会都为了某些社会目的而承认这类亲属关系中的某些部分:实际上,社会把一些权利和义务或者一些不同的行为方式与这些亲属关系联系在一起。在做出这样的认定之后,这些关系构成了我称之为亲属制度,或者更完整地说,血亲和姻亲制度的东西”[2](P41、117)。
在布朗看来,亲属关系是一种东西,权利和义务或者行为方式则是另一种。然而他却没有明确地说明亲属关系的各种性质。此外,他在从基本家庭中抽出的3类关系的排序中,将单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排在第一位,不论在母系或父系制度中均如此。这说明这一关系处于全部亲属关系的源头。当然,他从未正式提出一种亲属关系的普遍理论。显然,那时他还未能解决自己6年前提出的难题。
至今在该领域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全部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这似乎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
1949年,C·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建立在交换原理上的、在集团之间的“亲属制度的普遍理论”。作为布朗理论的反论,这一理论认为,是横向的联姻关系构成了所有亲属制度的基础。因为对inceste(生物血亲性关系)的禁忌具有普世性,这种禁忌必然导致不同集团或群体间的联姻,两性的劳动分工使婚姻须臾不可缺少。没有联姻,没有家庭,任何社会甚至人类本身都将无法存在[3](P779、82、84、91、92)。
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同样必须面对本文开始时陈述的难题:在被允许和被禁止与Ego交配的这些人的身份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差异?这个问题至为关键。因为它实际提出的问题是:夫和妻,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人”是否具有一种非生物性身份。依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证,得出的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即:亲属制度的结构和运作机制都是社会性的,而这个制度的因子却是生物性的。
可是,在此似有必要重申,社会结构必须、并且只能由社会性的因子建构。
危机的根源何在
布朗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两种观点,即单系血统理论与联姻理论出现对峙,是一纵与一横的对立。在此后的民族学研究中,这两种理论被研究者广为使用。但是,一些学者发现不论是这两种理论的基本概念还是理论命题均不适用于分析某些民族志事实。而且联姻理论受到了两种婚姻规则的质疑:一种是允许两兄弟或两姊妹的孩子开亲,即人类学家所称的“阿拉伯婚”;另一种是双系制度,与二元社会不同,它排斥在两个集团之间不断重复联姻。
在亲属关系研究史上,197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法国、英国和美国的3位杰出的学者著述的发表标志着理论危机的爆发。
第一部文献是法国人类学家L·狄蒙的《社会人类学导论》。他认为一纵一横的理论是当时最具价值的理论。可是,每种理论仅仅与一类制度相符,而且处于较低的抽象水平,只不过是两种狭义理论。必需有别的、可运用于其他类型社会的理论产生,才有望从全部这些理论中抽象出一个真正的普遍理论,必须“对社会从整体上进行把握。而这是欲做整体把握必付的赎金”[4](P8、19)。
1971年至今,近半个世纪逝去了。何以今天的研究还没有抽象出狄蒙所期望的“普遍理论”呢?在笔者看来,问题在于应当弄清亲属关系建立其间的两类个体(一方面是纵的理论所指的父或母及孩子,另一方面是横的理论所提出的夫与妻)是否具有同样的属性。从这两种理论中我们真能抽象出一些什么同质的东西吗?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抽象程度的问题实际是一个伪问题?
第二部作品是R·尼德姆主编的《反思血缘关系与婚姻》。按狄蒙的观点,要达成一个普遍理论,只需穷尽亲属关系的全部类型,然后对其基本构成要素进行抽象即可。尼德姆同意伯克利的意见,他的判断是当时人类学家的这个“理想”源于追求普遍性的激情和建立“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的执著幻想[5](P41)。他认为:“民族学只有能力把握——或者说无论如何,大概这也就是它所可做的,即随着人们认识的具体案例的增加,把握不同文化在逻辑上和心理上所采取的那些可能性的各种框架,这些可能性便是整个人类所拥有的用于安排她的经验的基本资源。”[6](P130)他承认:“的确,现在剩下的问题是需要知道,在亲属关系方面准确地说究竟应该做什么。”[6](P22)
有必要强调的是,尼德姆借用了不同民族的民族志材料指出,被人类学家归入同一类的不同文化的词汇时而覆盖不同的场域,例如,英语中的“inceste”和汉语中的“乱伦”就不完全一致,等等。可见,在尼德姆看来,在廓清亲属关系的概念过程中,使研究瘫痪的障碍和难题正在于研究对象的模糊性及复杂性,同时也在于一些谬误原理。
自然科学家也在寻找他们研究对象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的目的,一方面是尽可能完整的理解感知经验,并且把感知经验与它们的全部真实存在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使用最少量的基本概念和最少量的关系来完善这一目的(在世界的面貌中尽可能地寻求逻辑的统一性,即世界面貌的各种基础在逻辑上的简单性)。”[7](P26)这种理论导向也深深地影响了社会科学。在笔者看来,寻找普遍性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错误的原则,但首先应确定的是普遍性存在与否。而通过研究真正成功地证明一个领域里不存在普遍性也是一种进步。
此外,尼德姆是当时对各种亲属制度研究最深入的学者,他的论证同时透露了其方法论的无力和研究者所面临的难题。因此,最终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有其它可以用于分析亲属关系的方法吗?在我们的立场中是否还存在着其它错误的原则?在广义的亲属关系领域是否仅存在着多样性而无同一性?是否能够建立普遍理论?而在其题为“血亲关系究竟与什么有关?”的演说中,施奈德判处了血亲关系研究的死刑。在他看来:
考虑到目前的情势,被前人的理论当作唯一决定性的特性的那些生物性因子,当作表示种种社会关系的符号可能更容易理解,而且可能它们既不出自、也不表现那些理论声称能够在功能层面起支配作用的生物性材料。
……然而,若在文化层面上研究“血亲关系”,那么“血亲关系”显然是人类学家的分析工具箱中的一个虚构物,它在我们所研究过的任何社会的文化中均没有具体对应的东西。
为此,结论是,正如图腾主义、母系情结及母权一样,“血亲关系”不是一个研究主题,因为它不存在于人类已知的任何文化中。[8](P59)
这个结论下得急了些。不言而喻,一个生物学概念跟对文化和社会的研究毫不相干。可是,人类学家把与姻亲关系对立的“血亲关系”视为一个生物学概念意味着:在一种具体的文化中该词汇的内容也构成一个非研究主题,即人类学家使用的这个概念是一个生物学概念,而非一个人类学概念。因此,他的结论似乎有失偏颇。
截至施奈德,亲属关系研究在理论层面上进入了死胡同。当人们将亲属关系仅仅当作生物性的东西时,就注定只有两种出路可选择:要么继续搜集亲属关系的民族志材料并且最终建立男性与女性的区分,要么同时放弃民族志的搜集和理论追求。自1971年以来在该领域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
大致上,法国和英国的专家们选择了第一条道路,美国的走了第二条。例如,P·李维艾尔提出为了理解婚姻,应当考虑做出男性和女性的区分[9](P152~167)。而F·艾丽铁则认为由于男性与女性在解剖学上的区分“在连接整个象征思想方面起着根本的作用,并且它是全部血统和联姻规则的基础”[10](P228、253~254),这便走入了死胡同的尽头。因为,如果情况确实像她说的那样,在任何社会中皆禁止同类相交,那么她的论点就意味着在兄弟姊妹之间的交媾应当是被允许的,并且是必须的。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显然与此完全相反。
自那以后,亲属关系研究不再被作为专门的领域看待,人们仅仅在研究社会性别或家庭问题时有所涉及。
1986年,尽管存在诸多争议,列维-斯特劳斯在为《家庭史》作序时,依然再次肯定了布朗的命题具有普遍意义和他自己的联姻理论的有效性[11](P10)。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此时他已不再强调在集团之间进行的妇女交换,因为“阿拉伯婚”已构成了一个反例;他也不再强调在一些既定的集团之间的连续交换,因为,双系制度下两个集团之间的联姻不是每代都重复发生。在这里,他所赖以立论的唯一基础就是纵与横的关系。鉴于婚姻和家庭在当时人类学的知识范围内依然是两个常数,单系血统理论与联姻理论似乎尚能维持。鉴于婚姻/家庭悖论的无解,尽管在这一纵一横之间存在着互相对立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仍然显得可以被当作整个亲属关系的出发点。
列维-斯特劳斯一开始把布朗的纵的理论视为“危险品”,却以不仅仅接受这种理论,承认它为两种普遍假说之一而告终。为此,我们看到,与纵的理论相比较,横的理论只是一种竞争性理论。而我们应当相信这两种理论中的哪一种呢?是否我们必须两种都信呢?从一个对象中,每个学科应当只能抽出一种普遍理论。而以上这两种理论既相互对立排斥,又相存相依,所以它们中就没有一个是普遍理论。于是,亲属关系人类学领域的根本问题始终是:何为这两种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关系的各种角色(父或母与孩子,父与妻)的身份?这个问题的解决是认识人类亲属关系和性行为方式的基本前提。
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列维-斯特劳斯曾说:“我所完成的努力止于未知领域之门槛……有些东西逃脱了我们的理解,而且大概会永远逃逸于我们的理解之外。”[11](P2)
从既有的视角出发,是否真能引申出普遍理论?打破僵局、获得突破取决于两种或然性:要么在方法论的层面上突破原有理论,要么在实证的层面上发现新的案例,摩梭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实例。
纳人居住在喜马拉雅山东麓,是一个农业社会。在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中,兄弟姊妹终身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他们实行一种男至女方夜访的制度,而不是婚姻制度,分为暗访和明访两种。该民族在他们的任何两个支系(纳人社会中的基本亲属和经济单位,它仅由每一代的兄弟姊妹构成,在同一支系的成员之间,交媾是被严格禁止的)之间都既不交换女人,也不交换男人[13][14]。该社会无需求助于婚姻制度和家庭组织,而运行得与其他社会同样正常(详细情况见笔者著《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以下简称《纳人》)。这一事实证明了我们想象力的贫乏,并且它可能给予经典难题一些答案和挑战。以往理论已无力解释纳人的案例,它呼唤新的理论假说。
笔者在《纳人》一书中的结论是: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之存在,抽去了婚姻和家庭这两种现象的普世性的基础,直接导致了这两种理论假说的失效。这引起了西方学术界普遍的反响,在此仅仅引证其中一二。腊皮埃尔写道:“从喜马拉雅的边缘传来了一个发现,一个社会可以在无父无夫的情况下存在并延绵。它不仅搅乱了常人心目中坚信不移的东西,而且冲击了人类学中建立得最为牢固的那些理论。换言之,建立家庭的联姻和双重血统并非整个人类始终遵循的生活方式。”[15]格尔茨肯定地评论道:“由于纳人没有婚姻联系,他们证伪了两种理论(布朗的‘单系血统理论’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联姻理论’)。”[16](P27)同时,他还提出:“必须避免对西方式的‘科学’的考虑和这种‘科学’的先入之见……并且,‘特别是关于血亲制度的那些观念’,这种概念如果存在的话,由于它文化上深受羁绊而可能构成问题的主要部分。”[16](P27~30)1997年,在《纳人》发表几个月后,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舅舅的归来”一文。该文对纳人社会和文化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讨论。作者写道:
这些有意思的观察结果(《纳人》)的作者不无天真地相信发现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案例,这个案例颠覆了人们已经接受的关于家庭、血亲和结婚的全部概念。这就犯了一个双重的错误。纳人在亲属制度方面代表着的可能是一个极端的案例。而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便认识其他一些例子,特别是在尼泊尔、南印度和非洲。这些例子远远没有摧毁即有的思想,这些民族使用的家庭结构只不过提供了一幅与我们的家庭结构对称而反转了的图画。(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这只不过是一些这样的社会,它们没有给予血亲和婚姻一种调节的价值,以保证它们社会的运作机制,而是使用了其他的运作机制。因为,血亲和结婚制度并非在所有的文化中都有完全相同的重要性。这些制度向某些文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原则,以调节他们的社会关系。在另一些文化中,如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功能缺失或者说被大大地弱化了,毫无疑问纳人的文化亦如此。
以几个月来在公众的想象中引起动荡不安的一个事件为由头的这些思考将导向何方呢?为了更好地理解某些社会运作机制的深刻动力,不能仅仅求助于那些在时间或空间上距我们最为遥远的社会。[17](P39)
2000年,列维-斯特劳斯还在《人类》杂志的《亲属关系问题》专号的“跋”中扼要地重复了以上观点。他把纳人与英国人做了比较:“并非在纳人社会中,获取妇女者不能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扮演一个角色,像在我们的社会中给出妇女者那样。我们的社会经历过一些情形,舅舅以其身份在家庭范围内正式占有一个位置。但是这并未为亲属制度所预先安排……同理,在我们的社会中,出现紧张关系或危机时期,舅舅可以重新出现,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理论所陈述的关系体系的完整重构。思宾塞公爵在黛安娜王妃的葬礼上引人注目的出场就最好的证明。”[18](P715)
2001年,他为《纳人》的英文版撰写了评荐:“在亚洲(还有非洲)存在着几个民族,他们要么弱化,要么否认父亲的作用。蔡华博士通过使我们认识了其中之一而对西方人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多亏了他,纳人在人类学的典籍中获得了一席之地。”[13](封二)
在这场讨论中,问题的关键是,纳人的案例是否代表着一类亲属关系的独一无二性?
我们知道,在该社会的原型中,在Ego的上一辈男性中,惟一得到承认的是舅舅。至于婚姻、丈夫和父亲的作用,纳人并没有否认。真实的情况只不过是这些角色在摩梭人的文化原型中根本不存在而已。我们怎能让一个民族去否认一个对他们来说不存在的东西呢!历史上只有清政府对土官职权承袭方面的规定间接地将婚姻引入纳人之中,但这仅仅作用于纳人的首领。再者,这一历史事实纯系政治制度的变迁,而非亲属制度的变迁[13](第二章)。
此外,近20年来,由于中国的教育、经济和旅游的快速发展,摩梭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可是,许多人依然无父无夫,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结婚,特别是上年纪者毫无需要丈夫或妻子的感觉。在出现危机之际,纳人传统的后盾除舅舅外,仅有母亲或兄弟姊妹。女人的每一个走访者都是非姻亲,并不总是为人所知,甚至当人们知道他时,他也没有任何理由插手其中。相反,思宾塞的出场首先是因为黛安娜的父亲已过世,她的母亲早已离婚,按英国的传统,她不能代表其夫的家族,而思宾塞尽管不是其妹小家庭的成员,但是他始终是她的血亲,并且曾是查尔斯的姻亲,因此他是黛安娜所属家族天经地义的代表,而且他永远都是新一代王储的舅舅。可见,走访社会与婚姻社会是两种对立的、其运作机制相互排斥的制度[14]。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既无婚姻制度亦无家庭组织的情况下,即在既不把妇女也不把男人当作财产交换的状态下,一个社会是否能够运行。在列维-斯特劳斯提及的那些类似的案例中,南印度的例子所指的当为纳雅人。但是,人类学界的田野资料表明他们一直实行着婚姻制度。至于说尼泊尔和非洲的例子,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明确所指。如果真的存在一些生活方式与纳人相似的民族,显然也必须有关于他们的精细而完整的民族志,并将之与纳人进行仔细比较,才能使作者的意见获得支持。
然而,即使是这个问题,也不是最重要的。当从历史和结构这两个维度来看时,在笔者看来,纳人的亲属制度与我们的制度既不对称,也不是我们的制度被反转了的镜像,而是彻头彻尾的不同。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不向社会运作机制提供一种像婚姻制度所代表的那种有效的原则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意见进行判断,纳人的亲属制度只能证明笔者的上述观点。理由十分简单,在核心家庭中的男长亲是父亲,他是孩子们的母亲的丈夫,即她的姻亲。而在纳人的传统社会里,亲属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基本单位——摩梭“家庭”中的男性长亲是舅舅,即孩子们的母亲的兄弟。前者由血亲加姻亲构成,而后者仅仅由血亲构成。由于这一事实的存在,婚姻和家庭便丧失了普世性,直接导致“联姻理论”的失效。
再者,如果像列维-斯特劳斯似乎愿意宣布的那样,在纳人之外的几个罕见的民族中,还有别的民族“否认”父亲的作用,那么,人们对横向理论之失效的确认应当早已成立。甚至如斯特劳斯所说“大概会永久地逃逸在我们的理解力之外”,本身就意味着这些假说将永远都不可能成立。
再次,列维-斯特劳斯一方面肯定了纳人社会与其它社会(如英国社会)相比较而呈现出对称的或反转的图像,另一方面,他也肯定了在两类社会里起调节作用的价值观不受相同的有效原理的支配。因此这些价值观决定了两种完全相异的运作机制。他对这些现象的确定等于也肯定了一横一纵理论的失效。
1991年,列维-斯特劳斯重新回到了这个问题上来:“各种‘人文科学’只不过是作为奉承的赝品而成为科学,因为它们所渴望认识的真实存在与它们所操的智力手段具有同等的复杂性。为此,它们无法并永远没有能力把握它们的对象。”[12](P2)
所以,以列维-斯特劳斯之见,我们研究的羁绊来自同等重要的双重原因:智力的有限或不足和研究对象的复杂。这一立场可以说令人想起伯克利和尼德姆都否定的“我们知性中的自然缺陷”。其次,与上述判断相反,这种见解清楚地意味着,难题不是源于任何人类学家赖以为基本支撑的原理之谬误。此外,这次访谈中列维-斯特劳斯亦确认了尼德姆提出的不可得到普遍理论的结论。
笔者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发表的见解显然没有终结这场讨论,相反,他的这些意见促使我们展开精准的辩驳,并理清我们的理论工具。当然,本研究的目的与其说仅仅是有意“摧毁既有概念”,不如说旨在更好地解密各种社会的运作机制的内在动力。
此外,在我们辩驳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普遍命题后,“社会血亲”或者“社会血亲关系”,以及“社会血亲性排斥定律”在我们的理论化过程中占有首要的地位。它们才是亲属关系领域的两个真正的常数,甚至可以确认,它们是两个不变量。就知识论的角度而论,概念和定律代表的不是特殊性,而是普遍性或同一性。在笔者看来,“社会血亲”和“社会血亲性排斥定律”[13](P97~98、350~362)是廓清隐含于性行为多样性中的秘密的两个核心概念。是否能够抓住“filiation”(血统)、“inceste”(生物血亲性关系)、婚姻联系和家庭的本质属性,也同样取决于它们。
我们知道每个民族有自己的血亲划分规则。纳人社会中,Ego只与母亲、母亲的兄弟姊妹、自己的兄弟姊妹,以及母亲的姐妹们的孩子互为骨亲,往上代和下辈都以此类推。即使是任何在血亲关系中引入了生物学揭示的遗传规律的婚姻法或家庭法,人们也必须确定一个亲属范围,在它之内,禁止一切性爱,在它之外,则不受限制。
由此可见,相对于Ego来说,任何社会都将其成员区分为两类:一类与Ego相同,即他的血亲,另一类与其相异,即他的非血亲。可见,在人类学已知的各类社会,不论是古代的,或者今天的,它们执行的血亲规则的本质属性都是社会的,因此它们因社会的不同而异。据此,“社会血亲”概念和“社会血亲性排斥定律”不仅解释了人类不同民族的性行为的多样性,而且揭示了它们的同一性。为此,人类性行为方式中的多样性和普遍性不再呈现对立的、互不相容的面貌,并且被纳入了一个统一的理论解释中。
科学史中的大量事例一再地表明,“科学革命是打破传统的活动,它们是对受传统束缚的常规科学活动的补充”[19](P5)。我们知道,为了科学事业,研究者前赴后继,他们的论点相异,但目标是同一的:认识我们生存的世界。科学知识总是,并且只能是在不同研究结果的出现中增长。纳人的个案在亲属关系人类学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理论危机,这势必引发新的普遍理论假说的建立和对我们人类自身更深入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