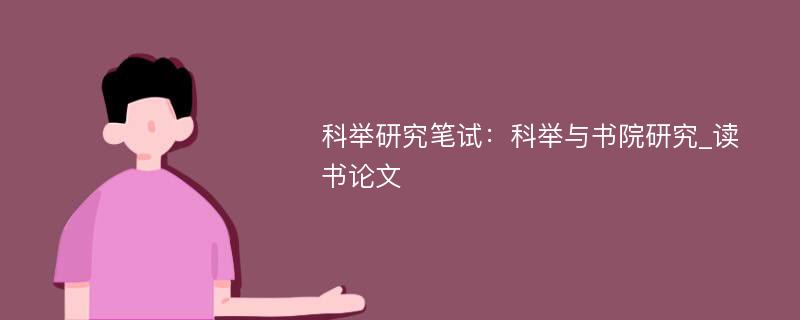
“科举学”笔谈——科举学与书院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笔谈论文,书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举制度是唐宋以后的主要文官选拔制度,而书院则是培养科举人才的主要机构。1000余年来,科举与书院密切关联,在中国古代教育史的大舞台上分别扮演了取士与养士的角色,成为关涉士人前途与命运最重要的制度。
对于这两种密切关联的制度,目前已经形成了两门密切关联的专学——科举学和书院学。科举学是一门以科举制度本身及其相关的领域作为研究对象的专学,无论从其时间跨度、空间分布,还是所涉及的学科、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等方面而言,科举学具有其他任何一门专学所无法比拟的包容性。而书院学则是运用历史、教育、哲学和政治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研究方法,以书院发展史、书院教育、书院学术学派、书院建筑等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门专学。由于科举制度和书院是相互关联的,科举学与书院学也是密切关联的两门专学。
由于科举制度是人才选拔的“抡才大典”,是唐宋以来的主要文官选拔制度,也是朝廷调控教育的重要手段,包括书院在内的教育机构产生、发展及内部体制的运作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科举制度。因此,科举学是书院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科举学理论是把握书院发展内在规律的重要前提。由于科举制是一种取士制度,并不具有人才培养功能,只是通过给予科举及第者的功名利禄来诱使读书人接受教育,这样书院在官学不能满足士人读书应举的背景下,往往成为培养科举人才的主要机构,书院也藉此获得极大的发展空间。
唐末五代,为获取参加进士科所需要的诗赋文学知识,不少士人隐居山林发奋苦读,从而在藏书、读书场所的基础上逐渐衍生出书院这一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可以说书院是因科举而生。北宋建立以后,在科举制度不断完善、地位日渐提高的基础上,书院替代官学培养人才,出现了书院的短暂兴盛,并涌现出史家所称的“四大书院”或“六大书院”。南宋中后期,随着程朱之学的正统化,科举考试内容与书院教学内容重合,书院再次因科举而兴盛。明代中后期,书院重新担负起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书院从明初的沉寂走向繁盛。清代中叶,朝廷改变出于政治目的而抑制书院的政策,引导书院为培养科举人才服务,书院数量因之急剧增加至3000余所。
科举制度不仅是书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往往是限制书院发展的主要手段。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王安石和蔡京先后三次实行大规模文教改革,将入官学学习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前提条件,甚至以学校的升级考试取代科举考试,书院完全被排斥在科举教育之外,使北宋前期替代官学而兴起的书院走向衰败。明代朱元璋立国之初,也以入官学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前提,书院因此沉寂了将近100年之久。1901年开始的书院改制依然受制于科举取士制度而少有作为,直至1905年,清廷宣布废止科举取士制度之后,书院改制的进程才明显加快,可以说科举停罢是书院改制的直接影响力量。由此可见,书院学在研究书院发展脉络时,必须借助和运用科举学的研究成果,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书院千年的发展脉络,而这正是书院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
其次,科举学研究能为书院学的重大理论问题提供理论支撑。理解和研究与书院相关的问题时,必须将科举制度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纳入研究视野,使之更能反映历史真实。如书院精神是区别书院与其他教育机构的主要特征,也是书院存在的主要依据。对此,书院学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观点分歧甚大,有的学者(如陈东原)从南宋书院大师批评科举的言论出发,认为南宋书院的主要精神是反对科举。笔者认为,书院学研究者阐释这一问题时,必须借鉴科举学的研究成果,这样不仅可以理解南宋科举社会已经形成之后,科举制度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且可以更加透彻地体悟士人对于科举制度的矛盾心态:一方面,科举制度与儒家所倡导“学而优则仕”的理论相一致,也是唐宋以后士人践行“治国、平天下”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科举制度又与其自身所宣扬的政治理念、人才培养标准有相当大的差异。这种矛盾心态迫使士人一方面从自己所信奉的学术出发,对科举制度及书院的科举教育进行严厉的批评,并提出了改革设想;另一方面他们不但自身积极应举,而且更不可能反对生徒应举,因此将南宋书院的精神归纳为反对科举显然是不恰当的。
又如,书院学研究者往往根据教授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不一致,甚至排斥科举之学的表象,将清代汉学书院视为反对科举的典型。但科举学的研究却表明,乾隆即位之后,不仅乡会试二三场的出题明显偏重于经史知识,而且殿试策论也多以经史考据知识为题,这种考试内容的变化有利于讲求汉学书院生徒应举。对于作为“敲门砖”的八股文,科举学研究者认为要使其言之有物、不落俗套,考生不但要掌握文体的结构和行文技巧,还必须有扎实的经史知识功底。因此,讲求汉学书院的教学内容虽然与考课试书院有相当差距,但其教学有助于生徒在科场中脱颖而出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亦可以从汉学书院极高的科举及第率上得到验证。显然,如果仅仅囿于书院学的相关文献,而忽视对科举学的研究,类似于这样的书院学问题的研究则很难切中肯綮。此外,科举学的相关知识还是正确领悟书院规制、章程等的基础。
由于书院受制于科举取士制度,其教育、教学活动的展开,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教学效果的检验等方面都体现出科举制度的影响,这样,书院学研究能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扩大科举学的研究领域,丰富其研究内容。
第一,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为科举服务的书院数量众多,它们不仅是书院学研究的主体,也是科举学研究主要对象之一。唐末五代,有教学功能的书院虽然为数不多,但其为科举服务的倾向十分明显。北宋初出现的书院基本上都是为科举服务的。赵宋南渡之后,虽然有少数书院反对科举之学,但大多数书院都直接或间接为科举服务。元代书院官学化之后,直接为科举服务的倾向更加明显。明代中后期,大多数书院都由官方创办或修复,占书院总数的70%以上。清代不仅绝大多数的书院都直接为科举服务,而且讲求汉学的书院也间接为科举服务,这样科举特别是与书院相关的科举制度是书院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中国古代书院的总数为7045所,[1]其中绝大多数是开展科举教学的,记载这些书院活动的史料主要有书院志、地方志和个人文集等,其数量相当庞大。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书院志有150余种,仅《四库全书·集部》所收录的书院记、书院碑记和书院有关的诗歌就达2300余篇(首),地方志记载的书院史资料更是汗牛充栋。这些文献中包含了大量与科举有关的历史文献,其中不少书院志和地方志以相当大的篇幅记载山长题名和生徒题名就是典型。这些既是书院学研究书院科举的重要文献,也是科举学研究一所书院和一个地区科举情况的翔实史料。如《道光如皋县续志》卷3所载《安定书院院长题名录》,共录山长10人,全部为科甲出身,其中进士2人,举人8人。《道光江阴县志》卷5《暨阳书院》载乾隆三年至道光年间的32位山长中,进士出身的18人,举人出身的10人,制科出身的1人,其余3人为副贡,科甲出身担任山长者占90%以上。这既说明书院将山长的科甲出身视为开展科举教学的重要保证,进士多出任山长也反映出清代江浙地区科第之发达。
此外,书院志和地方志中还收录了大量的书院学规和章程,它既是规范书院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文献,也是一所书院和一个地区科举活动的重要指标。如不少书院章程规定了书院的宾兴之费的数量和来源。从这些文献可以发现,不仅经济发达地区书院提供宾兴之费,而且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的书院也提供数量可观的宾兴之费,并有制度性的供给来源。如云南的碧晓书院乡会试资助经费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嘉庆庚午、癸酉岁科两试,廪生等议将认保童生画押钱捐集,以作会试等卷金、程仪之费”;一是道光四年(1824年),贡生严诚捐银100两。书院将这两项经费购置房产并生息得收入787两,以资助参加乡会试考试的书院生徒,并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条规。[2]这一章程固然反映了碧晓书院对书院科举的重视,而从提供经费者的出身来看,又相当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地区崇尚科举的风尚。此外,不少书院记、书院课艺和与书院相关的诗赋等,既是记载和颂扬书院的文献,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科举文学的范畴。
第二,书院学研究能丰富科举学的内容。不仅书院学与科举学内容有诸多的重合之处,而且书院学研究还能在一些方面丰富科举学的研究内容。由于培养科举人才是书院最为重要的活动,也是书院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因此研究书院科举教育及其相关问题,从山长的科举观、书院的创建目标、规制的形成与修改、祭祀活动等角度,展开对书院科举的深入研究,不仅是书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能将利,举学的研究范围由单纯的科举发展史、贡院规制和科举社会、科举文化等扩充至人才培养等领域,使科举学研究包括科举制度、科举人才培养和科举社会等主要方面,这也正是科举学进一步走向成熟的需要。
不仅如此,研究书院学还能在微观层面上丰富科举学。笔者在查阅地方志时,发现了一则北宋书院立科举题名碑的文献《道光徽州府志》卷7《书院》记载:徽州绩溪的云庄书院立有两块题名碑,“其一自嘉祐丙申科至端平甲午科,其一自淳枯丙午科至咸淳癸酉科。”前一块题名碑记载了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至端平元年(1234年)的178年间书院及第者的名单。另一块所记载的则是自淳祐六年(1246年)至咸淳九年(1273年)间书院登科第者的名单。科举题名碑既是对科举及第的褒奖,亦是对其他读书应举者的激励。进士题名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但由官方主持为进士立题名碑并将其制度化则是元代的事了。云庄书院题名碑的史料,一方面反映了这所书院的教学是为科举服务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科举题名的风尚在宋代依然存在,而且其影响深入到民间,说明宋代科举社会已经初步形成。
总之,科举学与书院学是密切关联的两门专学,科举学是把握书院发展内在规律、理解书院学关键问题的理论基础。书院学不仅将书院科举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而且书院学研究也能丰富科举学体系,使其成为一门外延更广的成熟的专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