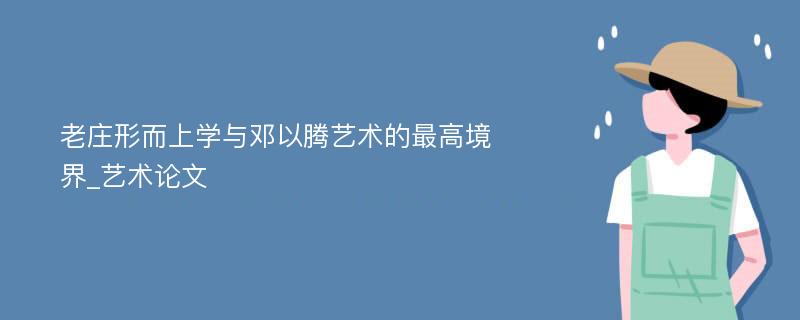
老庄玄学与邓以蜇的艺术至高境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玄学论文,至高论文,老庄论文,境界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4)01-0089-07 邓以蜇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邓以蜇认为艺术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能达到一种绝对的境界,得一刹那间心境的圆满,这就是艺术的至高境界。他认为中国书画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气韵生动”,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以及艺术鉴赏活动最终指向此艺术的至高境界。中国的艺术家要创造这样至高的艺术境界,要有人格修养和理想追求,老庄玄学在这方面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历代大画家、大画论家,他们所达到、所把握到的精神境界,常不期而然的都是庄学、玄学的境界,特别是在书画方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的学者与理论家,邓以蜇的艺术思想明显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至高境界——自然之境 道家崇尚自然的审美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艺术以及艺术家的主体心灵与境界。道家思想渊源当以老子、庄子为代表,“崇尚自然”“自然至上”的自然观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此所谓“自然”,是指蕴涵于物理世界之中而又超然其上的天道运行本身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法则。它引申为一种自然美学观,对中国传统绘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制约着传统绘画发展的方向。[1] 邓以蜇认为中国艺术是深受老庄智慧的滋养的心灵深处的性灵儿。他引用《文心雕龙》“老庄告退,山水方滋”,说晋六朝以来,诗皆以山水为对象,是与山水画之对象一致矣。[2]“六朝以后之诗与山水画皆所以继承老庄者耳,吾国谈宇宙玄理之学,舍老庄而何!故在诗画必曰直寻、妙得、玄解、明赏云者,盖以之为探求宇宙玄理之事耳。”[2] 邓以蜇认为中国传统之山水画与诗的追求皆是老庄玄理的境界。他指出,中国的诗追求一种“别境”,诗的别境就是要在艺术的表达中透漏出未知的境界。他说: 诗既以言词为工具,它所及的远处,应不止于情景的描写,古迹的歌咏,它应使自然的玄秘,人生的究竟,都借此可以输贯到人的情智里面去,使吾人能领会到知识之外还有知识,有限之内包含无限。卢克莱修,但丁,歌德以及陶谢的小诗,屈原的歌骚,释老的经典,都是人类的招魂之曲,引着我们向实际社会上所不闻不见的境界走去;(我们的扈从随在这些神曲之后的:前面有感情,中间有想象,最后有智慧随押着。)眼前所望的是万物无碍,百音调谐的境界。然后回顾到人世间,只看见些微末的物体,互相冲击,永无宁静。这是何等境界!何等胸襟!人生的知觉走不到这个处所,是不值得的!这才是诗的别境。[2] 邓以蜇这段论述,指明了人类艺术的最高境界应该指向哪里,就在于脱去世俗的认知,将知觉的触角尽力伸向那不闻不见的未知领域。这个境界就是释迦老庄的境界。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关注的是事物的功能关系与运动转换关系,追求事物之间相克相生及相互转化,它强调体验、感悟,强调审美的直觉与心灵体悟,以致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存在”境界。“天人合一”即是由道而德、由德而道的。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合一也是道和德的合一。从这个角度说,人类一切伟大的艺术均是“释老的经典”“都是人类的招魂之曲。” 中国传统哲学中永恒的理想境界是:永远不失去对“道”的内心体会;永远不失去对“道”的思想理解;永远不失去对“道”的价值认识。这是中国人心中始终孜孜以求,不倦探求,永不放弃的人生理想。这也是中国传统艺术发生发展,不断演变的最大动力与理想的境地。 这种天人合一,道和德合一的境界,体现老庄的哲学中,可以有几个关键词加以表述,“自然”就是其中一个概念。“自然”在道家哲学,以及中国艺术理论中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审美理念。同样,“自然”在邓以蜇的艺术观念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阐述概念。 邓以蜇结合中国艺术的发展历史认为中国艺术在形式与内容的发展上力求表出意境,是否做到“自然”对意境的表现是格外重要的。他说: 人物至六朝唐虽入神,但究为个体之描写,虽有群像,其结构亦借动作之呼应为连贯,仍未能参入于自然以成一意境也。意境者乃由内而外,为主观的;若表而出之,其方法有异于人物。禽兽人物为客观的,艺人用传摹或状拟以取之,主要功夫,犹在眼力。若意境者乃将自然看成一全体耳。自然中草木泉石,个个孤立,非如动物之有动作相呼应以成连贯,如何而能看成一全体?曰:艺术之发展,于兹已进于生动,再进于神矣。神之用在能得物之全。沙汰物之肤泛,凝化物之个别,使范围周洽,物自连贯。[2] 这是一段非常精到的论述。由生动——神——意境,这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基本的走向,邓以蜇对意境的解释,认为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个别到整体的过程。只有到了能够表出意境这里,中国的艺术才真正走到了一个很高远的境界。在意境的表现过程中,是否“参入于自然”,是否能将对自然的观照合成以全体,是否“沙汰物之肤泛,凝化物之个别,使范围周洽,物自连贯。”才是表现意境的根本。 中国山水画家更是把“自然”看得很重,山水家之所谓天趣也就是自然,何为自然就是表出物象最本真最鲜活的生命。 关于对生命的诠释,庄子的《养生主》是最好的注脚。庄子在《养生主》中所阐明的是一种大的生命观和大养生观。其大生命观是,认为人有三个生命:肉体的生命、精神的生命和价值的生命。[3]庄子认为养生的重点不在养形,不仅仅在养育肉体的生命,不仅仅在名利地位,而在精神生命,在养育自由的精神和对自由的追求。庄子对自由的追求是有一定的方法与途径得意实现的。对庄子来说追求自由最重要的方法与途径就是超越:超越名利,超越善恶,超越磨难,超越外表形体的完整及美丑与否。所以庄子世界里的生命,是要以肉体的生命的完好保全为基础,以精神生命的追求为重点,以价值生命的薪火相传为目标。最终的价值生命也是天地一心的生命,这个价值生命呈现出来的就是“神明”。 对于是否呈现自然万物的神明,历代的中国艺术家尤其是山水画家是极为关注的。他们“师法自然”,读书万卷,行走万里,为的就是在“游”的过程中,物我两忘,其心境摆脱现实的束缚,进入到了一种纯自然的状态,在无任何功利性目的中寻求一种“与天为徒”“入于寥天一”的状态,在这个状态里体悟神明。正如邓以蜇先生所言: 画不在画物之可见之性,而在根于玄解以画其神明。何谓神明?广川又言曰:‘世之评画者曰妙于生意,能不失真,如此矣,至是为能尽其技。尝问如何是为当处生意?曰:殆为自然。其问自然,则曰,不异真者,斯得之矣。且观天地生物,特一气运化尔;其功用秘移,与物有宜,莫知为之者,故能成于自然。今画者信妙矣。方且晕形布色,求物比之,似而效之,序以成者皆人力之后先也;岂能以合于自然者哉?’由是观之,生意,真,自然,气皆属一事。神明为物之真象,真象同于真,则神明,生意,自然,气无不相同矣。神明为不可见之物;若画之,必先得于心所谓玄解者而后可,画出此神明为不异真,不失真,或为妙于生意。[2] 这样艺术是能够“妙于生意,能不失真”。何谓“生意”?邓以蜇认为就是“殆为自然。”如何得之?要“观天地生物”而且要观出“一气运化”“成于自然”的境界。最后体现在艺术中“晕形布色,求物比之,似而效之”,关键是要“合于自然”。最后他总结说“生意,真,自然,气皆属一事”都可以概括为“神明”,神明为物之真象,这样看来神明,生意,自然,气都是一件事情。因为神明是不可见的,若要表现,必得玄解。如何玄解?庄子都有回答,就是“心斋”、“坐忘”。 这样看来老庄玄学里的“自然”就是天地万物融合无间的真象,就是神明,在主体精神上表现为庄子“逍遥游”的自由精神,“逍遥游”是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学说的最高理想。主张采取一种逍遥自然的生活态度,无所依赖、绝对自由地遨游永恒的精神世界,他强调“神”的概念,这一思想延伸到艺术领域就是要追求一种独立超拔、无所依傍的艺术创作精神,达到逍遥自在的艺术境界。 艺术形式上的“与天地精神独自往来”的自由境界取决了艺术家的心灵,邓以蜇在其论文中一直强调,笔妙、画妙源于心妙。心如何能妙?还需人品妙。妙即是心灵的自由、自在、自然的境地。 二、迁想妙得——不可言喻 道家一直主张,这个世界的本体真相不可以言说,同时道家又肯定我们是可以认识并接近此宇宙本体的。因为道的获得要靠“玄解”要“迁想妙得”。因此不可言喻。关于这一理念,在中国的艺术理论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艺术命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艺术以及艺术理论。 邓以蜇在《诗与历史》一文中,讲到了语言文辞的局限性问题。他说: 不过言词终不外乎理智对于具体的印象的一种抽象而已,用来和声音颜色相抗衡,总有些挣扎吃力的痕迹。所以用文字描写的情景,结果必堆砌得利害;汉赋便是一个明证。一方面想不失具体的印象,他方面又求表现的结果能得读者充分的领会,于是假借比拟,无所不用其极了。……文字的表现到了这样落套的时候,便成了表现的抽象,犹之乎一个字是一个印象的抽象,久之就唤不起印象的具体来了。所以看到这种缺憾,文字是不知声音颜色的了。[2] 在此,邓以蜇指明:每一种艺术语言都会有一定局限性。每一种艺术语言一旦形成其成熟的语言形式时,也会走到其极限,每一种语言形式都有来自它自身的局限性。突破的方法就是超越自身与忘言表意。即打破艺术语言形式的门户之见,极大限度的吸收与容纳多种多样的形式语言。关键的问题是表出意境为宗旨。邓以蜇在《画理微探》一文中讲南北宗时,进一步表述了这一观点: 其意境乃在乎山林泉石之天趣而洗尽北宗之台阁气也,以意为主者不仅超脱迹象,抑且不得以天然之理绳之。[2]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故有辋川诗什,亦有辋川图也。诗有声,而画无声,今以画为无声诗,是援诗之声韵入于画,使画为一生动之物而有气韵矣。诗有各种意境,如欧阳修之“萧条澹泊”、“闲和严静”,王安石之“荒寒”者是也。画有形而诗无形,今以诗为无形画,画为有形诗,则诗之意境皆可画可形矣。后之写意画实基于此也。[2] 另外他在阐释文人画与心画时多次借欧阳修的鉴画理论说:“画者能将萧条澹泊之意画出矣;难形,亦有能将闲和严静趣远之心形出矣。此意此心为画者创作之本。……意或心乃为画者心内无形迹可见之物。……凡无形迹可见之物表而出之者方为气韵。创作须表出心内意境而非摹仿物之形似,是创作之表现当为气韵矣。”[2]对于艺术创作,艺术家如能突破形表出意,就能达到艺术的至高境界。 对于艺术鉴赏,邓以蜇指出:“若真赏则当与画者创作之‘心’‘意’一致,画者之意为萧条澹泊之意,画者之心为闲和严静趣远之心,画出此意,形出此心,非形似而属于气韵,然则精鉴之事为识气韵可知也。”[2]可见对于艺术鉴赏就是能够意会出此难形之萧条澹泊之意,这种意会依然是超越语言的,无法用精细的逻辑分析与概念判断的。邓以蜇指认为真的创作,真的鉴赏都是会心人的事情。只可会心,会心的结果也许只能相视而笑罢。所谓知音也是指知道和领会的是彼此心底的声音,一旦付诸笔端,一旦言辞表达,就失之千里了。主要原因还是言辞,一切有形的形式难以捕捉动态的生命力。对于作为真象的神明无法用言语表达,只能让神明自我呈现。 这些顾恺之所谓“神仪在心”、“神属冥茫”的无形迹之气韵,无法言语道断的思想,在老子的《道德经》里有大量的描述。显然道家思想对山水艺术与艺术画论的影响是深远与深刻的。 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道即终极实在无法说明更不能命名,以人心的通常方式我们无法见道,或无法识别。这是老子思想的一个主轴,《道德经》之开篇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一章》) 老子又指出: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语言是不可能真正地描述道的。但是,如若道如此的无可名、不可言,我们又如何接近道,认识道呢?老子思想中几处透露古代圣人察天识地,在与万物同归于寂,物我两忘的境界下,体察出事物活动过程的规律性的动态情境,从而明白自己内在的认知与体悟实际上源自于道本身的性质。认识到人与道本为一体的道理。例如,老子曾这样描述道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传之不得名曰微。……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道德经·十四章》)在这里,老子描述道的特点,为夷,其精微不可见;为希,其冥渺不可闻;为微,其无形不可触。总而言之,道所呈现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在二十一章又有:“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德经·二十一章》)道的特点为惚恍、窈冥。但是惚恍非绝对的虚空,虽无形但有质。其中有物,有精、有信。我们可以通过体察这些信息来认识道。这些信息在人心达到宠辱不惊、寂静虚空时会独自呈现,但其间变动不居、仿佛灵光乍现一景,难以用语言把握与形容。因此道终究超越任何名词的限定,包括人为的预见、推理与想象。 另外,老子给我们一个认识道的途径与方法,即“明”。明为心性的纯净无染,明为心智的洞察明晰。明在这里就是一种超越语言或者不依赖于语言形式的本体诠释法。老子还指出心性如何达至“明”,即要致虚,要能静笃,要能归根,要能知常。最终的结果都是虚静,只有虚静才能洞达与明澈,才可以致明,能“明”就可以进到本体之观里,进而识道。这种获得宇宙真实实相的方法是靠心的虚静与明达,它不需要任何有形物质的依傍与辅助。只有当一个人认识道,体察道的时候,他才恢复了其真正本体,切实实践了道。所以圣人会“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道德经·五十二章》)所以老子才这样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德经·四十七章》) 当一个人确实与道相合,得到道的认识与体验之后,往往不再言语,也停止运用语言与思维来表达这样的认识,因为语言是分裂的,多样的,而道指向一致、整体、和谐的本体。正因如此,言语言说的就不会是道,因为道是自然的呈现,不是表现。 同样庄子强调,超出语言的道通过直接体验,以及要对其进行直接实践。人为了了解道,首先必须成为真人。真人的特点是与道合成一体,意会道的经验,庄子指出,虽然有一些语言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道,但是我们一旦拥有这样的知识,应该立即中止语言甚至忘记使用语言,以努力保持与道的合一性。这样忘言也就自然地发生。他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齐物论》) 相对于老子,庄子更善于运用鲜明活泼的形象,以具体而富有想象力的形象,来彰显道的本义。道家的这种智慧方式被后来的佛教徒以及禅宗派用来修习心智,开启智慧,通过心印或公案的自相矛盾达到头脑的暂时性断流,以实现对道的体悟。可见,对道家而言,在语言之中寻找生命本体是一种徒劳之举,言语根本不表示任何事物。所谓不可言喻之本体是指,我们对其理解超越了语言,我们不需要借助语言的表达而得以实现的本体。 虽然这不可言喻之本体只可以通过意会方式被认知,但它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符号系统被象征性地指称的。这就是艺术的象征性功能的范畴了。艺术符号可以通过象征性的形式符号使不可言喻之本体得以呈现。 三、游心于艺——技与道合 邓以蜇的艺术学文集有大量的内容谈论艺术技法的问题,如《画理探微》、《六法通诠》、《辛巳病馀录》等。文章中主张艺术家在艺术技法上既要有所继承与学习,也要有自己的风格与特点,要能够“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他主张学习中国古典绘画经营意象的理念,认为它全然符合艺术创作的本体自律性。传统书画艺术家笔妙,画妙,心妙,人品妙。艺术之技巧与人心达到“随人心得”,即“心与道合”、“一与道同机”,进而“遗去机巧”、“技进于道”,得乎自然的境界。邓以蜇的这些思想与宋代苏东坡的书画思想是一致的。 苏轼有“有道有艺”、“技道两进”、“道可致而不可求”、“学以致其道”等观点,“技与道合”是古代艺术的一个理论命题。苏轼认为,道非凭空自得,须经历一番艰苦的技艺磨炼,一般性的技艺只有历练升华为道的层面,与道相合而后方可称之为艺术。 “技与道合”论深入地揭示了艺术的本质和创造规律,可以视为中国艺术创造的纲领,这一思想从源头上讲来源于道家哲学。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整体风格与面貌。道家所提倡的质朴与无为更是中国艺术长期追求的一个至高境界。它要求艺术家摆脱后天人为的一切束缚,所谓去欲、去知、去为,将身心全然地融入到大自然中。中国的艺术作品在风格上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正是这种观点的实践与体现。 道家主张以“无为”的态度对待万千世界,追求恬淡的生活,含蓄内敛。道家认为真正的美不在感官的享乐与满足,而是精神安定和无所依傍的自在与自足。它要求审美主体超然物外,物我交融,达到“我与万物为一”的境界,如何实现这样的境界,即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文赋》),登高望远时,用整个身心去感受茫茫宇宙间生命的律动,进而在静观寂照中,进入天人一体、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样,在艺术创作时,才能化万物为神思,化神思为形象,将形象诉诸笔端,中国历代的画家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感受去铸造自己理想的艺术大厦的。这种对道的接近与追求构筑了中国山水艺术独特的审美内涵与精神品质。 (一)《庄子·养生主》与游心于艺 “游”是一种“玩物适情”的状态,审美主体的心境在娴熟的技艺中,出神入化,几近天趣,这种境界在《庄子·养生主》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庄子·养生主》描述的是一种“得于心而应于手”的“游刃有余”境界,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在技艺上达到“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文惠君诧异地问,为什么能到如此的娴熟的境地呢?庖丁回答“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庖丁在技术上达到了“游刃必有余地”。庖丁解牛的寓言故事描绘了“道技”的关系和“游”的境界。指明了道、艺关系是:道来自于技,技升华于道。这个寓言故事也说明了一个道理:“技进”首先是一个长期艰苦磨炼的过程,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践活动才能长进技艺。亦非简单的技艺提高,而是要超过、超越。要达到“进乎技矣”之理想境地,主体心灵要一心“向道”,真诚“好道”即有意识地追求道,以“得道”、“悟道”为理想目标。在老庄的思想中,“道”并非神秘的、不可得的事情。它是天地间的某种必然性,一物之所以为某物,肯定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天地万物无不各有其道。 这种对道的体验与向往对中国艺术家的修养、经历、知识结构、审美趣味、个性等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中国传统艺术家总是游历山水之间,忘情,忘我。他们对自我人格修养的关注与重视,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创作过程中本体与方法同一的独特路径。中国山水画家尤其重视“随人心得”,着意于艺术家个体的多样性,开放性、自在自为、恬淡自然的经营与布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能否创造出“虚”或“空”之意境美,是判断“技艺”是否合于道的一个重要标准。 (二)无用之用与由技而道 中国艺术的创作、欣赏的审美原则及艺术作品的风格无不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在艺术创作方面,中国山水画追求具有无限生意和深邃空灵的意境,物我浑一,虚涵空寂。艺术家在创作中不只是单纯的表现自然,而是以自然来传达艺术家的审美观,精神境界,人格涵养。使艺术家心中之境与艺术作品中的景融为一体,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只有这样,作品才有望达到神品、逸品。 所以,历来的山水画家都会把他的心灵完全融化在笔墨里,寄情于花鸟、山水间,浑然忘我,心与物游,与天地同一,达至艺术的最高境界。这是中国艺术的主体精神,也是中国艺术的义理与观念,它使得艺术家体验自然、升华自我,将追求艺术境界,讲求技法高妙与悟道修行结合在一起,成就的是中国艺术家艺术化的人生,追求恬淡自然,超然象外的人生境界。 道家追求“大巧若拙”,“大音希声”(《老子·四十一章》),崇尚“自然”与“质朴”,同时保持人与事物的真情与真态,故追求万物之神理运化与形象的生气灌注。所谓,“希音自然”(《老子·二十三章》),一方面是指物的自然混沌,未经人工污染的天真纯朴的状态,另一方面是指物的“虚”、“无”的本体特征,所谓“体道”即是体验宇宙的生气与生命的生生不息的流转与律动,是与天体万物无有分别的融合无二,是一种“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浑然之境。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庄子》)反映在艺术上则是指不仅写出物之“形而下”之形象,更要见出“形而上”之“气”,“形而上”之“道”的本体特征。 老庄崇尚“无味之味”,称之为“至味”。追求“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强调“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庄子·山木》)指经过精苦思力的过程之后,复归于朴素,是一个以深沉的内涵融合于外在形式的过程。之后的宋代山水理论家正是在此老庄辩证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平淡”的艺术理想,创造出“得意而忘言”的艺术境界,是“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庄子·杂篇·外物》)从而形成了“虚和萧散”、“出韵幽淡”的审美取向。 邓以蜇全面继承了老庄哲学关于由技而道,技道两进的观点,如在《画理探微》中有这样一段总结性的文字,探讨了在艺术发展的过程中技巧与艺术本体——道的关系: “艺术源于器用。造作物质以适应器用,而器用又适应于美感以成其形体,故艺术为人类美感之表现,同时美感亦因造作而显。渐次,由造作趋于装饰,踵事增华,不觉美感离于器用渐远,艺术渐成器用之赘疣矣。艺术既失其本而自安于装饰,遂为雕虫小技,游戏之事矣。若美感为艺术之源,艺术之表现当与美感愈逼近愈真,器用之体虽有物质之介在,而其形或浑沦开阖之形,或均称之形,或重叠之形,或上下大小之形,形既简单,与美感亦最为直接;倘能混物质之体积、重量、颜色诸性于造作表现之中而不显其为意外之迹者则更为工至。今装饰云者是离器用之体而为异外之事,去美远矣。画亦然。画者形也。非摹拟外物之形似,但为绘画者心中之意境以形象也。”[2] 显然这是邓以蜇对道家讲究“无用之用”,画家由技而道的规律的整体把握与总结。 总而言之,道家游心于艺,技与道合的思想对后来的山水画家以及艺术理论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艺道两进”,所能够达到的艺术创造境界就是苏轼所推崇的“随物赋形”和“行云流水”的艺术境界。“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苏轼:《自评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答谢民师推写书》)这其实就是“游心于艺”和“技与道合”的境界。又如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提出:“有画法而无画理,非也。有画理而无画趣,亦非也。画无定法,物有常理。物理有常,而其动静变化,机趣无方,出之于笔,乃臻神妙。”(方薰《山静居画论》)这是对道家“无用之用”思想的运用,它强调艺术创作过程中创造力与灵动性,不拘于成法,不墨守于成规,能“出新意与法度”,自然而然地在创作中从有法而进入至法,即无法之法,无为之法,在艺术修养和技能上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