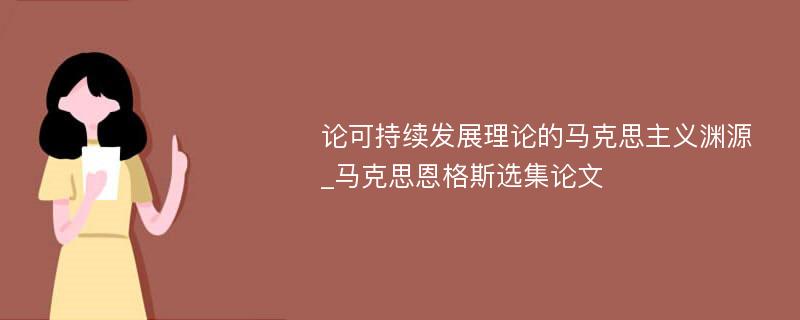
论可持续性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性论文,渊源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构成了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渊源。可持续性发展理论的这个方面应该引起我们广泛的和高度的重视。
一、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提出
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是指那些已处于发展中的或已发展了的社会能否及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资本主义是否可持续发展,自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就是一个涉及到意识形态之争的重要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自然规律和抽象的一般前提,实际上是从实质根据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乐观前景。19世纪中叶以后,这种论证转而诉诸于形式根据。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思考,实际上是从形式方面和主观方面重新或者说更严格地界定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尽管韦伯本人对资本主义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他在学术上还是认为,从世界范围看,起源于新教伦理并在经营上达到形式合理性的近代资本主义,相对来说,还是一种不多见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注: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10页。)。
本世纪60年代以来,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一批未来学家,痛心于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态、能源、资源、人口、环境和核危机的深刻性和严重性,指出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危机表明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达到了“增长的极限”(注:丹尼斯·米都斯等著:《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随着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类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必须改弦更张,走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罗马俱乐部认为,传统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上是不可持续性的,人类的未来发展前景也是悲观主义的(注:拉兹洛著:《决定命运的选择》,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14页。)。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韦伯再到罗马俱乐部的历史进程,逻辑地再现了资本主义在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上从实质根据、形式根据到事实根据,从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的演变。三者虽然持论不同、方法各异,但他们都是从西方资本主义视角上看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站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立场看问题。它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价值取向、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批判,构成可持续性发展理论的重要渊源。
二、可持续性发展的制度基础
人与人关系的核心是生产关系,是所有制问题。从这个方面看,由于私有制的限制,资本主义并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基础。
马克思认为,从其起源上看,“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从根本上看,资本主义只不过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不过是确立了“以剥削别人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形式上自由的劳动虽然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但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任何前资本主义的直接的暴力掠夺、传统主义的宗法和行政特权或者非理性的政治投机活动更具有持久性、连续性。然而,韦伯所强调的这个方面并不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私有和对抗性的实质。
即使从纯粹经济学观点看,维持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发展,也需要形成消费市场的有效购买力和对生产进行社会性调节。但是,这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是有限的。绝不是说资本主义注定了就是不可改变的,而是说所有制构成发展的前提。事实上,“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本主义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因此,正是资本主义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特别是其生产关系的扩张性再生产,促进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巩固和发展。而停滞或不能前进、不能扩张对资本主义来说则是致命的和意味着死亡。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对抗性的和扩张性的而不是可持续性的。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扩张对资本主义是一个绝对的要求。但是,这种扩张在性质上受资本的驱动,在经济上不断地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打断,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不断被两大阶级间的斗争所打断,并且最终在范围和程度上受到“增长的极限”和全球化社会的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扩张性是本质的,可持续性是现象的;扩张性是隐性的,可持续性是显性的。在扩张的尽头,发展上的不可持续性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三、可持续性发展的文化基础
人与其自身特定的精神关系,构成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文化气质。从这个方面看,由于普遍存在的物化和异化,资本主义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的足够的和真正的文化认同和精神资源的支持。
(一)社会关系的普遍物化,包括人与自身精神关系的物化,要求必须首先从客观的和实质的方面看问题,而不能只从主观的和形式的方面看问题。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韦伯命题,实际上是从主观方面(也是从形式方面)提出了资本主义是否可持续发展的精神资源和文化支持的问题。韦伯并不认为精神资源和主观因素决定着历史的进程,但他鲜明地主张,某些文化类型,如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有着独特的亲和性,并支持着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而其他文化则不同。应该看到,新教的精神气质,虽然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但这本身已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变,也可能更适合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主观方面和形式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本质的方面,还必须进行客观的和实质的分析。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独立的个人的接触而形成的社会联系,对于他们既表现为物的必然性,同时又表现为外在的联系,这一点正好表现出他们的独立性。对于这种独立性来说,社会存在固然是必然性,但只是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9~470页。)历史地看,社会关系的这种客观化、手段化和物化的进程,是从16世纪以来开始萌芽和准备,到18世纪才全面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前资本主义各社会形态”还是被“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还是一个“主观化”的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一个物化和客观化的社会。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从主观方面来看待资本主义问题,如新教伦理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关系问题,即使不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错误,也是一个时代性的错误;即使不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起源方面的错误,也是一个关于其发展方面的错误。
(二)文化的本质是人化而不是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很难说资本主义产生了足够的和真正的文化认同与精神资源的支持。在异化条件下,作为主体的人不是生产的目的而是生产的手段。劳动的客观条件同劳动相异化、劳动过程本身的异化、劳动结果的异化和劳动者的异化成为渗透社会生产一切领域的“恶的必然性”。即使资本家也完全同工人一样地处于资本关系的奴役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页。)。
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就没有创造出适应自身生产过程和社会需要的文化,而是说这只能是一种消极的、否定意义上的、异化了的文化。“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下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页。)从意识形态上看,甚至于文化和科学这种人类最崇高的事业也都沦为“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的牺牲品和祭物。
(三)从本质上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是因为二者具有共同的私有制背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正是路德的宗教改革从16世纪以来为资本主义的“职业化”劳动作心理的、信仰的准备。“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而从其经济、社会功能上看,“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适当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6页。)
(四)甚至钟情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本人,也悲叹于早在富兰克林时期,资本主义就已经丧失了它的宗教基础,资本主义精神不但失去了其神圣性而且彻底世俗化并腐朽死亡了。“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经不再需要宗教禁欲主义的支持”。“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色彩,而趋于和纯粹的世俗的情欲相关联”。面对资本主义“铁笼”般的资本和技术官僚统治的暗淡前景,韦伯以先知式的苍凉期望着在文化上能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注: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1~143页。),以支持和重现资本主义的昨日辉煌。即使站在韦伯的立场上看,如果说新教伦理曾经支持了资本主义的持续进步,那么,这只是它革命的过去,而不是它尚在未定之中的未来。
四、可持续性发展的自然(历史)基础
社会与自然的良性和建设性的关系,是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从这个方面看,由于资本的无限扩张本性所造成的二者关系的分裂和对抗,资本主义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的自然(历史)基础。
(一)社会与自然关系分化的历史进程。比较起来,原始社会既没有与自然分离和对抗的动机,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前资本主义的还是自然形成的各社会形态,有这样的动机但没有这样的能力。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既有这样的动机(而且动机更为强烈),也有这样的能力(能力也更为强大)。原始社会的“天人合一”无论在性质上还是水平上都是真正的“原始的同一”。而前资本主义各社会在性质上已经产生了分化、分离、对立和对抗,但在程度上、水平上还保护着基本的统一。它的分化是不充分的,它的统一是不完全的。而资本主义社会天人关系的分化,不仅是完全的而且是充分的。
还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天人关系分化的较高阶段上,这种分化已经不是那种基于对生存的基本需求的满足而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对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特别是“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和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与程度上通过社会组织起来的“共同活动”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和“利润成为唯一的动力”,这种对抗必然而且很快演变为对自然界的“征服”、“统治”、“剥削”甚至于“虐待”。正如桑巴特正确地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在于它不是满足于基本需要的需求型经济,而是获利型扩张性经济。我们要说,这种获利型扩张性经济的性质和动机,绝不会仅仅局限于对自由工人作为劳动力的掠夺性利用,而是也同样必然地指向对自然界作为劳动资源的掠夺性、进攻性、扩张性利用。那种“向自然进军”的口号所体现出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时代性特征,而且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意识形态特征。如果说,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还只是人类统治自然的可能性条件的话,那么资本的无限扩张本性则是追求这种统治的必然性条件。而二者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全面发展和结合,则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天人二分”的悲剧性后果变为现实。
(二)全球性危机的资本主义性质。我们认为,上述分析表明,60~70年代以来,罗马俱乐部据以向人类敲响警钟的“增长的极限”和各种全球性危机,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性质。所谓的“增长的极限”和全球性危机,从规模和范围上看,已经超出生产关系等人与人的关系的范围,而成为社会与自然关系范围内的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扩张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性质上看,这是作为对抗性社会关系和私有制度发展的最高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天人关系从原始的同一走向分离、对立和对抗并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蜕变为对自然界的“征服”、“统治”、“剥削”和“虐待”这个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前资本主义的各种自然形成的社会即使有动机也没有能力造成这样的恶果;社会主义(姑且不说它是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阶段和事实上它是在不发达条件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即使有能力也不应该造成这样的恶果。
(三)全球性危机的社会实践根源。我们认为,不能说是先有了(或由于)对抗性社会关系和私有财产的确立,才有了天人关系的二分,或者相反。“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或不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历史地发展着的、就其性质和程度看各不相同的社会实践进程。从这个意义上看,二者之间恐怕不是孰先孰后的因果性关系。作为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统一于和根源于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阶级社会开始的包括天人关系在内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社会实践及其“二重化”的历史进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页。)。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这种二重化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社会历史进程的最高阶段,是“各种颠倒错乱形式之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8页。)。“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0页。)人类社会实践的不同历史进程,决定了不但有着就其性质和水平看不同的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历史类型,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历史类型。罗马俱乐部所指出的各种全球性危机,特别是其中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危机,正是也只是本身“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不可避免的消极后果。
(四)全球性危机的历史观和认识论根源。
1.认识根源。全球性危机当然有各种认识不足和偶然失误方面的原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386页。)但是“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却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恩格斯指出,这个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路线,“自古典古代衰落以来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取得最高度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这种反自然的二元对立还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典古代世界没落时起,就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它现在还非常有力的统治着人的头脑。”(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页。)
2.历史观的根源。“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与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这些关系的总和形成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的生产方式,它构成历史的现实基础。“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五、马克思主义和可持续性发展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构成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渊源。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自己的关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理论体系。也不能说,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阶段时就已经预见了后现代社会的发展选择。但是,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包括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在内的整个后现代主义所无法回避也无法绕开的基本问题。“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就可持续性发展作为一个历史性的任务而言,从本质上看,它是无产阶级及其社会主义实践作为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在生成过程的时候,才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典政治经济学甚至还没有可能提出真正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因为它还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当然的事实来辩护。就问题的内容来看,马克思在问题还处在萌芽状态时就指明了问题的本质方面和客观方面,韦伯抓住了问题的主观方面和形式方面,罗马俱乐部则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并据以向全人类发出了警告。就问题的发展看,可持续性发展理论只是接着马克思思考问题而并没有超越马克思解决问题。
(二)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采取当然的、乐观的辩护态度不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持严肃的、辩证的批判态度。和韦伯从形式方面看问题,对问题持价值中立的超然态度不同,马克思主义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持客观分析和实质分析的立场。和罗马俱乐部面向全人类的价值诉求不同,马克思主义对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持阶级分析的市场。和三者都不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既对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充满人道主义关怀,又超越了苍白无力的道德评价,它根本上是一种历史辩证法的立场。
(三)马克思主义的可持续性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根源于社会实践的二重化,本质上是一个本身“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历史进程,因此,根本上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从而,“革命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构成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重建人与人、人与自身和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根本要求。
就人与人的关系看,它要求消除资本统治的扩张性、对抗性和剥削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危机,重新把人类社会活动的必然性占有为共同活动的自主性,重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构成了可持续性发展的制度性基础。就社会与自身的关系看,它要求改变人与其自身精神关系的物化和异化,重建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新型文化,这构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就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它要求彻底改变那种敌视、占有和虐待自然的进攻性、掠夺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重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共生和良性关系,这构成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历史)基础。三者有机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标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韦伯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