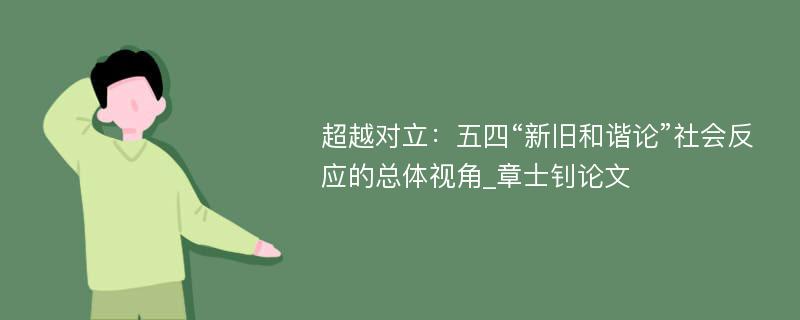
超越对立:五四时期“新旧调和论”社会反应的整体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旧论文,对立论文,透视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3)02-0089-04
1919年秋,章士钊先后在上海、广州、湖南、杭州等地的大学中宣扬新旧调和论。章士钊在舆论界、学术界的影响非常大,新文化人士对他的言论绝不能等闲视之。而且当时社会新旧规范混杂的状态,也使新旧问题成为时人的一个思想焦点,因此,又有一些人也借机发表对新旧的看法。这样,1919年末1920年初,各大报纸上就新旧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于新旧调和论的社会反应,已有一些很好的研究(注:如丁伟志先生的《重评“文化调和论”》(《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邹小站先生在《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章中也有论述。)但多侧重于其受批判的一面。笔者想考察批判以外更广泛的社会反应,以揭示出历史的复杂性。
一
章士钊运用了斯宾塞社会进化过程中新旧杂糅观点,来论证调和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斯宾塞曰:‘……特世变矣,而新者未立,旧者仍行,则时行,设图新而尽去其旧,又若运会未至而难调,此所以常沿常革,方死方生,孰知此杂而不纯、抵牾冲突者,乃为天演之真相欤?’斯氏之言,即所著调和精要也。”这就是他新旧调和必然性的主要哲学依据(注:章士钊:《调和立国论》,《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据此他提出,宇宙的进步如两圆台体逐渐分离,当其乍占乍脱之时仍是新旧杂糅,“此之为调和”(注: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而且他认为从实践角度来讲,提倡调和也具有合理性。因为社会上的情感、利害、嗜欲、希望决难统一,“为施行之便利计”,“当旧者将谢而未谢,新者方来而未来,其中不得不有共同之一域,相与舒其力能寄其心思,以为除旧开新之地。不然,世运决无由行,人道或几乎息”(注:章土钊:《进化与调和》,《甲寅周刊》第1卷15号。),如一意绝旧图新,不但事实上绝不容许,而且容易感召旧势力,使之复生,反而不利于新思想的传播、实施。
对于章士钊的言论,参与讨论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于“调和”这个观点,却并非简单地一概“否定”了之,而是在“调和”的时机、“调和”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以及自然调和与人为调和等问题上有更复杂的看法。张东荪第一个与章士钊公开商榷。但他虽然反对潜变的调和,却赞成突变后的调和,“潜变是不能调和的,调和潜变便是消灭潜变。但突变以后可以调和”(注:张东荪:《突变与潜变》,《时事新报》1919年1O月1日。);而且他也不否认新旧有共存的必然性,以及部分新旧道德有相同之处,“共存就是两个东西同时存在,这两个同时存在,却不是调和,……至于相同,譬如说旧道德主张克己,与新道德主张利他是相同的,但相同不是调和,因为只要取新道德就够了。”(注:张东荪:《答章行严》,《时事新报》1919年10月12日。)只是他不将之称为调和,而是提出了人为混合与自然融合之别,并反对甲乙人为的混合。
陈独秀和胡适虽否认调和的合理性,但实际上也承认了它的必然性。陈独秀反对把调和当作主观的故意主张,认为新旧因调和而递变,是人类惰性的作用,为了破除这种惰性的阻力,只有更加努力地向前。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即“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结果不过二元五角”(注: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第7卷第1号。)。他之所以有这个比喻,正是因为他承认了调和是客观的自然现象。就在同一期杂志上,胡适也发表了他的意见。他的思路和陈独秀的极其相似,即承认调和的必然性,否认它的合理性。“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而多数人至多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虽然认识到了调和为进化的真相,但新文化人士仍坚持反对调和论,原因正如止水所讲的那样:“假定社会进化底‘情状’和‘法则’就是曲线抛物线,然而主张文化运动底,却不能不认定一个理想底中心作‘直线’运行,若不然,那就只有自然底法则,没有人为底运动了,那还有什么‘社会进化’哦!”(注:止水:《〈止水君疑新旧调和论的研究〉·附志》,《晨报》1919年10月8日。)
有讨论者既承认调和的必然性也承认调和的合理性,但却不赞同人为的调和派存在,而主张自然调和。梦良认为,旧社会的现象在经过新派的攻击和旧派的清理两番淘汰后,只剩下了有存在的价值纯粹分子,可以与新的并行不悖,并行不悖便是自然的调和。而调和派“所期的效果,也不外等于自然调和的效果,或尚逊于自然调和的效果……并且先有此‘调和论’,反可以为‘自然调和’的防碍……所以无调和论的存在”(注:梦良:《“自然调和”与“调和论”》,《晨报》1919年10月19日。)。一位署名春禄的论者也承认调和的必然性,因为甲时代的国性民情的特性,一定遗传几分下来为乙时代的中心所吸收进去,只不过他认为“这个问题只有任天则的办法,不是我们人力所可以勉强做到底”(注:春禄:《止水君疑新旧调和论的研究》,《晨报》,1919年10月8日。)。
有讨论者不认同章士钊的调和界定,而另为调和下定义,但同样承认调和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管豹把自身无适当权衡的调和称为盲目的调和,他提出了自己心目中调和的内涵,即,无论对于欧化还是国粹,应该“一方当抱持续历史与顺应环境之态度,一方尤须有刷新历史与改造环境之精神”,寻求真理之所在,并加以消化作用,“始足以适应吾人之实际生活,始得成为吾人之所有”(注:管豹:《新旧之冲突与调和》,《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朱调孙批评章士钊对调和的界说不明晰,认为调和二字的界说,“决非两党利害相反因不得已而互相容让忍受、不问是非的妥协,乃是合人类智性的要求,将环境上所能搜集之有关事实,佐验参证,体贴入微,然后于每一思想中采取一定成分,造成一统括事实的臆说”。但他的界说实际上与章士钊调和含义中的一部分非常相似。
实际上真正与章士钊、杜亚泉在相似的含义上运用新旧概念,又坚决反对新旧调和的代表人物是钱玄同。钱玄同的新旧观真正与章、杜二人形成了对立,“咱们应该将过去的本国旧文化连根儿拔去,将现代的世界新文化‘全盘承受’,才是在正办。穆先生说我‘像是什么都不要了’,这确是我的真意。……我认为过去的各国文化,不问其为中国的,欧洲的,印度的,日本的,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都应该弃之若敝履。我对于它们,只有充分厌恶之心,决无丝毫留恋之想。”(注: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而他却没有参加这场论辩。
综合上述认识可以看到,讨论者大多认识到新旧一刀切开是不可能的,分歧点主要集中于如何调和及调和的合理性上。也就是说,对大多数的讨论者,甚至新文化人士来讲,辩论者对调和的意见是非常复杂的,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整体透视这场讨论,还会发现他们在思想态度上有一个大致趋同的闪光点,即希望在处理新旧问题时,采取批判的、理性的态度,而反对感性的,排斥一切的态度。
二
章士钊和杜亚泉对参加思想辩论者提出,考虑问题应该持理智、有选择的态度。出于一种理性的认知态度,章士钊认为,人的智力有限,所知道的大多是假定的“适然”或“或然”之理,并非“必然”之理。因此,当自己有所信仰的时候,不应该断然鄙视别人的信仰是不合理的。他感叹中国人对此缺乏认识,以至于反儒术专制的人,对儒术同样持废斥一切的专制态度(注:章士钊:《进化与调和》,《甲寅周刊》第1卷15号。)。杜亚泉则明确反对把感情和意志作为思想的原动力,认为这是把理性当作了情欲的奴隶。1915年当预感到中国将要出现“外来学说,又复标新而斗异”的局面时,他就提出:“吾国民于此时代,务宜力惩前弊,虚怀密虑,明辩审思,以宁静之态度,精审之考察,应付此纷纭之世变、繁赜之事理。”(注:杜亚泉:《论思想战》,《东方杂志》第12卷第3号。)后来,他还敏锐地观察到,那种推倒一切旧习惯的“新思想”,恰恰与新思想所标榜的批评的、理性的态度相反,“新思想依据于理性,而彼则依据于感性……吾以为今日之主张推倒一切旧习惯者,实因其心意中并未发生新思想之故”(注:杜亚泉:《何谓新思想》,《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
在思想讨论中持理性态度,这也是很多参加辩论者的愿望。早在1919年3月份那场新旧思潮大讨论中,就已存在一个基本的认同,即,对新旧问题进行学理上的讨论,避免感情用事,避免以势力压人。这不但是对旧派的警告,“吾愿守旧者流,勿为感情所趋,自陷而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注:源泉:《警告守旧党》,《每周评论》1919年4月13日。);也是对新派的希望,“今之以传播新思想自任者,其对于观察旧思想,必先有广博精确之见解,决不可以感情过激出之,非然者,终不免为少数偏狭之见,其不能有所贡献于吾社会也有断然矣”(注:鲁逊:《学界新思想之潮流》,《每周评论》1919年4月27日。)。
到1919年末1920年初的讨论时,持中派继续表达对偏激态度的不满。他们肯定新派的爱国心,也指出其言论有失偏激:“今之新思想激进派,目睹旧社会日趋于衰落景况,急思扶掖国人同登福利之域,但以其爱国心殷,改良情挚,故言论褊燥之弊,往往不免。甚者至谓:旧的思想皆应铲除净尽,无复孑遗;古的事物,今日皆无价值;古时伟人,今日皆等草芥。”(注:朱调孙:《研究新旧调和之必要及其方法》,《东方杂志》第17卷第4号。)论者担心这种激昂的心态会招致社会的反感,如一旦失败,情感的大起大落又容易使青年心灰意冷。当然,论者也反对旧派持极端态度。总之,他们认为正因为双方感情用事,缺乏研究事实的精神,才造成了新旧思想的排抵,“加以新派之偏激者,视吾国古来之学术文字,莫非老废死灭,欲一一摧毁之以为快。旧派之顽固者,更视由外输入之学术文化,莫非洪水猛兽,惟不能抵拒之是惧,各执成见,互相诋诽。”(注:管豹:《新旧之冲突与调和》,《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
为了避免感情用事,自目为持中派的朱调孙提出“新派旧派不研究学理则已,否则屏除客气成见然后可”(注:朱调孙:《研究新旧调和之必要及其方法》,《东方杂志》第17卷第4号。)。管豹则殚精竭虑,提出了六条解决新旧冲突的原则:(一)宜平心静气,探求真理。不要预存成见而相互抵排。(二)宜以研究学术为唯一的目的。不要怀有其他目的,而以研究学术为手段。(三)宜人人自居于研究者,不要人人自居于指导者。(四)宜潜心学问,积贮知识,避免道听途说,发直觉的议论或冲动的行动。(五)宜本着真挚诚恳的态度,以真理服人,切忌以强力压人(除凭借特殊势力外,如新派动诋旧派为复辟派,旧派每诬新派为过激党等皆含有强制之意)。(六)宜即事即物。要求满足,逐渐进步,不要笼统攻击,也切莫囫囵吞咽(注:管豹:《新旧之冲突与调和》,《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
正是基于理性的思考,对以新旧为是非,也有许多人表示反对。这里面既有新派人物,也有持中派。当然由于知识结构的不同,这些人的论证角度不同。潘力山根据经验讲到,“譬如作文的时候,不管新的材料,旧的材料,只要合我们的用,我们便用,所谓‘惟其是而已’。那时的理想,惟有一个是而已”(注:潘力山:《新旧调和说与突变潜变说》,《晨报》1919年10月15日。);梦良则从现实出发指出,有许多坏现象既不受新的欢迎,也不受旧的喜爱,所以不能把坏现象都算他是旧的(注:梦良:《“自然调和”与“调和论”》,《晨报》1919年10月19日。)。北京大学陈大齐教授的言论比较有理论深度。他敏锐地觉察到了以新旧为是非与新文化的宗旨存在着冲突,“前人以旧为是,以新为非,我们青年以新为是,以旧为非,趋向虽然不同,根本的误谬却是一样”(注:陈大齐:《新旧和是非》,《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号。)。他认为,新旧是事实判断,而是非为价值判断,二者根本不能混为一谈,对于旧而非的自然竭力打破,新而非的也当大着胆子去攻击,而且是非的标准,需要各种价值科学做出仔细研究,不是一语可以说得尽。
在身份认同上把自己归属于新派的人,也不希望人们把他们目为激进分子。在四川颇有影响的新派人物潘力山就为新派辩白:“殊不知言新的人,还有一个理想,并不是把旧的东西无意识的一概抹杀。世间上也难免有无意识的人,把旧有的东西,一概抹杀的,但不可以概一般讲新的人。”(注:潘力山:《论新旧》,《晨报》1919年10月18日。)另外一位署名三无的人,根据他另外一篇文章《文明进步之原动力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关系》和他的名字来判断,显然属于新文化人士,但他也反对盲目突进:“然必盲目突进,毫不加以思考抉择之功,则歧途正多,恐致流荡忘返,此新旧调和之说,所以恒出诸士大夫之口欤。”(注:三无:《新旧势力之强弱与文化转移期之关系》,《东方杂志》第17卷第7号。)时任《民国日报·副刊》主笔的邵力子在新旧调和问题上持反对态度,但他也强调,新旧两派“即使到了冲突底时候,也须以理性底争辩为主,勉力制裁感情地激战。”(注:力子《〈怎样调和学校里地新旧〉·附志》,《民国日报》1920年5月19日。)陈独秀在《答崇拜王敬轩者》中表明了他对待反对派的三种意见:“立论精到,足以正社论之失者,记者理应虚心受教”;“是非未定者,苟反对者能言之成理,记者虽未敢苟同,亦必遵重讨论学理之自由,虚心受教”;“世界学者业已公同辩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可见原则上陈独秀对思想辩论是主张持理性态度的。既然双方都反对感性、极端,主张理、平和,为什么还出现如此激烈的对峙呢?笔者认为,除了二者在对新旧文化的评价上确实存在着分歧外,对新旧涵义的理解不同,也是使这场争论趋向激烈对峙的原因之一。
三
在新旧之争中,许多人对“新”与“旧”涵义的理解并不一致。陈独秀有一段关于新旧关系的名论:“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注:陈独秀:《答配剑青年》,《新青年》第3卷第1号。)但这个新旧绝无调和余地的结论,却是建立在把旧道德中的一些美德共性化的前提下的,“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不过谓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通世间道德,不认为孔教独有者耳”(注:陈独秀:《答〈新青年〉爱读者》,《新青年》第3卷第5号。)。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他也认识到西洋道德中也有新有旧,提出应该选择西洋的新道德,抛弃它的旧道德。由此可见,陈独秀所讲的“新旧”并不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划分依据的,而是以“旧”特指孔教中的分阶级尊卑的三纲、定孔教为一尊,以及忠孝合一的政治伦理观念,“新”在前期是指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资产阶级政治伦理观念,到后期却是指社会主义政治伦理观念。
新旧在新派人士蒋梦麟那里另有一番含义。蒋梦麟不赞成以时间先后和空间西东来划分新旧,1919年10月蒋梦麟在《新旧与调和》中讲到,“若说从西洋输入的思想是新思想,那西洋的思想也有很多是旧的,若说西洋输入的思想就是新,那希腊的美术人生观罗马的法意建筑在我国可算是很新的。所以新思想不能以时代来定,也不能以西洋输入的来做标准”(注:蒋梦麟:《新旧与调和》,《晨报·副刊》1919年10月13日。)。他还解释,抱新态度的人并没有一味主张推倒一切旧习惯,不过把它来下一番批评,重定一个价值,没有把它们都当柴烧的意思。他非但不全盘否定孔子,而肯定孔子重人道的思想,认为“真科学是孔子、耶稣、佛的科学(按此指尊重人道而言)”(注:蒋梦麟:《改变人生的态度》,《晨报》1919年10月1日。)。他对新旧的划分是以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态度为标准的,“我说新思想和旧思想的不同,是在那个态度上,若那个态度是相那进化方向上走的,抱那个态度的人的思想,是新思想,若那个态度是向旧有文化的安乐窝里走的,抱那个态度的人的思想,是旧思想”(注:蒋梦麟:《何谓新思想》,《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正是从向前还是向后两种态度的角度上立论,他认为新旧不可能调和。
胡适对时人对新思潮的解释也不满意,根据他的设想,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评判的态度,落实到实践就是以这种评判的态度来讨论问题和整理旧学术。他反对盲从旧有的学术、反对调和古今中外,为什么要反对调和呢,“因为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蒋梦麟在与杜亚泉辩论时,还引胡适此话为同调。
景藏在《我之新思想观》中就讲以时间先后看待新旧并不符合实例,他认为区分新旧只看思想是否适合时世的需要而定,“故今日当问旧思想之是否尚可存留,是否已不适用,新思想之是否足以予人知识上充分的愉快,是否适应于时世之要求。换言之,即新思想中之某种思想,若不合于梦鳞君所举之条件,即不得称为新思想,即当排除,若合于此条件,即不能排除。”(注:景藏:《我之新思想观》,《东方杂志》第16卷第12号。)以此划分,当然不适合需要的就没有保留的价值了,因此新旧也绝不可调和。同年,陈嘉蔼在《新潮》上写了《新》一文,也表明“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新,决不同寻常人称为新旧的那个新”(注:陈嘉蔼:《新》,《新潮》第1卷第1号。),新旧的那个新,常受着时间、空间、认识程度的限制。他的结论是,“新就是适应,适应就是新。”
从这些界定和叙述来看,新旧之分既指的是前进与不前进的态度的新旧人士之分,也指的是适应与不适应新旧思想之分,但无论是指人还是指思想,根据他们的划分标准,稍有头脑的人也不会强求这样的新与这样的旧互相调和,更不必说身为《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和曾为清末民初思想学术界风云人物的章士钊了。更令人吃惊的是,前面这些人划分新旧的标准,与章士钊、杜亚泉对学说扬弃与否的标准倒有几分相似,比如章士钊所讲的“各种学说愚尝谓思想只求其适用,无所谓新”(注:章士钊:《新思潮与调和》,《东方杂志》第17卷第2号。),“思潮之切于时事者,为正当之思潮,不切于时事之需要者,为病的思潮”(注:章士钊:《新思潮与调和》,《东方杂志》第17卷第2号。);杜亚泉所讲的“新思想之赞成与反对,当视其内容如何而后定”(注:杜亚泉:《何谓新思想》,《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那为什么前者反对调和,而后者却宣扬调和呢?我们来看一下五四时期存在的另外一种新旧之分和章、杜二人对新旧的界定就会明白了。
首先拉开五四新旧之争帷幕的人是汪叔潜,在他那里,新旧之分既是空间之分也是时间之分。1915年9月,汪叔潜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写了《新旧问题》一文,主张维新者与守旧者就各自的信仰展开思想论战。为了使新旧论战的旗帜更加明显,他设定了新旧内涵,“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如是”。并明确表明了自己对新旧关系的认识,即,“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注:汪叔潜:《新旧问题》,《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汪叔潜把东与西这本来属于空间的问题,转换成了新与旧的时间问题,在进化论盛行的年代,中国文化一旦与旧等同,它自然处于一个必须被“天演”掉的位置上。当时,在这个含义上运用新旧一词的人决非汪叔潜一人,“盖今日揭橥新思想者,大率主张推倒一切旧习惯,而附之以改造思想,改造生活之门面语,其对于新思想之解答,诚不过如是”(注:杜亚泉:《何谓新思想》,《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对新旧含义的理解比较普遍,本来不赞同使用新旧之词的章士钊才勉强使用该词表达他对文化发展的看法。章士钊几次讲到,“思想者,亦求其与时与事适相印合而已。无所谓新旧也”(注:章士钊:《新思潮与调和》,《东方杂志》第17卷第2号。)。但因为他是针对时空角度上的新旧断裂观而立论的,因此他对新旧的含义也是从这一角度来使用的。如他在《新思潮与调和》中讲,调和新旧首先要把某种外来主义研究彻底,然后详细调查我国的社会状况,以确认如果实行此主义,与中国社会状况不适应的地方,何者需要排除,何者应该与旧有思想融合,这就是以东西之分为新旧之分的。当讲新旧文学的关系时,又是以时间先后为区分的。新是指正在创造的文学,而旧是指已有的文学。而且他对新旧的探讨又是在非常具体的层面上进行的,如新旧词语、技巧、境界的关系等。
在杜亚泉那里,新与旧是思想之分。他指出,新旧思想界定从戊戌到1919年有一个动态的历史变化过程,具体到当时而言,“新思想”应为“主张创造未来文明者”,而“旧思想”为“主张维持现代文明者”,具体到中国则以“主张刷新中国固有文明,贡献于世界者为新,而以主张革除中国固有文明,同化于西洋者为旧”(注:杜亚泉:《新旧思想之折衷》,《东方杂志》第16卷第9号。)。他的新旧思想的界定与新派人士恰好颠倒。而且在接下来解释新旧调和时,新旧的所指却又变成了新旧学说,如,他认为和平的世界主义是新,战争主义是旧,最理想的选择应是根据当时实际形势的需要调和世界主义与战争主义。在另外两篇文章中,他批判以“对于旧习惯,不论是非善恶,都主张推翻”(注:杜亚泉:《〈何谓新思想〉·附识》,《东方杂志》第17卷第2号。)为新思想的流行看法,为新思想另下界定:“新思想者,依吾人之理想,于事物或观念间,附以从来未有之关系,即旧思想而言,谓之新思想。”(注:杜亚泉:《〈何谓新思想〉·附识》,《东方杂志》第17卷第2号。)这里的新思想是指对事物关系的新认识,这不但与他所批判的相异,而且与他自己前面对新思想的界定也不一致了。
总结来看,新旧在当时应当有以下几个含义:适应与不适应、前进或是后退的态度、时间上的先后或空间上的西东之分。在论辩时,双方往往不是在同一概念下使用新旧,而且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语境中也常常变换新旧的涵义,因此除了二者在对新旧文化的评价上确实存在着分歧外,对新旧涵义的理解和使用不同也是使这场争论趋向激烈对峙的原因之一。时任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陈大齐的话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或许有人说:现在所谓新旧并非时间上的新旧,是适应环境或重估价值的意义。这种态度无以名之,姑名之为新罢了,上面的解释未免曲解了新旧。如此说法,自然又是另一问题。……新旧的普通意义确是指事实上的性质说的。我们即使勉强用作别义,别人看了,总不免仍旧牵扯到普通意义上去。而且事实上牵连到普通意义上去,或竟当作普通意义用,因以判别是非的,实例非常地多。所以我希望当别的意义用的,不如另选适当的字来用,不要再用新旧字样,以免引起许多误会!”(注:陈大齐:《新旧和是非》,《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