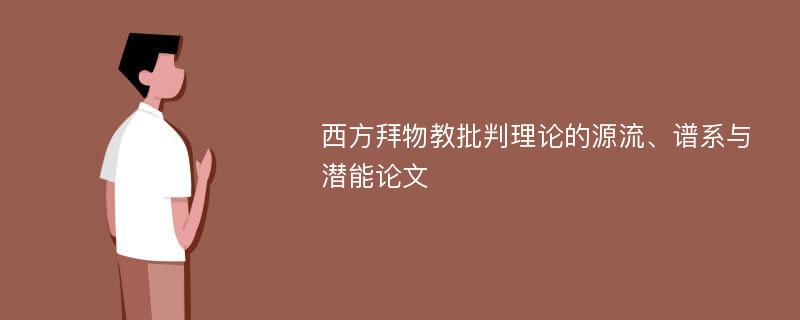
西方拜物教批判理论的源流、谱系与潜能
吴 茜
内容提要 | 在商品化进程继续推进的虚拟经济时代,拜物教现象仍然是一个尚待深度耕犁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关涉到如何摆脱异化与物化进而恢复人的生存本真意义的重要理论问题。本文基于拜物教研究的历史过程,分别从宗教人类学意义上的“拜物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拜物教”、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意义上的“拜物教”,以及精神分析学视域下的“拜物教”四个维度,探索“拜物教”一词在不同的学术领域所呈现的异质性的话语叙事和知识谱系,进而揭示马克思及其之后的西方拜物教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统治机制所进行的深刻揭露和批判。研究发现,这些理论尽管在学术渊源、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上与马克思主义路径迥异,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拜物教理论向21世纪演进发展提供了新的问题视域与解释框架。
关 键 词 | 拜物教 虚假幻象 叙事分歧 政治潜能
“拜物教”(Fetishism)一词有着复杂的理论内涵和历史渊源,它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思潮流派和发展阶段呈现出异质性的话语叙事和知识谱系。具体体现为宗教人类学意义上的“拜物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拜物教”、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意义上的“拜物教”,以及精神分析学视域的“拜物教”等不同研究路径。① Roy Ellen, Fetishism, Man, New Series, Vol.23, No.2(June 1988), pp.213-235. 从原始宗教赋予实物以人的精神幻想成分,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社会关系在“物”与“物”的关系上的隐遁、颠倒,再到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下人的主体性遭遇的纯粹哲学批判向度,色彩斑驳的西方拜物教批判理论共同勾勒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真实生存的“伪本体论”图景,充分显示出反抗资本主义从肉体奴役到精神殖民统治的激进政治潜能。
一、宗教人类学意义上的“拜物教”
拜物教是最原始的宗教信仰形式之一。在远古时代,原始部族由于生产实践的局限性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匮乏,对于自然界的许多事物和现象,如风雨雷电、水火林木、丰歉祸福,无法解释其产生的原因和运动规律,所以往往从宗教世界的幻想中去寻求答案。在神灵观念尚未产生以前,一些原始部族把某些特定的物体,例如人体、物体、神像和护身符等,当作有灵性的和具有神秘的超自然力量的物而加以崇拜,借以辟邪求福,从而产生了拜物教。事实上,这些被崇拜的物,并没有支配人类命运的神秘力量,而只是人脑主观虚构想象的产物。原始拜物教现象在古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中曾广泛流行,至今在某些尚未完全脱离原始状态的居民群落中依然存在,在文明社会中亦还存在对护身符和“圣物”、“圣人”遗骨的崇拜现象。
15 世纪下半叶,葡萄牙人航海到达非洲西部时,用拜物教“feitio”一词来指称当地原始部族所相信并崇拜的具有魔力的符咒或护符。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夏尔勒•德布罗斯(Charles De Brosses)于1760 年在《论物神崇拜》中首次将“拜物教”一词用于比较宗教学。他将非洲原始族群所崇拜的石头、树木、山川河流等称为“物神”,把原始族群对这些“物神”的崇拜本身称为“物恋”,并进一步将含混的“物神”和“物恋”概念统一为“拜物教”,把它提升为某种宗教理论。① 李瑞德:《拜物教研究的学术史清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2 月7 日。 美国人类学家威廉•皮埃兹(William Pietz)在《物恋问题》一文中谈到,在16、17世纪,“拜物教”主要用来描述非洲西海岸多文化交叉地区的一种宗教崇拜,尤指对无生命的“物”或人工制品的崇拜。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把拜物教视作宗教或神学发展三阶段的第一个阶段:从拜物教、多神教到一神教,即将非人的物体赋以人的精神特性。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 Tylor)认为,拜物教是万物有灵论的一种退化形态,专指信仰并崇拜体现或依附于某种物体或通过某种物体而发生影响的精灵。② Roy Ellen, Fetishism, Man, New Series, Vol.23, No.2(June 1988), pp.213-235.
5.5 药剂防治:在发病初期,使用77%可杀得可湿性粉剂500倍,或新植霉素400倍,或72%农用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00倍,或25%络氨铜水剂300倍液,也可用1∶1∶200的波尔多液喷雾,隔7~10天1次,连喷2~3次,防治效果达80%~90%。喷药前先将少量病叶、枝、果摘除,再喷药,效果更好。
马克思最初也是在宗教学意义上来理解“拜物教”概念的。在1842 年4—5 月,马克思曾研究了有关宗教史和艺术史方面的著作,并且写下了5 本摘录笔记,史称“波恩笔记”,其中便包括对德布罗斯的《论物神崇拜》中有关“拜物教”概念的详细摘录。马克思对原始拜物教持批判态度,他认为,“拜物教远不能使人超脱感性欲望,相反,它倒是‘感性欲望的宗教’。欲望引起的幻想诱惑了偶像崇拜者,使他以为‘无生命的东西’为了满足偶像崇拜者的贪欲可以改变自己的自然特性。因此当偶像不再是偶像崇拜者最忠顺的奴仆时,偶像崇拜者的粗野欲望就会砸碎偶像。”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12 页。 在《论犹太人的问题》的结尾部分,马克思研究了世俗的犹太教,称其为“金钱拜物教”。人们崇拜人手的造物即金钱这一现象引发了他的关注和思考。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拜物教”批判
德波认为,商品使用价值走向没落,交换价值再次抽象上升到视觉影像符号层面。他指出,影像景观制造出人们的主体性的欲望、动机与需要,从而消除人们的真实欲望,实际上是对人们的深层精神世界殖民和意识形态控制。因此,“景观是(资本逻辑)意识形态的顶点,它充分显示和证明了全部意识形态的本质:即真实生活的否定、奴役和贫困。”德波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策略,主张通过政治与艺术的手段,在日常生活领域的景观废墟之上建构反对异化的本真的生活情境。
疏血通注射液联合瑞舒伐他汀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后心绞痛的临床观察 …………………………………… 张彩霞等(2):216
马克思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显著特征时认为,劳动产品一旦其成为商品,就立刻具有拜物教的性质——变成一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即商品一旦被创造出来并进行交换,就会被赋予某种形而上学的神秘性质,独立于人并反过来控制人,似乎拥有决定商品生产者命运的神秘力量。马克思把商品世界的这种神秘性比喻为拜物教,称之为商品拜物教。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拜物教现象产生的深刻根源——人们在商品交换中完成对商品价值的社会属性的抽象。他指出,“人和人在他们劳动中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426-427 页。 “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环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9-90 页。 由此可见,商品的神秘性特质并非来自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来自商品的交换价值,来自人们在商品交换中完成的对商品价值的社会属性的抽象。
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更体现出商品的价值以及劳动力的价值被抽象化和符号化。尤其是,由于这个价值符号的作用,劳动力退出了交换过程,劳动力作为价值源泉的作用被遮盖、被否定或被拒认。马克思指出:“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100-101 页。
6.作者可根据自己意愿,自由选择《南方能源建设》、《广东电力》、《浙江电力》、《内蒙古电力技术》4种期刊之一,但不能重复投稿。
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真正来源被掩盖的过程就是资本的拜物教性质逐步加深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化加深并最终完成的过程。他指出,在“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完成了,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的世界。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937-940 页。
他心里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蹑足潜踪地向前查找。空气中的血腥味越来越浓,终于,在几块巨石旁,他发现了一大片鲜血。
第四,“奇观化拜物教”。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揭露了资本主义奇观化生产的机制和奥妙。他所研究的拜物教对象不是指实际在场的物本身,而是指人们投射到物上面的可以感知而又超感觉的幻影,即赋予物一种形而上学的、宗教性的价值和意义,以此来建构都市人的精神欲望空间,从而使人沦为欲望机器的视觉人质。本雅明分析并指出,商品的幻化不仅仅包括从“内容”上对主体的需要或欲望进行商业逻辑意识形态编码,还包括从“形式”上将商品的符号价值奇观化。他指出,巴黎的拱廊街市本身就是一种奇观化装置或奇观化生产机器——商店橱窗引诱人们驻足凝视,为消费主体建构起观看场景和视觉关系,从而使主体堕入拜物教幻象的摆布和控制中。本雅明对拱廊街和闲逛者的描述揭示了“对于一种开始与拱廊街市和奢侈商品以及昂贵的小商品的窗口陈列相关的景观消费主体性的建构。换句话说,它暗示了一种观看‘美丽而昂贵的东西’的鲜明的新方式”。② [德]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 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6 页。 商品的奇观化实现了对人们视觉的全面接管和彻底殖民控制,主体的意识通过让意义聚拢在符号化的视觉奇观中,沦为异化的主体。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意义上的“拜物教”
回顾分析120例高龄转子间骨折患者病历资料,均接受PFNA术治疗,依据其术前是否接受氨甲环酸药物治疗分2组,每组各60例。对照组:男性22例,女性18例,年龄60-76岁,平均为(70.5±1.1)岁,病程时间(3.51±1.11)d,致伤原因:12例交通伤,484例跌倒摔伤,Evans分型:Ⅰ型8例,Ⅱ型15例,Ⅲ型19例,Ⅳ型18例;研究组:男性23例,女性17例,年龄60-77岁,平均为(70.8±1.2)岁,病程时间(3.52±1.10)d,致伤原因:7例交通伤,33跌倒摔伤,Evans分型:Ⅰ型7例,Ⅱ型16例,Ⅲ型18例,Ⅳ19例。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P>0.05。
第一,“假象拜物教”。格奥尔格•卢卡奇(Ceorg Lukacs)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以“物化”为中心范畴,对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进行研究。卢卡奇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结构之谜”思考后,指出“商品结构的本质已被多次强调指出过。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144 页。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本质。由于卢卡奇受到韦伯“合理化过程”思想的影响,他从总体性的、同一的主客体辩证法出发,认为物化不仅是生产关系的物化,更是生产过程的物化——即人们创造了大机器生产系统,并使自身成为依附于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或齿轮,人们由此产生对“物的自动的合规律的过程”的崇拜,把合理化了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作自然界之外的人造“第二自然”,完全屈从于生产过程的合理化控制,从而导致主客体地位发生了完全的颠倒和异化。③ 张双利:《资本主义宗教与历史唯物主义——论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批判思想在20 世纪的复兴》,《世界哲学》2012 年第6 期。 卢卡奇不得不陷入工人阶级丧失阶级意识的悲观论调——工人阶级根本无力把握那个真正的总体,从而对自己的历史作用、地位陷入无意识。
事实上,卢卡奇未能深入把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矛盾运动方法论,而是被黑格尔总体性的同一的主客体辩证法吸引到另一条脱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运动、纯粹哲学思辨的道路上去了。卢卡奇开启了透过“现象”看其被遮蔽之“本质”的纵向意识形态批判方式,法兰克福学派继续沿着卢卡奇的思路展开了对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批判,并逐渐把战线从资本主义经济领域转移到对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哲学反思、批判。
第二,“符号拜物教”(或称“能指拜物教”)。如果说卢卡奇和其他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还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围绕着“物”来开展拜物教批判的话,那么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符号拜物教则是一个转折点。在《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等著作中,他对“物”进行了符号学意义的全新解读。
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已不再是对实体物品的崇拜,而是对“物”所承载的符号意义的迷恋。这种符号编码和差异性系列不断制造出消费者的欲望、动机和需求,并将消费者编织进不同的系统阶层之中。④ 张一兵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后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5 页。 符码实际上承载的是社会关系网络——“物的符号价值的编码功能不只是对物的意义的编码,也是对社会总体性的编码,是对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生产的关系、人与消费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编码”
⑤ [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67 页。 ——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身份、等级地位和权势象征。对符号意义这一最高“物神”的迷恋使人们心甘情愿地认同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和意识形态运作机制。
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符号价值”否定了马克思关于物的使用价值、甚至交换价值的观点。他认为,在消费主义的场域中,商品的符号价值赋予商品超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的意义内容,虚幻的“品位”、“情趣”、“幸福”和“身份”占据了主体的心灵,主体的欲望被凝定在强劲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从而实现了对主体的“催眠式”控制。
“Fetishism”除了“拜物教”的意思外,还可以翻译成“恋物癖”。与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层面的“物”去揭示拜物教的秘密不同,精神分析学的恋物癖话语“关注的是恋物主体何以会痴迷于拜物/恋物式的消费,主体在此种消费中是如何完成‘物’的升华和欲望的转移的,主体对‘物’及其意义的认同是如何实现的。这同样是一种症状阅读。”① 吴琼:《拜物教/恋物癖:一个概念的谱系学考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 年第3 期。 这种分析方法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他运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关于梦的解释以及雅克 •拉康(Jaques Lacan)的精神幻想公式展开对商品拜物教的精神维度的分析,开拓了拜物教研究的又一新维度。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拜物教”概念从原始宗教中解放出来,将其引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成为对资本主义“抽象统治真实”、“颠倒的社会现实”的强有力的批判工具和方法,开启了19 世纪拜物教批判的新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用了一节的篇幅来分析“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即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宏大画卷展开,“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三大拜物教现象浮出水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隐藏的人奴役人、物支配人的“神秘性”被逐一解蔽,其本质被无情地披露在世人的面前。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拜物教现象所导致的人的全面异化的后果:“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凭借死劳动对活劳动进行剥削和统治,用来控制、支配和奴役社会上的大多数劳动者。”⑤ 李怀涛:《物化理论:卢卡奇对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解读》,《广西社会科学》2010 年第2 期。 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克服自己在商品拜物教中的“异化”状态,恢复革命主体阶级意识,以生产逻辑突破资本逻辑结构才能获得最终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设想,只有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能消除商品拜物教,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物质生产活动处于人类的自觉调控之下,而不再作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必然性起作用。物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取决于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各种社会关系摆脱物的神秘外衣而呈现出简单明了的样态,拜物教因而才会失去其存在的现实基础。
与鲍德里亚等人不同的是,在本雅明看来,拜物教不仅仅是某种“虚假意识”,也可能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本身,即一种表象通过自身的异化、同时实现异化之扬弃的过程。这种拜物教理论否定了马克思拜物教理论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物与物的关系”的颠倒,更倾向于将商品拜物教的“物”本身看作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直接呈现。
总之,西方左翼学者认为,物、商品或景观作为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结晶化和组织化,是它们对人的社会认知和形象确认的操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历史现实和欲望之真实的遮蔽;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是“被建构的主体”,其精神欲望世界已被资本逻辑(“大他者”)的符号价值意义和影像幻觉殖民入侵,每个人坐在资本主义虚幻假象的精神囚笼中无法觉醒和反抗。西方左翼学者拜物教批判理论拓展了马克思之后拜物教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但是,由于西方左翼学者拜物教批判理论脱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历史进程,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阶级政治的回避等缺陷,导致其对于怎样摆脱资本主义母体对人的精神意识编码和操纵控制,进而恢复人自身的本真存在、获得自由解放等,陷入悲观和迷惘中。
四、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拜物教”批判
第三,“景观拜物教”。居伊• 德波(Guy Debord)认为,20 世纪60 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的丰裕和电子影像技术进入到日常生活中,西方社会进入到了以现代电子媒介影像为先导的景观社会,即“景观无限堆积的社会”。① Guy Debord,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Zone Books,1994, p.12. 原本被商品物化的社会关系再一次被颠倒化为以视觉影像为中介的社会,普通消费者跌落进景观真实“虚构”的更深的“颠倒再颠倒”的异化世界和意识形态中,无法觉醒也无从反抗。
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关于“物对人的统治”的“颠倒的、异化的世界”,已经触及资本化社会中个人将资本统治加以内在化这一命题。在他之后,西方左翼学者逐渐从对外在的“物”的神秘性“祛魅”,转而关注人的内在意识或者说主体性建构问题。他们敏锐地观察到,在消费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意识形态的外观和运作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假借公众需求的名义,即视幸福、自由、享受为公众的基本需要和基本权利来将种种惰性的、催眠式的布尔乔亚意识形态惯例铭写到商品之中,使商品的躯体成为意义和价值的殖民地,成为主体欲望和需要的锚定点。”① 吴琼:《拜物教/恋物癖:一个概念的谱系学考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 年3 期。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被隐匿和嵌入市场经济运作机制和实践中,内化为在人们日常生活意识中起作用,并由一种外在性的思想漂浮物转化成社会自身的无意识牵引机制,导致人们深深屈从资本主义商业化逻辑中而失去自我批判能力。只有戳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隐秘、狡诈的运作机制,才能使人摆脱生存的异化状态。最具有代表性的流派如下。
在旱灾监测技术方面,引进了区域蒸散量遥感监测估算、干旱遥感监测与预报、数字化区域旱情监测系统等旱情监测技术和设备;利用3S技术,开发了遥感数据处理与反演分析软件;成果在2006年重庆、2007年河南及2008年海河流域的干旱监测中进行成功应用;提高了我国旱情的遥感监测与预报能力,为减轻我国大范围旱灾损失提供了技术支撑。
与马克思的研究理路不同,齐泽克运用弗洛伊德关于梦的无意识结构和运行机制来分析人对物的迷恋机制。齐泽克谈道:“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二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同宗同源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关键在于避免对假定隐藏在形式后面的‘内容’的完全崇拜性迷恋:通过分析要揭穿的‘秘密’不是被形式(商品的形式、梦的形式)隐藏起来的内容,而是这种形式自身的‘秘密’。”② Slavoj Zizek,The Sublime Objiec of Ideology,Verso,1989,p.15. 齐泽克提出商品交换形式的“无意识”观点,即支配人们日常交换行为的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由商品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交换价值,而是商品交换中蕴含的无意识形式,这种无意识已经内化于人们的日常交换行为中而不能自觉。
齐泽克认为,商品拜物教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对商品交换形式神秘性的崇拜,拜物教的本质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为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这么简单的指认,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结构性错认关系——“货币不是由经验的、物质的材料制成的,而是由崇高的物质制成的,是由其他‘不可毁灭和不可改变的’、能够超越物理客体腐坏的形式制成的。这种‘躯体之内的躯体’的非物质的肉体性,为我们提供了崇高客体的精确定义”③ 孔明安等著:《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研究——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年,第 675 页。 ④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第 25 页。 ——人们疯狂追求金钱,不是崇拜其物质客体,而是无意识地指向在货币中存在的那种非物质实体性的、抽象的、象征性的“凌驾”地位。⑤ ⑤ Slavoj Zizek,Our Daily Fantasies and Fetishes,Journal of Advanced Composition Quarterly,Vol.21,No.3(Summer 2001), pp.647-653. 齐泽克借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颠倒的“主奴关系”来隐喻人们把货币错认为“天然的君主”,从而产生了对商品交换形式的顶礼膜拜。
在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将商品交换形式的“无意识”主宰着人们的行为归因于“先验主体”的观点的启发下,齐泽克认为,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先验主体”指的是主体的某种先天的时间空间结构和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范畴,在主体形成其意识之前,商品交换形式的抽象性或神秘性就已经存在了。
4)将得到的图像(图4(d))与原鸡蛋轮廓二值图像(图3(c))进行“异或”运算,提取出鸡蛋的蛋黄特征,此时发现图像中除了蛋黄区域外还有鸡蛋边界的存在,如图4(e)所示。
其次,齐泽克进一步从精神分析视野将虚拟资本与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中的主体性遭遇关联起来思考,他运用拉康精神幻想公式得出了从信用到赌博欺诈制度内在机制的精神阐释。“现实社会中不是主体决定客体,也不是客体决定主体,在主体与客体互动关系之间必须加入一个无意识维度,也即拉康的‘实在界’或‘对象a’的世界。”①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第23 页。 如同马克思所指的拜物对象不是实际在场的物本身,而是人们投射到物上面的可以感知而又超感觉的幻影性质一样,“对象a”是主体的幻想对象或欲望对象,但本质上却是伪装欲望对象的幻象场所,即是一个虚无或匮乏。主体表面上看似清醒、理智,但实际上却处于某种无意识之中并受制于无意识。齐泽克认为,现代信用本身是建立在一种“虚无”和“匮乏”的基础之上的,无论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或期货市场,虚无(“对象a”)替代物就是股票、债券、期货衍生品等,它们既是一张废纸,同时又具有巨大的金融价值。一旦虚拟资本进入到实际经济运行之中,人们很快就会忘记虚拟资本“虚假幻象”的这一特征,并陷入到疯狂的金融投机赌博游戏之中去。② 孔明安:《齐泽克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兼论精神分析视野下的虚拟资本及其功能》,《哲学动态》2014 年第11 期。 更为严重的是,尽管人们明知华尔街的金融信用体系是赌博欺诈制度,却不自觉地充当“意识形态幻象”的俘虏,陷入明知故犯的犬儒主义拜物教。但是,针对人们享受资本主义商业文化虚假幻象的病态“症候”,齐泽克也找不到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案。
1) 调控中心防误功能:将调控D5000系统对变电设备的遥控操作纳入防误管理范畴,远方操作时,需由D5000系统首先向网络五防服务器发送操作请求指令,五防服务器根据请求指令,结合已抽取的设备运行方式判断五防操作正确性,当五防校验不会发生误操作时,网络五防系统给监控系统发送允许操作指令,监控系统接到指令后操作实际设备,为运维班模式下各变电站提供进一步防误安全保障。
结语:话语体系的差异性与政治潜能的近似性
在马克思隐幽的批判路线中,物转换为商品的过程是物以及物的生产的社会性质和历史真相被“遮蔽”,劳动价值作为被压抑的历史真实被驱逐到黑暗隐秘的角落的过程。只有破除资本主义的三大拜物教“迷信”,工人阶级才能摆脱异化、获得真正的自由解放。马克思之后,许多西方左翼学者把拜物教问题作为构建自己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继续探索资本主义“抽象统治真实”、“颠倒的、虚假的现实”的问题。他们深刻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生存实在只能是一种“伪本体论”——主体生活在商品、广告、景观、奇观制造的幻觉的社会中,是由“伪事件、伪历史、伪文化”构成的世界,它“不是产自一种变化的、矛盾的、真实经历的事件、文化、思想,而是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体技术操作的赝象”。③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34-135 页。
以齐泽克为例,尽管他的拜物教批判思想基本上是拉康式的学术理路,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结构性危机的精神分析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式,但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揭露和剖析吸引了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并激发了人们进一步曝露更大的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热情。“这种曝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受压迫的无产者的觉醒,同资本贪婪的权力和欲望做斗争,将一个真正公平而和谐的世界带到这个世界上。”④ Peter McLaren,Slavoj Zizeke’s Naked Politics:Option for the Impossible,A Seondary Elaboration,Journal of Advanced Composition Quarterly,Vol.21,No.3(Summer 2001),pp.613-647. 在这种理论号召之下,当代激进左翼思想家巴迪欧、齐泽克、朗西埃、伊格尔顿、奈格里等人都提出“生命政治哲学”,力图摆脱资本主义母体中资本化和治理化的生命生产,重提“新共产主义”命题。⑤ Aijaz Ahmad,Three “Return” to Marx:Derrida,Zizek,Badiou,Social Scientist,Vol.40,No.7/8(July-August 2012),pp.43-59.
因此,尽管西方拜物教批判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批判理论之间存在着理论渊源和话语体系的较大差异,但它们在旨趣上都具有反抗和批判资本主义对人从肉体奴役到精神操纵的激进政治潜能。可以说,西方拜物教批判理论在继续马克思的谱系,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左翼话语权存在。在现在几乎整个地球都被卷入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商品形态和资本逻辑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更有利于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其次,西方拜物教批判理论的理论渊源和研究范式与马克思主义路径迥异,它们深受西方学术史上康德、黑格尔、韦伯、弗洛伊德、拉康、福柯等人影响,有些流派甚至否定和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畴、观点,例如劳动价值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些流派通过梳理西方学术史而精心锻造了一套又一套的概念工具创新,这些新的学术术语和观念体系为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拜物教理论向21 世纪演进发展提供了更加宽阔的研究视野和新的问题视域。在这些流派深奥难懂的哲学思想中,负载着大量关于急剧变化着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信息,他们的研究成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批判理论的时代化。总的看来,马思主义研究的多样性对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带来的积极性远大于其消极性。
另一方面,西方拜物教批判理论更侧重于思考探讨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即人自身内部身心之间的对立、人的单向度的日益加剧的命题。它们对现实社会的拜物教批判不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一极,甚至是弗洛伊德拉康式的精神分析学批判,又回到黑格尔式“从概念到概念的运动”的纯粹哲学批判路径,从而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的物质颠覆力量的理解和把握。我们在与当代西方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对话和交流中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时,应建立在对其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辩证分析基础上,既要重视它们批判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激进政治潜能,又要正确地剖析和避免这些拜物教理论流派的理论偏颇和局限性。
作者简介 | 吴茜(1975—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厦门 361005)
(责编:轩传树)
标签:拜物教论文; 虚假幻象论文; 叙事分歧论文; 政治潜能论文;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