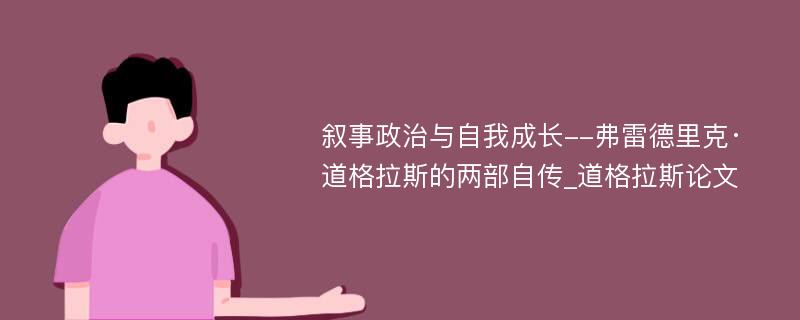
叙述的政治与自我的成长——弗雷德里克#183;道格拉斯的两部自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格拉斯论文,自传论文,两部论文,里克论文,弗雷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17—1895 )是美国黑人解放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坎坷,在南方的马里兰州做了20年黑奴,1838年逃往北方,成为废奴运动的骨干,到各地宣传废奴运动;他还写过书,当过编辑,担任过政府官员,也曾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官。他对19世纪美国黑人文学作出了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三部自传上,即1845年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奴隶的叙述,由他本人撰写》(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an American Slave,Written by Himself),1855 年的《我的奴隶生涯和我的自由》(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以及1881年出版(后于1892 年增订)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时代》(Life and Times ofFrederick Douglass)。这三部自传不但奠定了道格拉斯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奠定了他在美国历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他的每一部自传出版后都引起轰动,大大推动了美国乃至世界性的废奴运动及反种族歧视运动。道格拉斯在书中不但猛烈抨击美国南方的黑奴制度,还把美国的社会制度描绘为邪恶的,认为整个国家实体都已腐烂。(注:正因如此,道格拉斯遭到同时代人的辱骂,如有人骂他是“巧舌如簧的流氓”(glib-tongued
scoundrel)。对道格拉斯的指控和辱骂主要集中在1845至1847年他在英国避祸和演讲期间,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参见The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s,vol.1,"Introduction to Series One",liii-lix,(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史学界和文学界曾一度兴起研究道格拉斯1845年自传的热潮,(注:正如小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在《从惠特利到道格拉斯:替代的政治》(Wheatley to Douglass:ThePolitics of Displacement)中指出的那样,从20世纪60 年代末直到70年代末,对道格拉斯自传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历史学家,以1979 年斯泰普托(Robert Stepto)和费什(Dexter Fisher)的《美国非裔文学:教学的重建》为标志,文学理论家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拉开了重新解读道格拉斯自传的序幕。参见Frederick Douglass: New Literaryand Historical Essays,ed.E.J.Sundquist,New York: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0,p.48。)但到了80年代,有些学者开始对道格拉斯的自传提出质疑。如小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在《从惠特利到道格拉斯:替代的政治》一文中指出,以前对道格拉斯自传的解读特别是历史学家的解读大多从不怀疑其叙述的真实性,更没有注意到道格拉斯在不同的自传中对同一事件或人物的看法往往是不同的,对其父母的描述前后也差别很大。麦克道尔(Deborah Mcdowell)也通过对道格拉斯封圣过程的分析,对其封圣过程的实质及性别在当代文学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疑问。(注:Deborah Mcdowell,"In the
FirstPlace: Making
Frederick Douglass
and
the Afro-AmericanTradition", Critical Essays on Frederick Douglass,ed.WilliamAndrews,Boston:G.K.Hall,1991.)就文本本身而言,当前对道格拉斯三部自传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道格拉斯自传中的叙述是否可信?2.如果可信,如何解释三部自传中存在的前后矛盾现象?对此,西方的批评家见仁见智。 本文拟从叙事学的角度入手, 通过对道格拉斯1845和1855年自传的对比研究来解构道格拉斯的叙述策略,并揭示其叙述的政治以及自我在不同文本中的改变,从而从一个侧面证明自传文本中的叙述者不但与真实作者不同,其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的成长变化中。通过此番研究,本文希望能够引起当前批评界的注意,改变传统批评中不重视区分自传中的叙述者与真实作者和忽略叙述者自身变化的批评倾向。
一
道格拉斯的第一部自传《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奴隶的叙述,由他本人撰写》于1845年问世时,他逃离南方已有七年。自1841年起道格拉斯就作为废奴运动的先锋开始了成功的演讲生涯,他的演讲在深受欢迎的同时也招来了怀疑。因为尽管他在演讲时常以背上的累累伤痕来打动听众,以唤起他们对黑奴的同情和对黑奴制度的憎恶,但他一直拒绝透露有关他在南方生活的具体情况,如出生地点、主人的名字、家庭成员以及自己如何成功地逃脱等等,而且在那些北方白人看来,道格拉斯出色的演讲水平远非一个没受过教育的黑奴所能企及,因而他们猜测道格拉斯是受雇于废奴主义领袖的职业演说家,而并非逃自南方的黑奴。正是为了消除这些怀疑和敌意,道格拉斯才决定尽可能详细地写出自己的经历,进一步控诉吃人的黑奴制度,同时也是对那些怀疑和敌对者的有力反击。而他此举的代价则是同年8 月他不得不出逃英伦三岛,以躲避可能被抓回南方的命运。(注:关于1845年自传的写作背景和原因, 道格拉斯在1855年自传中作了详细叙述。参见FrederickDouglass:Autobiographies,New York:Literary Classics
of
theUnited States Inc.,1994,pp.367—368.)此书一出版即在北方引起轰动,4个月内卖出了5千册,后多次再版,而且在海外也极为畅销,在当时堪称奇迹。10年之后,道格拉斯又出版了第二本自传《我的奴隶生涯和我的自由》,再次引起轰动,原因并不是它比1845自传厚了三倍,而是它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道格拉斯的新世界;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叙事策略也明显不同。可以说,正是通过对叙事时间、空间和视角以及故事内容增减的成功操控,道格拉斯成功地达到了他的不同的政治目的。这种通过叙事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或曰将叙述当作一种政治手段的行为,笔者称之为叙述的政治。
二
就内容而言,与第二本自传相比,1845年自传明显缺少许多东西,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幸福童年、慈祥的母爱以及亲密无间的家庭生活的描绘:
我出生在马里兰州塔波特县的特卡荷依,那地方离希尔斯巴勒不远,距伊斯顿约十二英里。我不知道自己准确的年龄,因为我没有见到任何可靠的记载。绝大多数的奴隶都像马儿一样,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年龄……
我母亲名叫哈里埃特·巴莱,她是伊萨克和伯西·巴莱的女儿,他们都是黑人,肤色很深。……
我的父亲是一个白人。每逢人家谈到我的出身时都这么说,大家都悄悄地说我的主人就是我的父亲,不过这究竟是否事实,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一生中除了四五次以外,就再也没见过我的母亲,所以对她也只有这一点点的了解;每一次见面都非常仓促,而且又在夜里。她雇给了离我们家约十二英里的斯蒂华先生,她只能晚上来看我,一路都徒步走来,而且是在干了一整天活儿之后……(第15—16页)(注:本文所引道格拉斯1845年自传的页码均据Frederick Douglass:Autobiographies(New York: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1994)一书,引文均由笔者译出。)
“我”由此开始了1845年的自述——对黑暗奴隶制度的控诉:连知道自己生日和接受教育的权利都没有,也享受不到母爱和天伦之乐,童年的“我”完全被当作“另类”。令人吃惊的是,到了1855年自传中,“我”满怀深情地记述了几乎无异于白人儿童的颇为幸福的童年生活,这从1855年自传目录中前三章的内容揭示就可看出:
第一章 童年
出生地——地区的特点——特卡荷依——地名源起——乔普坦克河——出生时间——宗谱——计算时间的方式——外祖父母的姓名——他们的地位——外祖母尤其受尊敬——生逢好运——甜甘薯——迷信——木屋——她的吸引力——孩子分离——我的阿姨们——她们的名字——初知身为奴隶之身——老主人——童年的欢乐和哀伤——身为奴隶和奴隶主之子的相对快乐
第二章 远离第一个家
“老主人”的名字好恐怖——劳埃上校的种植园——威尔河——它名字的由来——劳埃家族的地位——家乡的吸引力——接受任务——从特卡荷依到威尔河的行程——到达老主人家之所见——外祖母过世——兄弟姐妹们奇怪的聚会——拒绝接受舒适——甜蜜之觉
第三章 父亲之谜
我的父亲是个谜——我的母亲——她的外表——奴隶制阻碍了母子天伦之爱——母亲的处境——她夜探她的孩子——突出的事件——她之死——她的埋葬地
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仅仅是两部自传在内容上的不同或矛盾之处,而是叙述者“我”的改变,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叙事者的口吻、视角及对所叙述内容的取舍操纵上。单就篇幅而言,第一部自传中对童年生活的描述不过五、六段,到了第二部自传中却变成了洋洋万言,几乎相当于第一部自传22%的篇幅。对同样的生活在叙述时空上的明显延拓显然是有目的的,至少可以说明一点, 即1855 年自传中的“我”已不同于1945年的那个“我”。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如此大的改变?
显然,文本自身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只能把文本放到产生它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去寻找答案,即从文本出发,走出文本,最后再回到文本。这种解读法是由自传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决定的。自传的英文词“autobiography”就其词源的构成来看, 可以理解为“auto(self)”+“bio(life)”+“graphy(writing)”,即自己书写自己的生活(self-life writing),与小说相比, 前者以历史真实和存在为基础,而后者则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以虚构性为本质特征。(注:关于自传文学与虚构文学的区别问题,可参见王成军、王炎《文本·文化·文学——论自传文学》一文,载《国外文学》1997年第2 期。)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文化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如果我们将道格拉斯置于他所处的时代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道格拉斯之所以要在1845年撰写自传,虽然部分原因是想澄清时人的怀疑,但主要目的恐怕还是要借助于自传这种文学形式来揭露和控诉南方黑奴制度的惨无人道。正是出于对奴隶制度的切骨之恨,道格拉斯才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废奴运动中。他曾在一篇演说中说道:“需要的是热情的人而不是博学的知识分子。奴隶的事业不需要知识来推动,就如同基督教不需要知识来推动一样。福音书最早的传道者是一些没有文化的渔民;而与他们同样无知的人也可以为反黑奴制度传道。”(注: 参见 TheFrederick Douglass Papers,1854年2月17日讲稿。)这种心情和反奴隶制的政治热情反映到自传的文本中,就是利用一切机会来抨击奴隶制,于是本来或许还有些幸福可言的童年生活到了1845年自传中也变成对奴隶制的控诉。叙述的政治由此可见一斑。换言之,道格拉斯在1845年自传中对童年生活的描写是有政治目的的,这就是揭露黑奴制度的罪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将童年生活描绘得越悲惨,就越能揭露黑奴制度的残忍,政治鼓动性就越强。对于叙述的政治性,道格拉斯毫不讳言,他在为纪念自己逃出奴役10周年写给老主人托马斯·奥德(Thomas Auld)的信中说:
要把你当作一件武器,用以向奴隶制发起攻击——当作一种手段,让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制度上,并加深他们对(此类)践踏人类灵魂和肉体(行为)的恐怖。我要把你当作一种手段,以揭露美国教会和教士的本质——当作一种手段,让这个罪孽深重的国家同你一起忏悔。我这样做,并非是对你本人怀有什么恶意……
我是你的同类,但不是你的奴隶。(注:这是道格拉斯于1848 年9月3日写给老主人的一封信, 他本人后来为此信作注:“奴隶给主人写信并不常见。下面这封信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可能是这一类信件中保存下来的惟一一个样品。它是我在英国时写的。”见Frederick Douglass:Autobiographies,pp.412—418。)
如果说1945年自传中的道格拉斯是出于对南方黑奴制的极端愤恨而把老主人、童年生活及其它一些历史事实当成一种政治手段而稍加扭曲,那么1855年自传则不同了。经过10年的历练,此时的道格拉斯无论从情感还是社会地位上都与10年前有了很大差别,他已经成熟了。尽管奴隶制仍是他抨击的对象,但他逃出南方后对自由的美好向往在北方的现实生活中被无情地粉碎了——北方并不是他想像的天堂,他逃出地狱却又进入了炼狱。他处处遭受种族歧视:坐车要与白人隔离,吃饭要另桌,住宿处处遭白眼,随从也不听话。道格拉斯越来越意识到大环境虽然改变,但他个人的社会地位在白人眼中依然如故,仍然是“东西”、“黑人”, 这是不可更改的铁的事实。 道格拉斯曾以愤慨和调侃的口吻在1855年自传中作如此描述:“每当有人对我说:‘道格拉斯先生,我会走上前去迎接你,我不怕黑人,’我就禁不住在想——我的外表没什么特别吓人的——‘那你凭什么要怕呢?’”(第393 页)(注:本文所引 1855年自传的页码均据Frederick Doulass:Autobiographies一书,引文由笔者译出。)
面对无处不在的白眼和歧视,道格拉斯虽然表面上已获得了自由,但在内心深处却越来越觉得自己正被整个白人社会所异化。如果说1845年前的道格拉斯由于初尝自由的美果而为之陶醉,尚能容忍被称作“东西”(chattel),(注:如1842年的一次集会上, 加里森(Garrison)介绍道格拉斯时将他称作“来自南方的一件东西”(a thing fromthe South);而道格拉斯“那天晚上站在那里是一个小偷和强盗! ”“这头,这四肢,这躯体,”他说道,“是我从我主人那里偷来的!”在1846年爱尔兰的一次群众集会上,道格拉斯也曾宣称:“在美国我受到迫害、追捕和凌辱,于是我来到了英格兰,看看我的变化吧!那件东西变成了一个人。”这些说明,道格拉斯在脱离南方后的几年间曾一度对自己被称作“一件东西”至少是没有什么不满意的,这与1855年自传中的叙述语气和视角形成了鲜明对比。)1855年的道格拉斯则对自己的这种身份十分不满——他已经意识到了被歧视的滋味:
我通常被介绍为一件“东西”——一个“事物”——一件南方的“财产”——大会主席向观众保证它会说话。那时,逃奴并不像现在这么多;而作为一名逃奴演讲者,我的有利条件是成为一项“崭新的事实”——第一个逃脱的。直到那时,自己承认是逃奴的黑人被认为是蠢蛋,这不但是因为有被重新抓回去的危险,还因为这样做等于承认自己的出身很卑贱。(第366 页)(注:着重(原文为斜体)和引号均系原文为强调所加,含有讽刺意味。)
与1845年自传中的“我”相比,此时的“我”确实已经成长了:“我”已经意识到自由与平等同样重要,奴隶制与人种歧视同样可怕。逃脱南方奴隶制的枷锁只是朝自由之路迈出了第一步,要在社会上获得真正的平等和自由,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此时的“我”显然已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以自身经历来揭露奴隶制的传声筒,而是对奴隶制有了新看法,只不过由于受到白人废奴主义者的歧视和压制而无法表达。对此,道格拉斯十分愤慨:
“让我们拥有事实吧,”人们说。我的朋友乔治·福斯特也如是说,他总希望能让我集中于简单叙述。“告诉我们事实吧,”柯林斯说道,“我们来对付思想哲理。”就这样产生了些许尴尬。对我来说月月重复同样的故事是不可能的,也无法让我一直对它有兴趣。对人们来说,那是新鲜事,这是事实,但对我,它则是老故事;就我的本性而言,日复一日地重复它实在是一件太机械的劳动。“讲讲你的故事吧,弗雷德里克,”那时我很尊敬的朋友威廉·劳埃·加里森经常在我走向讲坛时对我耳语道。我不可能每次都遵从,因为我那时在读书和思考。对同一问题的新看法涌现在我的心头。我已并不仅仅满足于叙述冤屈;我真想痛斥它们。(第367页)
事实上,1855年自传中的“我”已经认识到自己正在成长:“更何况,我那时正在成长,也需要空间。”(第367页)正如1855 年自传中的“我”所追叙的那样,1845年自传中的“我”与其说是在谴责,倒不如说是在叙述,即通过叙述自身的凄惨经历来达到揭露和控诉的政治目的,率真素朴的叙述正是1845年自传的突出特点和优点。与此相对照,1855年自传中的“我”作为一名“入世”者,已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所获得的“自由”只不过是躯体上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他还需要对付另一个大敌,这就是随处可见的种族歧视和白人至上的精神统治,她正环伺在他周围,随时都会把他吞噬。与奴隶制相比,这个“大敌”更为可怕,因为她的统治是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是整个美国白人社会,是美国制度本身的衍生物。对此,早已被社会异化了的“我”虽然很清醒,却又十分无奈:
我亲爱的朋友加里森:直到现在我都没有直接表露过我对这块土地上人民的性格和环境的看法、情感和观点。我这么做是故意的。……毋庸讳言,在谈起爱尔兰时,我肯定不会受到任何偏见的影响而站在美国一边。但我的情形却不允许我这样做。我没有目标可以服务,没有信条需要维护,没有政府需要辩护;至于国家,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在家我得不到保护,在外我没有居所。生我的土地欢迎我上岸却作为奴隶,对任何对待我有所不同的想法嗤之以鼻。于是,在孩提时我是社会的弃儿,是生我养我故土上的逃犯。“对你而言,我是一个陌生人,是一个过客,就如我所有的前辈们那样。”人们应当爱国,这对我来说十分自然;而作为一种哲理性事实,我可以从学识上予以确认。但我也仅能到此为止。如果说我曾经有过任何爱国主义的思想,或能够有此思想,它也很久以前就被美国的灵魂驾驶员用皮鞭从我的身上抽走了。(第372 页)
这是道格拉斯1846年1月1日写给他的朋友、白人废奴运动领导人加里森信中的一段话,从中不难看出,此时的“我”虽然已逃离南方八年之久,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民族、国家甚至祖国的失望,与1845年自传结尾时那个激动不安而又对事事感到新奇、充满干劲和希望的“我”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
三
与1845年自传相比,1855年自传除了对一些事实的叙述和议论有所不同外,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对“我”来到北方后的自由生活的叙述,道格拉斯把这部分的叙述命名为“作为自由人的生活”( Life
As
AFreeman)。 正是这后一部分叙述使得在1845年自传基础上大大拓展了的第一部分“作为奴隶的生活”(Life As A Slave )的叙述显得更为深沉有力,更加意味深长。从这种意义上来说,1855年自传的第一部分既是1845年自传的扩展和延续,同时也是该自传第二部分的起点和出发点。
如果从另一视角对1845和1855年自传进行解构,我们不妨这样来解释两部自传中的差异和“缺失”:如果说传统的观点认为自传就是以“我”为中心, 讲述的是“我”与“世界”的两极对立的故事, 那么在1845年自传中,中心已从“我”转移到了作为其对立面的“南方奴隶制”。道格拉斯更多地围绕“南方奴隶制”来叙述“我”的故事,叙述的着眼点在于揭露“南方奴隶制”对黑人肉体和灵魂的摧残,曾经身受其害而幸运脱逃的“我”只不过是用来达到揭露这种罪恶制度的一种最具说服力的手段。而这既是当初白人废奴主义者雇佣道格拉斯四处演讲的初衷,也是道格拉斯本人自愿积极参与废奴运动的动因和有利条件。毕竟,在揭露南方奴隶制方面,再没有人比逃自南方且拥有白人话语权的道格拉斯更有发言权和说服力。道格拉斯本人对此也十分清楚,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说道:“演讲者和所演讲的事情之间必须有一种和谐,否则演讲就不会有感染力,
也没有任何意义。”(注:
参见 TheFrederick Douglass Papers,1854年1月6日讲稿.)历史已经证明,道格拉斯不但是正确的,而且很成功。正因他是一名来自美国南方的逃犯,才使得他1845至1847年在英伦三岛的演讲每每座无虚席且无人置疑,他的演讲感染力之强,足以令“所有的教士都反对奴隶制”。他们说:“道格拉斯先生如此这般说过——他的权威是既定的——而谁还能比他更有发言权?”(注:参见“Introduction to Series One”p.iv,inThe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s,Series One:Speeches,Debates and Interuiews,vol.1 (1841—1846),New
Haven and London:YaleUniversity Press,1979。)简而言之,1945年自传中的“我”虽然是故事的主角,但就叙述的目的和意义而言,与“南方奴隶制”相比,“我”显然由传统的“中心”地位降为“边缘”。
与此相比,1855年的自传则要复杂得多。除了“主体物我”(或称“经验自我”)与“南方奴隶制”在第一部分中仍然形成两极对立的矛盾,“主体物我”在第二部分中又与“整个白人社会和种族歧视制度”形成两极对立;不但如此,第一部分中的“主体物我”与第二部分中的“主体物我”也显然不同:如果说前一个“我”尚显幼稚,那么第二个“我”则显然已经开始成长,表现在文本中就是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已与前一个“我”大大不同。更为复杂的是,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故事的层面,而是深入到话语的层面,就会发现,与1845年自传相比,1855年自传在叙述交流或话语层面上又“多”出了一个“读者”:(注:从理论上来说,任何叙述行为都必然牵涉到或曰包含“叙述者”和“读者”或“观众”。但“读者”或“观众”在叙述层面上是隐性还是显性存在,二者有很大差别。就道格拉斯1855年自传而言,“读者”在叙述层面上直接出现是有意义的,很值得进一步探讨。从文体上来说,它是1855年自传更接近演说体的一种标志,与1845年自传那种平铺直叙的风格完全不同;从自传的意义建构上来说,“读者”在叙述层面的显现也会对“自我”形象的构建产生直接影响:越是注意“读者”的存在,就越关心“自我”社会形象的塑造,也就越容易宣称“真实”而实际更不“真实”。)“叙述者我”多次在文章中直接对“读者”坦言。“读者”的直接出现在叙述交流层面上与“叙述者我”又形成了一对对立关系。如果说在1845 年自传中尚能找出一个“中心”, 那么1855年自传则从根本上排斥“中心”的存在,“主体物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处于一种动态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与多种“外在的世界”——先是“奴隶制”,后是白人至上的“种族歧视制度”——形成了多极而非两极的对立。
总之,道格拉斯的第二部自传无论从叙事的视角、策略还是事件的安排上都与第一部有着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存在并非偶然,它与作者的心态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指出:“有两种不同的、相互对抗的叙事力求再现历史:一种是线性的,另一种是交迭的;一种强调历时性,另一种把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区分纳入一个整体。”(注:参见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Ithaca,New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如果说道格拉斯的1845年自传强调的是一种历时叙事,即以叙述奴隶制的惨无人道为其要本,那么1855年自传则是历时与共时相交融的叙事——不但叙述历史,而且还面对更加严峻的种族歧视的社会现实,把自我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全部融入到自传的叙述中,叙事策略的改变和“自我”的不断成长是有理由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叙事的政治也正寓于其中。
标签:道格拉斯论文; 自传论文; 美国史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