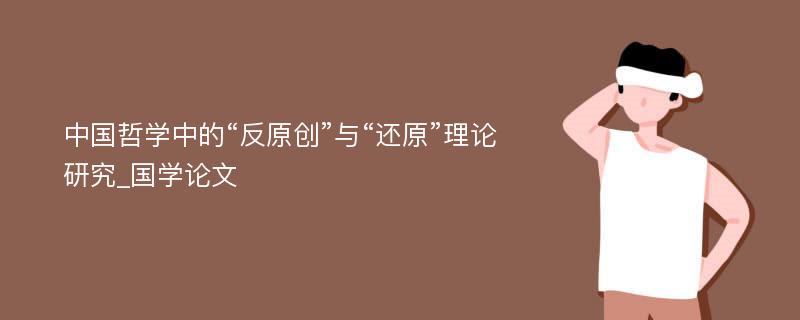
中国哲学“反本”“复性”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性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哲学的理论系统中,“反本”“复性”论充分刻画了中国哲学的特色,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目的追求。自先秦至宋明,这一追求展现给我们的,是它区别于向外、向上追寻超越的哲学本体,是它开辟了一条以回复到根源的“本”“性”为宗旨、为目的的独特哲学发展道路。可以说,正是这种从一开初就具有的以返归本根为定向的思维方式,造就了区别于西方的中国哲学(心性)本体论之独特的价值。
一、“反本”“复性”道路的奠定
“反本”“复性”论的发明与中国哲学的创生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是同步的。哲学家的使命重在揭橥宇宙和人生的意义,而这正是中国第一个典型的哲学形态——老子哲学的目的。老子不满于面向未来和外在的思维方式,因为这都是大道离散的无奈结果,所以他要求掉转目光回归本始。在他看来,只有反本复性或“归根”的追求,才能把握宇宙运动的真相,才能真正体现哲学的价值。老子说: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十六章》)
人的目光不应放在芸芸并作的万物身上,而是应当转向虚静的根本。“归根”是反本的落实,“复命”按河上公注为“复还性命”。“性命”二字如果分拆,可以看作是普遍的宇宙之“命”与特殊的人生之“性”的结合,万物之根与人生之本在这里是一致的,复“命”也就是复“性”。
老子以“静”为复还性命之表征,在于现实的躁动社会不值得肯定,这是其倡导反、复趋向在现实层面的一个根本理由。从理论层面来说,执著于外部的芸芸众生和是非荣辱,不但不可能走向永恒,而且会招致凶害的后果。因此,即便从利益的角度去看,“复命”也是必然的选择。故他又说: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豀。为天下豀,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
这种与“常德”联系在一起的“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和“复归于朴”,都说明“复归”云云是老子哲学实现自身目的的最一般的方法。常德对人生的意义在于设置一种内在的阶段性目标,以为走向无极之朴的复返道路提供一个可以量度的基准。
但在老子那里,反本复性采取的“知常”不妄、“知常”守辱的操作方式,似乎说明这是一种有意识的作为。庄子对此则做出了修正,将有意识的修养心性以求回复到本初的做法贬称为“俗学”。以为“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者,不过是“蔽蒙之民”(《庄子·缮性》)。因为“和”(德)“理”(道)本出于人之天性,恬静自然才有望回复到本初。但自尧舜之治天下始,社会的退化加剧,去性从心,灭质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庄子·缮性》)。这样一来,反本复初在庄子就更为严格,它是从对儒、法等“俗学”的批判角度表现出来的。因为“万物之本”既然是“虚静恬淡,寂寞无为”(《庄子·天道》)的存在,那么,返归本初之性就不能期待积极有为的追寻,而只能采取与此顺应的恬淡无为、因循自然的办法。老庄的反本既在于以太初素朴为参照表达对现实有为政治的批判,也在于动中求静、从道与世交相丧回复到上古的道德之世。
与道家比较,孟子的“求放心”说是儒家主动积极的反本复性论的发端。“求放心”作为孟子规定的唯一“学问之道”,意在向内体验扩充先天的良心善性,亦即“反身而诚”,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如此“反身而诚”的“求放心”工夫,在目标指向上与道家是有区别的:它不是反其初,而是求其内。但是,对宇宙生成而言的“初”,对本性良心的形成却是当然和唯一的源头,所以仍可以归属于“内”。儒道双方也就存在一定的相容性。
儒家虽不是反本复性之方的开创者,但却具有应用这一思维方式的思想基础。这就是善的先天定位。人向内体验善,也就意味着由后天返归先天,这正是孟子性善论的方法论意义所在。在这里,有必要提到《礼记·乐记》对后来影响深远的一段话:“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反躬”意味着反省体验人生而静的天性,可以说已经是反本道路的践履者。《乐记》虽说是儒家经典,但其反本复初的思维导向与道家恐有渊源关系。① 或许,作为一种一般的思维方法,反本是为道家所首创而为儒家所采撷和依循的。
儒家论心性不尚空谈,仁义作为人之本初是立足于现实。孟子讲“反本”便是力图将以利益为本的风向扭转到以仁义为本上来,促使为政者推行仁政。孟子劝齐宣王说: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这种以“仁政”为特色的治国之策上的反本要求,是心性论中反本导向的社会政治基础。正是在这里,儒家反本与道家反本明显区别了开来。
不过,儒道两家在是否认同以仁义为本并积极人世上的分歧,并不妨碍双方都以“反本”作为根本的进德之路。两家都认为上古人心纯朴,只是儒家言必称尧舜,仰慕三代的理想仁德;道家则远推到人之“类”刚成立,道德“未失”而“无所用”智慧和仁义的时代。但从目的一方说,老子的“复归于婴儿”与孟子要求的“不失赤子之心”,实际上认同和归依的都是人心的原初状态。而个体人心的原初状态,在社会国家就是上古的理想境界。后者在学术层面的意义,主要还不在于它自身多么美好,而在于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始终以它为参照、为标准去矫正社会人心的险恶不测。由此形成的传统是,后来无论哪一派的哲学家,如果有谁不能“反本”,不能适应这一思想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不管本身多么有价值,最终会遭到被排斥的命运。荀子的性恶论便是如此。
当然,荀子在秦汉及其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地位并不亚于孟子。从哲学史的角度来分析,汉以后的儒家,或者沉溺于章句的注疏,或者应付于有无的玄谈,或者困顿于佛学的思辨,在整体上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也就使得人们无暇关注儒家内部各派理论之短长。但中唐以后,反本复性的历史需要,最终还是决定了儒家学者后来的选择。因为性恶论不论作何解释,它在现象上总是与性善论相对立,对于“言必称尧舜”的儒家哲学来说,不能确立善(至善)作为原初的基点,就不利于社会建构主流的价值导向,也难以提供充分的人心向善的理由。可以说,随着反本复性方法的普遍被采纳,荀子及其思想必然受到轻视。
可以说,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道家的反本复性观很早便开始了对性善说的吸纳。只是道家批评儒家雕性拂情而行礼义,期望以此引导民众向善,实在是本末倒置。以礼义约束人心的方法只能治末而不能反本。其言曰:
夫仁者,所以救争也;义者,所以救失也;礼者,所以救淫也;乐者,所以救忧也。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阴阳从而包之,则财足而人澹矣,贪鄙忿争不得生焉。由此观之,则仁义不用矣。(《淮南子·本经训》)
就“反其初”的方法而言,从老庄到《淮南子》是一致的,但老庄那里尚未将此“本初”状态与性善相连。战国时期的道家,对儒家的性善说往往是采取抵制的态度。汉初以后,儒家思想复兴,性善之说逐步传播开来,道家的反本复初也开始具有复性(善)的新的内涵。或者说,主张性善有利于反本复性思维的普遍推广。
就《淮南子》这段话而论,由于其仁义礼乐本属于善的教化,故若只讲到救争、救失、救淫、救忧,儒家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道家认为“仁政”并非源出于人的天性,而是从外强加并束缚于人心的结果。所以,讲性善只有在反其初的意义上才是符合人的需要的。在此层面上,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贪鄙忿争之心根本不会产生,儒家的仁义规范当然也就用不着了。道家从“反本”讲性善,对儒家的性善说是一大补充。尽管在儒家性善说的典型代表孟子那里,性善是一种由内向外的弘扬扩充,原则上不存在像道家那样的回复本初之性的必然性。
二、儒家复性、原性之路的正式开辟
“反本”的实质是复性,但复性作为儒家学派的自觉诉求,却是随着唐宋儒学复兴运动而开始的。在文本的选择上,讲性善和求放心的《孟子》地位上扬,并与《论语》、《易传》和《礼记》诸篇一起得到了广泛开发和利用。学者们重新组合这些资源并进行理论的加工,促使反本复性的理论具有了更多思辨化的色彩,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李翱的《复性书》。
李翱《复性书》“以心通”《中庸》而“调和各家”,阐发了新的融合三教的性情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诸文本的融合,是唐代儒学复兴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作品。李翱云:
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圣人者岂其无情邪?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复性书上》)
此一段话,将《中庸》、《乐记》和《易传》的心性学说糅合在一起,但将情与迷惑和陷溺相联系,则是源于佛教的思想成分。李翱所以要吸纳这些不同的文本,是因为其中任一种都只能提供部分的思想资源:《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赋予人性以客观必然的地位,为反本复性预设了前提;但《中庸》言性却不及情,无法解释人性总是透过不同的情感活动而体现这一现实,《中庸》开篇虽也论及喜怒哀乐的未发已发,但却不能以情的范畴来概括,说明在《中庸》作者心中,性情的对偶范畴还没有提上日程。同时,《中庸》也不从动与静的角度去观察和认识人性。所以,《中庸》的天命之性和“尽性”之说,必须要与《乐记》等其他文本相结合。
《乐记》讲“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将动静问题联系到了《中庸》的天命之性(天性)上;情欲则是动而后的产物,而一旦动作则离开了天性,从而引出如何由动的现实情欲复归到静的先天本性的问题。但是,人的活动均在后天,受后天物欲引诱,人往往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所以《中庸》需要以“尽性”作为方法论的指导,而具体的典范就是圣人。不过,圣人虽为复性典范,却又不是“无情”的存在,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在魏晋时期就被重点讨论。
其时圣人的典范作用已经从传统的人伦教化之父转变为追求虚无玄谈的开路先锋,由此造成与一般公认的圣人品格的背离。在此境遇下的圣人显然已经有些“不近人情”。从何晏的“圣人无喜怒哀乐”到王弼的“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体冲和以通无”,都需要将《中庸》的喜怒哀乐未发已发与《乐记》的人好恶有节而穷天理灭人欲联系起来解释。然而,即便是《乐记》亦只描述了消极形态的人性由静到动的过程,并未说明正常状态下由不动到动怎样展开。所以《易传》还必须添加进来。
《易传·系辞上》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如此“至神”固然是易道的存在特性,在李翱也就是圣人不动而动、无情而情的状态。相对而言,李翱的观点接近于何晏而不是王弼。“情”在李翱,主要是指邪情,圣人也就必须超越它。其具体方法,就是“率性之谓道”——“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而将《乐记》由“性之欲”到灭天理的邪恶,一并归结到情上,因为圣人本是以寂然不动为特色的。
李翱“以心通”的方法是对“以事解”的传统儒学的否定和超越。人问之:“昔之注解《中庸》者,与生(李翱)之言皆不同,何也?”李翱回答说:“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复性书中》)“以事解”即传统“词句之学”的名物训诂方法,“以心通”则是李翱借鉴于佛学而来。惠能有云:“说通及心通,如日处虚空。……若欲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1] 惠能的“心通”就像是白日当空一样,一切俱明,“真道”也就自然得见。当然,见真道的前提是自己有正心,无正心也就无真道。因此,见“道”就不在于向外做工夫,着力于名物考辨,而在于向内正心,自家修清静。
惠能的这一思想,对于李翱“心通”《中庸》之方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是如同惠能要求从繁重的佛教经籍中解脱出来一样,李翱也力图从繁琐的经学“注解”中解脱出来,突出见真道的主题;二是见性见道实为回复到本来清静心,李翱因而要求妄情灭息,本性清明,“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复性书中》)。当然,在李翱这里,“正心”、“真道”的基点仍在儒家,因为只有儒家圣人能“正性命”。“正性命”就是闻道见道,就是灭情复性。按照《易传》的理路,就是“弗思弗虑,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复性书中》)。
这样一种由事返道、由动返静、由外返内、由邪返正的工夫,就是李翱“心通”之方所取得的收获。从人性论的角度说,李翱将历来从内外、善恶、动静去解释的性与情之别,按照佛教的思辨理路,统一为明与不明(昏)的差别。性本无过,而情则有昏,所以根本的问题是去昏而就明,灭情而复性。当然,文本的融合不仅是儒家自身,儒家与佛教、道家之间也是如此。《文子》、《淮南子》等还在佛教传入前就讲性善和人性本来清净,动而不正则“失性”,所以需要“反本”。因而所谓文本的融合,实质上是儒释道三教的融合,而其方向则是由动向静、由现实向先天的复归。
与李翱比较,韩愈首先开辟了“原性”、“原道”的形而上研究道路,尽管对这一道路他并没有太多的自觉。韩愈试图通过对性与天道本来意义的追究去匡正不符合儒家理想的现实政治,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其仁义“定名”与道德“虚位”说。仁义本位的重建从社会政治层面接续起孟子,并通过这一“反本”之路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
韩愈是唐代反佛的代表,欧阳修则可以说是宋代的韩愈。韩愈反佛重在仁义性情,欧阳修反佛却强调礼义。他分析佛之所以愈反而势愈炽的原因,就在于反佛者“盖亦未知其方也”。比方医者对于疾病,“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也就是说,需要找准病因反本治本,而不是纠缠于末节,像韩愈那样“火其书”、“庐其居”与佛激烈冲突。儒家反省自身,补阙修废,“诚使吾民晓然知礼义之为善,则安知不相率而从哉?”[2](P291) 儒家应针对佛有“为善”之说以诳惑天下的现实,以礼义之善教化引导民众,“修其本以胜之”。他以为这是他写作《本论》的目的。那么,反本在欧阳修实际就是“修”本。“修”者何也?“彼无他焉,学问明而礼义熟,中心有所守以胜之也”。[2](P290)
欧阳修所走的是与韩愈一样的从政治伦理层面反本的道路,在哲学思辨上的反本复性,王安石是一个新的开端。王安石对唐代儒家“原性”和“复性”之路两位主要开创者韩愈和李翱的性情学说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以未发之心为性、已发之心为情,从人的内心本然和见诸形色的特定情感去划分性情,让情对人的实际行为负责,所谓“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为小人,莫非情也”。[3] 王安石重在强调道德主体的价值选择和后天道德教化的作用,以服从他“一道德”而整肃社会风气的改革大局。但由此一来,性作为“本”的意义便被模糊,反本复性的导向也就趋于消解,因为反本复性需要的不是统一性,而是根源性或绝对性。王安石的性本情用说则忽略了这一点,从而使得他的学说最终得不到彰显,不能成为宋代人性学说的主流。[4]
三、宋明理学对反本复性道路的多方论证
宋明理学的产生是儒学复兴运动的直接成果,而儒学复兴的本质规定就是复性。反本复性在这里不仅是方法、道路,也是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但从北宋张载、二程开始,人性的形成已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性”的组合,反本复性的使命就不再停留于复返原初本根以实现哲学目的这类的宏观叙事,而是深入到变化气质和对天地之性的具体修复中,主体的自觉意识开始承担起了更重大的职责。
张载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概念的提出者,但又是气质之性概念在价值上的否定者。“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5](P23) 君子不以气质之性为性,在于气质之性的善恶混性质,所以他要求“善反”,以走向清虚湛一的天地之性(太虚本性)。这便是张载的“变化气质”工夫。在这里,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性善体现于过程之中。“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5](P22)
性本身处在生成变化的过程中,是张载反本复性观的重要特色。反本在这里并不限于一般地回复到本性,因为它已经成为使性形成和完善的唯一的方法。这既有由气质之性到天地之性的质的变革,也有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相互间的力量消长。从量的角度来说,“二性”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全与偏的关系。“变化气质”可以表述为去偏复全或自孟子以来的养气的过程,以最终实现天道本来的参和兼通。在这里,反本就是尽性成性,就是通过形而下的养气修身去成就形而上的性体、天体,“反之本而不偏,则尽性而天矣”。[5](P23)
气质的可变性不只是主张气本论的张载讲,主张理本论的二程同样也讲。二程力求将孟子的“性善”与告子的“生之谓性”协调起来:“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谓性,论其所禀也。”[6](P207) 二者间的关系,以水作譬,或者因污染而浊,或者因澄治而清,清者为善而浊者为恶。如此的“澄治”之方与张载的“善反”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张载“善反”论的前提是“未成”的人性,“善反”形式是在“变化气质”,实质却是正面创造人的善性——天地之性,使性由“未成”进达“已成”,实现完全的天地之性。但二程则不然,二程的“澄治”只是返回到水之“元初”本然,其反本复性主要表现在修错纠偏之中。结合文本阐释,《中庸》篇首有“修道之谓教”说,二程以为,这正是针对人之本性有失而言。其曰:
“修道之谓教”,此则专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复之,则入于学。若元不失,则何修之有?是由仁义行也。则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亦是万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为道。[6](P30)
“修道之谓教”专论的“人事”,就是本性有失而需要修复。“若元不失,则何修之有”?二程以“生生不已”的“生道”解释修复之方,是引入《易传》“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的结果,说明入道“成性”,只有在“存而又存”的不断修复或“行仁义”中才可能实现。一有停顿或懈怠,本性就失而不复了。
二程以“成性”解复性,可以解释为人性因为有失而“未成”,从而与张载的性“未成”说可以相通。同时,由于“修道之谓教”被表述为因失性而修复的过程,复性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当然,在这里需要参看二程关于天道、天德在人之自足的观点。程颢称:“圣贤论天德,盖谓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无所污坏,即当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所以能使如旧者,盖谓自家本质元是完足之物。”[6](P1)
可以看出,此处的“盖谓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无所污坏,即当直而行之”的假设,因为有“天命之谓性”的前提,所以可以容易做出。但从程颢所述“盖谓”、“元是”、“若无”的语气看,他显然意识到在现实之中“无所污坏”更多地还是理想,“污坏”反倒是更为普遍。“本质元是完足”的意义是为人反本“复旧”提供可能和动力,这也正是孟子“道性善”的理论价值之所在。
作为二程、张载哲学的继承者,朱熹对程、张的性气观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后者亦成为他著《四书集注》时的重要思想资源。就在孟子那一长段围绕性善论的“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的著名论证之后,朱熹分别引证程、张之言并发挥说: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则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学而知之,则气无清浊,皆可至于善而复性之本,汤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则自暴自弃之人也。”……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愚按:程子此说才字,与孟子本文小异。盖孟子专指其发于性者言之,故以为才无不善;程子兼指其禀于气者言之,则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是也。二说虽殊,各有所当,然以事理考之,程子为密。盖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学者所当深玩也。[7]
在朱熹这里,孟子与程、张所言不同,各有所当,但程、张之论要更胜一筹。因为只讲本然之性、才无不善,就无法说明人为何会产生恶的言行,也不能体现上千年来儒家一直倡导的通过反本复性之方走向圣人境界的历史要求,所以需要气质之性的概念来对此给予解释,即:气质之性的不善成分不妨害本善的存在,这保证了反本复性之可能;而本善之性又需要加之以“省察矫揉之功”,这强调了反本复性之必要。二者互不可缺,所以程、张之贡献绝非小。从价值的主导来说,气质之性的概念并不是为固守气质,正相反,它是为变化气质而反本即完全的天地之性打基础的,汤武就是以身践履的典范。
不过,程、张之论复性,前提是肯定本性有失。溯起源可以联系到孟子“求放心”的“鸡犬有失”。程颢甚至以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叫人收放心。而朱熹对此却颇不以为然。因为“鸡犬有失”的命题潜藏着一种危险:“然鸡犬犹有放失,求而不得者。”[8](P1412) 这会导致本善之性的基础被动摇,所以朱熹绝不同意。
实际上,按朱熹的思考:“人心才觉时便在。孟子说‘求放心’,‘求’字早是迟了。”[8](P1407) 心如果需要“求”时,它早就没了。故又说:“‘求放心’,只觉到:‘我这心如何放了!’只此念才起,此言未出口时,便在这里。不用拟议别去求之,但当省之而勿失耳。”[8](P1408) 就是说,“放心”(如果要用这概念的话)只是觉心、念心心境中的一种当下状态:觉有“放”是心之觉,而心觉则心已在,也就根本不存在心事实上“放失”的问题。相反,他以为禅宗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说得极好”[8](P1407),因为佛性随时而在,只要一念一觉,便即觉性而超脱。禅宗顿悟心境中的当下即在状态,可以说正是朱熹觉心念心状态下并无放心的绝好解释,所以他要通过此种有觉念无放心之说去矫正孟子的“求放心”。
明代王守仁批评朱熹的天理论,大倡良知为本;但在方法上,他与朱熹却颇有一致处,那就是以觉念工夫言复性。王守仁云:
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然才有着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去,复其体矣。此处能勘得破,方是简易透彻功夫。[9](P111)
陆九渊以简易工夫排挤支离事业的心学传统,在王守仁得到了继续。但是,简易如果不能从良知自身说法,是很难站立起来的,所以王守仁的简易方法要比陆九渊“透彻”。实际上,陆九渊虽倡导简易,但如何才能将简易之方落实,在陆九渊是不清楚的。无论是“尊德性”还是“先立乎其大”,心智都是立它(德性、大体)而非自立;只有到王守仁的良知自觉,才能真正使简易之方落到实处。
讲良知自觉可以将朱熹与王守仁联系起来,但再往前走一步,双方就有了明显的区别。从这区别可以看出,不是朱熹,而是王守仁更多地继承了北宋儒学的精神。譬如,以程、张为代表的北宋学者,并不认为反本复性是当下即在式的顿悟,而是需要持续不懈的努力;同时,他们还都以本性有失作为复性的前提。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刚好与此相衔接。
在前者,王守仁的“才有着时,良知亦自会觉”并不意味着一念便完成,简易并不妨碍有时间的要求。对于学生用功却未取得效果的疑问,王守仁回答说:
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里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浊水,才贮在缸里,初然虽定,也只是浑浊的;须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尽去,复得清来。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窣窣自能光明也。今便要责效,却是助长,不成工夫。[9](P99)
“良知存久”是良知自觉和“自能光明”的必要条件,即它与用功长久的时间磨炼分不开,是功到自然成。王守仁虽主张良知的简易自觉,但他并不奢望刹那般顿悟的立竿见影效果。后者在他只是不着实效的拔苗助长之工,不可能真正实现“复清”反本。
从后者看,王守仁虽然以本心良知为本,但反本复性以本性有失有偏为前提,则没有任何变化:
先生曰:“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9](P95—96)
“人心是天渊”点明了心本论的主旨,这也是“念念致良知”的本体论基础。由于天渊都容易遭受私欲的污坏而导致本体丢失,所以需要念念不忘去私欲、致良知,从而复其本体。王守仁强调在良知上用功,可以说是从孟子的“求放心”一贯而来,立足自我的去欲复本。换句话说,孟子的“求放心”在宋儒普遍得到继承,朱熹的不满反倒属于别类。当然,朱熹的不满也与孟子只是立足于心性自身说事,不能从天命天理出发矫治人欲、发明本性相关。
明清之际,作为气学的后继者的王夫之,对张载“善反”而存天地之性的观点进一步作了诠释:
即此气质之性,如其受命之则而不过,勿放其心以徇小体之攻取,而仁义之良能自不可掩。盖仁义礼智之丧于己者,类为声色臭味之所夺,不则其安逸而堕于成能者也。制之有节,不以从道而奚从乎!天地之性原存而未去,气质之性亦初不相悖害,屈伸之间,理欲分驰,君子察此而已。[10](P128)
仁义礼智是大体,倘若放其大体而追逐声色臭味之小体,则心放而堕于物欲,天地之性也就被气质之性所屈,而终不能得以保存。尽管天地之性本属于“原存”,但在人追逐利欲的情况下又难免不被气质之性所害。因而“放心”的问题始终需要予以警惕,需要强调收放心或反本,以从其道之大体。那么,如何才能叫做“善反”呢。王夫之说:“攻取之气,逐物而往,恒不知反。善反者,应物之感,不为物引以去,而敛之以体其湛一,则天理著矣。此操存舍亡之几也。”[10](P126)“善反”与攻取的气质之性无关,因为后者是追逐物欲而不知反的。“善反”者既能响应外物的呼应,又能把持自我,收敛气质,并从中体验到清纯湛一的天地之性,从而使天理能得以彰显。王夫之以为这是自孔孟以来一直看重的操存舍亡的隐微要旨所在。“善反”看似只是一种修养方法,但此方法实际上关系着儒家性命道德的存亡,实在不可小觑。
“善反”的方法依赖于纯熟的德行修养,如何能有这样的修养,王夫之继承了张载的“养气”之方。他发挥张载的“养其气,则反之本而不偏”说:
气本参和,虽因形而发,有偏而不善,而养之以反其本,则即此一曲之才,尽其性而与天合矣。养之,则性现而才为用;不养,则性隐而惟以才为性,性终不能复也。……教者,所以裁成而矫其偏。若学者之自养,则惟尽其才于仁义中正,以求其熟而扩充之,非待有所矫而后可正。[10](P130)
气从天论是太极、阴、阳三合一的产物,本原不偏;但凝聚成人却往往不能如意而各自有偏,即人生从才的方面讲都有其缺陷的方面,人性受此气禀或才的影响,也就有偏而不善,所以必须通过反本复性的方法,以求得完满的天地之性。
反本复性的重心已不是本性有失而修复,而是相对于天性完满而言的人性之偏,所以养气的方法虽然未变,但目的却转化为纠偏以复全。由于人的自然资质或“才”有高低,纠偏的方法亦有内外的不同:有的需要外在教化以强制矫正;有的则立足自我涵养以尽仁义,最终由偏而扩充完善。同时,由于人性本“得”于天命,所以复性的标志就是性安于德(得),达天而立命:“以善之纯养才于不偏,则性安焉于德,而吉无不利,皆德之所固有,此至于命而立命也。”[10](P130) 以天地之纯善养才,才用资质走向完满,人性以天德为安宅,反本复性的任务最终得以完成。
由此可见,反本复性作为集中体现中国哲学特色的理论和方法,既关涉实体,又牵连方法,融本体论和修养论为一炉,突出的是人人可以向往并以之为自己终生追求的境界和目标。这样的境界和目标不是超越于世界之外,而是内在于人性之中,是心性理论的起点——天命之谓性;也是心性理论的终点——归根曰静或尽性至命,最终是力求在躁动逐利的现象世界中找回清静纯粹的善的本性。只有清静的本性而非躁动的世界才具有真正的永恒性和常住性。中国哲学之生命力也在对反本复性的不懈追求中,得到最为绚丽的彰显。
注释:
① 此一段话,首先为道家学者所采用,如《文子·道原》、《淮南子·原道训》等都有对此的阐发。石峻先生早年便提出这是通于道家的思想。参见《略论中国人性学说之演变》,《石峻文存》,36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标签:国学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孟子论文; 朱熹论文; 王守仁论文; 乐记论文; 淮南子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李翱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道家论文; 中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