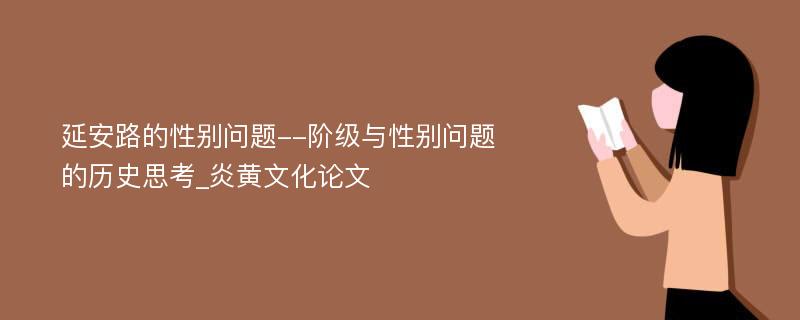
“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性别论文,议题论文,阶级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6)06-0016-07
1941—1943年中国共产党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施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政策,不仅成为此后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基础,也为新中国确立了基本的建国模型。这一新体制被一些研究者称为“延安道路”①。尽管许多研究者都承认中共取得抗战胜利和建立新中国,与其妇女政策有密切关系,如杰克·贝尔登(Jack·Belden)写到的:“在中国妇女身上,共产党人获得了几乎是现成的、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广大的被剥夺了权力的群众。由于他们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之心的钥匙,所以也就是找到了一把战胜蒋介石的钥匙”[1](p.395),但在具体的研究中,性别问题却没有得到重视②。
关于从延安新政策开始的中国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史,形成了一些影响广泛的“定见”,比如革命政权是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但没有特别关心女性性别本身的问题;比如革命实践尽管赋予了女性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但却忽略了女性在社会角色和文化表达上的独特性等;这些“定见”并没有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得到具体讨论。而自“文革”结束以来,当代女性文化则在反思以往的妇女政策的基础上,侧重于将女性问题与阶级议题分离,即其生理、心理和文化表达的独特性。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话语关注和表达的主要是“知识女性”的问题,从与新启蒙主义话语的结盟到引进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女性话语始终潜在地以中产阶级女性作为女性主体想象的基础。于是,革命时代的工农女性形象逐渐从文化舞台上消失身影,而代之以充满中产阶级情调和趣味的女性形象。重新回到对于形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女性文化和政策具有关键意义的“延安道路”,考察革命实践与女性话语间的冲突和磨合过程,就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研究,同时也尝试为当代社会主义女性话语实践提供一种理论参照。
一、“四三决定”的农村妇女政策与“妇女主义”
1943年开始全面施行的延安新政策,一个重要方面包括关于性别问题的新决议,这指的是由中央妇女委员会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后于2月公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在考量这一政策的意义时,新决定说:“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它并不否认动员妇女生产主要是为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问题,但同时也认为妇女经济地位的提升将帮助她们“挣脱封建的压迫”。不同的妇女运动文献和当时的介绍资料都强调,参与生产运动使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得到提高,她们的社会活动范围也扩大了;且由于边区政府采取一些鼓励妇女参与生产的特别措施,比如评选女“劳动英雄”③、“劳动模范”、有比例地选择妇女参与农村政权组织等,也提高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但新决定同时强调,提高农村妇女的地位,必须以保证“她们的家庭将生活得更好”为前提,也就是说,妇女地位的提高不得破坏原有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
“四三决定”的出台,事实上也是整风运动的一部分。1941年秋天,中共发起整风运动不久,即改组了中央妇女委员会,由蔡畅接替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并于9月,中央妇委、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妇女生活调查团,调查根据地妇女运动现状④。新决定一开篇便批评了原有妇女组织的工作方式“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充分的群众观点”。在列举具体的事例时,除指责她们没有把经济工作看作“妇女最适宜的工作”之外,主要强调妇女工作者“不深知她们的情绪,不顾及她们家务的牵累、生理的限制和生活的困难,不考虑当时当地的妇女能做什么,必需做什么,就根据主观意图去提出妇女运动的口号”,尤其批评那种经常招集她们出来“开会”的运动方式所造成的“人力物力”上的浪费。蔡畅在1943年3月8日发表于《解放日报》的社论文章《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中,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偏向说得更为具体:“特别是妇女工作领导机关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女干部,有不少是只知道到处背诵‘婚姻自由’、‘经济独立’、‘反对四重压迫’……等口号,从不想到根据地实际情形从何着手……当着为解决妇女家庭纠纷时,则偏袒妻子,重责丈夫,偏袒媳妇,重责公婆,致妇女工作不能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陷于孤立”,进而更尖锐地批评她们“甚至闲着无事时,却以片面的‘妇女主义’的观点,以妇女工作的系统而向党闹独立性。”——蔡畅在此激烈批判的“妇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与“延安道路”在性别问题上构成冲突的对立面。尽管难以找到行诸文字的直接史料来说明“妇女主义”如何阐述自身及其具体的行为方式,但可以断定,这种由“知识分子出身的女干部”所持的观点,大致是把女性(尤其是其中居弱势地位的年轻女性)利益视为主要衡量标准的,因此,在具体处理农村家庭纠纷时,才会“偏袒妻子,重责丈夫;偏袒媳妇,重责公婆”。
“妇女主义”造成的问题是,采取过于激进的做法,鼓动农村年轻女性的独立和个人要求,势必造成乡村矛盾,尤其是与根深蒂固的乡村男权观念,及通过家庭/家族秩序实施的男权控制之间形成冲突,这种激烈颠覆或破坏传统乡村结构的做法,显然会影响到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在不同的材料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做法对乡村社会的消极影响。如蔡畅的文章在介绍示范地区的妇女工作经验时提到,运动早期在鼓动妇女参加纺织厂时,即引起了乡村男性的抵制:“赚几个钱,老婆没有了怎么能行?”杰克·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中,详细讲述了一个乡村女性金花如何利用共产党的妇女组织迫使她的公公和丈夫就范的故事。金花迫于乡村习俗和父母意愿,嫁给一个大自己十多岁的“丑”男人。丈夫和公公、公婆、小姑子的虐待,使她了无生趣且充满仇恨。共产党在村里组织妇女会之后,金花依靠组织的帮助“教训”了丈夫,而教训的手段,则是妇女会集体出动,把男人痛打一顿,并迫使他答应不再虐待妻子。那个丈夫最后充满怨毒地逃离了家乡:“……我认为女的就应该听男的。可是,你看,在八路军管辖地区里,女的都狂得很,不听男人的话。”金花也和他离了婚,并满怀希望地畅想未来的新生活[1](pp.340~382)。——正是上面这个故事,使贝尔登得出结论,认为共产党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之心的钥匙”。尽管故事发生的时间在“四三决定”之后,且区域也不一样(冀中而非陕甘宁边区),但从故事描述的内容上看,金花及其所在村庄的妇女会的过激行为,显然并非延安新政策鼓励的方式。“四三决定”批评此前妇女政策的错误时,列举的内容与金花的故事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鼓励妇女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比较激烈的斗争手段。例如给虐待媳妇的婆婆戴高帽子游街,在大会上批斗打骂妻子的丈夫,轻率的处理婚姻纠纷等等”[2](pp.510~511)。尽管中共鼓励农村妇女争取平等的地位,但上述激烈的冲突,显然与中国共产党力图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赢得乡村农民拥护这一目标发生冲突。
为了减少之前妇女运动造成的问题,“四三决定”倾向于寻找一种更为实际的方式,以避免乡村矛盾,即强调妇女参与生产和增强她们对于经济生产的贡献。毛泽东在阐述新妇女政策的必要时,明确地提到需要得到乡村男性的认可:“提高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这是能取得男子同情的,这是与男子利益不冲突的。从这里出发,引导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动,男子们也就可以逐渐同意了”[3](p.46)。这事实上是通过从激进的妇女运动转变到保障妇女的工作、劳动权利,既通过社会权利的强化促使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又达到维护乡村稳定的目的。“四三决定”列举的妇女参与经济生产的诸项能力,既包括传统家庭女性的活动,“能煮饭、能喂猪”以及能“把孩子养好,保护了革命后代”[4],也包括此前不允许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参与的纺织、种地、理家等活动。在此,新决定一方面鼓励女性参与社会工作,提升了妇女的地位和自主性;另一方面,新规定在质疑和批判传统乡村的男女性别差异上又有所减弱,而把家务劳动视为女性理所当然的任务。当然,这种措施毫无疑问适应了当时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状况,保证了党的事业顺利发展。
把经济生产作为农村妇女工作的“首要任务”,极大地调节了乡村的性别矛盾并提升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但由于乡村传统的父权制家庭结构根深蒂固,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的影响,妇女地位的提高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制约。整风运动之后发起的“大生产运动”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纺织业,早期施行的集体大工厂生产由于战时环境、交通、组织生产等方面的问题,而改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作坊式生产。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由于原材料的获取、产品的流通等因素使妇女直接介入社会活动。但这不是破坏而是强化了家庭结构,如迪莉亚·戴维指出的:“家庭是基本的经济单位。这种家庭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小的(纯婚姻上的)家庭,而是乡村中的‘大家庭’,它的目的在于有效地利用劳动力。这种大家庭是正在支持抗战的农村经济的基础。所以,作为行动的基点,应该重新构造和巩固这类家庭”[5](p.4)。也就是说,不仅是由夫妻、公婆组成的小家庭,还包括由宗族、邻里等构成的乡村伦理秩序,亦同样被保持和巩固。尽管战争时期,由于男性参军而造成的空缺有可能削弱家庭内部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但由于维护家庭结构关系和乡村伦理秩序,事实上压制女性的父权制结构并未松动。而且因为强调生产,往往是那些此前控制家庭资金和有更熟练技术的老年女性(母亲或婆婆),更能在生产运动中得到好处,她们对年轻女性的控制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⑤。因此,如果说经济生产能够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话,但却不能改变由于资本的引入而导致的农村女性内部在年龄、经济地位、技术掌握等方面形成的新的控制等级。
“四三决定”与“延安道路”的新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即不再激进地强调“反封建势力”,而以动员民众为核心,与以父权制为核心的乡村伦理秩序形成协商关系。如果说“妇女主义”是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片面强调农村妇女(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利益,那么“四三决定”出于经济和文化动员的考虑所形成的乡村组织方式,在消除那些因前者而造成的社会不和谐音,强化人民团结的同时,农村传统的父权制家庭结构下女性如何摆脱男权压制,进一步得到解放的理论命题被弱化了。作为一种可能的结果,在贝尔登的故事中,金花或许将不是以打跑丈夫、规划自己的新生活作为结局,而是为避免农村矛盾,和她的丈夫、公婆勉强生活下去,尽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将不能如以前那样虐待她。
二、延安“新女性”和离婚事件
“四三决定”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倾向,是把农村妇女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整个妇女工作的核心地位。它发出号召,要求“妇女工作者”、“女党员”、“机关里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女干部”(被称为延安“新女性”),“深入农村去组织妇女生产”。整风运动之后,“新女性”经历了向工农兵立场的转移,旧有的自由主义倾向得以转变,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相应地,“新女性”所关注的性别问题,也因此被搁置起来。
在此之前,最有代表性和争议性的“新女性”是1942年3月9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杂文《“三八节”有感》的作家丁玲。尽管丁玲并非“妇女工作者”,但她提出的却是女性问题,且其关注的对象是当时的革命政权未公开讨论的性别观念及延安“新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上的两难处境。
《“三八节”有感》是丁玲即将卸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之职前写就的杂文⑥。她曾这样回忆文章的写作经过:“3月7日,陈企霞派人送信来,一定要我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我连夜挥就,把当时我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出来了”[6]。丁玲提及的两起“离婚事件”无法找到具体的文字材料。但尼姆·威尔斯提供的一则材料或可作为参照: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仅仅由于美学上的理由”,提出和“曾随他长征,而且刚生了一个壮实的男孩”的妻子离婚。这一事件在延安引发了争论和“斗争”[7](pp.166~168)。丁玲几乎将她全部的同情都倾注于为婚姻和生育、育儿所拖累的女性身上。她充满感情地写道:“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进而她发出了曾饱受批评的呼吁:“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在描述延安女性的处境时,丁玲格外强调“社会”而非“个人”因素:她批评包围延安女性的各种说法中的性别观念——“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非议”;她更批判结了婚且生了小孩的女性之间的不平等——“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了家庭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6];更重要的是,她提出在离婚问题上不应该简单地批评女性“落后”,而应该“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显然,强调社会因素的丁玲认为造成女性“落后”的因素之一,在于革命政权没有提供保障性措施来分担女性因怀孕、养育孩子而遭受的尴尬;另一更重要的因素是一种普遍的观念,即女性“天然”应该怀孕、生育和抚养孩子还包括照顾男性,女性因承担这些“看不见”的额外负担而付出的代价,被看作是应该的。因此即使一些女性愿意放弃社会工作做一个“贤妻良母”,她“落后”于革命时代的命运也并不被人同情。
丁玲就离婚事件提出的女性问题,不仅涉及到男女两性关系,而且特别关注已婚且生育的女性群体在家务劳动上遭遇的歧视和性别压迫。与农村女性相比,延安新女性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走出家庭”的问题,而是在拥有社会工作之后,迫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而承受的身体、心理压力,以及被迫“退回家庭”之后遭受的歧视。当丁玲指责延安女性永远处在流言蜚语的包围之中,且同情所有女性时,她强调的是,尽管延安“新女性”获得了与延安男性同等的社会工作权利,“延安的妇女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但那些制约她们的性别观念仍然存在,那些来自“男同志”的讥讽,或许是更能引起身处革命圣地的丁玲的愤怒的;而她关于已婚且生育的女性所受到的家庭牵累,则更触及家庭结构内部的性别关系模式。丁玲在此提出的问题,正是当时关于女性解放提出的解决方案——即通过赋予女性社会工作权利、参与社会事务来获得解放——所没有涵盖到的。性别观念并没有作为独立的问题在延安得到讨论,但从相关的史料中仍可隐约看出一些端倪。经常被提及的是红一方面军的30位女性高层领导⑦。尼姆·威尔斯写道,这些女性所赢得的重要地位,是因为她们“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自己赢得了在红星下的合法地位”。她并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对待大小问题,她们都是志同道合的集体。红军中只有真正有胆识的勇士才敢在大小问题上冒犯这个集体。”这些女性的团结一致,颇有意味地显露出女性革命者在性别问题上自觉的一面。但一方面,她们显赫的地位也笼罩在“作为苏维埃上层领导人的亲密伴侣和多年的老战友”这样的看法下,另一方面,在生育问题上,这30位女性或为避免麻烦,大多采取不生育,如康克清;或即使生育,也几乎无力照料孩子,如刘群先;或因身体虚弱和生育退回家中,如贺子珍。从这些相关的史实来看,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提出的问题并非虚词。
尽管丁玲的立场称不上是“女性/女权主义”,但她赋予女性特别的同情,她对于性别观念的敏感,以及对于造成女性弱势地位的“社会”因素的强调,都使她提出的性别问题有一定的真实性,不过与“妇女主义”存在的问题一样,丁玲一味地关注女性而忽略了中心的政治任务。因此,她和她的《“三八节”有感》在整风运动中遭到批判,只因受到毛泽东的保护才得以幸免。在检讨文章中,丁玲仍旧拒绝否定自己提出问题的真实性:“我在那篇文章中,安置了我多年的痛苦和寄予了热切的希望”,但承认“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党的立场说话”,而重新摆正“党”和“女性”的位置[8]。丁玲在女性问题上和延安时期主流观念间的差异,最终的解决方式,便是搁置性别问题,以“党性和党的立场”作为收束,这固然是当时革命形式的需要,但是这种性别方式,也使得隐约呈现的性别问题被遮蔽了。这种差异留下的余音,构成此后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问题,也是今天重新清理这段历史借以提出问题并展开理论讨论的空间。
三、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结合
不仅是延安新政策,事实上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都倾向于把妇女解放作为整个民族解放和阶级运动的现代化议程的统合而非分离的部分。从1920年代向警予等左翼领袖把妇女运动纳入劳工运动开始,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一直包含着一种潜在的冲突。蔡畅在1951年回顾共产党与妇女运动之关系时,提及的“右”和“左”两种错误倾向大致可以看出冲突的关键所在。“右”的倾向即“以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观点”,“只和上层妇女进行团结”,“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而“脱离了广大工农劳动妇女”;而所谓“左”的倾向,则是“将妇女运动突出,把它从整个的革命斗争中孤立起来,离开当时的中心政治任务来谈妇女解放”[9]。一是妇女内部的阶级差异,一是妇女运动和“党的中心政治任务”的关系,蔡畅的倾向性是明确的,既强调“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比“资产阶级妇女运动”重要,同时强调妇女运动必须服从党的中心工作。其中蕴涵的恰是阶级/性别议题的结合以及以何种方式结合的问题。
如果说阶级/性别议题的结合的问题不只表现于“四三决定”之中(“四三决定”不过表现得更明显并将其制度化),而有着更深远的历史脉络的话,则可以追溯到五四后期左翼革命话语如何整合女性话语,尤其是整合现代都市激进女性文化的方式。在此,丁玲还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恰当个案。作为后五四时代的都市知识女性,丁玲在她早期的作品中,相当清晰地表现了对现代都市资本体制中女性“色相化”处境的自觉。她的处女作《梦柯》(1927)以遭性骚扰的女模特事件为开端,以梦柯清醒地被迫步入由男性色相目光所构造的“女明星”位置而结束,显露出女性所遭遇的制度化的性别压制处境。罗岗相当有趣地借用“技术化观视”这一范畴,提出“丁玲不是在理性的层面上讨论‘娜拉走后怎样’,而是在都市的消费文化、社会的‘凝视’逻辑和女性的阶级分化等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把抽象的‘解放’口号加以‘语境化’了”[10]。丁玲后来陆续在《莎菲女士的日记》 (1928)、《阿毛姑娘》(1928)等作品中,深化了她在《梦柯》中提出的女性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期,有着激进女性立场的丁玲转向革命。就革命的本义来说,如果丁玲早期小说显露的是资本体制和男权体制的结盟,则女性解放势必应该在颠覆双重压制(性别和阶级)的意义上提出。但当时的权威左翼理论家冯雪峰在判定丁玲早期小说的性别批判的意义时,却认为那仅仅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传播的那种最庸俗和最堕落的资产阶级的‘恋爱文化’”[11]。即通过将激进女性文化指认为“资产阶级的”和“殖民主义的”,而取消其合法性。就更普遍的历史意义而言,冯雪峰的判断并非武断,而与第三世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女性主义理论暧昧的现代性特征联系在一起,即这种源自西方的以中产阶级女性作为主体想象的激进理论,显然需要更为复杂的转换环节才能得到“半殖民地”时期中国的阶级解放理论的认可。而这种“转换”无论在作为左翼理论家的冯雪峰还是在激进女作家丁玲那里,都没有成为自觉的问题。这不仅造成丁玲“向左转”后的革命小说取消了女性视点和性别议题的个人原因,也可以说是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简单取消激进女性文化的历史原因之一。
“延安道路”对性别问题的态度,事实上也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依据的妇女解放理论有着密切关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侧重从经济角度关注与工作相关的妇女问题,并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指认为资本制度,因此,解放妇女的实践方案就是鼓励妇女进入公共劳动领域。类似的妇女解放观念同样被实践于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把建立和建设独立的民族国家政权作为目标,并且动员“半数的女同胞积极参加”,但这种动员是以“男女都一样”的方式提出的,而女性的特殊问题和性别要求没有受到特别重视。从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展开的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来说,相当程度地借重了传统的家庭结构,也就是说,至少在乡村家庭中,男权中心的性别模式依然存在,女性介入公共领域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往往是在不改变家庭内部的性别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做法虽然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自主性,但也导致女性的双重负担问题,即在承担社会工作的同时,承担家庭劳动。如果说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始终将女性解放作为阶级解放的同一议题的话,那么在对待家庭父权制的方式上,则显示出女性解放与阶级/民族国家解放的不同面向。于是,当代女性主义者提出不仅应当对资本制度提出批判,同时也应该向父权制挑战,妇女解放应该在反抗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两个战场”作战[12]。由此,以更为积极的方式把女性主义结合进社会主义实践。类似发生于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界的讨论,或可作为思考中国妇女运动历史的参照。
收稿日期:2006-07-03
注释:
①参见[美]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②参见《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该书指出当时的农村政策“将农民问题视为男性村民的问题”,同时著者检讨道:“《延安道路》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后来的研究者所出版的著作都没有认真探讨性别及家庭问题。迄今人们对这些问题依然语焉不详”。第 270页。
③1943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组织了纪念“三八妇女节”会议,农村妇女们“手里打着毛衣、纳着鞋底、织着袜子,以崭新的姿态庆祝自己的节日”,并评选出7位农村妇女作为“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多少年来被人们所轻视的妇女竟成为英雄,这巨大的变化实在太令人兴奋了,整个边区为之轰动”(《中国妇女运动史》,第514页)。
④参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第508-519页,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⑤[瑞典]达格芬·嘉图:《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杨建立等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年)中提到“老中年妇女却在生产运动中占据着领导地位。这是由于后者有熟练的纺织技术,纺织是她们主要的生产活动,她们是‘劳动群众中仅有的有足够资金购买纺车、织机和其他设备以及原材料的人’。地主和富农出身的妇女也成为妇女协会的成员”(第281页)。
⑥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丁玲刚刚和陈明结婚不久(1942年2月),陈明是离开妻儿与丁玲结合的。参见周良沛《丁玲传》,第427页,十月出版社1993年版。
⑦参阅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6年版。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丁玲论文; 解放日报论文; 家庭论文; 社会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