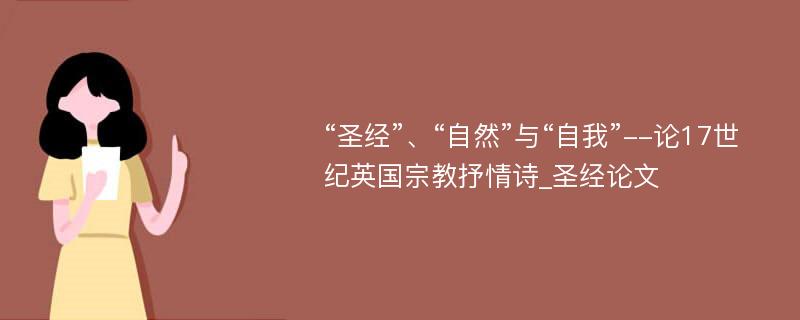
圣经、大自然与自我——简论17世纪英国宗教抒情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抒情诗论文,英国论文,圣经论文,大自然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610年,乔治·赫伯特从剑桥寄给他母亲一首十四行诗作为新年礼物,他在诗中说他要把自己全部的爱献给上帝,用他的诗使神坛兴旺,同时指责众多世俗爱情诗的粗制滥造,并哀叹“仰望上帝和天国的诗歌”寥寥无几。他写道:
难道诗歌
都穿上维纳斯仆人的制服?只为她服务?
为什么十四行诗不为你写出?并放在你那燃烧的圣坛上?
以上数行诗无疑是对传统爱情诗人的挑战。赫伯特把炽烈的爱转向上帝:“你就是我的美人,我的生命,我的光明”(《阴郁》)。他以全部的热忱追求着,精疲力竭,屈膝下跪,泪如泉涌地呼唤着他“心中的爱”和“灵魂的主”(《渴望》),渴望与“爱人”相聚(《探求》)。另一方面,他反对世俗诗歌的浮夸,摈弃世俗诗人甜腻的辞藻和比喻。主张朴实无华的风格。他在《约旦》(一)中表明,朴素的真理就是美,而诗歌应当反映神圣的真理:
我不钦羡别人的夜莺或春天,
让他们痛斥我毫无韵律吧,
我率直地说:我的神,我的王。
最后一行的后半句乃是《诗篇》(145∶1)中“神,我的王,我要宣扬你的伟大”的回声。诗人把自己与大卫联系在一起,试图召唤人们直接把《圣经》作为诗歌的典范和灵感的源泉。他本人身体力行,毕生只写虔诚诗歌。他的诗集《圣殿》(1633)不仅描绘了教堂门厅、圣坛、纪念碑、锁钥、地板和窗户的建筑之美,也描绘了在教堂中举行的与基督一生有关的宗教节庆和仪式,如圣诞节、受难日、复活节、洗礼、圣餐、降灵节和礼拜日,并挖掘这些庆典仪式的精神涵义,而渗透其间的则是诗人的虔诚冥想。
赫伯特或许受到约翰·多恩的影响。多恩比他年长21岁,是他母亲的好友。多恩出任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后,便由早年的世俗诗歌转向宗教诗歌的写作,创作了《圣十四行诗》和《献给基督的歌》等宗教诗篇。不过,赫伯特产生的影响更为广泛。据说亨利·沃恩几乎能将《圣殿》中的诗篇倒背如流,他在《闪光的燧石》(1650)“自序”中赞扬赫伯特是“成功地力图把那肮脏、泛滥的淫秽诗歌的溪流转为神圣之用的首创者”,因此他不仅对赫伯特作了大量借鉴,而且反映了赫伯特的诗学观点。理查德·克拉肖把自己的诗集献给赫伯特,并取名为《通向圣殿的台阶》(1646)。克里斯托弗·哈维的《犹太教堂》(1648)又称为《圣殿的影子》,甚至赫里克的《崇高诗歌集》(1647)也包含对赫伯特的众多模仿。总之,以赫伯特为典型代表的一批诗人卓有成效地开创了英国文学史上宗教抒情诗的鼎盛时期,使17世纪上半叶的宗教抒情诗与爱情诗同放异彩,成为当时英国诗坛上两颗璀璨的明珠。
宗教抒情诗的繁荣与英国当时的政治和宗教斗争密切相关。16世纪充满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矛盾,充满天主教和新教的冲突,而到17世纪上半叶,新教内部又爆发了国教与清教之间的激烈斗争,最终导致清教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斗争对17世纪宗教诗人产生了多方面影响。首先,他们收获了16世纪宗教改革和宗教冲突的果实(加德纳,192—193页)。由于伊丽莎白时代的统治采取了温和的折衷主义,宗教诗人们获得了较大的精神自由。他们不仅可从天主教的信仰和虔诚诗歌中吸取灵感,而且也可吸收作为新教灵感源泉的圣经语言,甚至还可借鉴早期基督教作家的神学著作。这就形成一种超教派的精神,使宗教诗歌的创作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其次,这一时期的文化氛围也有利于宗教诗歌的发展。1611年钦定本《圣经》的问世,以及布道文和寓意画册的涌现,都为宗教诗人提供了权威依据和重要参考。第三,在这充满纷争的时期,不少诗人感受到强烈的痛苦,失去了精神的平衡。譬如,多恩说他“最初的教育和交往是与被压制、受迫害的宗教信徒联系在一起的,习惯于受到死亡的威胁,想象中渴望成为殉教者(《论自杀》),而沃恩也因获胜的共和派所强加的一种不同的宗教秩序而遁入威尔士乡间。他们在诗中不仅表达了个人的痛苦,而且反映出时代的特征。正如布鲁斯·金所指出的,面对社会大动荡的局面,许多诗人纷纷逃离城市,退隐乡间,思考着自我的拯救,沉溺于宗教的沉思,以获得内心的宁静和灵魂的慰籍(King,127)。总之,为了逃避现实的痛苦, 这些诗人都把视线转向内心。这种状况必然促使宗教诗歌朝内省的、沉思的、忏悔式的抒情诗方向发展。
勒古伊把这一时期的英国诗人按其社会倾向和宗教派别加以划分。除骑士派诗人外,他把克拉肖等列入天主教诗人,把多恩、赫伯特和沃恩等列入国教诗人,把马维尔等列入清教诗人(Legouis,559—580 )。这种划分虽可说明他们的某些不同,但他们其实都是在共同的新教传统下成长起来的。多恩虽出身于天主教家庭,但后来改信了国教。克拉肖是清教传道士的儿子,后来虽成为天主教徒,但先前无疑也受过新教影响(加德纳,195页)。因此,新教观念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 诚然,这些诗人表现了各自的特色(Gottlieb,57—59)。譬如,赫伯特认为上帝完成了为人的拯救所必需的一切,在人与上帝的相互关系中,后者是主动的参考者,因而赫伯特在诗中表现了一种奇特的爱,他所描绘的不是灵魂对上帝的追求,而是上帝对灵魂的追求。这种思想是宗教改革强调的重点,它把路德教、加尔文教和早期国教联系在一起。诗中的说话者往往迷失路途,向错误方向跑去,直到上帝闯进诗中干预,并创造某种与人的关系,诸如主仆、父子、朋友,以及新郎和新娘之间的关系。多恩倾向于阿米纽观点,认为人的意志必须选择是否接受神恩,并与之合作,因而他经常表现“处于天堂与地狱刀尖上的灵魂”,在上帝和罪孽之间进行着痛苦的选择。那种内省的倾向,意志的折磨,激烈的冲突和犹豫不决,构成了情感强烈而复杂的宗教诗歌。沃恩则倾向于用新柏拉图主义说明超然灵性:从这“黑暗”的世界飞向那“永恒”的“纯净无边的光明”(《世界》)。然而,这些诗人所反映的普遍倾向却是新教、甚至是加尔文教观点。麦卡杜在《英国国教精神》中指出,加尔文教在英国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直至17世纪中叶。国教和清教之间的斗争是以教会秩序而不是以教义问题发端的。事实上,“伊丽莎白时代的主教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加尔文教徒”,而且“劳德的倒台和西敏寺大会的召开(1642)标志着加尔文教在英国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转引自Lewalski,13页)。这就表明,在某种意义上,国教教义在王朝复辟以前并未成为现实。可以说,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英国教会的神学基调是清教,甚至是加尔文教。因此,清教或加尔文教主张信徒通过沉思和精神生活与上帝直接交流而获得拯救的模式,决定了17世纪英国宗教沉思诗的基本发展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新教诗人在注重内心生活方面与欧洲天主教有两大不同。首先,他们将《圣经》看作解释一切主题的准绳,并认为它提供了沉思的典范,如大卫日夜沉思神的律法,又如以撒被奉为沉思的楷模,他“黄昏时在田间沉思”(《创世纪》24∶63)。因此,沉思诗主要是对《圣经》的沉思。《诗篇》(119∶97)说:“哦, 我多么爱慕你的律法,我整天默想着它。”《约书亚书》(1∶8)也告诫信徒:“你要诵读这本律法书,昼夜思考。”这些都是宗教诗人的权威性依据。其次,新教诗人强调将《圣经》用于自我内心的探索,其方式也与欧洲天主教不同。天主教沉思者寻求把自我用于主题,并参与其中。他想象一个仿佛正在眼前发生的场景,随后分析主题,激起对该场景、事件或自我精神状态的情感。但新教沉思者却相反,他不是把自我用于主题,而是把主题用于自我(Lewalski,148)。但是, 除了对《圣经》的沉思外,还有对大自然的沉思。托马斯·布朗说:“世界上有两本书,从这两本书里我获得神学,一本是上帝写的,另一本是上帝的仆人大自然”(《医生的宗教》1.16)。这就是通常所指的“上帝之书”和“自然之书”。新教诗人把两者都用于自我的沉思。约瑟夫·霍尔在《沉思的艺术》(1607)中将沉思诗分为两种:是熟思的(deliberate),一是应景的(occasional)。前者以《圣经》为出发点,旨在将《圣经》中的文句或事件运用于自我精神的探索。后者以自然景物或个人生活事件为出发点,运用《圣经》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Lewalski,150—151)。这两种类型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明显地涉及沉思的三个对象:《圣经》、大自然与自我。据此,沉思诗也可分为三类,即《圣经》沉思诗、大自然沉思诗、自我沉思诗。但是,无论属于何种类型,诗中都贯穿着“堕落—再生”的基本主题。
第一类是对《圣经》文句的沉思。赫伯特的诗篇大多是沉思《圣经》的产物,有些标题就指明《圣经》引语的出处,如《珍珠·〈马太福音〉13∶45》。查看一下《圣经》就知道此处所指的原文是:“天国又好像一个商人,四处觅购圆净的明珠。当他找到一颗价值连城的珍珠时,就变卖一切产业,来买下它。”不难理解,“珍珠”隐喻天国,而买下珍珠则意味着获得天国。此诗就是对这句话的沉思:诗人受到各种尘世事物的诱惑,如对学问、荣名和享乐的爱,但终于抵制了一切诱惑,放弃了一切世俗的爱,只保留对上帝的爱。最后他说:“你从天堂向我垂下来的丝线/既指引又教导我,如何跟着它/向你攀登。”诗人借用希腊神话中忒修斯凭着阿里阿德涅所赠的线走出迷宫的故事,说明他依靠上帝从天国挂下来的一根丝线的引导,穿过尘世的迷宫,升登天国。换言之,他“变卖一切产业”,买回了天堂。又如沃恩的《黎明》一诗,其标题虽未引《圣经》文句,但开头数行就暗示十个伴娘等待新郎的寓言(《马太福音》25∶1—13)。在该寓言的结尾, 基督告诫说:“你们要提高警惕,因为你们都不知道我回来的日子和时间。”对此,诗人最初的反应是“呵,您何时到来?何时那‘新娘来啦!’的喊声响彻天宇?”接着便想象“新娘”在不同时间到来的情景。最后,一个自然象征——“一边歌唱、一边驰过白昼和夜晚”的“春天”——告诉他对待神恩的应有态度,即他不应考虑时间,而应时刻准备观望那“白昼的破晓”。这是对《圣经》所载关于基督再临的沉思,表达了诗人对于拯救的渴望。
这类诗歌经常描述对《圣经》所载基督一生中富有象征性事件的沉思。冥想的诗人并不注重事件本身的细节,而是把对事件的沉思与《圣经》联系起来,旨在理解拯救的模式。赫伯特著名的两节图形诗《复活节翅膀》既是对《圣经》所载基督复活事件的沉思,又是对拯救模式的理解。第一节写道:
造人的上帝给人丰裕生活,
但愚蠢的人把它丧失,
就因为日益堕落
最后竟至于
极落魄;
让我像
宛转的云雀
和你呀同上天堂
并歌唱今日你的胜利:
于是堕落更促我奋飞向上。
(黄皋炘译)
诗人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并赐与他财富和宝藏,但人却因亚当的罪而失去乐园;然而,这一堕落并非绝对不幸,因为《圣经》上说,“罪恶愈增,就更显恩典之丰富”(《罗马书》5∶20)。 人倘能像云雀展翅升腾,歌唱基督的胜利,那么堕落就更能促人“奋飞向上”。第二节进一步说明,由于神用疾病和羞耻惩罚人的罪孽,人变得瘦骨嶙峋;但人倘能与基督“结合”,分享基督的胜利,那么痛苦就更能促人“奋飞向上”,因为《圣经》上说,通过痛苦,心灵将“仰望主”,并因“重新得力”而“展翅上腾”(《以赛亚书》40∶31)。这首诗产生了鲜明的视觉效果,其版面形式不仅像云雀翱翔的翅膀,而且“下半部从窄到宽的形式”也暗示“由贫到富、由弱到强”的含义(Keast,232—234 ),从而加强了诗中“堕落—再生”的主题。实际上,赫伯特《圣殿》中从《牺牲》到《复活节》构成了对基督受难事件的一系列沉思诗篇。
在这类诗歌中,对圣餐的沉思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主题。就像对基督受难的沉思那样,这类诗歌也强调基督的牺牲对人的影响。根据基督教传统,参加圣餐者切面包时要想到基督破裂的身体,倒酒时要想到基督流洒的血。人因基督受难而得救,所以应当忏悔自己的罪孽。在处理这一主题时,诗人们侧重于描绘基督所受的极大痛苦。赫伯特在《痛苦》中写道:“谁不知道爱,就让他试着/尝尝那汁液,它在十字架上由一支矛/穿透而流出来。”他还给爱下了定义:“爱是那甜蜜神圣的酒,/我的上帝感到是血;而我感到是酒。”但诗人们也同样侧重于沉思基督对人的深爱。赫伯特在《爱》中刻划了最富人情味的基督。他把基督化为“爱”,并以日常生活中的主人和客人来比喻救主与罪人。主人热情地欢迎一个旅途劳顿的客人,客人却自觉“有罪”,深感卑微而不相称,准备离去。但仁慈的主人说他已因忏悔而赎了罪,并坚持请他共进“圣餐”:
“你得坐下,”爱说,“尝尝我的肉。”
于是,我坐下来享受。
客人的矛盾心理一扫而空,坦然接受了主人的慷慨。诗中的宴席不仅暗示教堂的圣餐式,而且象征《圣经》中的天国宴席:神“束上腰带,请他们上座,亲自侍候他们”(《路加福音》12∶37)。显然,这首诗既是对教堂的圣餐式、又是对《圣经》中有关文句的沉思,但诗人却以主客之间的戏剧性对话表现了神的鼓励与深爱,以及自己的谦卑和对神的感恩和赞颂。
除《圣经》外,诗人们也喜爱把“自然之书”作为沉思对象,并把《诗篇》(104)中对伟大造物主的赞颂视为大自然沉思诗的典范。 对这类沉思诗人来说,大自然既富有道德寓意,又是神圣真理的体现。罗伯特·博伊尔提出人人都应成为伊索,把世间万物变成“伦理教师”或“神学博士”,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圣坛”,世间万物成为诲人不倦的“牧师”;加尔文则认为宇宙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窥见上帝(Lewalski,163)。在这方面,沃恩堪称一位代表人物。 如果说赫伯特在灵魂中建立了庄严的“圣殿”,那么沃恩则把“圣殿”建筑在大自然之中。他在日月星辰、草木流泉、山林砂石和鸟兽鱼虫之中获得教益。他把人的堕落与大自然的清纯加以对照,表明卑俗的造物远比人类优越,是人类学习的楷模。他赞美飞鸟、蜜蜂和花草的沉静稳定,鸟儿“像时钟一样把时代无声的日子和运行划分”,蜜蜂趁着夜色返回蜂房,花朵随着太阳起身,日落时又“幽闭在同一间闺房”。这些造物井然有序,固守着“神的旨意”,任什么都不能“打破它们的宁静”。对照之下,人“没有根”,只有“无休止的奔波”,四处飘泊,忘却“归路”,陷于混乱不安的状态。因此,诗人希望神也把那些俗物的品性“赐与人类”(《人》)。不仅如此,他也把自然界的造物视为神圣真理的体现。他描写潺潺的流水“踌躇不前”地“落下”峭壁,暗示人对死亡的恐惧。但他注意到落下的每颗水珠又都返回它所来自的那条光辉的溪流,于是想象他的灵魂也将同样返回它所来自的光辉的源头。他看到水珠落在水面形成的圆圈扩展到岸边后消失不见,认为这暗示人也将如此,逐渐走向天国的“无形境界”。这种境界在大自然中是不能直接看到的,只有通过沉思才能抵达(《瀑布》)。因此,他坚信沉思是理解自然界神秘象征的渠道,也是飞升天国的途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万物的“幕罩和影像”中看到了“神圣的路”,他将沿着那些“隐秘的阶梯”攀登,直到看见露出上帝曙光的那一天(《数日前的散步》)。他常从一种景象转入另一种景象,把自然景物同《圣经》和沉思融为一体,着重探索死亡与复活的寓意,说明“堕落—再生”的主题。
对《圣经》或对大自然的沉思都紧扣诗人自我“心灵的剖析”,因而又构成另一种独立的自我沉思诗。在处理这类主题时,诗人们经常表现沉思过程中的强烈情感。多恩《神圣十四行诗》第十四首是个典型的例子:
粉碎我的心吧,三位一体的上帝;迄今
你只轻敲、吹气、照耀、设法修补;
为了让我能站起来,毁灭我吧,鼓足
你的气力打碎、猛吹、猛烧,使我获得新生。
这首诗明显涉及“再生”主题(“使我获得新生”)。诗人首先请求神用全部力量“粉碎”他的心。神一般是“轻敲”门未召唤人的(《启示录》3∶20),诗人却要神“打碎”他的门; 神一般通过轻轻“吹气”把灵送入人体(《创世纪》2∶7;《约翰福音》20∶22),诗人却要神“猛吹”他;基督徒须不断祈祷才能使神的容光“照耀”他(《诗篇》80∶3,7,19),诗人却要神“猛烧”他。仅仅“修补”不足以使他得救,只有通过暴力才能使他“获得新生”。诗人之所以要神对他施用暴力,是因为他内心的堕落状况:他的灵魂犹如被敌攻占的城池,或落入敌手的女子,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救。随后,诗人又采用《雅歌》中新郎(基督)和新娘(灵魂)的隐喻,说明“新娘”不贞,已同基督的仇敌(撒但)订亲。因此,诗人说:“把我拉到你身边,把我关起来,因为我,/除非你奴役我,我是永远不会自由的,/永远不会贞洁,除非你对我施用暴力。”这首诗自始至终都是对《圣经》的沉思,同时也明确地表达了新教观点,即人在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因“原罪”而无能为力,他凭靠自身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必然是邪恶的,因此必须完全依赖神恩才能得救。
自我沉思诗也常涉及个人生活中的某些事件。譬如,多恩于1619年奉邓卡斯特侯爵之命作为牧师赶赴德国,临行前写下了沉思这一事件的《基督赞美诗》。他一开头就采用象征手法:
无论我登上什么颠簸的船,
对于我,那船就象征你的方舟;
无论什么海洋将我吞没,那洪水
对于我就象征你的血
尽管你以愤怒的阴云遮住
你的脸;但透过那面罩我知道那双眼睛,
它们虽然有时转向他处,
却决不会有蔑视的目光。
诗人把自己喻为生命海洋上被风暴摇撼、受洪水威胁的船只,他想象自己是即将经历一场新的洪水的新的方舟。那洪水是基督的血,他那船是获得精神拯救的工具,它将载他离开他所熟悉的世界。他的世界充满了引诱他偏离上帝之爱的事物,如荣名、机智和其他各种世俗的爱。他牺牲这个世界,出海远航,而离开这个世界,就可把他的爱集中在上帝身上,因而更能获得拯救的希望。以出海远航及其危险来象征放弃尘世去寻找上帝,也意味着在生命的“冬天”向死亡航行,从而最终逃离人生的风暴,进入永恒:“为了只看见上帝,我在视线中消失:/为了逃避风暴的日子,我选择/永恒的夜。”诗人把大海、风暴、船只、黑夜,都用作沉思的素材,深入分析其精神内涵,把“堕落—再生”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
值得注意的是,在表现上述各类主题时,17世纪沉思诗似乎具有相似的发展模式和艺术结构。马尔茨把17世纪主要诗人与反宗教改革和中世纪欧洲沉思传统联系在一起(Martz,25—26、145—149、249 —259)。然而,除欧洲大陆天主教作家的影响外,我们或许更应重视英国本土业已发展了的新教沉思传统。莱瓦尔斯基指出,有些批评家把宗教沉思与短小的随笔联系在一起,认为培根用拉丁文写的《宗教沉思集》(1597)提供了范例。他的十二篇沉思文涉及教义和宗教实践的各个方面,其典型模式是:开头一个警句,接着陈述一段《圣经》文句,然后根据所引经文来分析主题。这就形成一种“警句—经文—分析”的模式。霍尔在《沉思与誓言》(1605)和《神圣的观察》(1607)中就像培根那样,以源自《圣经》或源自大自然观察的格言警句开始,然后用几句话分析其内涵。他的《应景沉思集》(1633)中的沉思文相当于篇幅较长的随笔,每篇有一两个长段落,最后是祝祷。艾萨克·安布罗斯的应景沉思是篇幅较短的散文,往往是一种独白或自我谈话。这些模式对英国沉思诗的形式和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Lewalski,148—152)。
然而,沉思诗与布道文的关系或许更为密切。当时布道文的繁荣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第14卷,807 页)的一段记载可见一斑:
对布道文的贪求,至少在城市里,好象是永远也满足不了似的。亨利·史密斯,绰号“银舌”的作品,1589—1637年间,至少刊印了 128版,各版所收互有出入;清教传教士威廉·泊金斯的作品在1640年前,也出过128版。与此对比, 在同一时期内莎士比亚的作品出了约90版,马娄的31版,斯宾塞的19版……布道文不仅是拯救人类灵魂的工具;对当时英国人来说,布道文是政治情报和政治看法的主要来源,在革命的英国,它对民众的意义是极为可观的。(杨周翰译)
布道文的结构从中世纪起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模式。首先是选定经文作为题目,然后有一段简短的题前话或绪言,简要说明这次布道的意义,使听众的注意集中。再次介绍主题,主题分三部分讲。最后是“发挥”或“结束”(杨周翰,114—115页)。布道文在总体上包含两个基本部分和两个基本目的:一个部分是提出论点,对经文或教义进行分析,旨在指导人们深入理解;另一部分是把主题强有力地用于自我,旨在激起内心的情感。沉思也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布道”和“沉思”两个词语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在两个部分中,前一部分的分析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后一部分激起情感则是沉思的灵魂。从形式上说,理查德·巴克斯指出,沉思的两部分称为“沉思”和“独白”,最后加上“祝祷”。“独白”乃是为自己的灵魂向神祈求,这也是一种“自我布道”。“祝祷”则是对上帝讲话,以保持自己的崇敬、严肃的警觉状态。这样,沉思的模式可以归纳为“沉思+独白+祝祷”。托马斯·古德文提出,在沉思《圣经》时应把“独白”变成与经文的一种“对话”(Lewalski,155)。换言之,也就是“独白+自我布道+对话”。
赫伯特的《项圈》或许十分典型。诗人将“项圈”作为受到束缚的象征,他感到自己处于奴仆地位,他的生活受到种种义务和要求的束缚,因而产生对神的反叛情绪,牢骚满腹,甚至“胡言乱语”。但正当他的情绪越来越激烈时,最后两行中却出现一个戏剧性的突变:他仿佛听见神在呼唤他:“孩子!”于是他赶忙回答:“我的主。”在这里,“孩子”暗指《圣经》中保罗的话:“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儿女,当然有继承权了”(《罗马书》8∶16—17)。想到这段话, 诗人内心的风暴立即平息,因为他认识到神与他的关系不只是主仆关系,也是父子关系。他起初不肯接受主仆关系,但当他意识到自己是神的儿女和天国的继承者时,便乐于接受主仆关系了。显然,诗人通过对《圣经》的沉思解决了自己的思想冲突,而在形式上则表现为诗人与《圣经》(或上帝)的“对话”。
多恩的《病中赞上帝,我的上帝》也明显地遵循类似的模式。多恩在此诗中沉思自己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在1623或1631年左右身患的重病。一开头,他采用音乐意象渲染死前的氛围。他仿佛看见自己即将到达生命的终点,在那里他不仅将参加天堂的合唱,他本身也将是天堂音乐的一部分。因此,他此刻不打算歌唱,而要在死神的“门口”预先调谐他的乐器,在这过程中没有歌唱,只有“事先的思考”,即“沉思”。诗的主体就是描写这种沉思的。首先,他把想象的死亡场景变成了一种象征,一堂解剖课:医生们观察他,犹如宇宙志学者观察地图。他把对病况的探索喻为地理探索:如同麦哲伦向西南航行,穿过风暴的海峡,最后死在西行途中那样,他对病况的探索也导致他“在西南的发现”,他将穿过“发烧海峡”,并在“西方”的“海峡”附近死去。这种比喻又使他产生了充满希望的联想:他现在躺在床上,犹如平面地图,地图上东、西两端吻合,从而暗示“死亡”(西)和“再生”(东)也是相互连接的。随后,“发烧海峡”又使他想到传说中的乐园究竟座落何处。但无论它位于何处,都只有穿过“海峡”才能抵达。传说中的乐园和耶稣受难处、亚当的树和基督的十字架都在同一场地,而这场地不是别处,正是卧床不起、处于弥留之际的诗人自身:因为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基督)在他身上“相遇”:他在同一时刻即将因第一个亚当的罪(原罪)而死亡,又将分享第二个亚当(基督)征服死亡的胜利(Hunt,第96—117页)。诗人最后明确地说, 诗中的沉思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布道”:
让这作为我的经句,我自己的布道文;以便主提携被扔倒的人。
显然,全诗的结构是“沉思+独白”(或“自我布道”)。也许根据布道文的特点,17世纪诗人都十分重视诗的结尾。正如多恩在布道文中所说:“在诸如《诗篇》等所有的诗歌写作中,整个作品的力量主要在于结尾,诗歌的全部框架就像是一整块金子锤打出来的,但那最后一句话就像是印记,正是它才使诗歌具有活力”(转引自加德纳,198页)。换言之,诗歌的题材和冥想的场景犹如未经锤炼的金块,在诗歌主题或在沉思中提出的论点就像对金块的锤打,而“印记”则是诗歌主题所要得出的结论。
当然,“玄学派”宗教诗人尤其是以奇思妙喻著称的。他们常把看来毫无关联的意象强扭在一起,并充分挖掘每个意象的各种内涵来说明一个抽象概念,使说理和形象思维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如多恩将重病、地理探索、平面地图、海峡、乐园、基督受难处等意象全部用作沉思的素材,又把思想、感情、抽象概念和具体意象铸于一炉,最终说明“死亡—复活”的主题。有些评论家谈到早先业已发展而在17世纪更为流行的寓意画册(emblem books)的影响。寓意画册由格言、寓意画和讲解三部分组成,往往是拉丁格言、《圣经》引语,版画和英语诗歌的综合。当时最为流行的首推弗兰西斯·夸尔斯的《神和道德寓意画》(1635)。夸尔斯说,“寓意画是无声的寓言。”寓意画册对读者智力的要求同样表现在“玄学派”宗教诗人的“巧智”和“神秘性的语言、对悖论的调侃和强行联系的比喻”之中(桑德斯,314页)。因此, 寓意画的诸多特点对宗教诗人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总之,17世纪宗教诗人都很重视艺术性,他们对文学的贡献就在于他们以宗教的热忱写出了卓越的抒情诗。正如加德纳所说,重视艺术的时代也是最有利于宗教诗歌繁荣的时代(191—192页),而17世纪上半叶英国宗教抒情诗的发展就处于这样的时代。
然而,到了17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学便进入了古典主义的“理性时代”,不仅诗歌形式和风尚发生了变化,而且从内容上说,批判和讽刺的诗歌也逐渐取代了包括宗教沉思在内的抒情诗。然而,17世纪宗教沉思诗引用宗教术语、描述“宗教心理传记”的诸多特点,不仅在18世纪具有“宗教的崇高风格”的诗歌中,而且在19世纪浪漫主义作品中,甚至在20世纪现代派诗作中,都可明显地察觉到。这一切都有力地证明17世纪宗教抒情诗在英国文学发展史上所占有的不容忽视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