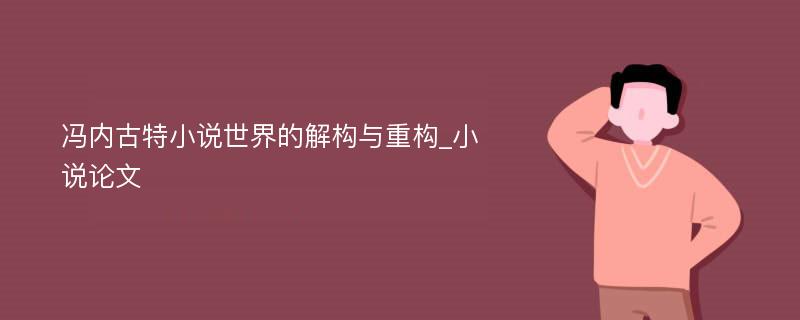
冯内古特对小说世界的解构与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论文,小说论文,冯内古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最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小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Jr.1922—)的代表作《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1969)[1] 一问世,就以其重大的主题、深刻的思想和艺术的创新立刻成为畅销书。《五号屠场》是在“较深的意义层面上,表现了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因此可被视为对一个不确定世界的暗喻。但小说中的不确定性也反映了作为小说人物的冯内古特的艺术问题,特别是反映了他多年来一直想重构并准确地、系统地表现他德累斯顿经历的努力”[2](P423)。冯内古特认为,传统小说遵循因果假设和僵化的时间与内容概念, 这种手法不适于表现德累斯顿毁灭这样一个非逻辑性的题材。他需要一种既给读者提供可以理解的叙述,又不显得是以理性解释事件的小说形式。他尤其需要一种将持续时间视为第四维的小说形式。后现代主义认为,“对于今天的世界,决定论、稳定性、有序、均衡性、渐进性和线性关系等范畴愈来愈失去效用,相反,各种各样不稳定、不确定、非连续、无序、断裂和突变现象的重要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所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们的意识:它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公式和原则以及普适的规律来说明和统治世界,主张变革和创新,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承认并容忍差异”[3](P46—47)。冯内古特在被认为是“美国后现代文学的里程碑”[4](P6) 的小说《五号屠场》中,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创新,解构了传统小说线性叙事模式,同时“提出了一种非线性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创造了历史与想像、现实与幻想、历时与共时、作者与文本之间重要的新关系”[2](P421),重建了一个后现代主义小说世界。
一、历史与想像结合
小说《五号屠场》中最引人注意并使小说独具特色的是:历史人物兼非想像的作者冯内古特出现在小说文本中。他在小说的书名页作者署名下面作了自我介绍:
小库尔特·冯内古特,现在是科德角生活舒适的第四代德裔美国人(烟吸得很凶),很久以前当过美军步兵侦察兵,当过战俘,目睹了对德国以“易北河的佛罗伦萨”而著称的德累斯顿的轰炸,幸存下来讲述这个故事。这是一部多少用大众星上讲故事的简洁的患精神分裂症风格写的小说,那里的飞碟来自和平。
第一章叙述的焦点就是历史人物冯内古特。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艺术家,一个怀旧的人。他对战时的回忆,特别是对德累斯顿平民被大批炸死的回忆,总时刻缠绕着他,引诱他非写出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不可。他描述了他多年来是怎样努力地把关于德累斯顿的各种说法拼凑起来,写成一本小说。现在,这本关于德累斯顿的战争小说终于完成了,但他对出版商表示歉意地说:“山姆,这本书又短又杂乱,因为关于大屠杀没有什么聪明的话好说。”小说的杂乱是有目的地设计的。因为它不仅是一部关于德累斯顿的小说,而且是一部关于一个在战争结束后以作家的角色编造故事和幻想时怎么也不能抹去关于战争经历和德累斯顿轰炸记忆的小说家的小说。这部小说是一个事实与虚构的混合体。冯内古特将历史与想像结合,虚构了一个名叫毕利·皮尔格里姆的人物,他不仅再次经历了冯内古特所回忆的战争,而且卷入了冯内古特的科学幻想之中。
历史人物冯内古特明显对时间飞逝的本质特别着迷,但他对时间的概念却模糊不清。他慨叹:“啊,光阴似箭。”但他却记不准到底是哪一年去看了他的老战友奥黑尔。在波士顿旅馆等飞机的那个夜晚,因“无所事事”,他又感到“时间无法消磨”。他不仅对时间和过去着迷, 而且对死亡特别专注。冯内古特用特拉华河暗喻时间流逝的本质:“关于现在,我自问:它有多宽、有多深,我有多少东西能留存。”随后,他将这一暗喻扩展到整部小说,不断地把活人描写为流淌的水,把死人描写为冻结的冰。冯内古特两次说自己的呼吸散发着“玫瑰花和芥子气的味儿”。这一形象的全部含义在小说倒数第二页清晰地表现出来:在德累斯顿的“死人坑”里,尸体因开始“腐烂,化水,发出了玫瑰花和芥子气的味儿”。冯内古特的呼吸也标志着他不能不死。这两个形象暗示,时间使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一死,生命是逐渐、不断衰朽的一种状态。
从第二章起,历史人物冯内古特就变成了虚构人物毕利情节的叙述者。但他同时作为次要人物,也几次出现在毕利情节的场景中。直到第十章即最后一章,历史人物冯内古特才再次出现。他又想起与奥黑尔的谈话,他仍然对时间概念模糊不清, 将罗伯特·肯尼迪被谋杀事件和马丁·路德·金被谋杀事件说成中间只隔一个月;而且他对死亡仍旧念念不忘。本章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描写德累斯顿“死人坑”时,叙述者在小说中第一次改变为复数第一人称:“毕利和其他人被卫兵带到废墟堆上。我当时也在那儿。奥黑尔也在那儿。我们……去废墟中的某某地点劳动。”人称数的变化表明,小说讲述的故事不仅仅是毕利的,也是叙述者的。他也遭受了被俘、营养不良和毁灭性轰炸的痛苦。他也在死人坑里干活,看到一位朋友因从废墟堆上“抢劫”了一把茶壶而被枪毙了。
虚构人物毕利与他的“创造者”——历史人物冯内古特,并且与作者冯内古特本人,有着完全相同的经历。皮尔格里姆和冯内古特都出生在1922年;他们两人都在第二次大战中德军的最后一次攻势时在卢森堡被俘,被送到德累斯顿,待在五号屠场, 在一个为孕妇生产麦芽糖浆的工厂里干活;都幸免于德累斯顿大屠杀,事件发生后帮助挖掘尸体;都在1945年退伍,回到大学里读书,后来很快结婚了。于是,毕利成为双重角色,不仅是历史人物冯内古特的面具(历史人物冯内古特也是作者冯内古特的面具),也是作者冯内古特的面具。冯内古特通过把自己当作一个人物写进小说的办法,获得了作者与第一人称叙述者之间必须存在的距离。再通过虚构毕利这个人物作为小说中的小说的主人公的办法,冯内古特进一步远离了他再现历史的痛苦感[2](P422)。有了毕利这个虚构人物,冯内古特获得了一种与他所要描写的事件的距离,使他得以用第三人称从外部观察、外部聚焦的视角,以单纯的感知方式像一部没有思想的摄像机一样,客观地、超然地表现了实际上是他亲身经历的战争的残酷和不人道:
即使毕利乘坐的这挂列车不开动,车厢也锁得严严实实的。……对在火车外面走来走去的卫兵来说,每节车厢都是单个儿的有机体。它通过它的通气孔进行吃、喝和排泄。它也通过通气孔说话或喊叫。饮水、黑面包、香肠和干酪从这儿进去,尿、屎以及语言又从这儿出来。
描述难以形容的德累斯顿轰炸,冯内古特需要更大的距离。这一场景构成小说存在的理由,读者可能会期待一种扩展的、生动的描述。但是,这一场景不仅简短,而且是用间接、多层次、多视角的方法表述的。冯内古特本人并没有看见轰炸,他是听到的,因为他当时坐在五号屠场地下很深的冷藏室里,这个冷藏室成了个很安全的防空洞。毕利也是如此:
德累斯顿被轰炸的那天晚上,他坐在冷藏室里。头顶上似乎有巨人的脚步声。原来是对轰炸目标投下了一连串烈性炸弹。一个个巨人不停地走动着。……隔一会儿,有个卫兵到楼梯口看看外面的情况,然后再走下来同其他的卫兵窃窃私语。外面是一片火海。 德累斯顿成了一朵巨大的火花啦。一切有机物,一切能燃烧的东西都被吞没了。
这一场景不仅是间接表现的,而且是被回忆起来的。回忆提供了一个二十三年的缓冲。如果说那次间接目击的轰炸是令人痛苦的,那么第二天一百个战俘和四个卫兵所面对的被完全破坏的城市则更令人痛不欲生了。为了描写这一场面,冯内古特需要比回忆所能提供的更大的距离。所以,这个场景是通过毕利在大众星上回忆起来,以讲述给蒙塔娜·怀尔德赫克的故事形式表现的。历史人物冯内古特尽可能远离他所叙述的场景,用多视角来缓冲它,最后构建出小说中回忆的故事。而作者冯内古特则通过写一个小说中的小说中回忆的故事,使自己更进一步远离那个令人痛苦的场景。而且在讲述这一重要场景之前,叙述者冯内古特撤退到了大众星的保护性幻想之中。只有从那个无时间性行星的视角,他才终于能够用艺术形式再现了缠绕他二十三年的德累斯顿轰炸的场景。冯内古特巧妙地将历史与想像结合,终于讲述出了那个难以言说的历史事实,超然地表现了现实世界中战争的恐怖、不人道和战争带来的毁灭。
二、现实与幻想结合
如何解决人类现实世界中战争与死亡这一严重问题是小说《五号屠场》的第二个主题,冯内古特运用现实与幻想结合的手法深刻地表现了这一主题。第一章中,历史人物冯内古特清醒地认识到:“战争总会有的,反对战争就像拦截冰河一样,谈何容易。 ……即令战争不像冰河那样不停地涌来,人总还是要死的。”看来,在现实世界,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了。于是,作者冯内古特利用他虚构的主人公毕利向幻想的大众星居民求教,毕利成为外星人战争与死亡世界观的主要代言人。
毕利在幻觉中自由地往返于人类世界和幻想的能见到四维空间的大众星居民的世界。毕利在纽约市广播电台的通宵节目里发表讲话,大谈挣脱时间羁绊的问题,并说他“一九六七年被一架飞碟绑架,这飞碟是从541号大众星来的”。他在写给埃廉市的《闻领袖报》的第二封信中说:
我在541号大众星知道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是:当人死去时,他只是貌似死去。他在过去仍然是非常富有活力的。因此人们送葬时哭泣是很愚蠢的。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时间一直存在,而且永远存在。
毕利接受了大众星居民对死亡的看法,于是在充满暴力、战争和死亡的现实世界中,毕利说:“如今,当我听说某人死了,我只耸耸肩,并像541号大众星生物谈到死人时那样讲一句:‘就这么回事。’”作者冯内古特也在小说中,每当叙述或描写完一个与死亡有关的事件时,就重复一下这句话,表现出一种对死亡冷漠、超然的态度,如冯内古特这样讽刺地描写地球上的战争:
炮弹在树梢上像巨雷似的轰隆隆地爆炸,扔下了如雨般的钢刀、针尖和刀片。当炮弹爆炸时,镀铜的小块铅片在树林里交叉乱舞,飕飕地飞过天空,闪电般的速度超过音速。
许多人被击毙或负了伤。就这么回事。
一个大众星居民对毕利解释说,时间“永不改变,它不需发出警告也无需解释,它只不过是时间。如果你一会儿接一会儿地看时间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大家都如同我说过的——琥珀里的虫子”。所以,对大众星居民来说,地球上居民所侈谈的“什么自由意志”完全是无意义的话。 大众星居民们知道,当他们的试飞使用新燃料飞碟的飞行员按下起动器揿钮时,整个宇宙就会被炸毁并从此消失。毕利被告知,像地球一样,大众星上也会发生战争,而且和毕利“亲眼看到的和从书本上读到的一样可怕”。针对战争能做些什么呢?大众星居民说:“我们无法阻止战争,所以干脆不看算了。我们不理睬这些战争,而把人生用来看愉快的时刻……”因此毕利感到,“在地球上阻止战争的想法也是愚蠢的”。由于接受了大众星居民的教导,“不去理会糟糕透顶的日子,专注于美好的时光”,回到现实世界中的毕利“平静地接受所谓应该发生的一切(包括他自己的死)。他抛弃了西方人关于焦虑、道德和悲剧的观点,而接受了一种平静的消极意识……”[5](P428) 冯内古特这种“消极”和“无为的苟安接受”[5](P428),实际上是对荒诞世界的无奈,是黑色幽默。
三、历时与共时结合
《五号屠场》不仅超然地表现了现实世界中战争带来的毁灭、探讨了如何解决人类现实世界中战争与死亡这一严重问题,而且以元小说的形式关注小说的虚构成分及其创作过程,通过小说创作实践来探讨小说创作理论,是一部有关小说的小说。小说中, 毕利参加了纽约一家无线电台举办的文学评论家讨论会,话题是“小说是否已经消亡的问题”。有人主张埋葬小说;有人指出,“许多读者在他们的头脑中想像不出书里描写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情景,所以作家们必须按照诺曼·梅勒的样儿去做,向公众表演他所写的东西”。看来,地球上人类世界的小说发生了危机。但毕利在发言时,避而不谈“小说在当代社会可能起的作用”,却大谈特谈飞碟和他在大众星上的所见所闻。
在大众星上,毕利学到了大众星居民的文学理论。大众星居民的时间概念产生了大众星特点的小说。既然“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时间一直存在,而且永远存在”,那么小说就可以由同时阅读的“一簇簇简洁的符号”构成。这一簇簇符号看上去就像电报。大众星居民对毕利解释说:
在541号大众星上没有电报。不过你说得对:每一簇符号是一则简明而急迫的消息,描写一桩事态,一个场景。我们阅读这些符号并不按先后顺序,而是一览无余的。所有的消息之间没有特定的联系,除非作者细心地进行加工。这样一下子读完以后,符号便在读者脑海里产生一个美丽、深刻和令人惊异的、活生生的印象。故事没有开头,没有中段,没有悬念,没有说教,没有前因,没有后果。我们的书使我们感到喜爱的是:一下子就看到许多美妙的时刻的深奥道理。
显然,大众星居民的小说不是按时间,而是按空间安排的,其松散结构,颇像电影的蒙太奇技巧。电影蒙太奇指的是一种表示一连串连续出现的意象或叠加意象的,或表示构成一个中心意象环境的相关意象之间相互关系或联系的手段,包括“多视角”、“减缓”、“剪辑”、“特写”、“全景”和“闪回”等。
冯内古特也试图写出一部“简洁的患精神分裂症风格的”大众星式的小说。他在小说《五号屠场》中运用了类似意识流的蒙太奇技巧的叙述手法。这种手法追求在人们的头脑中再现来自回忆的过去、来自感觉的现在和来自预期的未来的共时的混合。 冯内古特的生活和毕利的生活都具有着迷地回到过去的特点。像《圣经》中罗德的妻子一样,冯内古特也不顾有被化为象征死亡的盐柱子的危险,忍不住回头看。而且为了触及德累斯顿事件的核心,冯内古特感到他不得不放弃作家通常使用的历时手法——悬念、遭遇和高潮,而是运用以不同的逻辑走向未来的小说形式。这样,冯风古特放弃了小说第一章中提到的本应是他小说中传统意义上的高潮——毕利的朋友埃德加·德比“因为拿了别人的茶壶而真的在德累斯顿被枪毙了”这件事。在整部小说中,他故意事先提及各种冲突的结局,来降低悬念的重要性。如读者早早就得知毕利将在1967年被飞碟绑架到大众星上,他将在那里了解到大众星居民不同的世界观,他又将在1976年2月13日被二战期间与他一起被俘的、过分猜疑的、有残忍癖的保罗·拉扎罗开枪打死。读者甚至与毕利一起了解到了宇宙的最后命运:大众星居民将会在试验一种新型火箭燃料时意外地将宇宙炸毁。另外,毕利在时间旅行中,实际上是在幻觉中,即在意识流动中,“挣脱了时间的羁绊”:战争期间,幸存于德军最后一次强大攻势的毕利,在森林里停了下来,倚靠在一棵树上,闭上眼睛,“他的注意力开始庄严地回旋在他生命的圆弧中,到达死亡,它是紫色的火光”;“接着,毕利又回旋到活的时刻,再倒退到出生之前,这时是红色的光和噗噗声”;“然后他又回旋到活的时刻而停了下来”;这时,小毕利在被父亲扔入游泳池后,沉入水底,失去了知觉;当他模糊地意识到有人在援救自己时,他对此感到不高兴;“他从那儿作时间旅行来到一九六五年。这时他四十一岁,正在松树丘访问他衰老的母亲”;“毕利于一九六五年眨眨眼睛,便在时间上旅行到一九五八年,他参加为小联队举行的盛宴……”
可见,小说的叙述结构不是线性的,而是空间性的。小说中时间的空间化把传统小说按先后顺序叙述的事件劈成碎片,再将它们重新安排,使过去、现在和将来以颠倒的或结合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此安排的事件之所以变得空间化是因为它们在小说中“对现实的取向”不是它们在何时而是“在何地发生”。通过空间化所获得的重要效果就是同时性,即“对发生在相同时刻但不同地点的两个或更多行为的表现”[6](P423—424)。尽管读者不可能同时读完小说的所有章节,但它短篇幅混乱年代的排列、它为表现主题思想将不同时代的巧妙并置,和它复杂的意象形式结合起来,给读者创造了那样一种同时读完的效果。当读者读完这本小说几个小时后,也许只是坐了一小会儿后,会在想像中感到毕利一生中所有不同时刻就像落基山脉一样在他眼前伸展开来;而且,读者能看到作者的一生也以同样方式展现他的眼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冯内古特正在写《五号屠场》最后几页的1968年。读者自然会产生类似大众星上“不按先后顺序,而是一览无余”的同时阅读的感受。
四、作者是小说文本的解释者
在传统语境中,作者被赋予某种优先的地位或作用,即作者在决定文本的意指方面具有某种优先权。人们相信,作者的文本如果真的是天才之作,那么它就会给人以启迪,并且其地位也因此而得到确立,作者便理所当然地具有确定文本意义的某种特许权利。 后现代主义者则在所有形式上消解传统作者在创作中所具有的无所不在的魔力。他们不否认作者的生存权,但否认作者具有制约文本的能力。他们认为作者是文本的解释者,作者并不造就普遍的真理主张,也不向读者提供任何指令,他只是勾画出各种见解,以与读者平等的身份参与各种讨论[7](P156—159)。
冯内古特在自我介绍中从两个方面向读者发出参与讨论的邀请:(1)一起回顾德累斯顿轰炸这一历史事件,由一个真实的人物——那次事件的幸存者,来讲述这一真实故事,其意义将由读者阐释;(2)一起探讨如何用大众星上的简洁的患精神分裂症风格写这部小说。为什么要进行那场大屠杀?怎样才能写出一部“简洁的患精神分裂症风格的”大众星式的小说?这两个问题对读者是很有吸引力的。
在小说的第一章和第十章,冯内古特以假托作者雍永森这一人物形象出现,回忆他所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累斯顿轰炸事件,语气超然冷漠,不作任何评论。小说开头的第三个句子就直接点到了德比“因为拿了别人的茶壶而真的在德累斯顿被枪毙了”这件极具反讽意义的事。 至于他死得冤不冤,值不值,作者没说,但他把这件事在小说中重复多次,在小说结尾处,作者又重复了这件事。冯内古特把思考留给了读者:如果说德比在轰炸后的废墟上捡了一把茶壶被判抢劫罪并被枪毙是执行正义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审判、枪毙那些扔炸弹、炸死了十三万五千个无辜平民的飞行员、实施轰炸任务的美国空军司令和策划轰炸的同盟国决策人呢?正义何在?冯内古特问奥黑尔:“你不认为这件事的确应当成为全书的高潮吗?”这个问题也是提给读者的。应该如何表现战争的荒诞、残酷和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死亡,是小说作者要和读者反复讨论的问题。
在小说的结尾,一只鸟儿对毕利说“普——蒂——威特?”这是小说《五号屠场》最后留给读者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难道对大屠杀只叫一叫“普——蒂——威特”就算完了吗?以上分析表明,小说《五号屠场》的作者从未表现为具有赋予其文本以某个单一的正确意义的权威,他只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兼叙述者,他提出各种见解,但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它期待着读者的解释。
在小说《五号屠场》的创作中,冯内古特“注意的是作家如何重新安排故事成分并使其产生意义的艺术,因此给读者提供了以新的方式经历和认识世界的机会,而不被囚禁在任何一种文化的典型描写形式之中”[8](P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