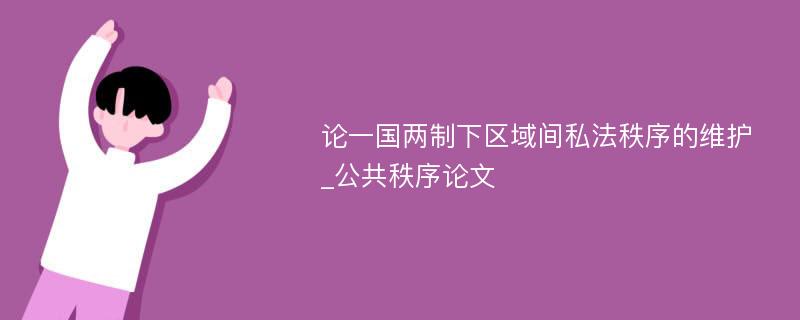
论一国两制下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法论文,一国论文,公共秩序论文,两制论文,下区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地区之间实行不同的法律制度。三地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问题,是指内地人民法院或香港、澳门地区法院在处理跨地区民商事案件中涉及到适用对方法律或者执行对方裁决时是否运用公共秩序概念予以拒绝适用或执行问题。鉴于三地法律对于公共秩序的内涵与范围均未予以界定,因此在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方面存在着不确定因素。对公共秩序保留的滥用会损及内地与港、澳之间正常的民商事交往及司法公正,但对此不予采用又会动摇法治基础与社会秩序。
本文的目的在于透过司法理论与判例的实证分析,从理论上界定公共秩序的范围、标准与适用原则。文中涉及到司法判例对公共政策的援用以及赌债性质与公共秩序保留关系的分析。
一、公共秩序在内地与港、澳地区的法律地位
公共秩序一词在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不同表达,在前者称为“社会公共利益”,在后者称为“公共政策”,两者显然具有共同的基本内涵。199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最高法院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中对此有所体现,具体规定为:“如内地法院认定在内地执行该仲裁裁决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或者香港法院认定在香港执行该仲裁裁决违反香港的公共政策,则不予执行该裁决。”不过,内地与香港之间至今仍未就相互执行法院判决签订类似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的协定。公共秩序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用语,在英美法系国家则通称为公共政策,而在我国立法中则称之为社会公共利益,三者只是法律用语的表述不同,含义基本一致。其重要性还在于公共利益,一定要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我国法律与司法解释并未对公共秩序作任何解释与界定。依照一般理解,公共秩序指一个国家的重大社会或经济利益、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基本道德准则。(注:赵健:《论公共秩序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这种理解比较抽象,反映了公共秩序具有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的特征。
(一)中国内地的社会公共利益
公共秩序保留的法律功能可见之于我国法律中的多处规定,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民事诉讼法》第262条第2款规定:“外国法院请求协助的事项有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以及第268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民事诉讼法》第260条还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应裁定不予执行……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此外,我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技术引进合同中不得含有限制性商业条款。该条属禁止性规定,所以技术引进合同中的这类限制性条款应当归于无效,因为这类条款与国家基本经济政策相抵触。对此,《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第4条明确规定:“技术进出口应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
(二)香港的公共政策
香港适用英国普通法制度,亦采用公共政策的概念,但对于什么属违反公共秩序并未予以明确规定或定义。不过,公共政策在普通法系中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不具政治或行政含义。对于哪些事项属于公共政策问题,不是由行政机关而是由法院来决定的,因此香港的公共政策所涉及的内容,实际上是法官认为应当能够反映社会公众利益、基本道德和自然公正信念的事项。在香港,违反公共政策与违法有相同的法律后果。例如合同违法或违反公共政策,即导致该行为或合同无效或者不可强制执行,因此香港称之为违法行为的概念包含了违反公共政策的行为。凡是违反刑事法的行为或民事侵权的行为通常被视为违反公共秩序的行为,例如目的在于欺骗对方而订立的不诚实的协议,通常是被判定无效的。此外,在香港合同的订立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亦属违法。在普通法中,被认为违反公共政策的合同包括以下各种合同:(1)向第三者进行犯罪、侵权或欺诈行为;(2)损害公共安全;(3)妨碍执行司法公务;(4)导致公众生活腐败;(5)骗税。(注:Cheshire,Law of Contract,Fffoot & Furmston,13 th Edition,p.372.)法院在有关判例中的裁定是,如果合同违法则不可强制执行。合同违法与否,只有通过司法审查才能确定。
除了普通法外,公共政策在香港的成文法中亦有规定。根据香港《外地判决(相互执行)条例》[Foreign Judgment(Reciprocal Enforcement)Act]的规定,法院可以基于以下任何一个理由,拒绝执行外地判决:(1)该判决是在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下取得的;(2)该判决是以欺诈手段取得的;以及(3)强制执行该判决违背香港的公共政策。
(三)澳门的公共秩序
澳门1999年《民法典》第20条亦直接规定适用外国法或外地法不得违反法院地公共秩序,具体内容为:“如果适用冲突规范所指之澳门以外之法律规定,导致明显与公共秩序相违背,则不适用该规定。”上述规定中的“澳门之外的法律规定”,从文义上看,其适用范围应当包括一国两制下的澳门与内地、香港之间的区际私法冲突问题。
以上内容表明,一国两制下的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在公共秩序保留的法定含义上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内地的“社会公共秩序”的内涵涉及范围相对广泛一些,包括了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法律基本原则、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等内容;而香港对“公共秩序”的理解主要针对法律范畴上的“公共政策”和公众利益,较少考虑政治因素,涉及范围相对狭窄。而澳门则在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条件上有严格限制,即其民法典第20条中的“明显与公共秩序相违背”的提法,是以“明显违背”为适用条件,但内地相应法律中并无此类限制。
二、公共秩序范围界定与标准
(一)关于国内公共政策与国际公共政策
国内学界多数人认为公共秩序应区分为国内与国际公共秩序两种,即“国内法意义上的公共秩序可以理解为是国内法中的所有强制性规范,以及宪法和各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构成国内正常社会生活之基础的善良风俗,亦应属于国内法意义上的公共秩序之范畴;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公共秩序至少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内强制性规则中被认为十分重要,因而在国内具有绝对的属地效力,可强制适用于在国内的所有人,包括外国人的规则,另一部分是国内专为国际民商事关系规定的法律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则,如我国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管制等的有关立法。”(注:金振豹《国际私法上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之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6期。)
国内流行的观点还认为,类似这种区分在美国早年的司法判例中亦有反映,而FritzScherk v.Alberto-Cclver Co.(注:lune 17,(1974)U.S.no,4.)一案则为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区分这两种公共秩序的典型案例。该案中Scherk对诉讼管辖提出异议,要求按双方事先的仲裁条款对证券交易纠纷进行仲裁。由于联邦法律禁止当事人在国内有价证券交易案件中放弃诉权,故伊利诺斯地区法院否决了Scherk要求进行仲裁的动议,并且完全依照最高法院曾在Wilko.v.Swan(注:346 U.S.Supreme Ct.Reporter 427(1953).)一案中所作的判决,即根据证券法,仲裁协议并不能排除证券购买者因受欺诈而寻找司法救济。第七巡回上诉法院亦维持了该判决,然而最高法院审理后最终推翻了一、二审法院的判决,其理由是Scherk案处理的是国际证券交易,而Wilko案中的证券交易不具有国际合同性质,因此所考虑的政策应有所区别。最高法院在Wilko案中适用了联邦证券法中的公共政策的规定(即证券交易案不得排除诉讼管辖权),但在Scherk案中显然没有通过这一公共政策的规定去排除国际仲裁协议。最高法院认为:虽然有价证券交易纠纷在国内合同中是不可仲裁的,但在国际商事交易情况下这类纠纷具有可仲裁性。
其实,该案要说明的并不是区分国内与国际公共秩序,而是联邦证券法的强制性规定的适用范围问题,即本案准据法的适用范围。本案中最高法院未适用证券法中的公共政策规定,并非因为该规定是国内公共政策而非国际公共政策问题,而是这一公共政策的规定并不适用于国际证券交易,而仅适用于纯粹的国内证券交易(涉内交易)。对公共政策作这种区分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所谓国内公共政策与国际公共政策在性质上均为一国之公共政策,具有国内法属性,只是在内容上有一定区别,即国内公共秩序概念大于国际公共秩序,或者说前者中有一部分内容即核心部分为国际公共秩序,因此后者是狭义的公共秩序,范围要小于前者。将国内公共政策与国际公共政策加以区别是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做法,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均有体现。但在中国并未形成或接受这种理论,在司法实践中也未见有对两种公共秩序加以区别。
由于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领域为涉外民商事关系而非涉内关系,因此将国内法中调整涉内关系的所有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称为国内公共秩序时,作出这种区分有一定意义,也是可以理解的,即国内公共秩序适用于涉内关系,国际公共秩序适用了涉外关系。但是有些国内强制性的规定(例如合同法与担保法中的某些规定)既适用于涉内关系,又适用于涉外关系时,就没有必要对公共秩序硬性作出这种区分,这实质上还是公共秩序的适用范围问题。例如,一国有关法定婚龄的规定具有强制性,应无条件地适用于其国民或公民,但不一定适用于涉外婚姻关系,因此仅适用于涉内关系的强行性规定,不是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公共秩序,只有既适用于涉内关系又适用于涉外关系的强制规定或者仅适用于涉外关系的强行规定,才是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公共秩序,或者称之为国际公共秩序。
按照美国联邦法律的规定,凡属公司破产发生的争议只能由破产法院来管辖,而禁止通过仲裁解决。但这一法院专属管辖的强制性规定(注:这类专属管辖在美国称诉讼为标的管辖(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却不一定适用于跨国破产案件。在Potochrome Inc.V.Copal Co.一案中,美国公司在破产前曾与日本公司订立的合同中有仲裁条款,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承认了该仲裁条款的有效性,并执行了仲裁裁决。(注:517F.2d512(2d Cir.1975).)该案例表明美国这一“不可仲裁性”的公共政策并不适用跨国破产案件。
(二)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主观说与客观说
在国际私法领域中,虽然各国的理论与实践均普遍采用公共秩序保留的制度,但对公共秩序的内容与范围却无明确界定,并长期为此争议与困扰。有学者指出:各国对于什么是公共秩序,观点不一,历史上试图对公共秩序下一个完整明确的定义的种种努力,无不以失败告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共秩序具有内容不确定性、含糊性和主观性,同时,在空间乃至时间上,它都具有相当强的相对性,此国的公共秩序不一定就是彼国的公共秩序,此时的公共秩序不一定就是彼时的公共秩序,现在的公共秩序未必将来还是公共秩序。(注:赵健:《论公共秩序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页。)欧洲大陆学者主要从法律分类的角度来确定何为公共秩序,而英美学者习惯于从在什么场合下适用公共秩序来探讨公共秩序的内涵。(注:肖永平:《中国冲突法立法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在各国对公共政策的内涵没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英美学者的主张显然更符合实际,更加合理。对于适用公共秩序的条件,国际上历来存在两种学说,即“主观说”与“客观说”,上述英美学者的观点应为客观说。主观说认为,只要原应适用的外国法律或者仲裁所适用的法律与法院地国或执行地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就应拒绝适用该外国法律或拒绝承认与执行该外国裁决,而不管适用法律或执行裁决的结果如何。这是各国适用公共秩序的传统做法,该学说只强调外国法律本身的有害性,而不注重法院地或执行地国的公共秩序是否实际受到损害。(注:陈治东、沈伟:《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化趋势》,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
“客观说”与“主观说”相反,只强调适用外国法或承认与执行外国裁决的结果与影响,而不注重外国法律本身是否与本地的公共秩序相违背。国内不少学者认为,“客观说”较“主观说”合理,因为裁决所适用的法律与承认及执行地国的公共秩序相违背,并不必然意味着承认和执行裁决也与承认和执行地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有时,仲裁裁决适用一个与承认及执行地国公共秩序不一致的法律反而恰恰可以维护该国的公共利益。(注:赵健:《论公共秩序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页。)显然,采用客观说,实际上大大减少了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的机会。
支持“客观说”的一个实例是未经政府许可的保险协议执行问题。按保险人所在国法律,未经许可,保险人不得签订保险合同,如果签了,可以罚款。在未经许可情况下,保险人与一外国人签订保险合同,并含有一项在出险地仲裁的条款。出险后因保险人拒赔而在外国仲裁,而裁决所依据的外国法并无保险许可的规定,裁决确认保险人赔偿。申请执行时,保险人提出保险合同无效的抗辩,仅同意退还保险金。执行国法院裁定要保险人承担保险义务,而并未以该国强制许可规定拒绝执行。因为立法所要追求的公共利益是要限制保险人违法获利。
香港于1990年通过成文法,宣布由未经许可的承保人成立的保险合同仍可由保险单持有人强制执行,或者由他选择撤销。(注:参见香港《保险公司条例》第6条A款。)但从判定许可证规定的公共政策出发,就应当认为成文法之目的乃是保护原投保人,如使保险合同不可强制执行,受损害的恰好是立法目的要予以保障的人,因此,相关的司法判决强制未经许可的承保人执行它签发的保险单。(注:Stewart v Orient Fire and Marine Insurance Co Ltd[1985]1 QB 988.)
德国在适用公共秩序时,亦采取客观说。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典》,如果承认仲裁裁决,其结果将会明显违背德国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不符合基本法的,德国法院才可不予承认。(注:《德国民事诉讼法典》(1998)第1044条第2款第2项。)
(三)界定公共秩序范围的标准与方法
有的学者认为,国际公共政策所反映的是国际商业社会的普遍利益与基本价值观念,由自然法的正义原则、国际公法中的强制规定等组成,范畴比国内公共政策狭窄。(注:王亦非:《浅析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中公共政策的审查》,2004年中国涉外仲裁司法审查研讨会论文。)其实这一界定过于空泛、抽象,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具指导意义。国内司法界已达成共识的是:不能因三地法律不一致就以公共秩序保留为由拒绝适用对方法律,也不能因判决、仲裁裁决依据的法律规定与本地法律规定不一致就以公共秩序保留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注:广东高院民四庭:《内地与港澳特别行政区商事法律实务问题》,载《人民司法》2004年第10期。)这一看法在“一国两制”原则背景下显得尤其重要,处理同一主权下的区际法律冲突时应当慎用公共秩序保留原则。
德国司法判例也认为违反本国强制性规定并不必然构成对公共政策的违反。美国司法判例的态度是,只有当外国仲裁裁决违反执行国最基本的道义和公正观念时,才可拒绝执行。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审理的Parsons T Whitkmore Oversea Co.v.Soeiete General (Rakta)一案,表明了其限制适用公共秩序的立场,法院在本案中认为,对于《纽约公约》中的公共政策,应予狭义的解释,只有执行裁决违反法院地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和公平理念时,法院才应根据公共秩序拒绝执行,如将公共秩序抗辩理解为保护国家政治利益的狭隘工具,将严重损害《纽约公约》的作用。(注:508F.2D969(2DC Cir.1974).)
司法审查中涉及的公共秩序问题一般都仅涉及实体法内容,而不涉及程序法。因为法院审理涉外案件,在程序法上只适用法院地法,不涉及外国程序法适用问题,即程序上并不存在法律冲突。但这是针对法律适用领域的公共秩序而言的,在司法协助领域,尤其是外国仲裁裁决问题,则情况另是一样,不仅涉及实体法也涉及程序法。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程序问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当事人有协议选择仲裁规则的自由。如果当事人所约定的仲裁程序或者仲裁机构处理的程序事项违反了国内法中有关程序问题的强制规定,法院就会拒绝承认与执行依该程序而作出的仲裁裁决。这就是为什么各国对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主要集中于仲裁程序事项,而不是实体问题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对实体事项进行审查,而是在实体问题审查时更为严格地执行公共秩序的标准。
我国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立法未给其下过明确定义,对于哪些行为构成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法院亦未对此进行过司法解释。一般认为:除了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等重大社会公共利益事项外,凡与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道德观念相抵触的行为,如种族歧视、暴力或色情文化、从事性交易行为等,也都构成公共秩序保留对象。由此可推定,凡是法律所明令禁止的行为,如赌博,欺诈等,均构成对公共秩序的违反。
关于公共秩序的形式,涉及到我国法律、法规,包括民商事法律中的有关强制性与禁止性的规定,但应对这两者加以区别。强制性的规定不一定都构成公共秩序保留,而禁止性的规定则构成。例如:对外提供担保必须经过批准、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的变更必须经过登记,均是强制性的。但未经批准的对外担保未必一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实践中企业之间进行相互借贷及违规进行对外担保等现象时有发生,但法律并不禁止这些行为本身,只是禁止这些行为的违规形式,所以不宜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原则。按我国法律规定,未经过外汇管理局批准或登记的对外担保合同无效。(注: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对上述管理办法颁布的实施细则。)对于无效的对外担保是否适用公共秩序保留不可一概而论,如果仅是未履行报批手续,而担保本身无问题的,可以补办手续,而不一定非要适用公共秩序保留。但如是当事人为了规避审批手续而未报批,则可按公共秩序保留定为无效担保,因为显然得不到批准才规避。对于骗保的情况,应按公共秩序保留确定无效,具体可参照最高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解释》中所规定的对外担保无效的五种情况处理。
在涉及外国法律适用或外国裁决执行的司法审查中,由于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范围针对的是国际商事交易,因此,凡是我国在相关的国际条约中所作的保留或特别声明的事项,往往属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范围。对国内法中的强行性、禁止性的规定是否属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范围,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具体分析。例如,违反内地的外汇管制规定的,似应属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范围。刑事法律的效力可以渗透到一切领域,因此各部门法中均有刑事条款,涉外民商事领域亦不例外。因此,凡适用于国际民商事或国际经贸领域的刑事条款,应当属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范畴。例如禁止重婚、禁止走私的规定,具有绝对的强行效力。
在Marchlikv.Coronet Insurance Co.一案中,(注:40Ⅲ.2d 327,239,N.E.2d799(1968).)美国伊利诺斯州(以下简称伊州)法院就曾以公共政策保留为由,拒绝适用威斯康星州(以下简称威州)的“直接诉讼法规”。伊州颁布的“非诉讼条款”禁止在对被保险人作出最终判决前直接对保险公司起诉,而威州的“直接诉讼”法规却允许对保险公司直接起诉。本案要解决的问题是伊州的公共政策(非诉讼条款)是否排除因被保险人的侵权责任而对保险公司起诉?本案中的侵权行为地(威州)允许直接起诉保险公司。如果公共政策对此排除,伊州是否应按美国的“充分诚信条款”去执行外州救济?
伊州法院的判决认为:直接受理按威州法规对保险公司起诉将违反伊州的公共政策,而拒绝受理这类起诉并不违反美国宪法中的“充分诚信”的规定,因为司法判例对保险法规的解释表明:立法政策反对在责任确定和对被保险人作出判决前就对保险人直接起诉,美国该判例表明的是一般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三、公共秩序保留适用中的特定法律问题
(一)合同违法与公共秩序保留
在香港合同违法或违反公共政策的后果一般是该合同不可强制执行,法院在相关判例中的立场是违法的抗辩最终建立在此公共政策原则上;法庭不会协助违反法律的原告,而该等行为是法庭应该主动注意到的,抗辩在这些情况下适用;假如法庭给予原告其要求的援助,会冒犯公众的良知,因为人们会以为法庭协助或者鼓励原告从事他的违法活动,或者鼓励他人从事同类活动。(注:何美欢:《香港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当事人之间涉及补偿罚款的合同在香港亦被认为是违反公共利益的。一般的观念是,不应让受罚者就惩罚取得补偿,“因为假如法律不责令某人赔偿,而加诸惩罚,让受罚人把惩罚转嫁他人,便会使立法的目的失效。该等法规为公众利益而设的目的,不是以罚款方式收取若干款项,而是使处在这种情况的人被惩罚,使得这些人日后可阻止同样事故发生……假如有罪的人可以在民事法庭中因刑事法庭加诸他人的惩罚而取得补偿,法规就达不到预期的后果。”(注:何美欢:《香港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3页。)
如果合同形式上合法,且可以合法地履行,但当事人双方或一方以不合法的方式履行的,亦可导致合同无效,这方面已有相应的判例予以确认。(注:Ashmore,Benson,Pease & Co Ltd v.A V Dawson Ltd[1973]1 WLR 828.)中国司法实践中近年亦有运用公共秩序保留拒绝执行涉及以不合法方式履行演出合同的涉外仲裁裁决。
在Laminorirs,S.A.[LTCL]v.Southwire Co.一案的执行程序中,败诉方援引《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b项,反对联邦法院执行仲裁裁决,其抗辩理由是本案中钢铁购买协议具有高利性质,因而违反了美国公共政策,法院认为在本案中逐步增高的利润实际上构成了罚款,这种私人交易中的安排不符合公共政策之目的,因此决定拒绝执行裁决中逐步增加的利益。(注:484 F.Supp.1063(N.D.Ca,1980).)
Soleimany v.Soleimany案是英国法院以公共政策为由而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本案中的上诉法院认为一个无效的协议是不应该得到执行的,对于一个合同缔结时就违法的合同,执行一个据此作出的仲裁裁决将违背英国的公共政策。(注:31[1999]Q.B.785.)
(二)欺诈或胁迫行为与公共秩序保留
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欺诈与胁迫构成对公共秩序的违反。在美国法院处理的BiotronikMess Co.v.Medford Medical Instrument Co.一案中,Medford公司提出公共政策抗辩,指出Biotronik公司隐瞒证据,通过欺诈手段获取了一项对其有利的裁决,执行该裁决将违反公共秩序。由于Medford公司未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欺诈的成立,法院因此没有支持其主张,但法院也表明了如下立场:如果构成欺诈,法院执行这样一项仲裁裁决将“违反法院地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和公平理念”,即违反了美国的公共秩序。(注:415F.Supp.133(D.N.J.176).)在Transmarine Seaways Corp v.Marc Rich & Co.A.G案中,法院提出,如果确有胁迫,法院可以依据公共秩序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注:480F.Supp.352(S.D.N.Y,1979).)
此外,仲裁过程中的仲裁员不公正的行为,尤其是违反正当程序的行为,亦是法院可以依公共秩序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这在各国已得到普遍确认。(注:韩健:《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
英美司法判例一般均认为依欺诈成立的合同构成违法,如此看来,欺诈的抗辩应属于公共政策保留的范围。在1984年的一个海事案件中,美国第二巡回法院认为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b项,只要有证据证明欺诈的存在,外国仲裁的裁决就不应执行。(注:737 F.2nd 150,153(2nd Cir,1984).)在另一桩海事案件(Transmarine Seaway Corp.v.Matv Rich Co.)中,美国法院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基于胁迫所订立的协议是违反国家公共政策的,只要胁迫成立,就构成《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b项所规定的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的基础。
如果一项涉外合同是以欺诈手段订立的,这类合同依我国合同法规定为无效合同,应为不允许订立的合同。如果依该合同准据法并不禁止该项合同之成立,但适用该外国法的结果却违反我国民事法律中的“诚实信用”基本原则,亦可视为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因为如使其有效,则破坏了民事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该项原则不象公平原则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有意义,而是事关整个社会之经济秩序,因此诚信原则的效果及于合同之外的公众。应适用公共秩序原则。
(三)限制竞争与公共秩序保留
在香港,对于限制竞争的合同是否违法或违反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具体分析,虽然从当事人角度,限制可能是合理的,但仍可能被法庭视为违反公共利益而无效。声称限制合理的人有举证责任,证明其限制按上述看法仍然合理。声称“虽然限制合理,但因损害公众利益而应判无效”的人,有举证责任证明所损害的公众利益。(注:Herbert Morris Ltd v Saselby[1916]AC 688,700,Atkinson.)通常理解上,竞争是公法领域问题,通过私人交易限制竞争,当然会损及公众利益,除非当事人能证明这属于合理的限制。因为合理限制范围相对较小,一般不涉及公众利益。
根据美国反托拉斯法,商业搭售属于自身违法行为,不管是否给对方造成损失均属违法行为。而在香港则有不同看法。相关案例为:原告在魁北克经营制造和进口造鞋的机器,被告经营造鞋业务。原告租予被告某些机器,租赁合同载有搭租条款,即假如某批鞋中有部分不是用向原告租赁的机器制造或加工的,不得使用租赁合同标的来制造该批鞋。后被告中止了搭租的机器租赁合同,原告提出诉讼,要求禁止令。法庭裁定承诺有效,法庭所持的理由是:“搭租本身不违法,原告有权按他们认为最符合本身利益的条款处置产品,只要处置方式本身不违法。诚然,这项权力是自由贸易的要素,正是被告用作逃避合同义务的藉口的自由贸易主义。”(注:United Shoe Machinery Co of Canada v Brunet[1909]AC 30,转引自何美欢:《香港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页。)但在另一涉及新加坡案件中,在新加坡只有原告及被告二人获准许以氰化氢杀虫,法庭拒绝强制被告执行不竞争承诺,因为这样做会实际上给原告垄断市场的机会,而这是违背公众利益的。(注:Thomas Cowan & Co Ltd v Orme[1996]27 MLJ 41,转引自何美欢:《香港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页。)
(四)赌债与公共秩序保留
赌博在香港是非法的,各国之所以禁赌是因为赌博损及社会公共利益,尤其是用公款赌博。香港《赌博条例》规定赌博违法,但有少许例外。例外包括在社交场合或有执照的公所赌博或另经批准的赌博。该条例规定,向他人提供金钱或其他财产,而知道其用途是非法赌博或与非法赌博有关者,则属违法。(注:香港《赌博条例》第3条、第14条。)
《赌博条例》规定赌博合同不可强制执行,但该条例允许的除外。为非法赌博贷款的合同,也不可强制执行。此外,唯一还管制香港的英国成文法(涉及赌博的)规定:为赌博或在赌博下注提供的保证无效。虽然法规提及赌博而没有区别合法和非法赌博,有人提议无效的只是与非法赌博有关的贷款及保证。(注:CHT Ltd v Ward[1965]2 QB 63,Carlton Hall Club Ltd v Laurence[1929]2KB,转引自何美欢:《香港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赌博在世界大多国家与地区均属非法行为而受到禁止,因而因赌博产生之债务为无效债务而不受法律保护。但因澳门法律允许赌博及打赌,由此产生的赌债就可成为法定债务。《澳门民法典》亦对赌债的性质作了规定,其内容为:“特别法所有规定时,赌博及打赌构成法定债之渊源:涉及体育竞赛之赌博及打赌,对于参加竞赛之人亦构成法定债务之渊源:如不属上述各情况,则法律容许之赌博及打赌,仅为自然债务之渊源。”(注:《澳门民法典》第1171条。)但赌博行为在内地则属非法活动,因此赌债不受法律保护。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1条明确规定:“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有关赌博的特别法是澳门特别行政区颁布的《娱乐场博彩或投注信贷》法规,用以规范博彩借贷行为的运作,从而使得澳门的赌博借贷行为有了法定依据。在这一赌博借贷立法出台后,澳门赌债已成为法定债务,其法律效力在于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通过司法途径强制执行。但澳门法律允许的其它形式的赌博或打赌产生的债务,仅为自然债务,当债务人不履行时,债权人不能诉诸法律强制执行。此乃澳门法定债务与自然债务的最大区别。
在少数国家或地区,赌博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如果中国内地某居民在澳门的赌场赌博输了钱又想索回赌资,他不能以赌博在中国违法为由在内地法院起诉来内地旅游的该赌场老板,请求法院运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判令退还赌资。但如该居民在澳门借了赌债回到内地后不予归还或者为了逃避赌债回到内地,澳门的债权人再到内地法院起诉要求其清偿赌债,虽然按我国冲突规范应适用赌场所在地法,但内地法院则会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为由拒绝适用澳门法而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的情况,前者不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原则是因为虽然澳门有关合法赌博的规定本身违反内地公共秩序,但该规定并未在内地适用,或者说并未在内地发生效力,这也符合公共秩序保留中的客观说或者英美法中的“既得权理论”,亦符合在中国实行的一国两制政策。后者应当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是因为赌博债权在内地的适用的结果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从属地原则出发,赌债在中国境内不得成立,严重的赌博行为构成刑事犯罪,更是刑事法规所管辖的事项,这亦体现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中的客观原则。本案特点是基于同一事实(赌博),同样的法律规定(在内地为违法与在澳门为合法),不同条件(境内与境外适用),而产生的不同结果(适用与不适用公共秩序保留)。
对于网上赌博债务纠纷的法律适用与公共秩序保留的运用,情况更为复杂一些。例如境外网络赌博公司通过广告引诱境内居民以电子货币参赌(投注足球赛或赛马)。而该公司所在地法律并不禁止该项业务。如境内居民进入该网站赌博后输钱,该居民能否以赌博在中国非法为由在内地法院起诉该网络赌博公司以索回赌资?内地法院应驳回还是支持其诉求?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案中虽然网络赌博公司不在中国境内,但境外允许赌博的规定事实上可通过内地居民的网上点击参赌而在内地产生效果。因此,本案不能简单驳回诉请,而可考虑按以下原则处理:要么适用中国法(行为地法)来处理纠纷,要么采用客观论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来排除境外有关赌博合法规定的适用。
四、公共秩序保留的实质与结论
公共秩序保留的法理来自“一国私法可以具有域外效力,但公法不具域外效力”这一基本原则。一国的公共秩序的基本内容与含义应当属于公法范畴,因为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当然不允许外国私法进入或违反,否则在效果上就无异于承认外国公法可以有域外效力。强制性的法规一般不具有域外效力,而私法在性质上属于任意性规范,只要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就可能通过冲突规范之援引被外国法法院所适用。1928年,美洲国家会议通过的《布斯塔曼特国际私法典》中第3条将各缔约国的现行法律和规则分为三类:即国内公共秩序法,国际公共秩序法和任意法(或私法性质的程序法)。由此可见,公共秩序法应属公法性质的法律。
国际私法或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实质上处理的是私法与公法的关系问题,私法处理的交易不能替代公法所处理事项。例如“抑制刑事诉讼不能私下协议决定,此乃公众利益所在”(注:参见Kaufmanv v.Gerson[1904]KB591。),私法之适用与判决亦不能破坏公法规则。民商法为私人交易范畴,不能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否则会混淆私法与公法的界限。
法律适用方面的公共秩序保留与裁决执行方面的公共秩序保留,这两者在保留的客体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是指域外法本身违反公共政策,后者是指域外法庭或仲裁庭支持的私人交易结果违反公共政策。在适用上前者更为严格,因为两国或两地法律规定的区别不构成保留的理由,而交易结果的正当与否,更容易导致执行中的保留问题。
一国法院通常会拒绝适用具有某些公法效果的外国私法,或者是违反本国公法规定的外国私法。例如,美国有时会将外国私法中带有惩罚性的规则借助识别制度将其定性为刑事法规而拒绝适用。(注:Peter Hay:Conflict of Laws,2ed.,West publishing Co.1997.p.156.)国内亦有一些学者认为:无论如何,此种认别在一定情况下起到了与公共秩序保留相同的作用,因为一国亦可以外国的某些禁止性规定违反本国的公共秩序为由予以排除。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将外国法识别为刑事法规,意味着此种法律具有严格的属地性,因而不能为国内法院所适用。(注:金振豹:《国际私法上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之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6期。 )实际上,这是将该禁止性规定定性为外国公法而拒绝适用。
在司法协助领域,尤其是执行外国裁决方面,公共秩序保留运用更多,但不能仅从裁决结果确定是否违反公共政策,也会涉及到对裁决本身的审查,如不进行实体审查,便发现不了可能存在的司法不公问题。
在美国,公共政策保留不仅适用于美国与外国之间,也适用于美国的州与州之间的民商事案件。同理,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也是可行的,更何况中国还在不同法域之间实行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即一国两制原则。但处理同一主权下的区际法律冲突时应慎用公共秩序保留,违反法院地强制性的规定并不必然都构成对公共秩序的违反,因为强制性规定所涉事项并非都是事关法院地的基本法律原则和重大或根本公共利益。
标签:公共秩序论文; 法律论文; 公共政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商事登记论文; 美国法院论文; 一国两制论文; 合同管理办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