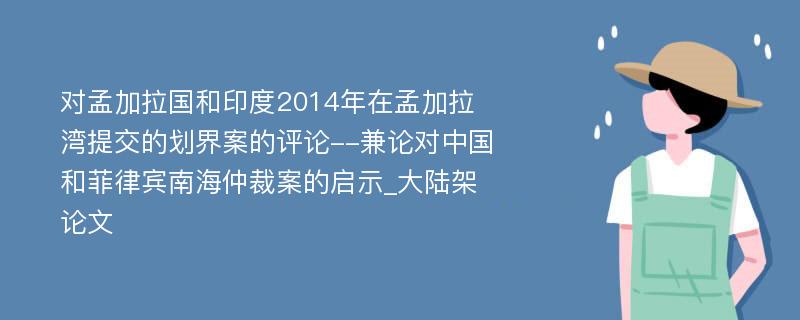
2014年孟加拉国与印度孟加拉湾划界案评述——兼论对中菲南海仲裁案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加拉国论文,孟加拉湾论文,南海论文,印度论文,对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87条和附件七组成的仲裁庭于2014年7月7日就孟加拉国与印度之间孟加拉湾海域划界案作出裁决。仲裁庭一致认定其对孟加拉国与印度之间的陆地边界终点的位置、领海划界、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问题拥有管辖权。依据4:1的多数表决结果,仲裁庭确定了两国之间领海、专属经济区与200海里内及200海里外大陆架的界限。 该案五位仲裁员中有三位是中菲南海仲裁案的仲裁员,分别是Rüdiger Wolfrum(德国籍,本案首席仲裁员)、Jean-Pierre Cot(法国籍)、Thomas A.Mensah(加纳籍,也是中菲南海仲裁案首席仲裁员),并且孟加拉国律师团队构成中有几个关键人物同时也是菲律宾律师团的组成人员,包括Paul S.Reichler、Lawrence H.Martin、Alan Boyle及Philippe Sands QC。①虽然该案中当事国的仲裁请求与菲律宾的仲裁请求表面上并不相同,但实质的争议焦点具有相似性,②因此,该案裁决以及孟加拉国的仲裁请求及其理由对于中国预测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结果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案件基本脉络及仲裁庭的裁决 孟加拉湾位于东北印度洋,面积约为220万平方公里。孟加拉湾被印度、孟加拉国、缅甸和斯里兰卡四国环绕,孟加拉国和印度的争议海域位于孟加拉湾北部。 孟加拉国与印度之间的争端自英属印度根据1947年联合王国颁布的《印度独立法案》(下文简称《法案》)分立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时即已开始。《法案》第二部分特别强调,新设立的东孟加拉邦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而西孟加拉邦则依然作为印度的组成部分。《法案》第三部分划定了东孟加拉和西孟加拉的临时边界,并在这一部分第三段中明确规定最终界线由印度总督任命的边界委员会裁定。③边界委员会于1947年6月30日成立,主席由西里尔·拉德克里夫爵士(Sir Cyril Radcliffe)担任,任务是划分东孟加拉和西孟加拉的边界。1947年8月13日委员会提交了报告,在报告的附录A中委员会描述了东孟加拉和西孟加拉之间的边界,并在其附录B的地图中描绘了这条界线,该报告又被称为拉德克里夫裁决(Radcliffe Award)。④ 1971年3月26日,孟加拉国宣布从巴基斯坦独立,并继承原东巴基斯坦的领土及领土边界。由于孟加拉国与相关邻国之间并未达成任何有关海域划界的协议,因此孟加拉国希望通过国际司法或仲裁方式解决与相关邻国之间的海域划界问题。⑤ 本案争端双方孟加拉国与印度均同意根据拉德克里夫裁决确定双方陆地边界的终点,并将该终点作为海域划界的起点,双方也同意适用《公约》第15条、第74条和第83条作为海域划界的依据,但是双方对拉德克里夫裁决的解释、陆地终点的具体位置以及《公约》第15条、第74条和第83条的解释与适用问题存在争端。⑥从1974年开始,孟加拉国与印度已经就双方在孟加拉湾的海域划界问题举行了11个回合的谈判,但始终未达成协议。2009年10月8日,孟加拉国根据《公约》第287条和附件七对印度提起强制仲裁。由于本案双方当事国均未根据《公约》第287条第3款作出声明⑦,也未根据第298条作出排除强制程序的声明⑧,意味着当事国接受《公约》附件七的强制性仲裁程序。根据《公约》第283条,缔约国有交换意见的义务。虽然印度认为双方有关海域划界问题的谈判已经接近达成协议的阶段,但是它并未主张孟加拉国的行为违反了《公约》第283条,⑨也未反对仲裁庭对本案行使管辖权。⑩仲裁庭由此认定孟加拉国符合《公约》有关提起强制性仲裁的规定,仲裁庭对争议事项具有管辖权。 仲裁庭认为关于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的国际法十分有限。另外,仲裁庭考察了巴巴多斯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孟加拉国和缅甸海域划界案、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陆地与海洋边界案有关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的相关论证与处理方式。虽然在本案中,根据大陆架外部界限委员会的工作,孟加拉湾200海里外大陆架的界限尚未确定,但仲裁庭根据2012年孟加拉国和缅甸海域划界案的推理过程得出结论:仲裁庭没有理由在大陆架双边划界中将自己的管辖权限制在200海里内。仲裁庭强调,《公约》第76条体现的是单一大陆架概念,这一观点被第77条所确认。根据第83条,在大陆架划界过程中,也并未区分200海里内还是200海里之外的大陆架划界。总之,大陆架划界和大陆架外部界限的确定二者相互补充。(11)最终,仲裁庭在确定了两国陆地边界终点的基础上,运用“等距离线/相关情况”方法为两国领海、专属经济区、200海里内大陆架以及200海里外大陆架划定了界限。 二、两国争议焦点与仲裁庭的意见 (一)两国陆地边界的终点 孟加拉国与印度均同意根据拉德克里夫裁决确定双方陆地边界的终点,但是该裁决并非由边界委员会五位成员一致作出,而是由主席拉德克里夫爵士一人作出的,同时该裁决的表述存在模糊之处,争端双方由此对该裁决表述的两国陆地边界终点的位置存在不同理解。 1.如何理解拉德克里夫裁决附录A的相关规定 与本案双方争议直接相关的是拉德克里夫裁决附录A第8段中列出了两国陆地边界线的末段,即“这条线应向南沿着库尔纳地区(Khulna)和帕甘纳斯24(24 Parganas)地区之间的边界直达孟加拉湾为止”(12),而这段界限直接来源于1925年孟加拉总督的第964号通知(13)。拉德克里夫裁决附录B是一份标绘着边界委员会所确定的两国之间陆地边界的孟加拉地图。但是拉德克里夫爵士在其介绍性报告中指出,该地图“只是用作说明目的,如果该地图标绘的边界与附录A对边界的描述不一致,以附录A为准”(14)。由此,双方对附录A的解释产生了分歧。 关于如何解释拉德克里夫裁决附录A确定的界限所依据的第964号通知中有关“for the time being”的含义时双方存在分歧,由此导致了本案当事国对请求仲裁庭确定的陆地边界的终点是1925年时确立的终点,还是之后随着河道变化而改变了的终点。 孟加拉国承认,陆地领土的边界随着河道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但是它认为当1925年第964号通知被并入拉德克里夫裁决时,陆地边界就不再改变了,即1947年8月是一个关键时刻,从这一刻起,两国间的陆地领土边界以及陆地领土边界的终点位置都已经确定下来,任何发生于其后的河道变化都不能改变业已确定的边界。(15)为支持这一观点,孟加拉国援引了印度诉巴基斯坦边界争端仲裁案的裁决。由于该案仲裁庭内部意见不统一,最后裁决依据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该案仲裁裁决明确指出,当1947年8月12日拉德克里夫裁决作出时,两国之间的边界就已经被固定下来。(16)印度认为,“for the time being”应该理解为河流边界应该在划界时才能确定,除非拉德克里夫裁决已经清楚地确定了边界的位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另外,孟加拉国所援引的印度诉巴基斯坦边界争端仲裁案的裁决是首席仲裁员独自作出的,印度本身反对这一观点。更何况首席仲裁员在作出裁决的同时也阐明,“如果划定印度与巴基斯坦在这一地区的边界被证明是不可能的,那么该边界……应该按照划界时的河流主航道中心线来确定,而不是拉德克里夫裁决中规定的日期”(17)。 2.关于地图的证据效力问题 为了支持各自对拉德克里夫裁决的解释,争议双方使用了不同的地图用来说明陆地边界终点的位置,而每一方都质疑对方所依据的地图的证据效力。 印度提供了经过认证的拉德克里夫地图副本,但孟加拉国否认其真实性。孟加拉国进一步指出,即便这一地图副本是真实的,仲裁庭也不能依据这一地图副本确认两国陆地边界的精确位置,理由包括四点:第一,该副本缺乏足够的精确性;第二,拉德克里夫裁决自身规定其对边界的描述是具有权威性的,而地图只是说明性的;第三,该地图绘制的河口区域不准确;第四,小比例尺的地图不适宜进行划界。(18)这里,仲裁庭注意到,在1944年孟加拉绘图办公室在绘制拉德克里夫地图时并没有意识到它绘制的这张图未来可能构成一条国家边界。(19)印度指出,拉德克里夫地图是作为整体的拉德克里夫裁决的组成部分,是可以作为对于边界的真实的、权威的说明而被接受的,并且援引布基纳法索与马里边界争端案中关于地图证据价值以及地图可能获得法律效力的相关论证作为支撑,即“当地图附属于官方文本时,它们构成一个整体”(20)。 争议双方随后又就什么时候的地图可以具有证据效力产生分歧。孟加拉国认为应当确定关键日期,关键日期当时的或之前的地图可以作为证据。1947年拉德克里夫裁决作出的时刻应被确定为关键日期,因此孟加拉国提供了1931年印制的英版海图859作为证据。孟加拉国认为英版海图859是最权威的海图,因为它在1947年作出的拉德克里夫裁决时是可被参考的。同时英版海图859提供了足够多的细节使得根据英版海图859确定陆地边界的终点变得可能。而孟加拉国认为印度依据的拉德克里夫地图“只是描述了陆地边界的路线,但并未给出具体坐标。它告诉我们如何去找到陆地边界的终点,但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们终点在哪里。”(21)在贝宁与尼日尔边界领土案中,国际法院依靠与关键日期同时期的证据来确定边界。(22)在卡西基里和色杜杜岛案中,虽然国际法院最终使用了现代文件作为证据,但只是因为争端双方都认为河道“在那段时间一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23)印度反对孟加拉国以英版海图859作为证据并质疑这张海图的精确性以及与本案的相关性。印度随后对孟加拉国关于只有与关键日期同一时期的海图可以作为证据,而之后的海图则不能作为证据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如果陆地边界的终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变化,那么使用之后的地图证据更为可取并应加重其证据分量,因为这种地图是能够证明事实的更好的证据。同时印度认为孟加拉国对卡西基里和色杜杜岛案判决的解读有误,并且质疑孟加拉国引用贝宁与尼日尔边界领土案与本案的相关性。(24) 3.仲裁庭关于陆地边界终点的决定 由于两国在如何解释拉德克里夫裁决上存在争议,致使它们分别提出了不同的陆地边界终点位置。仲裁庭会依据拉德克里夫裁决并考虑当事国各自主张来确定两国陆地边界终点的位置。 孟加拉国与印度就如何解释1925年第964号通知以及1947年拉德克里夫裁决中“for the time being”这一表述存在极大争议,仲裁庭承认它的含义是模糊的,既可指“当时”,也可指“随时”,即“流动的”边界线。在这个问题上,仲裁庭支持了孟加拉国的主张:“for the time being”应理解为“当时”。界河河道中间线应该是1947年作出拉德克里夫裁决时的中间线所处的位置,而不是在这之后发生变化了的位置,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当时确定这条界限是不可能的。(25) 仲裁庭注意到,利用河流的活动在解释拉德克里夫裁决过程中没有起到作用,没有任何一方当事国提供有关航行历史或其他有关河流利用方面的证据,特别是在1947-1951年之间。当涉及历史性航行时,争端当事国都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基于上述分析,法庭得出结论:界河河道中间线应该是1947年作出拉德克里夫裁决时的中间线所处的位置,同时应该考虑拉德克里夫裁决已经将第964号通知的内容包括其中。确定陆地边界终点在关键日期时的位置,需要参考1947年时的“领土照片”(26)。法庭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的先验:存在于关键日期之后的地图、研究成果和其他文件可能对建立、运用保持占有原则具有相关性,它们体现了当时的情形。在布基纳法索与马里边界争端案中,法院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鉴于保持占有原则目的在于冻结领土主权要求,(27)验证国家获得独立之后的文件不能修改关键日期时的“领土照片”,除非这一文件清楚地表明当事国同意进行这样的修改(28)。所以,本案仲裁庭确定陆地边界的终点根据1947年的信息以及其后补充的其他信息。 为了证明自己对拉德克里夫裁决的理解是正确的,争端当事国使用了不同的地图。仲裁庭主张地图应该有助于确定陆地边界终点在1947年时的位置,因此,应以1947年时的地图为准(关键日期)。如果无法提供此时的地图,则仲裁庭考察了三份地图,最终仲裁庭使用了拉德克里夫地图。虽然这份地图不够精确,无法断定河流主河道中间线,但并不代表拉德克里夫爵士在作出裁决的时候没有其他足够的信息作出判断。这份地图一定使用了其他比英版海图859更接近关键日期的地图。仲裁庭认为,只关注拉德克里夫裁决的文字表述而没有给附带的地图以足够的关注是不可以接受的。(29) (二)基点的选择 1.双方的争议 虽然孟加拉国与印度对海域划界的方法存在争议,但是它们都提供了不同的基点作为划出一条临时的等距离线的起点。 印度提供了9个基点,孟加拉国反对其中的7个。孟加拉国认为I-1、I-2、I-3、B-3和B-4属于低潮高地,不适宜作为基点,尤其以对I-1和I-2的反对意见最为强烈。I-1和I-2都位于南达尔帕蒂岛/新穆尔岛(South Talpatty/New Moore Island)上,孟加拉国指出该岛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或90年代早期已经永远位于水面以下了。孟加拉国举出一系列国际法院的案例反对使用低潮高地作为基点。孟加拉国指出,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如果低潮高地位于双方主张的重叠区内,为了划出一条等距离线的目的,其必须被忽略;在孟加拉国和缅甸海域划界案中,争端当事国都尊重了不将低潮高地作为基点来划定领海界限这一实践作法。(30)至于南达尔帕蒂岛/新穆尔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孟加拉国认为只有在领海划界之后才能确定,即由低潮高地所在的领海的沿岸国享有主权。(31)孟加拉国还提及了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国际法院认为“低潮高地不能被据为领土”(32)以及在马来西亚诉新加坡案和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中国际法院拒绝裁定争议的低潮高地主权归属问题。(33)孟加拉国提及在仲裁庭进行实地考察时,这些基点均不可见。即便一些印度提供的基点不是低潮高地,包括B-1和B-2,孟加拉国认为其受到海洋的侵蚀依然缺少稳定性,并提出印度提供的基点是“任意而主观”的。(34) 印度反驳孟加拉国,认为使用低潮高地作为基点具有广泛的国际实践的支持,更举出了《公约》第13条(35)的规定。另外,印度列举了三点理由证明低潮高地并非总是“不可见”的,在实地考察时没有看到这些基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实地考察那一天刚好赶上了小潮;其次,南达尔帕蒂岛/新穆尔岛只有在早晨和晚上6:30才可见,而实地考察错过了这两个时间点;最后,实地考察那一天恶劣的气象条件也是导致这些基点在当时“不可见”的原因。另外,印度认为,国际法院在一些案例中,例如卡塔尔诉巴林案中国际法院否认低潮高地作为划界的基点主要原因在于存在领土主权争端,而这一情况在本案中并不存在。(36) 2.仲裁庭的意见 仲裁庭分别总结和评价了双方的观点,并决定依据国际社会习惯作法,考察双方提出的基点,作出自己的决定。(37) 本案中,争议双方都不同意使用直线基线,而是通过各自提供基点,由仲裁庭根据这些基点为两国划定海洋边界。根据《公约》第13条,低潮高地可以被用作基点。但该条主要是为了解决领海宽度的测量问题,并不能用低潮高地来解决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海域划界问题。在黑海案中,国际法院对基点的选择有过详细的论述,主要观点是要使基点最接近要划界的海域,为了划定一条单一目的的界限,法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当事国所提出的基点。为了划一条等距离线,法院可以自己选择基点,但要注意这样的一条等距离线必须依据客观地理条件和双方海岸向海洋一面的基点。(38)仲裁庭认为,根据黑海案,基点至少是一个海岸上突出的点,因此它认为印度提出的南达尔帕蒂岛/新穆尔岛在高潮时位于水下,不适宜作为本案中的基点。(39) (三)海域划界的方法和相关因素 双方同意划界的第一步是确定一条等距离线,但是它们的分歧在于是完全依照等距离线还是在相关情况影响下使用角平分线方法。 1.等距离线方法的适用 孟加拉国认为国际法不存在一个假定支持等距离线规则,这种规则的运用主要是出于实践中的便利和适用上的确定性。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明确指出:“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40)从北海大陆架案以后,只有两个案件完全基于纯粹的等距离线,而其他的案件或者使用了调整后的等距离线,或者完全抛弃该方法而使用了其他的方法。最晚近的两个案件——孟加拉缅甸划界案和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在裁决中都使用了等距离线/相关情况方法,但最终的划界结果都严重偏离了等距离线。(41) 印度认为在《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中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划界方法,但是国际法的发展支持了等距离线方法。它引用了圭亚那诉苏里南案指出,近20年国际法院或法庭在海域划界案中的裁决明确了等距离线的角色。而且最新的国际司法实践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也并未偏离等距离线。印度认为,孟加拉国关于海岸线不稳定和凹陷的主张并未使得使用等距离线方法不适当。印度强调,不应混淆相关情况与导致等距离线的适用不可行的因素。(42) 2.角平分线方法的适用 孟加拉国依据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认为这种方法关注宏观地理情况,而不是微观地理特征。它指出在几个海域划界案中国际法院或法庭都使用了角平分线法,例如缅因湾案。在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中,法院发现角平分线方法是在等距离线方法不可能或不适当的情况下的一种可行方法。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孟加拉国还引用了法院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的论述。同时引证了几内亚诉几内亚比绍案中由于海岸凹陷,导致仲裁庭拒绝使用等距离线方法。它同时认为,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的情况与本案有诸多相似,因此使用角平分线方法是适当的。(43) 印度认为现代国际法有关海域划界最权威的案例应该是黑海案。在该案中,法官质疑几内亚诉几内亚比绍案,认为该案只是一个特例,没有被随后的案例所遵循。缅因湾案之所以没有使用等距离线方法的原因在于使用该方法用到的基点存在主权争议。国际法的决定性趋势是国际法院或法庭更关注海域划界的客观性和可预测性。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国际法院拒绝了尼加拉瓜偏离等距离线的主张,法院指出,不同于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本案并不存在等距离线不可行的情况。孟加拉国试图重新唤醒已经过时的国际法规则,在利比亚诉马耳他案之后的13个海域划界案中,只有一个使用了角平分线方法,而且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了。(44) 3.仲裁庭决定的划界方法及考虑的相关情况 仲裁庭认为需要澄清两个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问题:一是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中是否存在支持等距离线/相关情况方法的假定;二是在这个特定的案件中所使用的方法。 鉴于《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中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划界方法,而争端当事国又无法达成一致,仲裁庭可以决定采取何种方法。国际法院或法庭在划界中所遵循的首要目标是选择合适的划界方法以获得公平的划界结果。仲裁庭认为,划界的第一个阶段是使用等距离线/相关情况方法,要求使用可以满足几何学上的客观性以及划界区域地理特征的适当性的方法划出一条临时的等距离线;第二阶段考虑所有相关情况决定是否调整临时的等距离线以得到公平的结果;第三阶段运用比例校验方法来校验边界线是否公平。孟加拉国主要根据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来支持角平分线方法,但是仲裁庭注意到,在该案中运用角平分线方法是为了通过近似直线的海岸线把不规则的海岸线进行概括。使用等距离线/相关情况方法的优点在于通过明确的三步走使得划界过程和结果更为透明,而角平分线法则包括了太多的主观因素。在本案中,如果通过直线基线会导致不止一个相关海岸线。在第二阶段,会根据相关情况调整临时等距离线,这个阶段会获得高度的透明度,而其他方法则不会。基于此,仲裁庭认为等距离线/相关情况方法应优先适用,除非“存在相关因素使运用等距离方法不适当”(45)。而这种情况,在本案中并不存在。(46) 仲裁庭需要考虑,在本案中“相关情况”是否存在以及是否需要依此调整临时等距离线。仲裁庭引用了北海大陆架案的相关观点。在该案中法院认为,公平并不是要分配给一个不接近海洋的国家以大陆架区域,更不是赋予一个海岸线长的国家和一个海岸线有限的国家以相同的地位。假定国家间的地理情况是“准公平的”,并不是不顾实际情况如何而进行完全的地理重塑,而是为了减少在特定情况下偶然的地理特征所导致的不公平的划界结果。(47)仲裁庭认为孟加拉国海岸线确实不稳定,但它并不认为需要详细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海岸线不稳定不是能够调整临时等距离线的“相关情况”。更重要的是,仲裁庭认为,只有当前的地球物理情况在本案中才具有相关性,自然进化以及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海岸线在将来的变化不能成为调整等距离线的考虑因素。 仲裁庭下一步需要考虑海岸线的凹陷是否构成“相关情况”。它注意到海岸线的构成特别是海岸线凹陷的情况,在国际裁判中经常被作为相关情况予以讨论。仲裁庭认为,国际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凹陷没有必要构成可以对临时等距离线进行调整的“相关情况”。然而,当作为海岸凹陷的结果,国家间的等距离线对国家的海洋权益产生切断效果时,需要根据这一情况调整临时等距离线以达到公平的结果。仲裁庭认为切断效果的存在需要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上,除此之外,切断效果还需要把权利争议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并进行个案分析。仲裁庭同意,在本案中,孟加拉国的海岸线凹陷的确产生了切断效果,需要调整临时的等距离线。孟加拉国与缅甸海域划界案确认了孟加拉国对200海里外大陆架的权利,但是沿海国在200海里外大陆架的权利并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相关情况,仲裁庭还需要把地理情况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同时,调整的结果不能将切断效果从一个当事国转移给另一个当事国,因此仲裁庭在作出有利于孟加拉国的调整时不能对印度产生不合理的结果。 (四)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问题 1.划界方法 争议双方都同意它们各自享有200海里外大陆架上的海洋权利,并且都向大陆架外部界限委员提交了提案,双方也同意依据《公约》第83条划定界限。 孟加拉国撤回了它在书状中所主张的“200海里外大陆架是它海岸自然延伸的最远处”,因为这一主张已经被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孟加拉国和缅甸海域划界案中否定。孟加拉国重申了国际海洋法法庭在该案判决中的结论:“对于自然延伸的理解应该依据公约中关于大陆架和大陆边缘的定义条款”,适用《公约》第76条第4款。(48) 2.当事国提出的200海里外大陆架的划界界限 孟加拉国主张海岸线的凹陷构成划界中的“相关情况”,影响200海里外大陆架的划界。适用等距离线方法会在离海岸更远的外大陆架造成更加不合理的结果,切断了孟加拉国潜在的海洋权利,只保留了一个小块三角区域。孟加拉国认为等距离线会分配给印度在其向大陆架外部界限委员会提案前从未提出过权利主张的大陆架,而这部分大陆架一直以来为孟加拉国和缅甸所主张。虽然存在单一大陆架的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适用于200海里内的海洋界限必然要原封不动地延伸至200海里外。孟加拉国认为它应该在180度线与200海里界限交叉点上向孟加拉国与缅甸215度分界线的平行线方向延伸直到外大陆架的边缘。孟加拉国坚持认为这种方法符合位于凹陷海岸中间的国家主张海洋权益的实践,也符合查尼教授提出的“最大可及”原则。(49)孟加拉国提出了一系列在裁决过程中暗含了“最大可及”原则的案例,如北海大陆架案、缅因湾案、圣皮埃尔和米克隆群岛案、几内亚诉几内亚比绍案、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50) 印度反对在200海里以内和以外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印度指出孟加拉国与缅甸划界案是在200海里以外依然适用200海里以内的等距离线/相关情况方法来进行海域划界。印度在提交划界案时认为孟加拉湾的界限应该由两条等距离线组成,孟加拉国所享有的海域不会达到200海里外大陆架,因此印度的划界案只涉及到印度半岛海岸和缅甸朗肯海岸的等距离线。尽管印度的提案中没有涉及本案中所涉部分海域,但印度不承认孟加拉国所主张的这一海域早已归属孟加拉国的论断。印度特别强调了它已经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普通照会,指出印度向大陆架外部界限委员会提交的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可能会进行修改。印度反对孟加拉国所主张的200海里外印孟海洋边界应该与孟加拉国和缅甸的海洋边界平行线的方向延伸直至到达大陆架边缘。印度首先反对因为等距离线所产生的切断效果可以第二次调整海洋界限,并指出第二次调整会产生对印度海洋权利的切断效果。印度也不承认“最大可及”原则的合法性。印度反对孟加拉国自动将孟加拉国与缅甸之间的海洋边界延伸至390海里处,因为在该区域三国之间存在权利重叠区,更何况孟加拉国与缅甸海域划界案的判决不能约束第三方,因此不能影响印度。(51) 3.仲裁庭划定的200海里外大陆架的界限 仲裁庭首先为确定200海里外等距离线选定基点,之后根据基点确定200海里外等距离线。仲裁庭没有采纳孟加拉国的平行线的方法,而是延续了200海里内等距离线的走向直到与孟加拉国和缅甸之间的海上边界线相交。仲裁庭认为本案只有单一大陆架,因此在200海里内外区域都应采取等距离线/相关情况方法来划定界限。仲裁庭认为,如果按照孟加拉国的方法,则会导致对印度海洋权利的切断效果。另外,国际法关于大陆架划界的理论不承认沿海国有权将自己的海洋权益延伸至最远的海洋区域而不顾及其他国家的合法权益和地理条件。如果按照印度的观点使用一条不经过调整的等距离线,又会对孟加拉国的海洋权益产生切断的效果,因此也是不可取的。仲裁庭注意到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孟加拉国和缅甸海域划界案中的观点:考虑到孟加拉国海岸线凹陷作为一个相关情况会影响其200海里内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这一相关情况也会影响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仲裁庭最后决定对200海里外临时等距离线进行调整以达成公平的结果。(52) 4.调整200海里内和200海里外的临时等距离线 仲裁庭调整临时等距离线主要出于如下考虑:首先,仲裁庭应当寻求减轻临时等距离线对孟加拉国权利产生过大的消极后果;其次,这种调整也不应侵犯印度的正当权益,应当使沿海国以一种合理的、相互平衡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海洋权利;最后,这一调整也不应损害第三国的合法权益。为减轻临时等距离线对孟加拉国权利产生过大的消极后果,仲裁庭从Prov-3点开始调整临时等距离线使其沿着东经177°30'00″的方向从200海里内延伸至200海里外,直至与孟加拉国与缅甸在200海里外的界限相交。这一调整没有对印度权利造成不合理的限制,同时这一调整避免了转点,使当事国行使权利和进行管理更加简单。 (五)灰色区域 这一划界结果出现了灰色区域,该区域存在于印度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而在孟加拉国200海里外大陆架上。所以,本案划定的200海里外界限只是大陆架的界限。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孟加拉国和缅甸划界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判决中划分了当事国在灰色区域内的权利:存在许多方法可以分配当事国的义务,包括达成特定协议或建立适当的合作安排。当事国决定采取何种适当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53)孟加拉国支持国际海洋法法庭作出的裁决,并认为可以适用于本案:位于孟加拉国200海里外而位于印度200海里内的区域,由孟加拉国行使大陆架的主权权利,而印度行使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印度200海里外的区域,边界线只是大陆架的界限。然而,印度在书状中对此问题没有提及。 仲裁庭强调,在200海里外大陆架,孟加拉国根据法律制度只能对海床和底土享有权利。在灰色区域内孟加拉国行使大陆架的主权权利,而印度行使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根据《公约》第56条第1款(a)项,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包括水体和海床底土。而在实践中,公约区分了适用多种制度的区域所产生的权利。根据《公约》第56条第3款,专属经济区内关于海床和底土适用大陆架制度。第68条排除了定居种生物资源适用专属经济区制度。根据第77条,孟加拉国享有灰色区域内矿产资源、非生物资源和定居种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但是这一界限并不能限制印度在灰色区域内对专属经济区享有主权权利。同时,最后的划界结果还出现了印度与缅甸之间灰色区域的重叠区,由双方协议解决。仲裁庭认为这是合适的解决方式,而且对当事国之间共同或单独采取行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充满信心。(54) 三、对中菲南海仲裁案的启示 (一)“禁止反言”和“维持现状”原则 孟加拉国在解释“for the time being”的含义时,使用了印度与巴基斯坦边界案中印度的陈述,并提炼出这段陈述中有关国际法上“禁止反言”和“保持占有”原则。此外,印度也提及了“保持占有”原则,但否定受“禁止反言”原则的约束。两国在“保持占有”原则解释上存在分歧。仲裁庭认为保持占有原则在决定陆地边界终点时不起作用,因此不予考虑。 中菲南海争端同样涉及到这两个重要原则。从历史上中国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利用,到历代政府连续不断地对这些岛屿与相关海域行使管辖权,再到1948年开始的一系列绘有南海断续线的公开出版的地图、政府公告等,中国早已确立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及对断续线内的海域的历史性权利。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菲律宾(以及独立前的宗主国)从未表达过反对意见,其应受“禁止反言”原则的约束。另外,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菲律宾的法律对其领土范围有明确限定,没有涉及中国的南海岛礁。(55)所以,菲律宾独立后应依“保持占有”原则确定其领土组成及管辖权范围。根据本案裁决,只有中国充分证明这两个原则可以“归因于”(attribute to)岛屿归属和断续线的合法性,才可能被仲裁庭考虑,这对中国提出了更高的证明要求。 (二)地图的作用 为了证明自己对拉德克里夫裁决的理解是正确的,本案当事国使用了不同的地图。仲裁庭主张应以1947年时的地图为准(关键日期)。如没有1947年地图原图,则仲裁庭考察了三份地图的证明力(1947年或之前),最终仲裁庭使用了拉德克里夫地图(是1947年拉德克里夫裁决所附的官方复制版地图)。本案中,仲裁庭肯定了关键日期之前的官方地图具有很强的证明效力。 在这里,关键日期的确定是一个核心问题。关于中菲南海争议的关键日期虽存在不同观点,但基本集中在20世纪50-70年代,因此,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官方地图对确定中国在南海的权益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清代以来标明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世界各国出版的地图有200多种,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48年标有断续线的官方出版的地图。这份地图会在南海仲裁案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三)低潮高地可否作为基点的问题 孟加拉国举出一系列国际法院的判决反对使用低潮高地作为基点,而印度则认为使用低潮高地作为基点具有广泛的国际实践的支持,更举出了《公约》第13条的规定。仲裁庭认为《公约》第13条主要是为了解决领海宽度的测量问题,并不能用低潮高地来解决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海域划界问题,最终否定了印度提出的以南达尔帕蒂岛/新穆尔岛作为基点的主张。 低潮高地能否被据为领土,国际司法实践和国家实践有不同作法。菲律宾提出仁爱礁、美济礁和渚碧礁是低潮高地,不能据为领土,不能产生任何海洋权利,即使是领海;西门礁和南薰礁也是低潮高地,但因为他们位于高潮地物12海里的范围之内,可以作为测算领海基线的基点。(56)其中仁爱礁、美济礁和渚碧礁在构成特征上与南达尔帕蒂岛/新穆尔岛相似,因此菲律宾的这一主张很可能会被仲裁庭采纳,对我国极为不利。因此,我们应把重点放在岛屿主权归属的证明以及南海诸岛适用群岛制度的论证上。最好的结果是通过提示仲裁庭其对岛屿主权问题无管辖权从而回避对上述海洋地物的分别进行定性;如果仲裁庭依然坚持自己对上述海洋地物定性问题上具有管辖权,则我们可以考虑如下两条路径:一是强调对断续线内的岛礁享有历史性所有权,在整体上确认对南海诸岛(包括低潮高地)的主权;二是不提及中国在断续线内的权利,但是明确提出南海诸岛适用群岛制度。这两条路径都绕开对上述海洋地物进行分别定性的问题。 (四)仲裁庭对历史性权利的提及 仲裁庭在领海划界过程中,依据《公约》第15条考察了争端当事国是否存在历史性所有权,以便决定是否调整等距离线。但本案当事国均未主张历史性所有权,所以仲裁庭在裁决中未再提及该权利。 我国在南海争端中面临岛屿归属的证明和断续线性质的界定两个关键问题。由于中国始终未明确断续线的法律性质,因此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诸多揣测与压力,(57)菲律宾更是将中国对断续线内的水域、海床和底土所主张的“历史性权利”与《公约》不符作为首要仲裁事项。(58)菲律宾认为《公约》中并不存在空泛的“历史性权利”(historical rights),只有“历史性所有权”(historical title),而中国从未主张过“历史性所有权”。一部以分配海洋权益为目的的《公约》对“历史性所有权”的明确规定不等于对一般国际法上“历史性权利”的否定,也不应迷信《公约》可以解决包括领土归属争端在内的南海争端的所有方面。退一步说,这一来自英美法的词汇“title”是否能够完全对应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所有权”的概念,值得商榷。本案裁决对“历史性所有权”的提及为我们进一步细化历史性权利的特征、构成要件等留下了余地。 (五)体现“公平原则”的划界方法 北海大陆架案明确了“公平原则”的习惯国际法地位,并被《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所明确,但为获得“公平的结果”所使用的方法却并无定论。印度认为国际法的发展支持了等距离线方法是体现“公平原则”的方法,孟加拉国则认为国际法不存在一个假定支持等距离线规则,这种规则的运用主要是出于实践中的便利和适用上的确定性。仲裁庭最后选择了等距离线/相关情况方法作为划界的方法,而把孟加拉国要求适用其他划界方法的依据作为“相关情况”,在调整临时等距离线时加以考虑。 由于海域划界问题是隐藏在菲律宾仲裁请求背后的真实目的之一,所以我们需要对此进行简单分析与预测。在完成岛屿归属的充分证明之后,等距离线/相关情况方法对确定我国与菲律宾之间的海洋界线影响不十分显著,因为中菲之间断续线的位置基本上就在南沙群岛与菲律宾群岛的中间线上,岛屿间相向距离不足400海里。再加上国际司法机构在适用此方法划界时所考虑的“相关情况”趋于稳定,主要包括:地理因素,如海岸形状、相关当事国海岸长度比例、岛屿和海港工程;地质和地貌因素,如在南沙群岛东侧与菲律宾和文莱西部之间有深达2000多米的深海槽,从而将南沙群岛与菲律宾、文莱分开;当事国的行为;第三国利益,等等。中国在这些方面并无明显劣势。但是鉴于我国在东海同日本、韩国存在海域划界争端,在该部分适用等距离线/相关情况方法对中国明显不利,因此不宜对此方法持肯定态度。 (六)灰色区域 仲裁庭的裁决体现了海洋边界的划定趋于简化这一趋势,以致于出现新的问题,即灰色区域。该区域在印度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而在孟加拉国200海里外大陆架上、在缅甸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而在孟加拉国200海里外大陆架上以及在印度缅甸共同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但在孟加拉国200海里外大陆架上。在该区域内,当事国需要达成特定协议或建立适当的合作安排来分配海洋权益,可能引发新的争端。在此裁决之前,国际社会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存在“灰色区域”的判决就是2012年国际海洋法法庭所裁判的孟加拉国和缅甸海域划界案,这是调整临时等距离线所产生的副产品。 这一结果对中国而言有利有弊:好处在于因为它肯定了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基于不同的考虑可以分别划界,是对国际司法机构海域划界结果所体现的“单一海洋界限”趋势的挑战,对于未来中国与日本、韩国协议解决海域划界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弊端在于使南海局势更加复杂。南海周边国家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都向大陆架外部界限委员会(简称“委员会”)提交了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或初步信息,其中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印尼的提案涉及到中国断续线内海域。虽然由于中国的强烈抗议一些划界案已经被委员会搁置,并可能由于委员会权限所限被无限期搁置,但这一问题只是暂时被回避并未解决。这些国家对南海的立场与主张日趋明确、强硬,不排除今后会通过其他途径继续试探、挑战中国南海断续线的可能。虽然菲律宾提交的划界案并未涉及中国南海,但它在该划界案的执行摘要部分明确指出:“提交本划界案不妨碍菲律宾今后就其他地区提交其他划界案的权利。”(59)如果中菲南海仲裁案以菲律宾失败告终,那么不排除它会通过提交涉及中国南海的大陆架外部界限划界案继续对中国施压。 注释: ①“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v.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ttp://www.pca-cpa.org/showpage.asp?pag_id=1529,last visited on 23 July 2014. ②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孟加拉湾的海域划界问题。虽然菲律宾请求仲裁庭就中菲在南海的“海洋管辖权”问题作出裁决,但事实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裁决的前提是确定相关岛礁主权归属以及完成海域划界,海域划界问题正是菲律宾所提仲裁事项的实质问题之一,所以两个仲裁案争议的实质问题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菲律宾仲裁请求的主要内容参见Note Verba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to the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No.13-0211)and the Attached Notification and Statement of Claim(22 January 2013),http://www.dfa.gov.ph/index.php/newsroom,last visited on 23 July 2014. ③Memorial of Bangladesh,vol.I,31 May 2011,paras.3.3,3.4,http://www wx4all.net/pca/bd-in/Bangladesh's%20Memorial%20Vol%20I.pdf; Counter-Memorial of India,vol.I,31 July 2012,para.3.4,http://www.wx4all.net/pca/bd-in/India's%20Counter-Memorial%20Vol%20I.pdf,last visited on 8 July 2014. ④Bay of Bengal Maritime Boundary Arbitration between Bangladesh and India,Award,7 July 2014,p.14,para.52,http://www.pca-cpa.org/showpage.asp?pag_id=1376,last visited on 8 July 2014. ⑤为解决孟加拉国与缅甸之间的海域划界问题,2009年12月14日两国协议将两国在孟加拉湾的海域划界问题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该案也成为法庭受理的第一个关于海域划界的案件。2012年3月14日,国际海洋法法庭就孟加拉国与缅甸在孟加拉湾的海域划界争端作出了终审判决,划定了两国之间领海、专属经济区与200海里内及200海里外大陆架的界限。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Bangladesh/ Myanmar),Judgment,ITLOS,No.16,2012. ⑥Supra note④,p.15,paras.56-59. ⑦《公约》第287条第3款规定:“缔约国如为有效声明所未包括的争端的一方,应视为已接受附件七所规定的仲裁。” ⑧《公约》第298条规定了适用第二节(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的任择性例外。 ⑨Supra note④,p.20,para.72. ⑩Ibid.,p.19,para.64. (11)Ibid.,pp.21-22,paras.76-77,80. (12)Bengal Boundary Commission,Report to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General,Annexure A at paragraph 8(12 August 1947). (13)原文为“[T]he western boundary of district Khulna passes along the south-western boundary of Chandanpur...till it meets the midstream of the main channel of the river Ichhamati,then along the midstream of the main channel for the time being of the rivers Ichhamati and Kalindi,Raimangal and Haribhanga till it meets the Bay”。See supra note④,pp.25-26,para.88. (14)Ibid.,p.26,para.89. (15)Ibid.,pp.27-28,para.98. (16)Case concerning Boundary Disputes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Relating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port of the Bengal Boundary Commission,12 and 13 August 1947,Decision of 26 January 1950,RIAA,Vol.XXI,p.13. (17)Ibid.,p.12. (18)Supra note④,pp.31-34,paras.114-121. (19)Ibid.,p.34,para.122. (20)Frontier Dispute(Burkina Faso/Mali),Judgment,ICJ Reports 1986,p.582,para.54. (21)Supra note④,p.37,para.131. (22)Frontier Dispute (Benin/Niger),Judgment,ICJ Reports 2005,p.133,para.33. (23)Kasikili/Sedudu Island(Botswana/Namibia),Judgment,ICJ Reports 1999,p.1065,para.31.See also Frontier Dispute(Benin/Niger),ibid.,para.26; Land,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El Salvador/Honduras:Nicaragua Intervening),Judgment,ICJ Reports1992,p.548,para.313. (24)Supra note④,p.38,para.135. (25)Ibid.,pp.46-47,paras.159,162-163. (26)Frontier Dispute(Burkina Faso/Mali),supra note(20),p.568,para.30. (27)Ibid.,p.568,para.29. (28)Frontier Dispute(Benin/Niger),supra note(22),p.109,para.26. (29)Supra note④,pp.49-51,paras.173-184. (30)Ibid.,pp.58-59,para.198. (31)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Merits,Judgment,ICJ Reports 2001,p.101,para.204. (32)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Nicaragua v.Columbia),Judgment,ICJ Reports 2012,p.19,para.26. (33)Case Concerning Sovereignty over Pedra Branca/Pulau Batu Puteh,Middle Rocks and South Ledge(Malaysia/Singapore),Judgment,ICJ Reports 2008,pp.99-101,paras.291-299;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between Nicaragua and Honduras in the Caribbean Sea(Nicaragua v.Honduras),Judgment,ICJ Reports 2007,p.704,paras.144-145. (34)Supra note④,pp.59-60,paras.201-203. (35)《公约》第13条第1 款规定:“低潮高地是在低潮时四面环水并高于水面但在高潮时没入水中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如果低潮高地全部或一部与大陆或岛屿的距离不超过领海的宽度,该高地的低潮线可作为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 (36)Supra note④,pp.60-61,paras.204-207. (37)Ibid.,pp.61-65,paras.208-225. (38)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Romania v.Ukraine),Judgment,ICJ Reports 2009,pp.101,105,paras.117,127. (39)Supra note④,pp.72-74,paras.250-261,263-264. (40)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Denmark;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Netherlands),Judgment,ICJ Reports 1969,pp.23-24,para.24. (41)Supra note④,pp.91-92,paras.314-318. (42)Ibid.,pp.92-93,paras.319-322. (43)Ibid.,pp.93-96,paras.323-329. (44)Ibid.,pp.96-97,paras.330-335. (45)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between Nicaragua and Honduras in the Caribbean Sea,supra note(33),p.741,para.272. (46)Supra note④,pp.97-100,paras.336-346. (47)See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supra note(40),pp.49-50,para.91. (48)Supra note④,p.131,para.438-439. (49)“最大可及”原则是指海洋划界应该按照一种让所有的争端国都分配到进入从其海岸线起算允许到达的最远的海洋区域的方法进行。 (50)Supra note④,pp.131-135,paras.440-448. (51)Ibid.,pp.135-138,para.449-455. (52)Ibid.,pp.142-144,para.465-475. (53)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supra note⑤,p.137,para.476. (54)Supra note④,pp.155-157,paras.498-508. (5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2014年12月7日,第5段,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17143.shtml,2014年12月7日访问。 (56)Notification and Statement of Claim (22 January 2013),supra note②,paras.14-19. (57)U.S.Department of State,China: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5 December 2014,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34936.pdf,last visited on 7 December 2014. (58)前引(55),第8段。 (59)《200海里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划定——划界案的执行摘要和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建议摘要》,高建军译、张海文审校,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