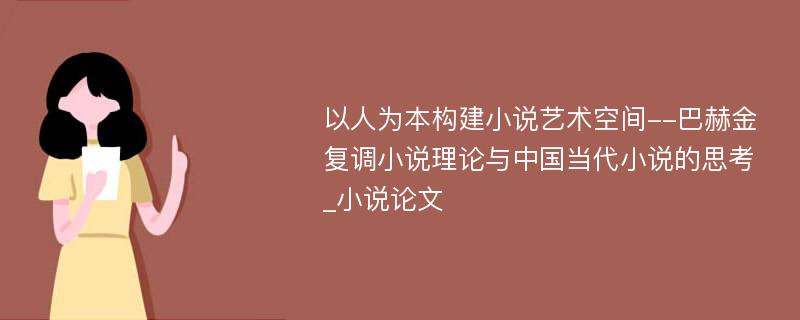
以人为根基建构小说的艺术空间——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和中国当代小说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小说论文,根基论文,中国当代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洋洋四十万言的《巴赫金文论选》在去年翻译出版以来,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在仔细习阅这部浩繁的小说理论著作之后,我感到在理论思维上颇受启迪,也获得一些考察中国当代小说的新视角。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建立于二十年代,那个时期俄国出现了形式主义文艺理论流派,被今人视为是结构主义美学的早期形态。此派主张研究艺术的形式结构特征,故巴赫金的研究不免被人看成是对形式主义运动的追随,是小说结构手法和结构形式的阐述而已。[①]如果抛开这种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判断定势,把注意力深入到其理论内部的人学与诗学的基点和创见上,并以此去慎思我国当前小说创作的倾向与问题,我们将获得不少裨益。
一、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说起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主要来自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及相关评论。陀氏属于十九世纪文学巅峰阵容中的作家,在寻求叛逆与颠覆上一世纪文学传统的二十世纪文学中,陀氏的创作却对一批叛逆的精英萨特、加缪、尼采、卡夫卡、福克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复调形式结构本身,而在于其小说作为人的学说和生活学说的巨大包容力。布拉格哲学家米兰·马克弗西曾在他的《论人类生活的意义》一书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包罗万象的艺术家,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对立,因为他“是在冲突和错综复杂的总体上来描写人的内在精神的。”[②]这提示我们,“冲突和错综复杂的总体”是陀氏创作的根本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一特征,二十世纪中人们对陀氏小说的批评众说纷纭,宗教神学的阐释认为陀氏“极为强调的人类牢固的团结是各方济会的基督教信仰之一,它把人和大自然——甚至包括禽兽——设想成在博爱和普遍宽恕中最终团结一致。”其小说“忠诚于东正教教会和迷恋于民族主义思想”;[③]存在主义阐释则看取其小说中的非理性、虚无主义和世界的荒谬性与无秩序,“只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那个‘地下室人’而忽视了那个有神论者、乐观主义者,那个甚至还盼望着一个黄金时代——人间天堂——到来的乌托邦空想家”;[④]心理学批评指出他的小说深蕴着“对梦的生活”和“人格分裂的兴趣”,认为他源自基本的俄狄浦斯情结(父亲被人杀害而蒙生精神创伤)的癫癎症和“赌博狂”对创作影响巨大;[⑤]持社会意识形态立场的批评认为:陀氏是一个颓废派作家,是“疯人院里的莎士比亚”,因为他“摈弃理性,歌颂疯狂、白痴和低能”,“宣扬贱民的道德、奴隶的道德”(此为法国批评家的看法),他是“一个以苦难为快乐的虐待狂,一个能产生伤害者和被伤害者的制度的捍卫者”,“只擅长于描写狼吞噬羊时和羊被狼吞噬时的感觉。”是“一个反动派,一个对压迫持逆来顺受态度的辩护士”(此为包括高尔基在内的一些俄国批评家的意见)。[⑥]而别林斯基在评《穷人》时又高度赞扬陀氏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缪斯爱怜那些蛰居阁楼和地下室里的人们,告诉那些豪华宅邸的居民。‘瞧,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你的同胞兄弟’。”[⑦]此外还有哲学“二元论”的阐释、形式主义阐释、象征主义阐释、现实主义反映论的阐释。各派阐释毁誉掺半,甚至个别批评者自身的观点也前后不尽一致(如别林斯基、D·H·劳伦斯)。这其中有批评视角和语境相异的问题,但主要取决于陀氏对人的内在与外在世界的丰富性、矛盾性的旷世体认与表现。陀氏的小说无不以人为考察对象,并将笔力投注于个别人和一般人的思想、情感、事业、生活上的矛盾,投注于人们相互间的矛盾。斯·茨威格曾在一本陀氏小说集的序言中指出:“从他的每位主人公那里道路直接通到尘世生活的极深处,但在精神的腾飞中他略微窥见上帝的面容。”[⑧]一方面是“尘世生活的极深处”,另一方面是向“上帝的面容”腾飞。为了不使这种对立存在最后统归在自己的主体独白的笼罩下,他因此往往要描写异常的生活环境和极端的现象、极端的情势,这的确要冒险——被人错误理解。但也正因如此,他的小说世界才有了各色各样的人物:梅什金公爵和阿辽沙·卡拉马佐夫的基督徒的谦卑;拉斯科尔尼科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撒旦似的傲慢;基里洛夫的辨证的无神论;沙托夫的以救世自居的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这些人物的艺术展示没有教会气,没有理性教条欲,也没有法官式的权威,更没有野蛮人的霸道。而是以“复调”的方式奏响了人的交响乐。
二、“复调小说”与人的复调
巴赫金指出:陀氏“创造的不是无言的奴隶,而是自由的人——他们能够同自己的创造者并肩而立,能够不同意他的意见,甚至起而与之抗争”。[⑨]巴赫金也正是基于人的言说性与自由性来研究小说的复调艺术的,而不仅仅是在文本学这一平面上展开论述,不首先确定这一点,就不能完整确定巴赫金小说理论的价值。巴赫金在其著述中触及到人的自我意识、人的言说性、人的自由与平等、人的差异性与完整性、人的对话性、人的互为主体与互为客体等诸多方面,并将主人公提到作者平等的位置上加以研究,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文学在本世纪所走过的道路。
从古代哲人苏格拉底对“认识你自己”的名言赋予哲学意义以来,认识人自身,探索斯芬克斯之谜,就成了两千多年来人文学家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一事实本身说明这个问题是何等重要和艰难,就以哲学中对人的定义来说,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柏拉图及近代哲学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卡西尔“人是符号的动物”——马克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已显示出认识人的过程多么漫长,而文学为人类认识自身做出的贡献绝不亚于哲学。但是文学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对“人”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人们首先是听到关于上帝消亡,人道主义消亡和悲剧崇高消亡的断言,随后又听到了声称人物在文学中已消亡的论调。罗兰·巴特宣称“在今天的小说中,已过时的不是小说的特性,而是人物;专有名称(Prope Name)再也不能写了”。[⑩]许多现代作家都欲摆脱上一世纪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强大优势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和窘境,D·H·劳伦斯、纳塔丽·萨洛特拒绝写“个性化”的人;阿兰·罗布—格里耶拒绝“深奥而过时的神话式人物”以及有心理学深度的人物概念;弗·伍尔夫反对写人的稳定性,只把人物看作是一种流体,她只记录“落到心灵上的各种微粒”;海伦·瑟克索斯则对人的整体性表示怀疑。(11)当代不少流派的理论又为这一论调推波助澜。结构主义理论就很难容纳人物,而信奉背离人、违反个性和心理深度概念的思想,符号学理论则把人物融化在文本的特性之中,作为封闭的文本的组成部分,人物只在其它母题里不断构成上下文。这些理论不只是摧毁了关于人物的传统概念,也摧毁了人物在小说中的中心地位,还大有倒回去“杀死”十九世纪小说中的人物的架势。
在当代中国,幼稚的现实反映论曾经一度将小说中的人物等同于现实中的人,阻碍了人们对人物文学特性的研究,也限制了小说艺术空间的开掘。新时期小说则首先是在“人学”上的回归,那些经历了生活磨难的“再生者”,那些感受着现实矛盾的“思考者”,那些时代变迁中的“半是天使、半是魔鬼”式的人物,那些普通得让你认同的“小人物”们支撑着文学的一个高峰,后来的新潮批评将这一文学的辉煌成就归结为意识形态的热点渗透是有失公允的。陈晓明就认为新时期小说中“大写的人”是一种设想、一种幻想,“成为一个时期的意识形态”(12),但他又不得不承认,1987年之后,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等人“追寻叙事策略和话语风格并没有把‘人’(自我)放置于话语中心”,“个人被话语分解为一个不断错位的角色,一个不断改变本质的身份不明的语言怪物,不管是叙述人还是被叙述人(人物)总是卷入强烈的表达欲望而异化为语言碎片”。(13)这里提出叙述表达对人物“异化”的现象,下语不谓不重,却也切中要害。
其实要检讨的还有心理学,它在拓展人的主体感性的同时,也带动文学将人降低到“本我”这一生理层面,而且心理学意味着现代科技理性对人的心灵空间的侵占。巴赫金告诉我们,陀氏早就敏感到“心理学把人的心灵物化,是轻视人,是完全不考虑心灵的自由和不可完成性”,(14)所以他在自己的“艺术形式中使人解放和摆脱物化”。(15)无疑,当代中国小说家将弗洛伊德的研究过高地奉为人类的伟大发现并加以崇拜,“意识流事变”和“向内转倾向”也被一些理论批评家抬到过高的位置,说他们是新潮小说纯感观化的始作俑者并不过分。巴赫金把“窥视”他者的物质性存在与尊重他者精神性的主体自由看成是复调小说的一个重要内核,他指出:一个人总有“超出其作为一个物质存在这一点”,“而物质存在则是可以在人的意志之外,即‘在背后’去窥视、判定和预言的”,但“个性的真正的生活只能通过对它的对话性体察来把握,它本身则会向这种体察自由地揭示自己作为回答”。(16)他指出陀氏有一个独特的见解,即“人身上的人”,包容了人的客体性和精神性两个方面,并提出“不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为那种在想象中被盖棺论定的无声客体。在一个人身上,总有某种东西只能由他自己通过自由的自我意识活动和言语活动去发现,不能凭他人想象从表面上去论断”。(17)这使我们警觉到先锋小说将人定格在感观上,定格在性欲、罪恶、灾难、暴力、绝望、死亡等虚幻性人类生存的主题上,其结果与“文革”前的小说将人定格在战斗、生产、运动等事件过程中是殊途同归,剥夺了人物独立于作者之外的精神主体的自由存在。
当代小说还有一个时髦的话题,即不将作者的意识与价值取向介入作品,意欲创造一种纯客观的小说。但这并不等于人物没有意识倾向。巴赫金介绍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纯客观的小说”观点就是要让“每一个人物都能自由地(不受作者的干预)展现并论证自己的正确性”,(18)如果剥夺了这一切,那就不是客观的“复调小说”,而是主观决断的“独白型小说”了。
巴赫金还强调,任何抽象的主题性、哲学性、伦理性、价值性的思想,都有其无限性,但在进入审美创作的范畴之前,或从审美客体中提取出来之后,它都是假定性的。它必须“进入人”,甚至还必须进入人的具体语境,才具有审美价值性。(19)时隔半个多世纪,这些理论对我们今天的小说却仍具极大的穿透力。新潮小说先后经由了对人的现实的绝望、对人的命运的绝望、对人性的绝望、对人的精神的绝望这么一个过程。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曾用“深渊时代”和“世界之夜”两个词来描述人的绝望,他认为这是人的精神沦落和毁灭的一种境遇,是一种“世界的黑暗化”,即“精神的阉割、瓦解、荒废、奴役与误解,如此,人的世界成了非精神之物的在所,人的存在也就落入“深渊”。可喜的是,一些作家已意识到文学对希望和拯救的遗忘,余华的《呼喊与细雨》、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北村的《施洗的河》等作品已不同程度上重获了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深度,人物的精神世界成了小说最为动人的部分。特别是《施洗的河》,以两大恶人刘浪和马大相继弃恶从善被拯救的故事,第一次在中国文学中讲述了宗教救赎的主题,把神和上帝带入了新潮小说的文本世界,滋生出神性救赎的话语并受到人们广为关注。一些作家从海德格尔描述的天、地、人、神共在的四重结构中似乎一下子醒悟了中国文学中神的缺席,因而大谈终极关怀与神性救赎。然而,文学对人的真正终极关怀应首先确认人的生存根基、人的客体与主体的同在、理性与感性的共生、人的整体性存在,而不应以神性乌托邦掩盖人的终极实在,否则只会将人推向更深的绝望之境。不在“人”的问题上回归,当代小说的艺术空间就是一个虚空的蝉壳,主题话语也罢脱不了形而上话语形态,文学也绝对成不了现代人寻找“家园”的精神方舟。
三、小说中的“对话”观
如果说巴赫金有关“主人公”的理论足以启迪我们建立一门“小说人物学”的话,那么他的“复调”理论还促使我们感到建立“小说对话学”的必要。巴赫金指出:“所有的解说、所有的看法都被写成对话的一部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里没有一句最后的决定性的话”,“复调小说从里到外整个是对话性的。在小说结构的所有成分之间,都存在对话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是以对位方式相互对立的。要知道,对话关系较之表现在布局上的对白关系,是远为广泛的现象,这几乎是渗透于整个人类言语和人类生活一切关系、一切表现,总之是渗透于一切有意义的事物的普遍现象。”(20) “对话”问题被提升到小说理论中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在这一观点上的论述颇为周到。
(1)小说的“对话性”不同于传统概念的人物对话。巴赫金将小说中一般性的人物语言称之为表现性格和形象典型性的“客体性语言”,它只是表现人物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的立场”或为演绎小说情节而服务。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这种“对话”性语言的功能体现得极为充分。巴赫金赞赏陀氏“断然否定这种关系对理解和解释人的生活和行为有什么意义”,(21)这在“人学”上有深刻的一面,但在艺术上是片面的,因为对话与人物主体、性格、形象的相互映证在小说中是不可避免的。
(2)每个人物都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是小说对话性的前提。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让自己的主人公承受一种独特的精神折磨,借以迫使主人公把他接近极限的自我意识的意见说出来。这种精神折磨可以把一切物质的和客体性的东西,一切固定不变的东西,一切外在和中立的东西,都溶解于在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陈述领域进行的对人的描绘中”。(22)而这种“自我意识”的一个体现是对自己的“最后发言权”属于自己,这个最后发言权一旦属于叙述者或他者,这个人物就成为客体性形象了。陀氏“把作者和叙述者连同他们的一切观点和他们对主人公的一切描写、刻画、说明,都转移到主人公自己的视野,并从而把主人公的整个既定现实都变成了主人公自我意识的材料。”(23)巴赫金将此称为一场“小规模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确,没有发达的“自我意识”,就不可能有小说布局上人物之间外在的“大型对话”,也不可能有人物心灵内部的“微型对话”。鲁迅在评介陀氏的小说《穷人》时也曾提出:“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样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24)这恰也道中“深的灵魂”自我意识的“对话性”意义。
然而,“自我意识”也只有体现在“对话性”原则中才具有巨大的价值,它应该在人类意识差异性存在的整体中保留才产生意义。巴赫金因此批评“表现主义者准确地抓住了自我意识在主人公塑造上的主导地位,但他们不会迫使这种自我意识自发地,具有艺术说服力地展现出来”。(25) “自我意识”应该是自我确证,自我省思和与他者对话的对象这三个层面上的共同存在。本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也非常看重“自我意识”,但多半只抓住了作者自我意识的一维,而忽视了他者“自我意识”的一维,这种作者立场的“唯我”倾向因缺乏对话性而导致小说整个文本的“独白”化,这实际上压缩了小说的艺术审美空间。如果说尼采式的非理性“自我意识”多少还带有自我确认的建构性的话,那么雅克·德里达式的非理性“自我意识”则是彻底解构的,最后人类自我意识本身也出现空缺。这种理论对当代中国小说破坏性影响巨大,先锋小说大多只展示人的视野与感觉,世界不归属于人的主体,人也不属于人自己,“自我意识”的熔炉被捣毁,人被植物化或动物化。文学走向理性哲学相反的另一极端,也就成了“异化”人的罪恶杀手。
(3)“对话”与“言说”权的问题。格罗斯曼在评论陀氏小说时讲到,“在交谈和争论中,各种不同的观点可以轮番占据主导地位,反映各种对立信仰的种种细微差异,所以交谈和争论的形式特别适合表现这种永远处于形成过程、永远不会僵化的哲学”。(26)巴赫金在述及这一见解时只提出了意识互不相融的重要性,其实人物的“言说权”也是“对话性”的一个重要问题。没有每一个人物对他人,对世界的言说权,小说的“对话性”就只能限于意识内部并导致消亡的可能。
当今有一种走俏的观点,认为人的言说是对他人意志的毁止,言说会助长“权力”的生长,人的“言说行为,都是权力意志的体现”,“言说中的权力因素不断渗透、强化”。(27)不少人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第一章)和庄子的“不言则齐”(《庄子·寓言篇》)那里找来根据,认为人一说话,就把主观的东西附加到自然万事万物并使“道”走样了。老庄的观点在先锋理论中似乎变得特别吃香,庄子的“道”的不可言说的恍惚性与存在主义的“存在”的无可把捉的虚无性确有惊人的相通之处,存在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是: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灾难,而自我的存在又无疑是他人的灾难;来自老庄的“混沌”学说也似乎有这么一个相近的命题:人的言说本身就是一种灾难,自我的言说对他人也是一种灾难。再加上罗兰·巴特“零度写作”理论的呼应,小说中作者的“无言”乃至人物的“无言”几成潮流。其实,庄子一方面认为“道”无法被言说,但另一方面始终在论“道”,“道”并非不可论,而只是人们难以穷尽它。真正的“无言”只存在于人类尚未走出远古未开化的混沌之中,庄子自己也只能用言去表达“无言”,而庄子式的“边缘解构话语”也只有在与孔子式的“中心权力话语”的“对话性”中显现真义。
(4)对话的“平等”原则。我在上文第一个大问题的末尾已提到陀氏小说中人物的平等性。小说中的对话机制也必须遵循这么一个平等的原则。人的“自我意识”必须有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能用来决定高低之分,巴赫金指出它们都有各自的未完成性,因而只能是平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各种极其不可相容的材料成分,是分属若干世界和若干平等的意识的,它们不是呈现在一个视野上,而是呈现在若干完整和平等的视野上”。(28)在极“左”年代,我们的小说很难享受到这种主体意识的平等,但今天的小说中,那些可怜的主人公却被作者剥夺了这种“平等”。许多人热衷于在语言大众化、题材大众化、主题民众化、人物普通化上去寻找平民文学的道路,其实真正的“平民”性在于小说中能否确立这种“平等”意识。对话必然是建立在对应、对位、对等与对立等概念之上才成为可能。所以巴赫金一再强调每个人物都应是“在场者”,而不是“缺席者”,都是相对于叙述者而平等存在的“你”,而不是“他”。复调中的对话也因这种“平等”而完成了小说叙事上由自我中心状态向非自我中心状态的转变。
除以上几个问题之外,巴赫金还指出复调与“戏剧性独白”的区别,戏剧性质的对话不能算是复调的对话。八十年代前期也出现过一些对话体小说的尝试,如蒋子龙的短篇《关于鞋后根的问题》、沙叶新的短篇《无主题的对话》、林斤澜的短篇《纪录》、刘心武的短篇《寻人》、祖慰的中篇《人鸦对话录》,但未成大器,没有在人的整体复杂性与复调的恢宏结构上作出开掘,而流于对话的戏剧形式。相反。一些当代探索剧如《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野人》、《潘金莲》等却具有了一些对话的复调意味。至于先锋小说,也有人指出其对话意味,“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以其激越的历史冲动与话语表达的欲望,显示了开放性的对话语境”,“莫言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叙事方式,把叙述人首次推向历史对话情境”。(29)以此类推,先锋小说中的叙述人——我,无不是“对话”的角色,通过个人自语的叙述方式“与历史直接对话”。然而这是一场不公正的对话,是一方独占话题与语境的对话,由于“历史”在叙述中是个缄默不语的虚构,加上作品中人物精神独立性与言说性的空缺,所以先锋的文本只是对话的发言稿,它没有对话的对象,也没有回音,以至听众也一哄而散,“先锋人”因此而成为空旷舞台上孤独的“独白者”。早在欧洲中世纪繁盛期到文艺复兴后期最重要的一所大学——巴丢阿大学中,一个教授在讲课时总有另一个持相反观点的教授在场,大家从他们不同观点的争论与对话中往往得出“第三种”更高尚博大的相对真理。由此可见对话不同于独白,其增殖性是巨大的。八十年代文学批评一句“深刻的片面”的呐喊至今仍使人感到余音不绝,但五个世纪前西方哲人莱奥纳多·达·芬奇的观点更值得我们今天深思:“每一部分都希望在它的整体之中,因为在整体中部分可以得到更好的保存,每一部分都倾向于与整体相统一,从而逃避其不完善性。”(30)而“对话”也是我们的小说躲开不完善性的通途之一。
四、当代“复调小说”及有关问题
新时期的中国小说曾经在“复调”的结构形式上有过一些探索和开拓,又因只限于结构形式上的价值理解和追求,所以不免留下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也有些有益尝试因其它更突出问题的掩盖,其审美艺术价值又不被人们看重。如戴厚英的《人啊!人》,作品中的人物轮流担任主角,一个叙述者“我”变成了众多叙述者“我”,这种第一人称多元转换的复调意味克服了作品囿于单一视角的局限,但作品强烈的人道主义主题遮盖了这种探索的艺术可能性。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交织着写实性描绘与象征性抒写,王蒙的《杂色》交叉着曹千里与杂色马的情绪流,都具有了复合的形态,但还没有上升到复调的档次。八十年代中期的三篇小说则向复调形态跨出了大步,它们是王安忆的《小鲍庄》、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区分细腻一点则可将其分别称为故事的复调小说、叙述的复调小说、情绪的复调小说。
《小鲍庄》被人所看重主要基于文化寻根的主题,其实它的优势在于“故事”与“复调”。捞渣与鲍五爷的故事隐喻人的仁善本性,拾来与寡妇二婶的故事隐喻着人的生命本能,鲍仁文的故事隐喻着人追求精神的艰难……这些故事交织在一起引人入胜。巴赫金其实颇看重复调小说中事件的因素,并将其区别为“认识事件”、“道德事件”和“审美事件”,还进而提出小说中的叙述者可取审美观察、审美体验、审美评判、审美包容等诸种视角。(31)当代小说评论习惯于将新时期前期小说概括为“讲什么故事”、后期小说概括为“怎样讲故事”,把故事放在一个极被动与低层的位置。其实小说不应放弃和摆脱故事,故事有它的自足性,人的全部丰富性往往通过故事得以体现。相比《冈底斯的诱惑》和《你别无选择》,《小鲍庄》在审美可读性上占绝对优势,而它的主题旨意决不亚于这两个作品。既然故事性更符合审美接受的感性需求,那么建立“小说故事学”也就有巨大的价值。但《小鲍庄》忽略了人物的主体意识的存在与对话,我们感受不到人对自身的理解、对生命的体悟、对历史的叩问、对意义的追思。故事因而有下降为“状态”的趋势。
《冈底斯的诱惑》则是纯技巧上的“复调”,是结构多元的复调小说。由于作者不断变换叙述圈套,冈底斯高原的图画得到多样、多层次的展开和复合,人的、自然的;静的、动的;远近有致,或清晰或朦胧,隐约有如“交响诗”的音响留在人们印象中。但叙述的随意切换使小说外观形式破缺无序,难以统一。这篇小说的魔幻性和叙事学价值被人过于看重,所以它在复调形态上的不完美并没有多少人去指正。
《你别无选择》中,那群音乐学院的学生流露着浮躁不安的情绪,他们刻意追求的既不是什么非凡的人格品质,也不是什么伟大的理想,而是一种无目的性的、与众不同的自我意识和个性。这些各不相同的自我意识与个性化情绪构成小说的复调形态,同时也使作品中的人物显得抽象化、意念化,而缺乏应有的审美感观性。巴赫金曾反对小说“通过抽象主题的选择达到”主人公的内在的深刻的自由与独立。这篇小说因黑色幽默的语调和解构的现代派倾向而过于受到人们的青睐。85年也被人们命名为小说技巧“演习年”,不少小说家都意图通过技巧带给人们新鲜的艺术感受,却又象猴子摘桃,边摘边丢,难怪有人慨叹:“文学被创新这条疯狗追得喘不过气来”。
综合以上创作中的倾向与问题,足见我们不少小说家还没有真正把握人的主客体关系,在创作实践与研究中探索人的自然感性、社会感性、理性感性及其相互关系,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巴赫金的研究已提供给我们不少精微的体察,他的“复调小说”理论,恰如昆德拉对复调小说的理解那样,“与其说是技巧性的,不如说更富于诗意”。(32)它提供给我们把握世界方式以一种新的可能,也给我们指明一条拓展小说审美观照的版图与艺术空间的广阔思路。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参见〔美〕勒纳·韦勒克《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史概述》一文。《波佩的面纱——日内瓦学派文论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②、(30)〔德〕古茨塔夫·勒纳·豪克《绝望与信心》,第214页,第2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⑧〔德〕沃·卡托克《德语作家眼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编入《波佩的面纱》一书。
⑨、(14)、(15)、(16)、(17)、(18)、(19)、(20)、(21)、(22)、(23)、(25)、(26)、(28)、(31)《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第75页、第78页、第73页、第72页、第83页、第339—340页、第51—52页、第52页、第66页、第59页、第66页、第17页、第361页与第321页。
⑩罗兰·巴特《S/Z》第95页,1974年英文版。
(11)以上名人主张见[以]施洛米丝·雷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第35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2)、(13)、(29)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第222页、第279—281页。
(24)《集外集·〈穷人〉小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7)张闳《听与说:汉语言说的策略》一文,载《今日先锋》(第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3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7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标签:小说论文; 巴赫金论文; 艺术论文; 复调论文; 文学论文; 当代小说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化论文; 你别无选择论文; 读书论文; 小鲍庄论文;
